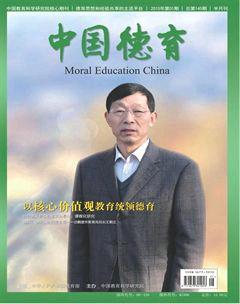治道顺人性而为:韩非的思考
蒋重跃
人性与治道具有内在的联系,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对此进行过深入思考。例如,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即“新旧约全书”)持原罪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救,由此形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成为西方政治和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渊源。西方经济理论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的,这种利己主义与社会利益又是一致的,满足人类利己本性的最好途径就是实现经济自由。这就是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正是根据这种假设,才发展出成体系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古代中国的儒家也有自己的主张:孟子持性善说,认为人人先天具有恻隐、是非、羞恶、辞让之心,所以主张通过教育,发扬人的这些良知良能,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荀子则持性恶说,认为人人先天具有谋求生存和利益的本性,在此基础上,既可成群成善,也可为邪为恶,所以需要教化,以使人改恶从善。其实,对于这个话题,古代中国的杰出思想家韩非也有着独特的贡献。只是在后来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儒者一家独大,士大夫以谈论申韩为耻,结果韩非的相关思想一直未受到重视。今天,认真研究韩非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的文化和道德建设,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反对传统礼治,主张法、术、势
相结合的国家治理观
韩非是战国后期的著名思想家。他出身于韩国王室,属于高级贵族。可是阅读他的著作,我们却感受到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处于边缘地位的,而且还经常受到压制和排挤。从《韩非子》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韩非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关注现实政治,关注韩国命运,关注历史潮流的发展和走向。史家记载,他经常上书韩王,揭露韩国的弊政,建议改革,但却没有引起韩王的重视,不过也并未因此而获罪。史家说他口吃,不善言谈,但却精于写作。他的作品流传很广,邻国的秦王政就是因为读了他的《孤愤》和《五蠹》两篇文章,才大发感慨,非要与他交朋友不可的。
那么,韩非提出了怎样的主张,竟然引起邻国君主如此的共鸣呢?
其实很简单。韩非对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和道德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用“五蠹”(五种蠹虫)来比喻儒家所赞扬的五种人,要求坚决铲除。他沿着法家的路线,把前辈关于治道的主张和做法加以综合,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就是用法、术、势相结合的办法来治理国家。
什么是法?韩非有一个定义:“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臣无法则乱于下。”(《韩非子·定法》)又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莫如显……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韩非子·难三》)就是说,法是赏罚制度,它要形成文字,记录在官府,向百姓公布;国境之内,不论贵贱,人人都要知道;守法的有赏,违法的有罚;没有法,臣民就会乱。法家前辈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用什伍连坐之法,把百姓管得服服帖帖,个个拼尽全力替国家种地、打仗,结果秦国国富兵强。
什么是“术”?韩非也有定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说的是君主根据臣下的能力委以相应的官职,再按官位的职责来考察他们的行政绩效。合乎标准的,赏;不合标准的,罚。可见,术就是管理臣下的办法。按照韩非的说法,术包含文官任用法、行政管理法、官吏考绩法等制度化内容,也包含君主暗中控制臣下的非正规做法,如预先侦查、突然袭击、无中生有、试探真伪、颠倒黑白、蒙骗欺诈等,无所不用其极。据说,韩非的术治前辈申不害就曾使用这些办法帮助韩昭侯治理臣下,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什么是“势”?势就是权势,就是君主的权位。势治就是要求君主以势压人,运用权力实行统治。势治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由稷下学者赵国人慎到倡导。韩非的贡献是告诉人主要用法律来巩固权力,这样,即使自己不太优秀,也不至于丢掉权柄。
韩非的理论贡献是把三者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单纯的法治,尽管可以驱使百姓为国家尽力耕种,拼命杀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却无法管住官员,有时反倒让官员利用而得到了贪赃枉法的机会。而术恰恰是管理官员的。不过,单纯用术,官员是管住了,可是法治若不统一,国家仍然难免要乱。法治不统一的根源在于君主不能有效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君主手中若没有权力,术治与法治都无法实施。所以,在韩非看来,法、术、势三者必须结合着使用。
法、术、势相结合而实施治理,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大家知道,春秋时期被认为是礼坏乐崩,人心不古,但那时兴起的儒家还只是主张用礼乐来加强社会管理,用仁爱来教育和感化民众,法律只是辅助性的手段。战国时期,变法成为时代主题,法治——制定和实施成文法,成为时代潮流。但战国前期和中期,儒家的大师孟子和荀子仍然相信仁爱和礼乐可以担负起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到了战国末年,法家大行其道。在韩非看来,儒家的礼乐和仁爱根本无法治理社会,甚至单纯的法治也无法完成社会治理的工作,民众要用法来治理,官员则要用术来管控,君主则更要关心自己手中的权力势位,一不小心,就可能丢掉。所有这些都说明,这个时候,社会矛盾、政治矛盾已经非常尖锐。韩非引用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黄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战”,来说明当时矛盾尖锐的程度。
以君主与臣下百姓的矛盾为代表的社会矛盾,竟然到了“一日百战”的境地!那么,以有效的办法来实施治理,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了。而采用法、术、势相结合的办法,实施高压统治,正是这样一种“合理”选择。在韩非看来,采用高压的手段来治理社会,实在是不得已——社会已经堕落到了“一日百战”的程度,人性已经堕落到了恶者大行其道的境地,无法靠道德说教来扭转,无法靠同情和感化来改善。
二、否定宗法道德,
坚持趋利避害的人性论
西周时期,贵族中实行宗法制度,宗法道德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到处都弥漫着宗族伦理精神。周人相信,“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到了春秋时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仍然是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基本信条。在这种伦理道德的笼罩下,对人性的基本估计是乐观的。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尽管没有说明人性的善恶,但基本倾向是善的。
战国时期,人性的状况越来越下滑。面对这种形势,儒家仍然坚守着传统宗法道德的基本精神,稍加改良,主张用仁爱和礼乐维系人与人的基本关系。不过,在道家和法家看来,宗法已经打破,传统宗法道德成为虚伪矫情的累赘,更可怕的是,人性已经沦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再用宗法道德来维系人心,就仿佛刻舟求剑,不但于事无补,还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在这派观点中,韩非的见解最为偏激,他对社会现实做了最彻底的揭露,对传统宗法道德本身做了最猛烈的批判。
在传统观念中,德是宗法制度的精神根源。人们相信,德出于宗族血缘相爱的本性,也是上天的属性。可韩非却给予彻底的否定。他指出: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既不是为了马,也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奔驰和战争的需要。医者用嘴巴吮吸病人的伤口,含吐病人的脓血,本非骨肉之亲,只是利益驱动才这样做的。造马车的舆人,就盼着有更多的人富贵;做棺材的匠人,就盼着有更多的人夭死。这不是舆人仁爱,也不是匠人狠毒。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出去;人不夭死,棺材也卖不出去,不是本性憎恨人类,而是利益就在人的夭死啊。
传统宗法道德建立在宗族之爱的基础上。人们相信,社会上有爱,是因为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有爱。对此,韩非用事实给予断然的否定:小的时候,父母贫穷,生活艰苦,孩子长大后就产生了怨恨;孩子长大成人,供养父母不足,父母就会发怒而责骂。孩子和父母本来是至亲啊,可却有抱怨,有责骂,为什么呢?是因为相信亲人之间应该有爱,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啊。你看那些卖苦力替人耕种的,主人舍得花钱,给他们吃好的,为他们准备好工钱,这不是因为爱这些苦力,而是因为主人知道,只有这样,苦力们才会深耕细耘。苦力们下力耕耘,精心侍弄田垄菜畦,也不是因为爱主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主人家的肉汤才做得精美,工钱才付得痛快。可见,为了功利目的,陌生人可以有父子般的恩情啊。所以,人际关系根本不是由血缘决定的,若相互有利,与越人也容易相和;若相互为害,就是父子,也会分离而且怨恨啊。
按照周代传统,在宗法道德上,贵族应该更高尚一些吧。可在韩非看来绝非如此。不信,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不论大国小国,那些后妃、夫人、王储们,就有希望君主早死的。怎么知道的呢?夫妻啊,本来没有骨肉之亲,有爱就亲近,无爱就疏远。谚语不是说了嘛:“其母好者其子抱。”反过来道理也是一样的:“其母恶者其子释。”男子五十岁了,好色之心未尝减弱;可妇女到了三十岁,容貌就衰老了。衰美的妇人侍奉好色的丈夫,到死了也不会得到亲近的。这种情况下,儿子自然就会担心自己无法继承王位了,后妃和夫人就会希望夫君早点死亡啊。而母亲当了太后,儿子当了君主,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生活享乐丝毫也不少于先君在的时候,这就是毒药和绳索之所以常用的原因啊。《桃左春秋》不是说过嘛:“君主得病死的,都到不了一半啊!”
按照韩非的上述说法,在当时的人群中已经无法找到宗法伦理的根据了。那么,像尧、舜、禹这些周代文化和儒家文化盛赞的古代圣人又是怎样的呢?韩非同样加以断然的否定:尧当天下的王,屋顶的茅草不知修剪,椽子也不会雕琢,吃的是粗粝的粮食,喝的是野菜的羹汤,冬天只穿兽皮,夏天也不过是粗麻,看门人的生活,也比这强啊。大禹做天下的王,亲自拿着耒臿走在民众的前面,腿肚子上不长肉,小腿上不生汗毛(上古时裤子还未发明,人们可以从小腿来看劳作的状况),奴隶的劳苦也不至于此啊。这样看来,古代圣人让出天子之位,不过是逃离看门人的生活条件和奴隶的辛苦啊,所以,古代传天下不足以表扬啊。如今的县令,一旦身死,子孙世代乘车,所以为人看重。两相比较,人们很轻易辞去古代的天子之位,却很难辞去如今的县令之官,这都是由于利益的薄厚决定的啊。饥馑之年的春天,再幼小的弟弟也不让食物给他吃;丰收之年的秋天,再疏远的过客也要请他吃饭。这并非远骨肉而爱过客啊,而是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所以,古代看轻财物,并非仁爱,而是财物丰盈,如今争夺,并非卑鄙,而是财物短缺;轻易地辞去天子之位,并非高尚,而是权势薄啊,寸土必争,并非卑下,而是权力重啊。所以王者政治,惩罚轻并非出于慈爱,惩罚重并非出于暴戾,而是与世风相称而行啊。
行文至此,可以断定,在韩非眼里,传统宗法道德一点存在的余地也没有了。
三、法、术、势结合为用,以人性为基
韩非对传统宗法道德的批判,为他的法治主张,为法、术、势相结合而治理的观点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这里的“人情”是“人性”的通俗表达。人情有好恶,所以相应地就要用赏罚来加以管理,因为赏是针对“喜好”的,罚是针对“厌恶”的。“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韩非子·难一》)这条材料恰恰说明赏用来激励,罚用来禁止。两者都是根据民之所“欲”所“恶”来设定的。
人性与治道的这种内在联系,与法、术、势结合为用的思想是一致的。按照韩非的定义,法是“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可见法的核心就是赏罚。术呢?术要“操杀生之柄”,“杀”是罚,“生”是赏,可见赏罚也是术的内容。势就是权势,权势的作用就是可以合法地实施赏罚。赏罚的治道到了韩非那里,就是法、术、势相结合的国家治理。这就是韩非对治道与人性内在联系的说明。这个理解是具有理论性的。
人性与治道关系的这种理解还被韩非具体化了、政策化了。他说:“掌好恶以御民力。”(《韩非子·制分》)用民力来做什么呢?“(人情)莫不好富贵而恶贫贱……夫耕者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韩非子·五蠹》)耕战政策是法家的核心政治主张,韩非从人情好恶的意义上给予说明,再一次阐述了两者的内在联系。他说:“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一》)这又从人情“所好”的意义上说明臣下服从君上的理由,就像主人驯养猎鹰一样,让它仰赖主人的喂养才可生活。韩非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术的合理性。总之,法和术都是政策在人情好恶——人性基础上的具体实施。
四、启示与反思
其一,韩非发现了什么。韩非主张法、术、势结合为用,一方面是因为他认识到,当时各个阶层的人性状况已经到了无法用传统宗法道德来改善的地步了,所以需要采用宗法道德之外的办法来实施治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识到,法、术、势所共同拥有的赏罚功能与人类所拥有的趋利(“好”“所欲”)避害(“恶”“所恶”)的本性相吻合,赏罚政策恰恰以人性好恶为根据。也就是说,韩非发现,政治主张一定有着相应的人性依据。
其二,韩非未能发现什么。韩非在纷繁复杂的经验现实中敏锐地抓住了治道和人性之间的同一性,思想是犀利的。不过,他虽然揭露了一些社会现象,对宗法道德提出了严正挑战,但这显然不是当时社会的全部现实,他的思想的触角还未深入到治道和人性之间的矛盾层面。这样看来,他的思想深度是有限的。他对当时道德状况的估计过于悲观,对传统宗法道德中有价值的因素视而不见,都说明他的思想具有片面、偏执和狭隘的不良倾向。
对于我们来说,以上两点既是启发,也需要反思。
责任编辑/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