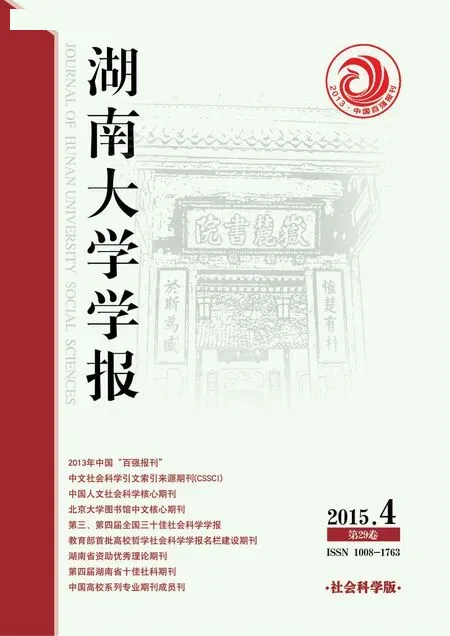论熊赐履《四书》学诠释的经筵特征*
王胜军
(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论熊赐履《四书》学诠释的经筵特征*
王胜军
(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熊赐履是清初理学名臣,其《四书》学诠释具有鲜明的经筵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宗旨上,尊崇程朱、辨正道统;在风格上,直说大义、明白易晓;在致用上,由经及政、以道正君。熊赐履《四书》学是《四书》学在现实政治中的典型性展开,代表了《四书》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
熊赐履;四书学;诠释;理学
《四书》学是理学的经学形态,[1](P2)两宋以降,理学家以《四书》为文本依据,通过对《四书》的精心阐释,开启其得君行道、治平天下之路。然而,揆诸历史,得君实难,即便学问操行如朱子,立朝亦不过四十余日,晚年且有“伪学”之目,之后,阳明学派则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2](P188)只是在清初,才出现理学家跻身庙堂、“得为君王傅保”的现象。[3](P23)其中,作为理学名臣的熊赐履最具代表性。熊赐履(1635~1709),字青岳,又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九年出任翰林院掌院学士,长期知经筵,累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赐履的理学渊源及“得君行道”的核心文本依据是《四书》,其对《四书》的诠释集中在作为经筵讲义的《日讲四书解义》*该书现列总裁官为库勒纳、叶方蔼,但实际本应为熊赐履所作,或至少是其主持完成的。康熙曾明确讲过说:“前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刊刻之时朕以为熊赐履所作应列其名;原任大学士索额图、杜立德、冯溥以熊赐履名教中罪人,不应列名。”(《康熙起居注》(第2册),1984年,第1901页)高翔《熊赐履述论》(《清史论丛》2006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第122-123页)对其原因有说明。另外,熊赐履《澡修堂集》收录数篇,与《解义》相同或基本相同,可为佐证。视《日讲四书解义》为熊赐履《四书》学思想之体现,是不应有疑义的。,其他论断散见于《闲道录》、《下学堂札记》、《经义斋集》、《澡修堂集》等论著中。熊赐履将《四书》学推向经筵、庙堂,是康熙帝理学的发蒙者[4](P639),其诠释彰显出极为鲜明的经筵特征,在《四书》学史上独树一帜,绝非现代学者所谓的“套语常谈”、“毫无新义”。
一 宗旨:尊崇朱学、辨正道统
熊赐履《四书》学的经筵性主要表现在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以程朱理学折中诸家学说,为学术发展确立秩序,为清王朝的政治运行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在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动乱之后,作为异族建立的新王朝,说服疆域内的民众对其政权进行认同,进而维护帝国的统一、稳定、繁荣,是极其必要和紧迫的。而面对这个新王朝,汉文化又怎么应对呢?熊赐履以《四书》为文本依据,独尊程朱,批判王学、佛老,为新政权构建了一套汉文化意识形态。于是,程朱理学便借《四书》走向了经筵和庙堂。
熊赐履《四书》学具有鲜明的尊朱辟王色彩,有学者甚至认为清初朱陆之争便始自熊赐履。[3](P16)熊赐履称其自幼便“读洛、闽书与前代薛、胡诸儒语录,已心知笃好之,既而得象山、姚江辈所著,意殊不然”[5](P266)。《学统》是其尊朱辟王的代表作,该书以正统、附统、翼统、杂统及异端分判历史人物,将陆九渊、王阳明仅列入到杂统,并将王学诠释为告子之学、禅学,加以批判。
心体“无善无恶”说是阳明晚年的重要思想,因其表述与孟子“性本善”有很大差别,故而倍受责难。阳明诠释《孟子》,认为告子论“性无善无恶”也无大差,“性原是如此”,因为“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6](P61),而告子是兼气质讲,只是执定看了而已。清初很多学者都认为告子“性无善无恶”说与佛学有关,因为佛学也讲“无善无恶”,从这个角度,阳明学则是两者的进一步发展,熊赐履亦然,在其看来:“无善无恶云者,告子之见,佛老之祖也”[7](P39),“象山之所谓心,分明是告子之心;阳明之所谓性,分明是告子之性”[7](P36)。熊赐履由此批判阳明,并肯定朱子对孟子“性本善”说的诠释:
性善之说始于孔子,著于孟子,发挥于洛闽诸子;无善之说昉于告子,盛于姚江,遏止于东林诸子。[7](P30)
朱熹言性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性本无恶,故反之而后为恶,诠孟子之义极明,邪说不攻自破矣……所谓性者,即此浑然同具之理……告子不知理一分殊之义,而误以气为性,所以其说愈变而愈谬也。[8](P552-553)
在熊赐履看来,自阳明学大行之后,“人人儒也,而实人人释也,名为三教,实唯有佛尔”[9](P523)。因此,辟阳明“无善无恶”说就成了紧迫的任务,熊赐履《学统》大量援引顾宪成与管东溟的论辨及顾氏《论学》中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顾宪成指出工夫与本体应该一致,本体无善无恶,工夫又何以为善去恶?于是将阳明打到告子、佛氏一派。
在批判王学的同时,熊赐履不遗余力地推崇朱子,说“朱子善学孔子”,“朱子合颜、曾、思、孟、周、程、张、邵而为一身”,“朱子,宋之孔子也”[10](P61),认为接续孔、孟之学的是朱子,并用《四书》来贯穿孔子、朱子道统谱系:
《论语》“吾十有五”章是孔子学谱,《大学》“补释格物”章是朱子学谱;《大学》“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目是孔子学规,《中庸》“择善、固执”两纲、“学、问、思、辨、行”五目是朱子学规。[10](P62)
熊赐履通过《论语》、《大学》、《中庸》肯定了朱子作为儒学正传的地位,因为朱子学是建立在《四书》经典上的,是阐发《四书》基本精神的。虽然朱子与孔子有不同,但是基本精神却是一脉相承,如熊赐履讲的“有孔子之六经,朱子之解经,天地古今之理备矣”[10](P56),对朱子诠释学进行了高度评价。
熊赐履旗帜鲜明地反对阳明的《大学》古本说,从《四书》角度出发,认为“阳明表章《大学》古本,转解转支,以予观之,莫意见于象山,莫支离于阳明。”[10](P63)阳明、程朱对《大学》诠释是王学与程朱理学学术分野的主要依据。《大学》原为《礼记》中一篇,该版本称为“《大学》古本”,它与程朱改本《大学》不同。程朱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为经,其余为传),认为《大学》有脱简,即传文中缺少对经文“格物致知”的解释,故而作“格物致知补传”;又据传中文字,认为经中“亲民”应为“新民”,并由此将原文次序作了调整,从而赋予《大学》以程朱式的解读。阳明认为《大学》古本“本无脱误”,用心学对《大学》进行重新诠释。阳明《大学》古本说对程朱《大学》诠释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自此之后,很多学者都倒向了《大学》古本说,甚至反对阳明的程朱一派学者也在所有之。
熊赐履支持程朱《大学》的诠释文本,强调“新民”说。王阳明主张“亲民”说,批评朱子,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6](P2)有学者认为“新民”重于“教民”,而“亲民”重心在“养民”[11](P336-337),是有道理的。《日讲四书解义》从“新民”的角度诠释说:“故自明其德,更当推以及人,鼓舞振作,使天下之民凡具是德者,咸有以去其旧染之污,而臻于大同之治,方为有用之学也,所以大人之学在新民。”强调“新民”的对象为君主,《大学》是“为古帝王立学垂教之法”,对于帝王,“己之明德既明,而后可以新民之德”[8](P9-10)。由此来看,熊赐履是继续程朱理学“格君心以行道”的《大学》诠释路线的。
在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上,熊赐履也采取朱子的诠释。朱子、阳明对《大学》诠释不同,导致了对“格物致知”理解的差异。朱子认为“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阳明则以“正”训“格”,以“心”训“物”,认为“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6](P5)。朱子认为“穷理致知在先,而后才能诚其意”,阳明则将“格物当作诚意的实现方式”[12](P143-144)。因此,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认为“格物”不是外在的“穷理”,只是内在的“诚意”,试图排除朱子学向外求知穷理的过程,而用“诚意”作统率直接进入“践履”。在《学统》中,熊赐履大篇幅引用罗钦顺、陈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的文字对阳明进行批判,不少都涉及到对“格物”的理解,主要是强调程朱外在的致知穷理,反对阳明讲“诚意”,比如“《大学》之先格物致知也,以其求端用力言之,然岂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谓哉?”[9](P521)熊赐履在《下学堂札记》中也批评说:“今人不肯耐烦去穷理,硬将‘格物’二字解向别处去,真是强圣贤从自己,认便利作究竟,到头有甚结果?”[10](P70)
朱子解“格物致知”包含有程朱理学对“知”、“行”的特殊理解,通过外在致知穷理,即格阳明反对的事事物物皆有的“定理”,进而指导具体的道德行为,程颐讲“进学在致知”,意即在此。因此,朱子虽然讲过“知行相须”,但在为学次第上“知”是第一位的,即“知先行后”。阳明则认为朱子割裂了知、行之间的关系,故而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意图将“知”消融在行中。康熙十二年(1673年)八月,在一次论及治道的召对中,当康熙帝表示“合理的决行,不合理的决不行”时,熊赐履当即便向康熙帝指出程朱理学致知、穷理的重要意义,认为:
合理的决行,不合理的决不行,虽二帝三王不过如是。然何以为合理,何以为不合理,必须讲究烂熟,方能泛应曲当,不然恐未免毫厘千里之谬也。[13](P115-116)
在熊赐履看来,王道政治首先在于格物致知,在于明白道理,这是措诸实用的必要前提。康熙帝似乎有些不认同,就说“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不行,徒空谈耳”,熊赐履还是坚持己见,认为“非知之艰,行之唯艰。然行之不力,正由知之不真也。”[13](P116)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致知的过程,亦即穷理、求学的过程,正如熊赐履说的“周公朝读百篇,孔子韦编三绝,试看大圣人是何等样读书!”[10](P70)该年十一月,某次召对中,康熙帝又明确就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求教于熊赐履,问其“知行合一之说何如”,熊赐履回答说:“宋儒朱熹云:论轻重行为重,论先后知为先。此言极为稔实。知行合一乃后儒穿凿之论,毕竟有病。”[13](P136)康熙帝随即首肯。这说明,熊赐履对“格物致知”的程朱式诠释最终赢得了皇帝的认同。
二 风格:直说大义、明白易晓
一般而言,《四书》学著作会以训诂为基础,阐发新见,知识性、学术性较强。熊赐履《四书》学却不以训诂为特征,它往往直说大义,以“明白易晓”为准则。熊赐履认为诠释简明便是论学之道,如其所谓:“世人论学,只是要人难晓;履只要人易晓……易晓的便是当晓的。”[10](P57)“晦翁谓浅近之言,皆有至理寓焉。若予之为说,大都不过浅近而已。”[5](P268)在其看来,儒学原本并不追求诠释层面的艰深,相反,熊赐履还批评说:“后人好高耽异,炫巧凿空,圣经贤传,直等诸老生常谈、拘儒陈说……此所以畔道日远,而害理滋甚也。”[7](P40)鲜明地表现出其诠释方法和风格。
熊赐履《四书》学的对象是皇帝,其主要任务是给皇帝提供一种修己安人、治国理政之道,而不仅仅是与《四书》相关的知识,这就对诠释者“明白易晓”地“直说大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讲四书解义》这种诠释《四书》的“解义体”,最能体现熊赐履的《四书》学风格。康熙帝对该书很是称许,认为较张居正《四书集注阐微直解》“更为切实”[13](P119)。《直解》也是经筵讲疏,但与《解义》相比较,它更侧重说明、解释,贯通性不够;又以朱注《四书》即《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阐释过于复杂。
作为经筵日讲的主要推动者,熊赐履构想编纂一部针对皇帝的讲疏,尤其是如何编纂一部日讲讲疏,因为日讲较形式意义的经筵对皇帝的教育更为切实。在《条陈日讲切实事宜疏》中,熊赐履提出了自己的编纂构想,在其看来:
日讲直解与经筵讲章不同,要在直说大义,明白易晓,不必杜撰词藻,支蔓训诂,以溷渎宸聪,荧惑圣听,圣心偶有疑义,赐之资问,亦惟诠解明显,对答简当,务期发挥道理,畅达事机而止,繁文阔论,一概不用。[5](P229)
可以说,这一构想,实际上就是《日讲四书解义》编纂的理论原则。“直说大义”,并不是普通的翻译,为求其“明白易晓”,更容易让皇帝接受,往往还要加入许多前因后果的说明,它考验着诠释者知识、学问的贯通程度。从对象角度上看,它往往站在教育君主的立场上,从而使诠释的重心及某些解释与朱注发生偏离。具体来看,《解义》一般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总括大义,可称为“解”;第二部分是对原文进行的翻译,可称为“释”;第三部分用以发挥议论,可称为“议”。
总括大义,一般而言,不管原文或长或短,“解”语仅为一两句话。比如《大学》“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至“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一节,九十余字,该书概括为一句话:“此一节书是曾子言明明德之止于至善也。”[8](P15)《孟子》“孟子见梁惠王……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一节,一百五十余字,该书概括为一句话为“此一章书是言为人君者当躬行仁义也”[8](P329)。以上便是“解”语部分的基本格式。有些“解”语会附以评价和解释,但也都极为简明。比如《论语》“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一章,该书解为:“此一章书是孔子论治国之要,实千古治天下之本务也。”[8](P80)再比如“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一章,该书解为“此一章书是子夏勉人以躬行实践之学。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8](P81)
朱注《四书》中也偶有类似的“解”语,但多偏于说明,比如“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14](P4)不难看出,这些说明基本是针对文本本身的。《日讲四书解义》却基本都是概括主要内容,比如“教人勤学”、“重本”、“观人之法”、“勿自欺之学”等,其中,很多是朱注《四书》没有讲到的。
“释”语部分与原文关联性最大,它往往在释义之前要冠以原理性质的论述,揭示该部分《四书》文本的主要精神,这属于增添的文字之一。比如,《大学》“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一节,《解义》在释文“孔子有言曰:有人争讼……”之前,写道:“曾子曰:大学之道,莫要于明本末先后之序。”[8](P16)所谓“本”就是“明明德”,该句将《大学》先内圣而后外王的精神予以揭示,其中,“曾子曰”三字也是原文中没有而增添的。再比如,《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一节,《解义》在具体释义前,也是先给以原理性说明,其文为:“子思曰:君子主敬之功,其于道不敢有须臾之或离者。盖以道体之用即人之性情也。”[8]36
融通字句、求其易晓是《解义》在具体解释时的鲜明特点。再以《大学》“诗云瞻彼淇奥菉竹猗猗”至“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一节为例。朱注《四书》对该节中澳、菉、猗、亻闲等许多文字都进行了注释,如下:
澳,于六反。菉,《诗》作绿。猗,叶韵音阿。亻闲,下版反。喧,《诗》作咺。讠宣,《诗》作谖;并况晚反。恂,郑氏读作峻。○《诗·卫风·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兴也。斐,文貌。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钅虑钖,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也。……[14]5-6
从引文中可见,朱注中既有针对字音,也有针对字义,还有文字背景,以及《大学》引《诗》与原《诗》区别,包括郑玄对“恂”字读音的看法,如此等等。《解义》则将这些解释糅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其文如下:
……瞻彼淇水环曲之处,猗猗然之菉竹何其美盛也!我斐然有文之君子何其学问之精密而德容之昭著乎!彼治骨角者,既切之以刀锯,复磋之以钅虑钖;治玉石者,既琢之以锥凿,复磨之以砂石,我君子用功之精密而有序也如此。[8](P15)
从上文可以看出,《解义》化用了许多朱注,比如环曲(澳,隈也)、美盛(猗猗,美盛貌)以及切磋、治骨角、治玉石、磨砂石等,最终巧妙地融合成一段文字。应该说,相对于朱注将其切为十七八条进行解释,《解义》该段文义是很连贯的,两者不同显而易见。将朱注如此复杂的解释贯通一气,不仅是作者《四书》学功力的体现,也使该段文字更易理解。
“议”的部分有长有短,都是作者自己的发挥,或对前文进行总结,或作进一步解释,或作其他角度的说明。比如,《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一节,《解义》在解释完具体意思之后,说“仲尼之言如此”,之后便是“议”的部分,如下:
夫中庸之理,人所同得,乃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何哉?盖君子静时既能戒慎恐惧,心存天理,而动时又能随时处中,合乎大道,此所以为中庸也;小人静时既心徇人欲,而动时又肆欲妄行,此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之辨,只在敬、肆之间而已。……中庸之统必归君子,而非小人可得而窃取也。[8](P37)
这段文字虽然主要思想来自于朱注《四书》,但是相比而言,发挥更多、更为融通,并且将程朱理学天理、人欲之辨纳入其中,使其意思更为清晰。
进一步说明的情形比如《论语》“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一节,“解”、“释”部分的文字都不是很多,其文为:“此一章书是孔子托物以比君子之节行也。孔子曰:春夏和暖之时,草木无不畅茂,虽有坚刚柔脆之不齐,然未可辨也。及岁暮寒凝,草木零落,而松柏犹苍然不变,然后知其后彫也。”解释之后,只能讲到最浅层面,因此,该书便在“议”的部分大加发挥说:
盖治平无事之时,小人或与君子无异,至于遇事变、临利害,改节易操,甘与草木同腐者多矣。惟君子处之弥艰,守之弥固,威武不能挫其志,死生不能动其心,即如后彫之松柏然……[8](P185)
关于该节,朱注《四书》则仅引范氏、谢氏两人言论,因此,上述文字基本属于《解义》的发挥。“议”的部分也有转折,比如《论语》“子曰中人以上不可以语下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朱注认为是讲“施教不可躐等”,《解义》“释”的部分基于朱注《四书》进行发挥,但在“议”的部分,《解义》却写道:“然上下岂有定哉?奋志图功,下学亦可以上达;因循玩忽,中人亦等于下愚。总在人之自励何如耳,学者其勉诸!”[8](P141-142)完全由朱注所诠释的如何“教”转向了如何“学”。此外,还有纯粹的总结、升华,常用“盖”、“总之”、“要之”等词连缀,比如“子曰巍巍乎禹舜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一章,“议”的部分为“盖圣人气象度越千古,洵乎其不可及也!”[8](P172)诸如此类,兹不赘述。
三 致用:由经及政、以道正君
“格君心之非”由孟子提出,孟子认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从而为后代儒者“得君行道”作了理论开辟。宋代以降,孟子这一思想与程朱理学紧密结合,以《四书》为文本依据,在历史中进一步展开。熊赐履与程朱的思路一脉相承,在其看来,“君心者万机之枢要,而万化之权舆也,故王道必以正心为本”[7](P44),“有美意即有良法,有仁心必有仁政。”[13](P88)因此,熊赐履在经筵中、庙堂上积极行动,期图以程朱理学“格君心之非”,实现儒家的王道理想,从而使其《四书》学诠释彰显出浓郁的政治向度。
在经筵日讲中,熊赐履时时将诠释向度引向君心与政治。在其看来,“读书必明其理,明理必达诸用。不明其理,口耳之习也;不达诸用,章句之功也。况帝王之学尤与儒生异,岂可不审所要务乎?”[8](P227)有选择性的诠释当然是必要的。比如,对于《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注《四书》诠释向度为“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14](P3)。《日讲四书解义》则引申为“为人君者能究心于此,身体而力行之,治天下无余事矣”[8](P9)。诸如此类,有“古帝王为治之道与此更无二理,诚为人君者所当究心也”、“帝王敬业之心,圣贤谨几之学,有天下国家之责者,时存敬慎之心,则凡事止至善无疑矣”,“必须尧舜之德而后成唐虞之治,人主一身于百姓相感化者捷于影响,有天下国家者诚当以知本为要务”,不胜枚举。
这种致用性的、有选择的诠释,自然不少时候与朱注《四书》发生偏离。以“樊迟问仁”一章为例。朱注《四书》引二程语,认为圣人教人语言因人变化;引尹焞语,认为樊迟问孔子,又问子夏,是“学者务实”。两人是从教育的、修养的角度出发的。《解义》关照的却是该章最后一段,“樊迟问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对于该段,朱注《四书》认为是子夏“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解义》却引申到君主知人善用上,认为:“盖选于众而举皋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谓举直措诸枉也……仁乃天地之量,智乃日月之明……仁、智二者,信人君之全德、王道之大端也。”[8](P221)再比如,《论语》“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章。朱注只引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则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为患也。”[14](P53)《解义》却引申到君主的治国理政上,其议论如下:
夫知人之明,自古帝王皆以为难,有正直之人,有邪曲之人,又有似贤非贤、似忠非忠之人,倘不审择,势必是非颠倒,举措乖宜,然则所以清心明理,以为鉴别之地者,又何可已哉?[8](P86)
很显然,这种议论,基本上不是由朱注引申出来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朱注也未必就能引申出以上的议论。但是,正是这种诠释方式,使《四书》与君主的行政、用人生动活泼地结合起来,不再是枯燥的知识学传授。
经筵日讲之外,熊赐履还利用皇帝单独召见垂问理学的机会,进一步以诠释《四书》来格正“君心之非”。其中,《大学》中的“正心”是熊赐履多次提及的。在熊赐履看来,《大学》如真德秀认为的一样,是“正君心”必不可少的儒学经典,如其所谓:
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原;为人臣不可以不知《大学》,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至哉斯言,圣人弗易矣
那么,熊赐履是如何在书本之外的现实政治中来诠释《大学》呢?试看一例。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二月某次召对中,皇帝发感慨说:“从来与民休息,道不在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为可鉴”,熊赐履回答道:
《书》云,临下以简。又云,监于先王成宪。皇上此言,诚千古守成之要道也。但欲省事,必先省心,欲省心,必先正心。自强不息,方能无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人君诚能清心寡欲,日新又新,则大本已立,凡举措设施可不劳而理矣。[13](P68-69)
康熙帝讲到省心,熊赐履便指出非正心则不能省心,省心只能在事务上,在理欲之辨上不能省心,相反要“自强不息”。熊赐履的这段话,脱胎于《大学》文本。“正心”是《大学》八目之一,关于“正心”,《大学》认为“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正心”是清心寡欲,不间断洗涤心中的私欲污染。这样,才能“日新又新”。“日新又新”亦出于《大学》,原文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子解为:“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14](P5)在熊赐履来看,“正心”其实就是“敬”,“敬”就是自强不息,不断洗涤,日新又新,只有君心正,才能垂拱而治。
熊赐履诠释《大学》的“正心”说,是与程朱理学的理、欲之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朱子认为本原之性只是理,“蔽锢少者,发出来天理胜;蔽锢多者,则私欲胜,便见得本原之性无有不善。”[15](P66)“心之发则意也,一有私欲杂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未实,则心为所累,虽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16](P511)君主不能正心,在于私欲胜,私欲胜便会躁进。康熙帝总是急于致用,故而熊赐履每以“知先行后”、“致知穷理”为对,这在第一部分即康熙十二年(1673年)八月那次召对中已经述及,在那次召对中,熊氏便将这种急于致用归结到“私欲”上,说:
……为治固患废弛,然求治甚急,将纷更丛脞,为弊滋甚,所讲欲速不达也。……求治太急,还是人欲用事,必无欲然后可以言王道。[13](P115)
紧接着,熊赐履又对康熙帝讲“凡事有始终,有本末,人主根本既立,方讲得用人行政。盖用人行政,原无穷尽。先将道理讲明,根本立定,不惑于他歧,不迁于异物,一以二帝三王为法,而后用人行政,次第讲究施行……”[13](P118),为康熙帝解释了《大学》由内圣而外王的为学次第。次日,在召对中,康熙帝承认说:“看来讲明道理要紧,若无这道理,一切事务都无凭发落”,还表示“学问之道,毕竟以正心为本。”熊赐履“正心”说终于赢得了康熙帝的认同。熊赐履针对康熙已经认识到“正心”的重要性,进一步引导其如何正心,便接着说:“圣谕及此,得千古圣学之心传矣。人主清心寡欲,如鉴空水止,声色不乱其聪明,便佞不惑其志气。……本体一失,诸事尚可问乎!”[13](P119)
要“正心”,便要“格物”,君臣议论一直在《大学》文本中回旋。该月十三日,讲毕召对,康熙帝说:“朕昨观《大学》,格物二字最是切要工夫,盖格物即是穷理也。”熊赐履回答说:
圣贤本体工夫,只是格物二字包括无余。内而身心意知,外而家国天下,皆物也。物无不格,斯知无不致,而德无不明。圣经贤传,千言万语,无非发明此理。但其间有根本,有切要,非泛骛于一草木、一器具之末,为支离无本之学也。孟子曰物皆然,心为甚。盖心又物之大者,万理之所具,而万事之所出也。[13](P121)
康熙帝对“格物”的理解是程朱式的,这与熊赐履相通,然而天下万物岂能尽格?一一格去岂不支离?因此,熊氏进一步引申说,“物”分为“身心意知”与“家国天下”两部分,学问要有根本、切要处,那就是要以“格心”为本。康熙帝领悟道:“天地古今,道理只是一个,故曰一以贯之。然则博文约礼,工夫合当如是。”熊赐履回答说:“诚如圣谕。”[13](P121)可见,这里所谓“格物”、穷理的目标仍然是“正心”,也就是要君主在现实政治中去实践程朱理学的“去人欲、存天理”。
四 余论:从直言讲论到缄默自容
与黄宗羲、顾炎武、张履祥、王夫之等人不同,面对新朝,熊赐履选择了出仕的“得君行道”之路。然而,熊赐履要面对的是清初这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王学未衰,考据学又勃兴,程朱理学建立的《四书》学体系面临着儒学内部的挑战。另一方面,来自外部的佛、道,满洲贵族从关外带来的意识形态,更兼政治的波谲云诡以及帝王的无尚权力,也都是程朱《四书》学精神在政治中展开所要应对的。熊赐履经筵式的《四书》学诠释,必将是艰难的,这种艰难,远在书本之外。
早年的熊赐履,表现出“正君心”的一往无前的任道精神。顺治帝去世后,鳌拜专权,率复旧章,反对汉文化。熊赐履便不顾个人安危,上万言书,从民生、吏治、学校、风俗等方面为清王朝提出了程朱式的治国纲领。当时专有朝政的鳌拜“恶其侵己”,欲治熊赐履之罪,康熙帝表示说:“彼自陈国家事,何预汝等邪?”[17](P268)熊赐履的万言书虽然并不直接针对鳌拜,但是以理学格君心、正治统,却与鳌拜等满洲贵族的治国理念相冲突。次年,熊赐履再次上疏,不顾被鳌拜传旨诘问。观其言行,真有众人唯唯、一士谔谔的豪杰之概。
熊赐履这份忠直赢得了少年皇帝的心。鳌拜倒台后,熊赐履以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知经筵,开启了对皇帝的理学启沃,康熙帝每每“虚己以听”,日讲余暇,还时时单独召见熊赐履加以垂问,熊赐履则“上陈道德,下道民隐,引申触类,竭尽表里”。[17](P269)直到晚年,康熙帝还回忆说:“朕初立讲官,熊赐履早夜惟谨,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18](P475)此外,熊赐履还向皇帝进献自己的著作《闲道录》,康熙帝认为该书“正大精醇,斯诚斯文的派也”,“有功圣道不浅”[17](P256),并将其置之案头,题为“熊学士闲道录”,时称“异数”。
当时王学在朝廷中还有很大声势,汤斌、李光地(晚年有变)、崔蔚林、许三礼等许多高级理学官僚,学术皆近于阳明,而讲程朱理学的熊赐履实为“独树一帜”,正如康熙帝讲的:“许三礼、汤斌、李光地俱言王守仁道学,熊赐履惟宗朱熹,伊等学问不同。”[13](P1902)王学一派也试图影响皇帝的道统取向,许三礼参徐乾学荐举熊赐履,汤斌又谓在康熙帝眼中“甚佳”的《日讲四书解义》为“不然”。康熙十八年(1679年),崔蔚林进呈《大学格物诚意辨》,为王阳明辩护。康熙帝与崔蔚林论辩,认为虽然人性本善,但是“不用存诚功夫,岂能一蹴而至?”得出结论说:“蔚林所见与守仁亦相近。”[13](P452-453)
熊赐履不仅奋力批判王学,在庙堂上屡说皇帝远离佛老,私下还与友人议论说:“《黄庭经》有成议否?主上留心文事,乃崇儒重道之一机,而好事者先以此进,正不可不防其渐也。”[5](P373)对与程朱《四书》学不合的新说怪论,熊赐履也加以辟说:“今人说着圣贤正论,便摇头不许曰:‘此是旧话,是常套’……学者能除却好新喜异的心,这道也不难明。”[10](P63-64)为了让理学在朝廷立足,熊赐履还借机向皇帝推荐魏象枢、李光地、王宽兹等人。
然而,正人心难,何况要正的是君心?熊赐履虽然一度得君,但是“因备受康熙帝信重而受众人侧目”,于是“成为一些官僚攻击的对象”[19](P122)。早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就有人弹劾熊赐履,认为其会试拟题《耻之于人大矣》“近于讥刺”,熊赐履回答说:“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即以出题,论圣贤之言,字字龟鉴,无容简择,有何避讳?凡避讳者,衰世之事,而庸人鄙夫之见也。……况孟子分明说‘耻之于人大’,朱子亦曰‘所系甚大’……”[5](P234)表现了凛然正气。然而,康熙十五年(1676年),刚入阁为大学士一年多的熊赐履终于栽倒在“嚼签案”上。关于该案,李光地认为是索额图所陷害。该案发生后,朝廷“皆言熊赐履不好”,成为“名教罪人”的熊赐履却难以理解地保持缄默。从鳌拜到索额图,熊赐履从得君到失势,基本上结束了“以道正君”之路。
熊赐履由此被革职,之后寥落江宁,在清贫中度过了十余年岁月。虽然之后被朝廷重新起用,依然被皇帝信任,不仅知经筵如故,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还被委以教导东宫太子,但是,熊赐履发生了很大转变,不再直言讲论。康熙曾讲说:“九卿会议时,但一二人发言,众俱唯唯……熊赐履尝讲理学,后为大学士,亦唯缄默自容。”[18](P361)其中原因是什么呢?
康熙帝在位中期,经受熊赐履等人的理学熏陶之后,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真理学”的理论,君臣道统之争难以避免,熊赐履自然首当其冲。康熙帝不仅批评说:“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没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13](P2222)还认为熊赐履“务虚名”。[20](P785)以程朱自期的熊赐履成为世人眼中的“名教罪人”,这种心理落差可想而知,揆其文集,诸如“以迂拙忤时,落魄江左,厌厌如泉下人”[5](P374)、“仆被出国门矣,何敢复言天下事”[21](P567),悲愤之词难以尽举。熊赐履还将江宁寓所某亭名为“默然轩”,并作记感慨说“缄默以取容”是君子“明哲保身之道”,反嘲自己以前“在朝论治谔谔如也”[5](P292)。
枉尺不能直寻,在这种情形下,又如何“以道正君”呢?更何况朝廷党争波诡云谲,一招不慎,便可能是身败名裂,熊赐履已然亲身经历过。康熙帝认为熊赐履的缄默“皆为彼门生掣肘故也”,这显然不是根本原因。不仅熊赐履对政治有失望感,再次复出后,还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康熙朝的党争中。[19](P122-126)这就更使熊赐履难以“以道正君”,而是只好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高位上。不过,康熙帝从心底仍然对熊赐履怀有很深的敬意和信任,这种敬意和信任,应该来自于两人对程朱理学理解,熊赐履对《四书》的诠释,已然深深地印在康熙帝的心中,御制碑“领袖玉堂,品行无惭师表;从容丹陛,文章不忝儒宗”,可谓是康熙帝对熊赐履中正的评价。
[1] 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
[3] 王茂,蒋国保等.清代哲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4] 徐世昌.清儒学案[M].北京:中国书店.1990.
[5] 熊赐履.经义斋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0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7.
[6]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 熊赐履.闲道录[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5.
[8] 日讲四书解义[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8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
[9] 熊赐履.学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10] 熊赐履.下学堂札记[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5.
[11] 曾亦,郭晓东.宋明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3] 康熙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 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朱熹.四书或问[A].朱子全书(第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7] 钱仪吉.碑传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8] 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 高翔.熊赐履述论[A].清史论丛2006年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20] 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1] 熊赐履.澡修堂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0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7.
The Interpretation Features of Xiong Cilv'sTheFourBooksTheory on the Emperor Education
Wang Sheng-jun
(Guizhou university,Chinese Culture Academy, Guiyang 550025,China)
Xiong Cilv is a renowned Neo-Confucian minister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TheFourBooks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on the emperor education which mainly demonstrate in three aspects: in philosophy, honoring Cheng-Zhu and identifying Confucian orthodoxy; in style,directly expressing the main meaning and making it easy to understand ; in practical level, stretching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to politics and rectifying the emperor moral by Dao.TheFourBookstheory of Xiong Cilv is the typical spreading of the theory in the political reality and i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TheFourBookstheory research.
Xiong Cilv;TheFourbookstheory; interpretation; Neo-Confucianism
2015-05-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13&ZD060);教育部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清初庙堂理学研究(12XJC770001)
王胜军(1979—),男,河北高邑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理学、书院教育.
B222.1
A
1008—1763(2015)04—00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