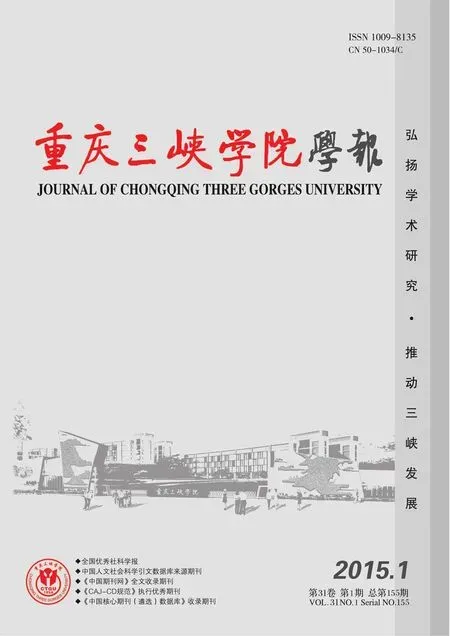合同无效问题研究
孙文桢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合同无效问题研究
孙文桢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合同无效只意味着合同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而不意味着不得履行,更不意味着任何公法性的后果。目前的合同无效概念无法涵盖合同绝对无效的全部情形,亦无法涵盖合同相对无效。“任何人均得主张其为无效”中的“主张”有其特定的含义。合同相对无效的类型只有“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型”这一种,学界迄今所提及的其他类型的合同相对无效均非真正的合同相对无效。
合同无效;合同相对无效;合同的法律约束力
一、解题和前提
顾名思义,本文拟研究合同的无效。关于合同的无效问题,学界迄今已有诸多论述。之所以在知道有此等诸多论述的情况下,依然还要“研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已有的关于合同无效的论述存在不科学之处。其中,有的观点(包括主流观点)违反了法理,因而是错误的;有的观点虽然其结论似乎符合法理,但是论据难谓充分,理由难谓充足,或多或少地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经不住反驳。其二,在合同无效问题上的主流观点目前正在被学界的权威学者和著名学者所提倡,并且已经通过这些学者的著述、讲座、谈话等途径正在学界广泛传播,影响巨大,尤其是对相关法学研习者,其消极影响实在不可低估,很有必要尽快纠正。其三,《合同法》颁行迄今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合同法》经过实践检验,已经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因而《合同法》的修正就是迟早的事情。对于合同法来说,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可谓其核心问题,故此,笔者真诚地期望,本文的见解能够为《合同法》未来的修正提供理论指导,从而为共和国的法治建设略尽作为公民兼法学研究者的绵薄之力。需要预先说明的是,鉴于《合同法》立法方案及学说均认为《合同法》规制的是债权合同[1]122,故本文如无特别提示,所称“合同”均指债权合同。
二、合同无效究竟“无”什么?
合同无效究竟“无”什么?合同无效尤其是合同绝对无效都是因为合同标的违法?合同无效就意味着合同不得履行?合同无效与“追缴财产”、“罚款”、“吊销营业许可证”等公法性后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均值得深思。
(一)合同无效概念的界定
学界长期以来直至目前在界定合同无效概念时,使用的均是“不许按……赋予……”、“不按……赋予……”、“不能被赋予……”、“不能产生……”等等诸如此类的表述。例如,崔建远教授主编的《合同法》将“合同无效”界定为“合同严重欠缺有效要件,不许按当事人合意的内容而是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赋予法律效果。”[2]97韩世远教授在其颇负盛名的专著《合同法总论》中将“合同无效”界定为“当事人所缔结的合同因严重欠缺生效要件,在法律上不按当事人合意的内容赋予效力。”[3]168陈小君教授主编的《合同法学》将“合同无效”界定为“合同因欠缺法定生效要件而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当事人的合同不能被赋予国家法律体制层面上的效力。”[4]96韩松教授主编的《合同法学》将“合同无效”界定为“已经成立的合同因违反根本性生效要件,因而自始、当然、确定地不能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5]66
这些对于“合同无效”的界定相互之间存在差异,而有的表述甚至还违反了法理。对同一事物,有的界定称其为“有效要件”,有的界定称其为“生效要件”,有的界定称其为“法定生效要件”,有的界定则称其为“根本性生效要件”。很明显,这些说法不可能都正确。同时,这些界定混淆了“缔约人”与“当事人”这两个概念。诚然,在很多情况下,缔约人都是以他自己的名义缔约,都是在为他自己缔约,这时候是否区分“缔约人”与“当事人”意义不大,使用无论哪个称呼都可以,因为这时候“缔约人”与“当事人”的身份完全重合了。但是,在由代理人缔约的情况下,这种区分就很有必要,因为这时代理人是真正的缔约人,他实施了缔约行为,而“本人”才是当事人。所谓“当事”,就是“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上述那些对“合同无效”的界定中所使用的“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所缔结的合同”和“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这三个表述,就明显混淆了“缔约人”与“当事人”这两个概念,因为“合意”并非总是当事人的,“合同”并非总是当事人缔结的,“法律效果”亦并非总是当事人所预期的。只要考虑一下法定代理人或意定代理人以“本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情形,就可以知道“缔约人”与“当事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了。
退一步讲,即使对于上述差异和违反法理暂且不论,仅“不许按……赋予……”、“不按……赋予……”、“不能被赋予……”或者“不能产生……”这样的表述,其语气、风格和文字含义就均与“无效”的“无”严重不符。
如此界定“合同无效”,实际上是误将原因当成了结果,从而颠倒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本来关系。本欲表述什么是合同无效,但实际上却在表述合同为什么无效。无论“不许按当事人合意的内容……赋予法律效果”,还是“在法律上不按当事人合意的内容赋予效力”;无论“不能被赋予国家法律体制层面上的效力”,还是“不能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实际上都是在解释合同为什么没有法律约束力。衡诸合同法的法理,正因为此等“不许按……赋予……”、“不按……赋予……”、“不能被赋予……”和“不能产生……”,合同才没有法律约束力,换言之,合同无效。
笔者认为,合同无效的“无”就是“没有”,“无效”就是“没有效”,就是“没有法律效力”即“没有法律约束力”。简而言之,所谓合同无效,即指合同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种理解不但符合语言表述的规则,而且亦有着法律依据、法理依据和生活依据。首先,法律依据。《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据此可知,“合同无效”即指合同没有法律约束力。其次,法理依据。依法理学原理,“法律效力”一语指的就是法律约束力。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效力,即法律约束力,指人们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那样行为,必须服从。”他还认为:“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指判决书、裁定书、许可证、合同等的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在经过法定程序之后也具有法律约束力。”[6]463换言之,法律效力就是指法律约束力,无法律约束力就意味着无法律效力,简称为“无效”。最后,生活依据。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问某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时,我们其实是想知道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该合同在法律上算不算数?能不能管住当事人?如果一方不认账了,法律能不能想办法让他认账?或者想办法让他承受不利后果?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合同有无法律约束力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学界目前对合同无效的界定,皆单一地从合同标的违法角度考虑问题,而未考虑意表瑕疵所导致的合同无效,未考虑效力待定合同被拒绝追认所导致的合同无效。这样界定的合同无效概念只能涵盖合同绝对无效的部分情形,而无法涵盖合同绝对无效的全部情形,更无法同时涵盖合同相对无效①按照意思表示瑕疵理论,意表瑕疵所导致的意思表示无效中,有的无效可对抗任何人,有的无效则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前种情形下的合同无效(例如合同因胁迫而被撤销)属于绝对无效,后种情形下的合同无效(例如合同因欺诈而被撤销、因通谋虚伪表示所致无效)则属于相对无效。又,效力待定合同因被拒绝追认所导致的无效亦属于绝对无效。这些合同无效情形均无法被目前的合同无效概念所涵盖。,因此带有先天的片面性,有待纠正。
(二)不强制履行还是不得履行
合同无效既然意味着合同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就不存在债务人必须履行债务或者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这回事。自法律角度观察,合同无效意味着法律不强制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意味着法律不支持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履行请求。换言之,合同无效意味着法律不强制履行合同。
那么,合同无效是否还意味着合同不得履行?王利明教授认为:“无效合同有一个重要规则就是不得履行性。所谓无效合同的不得履行性就是说当事人在缔结无效合同之后,不得根据合同来继续履行。”①参见王利明《合同无效制度的问题》,载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 default.asp? id=18694。笔者通过百度、搜狗、搜搜等各大网络搜索引擎搜索到的“合同无效”词条,亦均表达了同样观点,可见此观点非常流行。
衡诸事实层面,的确有无效合同不得履行的。例如,贩卖毒品、拐卖儿童的合同系无效合同,法律不但不会强制履行,而且还会禁止履行。但是,此种现象并不能证明合同无效即意味着合同不得履行,而只能说明,此时的合同因为其内容违反禁止性法律规定(例如实施犯罪的合同),因此不但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而且还要遭到法律的禁止。
有的无效合同,法律固然不强制其履行,但亦并不禁止其履行,某些违反善良风俗的合同即为适例。甲乙均系大三学生,双方约定乙在大庭广众之下给甲下跪并磕三个响头,而甲则在乙下跪磕头之后把自己的某名牌手机的所有权移转于乙。该合同因为内容违背善良风俗,所以无效。该合同无效只意味着乙在法律上没有义务非下跪磕头不可,相应地,甲亦没有权利请求乙下跪磕头;如果乙不愿意依约下跪磕头,则法律不会强制他这样做。这就是该合同无效的含义。
那么,如果乙愿意下跪磕头呢?法律当然不会禁止,因为此等行为并未违反禁止性的法律规定。(自愿受辱,其不值得提倡,且在道德上应受谴责,这一点自不待论。)
所以,合同无效只意味着法律不强制债务人履行合同,而并不意味着法律在此之外还禁止合同的履行。在不强制之外是否禁止,须依有无相应禁止性法律规定而为判断。
英国著名合同法学家阿狄亚教授有言:“在合同仅被宣告无效时,当事人仍然完全有自由履行该合同,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法律所做的只是拒绝强制履行合同。”[7]337此话的意思与笔者的上述理解完全相同。
(三)还有其他法律后果
如上所述,合同无效只意味着合同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意味着法律并不强迫当事人履行合同,而并不意味着其他。但是,学界长期以来直至目前在阐述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时,均会使用相当的篇幅阐述“返还财产”、“缔约过失责任”、“追缴财产”、“罚款”、“吊销营业许可证”、“吊销生产许可证”等等,甚至还提到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②这种情况在我国合同法学界非常普遍,几乎难以发现例外。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124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229页;陈小君《合同法学》,高教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117页;韩松《合同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5页。。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妥当,误解了合同无效这一私法概念的含义。合同无效只意味着合同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作为合同法理论研究,仅指出这一点即为足够,或者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对于合同之外的其他私法性后果,稍作提及,亦无不可。但是,如果像学界长期以来直至目前的诸多著述那样,在阐述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时,对合同之外的私法性后果大费笔墨,甚至对合同无效可能会导致的某些公法性后果亦津津乐道,并且经年不衰,则不但多余而且非常不妥。显然,“返还财产”不但不属于合同法范畴,而且亦与合同无效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联系。有时候,合同虽然被宣告无效,但并无财产需要返还;有时候,虽然财产被对方无权占有,但当事人并未主张亦无意主张财产的返还。在后种情形下,有什么必要非要擅自代当事人做主不可呢?同理,“缔约过失责任”与合同无效之间亦缺乏必然联系;至于“追缴财产”、“罚款”、“吊销营业许可证”和追究刑事责任之类的公法性后果,就更是不但与合同无效之间缺乏必然联系,而且亦严重逾越了私法的范畴而进入公法的领域了。
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将合同法与私法的其他部分(如物权法)严格区分开来,而且亦反映了对于私法和公法的混淆,属于所谓的“私法公法化”,其立于公法之巅而居高临下地傲视私法傲视合同和合同法的姿态跃然于纸上,其中所散发出的那种高高在上俯瞰合同管制合同甚至恐吓合同主体的浓烈气息,与私法自治私权神圣的伟大理念极不相称,故此亟待纠正。有必要指出的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学者们在论述法律行为的无效后果时,均未提及任何公法性后果,这一点理应引起我们的深思①例如,德国梅迪库斯教授所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拉伦茨教授所著《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台湾王泽鉴、梅仲协、史尚宽等我国著名民法巨擘的著述在论述法律行为的无效时,对公法性后果均只字未提。。
三、合同绝对无效之“任何人均得主张其为无效”
合同无效有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之分,本文仅论述合同绝对无效。至于合同相对无效,作者将另行撰文予以论述。
合同绝对无效系指当然无效、自始无效和确定无效。其中的“当然无效”,依学者见解,意为“任何人皆得主张其为无效,亦得对任何人主张之。”[8]479但是,在如何理解“任何人皆得主张其为无效”上,却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其一,何为“主张”?其二,是否允许当事人以自己缔约时存在违法而主张合同绝对无效?如果允许,那么是否有违“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恶行中获益”的法谚?是否有违“禁止反言”的原则?
关于第一个问题,综观整个私法理论,未见有对“主张”概念的专门界定。笔者认为,所谓“主张”,并非一般性地对某事物表示一下看法,而是希望得到“权利或利益”即“权益”。如无权益存在,就无所谓“主张”。权益之所在,即主张之所在。通俗地讲,只有与某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有资格“主张”合同无效;同时,既然是为权益而主张,那么“主张”肯定只能向侵害了“主张”者的权益的人实施,而不能向其他人实施②笔者曾专门借助电子软件查阅了“台湾民法典”(2010年最新修正),发现其中总共有25处“主张”。经逐一分析,发现均可支持笔者此处的结论。另,王泽鉴教授在其《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83页谈及“台湾土地法”第30条时,有“承受人自耕能力之有无,纵未经当事人主张或抗辩”之语。显然,“主张”与“抗辩”系反义词,对“抗辩”的思考亦有助于理解“主张”。。
基于此种认识可以推知,如果有人与某合同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却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宣告该合同无效,那么,这只是一般性地对该合同的法律效力表示了一下看法,而非“主张”。对此,法院完全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项规定,以“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前),或者裁定驳回起诉(立案后)。
所以,“任何人均得主张其为无效”,其真意当指“任何与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均可以主张合同为无效”。王利明教授认为:“在(合同)与第三人利益无关的情况下,如果第三人也可以随意地在法院主张合同无效,就会导致很多人能够无端地干预别人的合同关系,……就会损害他人利益,影响社会安定。”[9]笔者认为,王利明教授在此误会了“主张”一语的含义。正如上述,与合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请求法院宣告合同无效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主张”,仅仅是表示了一下他本人对合同法律效力的看法而已。
关于第二个问题,学界有观点认为,如果当事人以自己缔约时存在违法而主张合同绝对无效,则属恶意抗辩,应在禁止之列,因为这种行为不但有违“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恶行中获益”的法谚,而且也有违“禁止反言”的原则[10]。
笔者认为,恶意抗辩固然应当禁止,但“当事人以自己缔约时存在违法而主张合同绝对无效”是否属于恶意抗辩则有待反思。既然合同绝对无效的“绝对”含有“任何人均得主张其为无效”之义,则当事人当然可以主张自己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即使他是以自己缔约时故意违法为理由而主张合同无效,亦不改变此结论。如果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的“违法”足以导致合同无效,那么,法院依照该法律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又有什么不妥呢?
问题在于,学界凡是论及无效合同认定中的恶意抗辩时,所说的“合同无效”,均非合同绝对无效。有学者举借款人以虚假担保骗取银行贷款,随后为不支付贷款利息,竟以自己于缔约时提供虚假担保从而构成欺诈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的实例,意图说明无效合同中恶意抗辩问题[9]。但显而易见的是,该实例中的合同并非无效合同,而是可撤销合同。按照可撤销合同的法理,欺诈方根本无权请求撤销,又何来恶意抗辩?
有法院人士举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以自己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的案例,意图说明出卖人恶意抗辩行为不应得到支持[11]。但事实上,按照效力性的强行性规则与管理性的强行性规则的区分理论,这种商品房买卖合同本来就不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12]。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既然如此,那么主张合同无效的恶意抗辩又从何谈起呢?
衡诸合同法的法理,导致合同绝对无效的“违法”只能是合同标的违法,而这种违法或者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或者是违背了公序良俗。因此,当事人无论以何种理由主张合同无效,其本质都是在抛弃不法,至少是在客观上使得自己的行为脱离不法状态,从而其行为就不属“恶行”。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有违“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恶行中获益”的法谚呢?毒品出卖者因为毒品价格猛涨,而以毒品交易违法为由主张毒品买卖合同无效,虽然其动机只在于自利而不在于守法,但衡诸基本法理,判断是否违法只看行为不看动机,故其主张合同无效的行为其实是在抛弃不法并遵守法律,而绝不应属于“恶行”之列。
至于“禁止反言”原则,作为英美法上的一项原则,与大陆法上的诚信原则一样固应遵守,但是综观英美法对于该原则的运用即不难发现,无论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原则作怎样的解释和演绎,总有一条基本的底线一直都在得到坚守而从未被突破:“禁止反言”中的“言”即允诺必须是不违法的,否则,对于违法的允诺,是完全可以违反的。在卖淫嫖娼合同、贩卖毒品合同等无效合同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违反自己缔约时的允诺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只要有证据证明当事人缔约时的允诺确系违法,则无论是否故意违法,他都可以违反自己的允诺,而与“禁止反言”的原则无涉。
四、合同相对无效的类型
在我国大陆,“合同相对无效”概念为王利明教授所最先提出[13]635。既然合同绝对无效系指合同“当然无效、自始无效、确定无效”,那么就解释论而言,合同绝对无效受限制的任何情形皆属合同相对无效[14]273。这种意义上的合同相对无效在外延上过于宽泛,甚至将给付已经实际发生的继续性合同被宣告无效[8]482、合同可撤销亦包括了进去。有鉴于此,学界对“合同相对无效”做目的性限缩,将其界定为不涉及所有人而只涉及特定人的合同无效[8]483。本文的论述即以此为基础。
综观学界见解,合同相对无效共有两种类型,其一为仅特定第三人得主张型,其二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型。不过,这两种类型的合同相对无效,其所谓“合同”,并非均为我国《合同法》所谓的“合同”。
(一)仅特定第三人得主张型
该类型的合同相对无效,系指合同仅对某特定第三人才无效,对其他人则有效。换言之,只有某特定第三人才有权主张合同无效,而其他人均无权主张合同无效。该类型的合同相对无效,近年来被学界广泛提及①例如,陈小君、崔建远两位教授在其各自所主编的合同法教材中对这种合同相对无效均有提及,而韩世远教授在其专著《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中,对此种合同相对无效也有提及。,法释[2003]7号第10条则被王轶教授认为是该类型的典范[12]。崔建远教授认为,“德民”(指《德国民法典》,下同)第135条规定的就是合同相对无效[2]101。
1.“德民”第135条
“德民”第135条被德国民法学者认为是德国民法上法律行为相对无效的典型[15]375。该法第135条第1款规定:“如果处分标的物违反了法律为保护特定人所作的禁止出让的规定时,其处分仅对该特定人无效。根据强制执行或者假扣押进行的处分,与根据法律行为进行的处分相同。”[16]26不难看出,该条所谓“仅对该特定人无效”(即“相对无效”)系指处分行为的无效,而并非指债权合同的无效。
2.法释[2003]7号第10条
法释[2003]7号第10条规定:“买受人以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其无法取得房屋为由,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如上所述,王轶教授认为该条规定的就是仅特定第三人得主张型的合同相对无效。
笔者认为,该条违反了债权的平等性和相对性,显非合理。当然,考虑到该条施行于《物权法》颁行前,因此它违反法理尚情属可原。如将该条所规定情形置于《物权法》颁行后的背景下考虑,则处理办法就截然不同。首先,考察房屋买卖合同订立后,买受人是否依《物权法》第20条规定办理了预告登记。如果办理了,那么他可以依法主张出卖人与第三人间的房屋过户登记行为(相对)无效①依《物权法》第20条,不动产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而处分该不动产的,处分行为效力待定。笔者认为,该条规定对德国法的借鉴不够彻底,其中的处分行为的效力应为相对无效。有学者亦持相同见解,参见侯国跃:《论不动产预告登记》,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2期。,从而保护自己的债权。如果买受人未办理预告登记,则可认为他并不重视自己的债权,可认为他并不在乎该房屋又被出卖给第三人甚至过户②法律一经公布,即应视为人民都已经知道,而不管人民是否实际上已经知道。例如,只要实际上构成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那么,即使行为人不知道《刑法》第340条的存在,亦依然应当接受刑罚。。这种情形下,如果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法院当然应当支持,但是如果他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就不应当支持。
由此观之,对同样情形,在《物权法》颁行前,依照法释[2003]7号第10条处理,买受人竟然可对他人间的债权合同主张无效,这显然违反债法法理,而在《物权法》颁行后,买受人如果办理了预告登记,在出卖人将房屋过户与第三人时,他就可以主张过户无效。这时,对一个法律行为(过户登记行为属于物权合同),利益受损的特定人有权主张无效,这不但未违反任何法理,而且还合乎法理和法律。只不过这时,该特定人所主张无效的是物权合同而非债权合同。
3.《合同法》第52条第2项
《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系无效合同。实际上,无论是否恶意串通,只要损害“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③王轶教授认为民法上不存在集体利益,笔者赞同此见解,但为行文方便,此处暂从法律条文的原文。关于王轶教授的观点,参见王轶:《合同效力认定的若干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即属违背公序良俗,合同均为无效,这一点已为学界共识。对此处的“第三人利益”,王利明教授将其分为“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和“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并进而认为“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侵害“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属于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而侵害“特定第三人的利益”的合同则属于侵害私益的合同,只能由该受害的第三人主张合同无效,该无效属于合同相对无效[13]649。
笔者认为,“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并非皆属私益。衡诸公序良俗,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亲属身份利益既属私益,亦属公序良俗,因为人格利益、亲属身份利益构成了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秩序,具有当然的不可侵性,因此,恶意串通损害特定第三人的人格利益和亲属身份利益的合同,理应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
经过如此剔除,“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中就只余下财产利益了。恶意串通损害特定第三人财产利益的合同,其效力如何,可分两种情形考察。第一种,恶意串通以实施违法行为(包括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方式损害特定第三人财产利益的合同,其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因而无效[17]207。第二种,双方恶意串通订立合同处分特定第三人的财产的,这种情形属于无权处分。依传统民法,无论双方是否恶意串通,债权合同效力均不受影响。至于对该特定第三人财产的处分行为(物权行为),依《物权法》规定,除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和标的物系盗脏、遗失物而适用专门制度之外,其他情形下的无权处分行为均属无效(传统民法规定其为效力待定)。所以,《合同法》第52条第2项并不会导致合同相对无效。
(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型
该类型的合同相对无效,系指合同虽然无效,但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学界在说明该类型的合同相对无效时,惯常引用王泽鉴教授所著《民法总则》中的这个案例④例如,李文涛教授发表于《法学家》2011年第3期上的《合同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一文就是如此。:乙出卖某屋与甲,其后见房价高涨,意图避免甲之强制执行,遂与丙约定假装作成买卖,办毕所有权移转登记,并交屋于丙。丙擅将该屋让售于善意之丁,并办毕所有权移转登记。
实际上,该案例引用得并不恰当,因为该案例中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丁)的合同是乙丙间的物权合同[8]359-366,并非债权合同,而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却仅指债权合同。
(三)合同相对无效类型之我见
前述两种类型的合同相对无效均与合同绝对无效相互对应。绝对无效中的“当然无效”,系指“任何人皆得主张其为无效,亦得对任何人主张之。”显然,前述第一种类型即系对“任何人皆得主张其为无效”的限制,而第二种类型则系对“得对任何人主张之”的限制。
1.仅特定第三人得主张型
债权合同系对未来活动的安排。此安排即使以侵害某特定第三人的财产利益为内容,在合同履行前,该特定第三人的财产利益亦不会受到任何侵害。毕竟,“准备侵害”与“现实地侵害了”并不相同。所以,对于债权合同,不存在特定第三人有权主张合同无效这回事。
这同时亦说明,特定第三人有权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可能会出现在处分合同中,因为处分合同是对财产权利的现实变动,该变动有可能现实地侵害了某第三人的利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前述学界所提及的仅特定人得主张型的合同相对无效中,其合同只是处分合同。显然,如果我国《合同法》继续如目前这样坚持认为合同仅指债权合同,那么,仅特定人得主张型的合同相对无效就无法在我国《合同法》中觅到立足之地。
2.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型
依民法法理,合同无效的原因有标的违法、效力待定合同被拒绝追认和意表瑕疵(如通谋虚伪表示)。标的违法的实质在于标的违背公序良俗,因而合同如因标的违法而无效,则其无效必定是绝对无效,可以对抗任何人。同时,为强力保护特定主体(缺乏相应行为能力者、狭义无效代理中的“本人”)①笔者认为无权处分情形下的(债权)合同不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故此处所称“特定主体”未包括无权处分情形下被处分财产的权利人。的利益,效力待定合同被拒绝追认所导致的合同无效亦是绝对无效,可以对抗任何人。唯有意表瑕疵所导致的合同无效,才可能会出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回事。
在笔者看来,传统民法上三种意表瑕疵情形下的债权合同无效,属于“不得对抗第三人型的合同相对无效”。这三种情形分别是通谋虚伪表示、单独虚伪表示、为相对人所明知者和受欺诈而为的意思表示被撤销。依传统民法,这三种情形下的意思表示均属无效,并且此等无效均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德民”第405条规定:“债务人已制作债务证书的,在出示该证书始得让与债权时,债务人不得对新债权人主张债的关系的缔结或者债的关系的承认系出于虚伪表示,或者主张与原债权人有不得让与债权的约定,但是新债权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情事者除外。”[16]78在这里,不得对抗新债权人的那个(通谋)虚伪表示,即指无效的债权合同。该债权合同虽然无效,但其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新债权人)。
五、结 论
综上所述,关于合同无效,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合同无效只意味着对当事人无法律约束力
界定合同无效概念就是要表明什么是合同无效,而不是去表明为什么合同无效。据此,本文反对学界目前对于合同无效概念的界定,而将合同无效概念界定为合同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只意味着法律并不强迫当事人履行合同,而不意味着合同不得履行,更不意味着任何公法性的后果。
(二)关于合同绝对无效
合同绝对无效之“任何人皆得主张其为无效”,此处的“主张”有其特定的含义。在合同因标的违法而无效场合,不适用“禁止反言”的原则。同时,合同绝对无效并非皆因合同标的违法所引起,其他原因亦可导致合同绝对无效。
(三)关于合同相对无效
合同相对无效的类型只有“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型”这一种,具体包括通谋虚伪表示、单独虚伪表示、为相对人所明知者和受欺诈而为的意思表示被撤销这三种情形下的合同相对无效。
近年来被学界所广泛论及的“仅特定人可主张型”的合同相对无效,其所谓“合同”实指处分合同而非债权合同,因此该类型的合同相对无效在我国《合同法》中难以立足。
[1]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2]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陈小君.合同法学[M].北京:高教出版社,2009.
[5]韩松.合同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6]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英]P.S.阿狄亚.合同法导论[M].赵旭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8]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9]王利明.合同无效制度[J].人大法律评论,2012(1).
[10]杨士海、陈灿平.无效合同中的恶意抗辩之司法应对[N].人民法院报,2012-04-05.
[11]中国法院网.禁发言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EB/OL].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 /2003/09/id/8314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08-25)
[12]王轶.合同效力认定的若干问题[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5).
[13]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4][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Ⅰ•民法总则[M].东京:成文堂,1995.
[1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6]德国民法典[M].郑冲,贾红梅,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7]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朱 丹)
On the Invalidity of Contract
SUN Wenzhen
(School of Law and Business, Wuhan Technology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205)
The invalidity of contract only implies that contract exercises no legal binding force upon contract parties, not implementation of contract or bearing any public law consequences. The conception of invalid contract at present can cover neither all types of absolutely invalid contract nor relatively invalid contract. The “propose” in“Everyone proposes the invalidity of contract” has its specific implication. The relative invalidity of contract is limited to the type of “Do not run against a bona fide third party”. The relative invalidity of the other types of contract discussed in academic circle is not the real-sense relative invalidity.
invalidity of contract; relative invalidity of contract; contractual legal binding force
F123.16
A
1009-8135(2015)01-0137-08
2014-11-03
孙文桢(1966-),男,陕西富平人,法学博士,武汉工程大学法学教授、硕导,民商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民商法学和法理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2YJA820064)、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yjg2014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