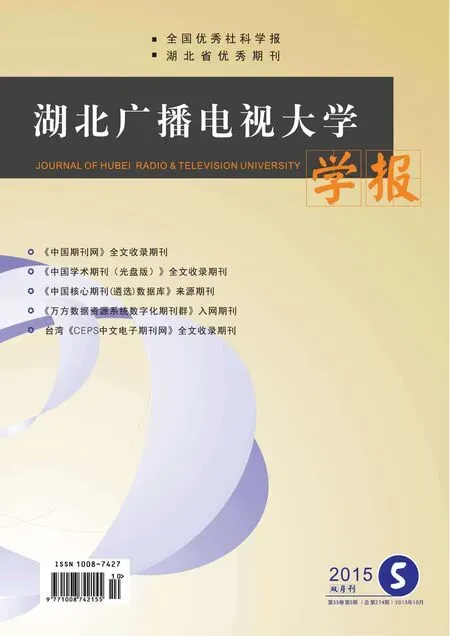《论语》“天命”概念新解
王凯立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论语》“天命”概念新解
王凯立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天命”是《论语》甚至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但因其含义复杂,故难有确解。在《论语》中,“天命”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的立体概念,它涵摄了“整体面向的含义”与“个别面向的含义”,其中“个别面向的含义”又包含着“无待向度”与“有待向度”。唯有分别理清这些方面的“天命”含义,我们才能整体而准确地把握住《论语》中的“天命”概念。
天命;整体面向的含义;个别面向的含义;有待向度;无待向度
《论语·为政》记载了一段孔子的生命独白: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此为了解孔子的重要材料,亦为了解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材料。”[1]248其中,“天命”的概念关涉着孔子生命境界的关键性转折,是把握孔子思想甚至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天命”的概念甚是难解。在以往汗牛充栋的注解中,各个注家都给出了自己对于“天命”的解释,但相互之间难以融通、争论不休,而无定论。基于此,笔者试图重新分析“天命”这一概念,并整合以往的注解以期提出该概念较为全面而合理的解释。
一、“天命”概念的两个面向
对于“天命”或“命”的解释,①首先需要区别出“整体面向的含义”与“个别面向的含义”。就前者而言,“天命”是一个指涉整体世界的客观概念,此时“天命”的概念是就其自身而言的,只存在“天”之“命”的纯粹意向性,而不特别针对于某个特殊个体或个别现象,或者也可以说,“天命”整体面向的含义具有普遍性,且正因其有普遍性,所以能适用于任一特殊个体或个别现象;就后者而言,“天命”是一个指涉特殊个体或个别现象的主观修正的概念,此时“天”之“命”连接了具体的对象,“天命”的概念落实在不同个体与不同境况中,且因个体德行修为与人生遭遇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含义,我们也可以认为,“天命”“个别面向的含义”是“整体面向的含义”落实在特殊境况中而呈现在不同个体心灵感受中的具体含义。笔者认为,这一含义面向的分疏对于“天命”的理解是必要的。因为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与客观“天命”相互作用的世界,这便决定了“天命”概念有一个对于任何个体和现象都普遍适用的客观维度;而另一方面,“天命”对于不同的个体显然有着不同的意义,“一个颓废怠惰者所说的‘命’,与一个志士仁人,当他力竭声嘶时所感到的‘命’,在内容上完全是两回事”[1]251,并且“人在处不同之位,于不同之时,有其不同之遇合,而人之义所当然之回应不同,而其当下所见得之天命亦不同。”[2]117这便决定了“天命”概念有一个针对于特殊个体与个别现象的主观修正的维度。
以上关于“天命”概念两个面向含义的分疏有着一定的历史依据。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中指出,“天命”的观念“可以被看作是远古宗教、政治发展史上的一种残余记忆,折射出地上人王(无论规模大或小)通过巫师的中介,垄断了与‘帝’或‘天’的交通。”此时,“地上人王与‘帝’或‘天’的交通是从集体本位出发的;他代表的不仅是整个王朝,而且是所有治下之‘民’。因此‘天命’也必然属于集体的性质,不是‘帝’或‘天’给人王个人的赏赐。”但到了孔子时代,“天命”已不再由帝王垄断,而是走向了个体化。每一个人都可以与“天命”相感通,“天命”成为了个人的心中之物。[3]37-39事实上,个体化的“天命”仍然会保留以往集体或说整体的性质,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决定了《论语》中的“天命”概念将具有“整体面向的含义”与“个别面向的含义”,同时还塑造了孔子关联这两个面向的思维模式。于是,“天命”在《论语》中便不是一个单一的平面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的立体概念。
“天命”这一概念之所以难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往的注家混淆了上述两个面向的含义,导致各种解释纠缠不清。以下笔者就将以此含义面向的区分为架构,结合以往诸家的注解,简要地对“天命”的概念做一番梳理。
二、“天命”整体面向的含义
在整体面向的含义上,“天命”就是继承古代宗教传统的天之意志。《论语·宪问》记载: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根据此句的句意以及以往诸家的注解,句中的“命”可以直接视为“天命”的缩写。句中另一重要概念“道”,乃“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之“道”,它可被视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轴心突破”后所找到的另一个“天”,[3]32-37是指涉整体存在的价值、意义之源。孔子以“命”来规定“道”之行废,便凸显了“天命”整体面向的含义。“公伯寮其如命何”一语便暗示了“天命”在整体面向上是个人在客观上无法改变的天之意志。
除了《论语》以外,我们目前可以找到的关于孔子天命观的最早理解是在《墨子·非儒》中: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
在墨子看来,孔子的“天命”在整体上就是天的绝对意志,个体的人只能顺从这种意志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它,“天命”对个体而言是宿命。史家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辩证》中同样认为“《论语》书中明载命定之义,墨氏攻之,正中其要害。”[4]550事实上,对于个体是宿命论的天命观推至“天命”整体面向的含义便是天之意志,它继承了三代宗教传统中对于“天命”的理解,因此“孔子所信之天命仍偏于宗教之成分为多。”[4]551考虑到孔子是三代文明的继承者②,以上说法所揭示出的孔子天命观的传承性无疑是合理的。周会民在批评徐复观将孔子的“天命”解释为“道德性之天命”时,同样强调了要注重中国文化的传承性。[5]然而,徐复观的“道德性之天命”是特针对于孔子而言,属于“个别面向的含义”。在“整体面向的含义”上,徐复观同样认为:
“天命”的“命”字所包含的意义,我们若把许多枝叶的解释暂时置之不问,就三千年来使用此字的实际内容来说,可以归纳成这样的一个定义,即是,在人力所不能达到的一种极限、界限之外,即是在人力所不能及之处,确又有一种对人发生重大影响的力量,这便是命。[1]251
这一解释与周会民的理解基本相同,只是周会民更进一步突出了这一含义所带来的宗教性意义,并且认为这种宗教性是传承于孔子以前的宗教信仰。[5]史家余英时在考察了大量史料后得出了与之相似的结论,他认为孔子继承了巫文化的“天命”概念,并由此发展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考虑到孔子对于鬼神的怀疑态度,故孔子的“天命”似乎不是前代观念中的“人格神”,而毋宁将其视为一种超越于宇宙万有之上的精神力量。[3]42-48
由此可见,孔子的“天命”在整体面向的含义上就是天之意志,这种天之意志可能并非是“人格神”的形式,而是一种人力所不能及的超越于宇宙万有之上的精神力量,并且这一含义还包含着孔子继承并发展的宗教性维度。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天命”整体面向的含义落实在具体情境中,并不是对每一个特殊的个体都意味着如墨子与傅斯年所说的宿命论。在个别面向的含义上,“不是‘命’字的本身来决定它的意义,而是各个不同层次的人格来决定命的意义。”[1]251于是,对于“天命”在个别面向的含义上的分疏,以及阐明它与“整体面向的含义”的系统性关系是解开孔子“天命”概念之谜的关键。
三、“天命”个别面向的含义
“天命”个别面向的含义在《论语》中特别针对于孔子及其所遇境况而言,其含义相对比较复杂。刘宝楠在解《论语》“知天命”章时言:
“天命”者,《说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书·召诰》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哲与愚对,是生质之异,而皆可以为善,则德命也。吉凶、历年,则禄命也。君子修其德命,自能安处禄命。[6]44
刘宝楠将“天命”划分为“德命”与“禄命”,这不仅符合《论语》的语境,而且其解释较之其他古注还融通许多,故程树德认为“刘氏释天命最为圆满,可补诸家所不及”[7]97。陈红杏在比较研究了诸多关于“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章中“命”的古注和近代注解后,吸收了黄克剑先生《论语疏解》中的思想,认为“天命”的概念“同时涉及人生的无待向度和有待向度,并在承认有待向度的独立性的前提下以‘无待’烛临‘有待’、引导‘有待’;或然性意义上的‘命’意识在这里依然若隐若现,只不再占居主导地位。”[8]可以说,陈红杏这一“无待向度”与“有待向度”的划分比刘宝楠更进一步,她真正完成了“天命”在“个别面向的含义”上的解释架构。
在“天命”的“无待向度”上,“天命”并不是与孔子(个人)相对待的客体,而是孔子在与整体面向的“天命”相互感通中所意识到的自己的应然之责。此时孔子秉承“天命”,与“天命”浑然一体,天人合一。在这个意义上,“天命”就是刘宝楠所说的“德命”。
要深刻理解“天命”无待向度的含义,需要借助郝大维(David L.Hall)与安乐哲(RogerT.Ames)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所揭示出的孔子宇宙论图式。他们认为,孔子的宇宙论可以称为“点域论”,这是一种勾勒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全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个别是一个焦点,它既为语境(它的场域)所限定又限定后者。域是全息性的,也即,它的建构方式使得每一个可识别的‘部分’都包含整体。从根本上说,一个既定部分与其整体会在场域被以某种特别强烈的方式聚焦时变得完全一致。根据这一模式,‘德’指称确定某一可识别‘部分’(如一个人)诠释‘整体’(即其社会环境)的模式的独特关注强度。……‘天’是‘德’(作为其确定关注点)的万物之域。[9]293
在历史上,正是上文提到的“天命”个体化转变铸成了孔子这一宇宙论图式,尽管孔子本人并未明确提出,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一思维模式深深贯穿在孔子的思想中。明确了这一点,对“天命”在无待向度上的理解便有了坚实的基础: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天”在这里具有“天命”整体面向的含义,它落实在孔子身上而成为孔子之“德”。此时,作为个体面向的“德”与整体面向的“天命”相互感通,个体包含着整体,整体渗透在个体中。孔子在修德学习的进程中,随着个体面向的“德”逐渐实现,它与整体面向之“天命”的关系也逐渐明晰。当孔子在某一时刻(五十岁)体知到自己之“德”所包含的天之意志时,一种应当承担“天命”、实现“天命”的责任意识随之激发。这样,孔子未来行为的理想方向也随之明确,个人所体知到的“天命”意涵随之产生。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斯文,即文王之文章也。”[10]211孔子认为自己因天之意志承接了周代文明(事实上也是三代文明),同时这种承接也就是天之意志将传承周代文明于天下的职责“命”之己身。余英时认为,“‘文’即‘道’的载体”,故此处的“‘文’字也可以‘道’字代之。所以分析到最后,孔子的‘天命’非他,传‘道’于天下是也。”[3]45这样,孔子在“天命”“个别面向的含义”中于“无待向度”上便激发出了一种带有天职观念的责任感。
在“天命”的“有待向度”上,“天命”是与孔子(个人)相对待的客体。具体而言,“有待向度”的“天命”就是外部环境在孔子的具体境遇中对他个人行为的作用,这一概念接近于朱熹所说的“气命”。当然,刘宝楠所说的“禄命”也包含在其中,但“禄命”仅指外部环境在政治穷通方面的作用,它并不是有待向度含义的全部。“天命”在有待向度上有着比“禄命”更广的含义。
“天命”在有待向度上涉及人的生死、富贵、身份、运气等,在相当一部分的注解看来,这些内容在人的生活中似乎总是突如其来,好似一种人力无法抗拒的或然性;但同时,正是因为人力的无法抗拒所以呈现出了无可选择的必然性。“天命”在有待向度上的这种人力无法抗拒性给个人行为带来的是一种限制性,但需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限制在它的另一面却构成了个人行为的外部条件。在这种限制性与条件性的张力中,那种或然性或者必然性却隐隐透露出一种向主体行为敞开的倾向性。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借助倪培民在《孔子——人能弘道》一书中提出的“同时性原则”。倪培民认为,中国思维中特有的“同时性原则”是“以事件之间规律性的同时共生来解释世界”,而与之不同的西方思维中的“因果关系”则是“通过事件以同样的时序先后重复发生来解释世界”。前者是横向的平面性思维,后者是纵向的线性思维。[11]34外部环境与个人的同时共生关系产生出了事态未来发展的倾向性,个人作为这种倾向性的构成要素,完全可以主动地调动外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来实现这种倾向性中的最好结果,甚至改变这种倾向性: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很多学者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语作为“天命”或然性或者必然性的例证,认为在“天命”面前人力完全无能为力。然而,郝大维与安乐哲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有无兄弟对于司马牛而言似乎是一个肯定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子夏的话却恰恰说明了“一个无兄弟的人可通过重新定义何谓有兄弟(即通过改变它的意义和指涉的基础,即其‘名’)来改变这一使得他无兄无弟的状况(他的命)。”[9]265这样,司马牛原来看似无可改变的决定性事实就化为了“敬而无失”、“恭而有礼”的行为方向,原来看似人力无法抗拒的或然性或者必然性在个人的创造作用下变成了向主体行为敞开的倾向性。
四、结论——系统性的“天命”概念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论语》的“天命”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概念,它包含了“整体面向的含义”与“个别面向的含义”,而在“个别面向的含义”中又包含了“无待向度”与“有待向度”。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且具有系统性的立体概念,它综合地影响着孔子的情感、观念与行为。
在“天命”整体面向的含义上,孔子在“天命”个人化的历史进程中继承了“天命”乃天之意志的传统含义,虽然他有理性主义的“天命”去人格化倾向,但“天命”在整体面向上对于孔子而言仍然是一种人力所不能及的超越于宇宙万有之上的精神力量。正是对这一股力量的信仰开启了孔子特有的宗教取向,余英时指出孔子这种独特的宗教取向是他传“道”使命感的源头。[3]49孔子相信“天命”在整体面向上代表了价值源头、意义的根源、行为的方向,所以他才会认为君子应“畏天命”(《论语·季氏》)。
孔子从“天命”整体面向的含义中所引出的宗教信仰使得他有种“天命”在身之感,这样,“天命”个别面向的含义于无待向度上便得以生成。这时,“天命”对于孔子来说就是传道于天下的责任感与天职观念。由于这一主观修正的“天命”概念与孔子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故孔子的“天命”在身之感是伴随着对天之意志(天命整体面向的含义)的体知而形成的。这一体知的过程包含着在“点域论”预设下个人德性的培养,故孔子五十岁方“知天命”(《论语·为政》),唯有个人下学的工夫方能上达知天,使得个人之德成为透视着整体天之意志的焦点。正是这种“天命”在身之感的形成,使得孔子在五十岁后开始了周游列国的从政传道历程。当然,无待向度的“天命”在现实中将会遇到有待向度的限制性作用,但即便如此,“‘天命’在承担者那里则将召唤出富于崇高感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强调以‘无待’穿透‘有待’。”[8]与此同时,“天命”在有待向度上的限制性给个人的行为带来了条件性,这时“天命”的或然性与必然性在“同时性原则”中化为了主体行为的倾向性,个人对这种“同时性原则”的参与意味着“天命”在有待向度上并不是人力全然无法抗拒的宿命,个人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动自己的能动性去争取这种倾向性中的最好结果,甚至改变这种倾向性。需要指出的是,个人对于“天命”有待向度的现实处理是一种实践智慧。在“无待”穿透“有待”的实践过程中,行为主体需要清楚地体认到“天命”于有待向度上的限制性与条件性,更需要在这种限制性与条件性的张力中明白由“同时性原则”所开启的倾向性在何种范围内是人力所能控制与改变的,以及找到这种控制与改变的方式。这种要求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就是一种“不惑”的境界,孔子说“知者不惑”(《论语·子罕》),“不惑”正是一个智者的境界。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可见孔子对于天命的体知与承担本身就包含了智者的不惑状态。正是这种实践智慧,使得孔子能够对外部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下调动一切外部的积极因素促使自己的传道理想得以实现。
[注释]
①如果将“天命”或“命”的含义严格区分(倪培民、刘殿爵),将会碰到很多解释上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论语》中“命”有时候可以直接视为“天命”的缩写,这种用法在与《论语》差不多同时期的著作中也可找到。在有些情况下,“命”似乎又与“天命”显示出一些区别,但这些区别只是指涉个别现象与指涉整体现象的区别。在本质上,二者应该被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着的整体概念。(参见郝大维、安乐哲著,何金俐译:《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
②在《论语》中,孔子表面上是要继承周代文明,实际上,孔子是把周代文明视为积淀了殷商两代文明甚至周以前所有文明的人文成果。此由《论语》中如下两句话可知: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继承周代文明事实上也就是继承三代文明。
[1]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一)[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3]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5]周会民.孔子“知天命”之本义及其途径探索——对徐复观《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一文的再思考[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1 3(5):1 7-2 7.
[6]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4.
[8]陈红杏.“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章“命”意识辨证——兼谈“五十而知天命”[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55-61.
[9]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M].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皇侃.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倪培民.孔子——人能弘道[M].李子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张锐)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of“Decreesof Heaven”in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
WANG Kai-li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
“Decrees of Heaven”is an importantconcept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even in the Chinese culture.But its meaning is complex,and it is too difficult to interpret the conceptaccurately.In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decreesof Heaven”is a stereoscopic conceptw ith systematicness.Itembraces“themeaning of theaspectofwholebeing”and“themeaning of theaspectof individualbeing”,and“themeaning of the aspectof individualbeing”subsumes“the dimension of subject-objectdichotomy”and“thedimension ofsubject-objectunity”.Theclarificationof themeaning of“decreesofHeaven”helpsusgrasp the conceptof“decrees of Heaven”in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 integrally and accurately.
decrees of Heaven;themeaning of the aspectofwhole being;the dimension of subject-objectdichotomy;the dimension of subject-objectdichotomy;the dimension of subject-objectunity
I 2 0 6.2
A
1 0 0 8-7 4 2 7(2 0 1 5)0 5-0 0 4 6-0 5
2 015-06-07
厦门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行与知——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2015X0045)的阶段性成果。
王凯立,(1 9 9 4-),男,浙江义乌人,厦门大学2 0 1 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比较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