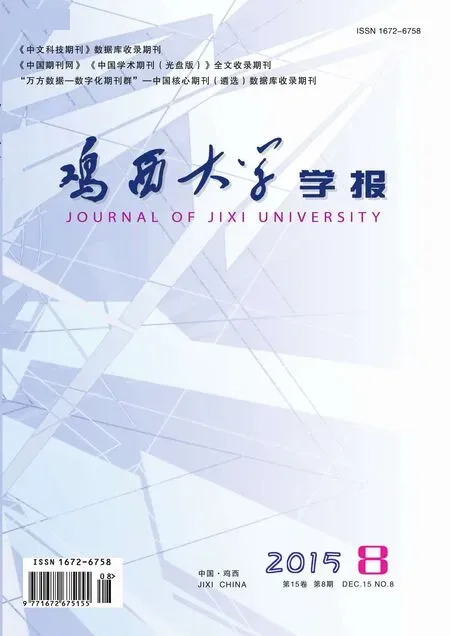网络流行语的对话主义解读
——以“任性”为例
李丹丹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重庆400031)
网络流行语的对话主义解读
——以“任性”为例
李丹丹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重庆400031)
网络语言的流行现象体现了人类生存的本质——对话。前人多从社会心理、语言特征等角度考察网络语言得以流行的原因,少有人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其加以审视。以网络流行语“任性”为例发现,人们对网络流行语的热忱是由人类渴望对话这一存在本质决定的。对话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网民之间的对话,政府与人民的对话,文本之间的对话。本研究意在为网络语言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网络流行语;“任性”;巴赫金;对话主义
“任性”是近日来最火热的网络流行语之一。2014年4月,各大晚报对1名男子明知受骗仍然给犯罪分子汇款的事件进行了报道。报道称,该男子早知道对方是骗子,但仍然掏光家本给对方汇款,原因竟是他“就是想看看,他们究竟能骗我多少钱!”此事件一经曝光,广大网友一方面称佩服男子的勇气,另一方面也调侃男子“有钱就是任性”。于是,“任性”一词开始走红网络。该词本是用来调侃有钱人令网友大跌眼镜的做事风格,随后网友们发挥想象力,创造出许多“任性体”,如“成绩好就是任性”、“年轻就是任性”、“携氧从不降价,效果好就是任性”等等。2015年3月,在两会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借用“任性”一词表达政府意志,凤凰网、人民网等网站纷纷加以报道,于是“任性”渐红于各大网络平台。至此,“任性”一词突破了网络流行语的界限,跻身于政府官方发言之中,由此更掀起了一场“任性”风。
“任性”一词为汉语固定词组。《现代汉语辞海》将“任性”释义为:“放任性情,形容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例:他太任性,谁说的都不听。”《近代汉语大词典》对“任性”一词的释义为“由着自己的性子不加约束。《红楼梦》第十九回: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荡驰纵,任性恣情,最不喜务正。”该词一直存在于汉语茫茫词海之中,直至近日才成为网络新宠。那么如“任性”一类的网络流行语现象蕴涵着怎样的哲学命题呢?研究发现,网络语言的流行现象源于人类渴望对话的存在本质,体现了深刻的对话精神。
一 对话主义
对话主义是前苏联著名学者巴赫金留给人类的精神财富。巴赫金在美学、文学、伦理学、语言学及哲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而对话思想一直贯穿于他各大作品的始终,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对话思想其实并不为巴赫金始创,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对话,如柏拉图与弟子通过对话形式阐释哲学思想。而巴赫金却将对话思想进行了独特的阐释,他运用对话智慧开启了人类求真之大门,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人文科学的各大领域。
1.对话形式与对话主体。
巴赫金的“对话”已经不再仅仅指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话语,而是抽象为一种哲学理念。在他看来,对话关系存在于一切可以用来表达含义的事物之间,它包括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言语相互作用,其形式既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具有对话性,这一特性早在人类学会用肢体语言交流的时期就已经存在。对话的主体可以是人物与人物,如主人公与主人公,作者与主人公,读者与主人公,听者与说话者;也可以是同一文本的内部结构之间;也可以是不同的文本之间。
2.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本质。
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一直思考的哲学命题。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提出“人是万物尺度(Human Being is the Yardstick of All Things on Earth.)”;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I think,therefore I am.)”;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巴赫金却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关系决定着人的存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结束、也不应该结束。”[1]人活着就要与他人交流,与他人对话。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基本工具,人们通过语言符号进行信息交换。即使丧失了言语能力的人也会通过肢体语言或文字符号来表达自己并让他人理解自己。人是社会动物,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不存在绝对孤立
的人,也不存在没有对话的社会。
二 “任性”的对话主义解读
巴赫金对话主义认为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网络用语的快速发展,不但有语言内部原因,更是人类渴望对话交流这一人类本质驱动下的必然结果。对话精神充当了推动“任性”一词快速发展的推手,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文本之间的对话,政府与人民的对话,网民之间的对话。
1.文本之间的对话。
“任性”一词的广泛使用也体现了文本与文本的交流对话。以“X,就是任性”为例,X在此句型中充当的句法成分为条件状语。通过对X进行语义分析发现,X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语义,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条件状语,二是状语中的形容词或者副词。条件状语的对立主要表现为“有y,就是任性”和“没有y,就是任性”这样的形式里。一面是表达拥有某种物体,并且此物能给说话者带来某种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利益。当说话者拥有某物,可以为说话者达成某种目的提供了便利或途径,因此说话者可以按照自己性情行事!例如:“有(钱/爱/时间/车/技术/Wifi),就是任性!”有钱,可以买想要的物质;有爱,那么生活就温馨甜蜜;有车,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技术,就有了谋生的本钱;有Wifi,就能够享受网络带来的乐趣与便利。另一面是表达说话者没有某物,并且说话者因为不能拥有此物而给说话者带来某种负面的影响,这里的“任性”已经慢慢失去了贬义的调侃意义,更多的是说话者用一种温和,幽默的方式缓解自己没能拥有某物的尴尬。例如:“没有(朋友/办法/心情/对象),就是任性!”在说话者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希望有朋友互相帮扶、有解决难题的办法等等。没有这些就自然显得孤单、窘迫,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是通过采用“任性”这一大众化而又带有自嘲意味的词汇,增加了一种轻松、有趣的气氛。第二种是副词或形容词的语义对立,表现为“漂亮/幸福/年轻/可爱,就是任性!”和“长得丑/胖/矮,就是任性!”此类词多是对人物外貌的评价性词语。将“X,就是任性”中蕴涵的条件关系补充完整,即为:(如果)“X”,(那么)“就是任性!”可以视为“X”为“就是任性”提供了不同条件或语境。那么为何如此对立的语境(条件)都可以到达同样“任性”的情感状态呢?
这是因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是本质存在的,而这种对话以文本差异性为前提。看似语义矛盾的X,实质是在保留各自差异性的基础上,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到达“任性”的最终情感状态。巴赫金认为,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话关系是以承认差异性或“他者”为前提的。没有“他者”,就不可能产生对话。这就是他说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一个声音是无法证明自己、无法生存的,只有通过其他不同的声音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为他人理解。正是因为有差异性的存在,才保证了对话和应答的可能;也正是在反复的对话和应答中,人类的生产活动才能进行下去。“他者”的定义很广泛,“一切离开了主体而存在的,不论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他者。”[2]这里不同语境X可看作“他者”。正是因为X为“任性”提供了不同的语境,使得不同语境之间相互映照,才使网民们在相互体验、感受的过程中,实现交流目的。在肯定差异性的同时,巴赫金还提出对话的相对性。在这里,“相对性”主要体现在事物的存在不是绝对性的,而是相互包容理解的。“X”虽然为不同语境,但是它是处于同一平面的,并无高低好坏之分。无论是外表出众还是平凡,体现的是网民对美丽的向往,而非对平凡的贬低,只是“温和的嘲弄”。正是在这种开放,包容和理解的话语鼓励下,广大网友才有了不断创作的动力,由此衍生出一系列“X,就是任性”文本,使得网络语言呈现百花齐放的势头,增加了社会语言文化的多元性。
2.政府与人民的对话。
“任性”之所以赢得如此高的关注率,原因之一在于高层政府官员的使用。2015年3月2日,在两会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回答香港卫视记者关于反腐问题时,答了一句“大家都很任性”,至此“任性”一词的英文翻译引起广泛热议;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权不可任性”赢得喝彩;同日,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在谈及发展战略之时,借用了流行语“也不能那么任性了,否则靠什么可持续发展?”国家领导人的使用为“任性”的盛行进一步提供了动力。
任何对话都体现着对话双方的相互关系。在阶级专制时代,统治阶级尊崇的是独白话语,他们使用正式严肃的语言塑造自身权威。例如,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诺曼人成为英国统治阶级,为了彰显统治阶级的权威,诺曼人将法语作为英国上层贵族的语言,而英语则沦落为下层语言,由此形成了英语双重词汇系统。如pork与meat,本都是指“猪肉”,但是统治阶级吃的是经过精心加工与挑选的pork,而下层人民吃的是又脏又臭的meat。如此便通过双重语言系统划定了官与民的界限,彰显官贵民贱。特别是在封建专制的朝代,这种独白式的话语成为了社会话语的主导形式。例如中国封建帝王自称“朕”、“死”称“驾崩”;禁止平民百姓使用与皇帝同音的姓与名;天子的话就是圣旨,无人敢违。在这种独白专制的社会里,人民没有发言的自由,自由的对话被高高在上的权威扭曲成了惟命是从、唯唯诺诺的形态。然而,这种为自己树立绝对权威的统治思想,禁止民众拥有自己的思想,拒绝与民众思想的交锋与摩擦,终究走向了灭亡。
巴赫金指出,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只有擅于与人民群众对话,敢于与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交锋的政府才能长久生存发展。“一切有文化的人莫不具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人群,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民,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中,不要有任何的距离、等级和规矩;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3]只有
鼓励民众思想,倡导与民众积极对话的政府,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主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都是政府亲近民众、进入民众的举措。中国高层官员对“任性”的使用,表明了政府尝试用大众、时尚的语言加强与人民的对话,缩短政府与群众的心理距离。这有利于打破政府官员严肃、疏远形象,推翻横隔在官与民之间的高墙,同时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传达政府意志,减少人民群众的心理负担,使国家政策更易实施。
3.网民之间的对话。
巴赫金指出,“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必须是在同他人另一个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链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1]人只有同他人积极交流,敢于与他人思想不断交错和摩擦,才能彰显自身思想的价值。“任性”盛行于网络实际是人们渴望交流和不断加强对话的结果。网络技术的发达为人们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拓宽了人们相互对话的渠道。在“任性”一词走红的过程中,“任性”一词语义有了微妙变化,其渐渐褪去了“贬低”的外衣,而更多的是一种轻松幽默的情感表达。年轻人求新求异,渴望交流,倾向于使用“任性”在温和、娱乐的氛围中表达思想,抒发感情。这种渴望对话的现象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
“任性”一词走红于各大社交平台有其深厚的社会土壤: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实力增长迅速,但是由于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有钱就是任性”表现了人们对富人的揶揄。虽是戏谑之言,却能非常恰切地用来评价当今社会一些有钱人令人大跌眼镜之事。如在海外奢侈店扫货的中国大妈,她们富而不贵,只要高兴就可以挥金如土,“任性”确实是对其消费风格的生动概括。网民通过“有钱就是任性”调侃富人,实现文本之外的“潜对话”,达到全民参与到批判丑恶的社会现象的过程中来。同时,在一起使用“任性”一词批判社会丑恶时,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达到了一种你我平等的心理慰藉。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鸿沟,映衬了一小部分“高富帅”的安逸闲适,也让广大“矮穷挫”心理失衡。“任性”二字带着几分不浓不淡的责怪,听上去极像一位家长对子女的温柔呵斥,让那些没钱的“屌丝”俘获了一种辈份上的优越感,从而达到一种奇特的心理平衡。
三 结语
交往对话的哲学精神贯穿于巴赫金大部分作品之中,他将对话上升为哲学命题,聚焦于考察人类的存在本质,阐释了人的生存价值。“心灵的外壳没有自己的价值,要靠他人施恩和爱抚。”[3]对话性贯穿于人类活动的始终,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交流和对话;只有在同他人的交往中,人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得以体现。网络语言的流行现象体现了人类渴望交往的存在本质,无论是文本,政府,还是网友,他们无不借用网络流行语积极参与到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社交平台上来。正是人类渴望交往的本质才促成了当今网络语言“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也正是人类拥有这种表达自己的冲动与勇气,才铸成了人类如今灿烂的多元文化;也更是人类敢于与不同思想进行切磋交锋的对话精神,使人们能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1]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三联书店,1994,19.
[3]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A Dialogistic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et Popular Words
Li Dandan
(Graduate School,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y University,Chongqing,Sichuan 400031,China)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popular words is actually resulted from the dialogistic human nature.Former studies usually explore the reasons of Internet popular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 or linguistic features rather than philosophical thinking.Taking the Chinese word Renxing as a case study,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dialogistic spirit in Internet popular words can be traced in three aspects:dialogue among cyber citizens,dialogu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ts people and dialogue among texts.
Internet popular words;caprice;Bahktin;dialogism
H030
A
1672-6758(2015)08-0139-3
(责任编辑:郑英玲)
李丹丹,硕士,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哲学。
Class No.:H030 Document Mar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