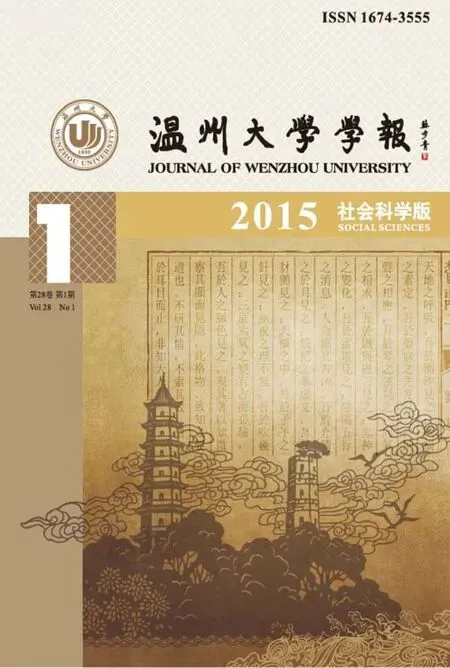《诗经•国风》声音意象研究
张明明,罗筱玉(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诗经•国风》声音意象研究
张明明,罗筱玉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诗经·国风》中声音意象的运用广泛而多样,不仅包括对自然界风雷泉、动物界鸟兽虫禽等声音的描写,也包括人类社会劳作、祭祀等声音勾勒。这种大量的声音意象描写是在自然与社会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不仅反映出先民对以声音为中介的意象审美感觉的创造,同时也蕴含着丰富且具体的社会文化意蕴,对整个后《诗经》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国风;声音;内涵;成因;影响
《诗经》在声音描写方面十分丰富,但历来学者对其研究颇少,目前只有马凤华、刘爽、谭德兴等人的文章专门涉及《诗经》中的声音意象[1-3],但仍不够全面、细致、深入。马凤华的文章将《诗经》中的部分声音意象作了爬梳,谭德兴选取了《诗经》中的某些动物声音而展开研究,刘爽从《国风》中的音声描写着手,但未对其文化内涵和影响作进一步考察。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拟对《国风》中涉及的众多声音意象进行较全面的整理,并探究其蕴含的社会文化及对后世的影响,以期为《诗经》研究添砖加瓦。《国风》中涉及声音意象的共42篇,整理如下:《邶风》10篇、《郑风》5篇、《周南》《召南》《秦风》各4篇、《齐风》《陈风》《豳风》各3篇、《魏风》2篇、《卫风》《王风》《唐风》《桧风》各1篇,作为联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纽带,这些声音不仅是对远古自然环境的再现,而且反映了商周时代的历史面貌和生活状态。本文即从《国风》中有关自然、动物、人类社会等三方面的声音为视角展开研究,探索其审美取向和所承载的文化习俗及成因和影响。
一、自然界的声音意象及文化内涵
《国风》中有11篇涉及对自然界声音的描摹,笔者将其分为四类。雷声:殷其雷(《殷其雷》)、虺虺其雷(《终风》)。风声:凯风自南(《凯风》)、习习谷风(《谷风》)、北风其喈(《北风》)、匪风发兮(《匪风》)、一之日觱发(《七月》)。雨声:风雨凄凄(《风雨》)。水声:毖彼泉水(《泉水》)、北流活活(《硕人》)、方涣涣兮(《溱洧》)。这四类声音前都用了不同声调的拟声词,正如施向东所言“不同声调的字,在模拟声音上应该有不同的价值。”[4]如写雷声,《殷其雷》用“殷”,《终风》用“虺虺”。“殷”描写了阴阳相薄、积郁既久之后突然爆发的惊雷声。而“虺虺”则指“雷将发而未震之声”[5]18。两词将不同强度下的雷声区别开来。再如写风声的不同,《北风》用“喈”,即“风急的样子”[6],凸显其“速度”;《谷风》用“习习”,它有多种解释,或认为“习习,谷风和舒貌”[5]21,或认为“谷风指山谷吹来的风,通常强度很大”[7]340,笔者认为后者更合理,因为谷风的大气环流较强,“习习”正是形容暴怒之风,突出其“力度”;《匪风》用“发兮”,《七月》用“觱发”,也都是为突出风之“强度”。《国风》中也多处写水声。如《泉水》用“毖”,摹拟了泉水迸出时所发出的声响。《硕人》用“活活”,“活活”作为入声字,因有塞音韵尾,所以适合模拟持续的间歇的声音,借流水之声以定愉悦基调,巧妙建立起人的感受与自然声音之间的联想。《溱洧》中“涣涣”,写出了水流的欢快情态。总之,《国风》中描写自然界声音往往是运用一些拟声词,夏传才认为拟声词“指的是用象声词,使语言具体形象,给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实感”[8],生动刻画了彼时彼景。
《国风》中诸多对自然声音的描摹不仅是一种文学表达方式,还是一种浑然蓬勃的诗性的自然刻画,寄托着先人们各种复杂的感情。
如《殷其雷》,《郑笺》曰“殷”为“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地,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然发声于山之阳”[9]99。用雷声之大,引出“何斯违斯”,从而将妇人思夫的感情推向高潮,表达“闵其劳而望其归”[9]100之情。这里将雷声之大与君令之威相联系,体现了奴隶社会君主至高无上的思想。《北风》一诗,程俊英说“是人民不堪卫国虐政,号召朋友共同逃亡的诗。”[10]“喈”既写风之迅疾凛冽,又隐含了逃亡之人对暴政的厌恶、对昏君的谴责。这里“风”成了暴政、残暴的象征。此外,雨声被视为“夫妇欢会的征兆与预感”[11]279的隐语,《风雨》便是例证,它用潇潇雨声渲染思妇盼夫的心情,所以张启成说雨声是“有关爱情与婚姻的象征”[11]279。《国风》中水的声音,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王政说“《诗经》中,水往往喻比婚爱或者婚媾”[12]199。《泉水》是“诗中女子远嫁异国,思归母家而不得,故其以流出去的泉水自喻,伤其怀抱,叹咏成诗。”[12]202马瑞辰说:“诗义盖以肥泉之异流,兴女之各嫁一方。”[13]所以“思卫者观其毖流远去,亦谓其流必将入淇,比喻女子远嫁终不得复归于卫。”[14]这里,泉水同样和先民的婚姻习俗紧密相连。总之,这些自然界的声音传递了先人复杂感情,代表了不同风俗。
二、动物界的声音意象及文化内涵
《国风》写到动物声音的共16篇,主要以鸟、虫、兽等为主,笔者将其分为四类。鸟类:关关雎鸠(《关雎》)、其鸣喈喈(《葛覃》)、睍睆黄鸟(《凯风》)、下上其音(《雄雉》)、雝雝鸣雁(《匏有苦叶》)、肃肃鸨羽(《鸨羽》)、交交黄鸟(《黄鸟》)、有鸣仓庚(《七月》)、鹳鸣于垤(《东山》)、予维音哓哓(《鸱鸮》)。虫类:薨薨兮(《螽斯》)、喓喓草虫(《草虫》)、虫飞薨薨(《鸡鸣》)。兽类:无使尨也吠(《野有死麕》)、卢令令(《卢令》)。鸡类:鸡鸣喈喈(《鄘风》)。
从分类可看出,鸟类的声音数量最多。据刘立志统计“《诗经》鸟类有三十多种”[15]150。先民喜欢鸟类,古代青铜器上多刻有鸟纹便反映了这点。《国风》中有大量拟声词,来再现鸟的鸣叫。《关雎》用“关关”形容“关雎”①“关雎”一词, 历来解释纷多, 有人认为是野鸭子, 本文选取“鸠鸟”说法.的和鸣。清人胡承珙说“‘关关’可能是鸠鸟雌雄交颈配合时发出的声音,所谓雌雄情意至者也。”[16]这里“关关”一词写出了鸠鸟相和对唱的自在情景。《葛覃》写黄鸟“其鸣喈喈”,“喈喈,和声之远闻。”[9]18这种婉转柔美的聚鸣,引发音响抑扬的美感。王政说“有结对的黄鸟飞集鸣叫在树丛间,那是一个少妇婚爱生活欢快和谐的心象写照……她是快乐而欢愉的。正是这种生存状态,灌木林中那嬉戏的雌雄黄鸟,才进入她的‘感受性’视野,称为她心臆间‘异质同构’的兴象。”[12]31涉及黄鸟叫声的还有《凯风》和《黄鸟》。其状声词的运用,既将黄鸟的声音进行了精妙加工,又准确的传达了各种复杂情感。
《国风》中还有大量诗篇描写了燕子、野鸡等的叫声,如《燕燕》和《雄雉》分别描绘了燕子和野鸡自在飞翔的姿态和在空中鸣叫的情景。《国风》同时也对虫类的各种声音进行了全面展现和艺术处理。如《螽斯》用“薨薨”写出了蝗虫展翅嗡嗡的状态,而《鸡鸣》用“薨薨”渲染一种浓郁的睡意。《草虫》用“喓喓”传达了一种忧伤的愁绪。《国风》中声音的审美还包括了对兽类声音的刻画。如《野有死麕》用“吠”写出了尨狂叫的情态,营造了少女警示吉士不要鲁莽的紧张氛围。
上述动物声音意象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人的感觉与其特征相通的基础上,由象征、衬托等手法而引出的赋比兴等表现方式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多与婚恋、祭祀相关。
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动物的叫声尤其是鸟鸣与人类婚姻生活的理想相关,亚里士多德就以鸽子为例,说“鸽的成对,雌雄常终身相守”,而这“表现着人类的生活方式”[17]。中国殷周时期,更是如此。《国风》鸟类的声音内涵多与民间婚恋礼俗有关。《关雎》 便“带有明显的周代礼乐文明的属性”[7]254。“关关”之声,《韩》说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故咏关雎,说淑女、正仪容以刺时。”[9]4其中“贞洁慎匹,以声相求”的特点体现了君子与淑女之间的琴瑟和鸣,也印证了先民以“和”为美的审美取向。再如《匏有苦叶》“雝雝鸣雁”“雝雝,雁声也。纳采用雁,旭日出谓之昕之时。”《笺》云“雁者,随阳而处,似女人从夫,故婚礼用焉。自纳采至请期用昕,新迎用昏。”[19]303所以江林说“这里隐含了周代婚礼‘六礼’的纳采仪式。”[18]116写到鸟鸣的还有《东山》“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孔疏“鹳是好水之鸟,知天将雨,故长鸣而喜也。妇念征夫行役之苦,则叹于室。”[9]536这里暗喻着羁旅行役和伤逝乱离之情。鹳鸟和雎鸠同为水鸟,它们的声音被先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于是“动物的声音也成为周代诗歌表达特殊思想文化内涵的最佳载体”[3]84。
其实,黄鸟叫声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也有差异。《葛覃》用“喈喈”形容鸟鸣。郑笺云“飞集丛木,兴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声之远闻,兴女有才美之称达于远方。”[19]276此处黄鸟的叫声被赋予女子才德远扬的审美取向。而《凯风》用“睍睆”,“言黄鸟有睍睆之容貌,则又和好其音声,以兴孝子当和其颜色,顺其辞令也。”[19]302这里黄鸟的叫声又被赋予恭顺孝敬的道德文化涵义。在《黄鸟》中鸟鸣还与表达君臣之间的忠义有关,“其创作的背后与周代的人殉制度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萌芽”有关[18]288。这说明同种动物的声音也是丰富多变的,“更表明《诗经》作者审美取向和情思具有多元化的特征”[3]84。《国风》中鸡鸣也被赋予了一定的内涵。上古时代男女相约多在天欲明未明的早晨,所以鸡鸣是一种合欢相聚的暗号,《风雨》正印证了这一习俗。王政说“鸡鸣是他们原初约定期会的暗号,更主要的可能还是取喻于鸡鸣报时,对时间的守信特征。”[12]32
《国风》中虫类的声音也有其特定内涵。如《草虫》写草虫“喓喓”声,“言喓喓然鸣而相呼者,草虫也;趯趯然跃而从之者,阜螽也。以兴以礼求女者。”[19]286这里草虫的声音蕴含了“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的习俗。兽类的声音同样有其内涵。如《野有死麕》中“无使尨也吠”,“此女愿其礼来,不用惊狗。”[19]293王先谦说“且无使犬吠而警他人,既儆以礼之难越,又喻以人之可畏,词婉意严,可谓善于立言也。”[9]114可见,一声狗吠也与先民心中丰富的心理、文化内涵紧密相连。
三、人类社会的声音意象及文化内涵
《国风》中人类声音主要有两大类:生活类,涉及劳作、行路、祭祀等方面;人类自身声音,涉及情态声音和对话声音。劳作类:椓之丁丁(《兔罝》)、坎坎伐檀兮(《伐檀》)、施罛濊濊(《硕人》)。行路类:坎其击鼓(《宛丘》)、大车槛槛(《大车》)、载驱薄薄(《载驱》)、佩玉将将(《有女》)、有车邻邻(《车邻》)、佩玉将将(《终南》)。征战类:二之日凿冰冲冲(《七月》)。祭祀类:击鼓其镗(《击鼓》)、简兮简兮(《简兮》)。人本身的声音类:嗟我怀人(《卷耳》)、其啸也歌(《江有汜》)、何嗟及矣(《中谷有蓷》)、泣涕如雨(《燕燕》)、兹之永叹(《泉水》)、倡予和女(《萚兮》)、我歌且谣(《园有桃》)、於(《权舆》)、可与晤歌(《东门之池》)、歌以讯之(《墓门》)。
上述两大类中劳作声有4篇,它们包含了先民复杂的劳动情结。如《兔罝》用“丁丁”写打木桩的声景,《硕人》用“濊濊”写撒网时的欢快,《七月》用“冲冲”写凿冰劳作的声响。除了劳作声,行路的声音也被记录下来。如《车邻》用“邻邻”、《大车》用“槛槛”等,这些车行之声,既有行路之态的审美愉悦,又有内心之情的委婉表述。《国风》中还涉及乐器演奏之声的渲染。《击鼓》用“镗”字写战鼓声,《简兮》用 “简”写万舞祭祀声,《宛丘》用“坎”写宴游之乐:可看出,当时无论是国事还是日常生活,音乐之声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风》中还出现了大量人类自己的声音,主要分为情态声音和对话声音。前者即含有某种神态情感的声音,如“嗟”“叹”“於”等。“嗟”是《诗经》中“最早出现的叹词”[20]。《卷耳》用“嗟”表达了思慕之怀,《权舆》用“於”体现了悲慨之叹,《泉水》用“叹”传达了无奈之情。后者即双方谈话的声音,《溱洧》《女曰鸡鸣》等都以对话入诗。这反映了先民对身边声音审美能力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赵沛霖说“初民实际上是不自觉的完成了感觉映象与观念内容的统一。以这种‘结合’与‘统一’为本质特征的象征性使初民的思维摆脱了个体性和偶然性,而具有越来越广泛的集体性和社会性。”[21]的确,《国风》中诸多人类声音便是先民活动社会性的产物,体现了一定的社会风俗。“周代有农业祭祀活动,一为春祈;一为秋报。”[15]61《七月》中的凿冰一事可看出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另外,也可以看出农夫的劳作之苦。因为“农奴在周代……便是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亦即徭役和赋税的主要负担者”[22]169,由此也就看出腊月里农夫去凿冰的深层阶级原因。
在先秦时期,配乐演唱歌诗,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以乐舞来娱神敬祖,祭祀天地宗庙……已然是一种蔚为大观的祭祀文化”[2]38,以《简兮》为例,它描写硕人执籥秉翟,于公庭前万舞以祭祀天地宗庙的场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万舞的形态和功用”[7]344,可见它与殷商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简兮简兮”又体现出一种紧凑有活力的动感,这“是对旺盛生命力的崇拜,是对力量的崇拜。”[7]345
四、《国风》多用声音意象的原因及影响
文字没产生之前,诗歌以口传的形式存在,所以“在口传文学阶段,声音更是文学表现的主要材料[1]。《国风》中声音意象如此大量运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其所产生的地理环境和文明起源的类型直接相关。《国风》的地域主要集中于气候湿润温暖的黄河长江流域,并出现了以炎黄为首领的氏族部落,后逐渐形成高度的农耕文明。声音作为农耕文明的一部分,显示了先民对天地运行规律、社会风俗制度的掌握与创造。《国风》中出现的动物声音与茂盛植被所提供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国风》中不少篇章提到了雷鸣风吹的现象,“印证了先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征,这与植被茂盛、水流充沛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2]31当然,《国风》中丰富多样的声音意象更离不开社会环境。周朝的生活方式主要以农耕为主,“传统的农耕生产是……人为的又是被决定,所以先民在从事生产劳动时,既顺应自然又有所作为。”[23]周公制礼作乐后,礼乐思想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旋律,诗歌作为礼乐的重要载体也为时所用。而《国风》中声音意象的描摹,又隐含着一定的礼乐文化,所以笔者认为,自然与社会为《国风》声音意象的丰满提供了必要条件,这种声音意象是社会礼乐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国风》中的声音意象与上古音韵有一定关系。它运用了大量的叠韵或叠字,这类词汇在古汉语中大抵为形容词性质,读来有声韵上的美感,这就为描绘自然、人类的不同情境下曲折幽隐的感情创造了条件。在自然和社会及上古音韵的发展规律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风》中的声音意象才显得饱满,成为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使得历代文人对它所做的继承和发展绵延不断。这种继承和发展主要有三种形式。
首先,采录或稍加点化《诗》语为己语。我们以拟声词为例,如“关关”一词,唐韦应物《拟古诗》有“黄鸟何关关”、五代欧阳炯《木兰花》词有“闲庭独坐鸟关关”。“邻邻”一词,杜甫《兵车行》有“车辚辚”、唐传奇《柳氏传》有“香车辚辚”。汉乐府仿《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音”写了“雉朝飞兮鸣相和,雌雄群游与山阿。”《七月》“有鸣仓庚”被陶渊明《答庞参军》仿为“昔我云别,仓庚载鸣。”
其次,对《国风》声音意象的内涵加以传播与发展,这类例证甚多。如秦嘉《赠妇诗》“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从主题和声音上都是对《鸡鸣》的继承。《牡丹亭》“闺塾”直接沿袭《关雎》的春情主题,“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场景引发了杜丽娘的春情。当然还有对同一主题的多重继承,以《黄鸟》为例。王粲《咏史诗》有“黄鸟作悲诗”、阮瑀有《咏史诗》其一“黄鸟鸣高桑”、曹植有《三良》“黄鸟为悲鸣”、陶渊明有《咏三良》“黄鸟声正悲”,这些文人都沿袭了黄鸟悲鸣的文化意蕴。
再次,《国风》中声音意象的语汇还被运用到人名的选取上。如汉代蔡邕,自伯喈,取于《匏有苦叶》“雝雝鸣雁”和《葛覃》“其鸣喈喈”,“雝”与“邕”同,皆为鸟鸣之意。还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先生,其名取意于《七月》“六月莎鸡振羽”,“振羽”,即振翅发声,将“羽”改“飞”,更显动感。
五、余 论
《国风》中声音意象十分繁多,它和周代的自然环境与生活状态、风俗民情息息相关,是先民璀璨智慧的结晶,更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创作材料。总体上看,《诗经》已“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书,它的思想、风格、语汇等已经深深融入古代中国人的血液里。”[15]151
《国风》声音意象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解释。从先秦至明清,其声音意象的内涵几乎都与宣德施教建立了联系。春秋士大夫赋《诗》基本上是从功用立场“断章取义”,借《诗》表达情志或作为外交辞令。到了“三百篇当谏书”的两汉,更是从美刺政治角度出发,如昌邑王刘贺废立之事,王吉等大臣征引《匪风》“匪风发兮,匪车偈兮”来说明王猎扰民之道,已经与《诗》本意有了差异。郑玄《毛诗笺》更是多以礼解《诗》,甚至曲解并掺杂谶纬内容,如“喈喈”“关关”等声音,都赋予了“礼”的内涵,前面已讲,此不赘述。到了后代,尤其是南宋朱熹,将《诗经》中的恋歌一概斥为“淫诗”,《国风》尤其是代表爱情的声音意象,已经完全按照“存天理灭人欲”来理解。但是,魏晋文学自觉的时代,人们在训诂和义疏上开始注重从其情感触发角度研究这些声音意象。总之,这种文化意蕴的异同显示了不同时代的政策和审美取向。但是《国风》的作者几乎都是民间人士,他们对朝廷礼乐的熟知度究竟掌握到何种程度,其实际为文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礼乐就很难得到一个量化的规定。声音意象在《鄘风》和《曹风》篇中为何颇少涉及,仍值得探讨,本文限于篇幅,未及深探。
参考文献
[1] 马凤华. 论诗骚中的声音色彩: 一个审美感觉发展问题的文本考察[J]. 北方论丛, 2002, (1): 85-90.
[2] 刘爽. 国风音声描写研究[D]. 锦州: 渤海大学人文学院, 2012: 14-35.
[3] 谭梅, 谭德兴. 诗经中动物声音及其文化意蕴[J]. 毕节学院学报, 2013, (3): 83-88.
[4] 施向东. 诗经象声词的音韵分析[J]. 南开语言学刊, 2004, (2): 130-137.
[5] 朱熹. 诗集传[M]. 王华宝,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6] 向熹. 诗经词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212.
[7] 李炳海. 中国诗歌通史: 先秦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8] 夏传才. 诗经语言艺术[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8: 29.
[9] 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M]. 吴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0] 程俊英. 诗经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62.
[11] 张启成, 付星星. 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新编[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
[12] 王政. 诗经文化人类学[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13]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M]. 陈金生,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51.
[14] 张树波. 国风集论[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361.
[15] 刘立志. 诗经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6] 胡承珙. 毛诗后笺[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9: 11.
[17] 亚里士多德. 动物志[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419.
[18] 江林. 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9]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0] 万益. 从尚书、诗经的语言现象看古汉语叹词的表意功能[J].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 (2): 95.
[21] 赵沛霖. 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83.
[22] 吕振羽.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3: 169.
[23] 王志芳. 从诗经和考古资料看商周时期的农耕信仰习俗[J]. 农业考古, 2010, (4): 104-107.
(编辑:刘慧青)
Research of Sound Image in the Book of Poems·Guofeng
ZHANG Mingming, LUO Xiaoyu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325035)
Abstract:Sound Image in Regional Songs from the Book of Poems Guofeng is so broad and diverse, including not only the birds and beasts such as pest birds sound wind spring, nature of the animal kingdom, including social work and sacrifice human voice outline. This in a great deal of sound image is described under the 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and social result, not only reflects the ancestors to sound as the intermediary of image creation of aesthetic feeling, but also contains the rich and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n the whole after mad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ge of the Regional Songs from the Book of Poems.
Key words:Book of Poems Guofeng; Sound Image; Cultural Connotation
作者简介:张明明(1988- ),女,河北沧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4-04-23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1.012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I207.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1-00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