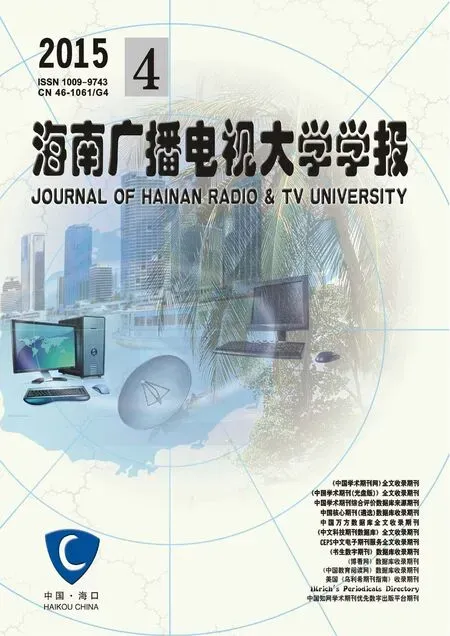深陷沼泽的人——卡夫卡《诉讼》中K的“生存困境”探析
明 炜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深陷沼泽的人——卡夫卡《诉讼》中K的“生存困境”探析
明炜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诉讼》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卡夫卡式”小说形成标识。以主人公K的人生遭遇为切入点,从比较具体的方面来分析与K有着或明或暗关系的一些“人”(包括K自己和一些“局外人”)和“物”(主要指“法庭” 和“法”)所起的作用,并力图探究这些“人”和“物”的象征意义,从而揭示出K的“生存困境”及其所象征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卡夫卡;《诉讼》;K;生存困境


《诉讼》是卡夫卡经典代表作,本文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探讨K的“生存困境”以及困境背后的内涵:K的“生存困境”外在展现、K的“生存困境”内涵探析。
一“生存困境”外显及其成因
银行职员K被莫名其妙逮捕,为摆脱法庭控诉他积极奔走。奔走挣扎过程中一些因素也自然构成了他“生存困境”最外在、最浅显表现。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
(一)荒诞的法庭,绝对的权威
K的被捕乃至最后被判处死刑都是法庭的命令,他积极奔走也是为了摆脱法庭的审判,可以说法庭以及其代表的法是将K置于“生存困境”中最主要的因素。
这个法庭极其荒诞,它莫名宣布K被逮捕,然而K又可以正常生活、工作。K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便利来决定审讯时间。第一次审判时K并不怯懦,他反而大胆抨击法官,指出他们无能、荒唐,也指出法庭臃肿、腐败,我们不禁怀疑拥有强大权威的法庭,此时它的权威究竟在哪里?
值得怀疑的远不止于此。初级法庭坐落在偏远郊外极不起眼的阁楼上,法院要借用听差的房间作为预审法庭,预审法官研读的法律书籍也只是沾满灰尘、肮脏破败的色情书和长篇小说。与其权威相比,法庭本身寒酸窘迫得让人惊奇。
高级法庭也一直未现身,K从法院画家那里得知,他将永远无法真正见到高级法官、高级法庭,教堂里神父所讲的乡下人故事似乎更加明确告诉了K这一结果,即使他终其一生在“法”的门外努力,他也还是不能进入“法”的大门,只能苦苦徘徊。
K积极奔走,努力接近法庭,希望得到最高法庭判决,但是迟迟没有,因而他便无法从这种“生存困境”中摆脱出来。更何况看起来荒诞的法庭根本无法接近,仿佛它为K专设了一道“法”的大门,K永远无法走进,也因而永远无法以活着的姿态从这种“生存困境”中解脱,直至被判处死刑,“生存”被以死亡方式消解,也就不存在“生存的困境”。
(二)自我悖谬而又徒劳的挣扎
如果说荒诞但又具有强大权威的“法”或“法庭”是无边沼泽,那么K就是一个深陷沼泽的人,所以无论他怎样挣扎抗争,怎样急于爬出沼泽,都是无效的、徒劳的,这种挣扎只会加快他被淹没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K为摆脱沼泽所做努力与挣扎在无形中也变成了他正常生存阻碍,即自我悖谬而又徒劳挣扎也是使他陷入“生存困境”的重要因素。
被捕之初,K很不以为然,在初审之时他犀利批评了法官等的腐败无能,他甚至质疑,“为什么要有这个庞大机构呢?它的存在无外乎是把无辜的人逮捕起来,对他们进行莫名其妙的审讯,大多数情况,同我的案子一样,毫无结果。”*(奥)卡夫卡著,孙坤荣,黄明嘉译:《卡夫卡文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11月(2003年12月重印),第34页。可以看到K在此时似乎隐约预知到自己命运,但他却丝毫不畏惧,他对法庭和法官都投以足够蔑视,从主观上而言,此时,他并未陷入到“生存困境”沼泽里,傲慢和抗争成了暂时救命稻草,掩盖住他内心惶恐;但从客观角度而言,K的这种蔑视与抗争,无疑加重了他的罪孽,因为“法庭”或“法”是不能违背的,人在他面前只能卑微屈服,就像预审法官最后所言“我只想提醒您注意,您在今天——可能您至今还没有恢复理智——自己错过了有利时机”。*同①,第36页。我们不清楚预审法官所说“有利时机”具体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K已经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他丧失了缓解自己生存状态的可能,只能向着更深“生存困境”沼泽滑去,直至最终被其完全吞没。
随着时间推移,被捕事件成了他心头挥不去的阴影,内心压力也越来越沉重。他已逐渐感受到自己正在滑向“生存困境”泥淖。首先是他原有生活、工作秩序被打破,他担心自己被捕事件传到银行经理耳朵里,影响到自己良好声誉。上班时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被捕的事,他无法像往常一样对工作勤勉认真。
其次,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罪感越来越强烈,已经逐渐将他紧紧的包裹。为了摆脱这种负罪感,K开始积极奔走。他自动上法庭去探听自己的案情,寻找画家、律师,甚至女人帮助。K越来越认可自己是有罪的。他努力挣扎着为自己争取一点生存权利。这种挣扎似乎到了病态地步,三十一岁生日前夕,他被两个刽子手带走,但“他反抗着不肯向前”,“我要使尽我的全力”,像在粘胶杆上的苍蝇一样拼命挣扎,“直到把一只只小腿都扯掉为止”。*(奥)卡夫卡著,孙坤荣,黄明嘉译:《卡夫卡文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11月(2003年12月重印),第165页。在押解过程中,K突然变得极为顺从配合,他用力拽着两位刽子手继续往前走,自己把头枕在石头上,等待着行刑,显得心甘情愿,惟命是从。K的这种异常举动似乎很难理解,仿佛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然而深入考虑似乎不难发现K或许终于认识到反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丝毫不会改变他的生存权利即将被剥夺事实,那么对于自己的死亡权利总得把握住。所有方法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就以死亡方式来抗争,K终于没有摆脱他所处“生存困境”,挣扎、努力的结果都是推着他往相反方向前进,犹如掉进沼泽的人,越是努力挣扎着要爬出来,结果越是陷入得深,越是加快了自己被沼泽吞灭速度。
(三)若干“局外人”作用
K的自我挣扎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积极向他人寻求帮助过程,随着他的奔走,诸如律师、画家、商人、工厂主、保姆莱尼、法庭女人等等许多“局外人”也都或直接或间接与K被捕案件发生了联系。这些“局外人”在K的挣扎过程中或提供帮助,或丝毫作用不起甚至起消极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局外人”也对K的“生存困境”起着或大或小或加重或缓解的作用,因而他们也值得略微探究一下。
第一类是“K期待着有用但实际却没用的人”。以律师和画家为典型代表。他们声称自己有能力帮助K,却一直拖延、耍弄着他。不仅没有将K从“生存困境”沼泽里救出来,反而消磨着他的时间与期望。无疑,他们恶化了K的“生存困境”。
第二类是“女人们”。主要指初审法院里法庭听差的女人和律师家保姆莱尼。她们二人都与K有着某种暖昧关系,但她们二人却都为K提供了实际帮助。听差女人告诉了K一些法院里情况,也让他看了预审法官的书。保姆莱尼时时向K通报律师的一些情况,并尽力在律师面前帮助K。虽然二人地位低下,帮助甚微,但与律师和画家相比,他们的帮助至少比较实际。尽管并不能缓和K所处“生存困境”,但从主观角度而言,她们的帮助是倾向于积极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她们或许也是消极因素。因为K的自我挣扎本来就是徒劳的,就是恶化他自我生存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她们的帮助,似乎是以另一种形式在恶化K的“生存困境”。法庭神父也对K讲过,“你寻求外部的帮助太多了,尤其是女人方面的帮助。难道你没有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帮助吗?”*(奥)卡夫卡著,孙坤荣,黄明嘉译:《卡夫卡文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11月(2003年12月重印),第156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女人们”的“帮助”对K的“生存困境”而言,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恶化。
第三类则是打破K幻想的人。以商人布洛克和神父为代表。某种程度而言,商人布洛克是K的同类人,因为他们都被法庭以莫名其妙的罪名控诉,都在为了寻求解脱而积极奔走。但是又有不同,布洛克虽然也为了摆脱法庭控诉而努力,但是他柔弱、怯懦,在律师面前卑躬屈膝惟命是从,生怕犯一点错误。与商人相比,教堂里的神父则来得更直接,他自称是法院的人,似乎代表着法院在做一种宣判。他责怪K寻求外部帮助太多了,特别是女人帮助,并且明白告诉他这些都不是真正帮助。他也厉声呵责K鼠目寸光看不到第二步。最后他讲了一个“乡下人”与“法的大门”的故事,并驳斥了K的种种辩解,似乎是在暗示K将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罪恶,永远无法走出“生存困境”的沼泽,因为这道“法的大门”也是专为他而设。如此而言,商人用他自身经历告诉了K现实残酷,他将不可能摆脱被指控的命运,而神父则似乎带着法庭权威在向K宣判,他将永远不能迈进“法的大门”。他们打破了K期望通过努力来摆脱被控诉的命运的幻想,使K直接面临血淋淋的现实——难以逃脱的“生存困境”。
二“生存困境”内涵及其象征
第一部分我们对K的“生存困境”外在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已经有所认识,下面我们就对这些构成困境的因素所象征的内在含义进行探析。
(一)“法庭”或“法”的象征含义探析
K因为“法庭”的控告而被捕,接着又积极奔走希望摆脱“法庭”或“法”的控告,最后又被“法庭”或“法”判处死刑。可以说导致K陷入“生存困境”的核心因素是“法庭”或“法”。因而探究“法庭”或“法”的内在含义十分重要。那么这里的“法庭”或“法”究竟象征着什么呢?
首先一个作家的作品可以有超时代意义,但它并不能完全超越时代,它多少总会与作家的时代、人生经历有着某种联系。如此而言,卡夫卡的《诉讼》或许隐约反应着其所处时代的问题。卡夫卡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迫于父命改学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而后又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最后进入布拉格半国立的波西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任职,退休之前还被提升为高级书记员。可以看到他的学科背景使他对法律知识相当熟悉而且所从事工作也使他对整个司法系统相当了解。因而在小说里K控诉法庭是一个臃肿庞大的机构,养着一群贪污腐化又无能的人,办事效率低下,层级关系严明,还时常以莫须有罪名戕害无辜的人以此彰显其存在,这可能更是卡夫卡对黑暗司法系统的控诉。所以“这个即具体(被告分明看到了那个设在阁楼上的法庭)又遥远(无人主持审判),既腐朽又恐怖的法院乃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律机器的象征”。*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花城出版社,1986,第48页。
同时法律又是一个国家得以正常运转的核心,是各种秩序得以维护的基本保障,如果连法律也变得朽败不堪,那么这个国家其他系统又是什么样呢?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卡夫卡这部小说创作于1914至1919年,此时正是一战时期,欧洲新崛起工业国家正在为谋求更多利益而强力争夺,旧有世界秩序被破坏,许多国家都陷入了混乱状态。更何况卡夫卡又是犹太人后裔,说着德语却又生活在捷克,这种复杂时代背景与身世背景交叠,让他更能够敏感捕捉到时代动荡与黑暗。因而,这里“法”或“法院”有一种超越它本身所代表范围的意义,即它象征着整个时代混乱、腐败、黑暗的状态。
但是“卡夫卡的作品是在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之外展开的”。*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2010重印),第539页。从抽象角度而言,这里的“法”或“法院”可以象征着一种广泛存在但又不能逾越的规则。从本质上讲,“法”本身就是一种规则,它引导或限制着人的言行,具有不可逾越性,但是在这里,“法”所象征着的则是一种更广泛的规则,它无需实际载体但又真实存在,而且具有超时空性,不可逾越性,甚至还具有某种神秘性。K一直在挣扎,他不但斥责法的黑暗、腐败,还积极奔走企图逃脱法律制裁,违逆了不可违逆的规则,最终被规则所惩罚。
另一种更流行观点则是从“存在主义”视角来解释。即“法”或“法院”或许象征着一种荒诞性。“存在主义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人的存在的凸显。”*雷碧乐:《卡夫卡小说<变形记>的存在主义》,《电影文学》,2010年第22期。而“荒诞,是存在主义的一种此在经验,是上帝“死”后的一种生存境况”。*叶廷芳:《卡夫卡及其作品中的荒诞意识》,《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如果说之前将“法”视为一种普遍不可违逆的规则,而在“存在主义”这里却连规则也没有了。没有了规则人也就没有了方向,处于一种迷茫状态。人生就是一个被抛入状态,从出生到死亡都不得不忍受痛苦煎熬。世界不可解释,人的行为也是非理性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都是不可预知的,也都是不可抗拒的。“人在这个不可解释的世界上无能为力,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世界是个荒诞的世界。”*刘岩:《卡夫卡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9年第1期。诚然《诉讼》也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荒诞世界。K被莫名逮捕,却依然可以正常工作;他明明无罪,甚至起初还勇敢揭露法庭和法官的黑暗与丑恶,但负罪之心日渐沉重;积极奔走挣扎,最终依旧是徒劳;最高法庭始终没有出现,也没有进行审判,K却被判了死刑;一直都在反抗,最后却自己把头放在断头台上。当然最具荒谬性的还是神父所讲的“乡下人”与“法的大门”的故事。“法的大门”敞开着却又设有重重警卫;警卫收受了贿赂答应让乡下人进入,却一直没有放行;守门人说法门是专为乡下人而开,却又阻拦他一辈子;乡下人在法的门前苦苦徘徊,直至死时依旧未能进入,却看到了从法门内射来的永不熄灭的光。神父似乎在暗示着K就是那个“乡下人”,苦苦努力,终其一生却依旧徒劳,因为这“法的大门”也是专为K而设。在一个充满荒谬与怪诞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法”或“法院”也正是象征着这种荒诞性,故而K注定要陷入这种“生存困境”,注定无法摆脱。
(二)K的形象特征及其象征意义探析
“法”或“法庭”与K是互相对立一组矛盾,K固然与“法”的对立面有交叉重叠一面,也有自身独立意义。
《诉讼》虽然充满了荒诞性,但并不妨碍我们窥探出K的性格特征。初审之时K敢于当堂怒斥法官昏庸无能和法庭黑暗腐朽。日后,他又积极奔走企图摆脱法庭控诉。在教堂里与神父就“乡下人”与“法的大门”的故事进行争辩。这显示了他的抗争性。特别是与同为被告人的布洛克卑躬屈膝的态度相比,他的抗争精神更为明显。但另一方面他又日渐觉得自己有罪,并极力寻求摆脱,甚至到了病态地步,在最后竟主动将头放在断头台上,等待着屠刀。这显示了他是一个既有抗争性又有软弱性的人。而且这两种精神一直在他体内奔腾冲突,使他处于一种越陷越深的困境。
不难发现,卡夫卡也具有相同气质。从某个角度说,K是卡夫卡自我形象的投影,K象征着卡夫卡他自己。这不仅是因为K与卡夫卡(Kafka)名字首字母存在着某种暗合性,更由于卡夫卡个人经历所决定。卡夫卡是犹太人后裔,却与犹太教、犹太民族文化有着深刻隔膜;用德语写作却又生活在捷克;作为资产者的儿子却又深刻同情劳苦工人......他身上有着太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他总是居于矛盾两极,也常常被矛盾拉扯着,备受煎熬。他像K一样苦苦挣扎于工作与爱好之间,爱情与婚姻之间,父子关系之间,但最终并未能求得一个圆满平衡,他并未跳脱这种令他挣扎处境。同时他也像K一样有深重负罪意识。
K另一种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应该是一个被揶揄的人,被这个荒诞的世界所揶揄的人或人类。法庭的控诉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被法庭控诉逮捕以前,他尚生活在一个理性世界,一个有着规范秩序的世界。K在一个银行任职,工作勤勉,得到经理器重。但厄运随着法庭控诉而来临,他被莫名逮捕,却不知道罪行是什么。而K日渐觉得自己是有罪的,积极奔走寻找帮助,律师和画家都宣称自己可以帮助,但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作用。在教堂里针对神父所讲的一个非理性世界的故事——“乡下人”和“法的大门”,他也固执与神父争辩,坚持认为是看守骗了乡下人。可以看到K完全是以一种理性思维,企图通过理性方式来逃脱来自非理性世界制裁。但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这个非理性的世界是不可解释的,不可违逆的,人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只能永远处于被揶揄、被戏弄地位。K的境况也就是现代人普遍境况,“甚至是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人受一种不可知力量任意摆布,任他如何挣扎都是徒劳”。*刘岩:《卡夫卡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9年第1期。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人类失去了信仰的精神支柱;新兴科学带来短暂希望之后,却被用在战争中成了杀人武器。于是希望也完全破灭,人丢失了信仰,又苦苦找不到出路,精神迷惘,饱受孤独、恐惧、痛苦,在这个陌生怪诞的世界里只能任其捉弄摆布。所以K只是卡夫卡为现代人或者整体人类找的一个代言,他的“生存困境”就是现代人或者人类整体的“生存困境”。
(三)“局外人”的象征意义
如第一部分所分析,围绕在K周围形形色色的“局外人”可以粗略分为三类。因而从大的方面来讲,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他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第一类是“K期待着有用但实际却没用的人”,以律师和画家为代表。律师和画家都宣称自己与法院有着密切关系,却丝毫无用。这类人更像现实世界里的人。他们不停吹嘘着自己的地位,自己结交的人脉,自己过往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针对被害人,他们却不能提供什么实际性帮助。
第二类是“女人们”。具体而言法庭听差女人和律师家保姆莱尼都与K有过暖昧关系,而且都予以K力所能及帮助。但K又对她们有某种负罪感,“我似乎专门在求女人的帮忙,他差不多吃惊的想,先是比尔斯纳小姐,后来是法庭听差的老婆,最后是这个小护理”*(奥)卡夫卡著,孙坤荣,黄明嘉译:《卡夫卡文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11月(2003年12月重印),第3页。。甚至这也成了他被控诉的一个理由,因为神父曾经责怪他寻求的帮助太多了,特别是女人帮助。当然这或许也是K的自我控诉。
的确,“女人”是卡夫卡小说中常见形象,她们似乎是与现实若即若离。甚至有学者提倡应该从女性视角去解读卡夫卡。“文学、姑娘和死亡:卡夫卡就在这个三角中游戏人生,消耗人生。”*曾艳兵:《卡夫卡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页。在卡夫卡一生中,他都期盼着拥有自己的婚姻、家庭却又害怕婚姻,因而几度与人订婚又解除婚约。但他依然从这几个姑娘身上获得了巨大的慰藉:菲利斯期待着成为“一个关怀备至的妻子,提供一个平静的家,一份明智的饮食”,在生活上给卡夫卡以莫大关怀;密伦娜则更能够从精神上理解卡夫卡,慰藉了卡夫卡孤寂的心灵;朵拉则在晚年一直陪伴着卡夫卡,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了卡夫卡巨大安慰。但卡夫卡最终并未能给予她们所期待的幸福。所以对此,卡夫卡也是一直怀有负罪感,就像K一样,一方面从女人身上获得帮助,一方面又对她们怀有负罪感。小说中的“女人”多多少少有着现实性,她们或许象征着卡夫卡身边的女人们,也是卡夫卡自我隐隐不能忘怀的负罪感的象征。“女人”构成了K被控诉、判决的一个缘由,也构成了卡夫卡自我审判的一个缘由。
如果说前两类“局外人”都有着某种现实性,那么第三类则更具有抽象性。以神父和商人布洛克为代表,他们似乎是荒诞的非理性世界的代言人。
在荒诞世界中,一切不可解释,人也无法掌控自己命运,只能任凭不可知力量摆布、捉弄。神父似乎是这种力量的正面代言人,他莫名其妙认识K,知道K行踪,并谴责K寻求外界帮助太多了,特别是来自女人方面帮助,也谴责K不能用长远眼光看到事情的第二步。这似乎是隐隐暗示了K的“罪行”。最后他对K讲了“乡下人”与“法”的故事,似乎也是在暗示K这“法的大门”也是专为他而设,他的挣扎注定只是徒劳。高级法庭和高级法官一直都没有出现,卡夫卡似乎是以神父这个角色代替了这个权势机构,换言之神父似乎就是这个机构代言人,也是这个荒诞的非理性世界的代言人。
另一个代言人则是商人布洛克,他与K有着近乎相同遭遇——同样被莫名其妙控诉,同样希望从困境之中解脱,但是他并不像K一样拼命挣扎,而是卑躬屈膝,对律师唯唯诺诺,完全放弃了自身尊严,像奴仆一样。尽管已经被捕五年,但是并没有被判处死刑。而K被捕一年,却被判处了死刑。因为荒诞的世界是不可解释、不可违逆的,人只有忍受被摆布、被控制命运,任何挣扎都注定是徒劳。从这个角度而言,商人布洛克言行举止则十分符合这些规则,换言之,他给K做了很好示范,从反面成了这一荒诞世界的代言人。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K“生存困境”影响因素及其外在展现、“生存困境”因素所象征的内在含义这两个大方面来探究《诉讼》中K所面临 “生存困境”。当然,作为开启现代主义滥觞的大家,卡夫卡作品充满了寓言性和多义性。他用质朴语言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谜语,尝试从不同角度去解析,或许最终我们能寻找到隐藏在文字之后谜底,也或许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找到,像K一样都以徒劳而终,也更像那个乡下人,终其一生也未能走进那个专为他而设的“法的大门”,或许卡夫卡也为我们设了一个“谜的大门”。
参考文献:
[1](奥)卡夫卡著,孙坤荣,黄明嘉译.卡夫卡文集(第2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003重印).
[2]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3]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2010重印).
[4]雷碧乐.卡夫卡小说《变形记》的存在主义[J].电影文学,2010(22).
[5]叶廷芳.卡夫卡及其作品中的荒诞意识[J].社会科学战线,1993(5).
[6]刘岩.卡夫卡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9(1).
[7]曾艳兵.卡夫卡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责任编辑:张玉秀)
The Man Trapped in the Marsh
——Analysis of K’s Survival Dilemma inTheTrialof Kafka
MING 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The Trial is one of Kafka's most important novel, which is also the typical symbol of "Kafka Style" novel.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functions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People”——including K himself and some outsiders——and “the Things”——mainly refer to court and the law which is around or connected to “K” by analyzing his suffering in detail so as to reveal K’s "survival dilemma" and its deep connotation.
Key words:kafka;the trial;K; survival dilemma
作者简介:明炜,男,汉族,湖北十堰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
收稿日期:2015-09-11
DOI:10.13803/j.cnki.issn1009-9743.2015.04.007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43(2015)04-0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