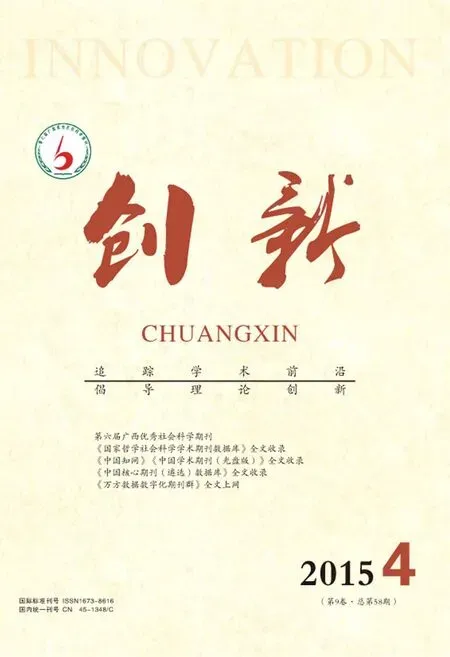《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制度的构造及改进
孙也龙
非自愿住院制度涉及精神障碍患者的健康权、自由权,监护人的监护权,国家亲权、治安权,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等诸多重大问题,因而是具有较强争议性的话题,也成为立法者、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棘手问题。直到2012年10月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立法上终于对非自愿住院做出了规定。但是学者对非自愿住院的理论争议仍未停止。通过对现行法的解读和比较法上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的非自愿住院在制度上仍有待改进,有必要针对我国非自愿住院制度的不完善之处提出改进的建议。
一、非自愿住院制度构造的现行法分析
《精神卫生法》第30条第2款对非自愿住院的构成要件做出了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这就是说,我国非自愿住院有两项基本构成要件:一是主体要件,即就诊者须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二是行为要件,其中又包括两种类型,即患者具有伤害自身的行为或危险,或者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
根据行为要件的两种类型,《精神卫生法》规定了对应的两种法律后果。针对第一类行为要件,即具有伤害自身的行为或危险,第31条规定“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由于在这种情形下监护人对患者是否住院起决定作用,因此本文将此类非自愿住院称为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针对第二类行为要件,即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第35条第2款规定“其监护人应当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阻碍实施住院治疗或者患者擅自脱离住院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由于在这种情形下对患者进行住院治疗是由国家授权的,因此本文将此类非自愿住院称为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
二、主体要件:严重精神障碍抑或自愿能力
非自愿住院的主体要件是就诊者须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那么,为什么要规定主体要件,主体要件的法理基础是什么?首先,必须分析《精神卫生法》对“精神障碍”与“严重精神障碍”的定义。该法第83条第1款对精神障碍的解释为,“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第83条第2款对严重精神障碍的定义为,“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第83条第1款的“精神障碍”是一个医学定义,第83条第2款的前半句所说“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在第83条第1款的基础上加上了“严重”,故该前半句也是医学定义。而第83条第2款的核心要素不在于前半句,而在于后半句,症状导致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不能处理自身事务”,即丧失认识能力和自理能力。这些能力都是患者行使自愿所必需的能力,因为行使自愿的前提是主体必须有能力认识客观状况,从而做出关于自己事务的决定。如果患者丧失了认识能力和自理能力,那么他就无法行使自愿,因而不具备自愿能力。
可见,《精神卫生法》所规定的“严重精神障碍”的实质性要素不是在于单纯的症状严重程度,而是在于症状的严重度是否使得患者丧失了自愿能力。单纯的症状严重程度是医生关心的问题,而是否丧失自愿能力才是法律人关心的问题。非自愿住院的主体要件的法理基础就在于自愿能力的丧失,因为如果患者有能力行使自愿,则应适用第30条第1款,即自愿住院制度,而丧失自愿能力的患者无法行使自愿,对此类患者的住院治疗就只能属于非自愿。
因此,《精神卫生法》关于“严重精神障碍”的定义性规定不仅没有必要,还会增添困惑,使得原本属于纯医学定义杂糅了医学和法学含义。故本文建议,取消“严重精神障碍”的规定,代之以自愿能力的规定;或者将“严重精神障碍”作类似于第83条第1款精神障碍的纯医学定义,同时仍须单独对自愿能力作出规定。
三、行为要件:危险性标准的重新审视
根据《精神卫生法》对第30条的解释,为了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因滥用非自愿住院治疗措施而受到侵害,本法严格设定了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条件,即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危险性时,才能对其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1]91此危险性标准,即危险性是非自愿住院的前置要件。那么对于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无自愿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必须具备伤害自身或有伤害自身危险的条件时,其监护人才能决定是否对其进行非自愿住院。危险性作为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的前置必要条件,将削弱我国精神疾病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非自愿住院制度固然有维护社会安全、体现国家治安权的价值,但其首要目标应是保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能够得到妥善的治疗,保障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丧失自愿能力的患者,只得依赖非自愿治疗,此时如若监护人将其送院治疗,医院经审查患者不具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但却以精神卫生法设置了危险性标准为由拒绝患者入院。这使得那些不具有危险性同时无自愿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无法得到住院治疗,而这些严重患者仅通过监护人对居家患者的看护管理是无法获得真正有效的救治的。因此,对于这些精神障碍患者,作为非自愿住院必要条件的危险性门槛,实际上损害了其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这也是为什么危险性标准在西方国家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有西方学者指出,危险性标准不必要、不公平、弊大于利。[2]经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在有危险性原则实行的辖区内居住的患者,比居住在没有危险性原则实施的辖区内的患者起始治疗时间延后了5个月。[3]所以,我国精神卫生法立法者在借鉴国外经验时,仅以国外法律文本为参照,而没有充分调查国外法律在实际运行中产生的问题与困扰,盲目照搬西方的危险性标准可能使我国将来也面临与西方国家类似的精神障碍医疗服务可及性不足的问题。
因此,本文建议取消伤害自身危险性作为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的前提要件。鉴于通说认为危险性要件是防止家属权利滥用的重要工具,本文的建议可能会引起疑虑,这实际上是对我国“被精神病”现象的误解。之所以发生“被精神病”,并不是因为我国法律制度没有规定危险性标准,而是因为自愿能力制度没有得到良好贯彻。在“被精神病”的情况下,精神障碍患者是具有自愿能力的,而当家属滥用权利将患者送往精神病医院时,医院没有审查评估患者的自愿能力甚至直接默认患者丧失自愿能力,因而否定患者的住院拒绝,从而违反患者意愿强制其住院。可见,“被精神病”准确地说应是“被推定无能力”。因此,要防止监护人滥用权利,根本的解决路径不是规定危险性要件,而是规定并切实执行自愿能力制度。对于无自愿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伤害自身危险性不应是非自愿住院的必要条件。无论精神障碍患者是否有伤害自身的行为或危险,如其监护人根据生活常识判断患者有住院治疗的必要性,如拒绝进食、骚扰邻居等,而将其送院治疗,并经医院审查该患者的精神障碍确实已使之丧失了自愿能力,医院就应允许其入院治疗,不得以患者无危险性为由拒绝其入院治疗。这也并未侵犯患者自由权,因为丧失了自愿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已经不可能行使自由意志,其无法表达有效的意愿,丧失了行使自由权的基础,所以,对其进行非自愿的住院治疗就谈不上对自由权的损害,自然也没有减损他们的自由权。可以说,是精神疾病剥夺了患者的自由权,本质上患者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进一步说,取消危险性门槛使得无危险性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获得医疗服务的充分可及性,这不仅不会损害患者的自由,还能增进其自由。既然一部分精神障碍患者已经无能力自愿入院治疗,而住院治疗的目标是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地和一个使他们控制病情的康复体验,那么只得求助于非自愿制度来获取有效的住院治疗。由于精神疾病限制了患者自由,那么治愈这些疾病将增进患者的自由。[4]医院不得以患者无伤害自身之行为或危险为由拒绝其入院治疗,这不仅不会侵犯自由权,还保证了虽无危险性但精神障碍已使自愿能力丧失之患者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四、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监护人的确定
(一)法定监护
对于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首先需要确定监护人。《精神卫生法》第83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是指依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人。”所谓“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人”只是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监护人,所以该款只是转介了《民法通则》第17条关于精神病人的监护人的范围的规定,故而对确定真正的监护人不具有指示作用。也正是由于《民法通则》第17条只是规定了监护人的范围,对确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不具有指示作用,因此2015年4月19日,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25条“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明确规定了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的确定规则:“由人民法院根据最有利于该精神障碍患者的原则从下列人员中确定其监护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职责的人。”[5]虽然这一建议比《民法通则》有进步,但是仍然存在缺陷——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必须通过司法途径予以确定,这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也不利于对患者被及时照护。本文认为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的确定应采取法律直接规定的模式,即首先列举有监护资格的人的范围,其次按顺序确定真正的监护人,前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死亡或无能力的,则后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为监护人,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23条“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确定规则,本文认为该规则是科学的,故而也应当适用于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的确定。
(二)意定监护
第二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意定监护制度是否可以适用于精神障碍患者。意定监护是独立于法定监护之外的另一种确定监护人的制度,它是指民事主体在意识能力健全时预先选定监护人并与之缔结委托监护合同,也就是由民事主体本人而非法律来确定监护人,体现了对个人自己决定权的尊重,正因如此,意定监护制度已经在两大法系监护制度中得到确立。[6]随着我国民众自治观念的勃发以及人口老龄化和精神疾病负担的加重,法律对意定监护制度显示出愈发强烈的需求。然而,《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者并没有意识到意定监护制度对精神障碍患者的重要意义。实际上,精神障碍患者在疾病未发作、意识清醒时,其有能力为自己将来丧失意思能力时的诸事务选定监护人,但《精神卫生法》第83条第3款直接转介《民法通则》的监护规定,而《民法通则》只规定了法定监护而未规定意定监护,这就使精神障碍患者难以依法自己选定监护人。从立法论的角度分析,应当在《精神卫生法》中加入意定监护的条款,或者在将来编纂民法典时加入意定监护条款同时《精神卫生法》转介民法典的监护条款。2015年4月1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就在第26条“成年协议监护”中规定了意定监护,未来在民法典通过后就可修改《精神卫生法》以转介此条款。从现行法的角度分析,我国法律制度中唯一规定意定监护条款的是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老年人未事先确定监护人的,其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可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这样的规定显然优于《精神卫生法》仅仅转介民法通则的做法。鉴于老年人中也有部分精神障碍患者,则这类老年精神障碍患者既可以适用《精神卫生法》也可以适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就产生了竞合。本文认为,本着尊重自己决定权的理念,对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问题,应当适用更加完善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条款。可见,从现行法分析至多只能解决老年精神障碍患者这类特殊群体的意定监护问题,而要赋予所有精神障碍患者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则还须立法做出改变。
五、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适用范围的再界定
通过对《精神卫生法》第30条第2款、第31条、第35条第2款的现行法分析,可以看出该法律将“伤害自身”和“危害他人安全”分别作为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和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的行为要件。一方面,不论患者伤害自身的程度有多重,都只能由监护人来决定是否对患者予以非自愿住院;另一方面,不论患者危害他人安全的程度有多轻,都需动用国家强制权对患者予以非自愿住院。前者贬损了国家亲权与治安权,后者忽视了患者自由权,故而,这种一刀切的规定必须得到纠正。
(一)应将严重伤害自身纳入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的适用范围
国家设置非自愿住院制度的法理基础在于国家亲权和国家治安权,前者体现在国家维持精神障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能够得到妥善的治疗,以恢复他们的健康,后者体现在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及他人不受该患者的伤害,以维护社会安全。[7]然而《精神卫生法》不分程度地将伤害自身的情形完全作为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的行为要件,将损害国家亲权和国家治安权的实现。
《精神卫生法》对伤害自身的无自愿能力患者适用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这样规定的立法理由是:“这种情形的患者并没有危害他人安全,只是伤害自身,应当由患者利益的维护者即其监护人决定是否住院,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不宜干涉。”[1]92确实,这对轻微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的情形是应当适用的,比如用利器割伤/划伤、打火机烧伤、在身体上打洞、烫伤皮肤等。[8]这些情形通过监护人的自行照管和决定住院是可以妥善解决的,即如果监护人有能力阻止患者的轻微自伤,则他会选择自行照管患者,如果监护人认为自己无法阻止患者自伤,他可以决定让患者住院治疗。同时,法律首先推定监护人会为了患者利益而履行监护职责,其次,即使监护人没有履行好监护职责一般也不会导致患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因而法律将轻微自伤情形交由监护人决定处理是妥当的。但是,《精神卫生法》所谓“伤害自身”不仅仅指轻微自伤行为,而是包括了极其严重的自残行为甚至自杀行为,这种行为将对患者健康或生命产生重大损害。例如,在德国司法实务中,精神障碍患者对自己健康的重大伤害包括:因病而实施的自杀或导致死亡或不可回复的健康上之伤害;有疯狂之症状的病兆,若情况恶化将导致自杀;厌食之患者因拒绝进食而发生危及生命的情况,或是BMI低于13,随时可能发生紧急的生命危险情况;有自残或服毒的具体危险;因拒绝服用治疗所必需之药物,导致丧失社会功能或发生心智重大改变。[9]对于具有这些极其严重自残或自杀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将监护职责仍交由监护人,就不甚妥当:一方面,一旦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则患者的健康将遭到严重损害甚至丧失生命,法律不应当冒此风险;另一方面,国家亲权和国家治安权也受到懈怠,国家保障公民重大健康利益和生命利益的责任不应被推到患者监护人身上。
已经丧失自愿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相对于他人是弱势个体,其自残或自杀(特别是当自残或自杀行为是可以被预见时)的社会消极影响并不比患者危害他人安全的社会消极影响小,既然法律规定危害他人安全即可构成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那国家也就更有责任行使国家亲权和国家治安权对严重自残或自杀患者进行非自愿住院。对此可能的疑虑是:国家是否有过多干涉之嫌,不免使人担忧国家趋向于以家长式的方式过多介入个人事务。然而,这种担忧是将国家行为误解为仅仅具有家长性,而忽略了这是对其国家亲权的合法行使。政府具有此项权力,这样它才能实现其为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人提供照顾的职责。当丧失了自愿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有严重自残甚至自杀情形时,他不仅无法照顾、保护自己,还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这时候国家有职责履行其国家照顾义务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再次,非自愿住院仅仅是一个执行机制,只有当国家适当地平衡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时,它才能行使其国家亲权。如果精神障碍患者伤害自身的程度较轻,则国家不应干涉监护人对其进行居家照顾的决定。但是如果精神障碍患者伤害自身的程度极其重大以致威胁其生命,此时在衡量国家权力与监护人权利时,就应偏向于国家权力(即国家亲权)了。不分程度地将伤害自身的情形作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不宜干涉”的事项一定程度上是推卸国家责任之举。综上,建议在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的适用范围中加上如下情形:已经发生严重自残或自杀的行为,或者有严重自残或自杀的危险的;因拒绝进食或拒绝服用治疗所必需之药物而发生危及生命的情况的。
(二)应对危害他人安全的情形做限制性规定
《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的另一个不合理之处在于不分程度地将危害他人安全的情形完全作为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的行为要件,这将损害患者的自由权。虽然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体现了国家亲权和国家治安权,但其本质上是行使国家权力对患者人身自由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的过程,因此必须受到法律的明文规制。我国《立法法》第8条列举了法律保留事项,其中第5项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据此,由于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构成对患者人身自由的限制,故而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必须由法律明定其构成要件。但是《精神卫生法》仅仅规定“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就足以构成非自愿住院,这是非常模糊的规定。“危害”须达到何种程度,是否包括轻微的危害?“危害”是指经常性的危害还是包括一时的危害?“安全”是指何种安全,是否包括财产安全或精神安宁?这些问题都无法从“危害他人安全”六字中得到确切答案,而将这种模糊的构成要件贯彻于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会产生侵犯精神障碍患者自由权的风险。例如,一位丧失自愿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偶尔将他人的门窗砸破,或者偶尔在家中大声哭泣影响到邻居的精神安宁,就以危害他人财产安全或精神安宁为由对其实施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这是不合理的,将严重损害患者的人身自由,因为这些情况完全可以交由患者的监护人来自行处理和决定,而无须国家公权力介入。如果将“危害他人安全”的阈值设置得很低,势必造成很多私人间就可以处理的事务也被纳入到国家权力的管控轨道上,从而对患者及其监护人的私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建议法律对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的“危害他人安全”要件作出更加详尽的限制性规定:“危害”仅指程度严重的经常性危害,而不包括程度轻微的或者一时性的危害,“他人安全”仅指他人的人身安全,而不包括财产安全或精神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