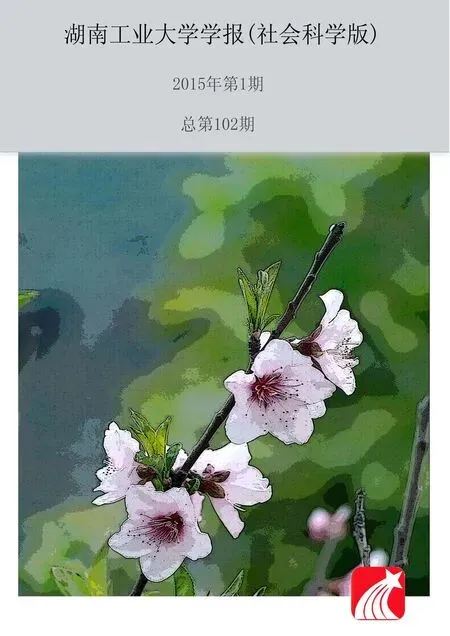以小人物展示时代风云*
——论吴刘维作品中“小人物”形象
余佩
(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114)
以小人物展示时代风云*
——论吴刘维作品中“小人物”形象
余佩
(长沙理工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114)
吴刘维以严肃的态度和调侃的语言叙述社会变迁中“小人物”的琐碎人生,以机敏的思维和朴拙的语言叙述城乡社会中“小人物”的生存境况,其作品颠覆了“小人物”逆来顺受、麻木愚昧的传统形象,赋予了他们不一样的智慧与激情,对他们在社会规则中寻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给予高度的赞扬和欣赏,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展示了时代的风云变幻。
吴刘维;小人物形象;时代风云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小人物”都是作家们致力书写的一大主题。西方的普希金、契诃夫、果戈里、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我国的鲁迅、老舍、张天翼、赵树理等,都是描写“小人物”的大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小人物”大致被赋予了逆来顺受、麻木愚昧、被侮辱被损害,像奴隶一般一声不响地操劳着、苟活着的劳苦大众的形象标签,作者在同情怜悯这些“小人物”的同时,更多的是批判他们性格的弱点和奴性的本质,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进入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小人物”这一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他们已经去除了“受压迫”“被剥削”等体现社会阶层的标签,不再局限于“五四”时期刚从俄国引入时的“小公务员、小市民”的特定指涉,也非单指黑暗社会的压迫人群或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劳苦大众。小公务员、小市民、进城务工者、乡土农民等,成为了新时期社会中的“小人物”。他们虽然一样的地位低下、生活贫苦,遭遇着社会规则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尴尬与无奈,但生活情态和性格追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者对他们不再仅仅是同情怜悯、批判无奈,更多的是赋予了他们不一样的智慧与激情,表达了对他们在社会规则中寻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的赞扬和欣赏。吴刘维就是这其中描写新时期“小人物”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作为新时期的作家,吴刘维的作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真实的亲切感,作品中呈现出的故事场景、人物、事件等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熟悉的、常见的,让我们在阅读时有一种历历在目的参与感。但通读完他整个作品,我们发现,这些平常的事物所构建的整个故事却又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也许与他的创作理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曾说:“我在尝试一种‘低空飞行’的写作方式,百分之八十的当下生活,加上百分之二十的想象。毕竟,‘贴地爬行’,交通太堵塞,难以快捷地到达目的地;而‘高空飞翔’,离地面又太远,不近人间烟火。”[1]他的创作理念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对于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尤其是小人物的塑造,他同样贯穿这样的理念。纵观他的作品,我们发现,他的创作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城乡社会中的“小人物”。他写农村矿工、城市工人、从农村步入城市的企业职工,这些人物在我们当今社会,都是常态存在却又经常被忽略的“小人物”。在以往的作品中,这些“小人物”的存在似乎不值一提,因为他们既不是推动历史车轮的名人英雄,也不是社会灾难的背负者,既没有曲折离奇的身世之谜,也没有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他们只是社会中真实存在的隐形者,可正是这些隐形者的生活状态和存在价值,成为了吴刘维创作的兴趣所在。在作品中,吴刘维以严肃的态度和调侃的语言叙述“小人物”的琐碎人生,以机敏的思维和朴拙的语言叙述城乡社会中“小人物”的生存镜象,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了这些小人物真实的生存境况和入世心态。但正如他所言:“优秀的小说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包括它的细节、情节、人物以及叙述方式、内在含蕴。”[2]他小说中的“小人物”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虽然同样处于社会底层,不被大众关注,但是他们敢于反抗,敢于以自己弱小的身躯与这个世俗的社会作斗争,即使需要他们放弃生命,他们也要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他们是来自底层的战士;他们虽然一样的平凡,一样的普通,但是他们真诚、善良、宽厚、大度,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这个社会证明,“真”情还在;他们是生活中平凡的女性,可爱的精灵。所以,本文将结合吴刘维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深入探析其作品是如何表现这些小人物的独特之处的,怎样通过他们的精彩人生展现我们这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的。
一 智斗现实困境,为生存而战
我把吴刘维作品中的“小人物”,称为“勇毅的战士”,虽然他们没有浴血沙场,也没有丰功伟绩,不能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物质财富,但这些生存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靠着自己的智慧,凭借着不屈的毅力,在现实困境面前创造了一片生存的空间,在道德滑坡和精神失落的大背景下,为社会人心铺就了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康庄大道。
吴刘维十分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将“小人物”的生活片段一一呈现,在平平常常的小事情中充分展现“小人物”的心思和智慧,直白地将“小人物”的生存窘状表现在读者面前,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为反映小人物的反抗做了十分必要的铺垫。
《天堂无窑》中的三叔,从小就表现出让人看着心酸的节约,为节省墨水而把钢笔尖磨得极细,用手指头充当橡皮擦。这些我们或许还可以理解,但每次吃完饭都会:“拿盆子接半盆自来水,用调羹将沾在盆沿上的饭菜和油星,刮进水里,当成汤,一口喝下,再从口袋里掏出一截小篾条,将藏在牙缝中的饭菜一一剔出来,吞下喉去”,“每天上学,必定带着一个2斤装的空塑料酒瓶,用来装自己在学校拉的尿”,“每早起床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上茅坑,将自己的屎留在家里”,如果遇上肠胃不好,“便用塑料袋将自己拉的屎装了,和尿瓶一块搁在课桌脚边”,“将吃完泥鳅后残留在骨头缝里的肉丝一一挑出,伸出舌头舔了……”[3]看到此,读者们肯定会唏嘘不已。但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不可思议的细节描写,将三叔窘迫的生存境况细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直击读者内心。进入中年,三叔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好转,仍是精打细算地过着艰苦的日子。最后一次进城,他舍不得打电话,舍不得打的士,“弓背从夜晚一直找到第二天天明”才找到“我”家。为了维持生计,确保两个孩子顺利念完大学,三叔强忍着让他“疼得刻骨铭心的骨癌”,下到随时都有可能丧命的深井去挖煤。尽管生存环境如此恶劣,但三叔并没有自暴自弃、逆来顺受,反而在人生路上充满斗志,依靠自己的智慧,将已经趋近死亡的生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他自知即将离开人世,便提前买好自己出殡用的猪仔,提前与给尸体化妆的画师对接,让赤脚医生替他体检开具证明,提前买了意外保险,提前到省城与儿女留影并寄出遗嘱,然后在当天下泻药使8个亲人腹泻,独自一人下矿遭遇矿难。当所有人都以为三叔已死的时候,他的家人因此获得35万元的赔偿金,三叔也因他的智慧打赢了这场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战争。通过这个感人的故事,我们看到,沉重的生存负担燃起的是三叔对生活的激情,他对现实不公发起挑战,他要向世人宣告,即便是弱势者也能凭自己的智慧赢得胜利。同时,他以他的死激起了读者对于现实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愤慨。
《我岳父就这样老了》中的宋清明,同样是一个为生存而战的战士。作为一个生存在城市底层的规规矩矩、任劳任怨的小市民,作者对他的生存状态也进行了细微的且是渗透了同情的描绘。为了用老年证省下一块钱的车费,原本“魁伟”“节省”“干净”的男人,不惜尴尬地装丑扮老,到公厕里糟蹋自己的形象,将全身弄得很邋遢,即便是这样,也还是被公交司机识破,被乘客讥讽,最后连工作都丢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老人。这是一场滑稽的战斗,残酷的社会现实,迫使像宋清明这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小市民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他们斗志昂扬,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绞尽脑汁,其奋斗饱含人生的酸楚。
二 直面世俗重压,为信念而战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世俗化、功利化变得越来越明显,道德的沦丧,职业的歧视,人心的冷漠,已成为城乡中常见的现实状态。作为一个在这样的社会中摸爬滚打的作家,吴刘维对这样的现实尤其深恶痛绝。他于是塑造了一批貌似平庸的“小人物”,通过这些小人物高尚、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品质,表明向社会黑暗势力宣战的决心和毅力。
《送雪回家》中的陈子鱼,一个出生于毫无背景的底层工人家庭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当他怀揣梦想,准备节衣缩食、勒紧裤带地为生活而拼搏时,现实生活中买房、买车、孩子出国留学等切切实实的压力,使他产生了彻底的厌倦感和挫败感,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心灰意冷,没有像他的同事那般绝望到去自杀,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决定换一种活法,“甩脱婚姻的羁绊,免除房子、车子、妻子和孩子的重压,不再为物质世界所困,单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活”,于是他辞掉原有的工作,做起了一名浪迹天涯的旅游体验师,“背起行囊,独自去远方”。作者在文中这样写道:这“曾经是他少年时代萌发的梦想。想不到当自己从现实中背过身去,一脚便踏进了梦想中”,[4]以此告诉我们,只要学会在现实面前潇洒转身,梦想就在我们眼前。踏着他的梦想,作者为陈子鱼虚构了一个“帮帮帮”QQ群,通过这个群,陈子鱼接受了一个极其特殊的任务——把北方常见的雪,送到三亚一个从未看过雪、即将病逝的陌生老人手中。这样一个任务,在大多数人看来不可思议,“谁会专程坐飞机千里迢迢将雪从北方送往南方?送给一个原本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陌生老人?”陈子鱼却偏偏做了。这种毫无功利心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陈子鱼区别于世俗人心的伟大。作者用很重的笔墨,对陈子鱼送雪的艰难,进行了铺叙。首先是陌生老人说:“要是太为难了,请不要勉强。”[4]可见送雪之不易,连要求人都觉得勉强;其次,快递和物流两方面的压力——由于时间的限制,任务完成很艰难;而来自博士的压力,主要是其代表世俗的观念,因为在博士眼中,“送雪”这个任务只是“小孩子的把戏”,博士说:“你让我带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让我带雪!我怕别人说我脑壳有毛病”;另外还存在着飞机晚点的因素。但这些都没有使陈子鱼退缩、放弃,在他心中,陌生老人弥留之前的这个美好愿望,是值得自己为之努力并实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在现实世俗重压面前毅然转身的小人物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人物”与世俗背道而驰的高大,也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现今这个充满世俗功利的社会的不满。
在《有人落水》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勇斗现实职业歧视与社会人心冷漠的小人物形象。“他”,是一个在仕途升迁上遭遇重挫,刑满出狱后当了一名职业顶贴师,不愿与外面世界打交道的小人物。但当他看到有一个做“鸡”的女子落水等待救援,而旁人“全都拢在水边,驻脚张望,脸上起了惊异的神色,但谁也没有下河相救的意思”的时候,他毅然拖着他早已被酒精抽空、毫无力气的病体,奔向水中,救起了这个被大家疏远、歧视的女孩,而他自己因此失去了生命,此后,他用灵魂观看着这个冷漠的人世,但沈殿来的温情、善良,让他相信世间还有爱,最后他“乘着光芒,去往天国”。[5]作者叙述这样一个因勇救他人而离世的小人物去往天国的故事,表达了对现今社会人心冷漠的批判和对小人物高尚品质的赞美和欣赏。
在《绝望游戏》中,作者对都市社会黑暗的鞭挞,集中体现在一个叫周未兵的角色身上。他有两个卑微的愿望,给老婆买一枚真正的钻戒,给女儿买一辆电动车。为了这两个愿望,他努力地挣钱,顽强地与这个社会做着斗争,却一次次地陷入骗局,血本无归。恶梦一般的经历,使他神志不清,被送进了医院,当他清醒过来之后,留下一封遗书,自绝于江河。这是一个极端的故事,它向人们暗示着虽然新世纪已经到来,但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中才有的好人被逼至死的事件,继续在上演。周未兵的死,代表着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呐喊,它是用生命的消逝来唤起人们对社会弊病的反思。
三 不甘歧视屈辱,为平等而战
女性在我国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处于一种卑微的地位,她们任人践踏,深受夫权、父权、神权、族权的压迫及“三从四德”“节烈”等封建伦理的桎梏,她们中有的甚至没有名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与动物毫无两样,如鲁迅作品中的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萧红笔下的麻面婆、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金枝等,女性悲惨的命运,一直是作家们关注的话题。另外,关于女性的恶毒、放荡、阴狠、凶残,也是很多作家描写的重点,张爱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心经》中的许小寒、《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第一香炉》中的梁太太、《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十八春》中的曼璐等,一连串“病”了的女性,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人间无爱”的女性画面。然而,在吴刘维的小说中,她们虽然各自有着不幸,但仍是一个个聪慧善良、勤劳朴实、美丽无私、倔强孤傲的女子,没有一丝旧式的卑弱、顺从,在她们身上,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她们是这个时代难得的可爱的精灵。
《我岳父就这样老了》中的张德英,在她大大咧咧的外表下,包裹着一颗宁静脱俗的心。她清醒,现实,宽容,贤惠。她这样看待丈夫对她妹妹的爱:“男人都是猫变的动物,本性偷腥”,“与其让他宋明清偷偷摸摸地去打别的女人的主意,倒不如让他大大方方地去爱自己的妹妹,借此转移他对别的女人的注意力”,更不得了的是,“倘若丈夫去追求别的女人,终归是要付出成本的,这无疑会给家里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这成本花在自己妹妹的身上,也就不算是损失了。”[6]虽然这很现实,但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老婆的宽厚大度和她独特的家庭经营之道。
《送雪回家》中的鲁琪,面对一个一起为梦想拼搏了三年,却要中途放弃的爱人,面对着现实的打击、梦想的失落,她没有绝望,仍然死心塌地地陪在爱人身边,关心着他的起居饮食,支持着他的工作和事业,默默坚守,最终换回了一份真爱。
《绝望游戏》中的原莹,作为情人,她无所求,无所盼,不为钱,不为名,真诚大方,只为守住心中这份爱。她爱上的是事业有成、有妻有女的杂志社主编吴谷生,这样的感情在现实社会人眼中,无非是她看上了吴谷生的钱财和名望,但事实并非如此,她与吴谷生的爱情,是一种纯粹的你情我愿,没有欺骗,没有交易,她真诚地对待这份感情,不求任何回报,她的这份情是我们至今很多人无法企及的。作者在全文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对这段爱情进行描写,为我们开启了新的视野,使我们对情人有了新的定义,对爱情有了新的思考。《我岳父就这样老了》中的张瑞英,同样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情人。她无所顾忌地爱着姐姐的老公,但她爱得有节制、有方法。比如她和姐姐姐夫出门遇上下雨,只有一把伞,她会对姐夫说:“你看你怎么打伞的?你老婆一条胳膊都淋湿了!”“你就不能把伞往你老婆那边靠靠?对我好有什么用?对自己老婆好,才是真好!”所以,对于这样的老公情人,张德英“从没干涉过。不仅不干涉,似乎还有些纵容”。[6]她们的大大方方、真诚实在,其实是对我们现实社会情人与老婆之间剑拔弓张、你争我抢现象的强烈讽刺,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真情的一种期待。
同时,她们作为朋友,淡雅清婉,知性友善,能共患难,能在不经意间如清风拂面般扫清漫布你眼前的阴霾,开启你人生新的视窗。如《绝望游戏》中的卜心吟,虽然文中对她着墨不多,甚至对她的相貌、气质也没有专门交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她那淡雅、清婉的大姐形象。作者这样写道:“卜心吟像蛇,始终遵守游戏规则,而且特别爱干净讲卫生;也像狐狸,不单漂亮,聪明,也很精明,往往你一开口,她就晓得你要说什么;也像狼,卜心吟的生存本领很强,不单事情做得出色,方方面面的关系也协调得很好;也像幽灵,不讨你的嫌,不给你添烦,在你需要她的时候及时出现,在你不需要她的时候又悄然消失。”这样一个具有侠义心肠的女性,是吴谷生为数不多的异性朋友中最让他敬重的,这种敬重,不单是因为卜心吟是一位出色女性,更主要的是缘于这些年她对吴谷生的悉心关照。是她看中了他的才华,将他从农村调入城市,改变了他的一生,并且在以后的生活中时刻给予他关心,这样的朋友很难得。
还有,她们作为母亲,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用涓涓细流般的母爱,对孩子极尽呵护之情。《绝望游戏》中吴谷生的母亲,可以说是一代母性的代表。这位没有上过学堂、始终讲着幽陵县土话的农村妇女,无时无刻不在播撒对儿子的关爱:当她夺过父亲手中的电话时,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儿子为生活奔波的心疼;当她用剪刀剪掉报纸上蓝萍萍的眼睛时,我们感受到的是她不问情由、全力护犊的天然母性;当她送给儿子一双绣着“其实你不用去远方,好地方就在你身旁”的鞋垫时,我们收获的是一位不善言辞的母亲规劝儿子不要远行的感动;当她用针线绣出歪歪扭扭的“我儿谷生平安”时,我们感受到的是她对儿子绵绵、殷殷的母爱。她们的善良、憨厚、朴实以及无私奉献,令我们感动,她们是伟大的。
吴刘维通过塑造这样一群可爱的女性形象,多角度地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做了一次全面深刻的刻画,映照出她们渴求平等、积极向上的美好情怀。
《文学界》杂志的原主编水运宪,曾为吴刘维的作品写下这样的推荐语:“吴刘维喜欢独辟蹊径。他的小说,即使是描写庸常与琐碎,也能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味道。那种味道,缘自云淡风轻里的出其不意。他的笔调,也往往于诙谐或调侃中,暗藏机锋。”[7]的确,即便是描写众人皆为熟悉的“小人物”,吴刘维也很能将他们写出自己的味道来,他笔下的“小人物”不再卑微,不再羸弱,而是敢于向现实困境、向庸常世俗发起挑战,他们以行动向社会宣告,他们是一名战士,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战。吴刘维笔下“小人物”的精彩表现,让我们心生温暖,也让我们对未来生活满怀期望。
[1]吴刘维.创作谈:小说理应比生活更精彩[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3):85.
[2]吴刘维.创作谈:做小说的乐趣[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10):100.
[3]吴刘维.天堂无窑[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 (10):86-100.
[4]吴刘维.送雪回家[J].创作与评论,2013(8):47-63.
[5]吴刘维.有人落水[DB/OL].[2014-05-16].www.niemao.net.http://read.douban.com/reader/ebook/2007270.
[6]吴刘维.我岳父就这样老了[J].文学界·湖南文学,2013(2):4-24.
[7]水运宪.我的岳父就这样老了主编推荐语[J].文学界·湖南文学,2013(2):4-24.
责任编辑:黄声波
Displaying the Situation of Timesw ith Nobody——On the“Nobody”Image in W u Liuwei’s Novels
YU P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Changsha 410114 China)
Wu Liuweinarrates the trivial life of“nobodies”in the social change with serious attitude and ridicule language,and also describes the living condition of“nobodies”in the urban and rural society with keen thinking and plain language.Hisworks overturn the traditional resigning and ignorant image of“nobodies”,and meanwhile give them wisdom and passion.Moreover,he greatly praises and appreciates nobodies’seeking self-value maxim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rules,which presents the change of times situation from a special profile.
Wu Liuwei;nobody image;situation of times
I207.42
A
1674-117X(2015)01-0020-05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1.005
2014-07-25
余 佩(1989-),女,湖南长沙人,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