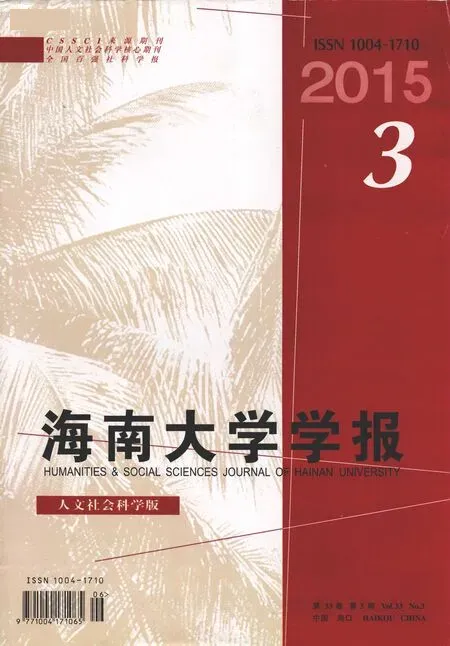略论西方现代小说中的“场所”及其生态意义
岳 芬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021)
“场所”(place)是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以及生态批评的重要概念①在布伊尔的《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中,“Place”一词也被翻译为“地方”。。环境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在《格里西湖是一个场所吗?》一文中为场所下了这样的定义:“就其最基本含义来讲,场所是指人类生命活动的背景环境。它是人类行为和意图的所在地,存在于所有的意识和知觉体验中。”[1]89这一定义的关键在于强调场所同精神之间的联系,场所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它意味着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场所的基础。正如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说:“地方的概念也至少同时指示三个方向——环境物质性、社会的感知或者建构、个人的影响或者约束”[2]70。
小说家对场所的思考始于18 世纪,在大部分传统小说作品中,场所是隐性的,它主要是指故事的自然环境,用于衬托人物存在的真实性,并为故事奠定情感基础。在20 世纪之后,自然环境不再是小说的边界,随着现代作家对自然和生态问题的关注,场所及其对应的生态观念逐渐成为小说的重要主题。场所成为沟通作者与自然之间的桥梁,通过对场所的塑造,作家从社会走向自然。场所具有基础性和指示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隐喻的场所暗示自然的存在状态,限定作品中主体的道德标准,并赋予主体以特有的审美感知力;另一方面,主体并非孤立地生活在场所中,而是处于“主体——场所”的相互关系之下,小说中的场所为主体的精神性存在提供多种诠释角度。
场所不仅是静止的序列,还拥有大的时代历史背景和自然时序。自然时序在小说中拓展了作为“背景环境”的场所的内涵,成为人物情感和心理变化的内在依托。自然还是小说原型的来源,小说场所随着自然的演替不断流转,情节的循环变换象征自然序列的改变。
一、“场所”的嬗变
场所这一概念几乎从小说诞生时就已经出现,在《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小说中,场所大多同荒野、孤岛等联系起来,它具有的自然属性远远多过社会性,它指示人与自然相处的早期方式。场所承载着人类探索世界的冲动与自然原始野性力量之间的对抗。场所及其美学象征意义也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只是自然的美学意义尚未超越其实用性,荒野的恐惧感尚未完全消失。
在18 世纪启蒙理性成为主流社会思潮时,浪漫主义者便开始在文化层面重建自然的形象,自然、荒野等词汇从蒙昧、恐惧逐渐转变为“善良”、“纯洁”,甚至庄严、高贵等词汇也被用于形容自然的美景②参见,戴维·佩珀:《现代环境主义导论》,宋玉波、朱丹琼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 页。戴维·佩珀在他的书中回顾了18 世纪以来生态观念的变化,他认为“原本被认为是与人类本性与理性相同一的前者,获得了善良、纯洁以及某些人类未曾谋面的观念;后者则从其所承载的恐惧与丑恶寓意那里,转而与纯洁挂上了钩。先前与宗教敬畏或畏惧相关联的世界之‘崇高’,开始被用于山川美景的描述之中:它的庄严、高贵与不同寻常激发出敬畏与讶异。‘有害的’也与合乎人意一道,在审美上被认可。”。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虽然它的初衷并非如是,但是它却为文学中场所的嬗变提供了契机,也为传统的自然观提供了新的内涵。
佩珀(David Pepper)认为,浪漫主义在两个方面对现代生态中心主义产生影响,即“释放、情感、激情、非理性主义以及主观主义”[3]224等浪漫主义特有的心理倾向和非凡人物的影响。相比而言,前一个方面显然更为重要,正是浪漫主义的心理倾向促进了自然场所的回归。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等人的诗歌成为这一转变的肇始。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则在小说方面为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开创了先例。在理性主义面前,浪漫主义更像是一种反抗的早期形式——“它显然是针对社会中的实质变化而发出的一种反抗,这些变化是与18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浮现与扩张相伴随的”[3]224。
从广义的生态批评角度来说,反省现代都市、歌颂田园牧歌生活以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18 世纪之后最重要的文学创作主题。小说家开始追寻浪漫主义者开创的道路,追求启蒙理性之外的情感自由,并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试图在现代城市生活之外描绘那些被遗忘的场所,如乡村、山谷、荒野等更具自然风貌的地方,以唤醒人的自然意识。到了19 世纪,小说家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更加深刻,启蒙理性的自然观遭到更多的质疑。小说创作者不再像湖畔诗人那样通过远离尘世的方法追寻自然和灵魂的安宁,而是直接干预社会,力图建立新的社会平等观,但是,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并没有为日益滑落的精神困境找到出路,相反,现实主义作家们却在不经意间巩固了自然的地位,并推动小说中的场所从社会走向自然。
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将小说叙事推向巅峰,也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边界消解,欧也妮·葛朗台最终只在她的花园里寻得灵魂的安放地,对现代社会精神状况的反思是早期浪漫主义自然观发展的结果。小说家们意识到,作为场所的田园或荒野不能完全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也无法扭转现代社会的道德下滑,他们必须要寻找另一种场所以寻回渐渐远去的自然。在他们的小说里,场所不仅包括自然的某个空间或地点,更重要的事,它象征了精神的存在方式。
雨果(Victor Hugo)的小说则在人道主义方面的思考拓展了公平、正义的内涵。雨果的人道主义可以被视作某种超越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之上的人的自然属性,人的存在首先应当是生殖和繁衍的自然本能,相应地,场所即成为人的本能和自然存在状态。这些思想实现了复杂的自然观念对单一社会伦理的超越,也为20 世纪环境伦理观奠定了基础。
在20 世纪,小说形式变得异常复杂,内容和主题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并没有抛弃18 世纪的浪漫主义回归自然的热情以及19 世纪以来的社会批判传统,只是在程度上要更深,对人类精神危机的思考也更为透彻。《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小说体现了浪漫主义的深度觉醒,它关注梦、记忆以及思想的内在变化,作者更希望在内心深处探索人类远离自然的原因,并期望在潜意识深处实现浪漫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回归自然的理想。《尤利西斯》将19 世纪的社会批判发展到极致,象征人类文明的现代都市变得毫无意义,生活其中的人时刻体验着孤独、荒诞和痛苦。《百年孤独》等作品强调场所的原型意义,场所在繁复的结构中变得捉摸不定,它不是确定的地点,也不是线性的时间,它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不断消解,实体与空间混淆不清。每一代人都在重复着上一代人的记忆和思想,最终又回到始点。所有试图突破自然宿命和生态循环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堪一击。场所还隐喻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对撞,带来外界消息的吉普赛人既是小镇的启蒙者,他们同时也带来了徬徨与惊恐。迷失的马贡多居民们在开放与闭塞之间徘徊不定。
另一些小说对生态问题的看法则更为极端。《乌拉尼亚》[4]继承了18 世纪以来的“乌托邦”传统,期望在堕落的现代文明之外建造一个新的文明之地。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设计了在现代文明之外重构乌托邦的方案,在勒·克莱齐奥的乌有之乡中,所有导致人类远离自然的规则和律法统统都被抛弃。类似的观念还表现在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乌托邦》[5]等作品中。此类作品里的场所更具生态理想主义色彩,或者说他们是在尝试建立20 世纪的生态乌托邦。
由此可见,场所在小说中的地位的变化反映了现代文明之下自然概念的演替,部分小说家开始主动从社会走向自然,并反思人类的精神困境。随着生态学观念的扩展,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一环,小说中的自然环境不再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而是情节变化和主题思想的内在驱动力。从浪漫主义的湖畔到反抗现代文明再到构建生态乌托邦,场所容纳了更多的理想、情结以及象征内涵。
二、场所与主体存在
从小说的发展来看,场所并非实实在在的空间,而被视作主体的存在方式,甚至是主体的一部分。“人的存在是什么,它的诗性在哪里?”[6]202这句话可以看作文学与自然的连接点,主体应当以何种形式存在于场所中是小说家思考的重要问题。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小说的艺术》开头引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于人的存在的讨论,他将二者意见综合并作出如下描述:“人原先被笛卡尔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dlt),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6]4米兰·昆德拉似乎更愿意将人类发展史描绘为人的精神性存在逐渐丧失的过程,它同时伴随着存在感的隐遁和自然的疏离。
随着存在主义哲学的扩展,对人物的描绘和情节的构建不再成为小说的重点,碎片化的叙事成为小说的主要形式。场所不再是独立于情节之外可有可无的点缀,它占据了小说的中心,主体几乎完全淹没在场所中,读者很难分辨场所与主体的区别。随着场所地位的提升,自然也获得了更多的叙事空间。小说家们开始越过审美的边界,从哲学和伦理学层面重新思考自然对于人类灵魂的意义。在一些小说中,山林旷野不再仅仅象征艰辛的生活和无休止的劳作,生活其间的人能够从自然中获取美感和愉悦。小说中主人公的幻觉刚好为作家逐渐丧失自我的精神生活找到新的寄托,作家的灵魂能够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幻境中寻觅安宁。尤其是在面对自然之时,作家能够得到真实的存在感。看似错乱的叙事非但没有剥夺小说的精神力量,相反却赋予他更多的诗意。
与传统小说相比,现代小说更好地描绘了作为观念的场所的生态意义。场所蕴含作家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一些作家更多地表现了他们对于主体存在的哲学思考。加缪(Albert Camus)赋予他的作品以存在主义的思辨,场所之于西西弗斯来说是永无休止的循环。在这样的作品里,场所即人生。同样,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作品,《恶心》中主人公罗康丹污秽龌龊的生活场所也是作品主体内心苦闷的外显。
另一些小说家通过复杂的结构来塑造场所。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习惯于将场所视作某种抽象的观念。场所的变化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线索,小说家通过场所来实现其创作思想,人物只是场所的一部分,他没有超越场所之外,也不能够独立地存在于时空中。在《树上的男爵》中,主角无法同其原有的家庭生活之间建立稳固的联系,相反,他与森林场所构成了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他只有在这一特定场所中才能找到存在的理由和意义。《看不见的城市》使得场所完全沦为一种观念,城市由最初的记忆转而成为想象,马可·波罗描述的城市同忽必烈汗想象中的城市融为一体。城市只具有观念意义,它并非实体,甚至仅仅是各种可能的场所。《帕洛马尔》则更深入地思考人的存在意义,这部小说读起来更像是一本哲学论著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故事。
总之,在部分西方现代小说中,主体的存在几乎完全融入到场所中,小说中的场所实现了生态主义者宣扬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作为场所的自然拥有主体同样的地位,并且构成了主体的存在基础。小说中环境与主体的关系超越人与环境的二元对立,场所应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是小说精神和生命的体现,包括场所与主体的相互关系、主体在场所中的存在方式体等问题,其内涵更接近拉伍洛克所提出的“盖娅”的定义③詹姆斯·拉伍洛克:《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肖显静、范祥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 页。在这本书中,拉伍洛克提出了“盖娅假说”等定义,他认为盖娅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包括地球的生物圈、大气圈、海洋和土壤,这些要素的全体组成一个反馈或控制系统,为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寻求一个最为理想的物理和化学环境。通过积极的控制,相关不变的条件得到维持,‘体内平衡’一词可以很方便地描述这种现象”。。
三、随自然流转的场所
小说中的场所几乎都是流动的,或者在空间和时间方面,或者仅仅在观念和意识领域。场所同情节保持一致,如同永恒流转的生态系统。
阿诺德·柏林特将《小径分叉的花园》视为景观生态学与小说的结合,他试图在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迷宫中寻找空间和时间的关联,他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是“一个体验的迷宫,一个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迷宫,而且,它是动态的——空间、时间和运动,三者同时发生而不可分开”[1]37。城市景观具有流动性特征,它能够存在于小说的想象世界中。流转的场所为小说对自然的描绘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其《批评的解剖》中分析作为原型的自然对于人物和情节以及作品结构的影响,自然四季对应特定的文学形式。在神话理论中,人的存在恰好是神谕世界的翻版:“人类的欲望和劳动施加于植物界的形式便是园圃、农场、树林、公园等。人类赋予动物界的形式,便是对各种动物的驯养,其中的羊历来在古典和基督教的隐喻中居于首位。人类赋予无机界的形式则是城市,这是人的劳动使石块变成的东西。”[7]弗莱虽然并未提到小说与自然以及神谕世界的关联,但是,从他对文学形式的分析来看,小说作为叙事的重要实现方式,同样是以模拟的方式来构造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抽象世界。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场所象征不同自然存在物及其各自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自然的生息刚好构成了小说时间的变化,小说借此完成其对自然的模拟。
在一些小说中,空间是被消解的,流动的时间替代固定的场所成为叙事主题。《双城记》中的空间转换对于小说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不同空间仅仅是为了突出时间的变化。在漫长的时间中,巴黎和伦敦的自然环境几乎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人的年龄却在不断衰老,记忆、仇恨也在随之变化。小说叙事主要通过时间的流转来完成,时间对于主体的作用显然要重要的多。《呼啸山庄》则用插叙的方式来描绘场所的突变,作为场所的时间占据了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的总体气氛是阴郁和压抑的,伴之以荒野、暗夜以及呼啸的风声,爱情、复仇、报恩等叙事主题纠缠在这样的场所中。相对固定的场所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遭遇,时间仍然是推动小说情节的主要因素。
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用流动的场所来展现自然对人类灵魂的影响,在《白鲸》中,船长亚哈对白鲸的追捕既是其个人偏执心理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带有复仇色彩的持续不断的追捕将人与自然的对立描绘得淋漓尽致,白鲸被描绘为恶魔,大海则隐藏着深广的恐惧、忧虑与痛苦。折磨亚哈的不仅有肉体的伤痛,更有噩梦般的记忆。对他而言,与自然搏斗是他存在的惟一目的。战胜白鲸的愿望让他完全迷失了本性,距离对手越近,他的精神也就越紧张,最终走向崩溃。
在西方现代小说中,场所地位的提升既来自于观念的变迁,更是由于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出现,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在科学与技术领域实现了许多奇迹之后,这个‘主人和所有者’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拥有任何东西,既非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渐渐撤离地球),也非历史的主人(他把握不了历史),也非他自己的主人(他被灵魂中那些非理性力量引导着)。”[6]52
人类无法给自己找到更好的借口来抵消因失去自然控制者的地位而造成的心理失衡。流动的场所在小说中具有捉摸不定的神秘力量,它处在潜意识的世界,对人类的行为构成影响,却无法被理性所把握,这也正是人类在面对自然时总是感受到焦虑的根源。
四、余 论
从18 世纪到20 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来看,文学也像现实自然一样,渐渐退出人类的视野,如同诗人在都市中隐去:“在人的脑子里,河流、夜莺和穿过草地的小径已经消失有些时候了。没有人需要它们了。当明天大自然从地球上消失时,又有谁会觉察到?奥克塔维奥·帕斯、勒内·夏尔的追随者在哪里?伟大的诗人在哪里?”[6]53
在西方现代小说中,消失的荒野既带走了诗人的激情也带走了小说家的灵感,丰富的自然经验已经不再成为小说叙事的重点,小说家们尽管竭力避免他们的作品成为毫无情感追求的技法训练,却未能阻止生态恶化和人类社会精神危机的日益加剧。小说家应当“消解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建构一件新的研究范式。”[8]这或许正是生态批评家和自然写作者未来努力的方向,如布伊尔所说,真正的生态批评家关心的是城市中“意外出现的自然迹象”[2]95,尤其是那些挣扎在城市缝隙中的自然生命及其场所。生态小说家试图“寻找人类与自然重归于好的和谐世界的新途径。”[9]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场所应当突破传统小说的话语界限,甚至成为小说的中心。
[1]阿诺德·柏林特.美学与环境——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M].程相占,宋艳霞,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2]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M].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戴维·佩珀.现代环境主义导论[M].宋玉波,朱丹琼,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勒克莱齐奥.乌拉尼亚[M].紫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80.
[5]欧内斯特·卡伦巴赫.生态乌托邦[M].杜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6.
[6]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99-200.
[8]陈新苗,汪东萍.生态审美视域中的西方当代文学审度[J].求索,2012(12):154.
[9]吴怀仁.皈依与升华:人类的诗意栖居——论当代生态小说的回归想象[J].江淮论坛,2011(5):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