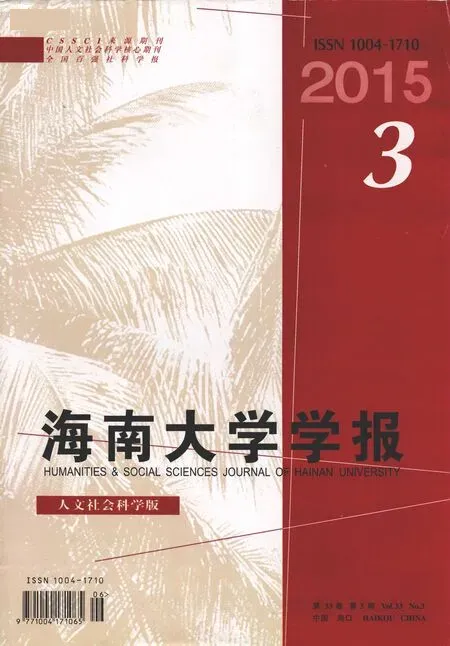论唐代文人对《法华经》的接受
张锦辉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禅诗,是一种融通宗教(禅)与文学(诗)的特殊创作,既包括受禅佛思想影响形成的禅意诗、禅境诗和禅趣诗,也包括示法、开悟等禅理诗、禅言诗。唐代文人禅诗,即唐代文人在创作中融入禅悟思维,以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为基础而形诸诗作,浸透着浓郁、强烈的禅学意蕴,具有一定的禅机、禅趣和禅意,渗透着醇醇禅韵和禅味。作为有唐一朝文学的代表——唐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对清人所编《全唐诗》和今人所辑《全唐诗补编》的检索,发现生活于大唐时代的文人,几乎都有诗歌流传下来。唐代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儒、释、道三教在相互融合中发展,正如吴怡先生所言:“在唐宋间的中国思想界根本是一个大熔炉。这时期,无论哪一家、哪一派的学说,都是兼有儒、道、佛三家的思想。”[1]由此造成唐型文化①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由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提出,傅先生在其文章《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对此做了详细论述,可参看。(傅乐成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的多元性,因此,在唐代很难说那位文人只受到一家思想的影响,他们的身上往往会呈现出多家思想的影子,而在这其中又以一家思想为主。唐代文人在浓厚的诗歌氛围熏染下,又直接接受禅宗教义的浸淫,那么作为其思想的载体——唐诗,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时文化的特色,文人禅诗即如此。在这些诗歌中,人们随处可以染指到禅宗思想的气息,相比于禅宗典籍的晦涩难懂、佶屈聱牙、缺乏艺术美感,文人禅诗在让人们享受唐诗无与伦比的艺术美感时,也有助于理解博大精深的禅文化。遍览唐代文人禅诗,发现里面涉及到很多法华意象,形成了唐代文人禅诗独特的法华特色。本文拟结合禅宗思想对唐代文人禅诗中出现的法华意象进行分析,探讨其蕴含的深层文化意蕴。至于僧人禅诗,如偈、颂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一
《法华经》全名《妙法莲华经》②《妙法莲华经》,梵文为:Saddharmapundarika-sutra。,它既是天台宗的教义理论,又被天台宗奉为经典。作为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僧叡大师在《法华经后序》中曾说:“《法华经》者,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2]它以大乘佛教般若理论为基础,蕴含着极为重要的佛学义理,吴言生师将其概括为“会通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实思想,诸法性空无所执着的超越思想、人人皆可成佛的佛性论思想等”[3]289,可谓指出此经之关捩。根据对总括历朝佛门高僧的四部《高僧传》③四部《高僧传》分别指:(梁)慧皎编《高僧传》,又称《梁高僧传》;(唐)道宣编《高僧传》,又称《续高僧传》;(宋)赞宁编《高僧传》,又称《宋高僧传》;(明)如惺编《高僧传》,又称《明高僧传》。和敦煌写经的统计,笔者发现当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法华信仰群体,即在大乘佛教诸经典中,持、念、讲、诵、注《法华经》的人数最多。至于《法华经》版本,学界论述颇多④秦丙坤在其博士论文《法华宗与隋唐文学》(四川大学,2006)中专列一节“《法华经》的版本”,对其做了详细论述,可参看。,且已取得共识,即以姚秦弘始八年(公元406年)鸠摩罗什大师译本为主。鸠摩罗什大师在文质兼顾的译经原则下,使得此经呈现出极浓厚的文学色彩,以致胡适先生看完此经不禁发出“《法华经》是一部富于文学趣味的书,……在中国文学上也曾发生不小的影响”的感慨[4]。所以历来不管是研治佛教思想,抑或佛教文学者,都对此经格外重视。关于其主要内容以及思想意蕴等,前贤论述颇详⑤张 海沙 先 生在 其专 著《佛 教五 经 与唐 宋诗 学》(北京:中华 书局,2012年版)中 对《法 华经》的地 位和 主 要内 容作 了 详细 论述,秦丙 坤在 其博士 论文《法 华 宗与 隋唐 文 学》中对 其 思想 蕴蓄 作 了详 细论 述,可 参看。,此处不再赘言。
产生于隋唐之际的禅宗,是印度佛教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后的一个高度中国化的产物,是异域外区文化(佛教)向内区文化⑥顾敦鍒 在《佛教与 中国 文化》一文 中,首 先阐明 了内 区、中 区、外区三 种文 化的区 别:“在中 心的文 化,像近中 心的 波圈那 样,是显殊 而有力的,这个区 域叫 做内区,或 中心区,或 发源地;一个 文化 由内区 向外 去推展,其 力量会 逐渐 衰减,这是文 化到 了中区 的普 遍性质;再 由中区向 外推展,这 种文化 力量 更趋微 弱,终至于 波平如 镜那 样,不 见迹 象,外 区文 化的性 质,大都如 此。”本文 在此采 用文 化内区、外 区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凝聚的智慧的结晶,其产生之影响南怀瑾先生概括甚是:
尤其在中国生根兴盛的禅宗,自初唐开始,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洪流,奔腾澎湃,普遍深入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在有形无形之间,或正或反,随时随处,都曾受到它的滋润灌溉,确有“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的功用。[5]
禅宗与《法华经》渊源很深,禅门典籍《五灯会元》中多处记载参禅者因持诵《法华经》而悟道,最典型的则莫过于慧能对法达的开示:
又有一僧名法达,唱诵《法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经上有疑:“大师智慧广大,愿为决疑。”大师言:“法达!法即正达,汝心不达,经上无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经。吾一生已来,不识文字,汝将《法华经》来,对吾读一遍,吾闻即是。”……大师言:“法达!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知见转法华,开众生知见被法华转。”[6]
”这段因缘发生在禅宗六祖与一度专修《法华经》的弟子之间,享誉禅林。《法华经》对禅宗的影响,吴言生师概括甚是:“《法华经》精警形象,使其极富哲理性与文学性,对禅宗思想、禅悟思维、禅宗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289生活于大唐时代的文人,在禅宗思想的濡染下,他们对《法华经》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正如张海沙先生所言:“文人普遍接受并崇信《法华经》与一般的社会成员的接受与崇信《法华经》有极大的不同,那就是文人由于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社会思考,对于佛教经典有自己的理解吸收、阐释与运用。文人之所以为文人,不仅是因为识文字、有文化,而且对于现实问题、精神世界、心灵皈依都会有热切的关注。”[7]换句话说,唐代文人汲取《法华经》的精髓不是盲目、被动地接受,而是在融合儒道思想的前提下,在继承中对《法华经》新颖奇特的譬喻,进行创造性的升华与转化,即他们将《法华经》的阅读与接受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在自己的禅诗中多次援引《法华经》意象,如衣珠、髻珠、药草、聚沙、一雨、火宅、三车、化城、龙女献珠、莲华等,形成唐代文人禅诗独特的法华景观。这些法华意象不能简单的视为一般的物态意象,每一个意象的背后其实都蕴含一定的审美意蕴和内涵,因此,法华意象除了构成《法华经》独特的譬喻艺术,增添《法华经》的文学性外,也在禅宗本心、迷失、开悟、境界⑦吴言生师在对佛禅经典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禅宗庞大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和境界论四大基石,本文在此沿用。这个体系中被赋予新的蕴含。
二
衣珠、髻珠——象征自家本心。衣珠、髻珠分别是法华七喻⑧《法华经》七喻,指的是《法华经》中七则最著名的譬喻:火宅喻;穷子喻;药草喻;化城喻;衣珠喻;髻珠喻;医子喻。之一,其中衣珠出自于《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
世尊,譬如有人至亲友家,醉酒而卧。是时亲友官事当行,以无价宝珠系其衣里,与之而去。其人醉卧,都不觉知。起已游行,到于他国。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艰难,若少有所得便以为足。于后亲友会遇见之,而作是言:“咄哉!丈夫,何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安乐,五欲自恣,于某年日月,以无价宝珠系汝衣里。今故现在,而汝不知。勤苦忧恼以求自活,甚为痴也!汝今可以此宝贸易所须,常可如意,无所乏短。”[8]547
髻珠出自于《法华经·安乐行品十四》:
文殊师利,譬如强力转轮圣王,……或与衣服严身之具,或与种种珍宝,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虎魄、象马车乘、奴婢人民,唯髻中明珠不以与之。所以者何?独王顶上有此一珠,若以与之,王诸眷属必大惊怪。……文殊师利,如转轮王见诸兵众有大功者心甚欢喜,以此难信之珠久在髻中,不妄与人,而今与之。[8]561-562
衣珠、髻珠喻不仅经常被禅门高僧用于开启学人,而且亦是唐代参禅、喜禅文人所常用之意象,例如岑参《晚过盘石寺礼郑和尚》:
暂诣高僧话,来寻野寺孤。岸花藏水碓,溪水映风炉。
顶上巢新鹊,衣中带旧珠。谈禅未得去,辍棹且踟蹰。[9]17
对于诗中的“珠”,有学者认为,“珠,指念珠,又名数珠,俗称佛珠,多以无患子(植物名)的果实做成,和尚每随身携带,念佛时用以记数。”[9]17即认为此珠为一般的普通佛珠。然而结合岑参一生与禅佛的关系看,笔者发现此“珠”并非一般念珠,而是象征参禅者本自具足的清静本性,也就是澄明佛性。作为得道高僧郑禅师,当他觉察到修行者的根机成熟时,便通过外在的机缘促使潜伏于修行者烦恼之下的佛性自觉产生,此时修行者则蓦然发现“明珠原在我心头”,就如同游子发现衣中宝珠一样。岑参此处借用《法华经》中的“衣珠喻”,其旨在于凸显郑和尚澄明心性和对禅佛智慧的彻悟。因此,在赏析这首禅诗时,切不可被“衣珠”表层语义所诱导,必须透过其表层语义挖掘其蕴含的象征义,这也就是元代杨载在《诗法家数》中所说的:“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10]另外再看卢纶《送契玄法师赴内道场》:
昏昏醉老夫,灌顶遇醍醐。嫔御呈心镜,君王赐髻珠。
降魔须战否,问疾敢行无。深契何相秘,儒宗本不殊。[11]3129
全诗写诗人送契玄法师赴内道场的情形,诗人以昏醉老夫自称,昏醉不仅指肉体上的昏醉,更指精神上的昏醉,即内心的迷茫。可是在遇到契玄法师后,诗人如醍醐灌顶,此时自己的的本源心性也正如髻珠一样显示出来。此外还有:
灯明方丈室,珠系比丘衣。[11]1371(綦毋潜《宿龙兴寺》)
苔封石锦栖霞室,水迸衣珠喷玉蝉。[11]8762(谭用之《送僧中孚南归》)
破暗衣珠明有焰,照窗心月净无尘。[11]10277(郁回《题照上人院》)
观心同水月,解领得明珠。[12]631(李白《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
新戒珠从衣里得,初心莲向火中生。[13]3835(白居易《吹笙内人出家》)
《法华经》以珠比喻大智慧,人人本具的佛性,禅宗创造性地将此二喻理解为人的本源心性。衣珠、髻珠,在禅宗看来其实就是人们的本来面目⑨吴言生师在《禅宗哲学渊源·禅宗哲学本心论》中对“本来面目”是这样解释的,“‘本来面目’又叫‘本地风光’、‘本觉真心’、‘本分田地’、‘自己本分’等,是本来的自己,人人本具,超越一切对立。”做了详细阐释,可参看,本文在此借用。(吴言生:《禅宗哲学渊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4-225 页),参禅悟道的终极目的就在于明心见性,在于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回归人最本初的状态,也就是“一个没有‘隔’的活泼自由天地,没有束缚的清净无邪心灵”[14]。但是对于参禅者而言,要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即所具有的佛性,却并非易事。对此吴言生师说道:“‘衣珠’、‘髻珠’对禅的参学具有很强的宗教实践性,它使人生发出在生死之中获得涅槃的体证,树立本心是佛,自己作佛的自信,培植起勇于承当的勇气,从而明心见性,荷担如来家业。”[3]295唐代文人在宦海沉浮中摸爬滚打,他们虽然外服儒行,但是内心却私淑佛禅,尤其是在感到空虚、迷惘时。换句话说,入世的儒学理想主义固可维系“光明”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信仰,但“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严刑峻法,却不能不露出“光明”之下的黑暗和恐怖,以致使得统治者、依附者和被统治者有着不同程度的不安和痛苦。当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这个夹缝中走钢丝时,利用或寻求禅佛精神上的调剂和庇护,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在诗文中使用“衣珠”、“髻珠”也是情理之中。在禅宗思想的指引下,去探寻自己迷失已久的本心,也就是人们的那颗“童心”⑪五浊,即五种妄识,包括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回到人的原初状态,重现自己的诗性生命和永恒智慧,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另一片乐土,诗意地栖居在禅天禅地中。
三
穷子、火宅——本心的迷失。“穷子”出自于《法华经·信解品第四》:
世尊,我等今者,乐说譬喻以明斯义。譬若有人年既幼雅,舍父逃逝久住他国,或十、二十至五十岁。年既长大加复穷困,驰骋四方以求衣食,渐渐游行遇向本国。其父先来,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其家大富,财宝无量,金银、琉璃、珊瑚、虎珀、玻璃珠等,其诸仓库悉皆盈溢,多有僮仆、臣佐、吏民,象马车乘牛羊无数,出入息利乃遍他国,商估贾客亦甚众多。时贫穷子游诸聚落,经历国邑,遂到其父所止之城。父母念子,与子离别五十余年,而未曾向人说如此事。但自思惟,心怀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财物,金银珍宝仓库盈溢,无有子息,一旦终没,财物散失,无所委付。是以殷勤每忆其子,复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财物,坦然快乐,无复忧虑。”[8]527
“火宅”源于《法华经·譬喻品第三》:
舍利佛,若国邑聚落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僮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多诸人众,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阁朽故,墙壁隤落,柱根腐败,梁栋倾危。周匝俱时欻然火起,焚烧舍宅。长者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即大惊怖,而作是念:“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隐得出,而诸子等于火宅内乐着嬉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火来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厌患,无求出意。”……尔时,长者即作是念:“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时出,必为所焚。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乐着,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与汝。”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珍玩之物适其愿故,心各勇锐互相推排,竞共驰走争出火宅。[8]521-522
此经以“火”比喻五浊、八苦⑪1等,以“宅”比喻三界。禅宗将“穷子”喻创造性地理解为修行者精神的流浪,将火宅视为妄心产生的温床。在唐代文人禅诗里,这两个意象也是随处可见,如杜甫《山寺》:
野寺根石壁,诸龛遍崔嵬。前佛不复辨,百身一莓苔。虽有古殿存,世尊亦尘埃。如闻龙象泣,足令信者哀。使君骑紫马,捧拥从西来。树羽静千里,临江久徘徊。山僧衣蓝缕,告诉栋梁摧。公为顾宾从,咄嗟檀施开。吾知多罗树,却倚莲华台。
诸天必欢喜,鬼物无嫌猜。以兹抚士卒,孰曰非周才。穷子失净处⑫下划线为笔者所加。,高人忧祸胎。
岁晏风破肉,荒林寒可回。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婴孩。[15]1059-1061
诗人一开始在展示山寺佛像蒙尘,破败荒凉,颓隳不堪景象时,也暗示出安史之乱给社会带来巨大重创,连山间寺庙也未能幸免于难,呈现出荒凉凋敝状。接着写梓州刺史章彝⑬根据此诗小序“章留后同游”,我们可以断定“使君”即为留后章彝。慷慨檀施,对于章彝此举,清代杨伦在《杜诗镜铨》中言:“大抵彝之为人,将略似优,乃心不在王室。是冬天子在陕,彝从容校猎,未必无拥兵观望坐制一方之意。公窥其微而不敢颂言,因游寺以讽喻之。”[16]可谓指其本质。“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成为全诗讽喻的关捩,“穷子”虽舍父逃走,但终归迷途知返,认父为亲,归于“净处”。而杜甫在此借用“穷子”,实指章彝拥兵自重,坐镇一方,不报效朝廷,反而处于观望状态,颇有舍父不归的意向。而诸如“龙象”所泣、“信者”所哀,看似是在烘托山寺的荒凉、山僧的落魄,实则是将“穷子”不识父所所带来的后果展示出来。穷子不识本心,逐物迷己,迷己逐物,放弃自家无尽宝藏,沿门持钵乞食,最终失去自已原本美好的精神家园。这样,杜甫通过对《法华经》中“穷子”喻的创造性改造,希望以此去告诫章彝,引起他的反省。最后诗人吟出“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婴孩。”道出杜甫当时复杂的心情:自己步入仕途多年,可到头来还是贫苦得象一个婴孩一样一无所有,也反映出自己内心迷茫的痛苦。如果说“穷子”喻道出不识本心的痛苦,那么火宅喻则直接传递出文人自己内心的不安,如白居易《自悲》:
火宅煎熬地,霜松摧折身。因知群动内,易死不过人。[13]1070
又如《赠昙禅师》:
五年不入慈恩寺,今日寻师始一来。欲知火宅焚烧苦,方寸如今化作灰。[13]1105
在唐代诸文人中,相比之下,香山居士白居易也算得上得意之人,不仅官职高,而且也是唐代文人中为数不多活到七十多岁的,但是,早年生活的艰辛和入仕后心系苍生,对现实的密切关注,使得他的内心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更易于感到矛盾与煎熬。世俗社会中的功名、权贵都在困扰着他,成为禁锢自己的枷锁,让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等到醒悟,最终留给他的只是幻灭,就如同身处火宅,内心蒙昧迷失,让其备受煎熬。所以,火宅喻也最能表达出唐代文人对于现实世界的感受:
始悟尘居者,应将火宅同。[11]3168(卢纶《同崔峒补阙慈恩寺避暑》)
乘闲无火宅,因放有虚舟。[17]117(沈佺期《从驩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
定应邻火宅,非独过焦原。[11]5817(李敬方《题黄山汤院》)
幻身观火宅,昏眼照青莲。[11]5517(李绅《题法华寺五言二十韵》)
《法华经》以穷子、火宅喻象征澄明本心的迷失与溷扰,禅宗将其作为本心迷失的象征,指出“父母未生以前,净裸裸,赤洒洒,不立一丝毫。及乎投胎,既生之后,亦净裸裸,赤洒洒,不立一丝毫。然生于世,堕于四大五蕴中,多是情生翳障,以身为碍,迷却自心。”[18]296可是随着二元相对意识的生起,世人蒙受情尘欲垢的翳障,迷失本心,以致于出现“迷头认影”、“舍父逃走”、“抛却家宝”、“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一幕幕闹剧,也正像吴言生师所说的:“正是由于对诸尘外境的执着,世人遂失去了‘本来面目’,而追逐俯就秽浊之物,在情天欲海里漂泊沉沦,导致了生命本真的斫丧。逐物迷己,迷己逐物,生命便如陀螺般旋转,无有了歇之期。”[19]对于生活在大唐那样一个尘世纷扰的社会里,敏感而又好表达的文人自然会接受禅宗思想的熏染,此时《法华经》中的这个譬喻无疑使他们眼睛一亮,在不敢直接批判现实的情况下,《法华经》中的穷子喻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成为他们批判现实和反观自身的武器,即通过对禅佛经典中特殊意象的使用间接达到讽喻劝谏之目的,收到借禅佛以援儒的功效。
火宅喻道出了当时文人内心的真实情景。自唐实行科举制以来,庶族地主阶级甚至出身于贫寒家境的文人们也看到了希望,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他们读书的功利性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得不在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社会现实中处处就范,甚至摧眉折腰。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的摧眉折腰就似被囚禁在火灾中一样,让其内心充满了煎熬与不安。虽然他们早已规划好自己的人生蓝图:科举及第—仕宦从政—施展抱负—建功立业—归隐山林,可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所有功名事业乃至荣华富贵都不可能永久长驻,最终留给自己的只是幻灭的感受。换句话说,他们中更多人迷失了自家的本心,以致于不能坦然面对生活,所以一旦获释,则觉得神清气爽。总之,如果不能体认自家的澄明本性,那么就不能做回自己的主人公,其结果必然导致精神上越来越难于高蹈振举。
四
三车、化城——本心的升华。“化城”是法华七喻之一,源于《法华经·化城喻品第七》:
譬如五百由旬险难恶道,旷绝无人怖畏之处,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珍宝处。有一导师聪慧明达,善知险道通塞之相,将导众人欲过此难。所将人众中路懈退,白导师言:“我等疲极而复怖畏,不能复进。前路犹远,今欲退还。”导师多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作是念已,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众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还。今此大城,可于中止随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隐!若能前至,宝所亦可得去。”是时疲极之众,心大欢喜叹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恶道,快得安隐!”于是众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隐想。尔时,导师知此人众既得止息,无复疲倦,即灭化城,语众人言:“汝等去来,宝处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为止息耳!”[8]538
三车喻出自《法华经·譬喻品第三》:
尔时,长者即作是念:“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时出,必为所焚。……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尔时,长者见诸子等安稳得出,皆于四衢道中露地而坐,无复障碍,其心泰然欢喜踊跃。时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许玩好之具,羊车、鹿车、牛车愿时赐与。”[8]522
三车即鹿车、羊车和牛车,比喻缘觉、声闻和菩萨三乘。要想获得开悟,必须超越各种对立,跳出二元窠臼。因此在禅宗看来,三车、化城便成为开悟的典型象征。唐代文人在自己的诗歌中也多次借用此意象,来象征解脱,脱离桎梏,如孟浩然《陪张丞相祠紫盖山述经玉泉寺》:
五马寻归路,双林指化城。闻钟度门近,照胆玉泉清。[20]
这是孟浩然陪同张九龄祭祀紫盖山途经玉泉寺时所作的一首诗,此时的张九龄已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面对眼前的玉泉寺虽有归隐之志,但王命在身,也只能是心往,相反陪同的孟浩然则将化城作为了自己的归路。王维则将“化城”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如《游感化寺》:
抖擞辞贫里,归依宿化城。绕篱生野蕨,空馆发山樱。[21]439
在《与苏卢二员外期游方丈寺而苏不至因有是作》中:
闻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安知不来往,翻得似无生。[21]340
把“化城”作为与同道相邀期会的美好宿址,化城成为他和友人的休歇之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大诗人李白也对“化城”表现出极大好感,在《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中是这样描述“化城”:
化城若化出,金榜天宫开。疑是海上云,飞空结楼台。[12]964
直接把化城想象成为海上片云结构的楼台,为他畅游天宫提供方便。李嘉祐《故燕国相公挽歌二首》:
大梦依禅定,高坟共化城。自应怜寂灭,人世但伤情。[11]2160
“化城”成为象征逝者的归化之途。此外还有如:
化城分鸟堞,香阁俯龙川。[22](骆宾王《四月八日题七级》)
因心得化城,随病皆与药。[11]1322(崔颢《赠怀一上人》)
郡有化城最,西穷叠嶂深。[11]1371(綦毋潜《登天竺寺》)
百丈化城楼,君登最上头。[11]3919(欧阳詹《和严长官秋日登太原龙兴寺阁野望》)
已悟化城非乐界,不知今夕是何年。[23](戴叔伦《二灵寺守岁》)
鹭涛清梵彻,蜃阁化城重。[11]3724(杨巨源《供奉定法师归安南》)
真相有无因色界,化城兴灭在莲基。[11]5513(李绅《龙宫寺》)
闻道化城方便喻,只应从此到龙宫。[11]5515(李绅《水寺》)
晓随樵客到青冥,因礼山僧宿化城。[11]2991(耿湋《宿万固寺因寄严补阙》)
邀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24](刘禹锡《贾客词》)
化城在唐代文人笔下成为他们心灵的栖息地,可以使他们于世俗生活中获得短暂的休歇。三车喻的使用,则使唐代文人在休歇之后看到了解脱的途径与希望,他们也从这里获得安慰与寄托。如宋之问《游韶州广界寺》:
宝铎摇初霁,金池映晚沙。莫愁归路远,门外有三车。[17]550
从繁华的帝都长安被贬到尚未完全开化的岭南,诗人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情形下,宋之问将“三车”作为自己精神的依靠。岑参《赴嘉州过城固县寻永安超禅师房》:
门外不须催五马,林中且听演三车。岂料巴川多胜事,为君书此报京华。[9]310
安史之乱后,岑参任嘉州刺史,此时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先前。赴任途中,相反他更愿听禅师给他讲演三车而推迟行程,并将这次听演三车作为巴川之盛事特意作诗报告给远在京华的亲友。对现实有着超脱之想的李白对三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12]406(李白《僧伽歌》),呈现出一种对禅佛的皈依倾向。杜甫于蜀中生活时,同样也是把听讲演三车作为自己生活的寄托,如在《上兜率寺》直接引用“白牛车”喻:
兜率知名寺,真如会法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
庾信哀虽久,何颙好不忘。白牛车远近,且欲上慈航。[15]992
此诗首联、颔联在写景,颈联、尾联重言情。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诗人来到梓州兜率寺,首先对兜率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作了介绍,放眼望去,江山兼有巴蜀,栋宇起自齐梁。颈联以周颙向佛自比,据《南史》所载:周颙“长于佛理,著《三宗论》言空假义。……颙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清贫寡欲,终日长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舍。”[25]所以言“好不忘”,足见杜甫对佛理的倾心接纳以及对佛法的由衷向往。尾联诗人没有选取羊车、鹿车,而直接欲驾“白牛车”以上慈航。与三年前所作“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15]727(《酬高使君相赠》)形成明显对比,可以看出杜甫他追求的是大乘佛法,将大乘佛法看做是实现自己心灵解脱的清凉剂,流露出欲乘白牛车登上佛乘“慈航”的愿望。白居易《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皆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
莲静方依水,葵枯重仰阳。三车犹夕会,五马已展装。[13]1152
一向要求诗歌要泄导人情,要有补于时政的白居易此时也通过三车来寻求心灵的解脱。此外,诸如:
高岫拟耆闍,真乘引妙车。[17]513(宋之问《游法华寺》)
殷勤结香火,来世上牛车。[11]2026(张谓《送僧》)
一尘多宝塔,千佛大牛车。[11]8563(陈陶《题居上人法华新院》)
谕鹿车虽设,如蚕绪正棼。[26](元稹《大云寺二十韵》)
谩夸鹙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27](李商隐《题白石莲花寄楚公》)
化城、三车喻在禅宗看来,它们象征着本心的升华。禅宗认为,人由于分别意识的生起,迷失本心,失去了本来的精神家园。那么如何重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呢?禅宗认为,必须“以铁石心,将从前妄想见解、世智辩聪、彼我得失,到底一时放却,直下如枯木死灰,情尽见除,到净裸裸赤洒洒处,豁然契证。”[18]316-317《法华经》中的化城只是一个暂时的止息之所,导师(即佛祖)很快就超越了它。禅宗将“化城”视为中道休歇之场,在这个短暂的休歇场所,个体借助三车,获得心灵的升华。唐代文人将渗透着宗教时空意识和人生感悟的“化城”、“三车”喻从宗教义理中引申出,经过夺胎换骨式的转化性的创造,纳入自己诗性思考和诗性表现的精神世界之中。当他们被生存困厄束缚压抑得走投无路时,此时他们只好借助禅佛来进行自我解脱,所以化城、三车喻也反映出唐代文人对禅佛的向往,所以胡遂先生说:
林泉固然可“隐”,但若谈到真正的“逸”,恐怕佛门更具有一种从精神上完全超越而不仅仅只是超脱于世俗社会的作用。只有放弃儒门而归依佛门,才能使这种从现实社会中逃离的行为不失清高体面,才能因“理得”而“心安”。[28]
只有通过栖心佛禅,他们才能获得心灵的升华和开悟,才能体会到生命的终极本质,而这也正好是禅的本质,正如铃木大拙先生所言:
从本质上看,禅是一种见性之法,并为我们指出挣脱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由于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源泉,使我们摆脱那让有限的生命常常在世界上受苦的一切束缚,因此可以说,禅释放出自然而又适当地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切活力,在普通情况下,这些活力是被阻挡并歪曲因而找不到适当活动的机会。[29]
所以,《法华经》中的化城、三车喻经过禅宗创造性的改造,在唐代文人笔下具有了新的意蕴,“在某种意义上都体现了诗人对当下现实的暂时逃离,对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一种能够安顿自己心灵的精神境界的寻访”[30],让他们在诗意的大地上,摆脱束缚,自由自在,无所牵挂,恬静而轻松,实现精神解脱,获取心灵升华。
五
一般来说,“一个语词所获得的语义内涵总有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稳定性”[31],可是一旦进入不同的场域,组合成不同的意象,其往往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特质,法华意象即是。法华意象作为特殊的“词”在唐代文人禅诗中频繁出现,它在呈现佛典本原义时,也被唐代文人赋予新的意蕴,即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已经成为涵摄社会意识的压缩体,在透露唐代文人审美情趣和个体理想的同时,也传递出社会思想界的真实状态: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文人对法华经的喜爱,佛禅精深的义理已被他们所接受,并逐渐融入意识之中;另一方面从侧面也可看出当时佛禅典籍流传之广度与深度。唐代文人以法华意象来传达诗情,在禅宗思想的浸润下,法华意象也呈现出新的内在蕴蓄,即衣珠、髻珠象征本心;穷子、火宅象征本心的迷失;化城、三车象征本心的升华。唐代文人将法华意象凝重丰厚的底蕴渗透于笔端,使得世间诗情与出世间佛理得到不同程度的融合。可见,文人对于佛禅典籍的接受与运用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换句话说,即他们赋予佛禅经典新的内蕴。
唐代文人在禅宗思想的指引下,对法华意象的创造性使用,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将禅化为一种体验,一种感情,扩散到自己生命的深处。“通过对这种生命境界的默认和把握,使人的身心达到一种圆满无碍、自在丰盈的状态,使人从心之迷执和生之痛苦中解脱出来,生命得到完全充分的肯认。”[32]所以当他们在驾驭这些法华意象时,这些法华意象也伴随着诗人不同的视境和心境在“能指”与“所指”的张力空间中处于不同的意义深度,无论从其自然物象层还是从其象征意蕴层都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召唤潜质,成为唐代文人禅诗中一道靓丽的法华景观,遂使《法华经》意象的精澹澄美和蕴蓄丰饶与禅韵诗情交相辉映,对形成唐诗丰厚凝重的文化底蕴,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具有禅意美的中国文艺,一方面由于多借外在景物特别是自然景色来展现心灵境界,另一方面这境界的展现又把人引向了更高一层的本体探求,从而又进一步扩展和丰富了中国人的心灵,使人们的情感、理解、想象、感知以及意向、观念得到一种新的组合和变化。”[33]
[1]吴怡.禅与老庄[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5:28.
[2]僧佑.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306.
[3]吴言生.禅宗思想渊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胡适.白话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7.
[5]南怀瑾.禅与道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93.
[6]郭朋.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81-82.
[7]张海沙.佛教与五经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221.
[8]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M]∥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5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9]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736.
[11]彭定求,沈三曾,扬中讷,等.全唐诗[M].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
[12]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4]葛兆光.门外谈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
[15]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79.
[17]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8]圜悟克勤.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12[M].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
[19]吴言生.禅宗哲学象征[M].北京:中华书局,2001:253.
[20]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8.
[21]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2]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5.
[23]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44.
[24]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262.
[2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894-895.
[26]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2.
[27]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19.
[28]胡遂.佛教与晚唐诗[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8.
[29]铃木大拙.禅风禅骨[M].耿仁秋,译.杨晓禹,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9.
[30]黄雪敏,林丹纯.唐诗“寻访不遇”主题的审美探析[J].江淮论坛,2012(1):162.
[31]葛兆光.禅意的“云”:唐诗中一个语词的分析[J].文学遗产,1990(3):81.
[32]庄穆.佛教哲学的致思趋向及其现代启悟[J].现代哲学,1997(2):67.
[33]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M].上海:三联书店,198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