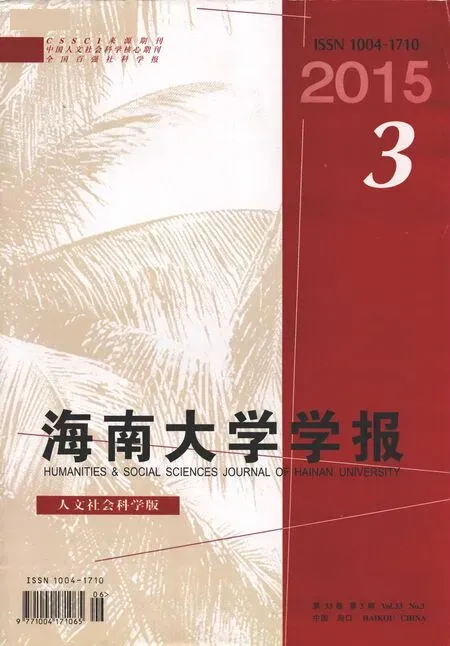汉唐小说文体演进与书牍文之关系
何 亮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1331)
书牍文是中国古代书信的总称。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呈兴盛之势。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春秋聘繁,书介弥盛。”[1]277书牍文产生之初,包括臣僚敷奏、朋旧往来两类文字。然随着文体的发展,书牍文后来成为朋友之间往来书信的专称,而奏章则从书牍文中分化,成为另一种文体类型:“考汉代书信……所写均系个人在政治生活、社会关系中的自我遭遇、经验、感受与见解。很明显,书牍已与奏书分道扬镳。”[2]书牍文主要写一己之遭遇,可叙事、议论,也可陈情,不拘文笔骈散,不限辞令雅俗,形式自由、灵活,内容真实,感情真挚,绝少浮夸、雕琢之气,有自己的特点和实际功用。
书牍文因其特殊功能而被汉唐小说吸收,成为小说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研究者虽对此进行了探讨,如日本学者内山知也在《隋唐小说研究》中分析了书简文在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莺莺传》等中的作用[3],但较少研究者从整个汉唐小说发展史的视野,对融入其中的书牍文进行全面梳理,系统考察书牍文的渗入对汉唐小说文体演进的影响。本文在对融入汉唐小说的书牍文进行详细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体学、文本学等理论与方法,阐释其对汉唐小说文体演进的意义。
一、融入汉、唐小说中书牍文的特点
汉魏六朝、唐代小说中的书牍文,受书牍文体自身在当时发展程度的影响。不仅如此,因融入的篇幅、数量、表现方式存在差异,唐代小说比汉魏六朝小说更能体现书牍文体对小说的渗透。
汉魏六朝时期,涌现了不少书信杰作,司马迁《报任安书》、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等是其中之佼佼者。史籍运用书牍文,以及书信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为小说提供了模本和范本。据现存的小说文献,《燕丹子》最先使用书牍文。如太傅写给燕丹子的《报燕太子书》,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层层递进,表达了太傅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不能派遣刺客刺杀秦王的理由,并指出了应对当前危机局势的举措。太傅在信中,丝毫不顾及燕丹子是太子的特殊身份,措辞犀利、直接,语气强硬,表现出策士不惧威严、敢于畅快淋漓地陈述自己政见的风骨。太傅和燕丹子往来的书信,在揭示人物思想和个性的同时,也为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埋下伏笔。又如《西京杂记》“飞燕昭仪赠遗之侈”条,仅用一句话简明扼要地交代飞燕与女弟相居两地,女弟传书飞燕的情况,接下来的正文全部都由书牍文构成,书牍文成为这篇小说的主体:“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嘉辰,贵姊懋膺洪册,谨上禭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心……”[4]昭仪在信中陈列送给赵飞燕的礼物“清单”,极尽人间之珍贵稀罕者,令人眼花缭乱。赵飞燕姊妹之奢靡,由此可见一斑。此条与“昭阳殿”、“送葬用珠襦玉匣”、“鱼藻宫”、“乐游苑”等相互映衬,从住所、玩乐、服饰、饮食等不同层面,反映了宫廷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西京杂记》“邹长倩赠遗有道”、《搜神记》“韩凭妻”、《拾遗记》“周灵王”、《语林》“庾公”、《异苑》“江神祠”、《幽明录》“阮瑜之”、《世说新语》“习凿齿”、《殷芸小说》“杜预书信告儿”、《述异记》“棋友”、《续齐谐记》“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等约40 条,都有或长或短的书牍文。
融入汉魏六朝小说中的书牍文与书信在此时期的发展,并不同步。汉魏六朝时期的书信,用词典雅、精工,讲究对偶、词藻:“在汉魏六朝散文逐渐骈化,骈文最终形成的过程中,书牍类文章是最早骈化的文体之一。汉魏之际是文章急剧骈化的时期,其间骈文对偶、用典、藻绘等艺术特点,在书牍文中,都较其他文体表现得更为典型。”[5]汉魏六朝小说中的书信,除《续齐谐记》“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张子房与四皓书”、“曹公与《杨太尉书》”、《燕丹子》篇幅较长,是完整引用外,其余各篇往往截取信件中与故事相关部分,多是三言两语,极其简短,仅作为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之用,艺术价值有限。
小说发展至唐,使用书牍文的作品数量不仅逐渐增多,有的词情并茂,文质兼美,写法富有艺术气息。这样,书信不仅是工具,还尽显小说作者之才华,成为一种美文。
唐代的书牍文,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初唐时期,文风继六朝之余绪,作者完全把书信当做一种专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进行创作,崇尚辞藻,追求雅致。“至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之时,以散体文代替了骈体文,并提倡‘载道’文学,要求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要有实际的社会效用,要‘惟陈言之务去’。……使作为文章一体的书信别开生面地走上了广阔的道路。”[6]古文家柳宗元留下不少与至交好友或晚生后辈交流思想、说文论道的书信,大多行文流畅,说理透彻,是不可多得的书牍文杰作。
唐代小说中的书牍文,与书牍文在唐代的发展步调一致。初唐小说中的书信,语句以四六为主,对偶精工,文辞华美。到了中唐,小说中书信的风格为之一变,多情真意切,不加雕饰,更真切地展现了故事人物的心理。据笔者统计,唐代小说使用书牍文的单篇传奇小说有张鷟《游仙窟》、元稹《莺莺传》、薛调《无双传》、牛肃《吴保安》等;小说集中融入了书牍文的篇目有张说《开元天宝遗事·梁四公记》、牛肃《纪闻·裴伷先》、赵自勤《定命录·梁十二》等50 多篇。唐代小说使用书牍文的数量,虽不如其使用的诗、辞赋、骈文、论说、史传等之多,但远远超过碑铭、判文、词、祭诔文等。唐代小说使用书牍文叙述,主要有完整引用、摘录、转述三种情形。
1.完整引用 唐代小说以引用完整书信来进行小说叙事的具体篇目有《梁大同古铭记》、《浮梁张令》、《非烟传》等。这些篇目使用完整书信叙事,书牍文是小说的主体。如《梁大同古铭记》,任升之在钟山圮岸悬圹中得古铭,上有37 字隐语,学官们集中讨论数月,仍然不能知晓其意。于是,任升之写信给钦悦,请他探发微旨:“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乐安任升之白。”[7]3762-3763书信以“升之白”领起全文后,即进入正文。正文内容结束,点名写信来意,文末署明写信之人。整个书信,除无提称语外,十分完整。纵览全文,充斥着阿谀溢美之词,违背了书牍文以真挚为主的宗旨。然文脉清晰,张弛有致,任升之写信的意图表达得非常清楚。此作品以任升之与钦悦往来的书信为主体,结合诗赋、议论展开故事的叙述,文体结构颇有特色,体现了唐小说“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
2.摘录 摘录书信中与故事相关的内容,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是唐代小说使用书牍文的主要方式。在唐代小说中,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的篇目非常多,有《梁四公记》、《梁十二》、《郭翰》、《秦中子得先人书》、《冯渐》等近40 篇。如《秦中子得先人书》,讲述一个假托鬼魂之名骗取钱财的故事。秦川富室少年,忽收到亡父要求他把三十五匹缣送到灞水桥边,否则将遭致灾祸的来信:“一日逮夜,有投书于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书……善计家事,急为窜计,祸不旋踵矣。”[7]2557小说省略了书信的程式化套语,只撷取与故事直接相关部分,折射出唐时弥漫着卜葬、卜宅、禄命之类阴阳迷信思想的习俗,突出了“惩恶扬善”、“破除迷信”的主题。
3.转述 唐代小说中,叙述者以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间接转述书信内容的篇目主要有《李参军》、《南柯太守传》、《李咸》、《李行修》、《崔无隐》等。如《南柯太守传》,淳于棼成为槐安国驸马后,叙述者转述了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屈……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7]788-789这种以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用概括性语言转述书信的形式,可以让叙述者一边转述书信内容,一边结合书信内容进行评论,渲染书信所要表达的情感,灵活自如地描述故事人物的心理活动。
整体而言,唐代小说中的书牍文明显长于汉魏六朝小说中的书牍文,表现形式更为多样,数量上也更具优势。较多、较长篇幅的书信文体融入唐代小说,是小说改变自汉魏六朝小说以来为“丛残小语”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书牍文以多种形式与唐代小说相融,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手法。
二、汉唐小说中书牍文的叙事功能
古人论文辨体,很多都是基于文体的功能。《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8]《释名·释言语》:“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9]《文心雕龙·铭箴》:“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1]116《尚书》、《文心雕龙》、《释名》等典籍,从文体的实际功用追溯铭、盟、诏书等文体的起源、特点及文体性质。今人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阐释了中国古代各文体之间的融合、吸收,主要是因功能所需,功能是文体生成的重要方式[10]。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亦指出,功用、功能是中国古代文体众多分类中重要的分类,以及文体的生成方式[11]。对叙事性文体小说而言,文体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叙事的功能。汉唐小说中书牍文的融入,也主要因叙事功能所需。因而,探讨融入汉唐代小说中书信的叙事功能,是考察汉唐小说文体演进的重要依据。
汉唐小说作家深谙书牍文的叙事功能,以之为“媒介”,巧借书信叙述故事。但汉、唐小说中书牍文的叙事功能,同中有异。相同之处为,汉魏六朝、唐代小说中的书信,多在情节过渡时作为衔接故事之用,并暗示即将展开的情节。
(一)串联故事
汉魏六朝时期,小说集《搜神记》“钟离意”、“段医”、“王母传书”、“韩凭妻”、“李娥”等,《幽明录》“鬼书”、《世说新语》“庾公书郗公”等,故事人物在不便于直接会面时,以书信传递信息,预知将要发生之事,为下文埋下伏笔。如《韩凭妻》,小说中共有两封书信:一封是韩凭妻以死明志的隐语;另一封是韩凭妻殉情前控诉宋康王暴行,并祈求与夫同葬的遗书。小说没有正面描述韩凭夫妇以死抗争的悲壮场面,而是以这两封书信为主线,从侧面烘托、渲染,却有着比直接描写更动人心魄的审美艺术效果。同时,信中隐晦曲折的文辞,暗示着故事人物的结局,与前文宋康王强夺何氏的情节相呼应。故事结构首尾圆合,俨然一体。
融入单篇唐代小说中的书信数量明显增多,书信成为串联故事情节的主线,故事情节也如书信中所预设而展开。如《李哲》,写李氏家中因鬼魅为祟出现的诸多异事。从鬼魅出现到李氏家人迫于无奈选择离开,鬼魅前后给李哲及其家人写了八封短信。故事中,鬼魅一次又一次地写给李哲家人的书信,成为串联故事的链条,推动情节的发展。书信的使用,也让小说在叙事时间上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标注具体时间的方式,使看似杂乱无章的事件与事件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衔接。
部分汉唐小说作品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有意识地使小说各事件之间出现一个合理的断层,设置悬念,激发接受者的阅读兴趣。然后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用书牍文衔接断层,串联故事,让事件与事件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因果联系,形成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
(二)刻画人物
唐代小说中的书牍文不仅用来勾连故事情节,还以之刻画故事人物心理,改变了长期以来小说极少对人物心理进行刻画,多通过叙述者代言或故事人物直白陈述而使人物形象不够真实、灵动的缺憾。
唐传奇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莺莺传》之所以成为文人笔下所钟情的题材,并被一再改编的重要原因,是作者采用多种手法塑造了鲜活可感的人物形象,其中就得益于小说中的书信。如莺莺写给张生的回信:“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7]811-812,全景式地呈现了她的内心活动。既有对往事的回忆,也有对目前处境的描述,还有对未来爱情的期待和憧憬。书信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这位少女反抗传统礼教时心灵的冲突:相信情人又怀疑情人,深爱情人又埋怨情人,追求爱情又被礼教禁锢。书信用语典雅精工,细腻、生动地展示莺莺的心路历程,刻画了一个才华横溢、温柔痴情,在情与礼之间挣扎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书信融入小说,实际上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通过“我”的口吻直接叙写人物的所思、所想,把单靠外部形象难以表现的内心感受揭示出来,从而更接近故事人物生活的原生态,加强小说的真实感。
《崔炜》、《非烟传》、《南柯太守传》等篇目也以书信陈情。通过书信,让远隔两地之人倾诉衷肠,展现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手法不擅长描述人物内心的局限,全方位地呈现故事人物隐秘的心理活动,引导接受者步入作品的精神世界。同时,作者对故事人物内心世界的极力关注,以浓墨重彩铺叔,标志着叙事体小说以事件为描写中心转入以人物描写为中心开始形成。
(三)改变叙事结构
唐代小说的体制相比汉魏六朝小说有很大发展,但仍然以史传惯用体例叙事,如以人名为标题,开篇介绍人物的身世、经历。“唐人《霍小玉传》、《刘无双传》、《步飞烟传》等篇,始就—人一事,纡徐委备,详其始末……”然“以千篇一律地写‘某时’、‘某地’、‘某人’的程式开头,然后又按时间的次序叙写故事的始末,这就给结构带来了单调、平板的毛病”[12]。在中晚唐小说中,叙述者巧用书信以故事人物自陈身世,改变了这种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写作方式和单一的文体结构。
如《非烟传》,非烟与赵象一见钟情。但特殊的时代、悬殊的身份,让非烟与赵象即使近在咫尺,也无法互通情愫。不能见面的他们,只能以书信倾诉衷情。非烟与赵象第一次会面后,在信件中向象讲述了积郁于心、不曾向人倾吐的身世经历:“于是阖户垂幌,为书曰……兼题短什,用寄幽怀。伏惟特赐吟讽也。”[7]2370-2371这封书信声情并茂,即使不融入小说,也是一篇佳作。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以追忆的形式,再现了非烟的悲剧人生。书信介入叙事,也使正在发生的故事时间、场景与非烟往昔所生活的情境双水分流,同步进行。接受者根据书信所述,发挥联想,展开想象,根据自己平时积累的阅读经验和审美体验,再现书信叙述所营构的时空。借书信叙事,实际上是让当事人非烟作为主体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直接介入故事情境,并以自身的境遇作为情感抒写内心的一种方式。当写信的人物在向另一个人物表明心迹时,引发了故事人物在不同时期所发生事件之间的时空转换。
《鬼传书》、《游仙窟》、《常夷》等作品,作者同样以自陈身世的书信融入小说,表现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想象、回忆、联想。这种叙事方式,将发生在不同空间的事件或场景置换到同一时间点,代替了传统小说中的顺时性、直线性叙述。如此建构起来的故事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多层次的,使读者的视点由一条主线向四周延伸。这种不再顺着时间线索叙述故事的辐射结构,展现出了空间的效果,使小说以线性时间为主的叙事结构变为空间化叙事结构。
三、书牍文对汉唐小说文体建构的意义
书牍文在汉唐小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小说文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重要的叙述功能,对汉唐小说文体建构也有重要意义。汉魏六朝小说《殷芸小说》“曹公与《杨太尉书》”、“张子房与四皓书”、“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燕丹子》、《西京杂记》“飞燕昭仪赠遗之侈”等,唐代小说《通幽记·李哲》、《通幽记·窦凝妾》、《异闻记·梁大同古铭记》、《鉴诫录·鬼传书》、《鉴龙图记·传书燕》等围绕书牍文展开故事情节。在汉、唐小说发展的不同阶段,书牍文与小说文体之关系的变化,对其演进有重要影响。
汉魏六朝志人小说《殷芸小说》,是第一部以“小说”命名的小说。整篇小说由曹操与杨修之父杨彪、卞夫人与杨修之母袁夫人往来的四封书信组成。除书牍文外,并无增饰性文字。根据书信内容,可推知故事发生的背景:杨修恃才无恐,一次次当众冒犯曹操,曹操早就想除之而后快。这一次,杨修猜出曹操在花园门上所写“活”字的用意,并收拾行装准备返回,曹操借机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斩之,将首级悬于辕门外。当时,杨修之父杨彪官至太尉,考虑到其家的声望、地位,曹操、卞夫人以书信安抚杨修父母,掩盖其因妒忌而杀害杨修的丑行。杨修父母忌曹操之权势,强忍失子之悲,对曹操夫妇的抚慰表示感激,曲承儿子被法律严惩是咎由自取。书信与书信之间,用“曹公与杨太尉书,论刑杨修云”,“杨太尉答书云”,“曹公卞夫人与太尉夫人袁书”,“杨太尉夫人袁氏答书”串联,充当过渡之用。既点名了写信的缘由,又指出写信的主体。这些散体文字与书信结合在一起,构成首尾相连的整体。
又如“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结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展开故事的叙述,但叙述故事的不是有首有尾的情节性文字,而是书信。作品通过书信反映时代特征,时人的思想、文化观念,为接受者提供了一个可揣摩故事情节的背景。接受者根据平时的阅读经验和知识积累,对故事的具体情节进行想象、填充:“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云……痛夫!痛夫!二君,二君!”[13]小说以“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开篇,点名写信之人,接下来进入正文,也就是具体介绍书信内容。苏秦、张仪是当时左右政局的风云人物,而鬼谷先生则是他们的老师。鬼谷先生写信给二徒,意在劝二位功成身退,以求永年。整体而言,《殷芸小说》在编选体例上,以历史发展的线索结构全书,有“通史”之规模,而这两篇小说以书牍文结构全篇,颇具特色。唐代小说《梁大同古铭记》的结撰方式,与这两篇小说类似,可看出汉魏六朝小说对它的影响。
汉魏六朝小说以书牍文结撰的作品,往往是对历史故事的戏剧化、传奇化①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具体阐释了魏晋时期,时人喜将历史故事传奇话、戏剧化的风气。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 页。。由于书信之间缺少敷衍情节的增饰性文字,小说的情节只能由接受者根据书信内容推衍,以致有些学者认为这一类小说只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不符合小说的概念,但这是一种新的编写小说的方式,打破了史传对小说文体的束缚。
唐代小说进一步发展了此种创作小说的方式,并在书信与书信之间,用大量文字敷衍、补充,小说的故事性、情节性得到了加强。
《开元天宝遗事·传书燕》,书牍文不仅占了较大的篇幅,而且是推动情节展开的核心线索。它与史传、志怪相结合,讲述了燕子替人送信的感人故事。《传书燕》开篇即以史传惯用笔法,简述故事人物——绍兰的身世经历:她出生于富裕之家,后嫁给巨商任宗。任宗在外经商数年未归,音讯全无。接着,详叙燕子送信的过程。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以志怪小说常用的幻笔,把燕子写得颇有人情味。她不但同情绍兰的遭遇,还为其送信。最后,神异的燕子在不知绍兰丈夫身居何处的情况下,准确地把信件送到他的手中。小说的主要情节链寄信—送信—收信—丈夫归家,都是围绕着书牍文而展开。书牍文不仅寄托了绍兰对夫君的思念,而且也是燕子为其送信的缘由,更是她与丈夫情感交流的纽带,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孤苦、寂寞而又眷念丈夫的思妇形象。
《鉴诫录》中的《鬼传书》,以书信为主融合诗赋、论说文、志怪等,通过人与鬼争地之事,影射当时官府抢占民田、民宅的阴暗现实。《鬼传书》没有用史传惯用的体例开篇,也没有用“某某曰”来结尾。文章以西川高相公筑蜀城、命诸指挥使开掘古坟开端,引出坟墓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冥司赵畚写给姜指挥使的书信,在解决矛盾的同时将故事推向高潮。冥司赵畚在书信中不是威逼利诱,而是自陈身世,以精诚感动姜指挥使,请求其不要开掘坟墓。尤其是书信末尾所附之诗文本:“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7]2964,进一步渲染了冥司的凄苦、无奈和对人生的感慨,丰富了小说的意蕴。替冥司赵畚送信给姜指挥使的鬼吏与姜指挥史之间关于钱财对话的论说文,暗含作者以冥间事来影射现实的创作目的。《鬼传书》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以书牍文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有条不紊地将发生在蜀地的人与鬼之间的故事写得真切动人。
汉魏六朝小说家对书牍文的运用,尚处于自发的摸索状态,与小说并没有水乳相融。因此,汉魏六朝小说以书牍文结撰的大多数作品,书信占了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小说中穿插的散体文字,字数有限,仅用来衔接书信,交代写信的主体及缘由,对故事情节没有太多的意义。而唐人“有意为小说”,在汉魏六朝小说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自觉把书牍文移用于小说的创作。唐代用书牍文结撰的小说作品,书信是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情节进一步展开的同时,刻画故事人物心理,建立思维更开阔的空间叙事结构,小说的文学、艺术品格逐步提升。同时,书牍文与融入的史传、碑铭、诗赋等多种文体相结合,形成了“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与“众体”共同叙述更为生动、完整的故事。
综上所述,书牍文是影响汉唐小说的重要文体。融入汉魏六朝和唐代小说中的书牍文的篇幅、数量、表现形式,以及叙事功能的差异,对汉唐小说从混沌走向清晰,从稚嫩走向成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融入汉魏六朝小说中的书牍文,除《燕丹子》、《邹长倩赠遗有道》篇幅较长,可看出其语言及结构特点外,其他都是以摘录的方式用来衔接情节、暗示故事结局,难以看出小说中的书信与书信文体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融入唐代小说中的书信篇幅较长,与书信文体在唐代的发展表现出一致性,叙事功能也更丰富。不仅用来串联故事,改变了线性化的叙事结构,而且建立了开放式的空间叙事结构。在叙述角度上,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也变为第一人称客观叙事视角。这些都体现了唐人的艺术构思。他们改变了小说一直以来以史传为叙事体例的单一的文体建构方式,汲众体之长,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学品格和特性。从“破体为文”的视角观之,一种文体的发展离不开对其他文体优长的借鉴与吸收,汉唐小说在演进的过程中正吸收和融合了书牍文体来充实、完善自己。
[1]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王凯符,张会恩.中国古代写作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391.
[3]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M].査屏球,益西拉姆,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6.
[4]刘歆.《西京杂记》校注[M].向新阳,刘克任,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62.
[5]钟涛.雅与俗的跨越:汉魏六朝及元代文学论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1:52.
[6]李回.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新注·集评:苏辙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508-509.
[7]李时人,何满子,詹绪左.全唐五代小说[M].北京:中华书局,2014.
[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 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293.
[9]刘熙.释名·释言语: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60.
[10]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5.
[11]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J].文学遗产,2005(1):28-29.
[12]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藉出版社,1997:10-11.
[13]殷芸.殷芸小说[M].周楞伽,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