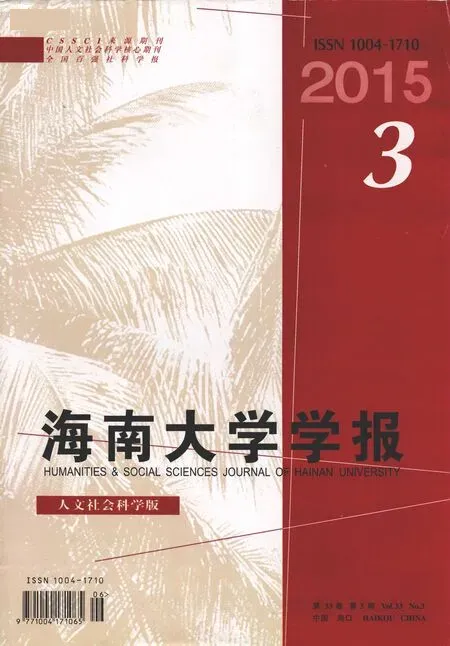古代诗学概念“句法”论
傅根生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
一、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概念——句法
句法一词,最初出现在佛教文献中,作为诗学概念运用是从宋代开始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率先大量运用句法概念来评点杜甫、陶渊明的诗歌,黄庭坚的学生范温更是明确提出了“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宋·范温《潜溪诗眼》)的观点,自宋至清末,句法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重要内容,在各种诗话、诗评、诗学著作中基本都有涉及,虽然著者对诗歌句法褒贬不一,但“句法”始终是诗歌评点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诗话史,就是一部诗歌句法研究史。近人王德明先生甚至说“对句法问题的探讨不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意义,甚至完全可以建立起一门学科——‘中国古代诗歌句法学’”[1]2。
句法作为古代诗论中的重要范畴,是和中国古代的诗学思维特点分不开的,体验感悟是中国诗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论,“中国古代诗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简略甚至没有思维过程的思维,由感而直接获得悟”[2]。古代诗歌评点,多喜“摘句寻篇”,多印象式、观念式的批评,而少理论体系的构建。故而,以文本为前提、以句法为基础的散点式的比较与分析,成为了诗歌批评的主流,虽然不够系统,但是具有灵活、直观、真实的特点。另外,由于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近体诗的创作结构形式比较固定,诗歌创作的自由空间比较狭小,能够自主选择的也就是诗歌句子内在的结构变化,“诗人之能事,其实最主要地表现在造句之工。而最能见诗法之精及诗人一家之诗法,就在于句法,创造独特的诗歌风格,也必须有独到的句法作为保证”[3]。这样对于前人诗歌句法的研究成为了提高自身诗歌创作水平的重要路径,诗话中经常提到的“用某某句法”、“得某某句法”等,句法分析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范式的思考与规则的提炼,这也是历代诗人热衷前人句法的重要原因。
对于诗歌语言及句法的重要性,一些学者也在论述中有所提及,如“我们在把握诗学精神时,自不能停留于情志、境象、气韵、趣味之类较虚的层面上,还要进一步将其落实于语言文辞”[4],“对诗歌的结构、语词、声律等方面的艺术技巧的分析研究,理应成为诗歌理论的主流”[5]469。近来,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诗歌句法的专项研究,如王德明的《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2002年)、段曹林的《唐诗句法修辞》(2005年)、易闻晓的《中国诗句法论》(2006年)等专著的出版,但是一直以来,诗学研究的重点依然是比兴、风骨、意象、韵味等形而上的领域,句法在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整体中涉及面还是非常之少。而在仅有的著作中,关于“句法”概念的含义既没有一致的认识,也没有清晰的界定,这一方面因为历代诗话论著中,句法的使用非常宽泛,概念的指涉差别很大,另一方面现在的句法更多的是基于语法学研究,与古代诗学领域的句法内涵相差甚远。“作为一个句法概念,灵活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内涵和外延都不太清楚,应用的时候随意性很大,因而大大削弱了对句法现象的解释能力。”[6]本文拟结合古代诗论中“句法”运用的实际,对“句法”概念作简要辨识。
二、句法概念定义述评
在现有的各种论著中,对于诗歌“句法”概念的定义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语法范畴的定义
在现代汉语体系中,句法首先是一个语法学上的概念,是利用西方的语法概念与体系对句子结构进行分析。同样,在诗学研究中,一大批语言学家从语法学的角度来进行句法的研究,其中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是其中的扛鼎之作。王著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诗歌句法概念,但是他“把‘诗歌句法’从古人宽泛笼统的理解,转变为诗句句式、诗句结构等严格的语言学范畴”[7]38,他的著作开启了“中国诗句西方文法化”的先河。其后,向熹先生的《诗经语言研究》(1987年)、蒋绍愚先生的《唐诗语言研究》、廖旭东先生的《楚辞语法研究》(1995年)、杨合鸣先生的《诗经句法研究》(1997年)、段曹林先生的《唐诗句法修辞研究》(2005年)、孙力平先生的《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流变史略》(2011年)基本都延续这一方法,以文法为基础,对诗歌的语言进行语法分析,部分涉及到诗歌的意象与审美。
从语法的角度研究诗歌句法,对于句法的定义也基本围绕诗句的语法结构成分组成而展开,关注的重点是句子成分间的语法关系,如,邵霭吉认为:古代‘句法’一词含义宽泛,总的说来是指句子的组织形式及组织方法[8]。孙力平认为:句法的现代意义是组词成句的法则,诗歌句法当指诗句内部词语的组合规则[7]50。王锳认为:“句法”主要是从现代意义的语法着眼的,指的是句子的样式和组织结构。除了语序之外,还包括诸如成分的省略、内容的紧缩、结构的扩展等[9]。诗歌句法究竟有何特点呢?周锡韦复认为如下四点是古、今汉语各体诗歌都具备的:1.只要需要,句子任何地方都可以插进语气助词;各种成分都可以复叠。2.句子任何部分都可按需要而省略。3. 词序、语序可以灵活变换,适当调整。4. 音句重于义句,即当声律和语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首先照顾声律的要求[10]。另外,重庆师范大学罗琴教授所带的几个硕士研究生都是将句法定义为“句子结构方式和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
上述诸家从语法角度对诗歌句法进行分析和评价应该说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范式,但是中国现代语法学依据于西方语法的分析体系,而中国古代的文学语言具有整体性特点,这不同于西方文字的分析性风格,特别是对于古典诗歌而言,语言往往是与意象、审美、风格、韵律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纯粹地运用现代文法对诗歌句法进行割裂分析,反而阻碍了诗歌艺术审美的观察与理解。
(二)外在形式的定义
中国古典诗歌具有非常严格的外部结构限定性,诗歌句法作为诗歌语言的核心组成部分,与诗歌形式密切相关,很多学者基于此,将诗歌句法仅仅限定在形式结构的框架内,如王德明在《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中将诗歌句法定义为:“所谓诗歌句法,一指诗句的构造组织模式,二指诗句的组织构造方法或方式。诗句的构造组织方法包括句子本身的构造和用字两方面的内容。”[1]12王著在总结前人句法语用的理解上,将句法概念限定在形式结构的范围内,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充分考虑了句法语言层面的内涵,他的定义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与引用。但是,将句法仅限定在语言运用和句子结构的范围内,而不顾及句法运用所带来的风格转变与内涵提升,这样的定义就流于表面了,王著自己也认为:“这一定义也带来了麻烦: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句法概念非常宽泛,对于有些诗论家来说,这一定义只能涵盖他的句法概念的大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1]13,持同样理解的还有萧涤非先生,他认为:“所谓句法,是指一句诗的组织法或结构法而言的”[11]。
张静则根据句法字面的意思,将句法定义为“针对‘诗句’写作的技巧与法则”[12],这个定义显然有问题,从古典诗论中句法的使用来看,句法的“法”更多指的是方法的意思,并不是法则的含义。在诗歌创作中关注句法,关注是句子构造的方法,而不是定义为必须要遵守的规则。同样,张怡在硕士论文中将“句法”定义为“指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排列顺序”[13],既流于简单,也显失准确。
(三)宽泛意义的定义
王运熙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中讨论黄庭坚诗学思想时,认为:“黄庭坚论句法主要指诗句的构造方法,包括格律、语言的安排,也关系到诗句的艺术风格、意境、气势,所蕴含的内容,是多角度、多层次的”[14],虽然谈的是黄庭坚句法,但基本代表了古典句法使用的各个方面,应该说,理解是非常宽泛的,几乎涵盖了诗学的各个方面,既提及“诗句的构造方法”,也提及“风格、意境、气势”,但是却没有考虑到二者之间相应的联系。
易闻晓在其《中国诗句法论》中,将中国诗的句法定义为“诗之造语特点的规律性的显示和概括性的总结”[15],易氏的理解结合汉语的特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从文化、语言、句式、体制、字法等几个方面进行整体考察与阐述,比较深刻,但是比较抽象,定义明显过宽,在实际诗歌句法分析中难有借鉴性。
而周裕锴先生认为“所谓‘句法’,含义甚广,既指诗的语言风格,又指具体的语法、结构、格律的运用技巧,而其精神,则在于对诗的法度规则与变化范围的探讨”[5]207。同时,他提出“句法不光指语词的排列组合,而是相当于诗歌中一切具有美学效果因素的结构(structure),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5]192。对周先生的观点很多人提出了批评,但实际情况是,周先生的理解也最接近于古人句法的真实内涵,句法关注的重点是形式,而关注句法的目的是要有“诗味”,即“意味”、“诗家语”,但是周先生将一切结构、形式都定义为句法,又显绝对化了,将章法、篇法也纳入了句法的范畴。
另外一些学者在讨论古代诗学句法过程中,涉及到句法概念,往往采用回避的策略,如张毅认为:“句法是诗歌语意结构的基本单位,在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和讲究对仗的近体诗里起关键作用”[16],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也有一些学者,将句法定义片面化,而如王世朝先生在《中国诗歌》仅将句法限定在诗句字数的范围,他认为中国古代诗歌“主要经历了从二言、四言到五言、七言的句法演进”[17],虽然他讨论的仅是形态学范围,但即使从形态学角度观察,也不仅仅是字数的变化,如此简化处理显失偏颇。
三、诗歌句法的内涵
概念是分析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要想对句法现象作出有效的分析,必须先把握好句法概念的边界与内涵。本文认为,诗歌句法指的是诗歌中能够获得审美意义的语词选择与组合方法,现就其内涵、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诗歌句法必须定义在诗学的范围内
作为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焦点讨论概念,由于较早介入研究的是语言学家,而现代汉语体系中的句法本身属于语法学范畴,故而,将诗歌句法研究带入了语法的范围。诗歌句法语法化研究,危害甚大。不少学者提出了疑义,如易闻晓认为“诗句之‘语法分析’,特今世之强凿解剥,斯为害之甚且著者”[18];傅斯年先生认为“以西方文法来规范中国语言的思维方式日渐深入,时至今日甚至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解析时出现‘中国诗句西方文法化’的现象”[19];叶维廉先生也曾举王力先生分析杜甫诗句“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的例子,认为“这是由重知性逻辑、强调科学分解性的‘先思后感’的解读方式所引起的,与原诗的实际视觉活动有违”[20];黄侃先生曾言“文法书虽工言排列组织之法,而于旧文有所不能施用”[21]。可见,句法研究的边界必须限定在诗学的范畴内,诗歌句法研究的范围不能离开古代诗论与诗歌的本体。
(二)诗歌句法不仅仅是与形式相关,更与意义相关
中国古典诗歌是高度形式化的作品,句法自然是形式的重要构成内容,但是句法不仅仅是形式。纵观古代诗话中的各种句法讨论,可以发现,讨论的多是一些诗歌中的经典句子,而不是所有的诗歌语词都在其讨论的范围。为何出现这种现象呢?说明句法关注的除了形式外,更关注诗歌审美本身,关注某些具有独特气质诗句的表达,只有诗句的形式选择具有自身的审美并有助于诗歌意义的表达,才是句法的核心特征。兹举数例说明,如:
“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宋·黄庭坚《山谷集》卷十九《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二)。黄庭坚评点杜甫律诗句法简易,是就其结构简单、语词平易而言,但分析落脚点是在诗歌的内涵上,提倡的是诗歌简易语言与丰富情感的有机融合。
《刈稻了咏怀》(杜甫):“稻获空云水,川平对石门。寒风疏落木,旭日散鸡豚。野哭初闻战,樵歌稍出村。无家问消息,作客信乾坤。”三、四乃诗家句法,必合如此下字则健峭。后四句亦惟老杜能道之也。(元·方回《赢奎律髓》卷十三)方回评价杜诗“寒风疏落木,旭日散鸡豚”两句合诗家句法,是言其中“疏”、“散”两字所使用的比拟手法,“疏”、“散”二字修辞的运用使得诗歌风格劲健峻峭。
实际而言,古人但凡论诗,很少就句法论句法,句法总是和诗歌意义的阐述、情感的表达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意合”既是诗歌句法的核心要求,也是它的基本标准,“‘语言上的经验’及‘诗意地表达’,使言说的语言,成了一个意义的图式所在”[22]。诗歌句法中诸如声律的适应、对仗的工整、语词的选择、语序的变化等句法变化都是以诗歌艺术效果为前提的,即高友工所言:“一种格律的形式,只有当它的形式要素对诗的总体艺术效果产生重大作用时,它才能被认为在艺术上是有价值的。……只有这样,形式才能称得上具有了自身的‘形式的价值’。”[23]
(三)诗歌句法既是诗歌创作的范畴,也是诗歌批评的范畴
现在一般论者,多看到了古典诗学中“句法”在创作层面的意义,但是就古代诗论诗话实际使用而言,既有创作层面的技巧探讨,也有批评层面的艺术分析,在创作方面多论句法技巧,在批评层面多论句法效果。
总结前人名作的句法技巧是历代诗论句法研究的主流,“《风雅三百》,《古诗十九》,人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明·王世贞《艺苑危言》卷一)句法创作技巧,从宋代开始就有全方位的总结,如惠洪在《石门洪觉范天厨禁脔》中就提到了十字对句法、错综句法、折腰句法、绝弦句法、影略句法、比物句法、夺胎句法、换骨句法、遗音句法、破律琢句法、古意句法,等等,虽然部分名称有牵强之处,但总体而言都是属于技法的范畴。魏庆之的《诗人玉屑》是宋代句法研究的集成之作,在其卷三“唐人句法”中总结各种句法三十六类,前二十六类实际属于题材、风格创作典范范畴,而后十类即“连珠(句中字相对)、合璧(句中意相关)、眼用活字(五言以第三字为眼、七言以第五字为眼)、眼用响字、眼用拗字、眼用实字实字妆句、虚字妆句、首用虚字、上三下二(七言上五下二)”,基本是诗歌创作的技法范畴,而在卷四“风骚句法”中,五言部分列举了一百零二种句法,七言部分列举了五十种句法,虽然名目奇特,很难索解,但也充分展现了宋代诗歌句法的全方位成就。而到了明清时期,考察更细,名称更多,明代梁桥在《冰川四式》列举了四十四种句法,基本都是语言技法的内容。而清初诗论家黄生,对唐人诗歌句法的解读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据清人朱之荆《黄白山〈杜诗说〉句法》记载,黄生在《杜工部诗说》中共提出五十二种句法,而据何庆善先生统计,黄生在《唐诗评》中总结出唐诗句法达六十种[24]。而王德明根据前人总结,将《杜工部诗说》、《唐诗评》、《唐诗矩》三书的句法名称全部统计在一起,他认为句法名称估计不下于八十种[1]199,由此可见一斑。总结前人句法创作技巧能够有助于诗歌创作水平的提升,诗话中经常出现的“得某句法、似某句法”等都属于创作技巧借鉴学习的范畴。如:王荆公五字诗,得子美句法,其诗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宋·强幼安《唐子西文录》)所谓“得子美句法”,就是学习杜甫诗中天、地、江、湖等比较阔大有气势的词语。再如李壁《王荆公诗注》引《松江》诗云:“宛宛虹霓堕半空,银河直与此相通。五更缥缈千山月,万里凄凉一笛风。”杜诗“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介父用此句法(南宋·李壁《王荆公诗注》卷三十八))是言王安石沿袭了杜甫诗中的句式结构与词语。
创作与批评本为一体,句法技巧既是句法批评的内容,也是句法批评的手段。句法的变化,是否能够契合诗歌艺术审美的表述,是句法批评的重要内容,所谓“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宋代许顗《彦周诗话》)“辨句法”是既有辩句法之变化,亦为辩句法之优劣。历代诗话评点诗歌一般都是主要两个方面的内容,本事和句法,而其中句法更为重要,是理解诗歌、评价诗歌和诗人的重要方面。一直以来,中国古典诗歌评点重感悟,重直观,而句法批评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古典诗歌批评的分析水平与理论水平。如:
“三过门中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句法清健,天生对也。陆务观诗云:“老病已多惟欠死,贪慎虽尽尚徐痴。”不敢望东坡,而近世亦无人能到此(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魏庆之将苏轼诗句与陆游诗句进行对比,虽然两者中表达的内容相似,描述的都是身老病死境况,但苏诗以“去来今”与“老病死”对比,境界不凡,格调提升,与陆诗迥异,故曰句法“清健”。
《登楼晚望》:“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此唐僧无可诗也。退之所称“岛、可”,岛谓贾岛也。此句法最有奇趣,然譬之嚼蟹赘,不能多得。一夜萧萧,谓必雨也,及晓乃落叶也,其境清绝可知。方远望谓斜阳自乔木而下,乃是远烧入山,其远可知矣(宋·释惠洪《石门洪觉范天厨禁脔》卷上)。“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为唐马戴《落日怅望》中诗句,惠洪评点“奇趣”,诗句中以远烧比微阳,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静中有动,意境空阔,突出了作者的孤寂之情。
(四)诗歌句法是演进的,在遵循中变异
诗歌句法研究的主要是句法变异,当然这种变异是相对的。诗歌本源于生活与音乐,最初并无特殊句法而言,质朴自然,随着诗歌的发展,诗歌体式和规则也一直处于演变之中,句法必然需要适应表达方式和抒情方式的变化,在遵循中变化,在变化中演进。
首先我们来看体式的演进。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看,诗歌最初的形态是四言为主,西汉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些五言体诗歌,东汉以后,五言诗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为五言诗的繁荣提供了典范,而从建安到永明年间,五言诗达到了高峰。进入初唐以后,随着七言歌行的盛行,杜甫七言格律典范的树立,七言体开始和五言体一样成为古典诗歌的主流。诗句字数的变化必然带来声气节奏的变化,进而影响诗歌句法的构造,如刘勰所言:“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文心雕龙·章句》)同时,随着诗歌每句字数的增多,诗歌表达的内容和情感进一步丰富,其句法变化也可以出现多种不同的组合,诗歌的风格也迥然有异,明末学者陆时雍曾言:“诗四言优而婉,五言直而倨,七言纵而畅,三言矫而掉,六言甘而媚。”(陆时雍《诗镜总论》)虽然风格标举有商榷的可能,但其差别当为确论。
另外,随着诗歌创作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以及其他文体的交相滋润,众多诗人开始总结各种技巧与方法,并上升为理论经验与规则,在规则变化演进的过程中,句法既为诗歌规则的总结提供了典范依据,同时也必然受到新的规则的制约。影响句法的两个最核心诗歌元素是格律与“诗家语”。格律涵盖声律和对仗两个方面,它是中国古典诗歌古今体的分水岭,也是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格律是影响诗歌句法的最核心因素,几乎所有的句法变异都能在格律中寻找原因,清人冒春荣所说甚好:“作诗以导其意所欲言,古体不拘排偶,可以直抒己意,故虽有句法,锻炼之工尚少。至五言八句,声律、对偶,格式一定,必须铸意成辞,命辞遣意,非锻炼句法,何以见工?唐人句法,备有多种,说者不能悉举,学者玩习既久,可自得变化之妙”,“法所从生,本为声律所拘,十字之意,不能直达,因委曲以就之,所以律诗句法多龄古诗,实由唐人开此法门。后人不能尽晓其法,所以句多直率,意多浅薄,与前人较工拙,其故即在此”,“唐人多以句法就声律,不以声律就句法,故语意多曲,耐人寻味。”(清·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一)应该说,“句法就声律”是诗歌句法最基本的规定。唐前,诗歌格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进入唐代,近体诗格律规则森严,促进了诗歌句法的变化发展,而杜甫在此基础上,极尽衍变,提供了众多的诗歌句法典范。另一个影响句法演进的因素是“诗家语”的追求,所谓“诗家语”最初即与句法相关,出自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王安石语:“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要有诗味,必须要讲究“诗家语”,“诗家语”指的是诗歌用语的独特性:它是一种在内涵表述上富于灵活性、在音韵节奏上富于旋律性的语言,丰富的情感与清醒的理性、直觉的感性与明晰的概念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仿佛有立体感的语言,凝练含蓄,而不是简单明了[25]。句法是“诗家语”产生的基础,所有的“诗家语”都必须通过句法来实现,故而在句法中,声律对仗、字句选择、句式安排、语序变化、虚实转化、前后贯连等一系列句法手段的使用都是为了“诗家语”的更好表达,而“诗家语”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句法的演进与变异。
(五)句法和字法融为一体,是语词的选择与组合
关于“句”的概念历代多有论述,如“句,止也,言语章句也”(《玉篇·句部》),“句者,联字以为言,则一字不制也”(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关雎疏”)等。关于句、篇、字之间的关系,最早在汉代就有论及,如“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汉·王充《论衡·正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推而广之,关于诗法,历代论者多分章法(篇法)、句法和字法三个层次,如“于一家之中,则有诗法;于一诗之中,则有句法;于一句之中,则有字法”(元·吴澄《吴文正集》卷十九《唐诗三体家法序》);“诗有三法,章、句、字也”(明·唐寅《六如居士全集》卷七《作诗三法序》);“篇有眼曰句,句有眼曰字,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篇有篇法,此三者不可一失也”(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八一《与华仲达》)。
诗歌句法虽然在古代诗论中涉及范围甚广,但必须限定在句的范围内,对于近体诗而言,也就是一联的范围内,不能无限制扩大,如此界定,并不是排除句与篇之间的关系,句法在功能方面主要为篇章、立意奠定基础,为诗歌审美、情感、艺术的表达服务。同样,由于汉字具有的具象思维、单音为词、词类虚活等独特属性,字实际即为词,故而,诗法中并无单独意义上的字法,字法即词法。而字法(词法)均属于句法的范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无论是诗论中经常讨论的“诗眼”、“句眼”,还是一些虚实字的分析,基本都在句法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离开句法,字法毫无意义,所谓“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宋·范温《潜溪诗眼》)。王世贞虽然将诗法分为字法、句法、篇法三类,但是在实际诗歌评点中,也是将句法、字法合二为一,如《艺苑卮言》卷二云:“‘东风摇百草’,‘摇’字稍露峥嵘,便是句法,为人所窥。‘朱华冒绿池’,‘冒’字更捩眼耳。‘青袍似春草’,复是后世巧端。”“摇”和“冒”实为诗中的“句眼”,但本身并无特别的意义,只有在一句中通过位置选择和其他组合,才赋予了其特别的诗学审美效果,这也是众多诗论家在诗法分析时,字法、句法不分的原因吧。
“选择与组合构成语言符号排列的两种基本方式”[26],句法内部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语词的选择与组合,“为句之法,在模写,在锻炼,在剪裁”(明·唐寅《六如居士全集》卷七《作诗三法序》),“模写”、“锻炼”属于选择的范畴,“剪裁”属于组合的范畴。选择与组合是句法的基本内容,也是其核心环节,格律是句法选择、组合的基本依据,而“诗家语”是选择、组合的基本追求。一般而言,选择是第一步,当然,对于一个作者而言,语词的选择首先建立在自己广泛的阅读和学识上,特别是一些经验型、历史性、惯性的痕迹思维,即时性地在某个时段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但同时,字词的选择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其基本要求是适切、新颖。适切,就是要准确,在合适的位置选择合适的词语,如杜甫诗“身轻一鸟过”之“过”字(宋·范温《潜溪诗眼》),王安石诗“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宋·洪迈《容斋随笔》。新颖,是选择的词语要有新意,务去陈言,夺胎换骨,如谢榛《四溟诗话》云:“子美‘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句法森严,‘涌’字尤奇”(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语词的组合是古典句法中讨论最多的内容,汉语表达的特点决定了诗句组合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选择,“词中之拼字法,盖用寻常经眼之字,一经拼集,便生异观”[27]。启功先生曾经就王维诗句“长河落日圆”提供了九种不同的组合,并就其在不同的语境下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各种组合“虽有艺术性高低之分,但语意上并无差别,句法上也无不通之感”[28],充分说明了汉语诗歌语言组合的多样性。诗句句法组合的基本要求是浑成、深健。浑成是言句法组合虽是人工雕琢,但和所有的创作一样,追求自然,这一点在古典句法理论中是基本一致的,如“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明·胡应麟《诗蔽·内编》卷五)。深健是笔者自创的一个评价术语,涉及深婉与劲健两方面含义,而在具体诗句中,这两方面艺术效果往往是相互融合的。句法组合的各种变化,如字词颠倒、语序错乱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句法力度的常规前趋性,在审美上增加了诗歌的深刻与婉转,从而避免了诗歌语言的平直简单,劲健有力,如“老杜多欲以颜色字置第一字,却引实字来,如‘红人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是也。不如此,则语既弱而气亦馁”(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三);“诗用倒字倒句法,乃觉劲健,如杜诗‘风帘自上钩’,‘风窗展书卷’,‘风鸳藏近诸’,‘风’字皆倒用。至‘风江飒飒乱帆秋’,尤为警策”(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诗歌通过语词选择与组合,提升诗歌语言的内在张力,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从而实现“语峻而体健,意亦深稳”(宋·王得臣《麈史》),“峻”和“健”在古典句法批评中经常使用,“峻”语词选择达到的审美要求,“健”是语句组合体现的审美效果,共同构建了诗家语的基本风范。
语句作为诗歌的构造材料,在诗歌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无论是从诗歌的欣赏,还是从诗歌创作而言,句法研究都理应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语言构造的微观层面关注中国古典诗歌的形成与发展、作品与风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句法的概念及其内涵作了简单的梳理,对于诗歌句法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仅仅是第一步,句法与诗法之间的关系、句法类型的科学划分、句法的艺术效果和审美效果分析、句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总结等都还需要下一步更多的梳理与探讨。
[1]王德明.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吴廷玉.中国诗学精要[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132.
[3]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3.
[4]陈伯海.“言”与“意”―中国诗学的语言功能论[J].文学遗产,2007(1):4.
[5]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7.
[6]石定栩.汉语句法的灵活性和句法理论[J].当代语言学,2000(1):18.
[7]孙力平.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流变史略[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邵霭吉.《马氏文通》句法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6.
[9]王锳.古典诗词特殊句法举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5.
[10]周锡韦复.诗歌句法与散文句法[G]∥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中国语言学报:1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3-104.
[11]萧涤非.一个小问题,纪念大诗人[M]∥萧光乾.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上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218.
[12]张静.“诗法”的概念、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M]∥蒋寅,张伯伟.中国诗学:1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59.
[13]张怡.从句法看南朝五言诗对唐诗的影响[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2.
[14]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22-323.
[15]易闻晓.中国诗句法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6:181.
[16]张毅.唐诗接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63.
[17]王世朝.中国诗歌[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114.
[18]易闻晓.中国古代诗法纲要[M].济南:齐鲁书社,2005:133.
[19]俞兆平.批评的纵横[M].福州:鹭江出版社,1996:220.
[20]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2:22.
[2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31.
[22]杨吉华.文学语言诗意逻辑的生成与存在主体的意义建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44.
[23]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218.
[24]何庆善.黄生析唐诗字法句法举要[M]∥唐诗评三种.合肥:黄山书社,1995:385.
[25]魏饴,刘海涛.文艺鉴赏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7.
[26]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41.
[27]林纾.春觉斋论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31.
[28]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