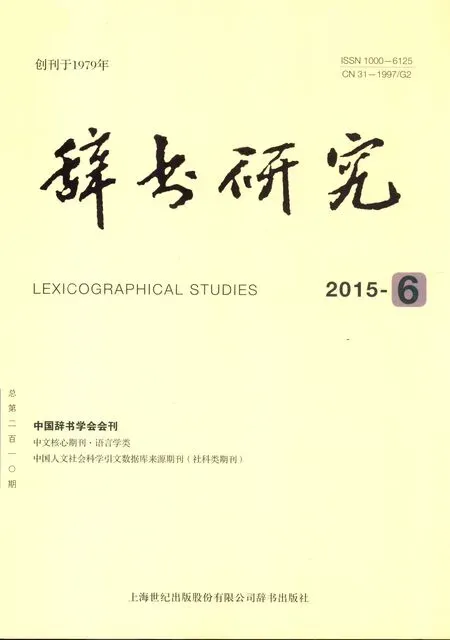南非英语词典的源发及其最新动态
雍和明 彭 敬
(雍和明 广东金融学院 广州 510521)
(彭敬 广东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广州 510320)
南非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拥有11 种官方语言[1]的多语国家,宪法确认国家的多语性(multilingualism),赋予所有官方语言同等的法律地位。南非英语的真正源头始于1806年大批英国士兵、管理人员、传教士涌入并定居开普敦。1870年和1886年涌向金伯利钻矿和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的矿工又加速了讲英语人群的聚集。这些既是南非英语的源头,也是其发展演进的根基。
虽然真正将英语作为家庭语言的人口仅占南非总人口的10%(Gough 1996),但是英语在南非官方语言中占据着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英语在南非的演进一直伴随着长期殖民统治、种族隔离和多语种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环境之中。根据网络出版物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民族语言志——世界语言》2013)统计,南非有31 种语言,其中25种为人所用,3 种为无母语人口的第二语言,3 种已经消亡。语言的人口和地理分布大量重叠、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导致的语言与文化的政治化倾向决定了南非语言规划政策、基本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南非的词典事业发展走向。
正是这种异常复杂的社会语言环境给英语(特别是词汇)在南非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形成了明显有别于其他英语变体的南非英语。(Klein 2009)像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其他英语变体国家一样,早期的南非在相当长时间里同样依赖从英国(后来从美国)引进英语词典。南非英语与英国英语之间存在的传统联系使英国词典进入南非处于优势地位,使南非成为英国词典出版商的巨大市场。(Gouws 1999)直到20 世纪末期,由于美国英语持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美国英语词典才逐渐成为南非用户(特别是年轻用户)案头的工具书。
南非英语词典的出现有其重要的国际、历史、政治、文化和民族背景。除了英美之外,其他主要英语国家也先后编纂了属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词典。(参见雍和明,彭敬2015)其他英语变体国家不断发展的词典事业刺激着南非学界的神经,南非必须拥有自己的英语词典的民族语言自立意识不断增强,从而使南非英语变体研究及其词典编纂事业得到空前的重视,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国家通过立法确定有关专业机构的举办、组织、拨款等事项。南非英语研究机构、南非英语词典研究所和专业词典出版机构都是国家立法的直接产物和衍生物,为南非英语词典的繁荣提供了理论、实践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据现有文献考证,南非词典编纂可以追溯到1776年Andrew Sparrman 附录于其游记A Voyage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Towards the Antarctic Polar Circle and Round the World but Chiefly into the Country of the Hottentots and Caffres from the Year 1772 to 1776(《好望角环球游记——经霍屯督兹国与卡非斯往南极圈,1772—1776》)之后的词单。从19 世纪中后期开始,科萨语词典编纂相当活跃,除了单语词典之外,更多地出现了科萨语与祖鲁语和英语的双语组合。(Nkomo & Wababa 2013;Mtuze 1992)
19 世纪中叶前后,A. N. E. Changuion 和Jacob L. Dhne 分别编纂了Proeve van Kaapsch Taaleigen(《开普语言特性表征》1844)(Gouws 1999)和A Zulu-Kaffir Dictionary:Etymologically Explained,with Copious Illustrations and Examples,Preceded by an Introduction on the Zulu-Kafir Language(《祖鲁/黑人语言词典》,1857)。前者是南非荷兰移民所讲荷兰语词的汇集,是南非荷兰语的鼻祖,后者则是祖鲁语与南非其他黑人语言的对译词典,开创了南非荷兰语和祖鲁语词典学先河。南非词典编纂从此改变轨迹,由南非荷兰语和祖鲁语词典学主导。
南非荷兰语的这种主导地位直到1969年南非英语词典研究所正式创建才逐渐受到挑战,最终因牛津大学出版社与该中心合作,通过选题策划、专业培训、理念引领、技术扶持等方式的强势介入而有取而代之之势。“英语,更为具体地说,南非英语在南非词典史上的地位绝不可低估。”(Gouws 1999)从类型上看,南非英语词典主要包括单语、双语和专科三类,以单语和双语词典为主体,尚未见到百科词典。其出版媒介主要是纸质、电子、在线和手机模式,仍然以传统的纸质媒介为主,电子、在线和手机词典基本上建立于纸质词典文本或者语料之上。在南非,“通用词典是覆盖面最广的类型,所有官方语言至少有一部通用词典”,“在专科类别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词典”,而电子、网络和手机等多媒体词典“通常是一些现有纸质词典的电子版本”。(Klein 2009)
南非英语单语词典可以追溯到1913年出版的Africanderisms(《南非用语集》),“由业余爱好者卫理公会派牧师Charles Pettman 编纂”(Silva 1999)。它“很有可能是南非英语词典早期发展最重要的突破”,“从历时角度看,其重要性在于强调南非英语作为新兴的发展中的英语变体”,“不仅应该看作是Penny Silva 的A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n English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历时南非英语词典》)的直接先驱,而且必须看作是南非英语词典发展最重要的基石之一”。(Gouws 1999)
在1913年之后长达60 多年的时间里,南非再也没有出版过英语单语词典。直到1975年,第二部南非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English Usage in South Africa(《南非英语用法词典》)面世,由Ridley Beeton 和Helen Dorner 合作推出。三年后,Jean Branford 编纂的A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n English(《南非英语词典》1978—1991)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词典的出版标志着南非英语词典研究所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进入实质性的合作。这种合作客观上主导了南非英语单语(甚至双语)词典的编纂,为南非其他官方语言词典编纂树立了范式。
从20 世纪70年代末起,南非英语词典研究所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开发了DSAE Publications(“南非英语词典出版系列”)。该系列后来发展为南非英语词典的主干,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词典有上文提及的《南非英语词典》、Penny Silva 等编纂的A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n English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历时南非英语词典》1996)、Kathryn Kavanagh等编纂的South African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南非简明牛津词典》2002)、William Branford 编纂的South African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袖珍牛津南非英语词典》1992)、南非英语词典研究所编纂的Oxford South African Concise Dictionary(《牛津简明南非英语词典》第2 版,2010)及几部学习词典——Joyce M. Hawkins 编纂的The South African Oxford School Dictionary(《南非牛津学生词典》1996)、Dorothea Mantzel 和Bernd Schulz 编纂的Oxford Afrikaans-Engels English-Afrikaans Skoolwoordeboek School Dictionary (Afrikaans Edition)(《牛津南非荷兰语—英语/英语—南非荷兰语学生词典》南非荷兰语版,2006)等。
《历时南非英语词典》历经“25年研究,扎根于引例佐证之中”(Hicks 2010),成为南非国家词典中的辉煌之作。这部词典只有825 页,收录南非英语特有的8000 余词目,包括南非荷兰语词、马来—印度尼西亚语词、印度语词、科伊桑语词、恩古尼语词、索托语词等,既有日常交际与广播电视口头用语(如indaba,robot),又有官方与行政用语(如group areas,stokvel),还有诸如矿业等专业技术用语(如cocopan,cheesa-stick,blue-ground),配以摘自文学作品、日常会话、广播电视节目中的4.7 万条引证,追踪从16 世纪末期至今南非英语的演变,全面展现了南非多语种、多元文化社会背景下英语发展的独特魅力。
在牛津“南非英语词典出版系列”中还有几部双语词典,如A. Fischer 等编纂的Oxford English-Xhosa Dictionary(《牛津英语—科萨语词典》1985)、G.-M. De Schryver 编纂的Oxford Bilingual School Dictionary:Northern Sotho and English(《牛津北塞索托语—英语双语学生词典》2007)、G.-M. De Schryver 编纂的Oxford Bilingual School Dictionary:Zulu and English(《牛津祖鲁语—英语双语学生词典》2010)以及G.-M. De Schryver 等编纂的Oxford Bilingual School Dictionary:IsiXhosa and English(《牛津科萨语—英语双语学生词典》2014)等。
苏轼偏爱饮茶,所以对茶道也很有研究,对烹茶的每一道程序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试院煎茶》中有“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这几句话刻画了诗人在考试的庭院中细致煎茶的场景,他仔细聆听茶的沸腾之声,看着飞雪般的泡沫来慢慢煎茶,创造了一种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境界。
从上述双语词典名称便可获知,这些词典都是落实南非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计划的一部分,重点是面向中下教育层次的学生,旨在培养他们的双语能力,尤其是用英语进行交际和接受教育的能力。除了《牛津英语—科萨语词典》之外,其他词典都是双向词典,可谓精品力作。《牛津英语—科萨语词典》是基于《牛津学习词典》(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y)编纂而成的单向双语学习词典,“是编者多年研究和教学科萨语的结晶,是多年应对英语—科萨语词典缺失状况的产物”,“毫无疑问是市面上最著名、最成功的科萨语词典”,截至2011年已经重印21 版次。(Nkomo & Wababa 2013)
很显然,南非英语双语词典编纂并非始于21 世纪初期的牛津系列,也并不仅限于上述语言,而是有着百余年历史。由于南非政府实施多语种政策,从法律上确立语言规划和词典编纂的组织机制,因而迄今为止,南非英语双语词典编纂基本实现了与其他官方语言组合的全覆盖。由于篇幅所限,下面仅对南非英语与祖鲁语、南非荷兰语和科萨语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官方语言组合的双语词典编纂进行简要的回顾。
祖鲁语是最早出现在英语双语词典中的南非官方语言。1861年,John William Colenso(1814—1883)编纂了Zulu-English Dictionary(《祖鲁语—英语词典》),开创了祖鲁语—英语双语词典编纂的先河。其后有Alfred T. Bryant 编纂的Zulu-English Dictionary(《祖鲁语—英语词典》),具体出版年代已经无从考证。1900年,Bryant 编纂了疑似为《祖鲁语—英语词典》姐妹篇的An Abridged English-Zulu Word-Book(《英语—祖鲁语词书节本》)。2014年《祖鲁语—英语词典》还推出了激燃版(Kindle Edition)。
1895年,Charles Roberts 编纂了An English-Zulu Dictionary(《英语—祖鲁语词典》)。这部词典共有292 页,其书名页显示,“附有详细的发音和分类规则”,2007年由凯辛格出版有限公司(Kessinger Publishing,LLC)推出当代版,2009年书目大王(BiblioBazaar)再推新版,最新版由珍本图书俱乐部网站于2012年完成后面世。继Roberts 之后,C. M. Doke 和B. W. Vilakazi 合作编纂了Zulu-English Dictionary(《祖鲁语—英语词典》)。(Nkabinde 1999)
1948年,C. M. Doke 编纂了Zulu-English Dictionary(《祖鲁语—英语词典》),收录普通语词,以英语—祖鲁语和祖鲁语—英语编排。1958年,C. M. Doke,D. M. Malcolm 和J.M. A. Sikakana 合作编纂English and Zulu Dictionary:English-Zulu,Zulu English(《英语—祖鲁语词典:英语—祖鲁语,祖鲁语—英语》),篇幅达到342 页,1990年由其他编者修订再版时更名为The English-Zulu / Zulu-English Dictionary(《英语—祖鲁语/祖鲁语—英语词典》),篇幅达到1608 页。这部词典屡次再版,影响颇广。2014年推出了第4 版。
进入20 世纪后半叶和21 世纪初期,比较有影响的双语和多语词典有G. R. Dent 和C. L. S. Nyembezi 合编的Compact Zulu Dictionary:English-Zulu;Zulu English(《精编祖鲁语词典:英语—祖鲁语/祖鲁语—英语》1959;2006,第14 版)和Scholar’s Zulu Dictionary,English-Zulu:Zulu-English(《学者祖鲁语词典:英语—祖鲁语/祖鲁语—英语》1969)、P. C.Taljaard 编纂的The Concise Trilingual Pocket Dictionary:English,Zulu,Afrikaans (Afrikaans,English and Zulu Edition)(《简明三语袖珍词典:英语—祖鲁语—南非荷兰语》南非荷兰语—英语—祖鲁语版,1999)、Shirley Illman 编纂的Illman’s English / Zulu Dictionary and Phrase Book(《伊尔曼英语—祖鲁语词典和用语手册》2014)等。其中,《学者祖鲁语词典:英语—祖鲁语/祖鲁语—英语》于1975年再版,1988年由Nyembezi 推出祖鲁语—英语版,1993年和1995年又由不同出版商推出新版,2009年推出第三版修订版。
20 世纪前25年见证了南非荷兰语和英语之间争夺官方语言地位的紧张博弈。这种博弈虽然最终以双方于1925年均被确定为官方语言而收场,但是在整个博弈过程中,“自视高人一等”的南非英语总是充当着样板和动力的角色。(Gouws & Ponelis 1992)这种政治博弈的结果便是南非政府做出一系列的语言规划和组织建设安排,成立词典研究中心和编纂词典自然是落实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非荷兰语,借助传统人口优势和厚积薄发的有利条件,于1926年组建了国家层面的词典编纂机构——Bureau of the Woordeboek van die Afrikaanse Taal(南非荷兰语词典编纂局,简称WAT),筹划规模宏大的词典编纂活动。南非官方语言之间的词典编纂竞赛就此拉开了帷幕。
南非荷兰语与英语组合的双语词典以D. J. Potgieter 和J. M. Potgieter 合编的Juta se Woordeboek Afrikaans-Engels end Engels-Afrikaans/Juta’s Dictionary Afrikaans-English and English-Afrikaans(《居塔南非荷兰语—英语/英语—南非荷兰语词典》1900)为起点,紧随其后的是Patriot Woordeboek/Patriot Dictionary(《爱国者词典》1902—1904),由S. J. du Toit 编纂完成。它们成为南非词典史上的第一批此类双语词典。《爱国者词典》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南非荷兰语—英语,第二部分为英语—开普荷兰语,其主要编纂用意“在于促进南非英国人和荷兰人之间的合作”(Gouws 1999)。由于《爱国者词典》“是首批尝试建立这两种语言之间词典学联系的作品”,所以“应该看作是对南非词典学发展的重要贡献”。(Gouws 1999)它们“在南非荷兰语标准化和词典事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展示了南非荷兰语的发展”,也“证明了其作为官方语言独立存在的权力”。(Gouws & Ponelis 1992)
由于受其影响,在整个20 世纪和21 世纪初期出现了不少名称雷同的此类双语词典,代表作有M. S. B. Kritzinger 编纂的Woodeboek Afrikaans-Engels Engels-Afrikaans(《南非荷兰语—英语/英语—南非荷兰语组合词典》1928,两卷组合)、D. B. Bosman 和I. W. van der Merwe 编纂的Tweetalige Woordeboek/Bilingual Dictionary(《南非荷兰语—英语双语词典》1931—1936)、M. S. B. Kritzinger 等编纂的Skool Woordeboek(《南非荷兰语—英语/英语—南非荷兰语学生词典》1962)、J. L. Van Schaik 编纂的Major Dictionary:English-Afrikaans/Afrikaans-English(《大词典:英语—南非荷兰语/南非荷兰语/英语》1986)、A. Venter编纂的English-Afrikaans & Afrikaans-English One-to-One Dictionary(《英语—南非荷兰语/南非荷兰语—英语对译词典》2012)、Alet Kruger 和Penny Grearson 编纂的Afrikaans-English,English-Afrikaans Dictionary (Afrikaans Edition)(《南非荷兰语—英语/英语—南非荷兰语词典》南非荷兰语版,2014)等。
英语与科萨语组合的双语词典始于1855年James Perrin 编纂的An English-Kafir Dictionary of the Zulu-Kafir Language:As Spoken by the Tribes of the Colony of Natal(《纳塔尔殖民地部落祖鲁语—科萨语之英语—科萨语词典》)[2]。这部词典共有232 页,凯辛格出版有限公司于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重印,足见其重要的语言文化价值。Perrin 编纂了另一部疑似其姐妹篇的A Kafir-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Zulu-Kafir Language,as Spoken by the Tribes of the Colony of Natal(《纳塔尔殖民地部落祖鲁语—科萨语之科萨语—英语词典》),初版面世年代虽然不详,但是有理由相信它们相距不远。这两部词典的问世标志着科萨语—英语双语词典编纂的滥觞。
1899年,Albert Kropf 编纂了A Kafir-English Dictionary(《科萨语—英语词典》),旨在“纪念很快被英语取代的黑人语言”。它基本上用英语解释科萨语,于1915年由Robert Godfrey 修订再版,“已经成为科萨语词典语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科萨语知识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Nkomo & Wababa 2013)与之形成对应的是William Jafferd Davis 编纂的An English-Kaffir Dictionary,Principally of the Xosa-Kaffir but Including also Many Words of the Zulu-Kaffir Dialect(《英语—科萨语词典》1903),共有514 页,如书名所示,主要收录科萨黑人语言,但也包括祖鲁黑人方言中的许多语词。2012年由乌兰出版社重印,2013年由哈德出版公司(HardPress Publishing)再次重印,可见也是一部极具学术、语言和文化价值的词典。这部词典的成书时间不详,但专家普遍认为至少是在1923年前面世的。
进入20 世纪,James McLaren 编纂了A Concise Kafir-English Dictionary(《简明科萨语—英语词典》1915)和A Concise English-Kafir Dictionary(《简明英语—科萨语词典》1923)。这两部词典包含许多陈旧用词,对当代词汇收录有限,但是“是许多年来仅有的可以依赖的、可以查阅的科萨语词典”(Mtuze 1992)。1955年,McLaren 又编纂了A Concise Xhosa-English Dictionary(《简明科萨语—英语词典》修订版),1975年推出A New Concise Xhosa-English Dictionary(《新编简明科萨语—英语词典》)。1985年,A. Fisher 等合编了The English-Xhosa Dictionary(《英语—科萨语词典》)。这部词典“对于需要将文件从英语翻译成科萨语的公职人员来说非常有用”(Mtuze 1992)。
讨论南非英语词典不能不提及“Pharos Dictionaries(法罗斯词典系列)”。其中有不少产生重要影响的词典,大多数为双语词典,也有为数不多的单语词典和多语词典,如Pharos Afrikaans-Engels-Engels-Afrikaans Woordeboek/Pharos Afrikaans-English-English-Afrikaans Dictionary(《法罗斯南非荷兰语—英语与英语—南非荷兰语词典》2005)、Pharos 5-in-1 Dictionaries/Woordeboeke(《法罗斯五合一词典》2007)、Pharos Afrikaans-Engels-English-Afrikaans Kernwoordeboek/Pharos Concise Dictionary(《法罗斯南非荷兰语—英语/英语—南非荷兰语简明词典》2007)、English-Xhosa/Xhosa-English Dictionary(《英语—科萨语/科萨语—英语词典》2011)、Pharos Afrikaans/English-English/Afrikaans Dictionary(《法罗斯南非荷兰语—英语/英语—南非荷兰语词典》2013)等。
以上不难看出,南非双语词典编纂目前仍然主要限于南非官方语言之间的组合,以南非英语、南非荷兰语和祖鲁语之间的组合较为常见,也有少数其他主要官方语言之间的组合,但较少发现南非官方语言与当代欧洲语言(如法语、德语)或者东方语言(如汉语、日语)的组合,屈指可数的是与当代荷兰语的组合,这完全是南非与荷兰存在殖民历史和文化传统联系所致。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南非与外部世界交往更加紧密,南非官方语言与世界其他语言组合的双语词典也会逐渐增多。
除了单语和双语词典外,南非英语词典中还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专科词典,如E. H. D Norval,A. J. Louw 和J. D. Arndt 编纂的The Economic & Legal Dictionary English-Afrikaans(《英语—南非荷兰语经济与法律词典》1933)、H. J. Terblanche 编纂的Engels-Afrikaanse Tegniese Woordeboek/English-Afrikaans Technical Dictionary(《英语—南非荷兰语技术词典》1953)、H.W. Snyman 编纂的Medical Dictionary:Afrikaans and English(《南非荷兰语—英语医学词典》1992)、Reino Ottermann 和Maria Smit 合编的Suid-Afrikaanse Musiekwoordeboek/South African Music Dictionary(《南非音乐词典》2000)、W. F. J. Steenkamp 和H. J. J. Reynders 合编的Ekonomiese en Bedryfswoordeboek:Engels-Afrikaans/Dicitonar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English-Afrikaans(《英语—南非荷兰语经贸词典》2004)等。专项词典有开普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World Englishes(《国际英语》2008)的作者、语言学教授Rajend Mesthrie 编纂的A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n Indian English(《南非印度英语词典》2011)。
南非具有代表性的词典都是在计算机、网络和电子技术成熟之后开发的,基本都具有多媒介运行的基础和可能,所以其主要词典基本都实现了计算机、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介运载和检阅功能的转换,覆盖通用和专科、单语和双语(多语)等类型。最具代表性的有《南非荷兰语词典》的电子运行版——Elektroniese WAT、多功能旅游与语言网络服务平台Travlangs(Travel & Language Services)、多模块的DDP Freeware、Pharos Afrikaans/English-English/Afrikaans Dictionary CD-ROM(《法罗斯南非荷兰语—英语/英语—荷兰语词典》CDROM 版)、祖鲁语—英语在线双语词典isiZulu.net、Pharos Woordeboeke Dictionaries 5-in-1 on CD-ROM(《法罗斯五合一词典》CD-ROM 版)、Multilingual Illustrated Dictionary CD-ROM(《法罗斯多语插图词典》CD-ROM 版)等。这些词典都具有“即时检索、关联项目链接、检索信息新路径、减少对字母顺序依赖、随意拼写检索、输入语词智能化推测、有声发音”(Prinsloo 2007)等特点。法罗斯词典出版机构是南非电子词典开发最为成熟的、具有引领能力的出版商。
南非虽然不是世界词典强国,但是在非洲绝对是词典大国,尤其是近30年的词典事业成就,实在令人刮目相看。近30年来,南非词典的演进,特别是南非英语词典的发展,具有规范性、法制性、计划性、前瞻性和全面性等特点,对南非语言规范化进程、语言规划政策落实、各民族和谐融合、国际交流合作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回顾南非词典发展,没有多层次、全方位的支撑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的,至少可以提供以下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首先是法律支撑。1995年,南非成立泛南非语言委员会(The Pan South African Language Board),南非宪法赋予该委员会“发展语言、推行多语政策”的职责,“为南非每一种官方语言成立国家词典研究所(national lexicographic units)”,“研究所按照1973年‘公司法’第21 条,以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运作”,国家“拨付经费以便研究所履行功能”。(Alberts 2011)“拥有这样的法律支撑应该是南非词典事业在过去十年中快速发展扩张的主要原因。”(Klein 2009)
其次是组织支撑。南非艺术、文化、科技部与泛南非语言委员会密切合作,为所有官方语言制定整体的词典政策框架,统筹协调词典项目和词典活动,在国家层面成立南非荷兰语编纂局,在比勒陀利亚大学成立了恩德贝勒语和塞皮迪语词典研究所,在祖鲁兰大学成立了祖鲁语和斯威士语词典研究所,在罗德斯大学、福特海尔大学、奥兰治自由邦大学、西北大学和南非大学分别成立了南非英语、科萨语、索托语、塞茨瓦纳语和聪加语词典研究所,文达语词典研究所则挂靠其他单位。所有研究所之间既相互协作,又各有分工。
第三是规划支撑。南非艺术、文化、科技部和泛南非语言委员会从宏观顶层设计南非词典发展规划,而编纂局和各高校研究所则根据自身的职能制定编纂计划,每个机构都有短期编纂和中长期发展计划。工作进度和成果按期向南非艺术、文化、科技部和泛南非语言委员会做书面报告,并接受业务检查和评估。
目前规划中正在进行的项目主要是尚未覆盖的南非官方语言双语词典的编纂和现有类型的补缺与修订,如IsiNdebele-English Pictorial Dictionary(《恩德贝勒语—英语图解词典》2016)、English-Xitsonga Comprehensive Bilingual Dictionary(《综合英语—聪加语双语词典》2016)、Xitsonga Cultural Dictionary(《聪加文化词典》2018)、Xitongsa-English/English-Xitonga Bilingual Dictionary(《聪加语—英语/英语—聪加语双语词典》修订第2 版,2020)等。
第四是队伍支撑。南非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将词典编纂职业化的国家。国家根据语言政策组建机构,配备专业人员,使词典编纂常态化和可持续化。“国家词典研究所成果和在研项目总结报告(2013)”显示,各研究所的主要成果和项目基本都是由专门人员完成和负责实施的,当然编纂团队也会吸纳非机构人员参与,尤其是进行技术含量复杂的大型项目研发。非洲语言词典编纂和研究基本为母语不是非洲语言的人士所主宰,其编纂和研究成果无疑是主流和主体。“所有编者都是操非母语人员,有些以非洲语言为母语的只是参编人员”(Prinsloo 1999),由此可见其队伍整体素质,当然也暴露出其结构缺陷。
第五是环境支撑。南非词典发展系统化的外部环境既包括上文提及的法律和政策,更包括成果的市场转化。成立词典出版公司是不二的选择,其中首推法罗斯词典出版公司及其设计出版的“法罗斯词典系列”。这是南非唯一一家致力于词典出版的机构,拥有自己的编纂、修订、改编和出版团队,专注于南非荷兰语单语词典和南非荷兰语与英语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兼顾其他语言词典、多语词典、专科词典、参考书等的出版。电子产品和在线图书馆是它的一大亮点和特色,在线图书馆收藏大批绝版词典资源,而且在不断扩充。
此外,南非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uth Africa)、书特射手出版公司(Shuter and Shooter Publishers)、南非传统出版社(South African Heritage Publishers)等出版商也在不同程度上兼顾词典的出版,而且各有侧重。南非牛津大学出版社侧重南非英语词典,书特射手出版公司侧重初等与中等教育程度的语言词典,南非传统出版社则侧重科萨语和索托语词典,当然它们也兼顾其他官方语言。
第六是理念先导。在开展词典编纂项目前,南非荷兰语词典编纂局、泛南非语言委员会、南部非洲语言协会(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Southern Africa)、南部非洲非洲语言协会(The Africa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Africa)、词典研究所和高校都会组织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座谈会、讲座或者报告等,对有关项目和课题进行理论和实践探讨,力求形成共识。
南非罗德斯大学于1964年成立“非洲英语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English in Africa),专司南非英语语言和教育研究之职。1969年,南非英语词典研究所(The Dictionary Unit for South African English)作为该所的一个部门正式诞生,1985年经南非国民教育部批准开始独立运作。该中心专门负责收集和记录南非英语特有用语和用法,反映多语种和多元文化对形成南非英语的影响,关注英语在全世界范围的演变。其语料档案和研究成果为编纂南非英语词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南非英语变体研究、词典事业发展以及语言政策制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5年创建的非洲辞书学会(The African Association for Lexicography)从第二年开始,每年举办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20 届,每年都有传统和热点议题供与会者发表见解。南非荷兰语词典编纂局1991年创办的Lexikos(《词汇与词典期刊》)从1996年第6 卷起更是成为非洲辞书学会的“官方喉舌”(见协会网站),每年出版一卷,所发表论文具有国际水准和影响力,聚焦非洲语言和语言词典发展成为其办刊的一大亮点。
附 注
[1]南非11 种官方语言分别是南非荷兰语(Afrikaans,又译为阿非利堪斯语)、英语(English)、恩德贝勒语(Ndebele)、塞皮迪语(Sepedi,又译为北梭托语)、科萨语(Xhosa)、祖鲁语(isiZulu)、索托语(Sotho)、塞茨瓦纳语(Setswana)、斯威士语(Swati 或Swazi,又译为斯瓦蒂语)、文达语(Tshivenda)和聪加语(Tsonga),除了英语和南非荷兰语源自印欧语系外,其他均为非洲本土语言。
[2]在南非语言标准化进程中,不少单词拼写和用法并不统一,如Kafir 有时拼成Kaffir,可以泛指非洲黑人语言,也可特指南非科萨语。所以,凡是词典名称中有Kafir 的词典一般归入科萨语类。
1.雍和明,彭敬.英语词典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Alberts M. National Lexicography Units:Past,Present,Future. Lexikos,2011(21):23—52.
3.Gough D H. Introduction to A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n English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Oxford:Oxford Unirersity Press,1996.
4.Gouws R H. Situating A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n English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within a More Comprehensive Lexicographic Process. Lexikos,1999(9):269—282.
5.Gouws R H,Ponelis F A.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frikaans Lexicograph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1992(12):1—44.
6.Hicks S. Firming Up the Foundations:Reflections on Verifying the Quotations in a Historical Dictionary,with Reference to A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n English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Lexikos,2010(20):248—271.
7.Klein J. South Africa’s New African Language Dictionaries and Their Use for the African Speech Communities. Lexikos,2009(19):423—435.
8.Kosch I.Review of G.-M. De Schryver’s Oxford Bilingual School Dictionary:Northern Sotho and English. Lexikos,2013(23):611—627.
9.Mtuze P T. A Critical Survey of Xhosa Lexicography 1772—1989. Lexikos,1992(2):165—177.
10.Nkabinde A C. Zulu Dictionary Project in Lexicography in a Multilingual South Africa. Lexikos,1999(9):239—241.
11.Nkomo D. Review of G.-M.De Schryver et al’s Oxford Bilingual School Dictionary:IsiXhosa and English. Lexikos,2014 (24):417—422.
12.Nkomo D,Wababa Z. IsiXhosa Lexicography:Past,Present and Future. Lexikos,2013 (23):348—370.
13.Prinsloo A F. Review of Philip Louw’s Oxford Afrikaans-Engels/English-Afrikaans Skoolwoordeboek/School Dictionary. Lexikos,2007(17):453—457.
14.Prinsloo D J. Sepedi Dictionary Project in Lexicography in a Multilingual South Africa. Lexikos,1999(9):231—233.
15.Prinsloo D J.Electronic Dictionaries Viewed from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Linguistics,2005(34).
16.Prinsloo D J.Review of G.-M. De Schryver’s Oxford Bilingual School Dictionary:Zulu and English.Lexikos,2010(20):760—766.
17.Silva P. South African English:Operator or Liberator. ∥Levin M,Estling M.(eds.)The Major Varieties of English.Vaxjo:Acta Wexionensia,1998.
18.Silva P. Dictionary Unit for South African English in Lexicography in a Multilingual South Africa. Lexikos,1999(9):224—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