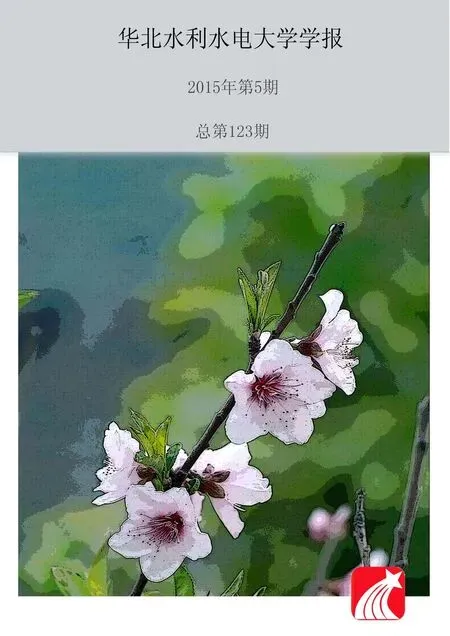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书写
冯学青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书写
冯学青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苏童在他的妇女生活题材小说中,刻画了个性独特的“红粉意象群”,描绘出处于过渡时期女性的生存状态,以细腻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她们内心深处对男权制度强烈的依附,并通过女性之间的相互对立斗争及其悲剧性的命运结局完成对女性的命运书写,显示出作者对女性生存困境及自身价值的思考。
红粉意象;生存状态;依附性;悲剧命运
从《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到《另一种妇女生活》,苏童构建了自己对“妇女生活”系列小说的书写,精雕细琢地刻画了一个个性格各异又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形成了他笔下的“红粉意象群”。苏童是善于描写女性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1]6苏童塑造得最成功的是那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过渡时期的女性形象。作为男性作家,他绕开男权话语,选择从中性视角来描述他所理解的女性,通过对大量女性世界的描摹和观照来展现女性的生存状态,试图再现女性如何面对自身,如何面对她们所处的困境。
一、女性的生存状态
苏童的作品在人文地理上展示出江南湿润的古雅境界,曲水深巷、绿树红花、布满青苔的石板桥、斑驳的砖木结构的粉墙楼宇……女性的意象便在这种背景之中显现出来。南方在苏童的笔下是美丽的、抒情的,但又是阴郁的、残忍的,充满了暴力、乱伦、颓败和神经质,而这正是小说中的女性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幽暗、迷离而又古旧的陈家大院,破落、冷清的照相楼,还是与世隔绝、凄冷的简家绣楼,这些女子生活的地方虽然富有江南水乡唯美典雅的意味,却又是淫靡、阴郁、颓败的。在这容易让人迷失的环境中,她们也似一只只迷途的羔羊,处于命运无形的掌控之下。这些女性大都脆弱、虚荣,甚至乖戾而残忍,聪敏而又尖刻,美丽而又淫乱,像一朵朵美艳无比而又给人致命伤害的罂粟花,开放在江南幽暗腐靡的角落里。在出场时,她们都富有饱满的生命力,后来却被不断地压抑,无法张扬自身自由,最终形成种种病态心理,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苏童所描写的是处于新旧社会过渡时期的女子,而不是旧制度下唯唯诺诺的女性。她们有的受到过新式思想熏染,有的能够在新旧社会的交替中选择新的生活,对未来的人生道路,她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可以说她们的未来是自身选择的结果。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她是受到过高等教育的,然而在父亲自缢身亡后,她首先选择的便是嫁入有钱人家做小。《红粉》中秋仪在妓院被关后,她跳下那辆带其驶向女性独立道路的卡车,去投奔老浦,后来虽因与老浦母亲争吵搬出老浦家而在玩月庵出家,但最终仍旧选择和冯老五结婚。这些女性在面对自己命运时,认为只有在男性身上才能寄托自己的未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受压迫者,是与男性相对立的,女性与女性站在同一战线上,她们应该是同盟军,共同对抗男性以维护女性的整体利益。但在苏童的小说中,却有着明显的女性与女性间的对立冲突模式。张爱玲说:“同行嫉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2]210她们为争夺在男性身边更好的生存状态而煞费苦心,明争暗斗,争风吃酷,相互迫害,将“同行”之间
的嫉妒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妻妾成群》中四房太太为争夺陈佐千的宠爱费尽心机,连丫环雁儿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即使是在梅珊死亡、颂莲发疯之后,妻妾之间的战争依然不会停止,新来的五姨太接替她们的位置将之进行下去。《红粉》里小萼和秋仪因老浦而从亲密无间的姐妹变成彼此的敌人;《妇女生活》中娴、芝、箫三人生活在对彼此的仇恨、敌视和窥探之中。在这种同性之间的对立冲突中,女性不再是美与爱的化身,她们有着自己先天的弱点和缺陷,母性、亲情、友情也在这种冲突中逐渐消解。
二、男权制度的附属品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男性牢牢地占据着统治地位,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男权文化。在男性的主导下,所有的权威位置都属于男性,男权话语被纳入整个社会的运行体制之中,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其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也是由男性所制定的。这种体系之下的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的命运系于男性身上,交出自己的话语权,最终处于失语的状态,对男权产生了深深的依附性。这种意识渗入到她们思想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面临对未来的抉择时,她们会毫不犹豫地将男人作为自己的归宿。苏童描写的那个时代虽然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女性对男性的认识态度已有所改观,她们清楚男性是不可靠的,但在生活之中男性又是不可或缺的,于是当选择出现时,她们纷纷摒弃那条可以通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依附于男性。
颂莲正值青春美貌,却选择嫁给可以做自己父亲的陈佐千当姨太太,自愿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为巩固自身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自恃年轻对他人不屑一顾的颂莲和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毓如、慈善面孔蛇蝎心肠的卓云、冷傲又不甘寂寞的梅珊展开了一场争宠夺爱的斗争,即使后来陈佐千性功能衰退,她们依旧绞尽脑汁,互相倾轧。秋仪和小萼在从喜红楼出来后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只能投身于男性的羽翼之下寻求暂时的庇佑。正如小萼说:“男人有时候像驿车一样,女人都要去搭车,搭上车的就要先走了。”因而,当老浦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牢牢地抓住了他,使老浦抛弃了秋仪。在没有男人的日子,女人和女人可以成为姐妹;男人一出现,情同姐妹的两人就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娴、芝、箫一家三代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娴一见到孟老板似乎遇见了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人,很快便搬离她家的照相馆,住进孟老板为她准备的公寓里。芝为脱离母亲的监控而和工人家庭出生的邹杰结了婚。箫与小杜的恋爱不冷不热,约会中多次不欢而散,但二人最后“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进了婚姻。绣楼里的简家姐妹独居多年,与世隔绝,在酱园的营业员顾雅仙的刻意安排之下,简少芬和鳏夫章老师见了面,并因要与之结婚而与姐姐简少贞关系破裂,显示出无力遁逃男性社会的困境[3]。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4]89在这些女性的潜意识之中正是如此,女人是离不开男人的,女人终究要和男人一起生活。
女性依附男性,以求生存状况得到保障,在这背后,其实质是对物质和金钱的依附。颂莲跟陈佐千的对话便道出了这一点:她拍拍陈佐千的脸说,是女人都想跟你。陈佐千说,你这话对了一半,应该说是女人都想跟着有钱人。颂莲笑起来,你这话也才对了一半,应该说有钱了还要女人,要也要不够[5]44。秋仪也清楚女人一旦没有钱财就只能依赖男人,但男人是不可靠的。当男性物化为金钱的替代品,这些女性在男性身上寻求的也只是满足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就是卖淫关系,是“以婚姻形式表现出来的钱与性的交换”[6]。这也就注定了其结局的悲剧性。在她们身上,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荡然无存,更多的表现为人性的贪婪、自私和冷酷无情。
三、悲剧性的命运结局
苏童“妇女生活”系列小说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妻妾成群》中四房太太及丫环雁儿争宠的结果是雁儿病死,梅珊让卓云设计捉奸在床被投井而死,颂莲因目睹这一过程而最终发疯。《红粉》中秋仪最后嫁给了鸡胸驼背的冯老五,小萼跟一个北方男人远走他乡。《妇女生活》中娴、芝、箫一家三代都逃脱不了被男人抛弃的命运。《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简少贞因接受不了妹妹出嫁、抛弃自己的现实,用绣花针扎破动脉血管,采取了异样的死亡方式。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完成了生命的最后仪式。她们的悲剧命运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千千万万女性的命运。在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女性不过是男性宣泄性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更不用说人性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她们的肉体和精神都是属于男性的,任其摆布并随时可能被丢弃[7]。
“连最平庸的男人在和女人相比时,也会觉着自己非同凡响。”[8]20男性文化的巨大压力驱动着女人的言行举止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男性文化的要求,接受着男人强加给她们的诸多观念,为了生存,她们也不得不将自己依附在男性身上,将自己物化。这也是她们悲剧性命运的原因之一。《罂粟之家》中的翠花花只是刘老侠送给刘老太爷的一份礼物,
像皮球一样被拍来拍去;刘老侠用自己的亲生女儿刘素子换来了三百亩地,土匪姜龙夜袭刘家时,他又用女儿的贞操去换刘家暂时的安宁。封闭的陈家老宅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将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形态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陈佐千是这个大院里的主人,四位太太得以维系和生存的支柱。在他的意识里,女人就是男人的玩物,是发泄自己欲望的对象,四位太太也时时刻刻逢迎着他,甚至不惜做“狗”来满足其淫欲,她们知道只有讨好了陈佐千,自己才会有在这个大院里生存下去的机会和空间。这些玩弄她们的男性也并非顶天立地、英勇威武、学识渊博之辈,有的生命日渐萎缩,有的懦弱无能,有的恬不知耻,然而,正是这样的男人主宰着她们的命运。
苏童作品中的女性对男权制度的依附,也显示出自轻自贱的自我意识,在她们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自卑感。陈家大院的几位女性自甘沦落为男性的寄生虫,无所事事。小萼并不认为自己被妓院剥削压迫,与他们苦大仇深,反而觉着理直气壮,还声称“你们是良家妇女,可我天生就是个贱货。我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就是个贱货”[5]77-78。织云出生于米店之家,本可以过着平淡、安宁的生活,但她渴望容身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世界,十五岁便做了六爷的情妇,最后因与阿保的私情暴露而被抛弃,生下孩子之后她毅然决然地收拾包袱进入吕公馆当姨太太,但却过着连老妈子都不如的生活。箫更是直言:“我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我不喜欢女人的生活。你们做男人的不知道做女人有多苦,有多难。女人不一定非要结婚,可她们离不开男人,最后都会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瞧不起女性,我也瞧不起自己。”[5]121这些女性都看不起自己,轻视自己,贬低自己,甚至萌生出做男人的念头。透过苏童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女性反抗意识的缺失,其中虽有一两位女性不甘于自己的命运,试图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其反抗力量是微弱的,很快便熄灭了。或许这也正是苏童表达对女性命运叹息与哀婉的一种方式,用她们的死对男权文化提出最有力的质疑。
苏童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深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展现她们在男权世界下的生存困境,并选择以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模式来刻画女性形象,将其性格中的弱点、丑陋之处呈现在读者面前。她们既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恶魔,而是有血有肉的凡俗女子,有凶残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着,寻求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苏童说他的创作目标是:“打开人性心灵世界的皱折,轻轻拂去皱褶上的灰尘,看清人性自身的面目,来营造一个小说世界。”[9]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女性的悲剧性结局,是她们在为生存挣扎中对于男性世界的绝望和妥协,是对生命力和自由被压抑的控诉,她们纯真善良的本性在生存中渐渐沾染了污点,为生存而向男性显示出谄媚的嘴脸,将自身价值的寻求放在一个个衰萎无能的男人身上,这样的做法只能是走向死亡。而苏童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完成了他对女性的命运书写,表达自己了对于女性命运的观照和女性应该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思考。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陶丽华,黄德志.无法遁逃的女性生存困境:析苏童“妇女生活”系列小说[J].电影文学,2010(10):116-117.
[4]张爱玲.有女同车[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5]苏童.苏童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6]王建珍,闫兰娜,王海静.男权文化中的女性悲剧: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妇女研究论丛,2006(4):63-65.
[7]吴云芬.无法逃离的生命归宿:论苏童小说中的死亡主题[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9.
[8]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9]周新民.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2):25-27.
(责任编辑:王菊芹)
Female Fate Written in Su Tong’s Novel
FENG Xueqing
(College of Arts,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In Su Tong’s women life theme novels,depicts a series of unique character of“women’s image”.Depicted in the“transition”women’s living condition,It descripts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wome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Through the exquisite and deep writing style,it reveals their inner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partriarchal system,and through the contradictory conflict between women and the fate of the tragic end to complete the writing of the female,which shows the authors’consideration about female survival plight and its self-worth.
women’s image;living condition;dependent;tragic fate
I206.5
A
1008—4444(2015)05—0122—03
2015-05-18
冯学青(1991—),女,河南信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