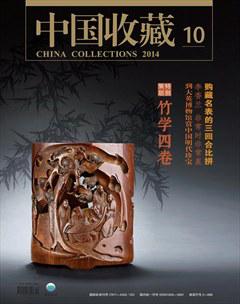“多事饶舌”老缶 不肯随意绘朱菊
胡西林

又近一年重阳时,朋友约我到龙井路上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喝茶,顺便看两幅吴昌硕的作品。两幅作品,一幅画梅,一幅绘菊,都是吴昌硕晚年所作,颇为养眼。尤其那幅菊画,竟然让我想起了在新加坡秋斋曾经看过的一幅吴昌硕的菊画,把一件几乎忘记了的事情又想了起来,令我高兴。
看画就是这样,常常会钩沉记忆,盘活脑子,给人快乐。
秋斋的菊画四尺整纸(纵137里米,橫68.5厘米),对角构图,画从左上角起笔,枝蔓抱团,花叶丛生,密实得仿佛花之瀑布,恣意倾泻。菊花则绘二种——白菊和黄菊。显然这不是“艺菊”之菊,未经园艺修整,却充满自然生气。
右侧长题曰:“每到重阳忆我家,便拈秃管写黃花。芜园风雨应如旧,老菊疏篱浅水涯。”这是吴昌硕的一首题菊旧诗,在他诸多绘菊作品上都曾题写。
秋天固然气爽宜人,却也让人思旧怀乡,但凡绘菊题此诗,无论酬人还是自存,吴昌硕总是笔蘸乡情,为什么?因为芜园在安吉,是吴昌硕老家屋前的一块园地,他当年曾经耕读的地方。由于常年在外,客居他乡(时为乙卯即1915年,吴昌硕定居上海已两三年),园因无人打理而“芜”,一个“芜”字便是乡愁。所以画中菊花不事修整,像金冬心在扬州绘野梅和郑板桥在山东范县、潍县画竹子,都因为身处异地,事关乡情,笔墨中有思乡愁绪。
但是如此布局显然让吴昌硕感觉有些不足,因为是对角构图,右侧又是自上而下即所谓一柱香式长题,这使得画幅下方,特别是左侧下角显得有些空。于是吴昌硕以一首六言小诗作补题。这一题就题出了名堂,让这幅画不仅耐看而且耐读,大家手段就是不一样。
六年后(1921年,辛酉。以笔者所见为限),赵云壑也画了一幅菊花,也是大幅,纵151.5厘米,橫82厘米,比吴昌硕这幅还大。此画满幅构图,两侧绘石,中间的菊花依石生发,笔墨及参差错落都很好,花则开得灿烂热烈。与吴昌硕所绘不同,此画绘菊三种——白菊黄菊以外,还有朱菊。朱菊敷色是洋红,又因为花放高枝,所以在画中格外惹人眼目。画的右上角也有题诗,题的正是吴昌硕画上的那首六言小诗。
赵云壑大家都知道,苏州人氏,出身在一个以父亲撑船为业的家庭里。家境清贫,他却自幼聪颖,受母亲的影响,喜欢读书,也喜欢写字画画。赵云壑最初是跟随擅长花鸟的医生蒋先农学画,继而转益秦子卿、李农如、任立凡诸师,30岁时在苏州经顾茶村介绍再拜吴昌硕为师,从此无论书画还是篆刻,艺事大进,是吴昌硕的得意弟子。
赵云壑的作品中有一些与吴昌硕不仅题材相同,画上所题也相类甚至相同,其中尤以菊桃类作品为多。比如吴昌硕喜欢韩愈的诗,常常以韩愈诗句“墙根菊花可酤酒”为题作画,赵云壑也是,他也以韩愈的这句诗为题作画,显然是受了老师的影响,当然在表现手法特别是在构图上他与老师有所不同。
但是,在这幅题六言小诗的菊花图上师生二人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吴昌硕画中所绘是两种菊花——白菊和黄菊,而赵云壑是三种——白菊、黄菊还有朱菊。这本无所谓,画家作画本来就是各有各的诉求,同一题材不同表达才好。何况对一些人来说,一幅画上多一色少一色、多一种菊少一种菊,仅仅只是为了服从画面的效果需要而已。但是这幅画却是一个例外。其实,吴昌硕的绘菊作品中并不乏朱、白、黄三种菊花并绘一图的,他更擅长用红色,与赵之谦一样,凡是作菊桃题材的画,一上红色,就更能显示他的胆气,艳而不俗。但是这幅菊花他却不绘朱菊,为什么?因为题了这首六言小诗,题这首诗,对所绘菊花是有前提限制的。且读小诗:
酤酒昌黎残菊,谋生杜甫长才。
学圃敢云韬晦,挥杯聊可上馋。
四句诗24个字,拿韩愈杜甫说事,但不论是韩愈为残菊酤酒,还是杜甫凭优异的才华(长才)谋生,在吴昌硕的笔下(画里),这个时候他们都被归结到了“挥杯聊可上馋”上,也就是画中的菊花是用来下酒解馋的。
菊花可以吃?可以,这许多人都知道。菊花的吃法大致有三类:一、酿酒。《西京杂记》卷三云:“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二、茶饮。古籍记载,菊花味甘苦,性微寒,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以及解毒消炎的功效,自古就是茶饮佳品。三、烹食。菊花佐餐古已有之,屈原诗中就有“朝饮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在广东顺德有菊花鲈鱼、菊花甜肉等名菜,在陕西西安以菊为佐料的菊花锅更是可以上溯至隋唐宫廷御膳谱中的佳肴,在我国其他许多地方也都有以菊花入肴的习惯。
但是菊花可食,并不等于所有的菊花都可佐餐。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无论是酿酒还是茶饮烹食,所用菊花大抵只取白菊和黃菊。为什么?因为朱菊味苦,难以入口。吴昌硕是浙江安吉人,安吉地属湖州,湖州和与之相邻的桐乡市是著名的茶饮名品杭白菊的产地,当地人都喜欢冲饮杭白菊,吴昌硕当然知道并且能够辩识菊之能食与否。所以他绘菊花不会违例,图文之间不会矛盾。并且他做事上心,如果不明物性,他会设法品偿。
有例为证,他有一首取名《朱鞠》(鞠与菊通)的题画诗,诗前有小引:“《离骚》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余曾试之,惟黄白二种可以煮食,下酒甚佳。红者味苦如药,但供看耳。”(《缶庐别存》)
因为有这样的经验,乙卯年(1915年)夏天当王一亭作《菊石图》请吴昌硕题跋时,大约王一亭画上绘有朱菊(笔者未见原画,臆测而已),吴昌硕于是借题发挥,题曰:“朱鞠味苦腹难受,黄鞠落英香可口。此泉明未曾道及,而屈原先生果能辨之否?多事饶舌吴老缶。”(王中秀《王一亭年谱长编》)
题跋要与画相配,不仅要言之有物,更要言之有理,文要添趣,更要对题。题得这么妙,他却说自己“多事饶舌”,因为把陶渊明(泉明即陶渊明)、屈原都牵涉进来了。陶渊明咏菊千古一人,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知陶醉了多少人,但是陶渊明没有说菊是否可食,或者哪种菊可食,哪种菊不可食,这让吴昌硕抓了“辫子”。屈原也是,虽然《离骚》中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但他也没有说夕餐之菊是白菊还是黃菊抑或朱菊,所以吴昌硕“黠问”屈原“果能辩之否?”这当然是文人的幽默和情趣,把一则题跋写得有趣极了。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吴昌硕画上题跋的严谨,画什么,题什么,都有斟酌,不违物理。
这就是前面所说吴昌硕以六言小诗作补题题出的名堂,所谓图文并茂,这才叫图文并茂,怎么不让人耐读耐看呢?
2014年9月20日于西溪勤礼草堂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