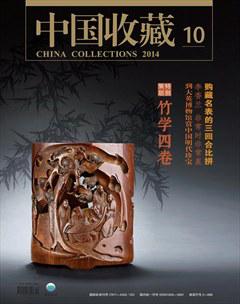话竹
假如没有人的赋予,没有人文精神的凝结。竹子,不过就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植物。人们对竹子的爱与升华,其实并非简单的情感与需要,细细琢磨,意味无穷。由此且来听听几位文化学者、艺术家畅聊心中之竹。
不可一日无此君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长山水文化、乐府诗歌等领域研究)
追溯起来,竹进入中国古代文学时间比较早了,古老的文献中就有记载,像《诗经》里面对竹子的歌咏,《汉赋》中也有关于竹子的赋。竹还可以作为乐器,有记载中提到,“黄帝使伶伦伐竹而作笛,吹之作凤鸣。”这位伶伦就是黄帝时代的乐官。再如我们常说的“丝竹”。由此可见,国人用竹、咏竹,已经有着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
文人对竹有特别的偏爱,这一时期主要是在魏晋。很多人或许想到了竹林七贤。当然,他们雅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竹林?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而最著名的例子是东晋时代的王羲之、王徽之,尤其是王徽之,他到任何地方,哪怕只住很短时间,都要栽上竹子,说“不可一日无此君”,“此君”由此就成为了竹的一个雅号。
有关王徽之爱竹的执着,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户人家的园林里栽种了竹子,王徽之经过时看到很感兴趣,便走进去看。由于他是名士,人家见了很高兴,热情招待他,但他也不怎么搭理对方,进门只为欣赏竹。王维有句诗——“看竹何须问主人”,说的就是这个典故。
魏晋的文人为何如此喜欢竹子?我想,竹主要生长在南方,如广东、湖南等地,在我的故乡浙江竹子也很常见。历史上西晋灭亡了以后,士族们到了南方,他们特别喜欢南方的山水风景,一草一木,自然,竹也作为其中的一种元素被喜爱并称颂着。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魏晋时期是庄园经济,这些士大夫都是庄园家,属于贵族阶层。而在南方,竹是主要经济植物,长得快,又有很多功用。从经济角度分析,竹园是一种财富象征。
上升到文化层面来看,东晋人这么迷恋竹,大概跟竹林七贤也有一定关系,他们是学坛名士,跟玄学有着密切关系。竹有节,且中空,这与玄学中清虚的意蕴不谋而合。清虚的“虚”字并非今人理解的虚心之意,清虚、玄虚、冲虚,这些都是玄学的重要概念。如果从思想来深究的话,竹提供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一些比兴的意义和一些联想。
魏晋文人崇尚玄学、崇尚自然,所谓风雅、风流就是自得,独立于自己,不太受外在的某种评价标准和规划的影响,从而达到一种美善的境界。这是他们一种基本的追求。超越于世俗之上,是那个时代的思潮,以后便作为中国文人一个基本的理想、思想的因子而积淀下来了。
文学中,其实唐代人并没有特别显示出对竹的爱好,比如王维的诗中竹只是作为一种环境。但宋代专门讲竹的作品很多。宋人特别讲究,与之离不开的概念就是士大夫、君子、雅,这些都是他们从魏晋人那里效仿并继承过来的。宋代人眼中,竹完全成为了君子的象征。而宋代以后对竹的人文精神基本上就是传承,内涵上没有新的发展。
当然,虽然竹的人文精神兴于魏晋,普及于宋代,但文化是有渊源的,魏晋崇尚自然的思想来自先秦,文化传承总是环环相扣,不能简单定论。
文化记忆带来温暖之感
吕德安(当代诗人、画家,崇尚自然生活)
我的故乡在福建,在当地郊区的一座山里我有一所小房子,算是属于自我的一方天地。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建造的,周围大片大片都是竹林,从远处看起来,俨然就是一幅出神入化的天然画作,青翠、静谧、安详;风拂过时似一大片翡翠的海洋,那么神秘莫测。而近观之下,竹是一种干净利索的植物,不由自主地就想要置身其中。
竹子的形象简练、高洁,有种独立、坚韧的东西在里面。长久以来,传统的诗意的教育使我们对竹子情有独钟,有种习惯性审美,比如竹为君子之说。其实,古代文人与自然界的接触远胜今人,在古代,无论是诗人还是画家,他们都崇尚自然生活。我认为概括地讲,古代文人艺术家与自然的接触,有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这种感觉被艺术强化,成为我们记忆中某种品质的象征。
关于竹子的艺术形象,无论是瘦或者肥,我觉得都好,只要适合每个人的创作状况或欣赏心理,明清人更喜欢瘦竹,不妨看成是当时的一种审美上的时尚化。从文人画中,我们看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他们对自然的一种记忆。在文人画里面,竹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植物被表达,被寄情,实际上是一种天人感应的精神的延续。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流传下来的竹画形象基本都是用水墨,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着深奥的文化精神。有关竹的中国画能延续至今,其他画种很难颠覆,这是因为水墨的元素最适合表达事物“朴素”的意境。当然,这种朴素不仅是趣味,更是一种对“返璞归真”的能力的追求。竹的形象,以水墨来反映恰到好处。所以,竹精神与笔墨的关系,如此思考起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今天聊竹,其实聊得更多是一种文化心理的传承。可能现代人与自然相亲近之说已经有所淡化。作为记忆中的一种元素,竹在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时候起到了特别媒介的作用,回想起来会发现,像这样的“竹子”曾经是先于我们经验的某种生活,既是一种文化记忆,能带来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甚至是我们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宗教”。
惠人之竹
胡西林(艺术鉴赏家、本刊专栏作家)
通常人们分别以一个字来概括梅兰竹菊的物性:傲、幽、坚、淡。竹子的“坚”性体现在四个字上,即虚心抱节。说到底是因为人性中有许多弱点。竹无意识,但有物性,这物性可以喻人性、塑人格,这是竹子最可贵也是最让人喜爱的品格。
历史上因为爱竹留下绝美诗篇和画作的倒是大有人在,现成的例子是人人皆知的成语“胸有成竹”的出典。苏东坡有个表兄叫文同,也就是文与可,他不仅诗写得好,画竹更出名,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指画竹叶) 绘竹法,在美术史上影响很大,追随者甚众,有“湖州竹派”之谓。他因为爱竹而画竹,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对竹的观察极为细致,到了了然于胸的程度。苏东坡在一篇文章中总结文与可画竹时第一个提出与可“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的观点,同时代另一位诗人晁补之也在他的一首诗中说“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这就是“胸有成竹”典故的由来。一个人因为爱竹而画竹,其画竹的成就又让人提炼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智慧,你看竹子多么惠人!
再说一个事例。明初有一位画家叫王绂,善画山水,尤其擅画墨竹,名气很大。王绂情怀高雅,秉性绝俗。一天他于月下隔船听到对岸有人吹箫,牵动雅怀,就趁兴画了一幅《石竹图》,第二天早晨他还寻访吹箫人并将画赠送给他。见面后知道吹箫人是一位商人,这让王绂有些失望。吹箫人当然喜欢王绂的画,他拿出红色毯子回赠并请王绂再画一幅以作配对。王绂不但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索还所赠《石竹图》当面撕毁,并退还红毯。这样的事例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理喻,但是在王绂的眼里,吹箫人未能免俗,并且贪婪,这与竹子不类,与《石竹图》不配,与那箫声给他的印象也不符合。这当然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事例,但是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古时候传统文人与竹相类的内心境界。苏东坡为什么“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就是因为“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而人瘦尚可肥,士俗则不可医!这事关人格,在古人的观念中不是小事。
竹既是文人咏物励志的常见题材,也是文人藉物尚艺(文)的常见载体。我们的先人在对竹子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单一停留在实用的层面上,而是加以审美,施以巧构,以无以伦比的艺术手法将历史故事、寓言传说和花鸟虫鱼等赋形其上,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比如这只一握大小的清代水滴,取材竹根尾节,柄、流(嘴)、盖纽通体借根须为饰,圈圈点点本为自然,却仿佛青铜器上的联珠纹,为水滴平添古朴之趣。试想,当古人拳握水滴往砚里注水,再把手研墨,那是何等的情趣!享用如此雅物,不写一手如意好字恐怕自己也过意不去。
至于竹子到底为何如此受中国文人青睐,我想是因为竹的物趣秉性,竹以物性喻人性,可以升华人伦,塑造人格。有谁见过竹制文房用品上雕饰春宫图的?就连一般格调不高的题材也很难见到,因为竹性高洁,让人去邪念添雅思,置于书房,物我观照,物我相携,所以备受文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