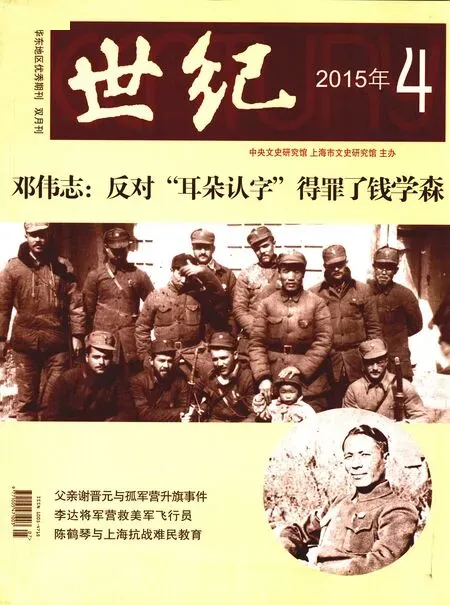陈鹤琴与上海抗战难民教育
陈一心
陈鹤琴与上海抗战难民教育
陈一心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不由回想起78年前淞沪抗战爆发,父亲陈鹤琴在担任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组负责人和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之际,利用他的声望和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推进难民教育的经历,以及他与在上海创建战时平民难民保护区——南市安全区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饶家驹神父的合作与友谊。
关于这段史实,赵朴初先生曾经写过一首诗,题为《茅屋济济教多士》,简洁而精练地概括了父亲陈鹤琴在上海孤岛时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亲自编写教材,开办难民教育学校,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设法营救进步人士等历史功绩。
艰难风雨忆畴昔,
茅屋济济教多士。
汉语拉丁新发硎,
抗战图强增利器。
口碑载颂满人寰,
手泽长垂富巨篇。
万里寻馨发兰桂,
应无遗憾到重泉。
一九八三年奉题鹤琴先生文集 赵朴初(钤印)
在上海国际救济会与饶家驹神父共克时艰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接连出动了百余架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闸北、南市火车站和大量工厂、民房被毁,数以千计的居民被炸死,熊熊大火延绵数里,满天红光,硝烟滚滚。那时候我还年幼,只有6岁。记得我们站在住家楼房(兆丰公园对面愚园路)的阳台上,亲眼目睹日机野蛮的大轰炸,机翼上涂有太阳旗的日机,疯狂地轮番向地面俯冲,隆隆的轰炸声震撼着大地,也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

1939年,为躲避敌人的跟踪,陈鹤琴蓄胡改装,继续从事抗日进步活动
此后数十万难民涌入租界,他们露宿街头,生活无着,无家可归。在上海各慈善团体的努力和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成立了大批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教育机构。
我父亲早年赴美留学,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回国后在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执教。1928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华人教育处,父亲从南京转赴上海,出任该处处长,负责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教育。在他任职期间,先后创办了工部局东区、北区、西区等6所小学(均附设幼儿园),1所女子中学,使华人儿童获得较多的受教育机会;在工人区开设职工夜校和简易小学,在上海和华东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1937年8月至11月,我父亲先后担任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组负责人和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开展难民教育和难童教育。
正是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父亲和当时的一些教育家,如知名人士刘湛恩等人,和同情中国人的外国友人一道积极投身难民收容工作。赵朴初先生曾回忆说,“陈鹤琴当时负责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他大力支持在收容所推行新文字运动。胶州路收容所几个教员被日寇指名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引渡,巡捕房把他们扣留了。我们通过陈鹤琴的关系,把他们保释出来”(《在陈鹤琴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北京教育通讯》,1992年第二期)。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1938年刊布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档案自民国廿六年八月十三日起,至廿七年二月十五日止,刊布会址: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三楼。报告内容包括成立经过、工作概况、难民教育、难民医院等八章。为中英文合刊。序言由上海领事团首席领事、挪威国驻沪总领事、上海国际救济会会长奥尔撰写。该报告第五章“难民教育”中,明确提出“本会教育工作属于本会行政之一部分,设置一教育组主持之,请由陈鹤琴先生为主任,办理所属六收容所之难民教育事宜,并请定视导员一人,专司教育视导工作。办事员一人,专司购办保管分发教育用品之职。关于行政方面由主任召集各所教育负责人员共同商讨解决,每两星期开会一次。本会所属六所教育,因环境及组织而异其设施”。
在这份历史档案中,还有一幅 “上海国际救济会组织系统”示意图,从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在上海创办了南市难民区的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负责人饶家驹,与担任难民教育组(又称难民教育委员会,实则是同一组织名称)主任的陈鹤琴,是同属一个“组织系统”,即上海国际救济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两个人其实还是真正的同事与国际友人的关系!
关于父亲和饶家驹神父在上海国际接济会的合作与友谊,有许多生动的事例和细节。
当时,在震旦大学操场上,芦席大棚搭成的难民营内,还设有一所难童的“国际中学”,约一百名学生分设两个班,陈鹤琴担任名誉校长。关于这所国际中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院顾问、《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难民》一书作者阮玛霞女士所提供的影像资料中,曾有过鲜活而生动的记录:学生们按照各自年龄分班之后,排着一队队的整齐的队伍,唱着歌曲,井然有序地走进教室学习。在另外一个影像资料的片断中,可以看到难民乐团的学生们在练习鼓乐,他们身穿长衫,一个个神情专注,训练有素。这些乐团的学生之中,有男生,亦有女生,年龄大约都是在十二三岁之间。针对当时的抗战形势,教师在难民教育中教难童唱抗日歌曲。当时的《申报》副刊上,有一篇署名冈沙的文章,题为《难民教育了我》,生动地叙述了一些难童学唱《大刀进行曲》的细节。

难民学校的女生与男生同班读书
此外,笔者又在上图的文献史料中了解到,由陈鹤琴领导的难民教育组还配置了难民乐团,并常常派难民乐团到饶家驹神父创建的南市难民区和其他区如沪西区的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救亡演出。如《战事画报》刊载的关于难民乐团演出的新闻报道,就曾经出现过14次。据图片显示,难民乐团1938年3月7日在南市难民区演出时,饶家驹神父还亲自观看,并与演员们合影。又如,同年3月19日的《战事画报》上,在刊载难民乐团演出新闻图片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上海国际救济会主办难民之乐团:南市难民区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之职员于各收容所之屋顶张悬红会旗帜以示区别。” “张悬红会旗帜”,表明难民乐团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所辖的一个演出团体,而陈鹤琴在当时担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
如何让难民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
“茅屋济济教多士”,这句诗所述的就是父亲在上海开展难民教育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在一个个大芦席棚里,难民们团团围坐着,他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父亲在当年的《红十字会月刊》上写道:“整千整万的人们,年老和年青的,男性的和女性的,疾病的和健康的,都挤在一起,据说有一万七千人齐集在那里,其中有一千多人集合在一个大礼堂,用心开始练习功课。”
父亲在抗战时期开展难民教育的初衷,是基于国家的前途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正如他在《上海的难民教育》一文的结语中所疾呼的——
最后我必须声明,现在难民的情形实在是为难民服务和谋幸福的良好机会。在人口密集的收容所里,整千整万的难民预备受教育。有了教育,这些儿童将长成为国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难民会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们。我们难道可以仅仅为他们预备充足的食物、衣服、住所、而让他们闲居终日,无所事事吗?要是那样,他们一离开了收容所,对于社会将有何等的危险!
我们想法给他们受些教育,受些简易的职业训练和公民的训导,使他们离开了收容所,可以从事社会上健全的活动,这难道不是很必需的吗?任何民主的国家,如果有一大部分人口在贫穷和无知中度日,决没有安全和繁荣的希望。所以难民的教育问题实在是一个当前的机会和迫切的挑战。
1938年初,父亲被推举为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任副主任,赵朴初、陈望道、陈选善、韦悫任委员,朱启銮为教育组组长,并聘请朱启銮、周克、丁瑜、杨昌镛、吴宝龄等5人组成巡视组,指导各收容所难民教育,扩大了难民教育的合法权利。他们在难民收容所的儿童和成人男女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和抗日教育。
总之,这些教育活动,使得难民中的儿童没有因为战火丧失受教育的机会,而一些成年人在经过扫盲教育与技术培训后,在战争结束后也更有能力适应新的生活。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通过查阅史料和实地考察为淞沪抗战后的难民教育提供了一个实证: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处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了两千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得到教育的难童约有三万人。除教授难童文化外,还注重品德教育,培养他们“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的精神。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立了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二百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起一个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除了文化知识学习外,还举办生产自救和技术培训,在16个收容所内组织了11种生产活动,如印刷、制袜、缝纫、编织、儿童玩具、木器等,这对节约救济经费、改善难民生活也起了积极作用。

陈鹤琴设计的徽章,用来奖励难胞们学习新文字,在他们学成结业时颁给
险遭特务暗杀
抗战时期上海的难民教育不仅注重教育和培养难民的谋生本领,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中共地下组织推动下,由陈鹤琴为首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在全市各区办起11所夜校,吸收工人、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夜校共办5期,有5000名学生参加,这是一支活跃在“孤岛”上的文化战斗队伍(凌集熙:《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载《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二辑,132页。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编辑,1983年6月出版)。
另,潘大成《关于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文亦云,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该所在组织难民参加劳动生产、对难民进行语文、算术与急救常识等基础知识的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国际救济会教育组负责人陈鹤琴的支持下,该所办了一至六年级小学、一年级的中学、无线电通讯训练班。该所地下党支部还以遣送难民回乡为名,把有的难民输送到浙东、苏北打游击,一部分从上海出发经过温州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争取国际救济会发给每人五元的路费。

陈鹤琴(右一)与刘湛恩(左一)在宜兴桥工学团踏勘时与该校农友等合影
据时任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副组长的杨昌镛先生撰文说,1938年上半年,中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交与他一个任务:在短期内在难童中挑选学员,筹办一个无线电报务人员训练班。杨昌镛即和难委党团领导朱启銮相商,由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掩护,征得难委领导成员丁瑜及吴宝龄两位收容所主任的支持,于1938年7月在宁波路川康实业银行内筹办了“电训班”,人数约50人。名义上是培养难童一技之长,谋取生活出路,其实是为中共革命根据地培养服务人员。电训班由于要求特殊,并未与后来的慈联中学合并,但编制是纳入慈联中学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训练,第一批15名能够熟练掌握收发报技术的学员,由刘少文、吴成方陆续送往新四军工作。嗣后又紧接着举办了第二期,“八办”派了电讯专家李绳铭担任技术教员,学员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前后两期训练班共培养约50余名学员,其中有38人被送往新四军工作。
由于父亲陈鹤琴及一大批爱国志士积极从事上述大量抗日救亡活动,遭到日寇和汪伪之忌恨,由此被列入暗杀名单。当时汪伪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76号特工总部”,专门从事对抗日进步人士的暗杀活动。1938年4月7日晨8时半,父亲的挚友、难民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携子出门,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公共汽车站候车去圆明园路学校时,突遭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即牺牲,年仅43岁。
刘湛恩先生被杀后,敌人的毒手伸向了父亲。当时父亲为了躲避敌人的跟踪,蓄起胡须,化装成商人的打扮,继续从事抗日进步活动。1939年10月26日他得到中共地下党和工部局警务处通知,立即秘密离沪去宁波隐蔽。1939年11月13日晚,汪伪特务持抢闯入我们家,企图行刺暗杀我父亲。当时,我们家在上海胶州路300弄17号,是一座小花园洋房,周围环境较清静。13日晚7时半左右,正当我们全家母亲和兄弟姐妹吃好晚饭时,突然有人敲门,一开门就冲进来3个男人,全部头戴西服帽,身着深黑色长大衣,每人手里都拿着手枪,为首的一个长着斜白眼,他把我们赶到厨房间,凶狠地叫嚷:“陈鹤琴在哪里?”并用手枪对着我们,母亲和我们说“不知道”。其他两人就手持手枪上楼对每间房间搜查,搜查无结果。为首的一个就用手枪柄将挂在客厅里父亲的大幅照片的玻璃打碎,将照片取下带走,然后在家门口用手枪连续打了3枪,3个特务才离开。第二天清晨,我们在家门口大理石的地板上拣到了3颗手枪子弹壳,我把它保存起来。我心里默默地想,这是日本鬼子和汪伪特务妄图杀害我父亲的铁的罪证,我要永记心头。我曾查阅过上海工部局警务处1939年11月13日的英文档案,其中有一份日寇资助的恐怖小组黑名单情报,其中就提到汪伪特务闯入陈鹤琴寓所(上海胶州路300弄17号)行刺的情报。
父亲逝世于1982年,他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如今我自己亦已步入耄耋之年。但是,父亲在抗战时期从事对难民教育的种种往事,如今回忆起来,依然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些遥远的往事,它是那么的温馨,烛照着后人,鼓舞着我们永远珍惜今天,面向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