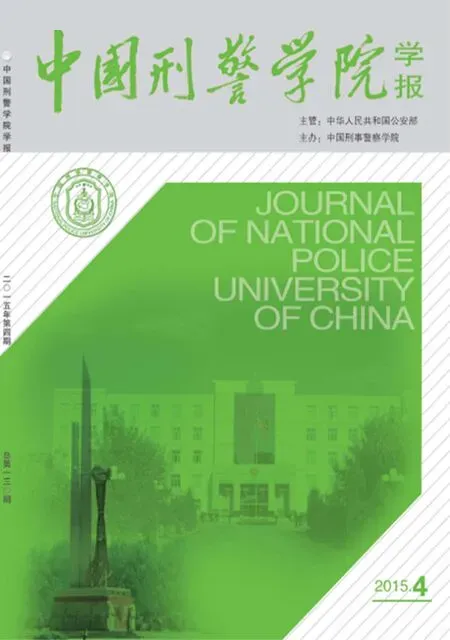人质危机中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解析
——基于警务谈判视角
于洋
(广东警官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30)
人质危机中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解析
——基于警务谈判视角
于洋
(广东警官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30)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效应在劫持人质、恐怖主义等众多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都曾对警方处置提出严峻挑战,有关其形成原因、作用机理、适用条件以及策略选择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从专业警务危机谈判视角出发,在实证性心理学解析的基础上提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在危机谈判中的正面作用与适应性策略,从而为危机谈判心理策略的专业化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危机谈判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心理解析
1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1973年8月23日,嫌疑人Janne Olsso手持自动步枪进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Sveriges Kreditbanken银行意欲抢劫。Olsson连开数枪并击伤1名警员,同时劫持了4名银行职员与警方对峙,经过谈判瑞典政府同意释放Olsson的狱友Clark Olofsson进入银行。经过长达近130小时的谈判,2名劫持者终于同意释放人质并向警方投降。事件和平解决,但走出银行的过程中4名人质却主动作为挡箭牌保护劫持者,并阻止警方进行拘捕。在后期的庭审中,4名人质均拒绝指控2名劫持者的犯罪行为。在2名劫持者服刑期间,人质之一的银行女职员Christian竟与劫持者Olofsson订婚。
人质与劫持者的过于良好关系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司法心理学界为之震惊。在近130小时的共处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人质可以“爱上”劫持者?经过实证性研究,瑞典犯罪心理学家Niles Bejerot将这种人质因受强大心理压力而引发情感导向倒置的表现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又称为“人质情节”效应。[1]研究表明人质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效应的过程中通常会经历如下阶段:
(1)极度恐惧:几乎极少有人具有作为人质的丰富经验,由此突如其来的危机使得没有任何经验的个体产生极大的心理冲击,理性思维通道严重受阻。
(2)害怕与认同:与劫持者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劫持者成为了人质唯一的信息来源。在交流中体会到对方的不得已行为,由此人质在并未受到实质性身体伤害的前提下,共同处于持续的困境当中使得劫持者与人质产生相互的认同与同情。
(3)提供帮助:基于认同和同情的基础,人质会给予劫持者无形的帮助,如配合劫持者、不逃脱、安抚劫持者等等,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劫持者产生心理依赖。
2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心理解析
对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产生原因的解释在学界从未中断,不同学科领域专家从生物学、犯罪学、遗传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见仁见智,给出诸多解释,如“人质被教化”理论、“犯罪本能激发”学说[2]等等。众多理论中以犯罪心理学家的实证性研究最具代表性与说服力,以下主要从心理学视角对于其原因进行解析。
2.1 危机环境中的认知偏差
劫持者挟持人质与警方对峙,由此在人质事件的处置过程中,人质——劫持者——警方三者间的复杂互动与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有利或不利的思想情绪会明显呈现于各方的表现中。警方作为事件处置的主体,力求控制事态发展并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将处置社会成本降至最低。但在处置过程中,人质的认知偏差甚至是误解可能会使其对警方产生不信任乃至埋怨,从而导致情感向另外一方(劫持者)倾斜以保障安全,进而认同劫持者而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以下通过情景案例加以阐述。
案例情景:劫持者提出需要车辆离开现场,拿到车辆后可以释放人质,自行驾车离开。
人质角度:这样的要求对于警方来说并非困难,警方应该尽快提供车辆,做好交换人质准备,人质由此对事件的解决抱有希望,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欲望。
警方考量:
(1)提供车辆会使得案件现场发生变化,外围控制难以在短时间内开展,现场容易失控;
(2)劫持者驾车行驶路线不确定,过程中可能会危及公共秩序与安全,造成更大危害;
(3)现场变化后事件管辖权全部发生转移,不同属地警方及多警种难于在短时间做好充分应对准备,如果劫持者不遵守释放人质的承诺,态势将更加严峻。
………
通过情景案例可以看出,在劫持者要求处理的过程中,警方并非可以很快地实现条件交换,甚至由于考虑角度与立场不同,如提供车辆等要求几乎很难获批,加之警方在现场无法与人质沟通与解释,容易造成误解。与此同时,从人质视角出发,在危机情形下的不安与焦虑状态中难于理性思考,可能会认为警方处置效率低下,不关心人质等等,从而导致对于警方的不信任而倾向于认同劫持者,从而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2.2 角色认同的心理防御机制
“心理防御机制”最早由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指出:“心理防御机制”在人格结构中属于自我的功能。当自我觉察到来自本我的冲动时,会产生一定的焦虑性负面情绪,自我调控机制同时会通过情绪管理进行干预,此过程通常称为心理的“自我防御机制”(Defense of Ego)。[3]
危机事件中的人质在遭遇极度恐惧、害怕以及惊吓等强大心理压力后,在潜意识中同样会激发心理防御机制的启动,通过有效的心理防御帮助主体减轻或免除精神压力,恢复心理平衡。特别是在与劫持者长期共处且缺乏外界信息支撑的情况下,人质的心理防御机制更大程度倾向于通过建立劫持者与人质的良好关系来维护主体安全。经过一定时间的共处与交流(语言、动作或眼神等),在劫持者并没有施害于人质的前提下,基于心理防御机制的扩散效应,双方甚至都会产生对于对方角色的认同:人质生命受到劫持者威胁,而劫持者也处于随时被警察攻击的生命危险当中,大家都处于困境之中难以自拔,且相互关系处于依赖状态,原本对立的立场寻找到交集,两者也会尝试体会对方困境乃至相互同情。由此,角色认同的心理防御机制会帮助人质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4]
美国F B I人质救援处谈判组(CIT)在长期的危机谈判实践中得出结论,当如下四项条件具备时,人质的心理防御机制更容易倾向对于劫持者的角色认同,由此促进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形成与作用发挥。
(1)人质处于全完地被控制状态,且经过安全评估逃脱是几乎不能的事情,会遭致更严重的危险后果甚至威胁生命安全。
(2)劫持者并无恶意严重伤害人质,在共处过程中会进行言语安抚或照顾人质的情绪,甚至会提供小恩惠给人质,让其感觉劫持者并非丧失人性的恶魔。
(3)劫持者能将人质与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绝,人质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都是劫持者所能控制、经挑选后所给予的,简言之,人质被劫持者导向。
(4)劫持者会让人质随时随刻都感到,除了顺从他、听他摆布、任他宰割,你无处可藏、无路可逃。[5]
2.3 危机情形下的群体意识再范畴化
人类对事物分类的心理过程即范畴化过程,其结果即认知范畴。群体意识的范畴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不断形成,如学生——老师,成人——小孩,好人——坏人等等。而在强大心理压力及极度恐惧心理状态之下,非理性的意识可能将群体意识再范畴化,从而导致分类乃至立场的改变。危机事件现场中劫持者与人质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劫持者深知,人质是其手中对抗警方的唯一筹码,人质生命被损害后,警方很有可能会诉诸武力解决;反之亦然,人质也非常清楚自身安全的控制权归属。这促使一种“我们”和“他们”的再范畴化区分,使得原本处于对立位置的人质与劫持者之间,因为共同的困境被再范畴化为“同质”群体。劫持者与人质所关注的共同问题都依赖于警方策略的实现效果。
再范畴化通常会导致角色的相互认同。当个体认为自己隶属于某一群体时,就会产生对于群体的自然认同。当人质将自身与劫持者感知为“我们”群体时,他不但会认同这一群体,而且对群体行为会产生怜悯甚至积极评价,而警方作为事件现场的封锁与控制者,会因拒绝允许处于困境者离开或难以满足其一定要求而遭致人质与劫持者的一致“对立”。由此,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候群进一步加强,使得人质甚至主动帮助劫持者、逃避警方的打击等等。
3 基于谈判视角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适用
3.1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正面效应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并非人质事件中的普遍现象。据美国F B I危机谈判数据库H O B A S系统显示,从1985年至2005年的近20年间发生的劫持人质案件中,大约23%左右会自觉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其中未成年人作为人质的案件中,最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其次是妇女。由此,选择利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还是尽可能避免使用,曾经一度使众多谈判人员困惑。而在全美人质事件频发的两大警察局——洛杉矶警察局(L A P D)以及纽约警察局(N Y D P)谈判小组的近两百分问卷显示,96%以上的谈判员认为促成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对于保障人质安全和事件的和平解决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并且此举在众多谈判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效。一定程度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警方可控范围内)可以有效保障人质生命安全,帮助谈判小组达成警方既定目标。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作为人质危机谈判中的双刃剑,警方应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
(1)安全需要。确保人质安全是警方在处置人质危机事件中的首要目标,通过一定方式促成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形成,在警方可控的范围内确保人质当下的安全同样是和平谈判的重要条件之一。作为事件重要当事人一方的人质,在全完被动受控情况下,积极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可以改善与劫持者关系,获得同情并且维持自身安全需要。事实上,这也是人质在危机状态下唯一能做的有利于事件和平解决的积极工作。
(2)回归人性需要。人质与劫持者长时间“近距离”共处,双方必定建立一定的关系。相对于紧张和敌对的关系而言,友善和相互理解的关系更有利于事件解决。警方谈判小组的目的正是期望利用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帮助劫持者回归人性,在良好的关系中感受人性关怀与体贴(如人质喂水给劫持者、相互帮助包扎伤口等等),从而选择放弃极端行为。
(3)理性思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良好共处,劫持者与人质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信任感,双方交流逐步开始。相对于向警方诉说不幸,劫持者通常会更倾向于向人质倾诉。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作用下的人质会成为劫持者忠实的聆听者,在帮助其宣泄的同时甚至可以给与对方建议,帮助其寻求理性思考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在一些案例中人质甚至愿意以自身力量与社会资源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方案来帮助劫持者(如经济困难、疾病困扰、情感矛盾等),而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产生之前,双方几乎不可能相互信任,更无法理性谈及如此深入的问题解决方案。
3.2 危机谈判中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适用
3.2.1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前提——中间人立场
在警务危机事件谈判的过程中,警方——劫持者——人质三方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每一方都依赖于对方而实现安全保障与条件的交换。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产生与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人质通常会将自身身份再范筹化而与劫持者处于相同立场,从而形成与警方的对立。此举虽在保障人质安全方面得到实现,但由于对立情绪与立场的产生,对于警方处置又无形中增加了难度。在实际操作中,通常会建议谈判专家以中间人身份介入(如图所示),谈判过程中采取中立立场,谈判员作为中间人介入谈判,不会被视为“他们”,又不会失去信任的主动。谈判中尽可能作为事件的斡旋人员来帮助劫持者与人质实现要求,从而在警方与劫持者间建立了一道“缓冲隔离区”,避免警方与劫持者直接的正面交锋,在缓解对方恐惧心理的前提下,使得劫持者与人质在相对理性的状态下与谈判专家共同商讨解决方案。[6]

3.2.2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形成——机会制造与策略设计
人质事件发生之初,包括劫持者、警方与人质在内的多方都处于紧张敏感的状态之中:劫持者狂躁而不信任警方;人质处于极度恐惧与压力之下甚至会生理失控。为了保障事件妥善解决,谈判专家应尽可能向劫持者与人质传递生存希望,传递和平解决问题的信号。过程中谈判专家可以有意创造一定程度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帮助人质与劫持者建立良好关系,引导人质面对现实,平复情绪而暂时听从劫持者的安排。此时人质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服从而保障生命安全,此举也有利于缓解劫持者的烦躁心情,有利于谈判专家与其展开对话。谈判过程中可以创造机会而促进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发挥作用:如送饭时采用“合餐”的方式(劫持者与人质共同进餐、增加沟通机会);鼓励人质关心和理解劫持者,如为其包扎伤口、喂水或传递物品等等。总而言之,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设计来帮助人质与劫持者建立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获取劫持者对于人质的怜悯和同情,从而确保其安全。
3.2.3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效应扩散——平衡性策略
经过谈判的初段介入,劫持者高涨的情绪得到缓和,人质逐步恢复理性思维,在谈判专家的策略设计过程中人质与劫持者也基本可以和平共处。此时,警方应采取平衡性策略进一步发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正面作用,从而保持这一良好关系的持续。
一方面,在与劫持者的对话中尽量避免过多谈及人质的状况(通常以关心人质的伤情或生命体征为主),以免使劫持者产生被冷落的感觉。谈判过程中也尽量避免使用“人质”等词语,可以直呼其名,从而人性化看待人质,而不是把人质当做劫持者的砝码,尽可能淡化事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有机会与人质对话,仍然尽可能传递和平解决的讯息,使人质对于生存希望充满信心。由于现实中谈判专家与人质的对话几乎很难避开劫持者的监控,谈话应避免谈及我方部署,切记策动人质的配合行动,谈话内容仍然鼓励人质努力关心劫持者,尊重劫持者的独立人格,理解其迫不得已的难处,使得劫持者在关怀与理解中恢复理性,尝试思考警方的解决方案。[7]
3.2.4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效应的延伸——非零和博弈
在危机谈判进入到后期的实质性磋商与问题解决阶段,基于前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作用,谈判专家可以通过继续维护三方的良好关系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方案,帮助劫持者与人质摆脱现实困境。
危机事件现场,劫持者与人质关注自身命运与安全,而警方同样面对工作职责与社会公众压力,劫持者——人质——警方三方同时处于危机事件的困境中难以自拔,警方可以继续借助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所产生的相互信任,将劫持者与人质均视为共同的“问题解决者”,将三方当事者同时纳入到问题解决的框架之内,共同商讨符合各方利益与要求的平衡性解决方案,而不是非输即赢的零和博弈。在外在表现方式中,尽可能多地尊重和听取劫持者的意见(如投降的方、接收人质的具体步骤等),甚至让劫持者感受到是自己更加主动地做出的决定,而非警方强加的意愿。事实上,也正是三方的不懈努力与良好合作才可以使得现场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尽可能减低伤亡可能性与社会成本。本质上讲,和平化解的结果也是最符合三方利益的终极目标。
[1]Gregory M.Vecchi,Vincent B.Van Hasselt,Stephen J.Romano.Crisis(hostage)Negotiation:CurrentStrategiesand Issues in High-risk Conflict Resolution[J].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05(7):67-70.
[2]John G.Waclawsky.The System Standards Stockholm Syndrome[J].FBILaw Enforcement Bulletin,2010(4):23-28.
[[3]Namnyak N.Tufton.Stockholm Syndrome:Psychiatric Diagnosisor Urban M yth[J].Act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2008(3):57-59.
[4]A Grubb.Modern Day Hostage(crisis)Negotiation:The Evolution of an Art Form w ithin the Policing Arena[J].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10
[5]Arthur A.Slatkin.Communication in Crisisand Hostage Negotiations.PracticalCommunication Techniques,Strategies,and Strategies for Law Enforcement,Corrections and Emergency Service Personnel in Managing Critical Incidents[J].Aggression and ViolentBehavior,2005(2):31-38.
[6]高明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表现、成因和应对[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43-147.
[7]张明刚,何睿,于洋.危机谈判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郭 帅)
D 918
A
2095-7939(2015)04-0011-04
2015-04-1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3C F X 041);公安部理论与软科学课题(编号:2012L L Y J G D S T 048)。
于洋(1981—),男,辽宁沈阳人,广东警官学院警务指挥战术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危机谈判、危机管理与警务战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