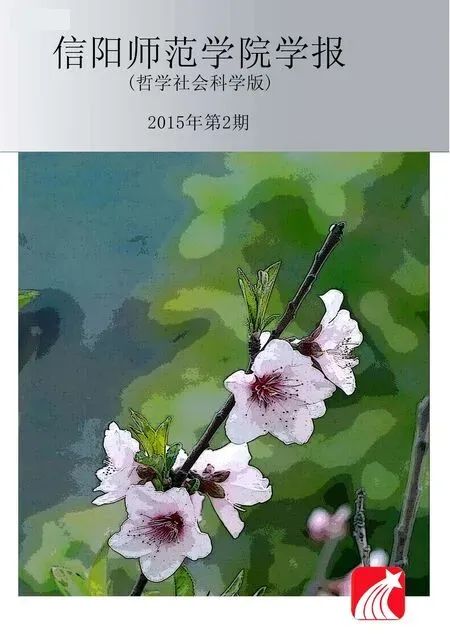戏剧艺术视野下的鲁迅小说概论
孙淑芳
(云南师范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专题研究:鲁迅小说修辞研究·
戏剧艺术视野下的鲁迅小说概论
孙淑芳
(云南师范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鲁迅在创作小说之外,还以多种方式进行了戏剧艺术活动。丰富的戏剧艺术素养使善于“拿来”创新和具有融会贯通艺术悟性的鲁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这方面的艺术感受融入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从戏剧这一非小说艺术的视角来阐释、解读、研究鲁迅小说,可以透视鲁迅小说对戏剧艺术卓有成效吸收的特点和主体原因,能够更全面地认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所具有的超强的吸收能力和创造能力。
鲁迅;鲁迅小说;戏剧;跨艺术;审美效果
在鲁迅研究的众多方法中,跨艺术研究方法的运用基本上还处于萌芽阶段。就鲁迅小说而言,跨艺术研究显然是在传统的鲁迅小说研究(就小说研究小说)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本文将从鲁迅小说的人物、语言、结构、艺术手法、精神等方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鲁迅小说与戏剧的关系,并运用“语言艺术规范—戏剧艺术效果”的研究模式,深入探讨作为现代语言艺术典范的鲁迅小说的独特面貌和杰出价值,并追踪鲁迅小说巨大思想容量和艺术感染力的“别种艺术”的根源。
一、鲁迅与戏剧的关系及其戏剧艺术素养
作为一名具有超强吸收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艺术大师的鲁迅,在创作小说之外,还以多种方式进行了戏剧艺术活动。从鲁迅的有关戏剧方面的著述来看,鲁迅所从事的戏剧活动主要包括观看戏剧演出、翻译介绍外国戏剧、开展戏剧批评、购买戏剧书籍、进行戏剧研究等。
(一)观看戏剧演出
鲁迅的戏剧艺术素养除了与他所受的西方教育有关,也与他生活环境中的戏剧氛围分不开。鲁迅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浙江绍兴度过的,家乡绍兴自古即发达的戏剧给了鲁迅沁入骨髓的文化熏染。绍兴每年都会定期举办“迎神赛会”“社戏”,还经常上演“大戏”和“目连戏”等,这些都给鲁迅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从绍兴走出后,鲁迅仍然处于戏剧的环境之中。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去看歌舞伎,其鬼戏中的角色、情节与中国的戏剧极为类似。1912年鲁迅到北京任职,据教育部官制,鲁迅所在社会教育司司掌范围有“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因此他经常有机会考查新剧,即早期现代话剧,在其日记中就明确记录了15次观看新剧。另外,由于鲁迅在北京的一些大学里任教,所以学生演剧也常邀请鲁迅观看指导。这种戏剧生活环境在其作品中也时常映射出来,《弟兄》中的寓客会深夜唱着京剧《失街亭》——“先帝爷,在白帝城……”回归寓所。《幸福的家庭》里假想这一幸福家庭主人所爱看的书是英国王尔德著的四幕剧《理想之良人》。
生活在戏剧环境中的鲁迅,一生中到底看过多少戏剧是无法精确统计的,但从鲁迅1912—1936年的日记来看,有关观看戏剧记载的共24次;至于青少年时期在家乡所看的戏虽没有明确记录,但根据鲁迅饱含深情而生动细致叙写家乡戏的专章,如从《社戏》《女吊》《无常》《五猖会》来看,家乡戏已经构成了鲁迅民间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除了看过中国旧戏外,也看过中国新剧和外国戏剧。对于京剧的观看记载有2次。鲁迅观看京剧的次数确实稀少,但他对京剧的批判却最多,这其中的原因后面再进行探讨。鲁迅离开绍兴后主要观看的是新剧和外国戏剧,日记中所记鲁迅看的最后一场戏是:1935年11月3日在上海“夜同广平往金城大戏院观演《钦差大臣》”[1]560。
由以上述略可见,尽管时断时续,鲁迅的一生始终近距离观看各种戏剧,这就使鲁迅对中国的戏剧现实情形一直有着颇为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对于广义戏剧中的三大类:话剧、歌剧、戏曲,鲁迅均观看过。就歌剧而言,鲁迅不仅在北京看过外国的歌剧,“我到第一舞台看俄国的歌剧,是四日的夜间,是开演的第二日”[2]403,而且在上海看过中国的歌剧,“饭毕同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1]40,观看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演出的歌剧《大葡萄仙子》《万花仙子》。可以说鲁迅对戏剧的内容和形式从整体上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
(二)翻译介绍外国戏剧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有意识地将寻求救治中国旧戏的良方转向国外戏剧的翻译和介绍,以期改革在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旧戏的审美规范,但鲁迅十分注重剧作的思想内容。鲁迅的外国戏剧译著有两部:一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戏曲——《一个青年的梦》;二是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鲁迅校订过的外国戏剧译著也有两部:一部是俄国安特来夫(安德烈夫)的戏曲著作,李霁野译的《黑假面人》;另一部是苏联卢那卡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戏曲著作,柔石译的《浮士德与城》。俄国安德烈夫的剧本鲁迅推荐的还有两部:《往星中》和《人的一生》。关于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其他剧作,鲁迅不仅翻译了《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其中的一幕,而且为这一剧本的中译本写了“后记”,“庆幸”此剧作的出版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3]425。鲁迅介绍的外国戏剧家除以上提到的外,还有易卜生、罗曼·罗兰、果戈理、萧伯纳。鲁迅不仅亲自翻译外国戏剧,而且十分重视介绍他人关于外国剧本的译作与国内的剧作,为它们尽力提供广泛传播的平台。
(三)开展戏剧批评
鲁迅的戏剧著述中主要是戏剧批评,有专章也有散论。对于中国传统旧戏,鲁迅都用了比较多的专章进行评述,但对少时所看的家乡戏往往是不由自主地情溢笔端,而对京剧则是毫不留情地加以讽刺和批判。对于从西方引进但发展尚未成熟的中国话剧,鲁迅虽然保持缄默,基本上不发表意见,实则抱以宽容、支持并寄予厚望的心态。
对于在绍兴所看的旧戏,鲁迅每每回忆起来总是充满了深情的回顾。鲁迅在他的三篇文章中向读者展示了家乡戏里所塑造的三种人物形象,描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评论中流露出肯定和赞美。具有人情味的“无常”,敢于复仇的“女吊”,极富讽刺力量的“二丑”,是鲁迅记忆最为深刻也最为喜爱的绍兴戏中的三种形象,这三种形象寄寓了绍兴人民的地域文化精神。鲁迅对家乡戏的情有独钟,从他专章叙写观看绍兴民间戏剧的演出情景,如从《社戏》《五猖会》和一些散论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充满乡野气息,轻松自由。二是戏剧表演的民众性、娱乐性。鲁迅对家乡戏记忆之深刻直接影响到了他以后的研究和创作。他在《朝花夕拾·后记》中记载了自己在研究全国各地关于“无常”画像时,家乡戏中的“无常”印象对他学术研究定势思维的影响。鲁迅生活在一个戏剧的环境中,每天都有戏剧在上演,他小说中的人物也如此。鲁迅常将家乡戏写入其小说作品中,作为小说的背景或人物活动的场景。
鲁迅对于京剧的批判,将矛头直指当时中国京剧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梅兰芳。对梅兰芳的批判并非对其个人的批判,而是对其所代表的整个京剧艺术的批判。在鲁迅看来,京剧不仅成为当时唯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髓而四处巡演,而且成为唯一能上得台面用来招待外宾的大餐。在《坟·论照相之类》《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且介亭杂文·脸谱臆测》等文中,鲁迅专门发表了对京剧艺术及梅兰芳的评论。鲁迅对京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男人扮女人;第二是“雅”而不“俗”;第三是脸谱属于象征艺术;第四是剧场环境的拥挤和嘈杂。鲁迅对京剧作为国粹根深蒂固于国民的心里十分愤慨,他认为京剧艺术几乎就是变态的艺术,违反人性、违反自然的艺术,是毫无美感、毫无活力的艺术。
鲁迅对中国话剧批评虽说极少,但并不是没有。鲁迅在《日记·壬子日记》中记录了1912年6月11日前往天津考察新剧,对所观剧目的评价:“夜仍至广和楼观新剧,仅一出,曰《江北水灾记》,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4]5鲁迅对这一新剧简要的评价可以说是切中了当时的话剧问题要害。然而鲁迅对由西方引进但发展尚不成熟的中国话剧,特别是学生演剧,总的来说还是持较宽容的态度,基本上对剧的演艺不发表意见。
(四)购买戏剧书籍、进行戏剧研究
鲁迅在其日记记录购买的书中也有一些戏剧书籍,鲁迅购买的戏剧书籍涵盖古今中外,种类样式比较齐全。不管这些书籍鲁迅是否都阅读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这些书籍是了解的。它们对鲁迅戏剧理论与知识的丰富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谈起鲁迅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知道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在其全集中也散见其对戏剧进行的严谨细致的研究。鲁迅阅览胡适所作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后,与之探讨有关戏曲书中《西游》的一些问题并给了胡适有关方面的意见。鲁迅还收集了全国各地有“无常”画像的书籍,仔细研究了这些画像,发现与小时候所见书中和戏中印象深刻的“无常”形象并不相同。鲁迅有关戏剧方面的研究不限于此,但都体现了鲁迅一贯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特别是对于戏剧的研究,他更是慎而又慎,“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5]407。
通过以上对鲁迅所从事的与戏剧相关活动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与戏剧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鲁迅生活中有戏剧,作品中同样有戏剧,他不仅生活在戏剧的环境中,而且他的作品中也时时展现出戏剧的生活背景来;鲁迅了解戏剧、关心戏剧,他还对戏剧的发展和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鲁迅对不同形式的戏剧褒贬不一,其实这种态度蕴含着他独特的戏剧价值观,也渗透着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丰富的戏剧艺术素养使善于“拿来”创新和具有融会贯通艺术悟性的鲁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这方面的艺术感受融入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从而使小说具有戏剧艺术的审美效果。
二、鲁迅小说与戏剧艺术的关系
鲁迅与戏剧的关系,是探讨鲁迅小说与戏剧关系的主体性参照,也是探讨鲁迅思想与艺术修养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语言艺术的规范与戏剧艺术的规范”及“语言艺术的规范与戏剧艺术的效果”两个模式,根据两种艺术相同或相似的美学效果,综合地探讨鲁迅小说与戏剧的关系。本文将从鲁迅小说的人物、语言、结构、艺术手法、精神等方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鲁迅小说与戏剧的关系,寻索戏剧艺术为鲁迅小说所增加的新的特质和美学品格,由此透视鲁迅小说对戏剧艺术进行卓有成效地吸收的特点和主体原因,更全面地认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所具有的超强的吸收能力和创造能力。在研究视角上,为鲁迅小说的研究另辟蹊径,从一个新的视角,即“非小说”的视角来诠释鲁迅小说。
(一)鲁迅小说的精神、人物与戏剧的关系
首先,鲁迅小说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启蒙、反封建、改造国民性及立人。这些思想的来源虽然十分广泛,但与戏剧也有不可忽视的关系,如家乡戏剧中所表现的“报仇雪恨”的精神,易卜生戏剧的个性意识等等,都是鲁迅小说深邃思想的重要来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与价值。堪称鲁迅精神土壤的家乡目连戏中的“目连”形象,深刻地影响了鲁迅。鲁迅将目连所具有的强烈负罪意识与执着救赎意念等精神营养灌注到自己的思想中,带入他的小说中,实践着他作为现代目连献身于民族的艰难救赎。基于这些精神,我们“要把鲁迅的作品看成是鲁迅生命的表达,因此要从生命体验出发去理解鲁迅的作品”[6]。目连戏同时也包蕴着对人性价值的张扬与呼唤,“无常”与“女吊”这两个颇具特色的“鬼”均散发着人性的光辉,“无常”的理而情、鬼而人,“女吊”强健的魂魄与勇于反抗复仇的精神都为鲁迅所激赏。而在鲁迅小说中,则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美好人性的缺失,以及鲁迅逼视黑暗历史的复仇精神。除了绍兴地方戏之外,鲁迅所译介的外国戏剧也给予了他丰富的精神营养:博爱平等的大爱胸襟,安特来夫式的阴冷,叫喊与破坏的反抗精神,爱恨两极的融合——无所不爱,不得所爱的悲哀,这些都渗透在鲁迅小说的思想与精神中。
其次,鲁迅小说的人物与戏剧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关系,一种是间接关系。
(1)鲁迅小说的人物与戏剧的直接关系大致有四种方式:看、唱、演、谈,由此也构成了四类角色,即看戏者、唱戏者、演戏者和谈戏者。看戏者当首推《社戏》中的“我”。鲁迅在《社戏》中以第一人称“我”回忆了自己作为成人和少年参与看戏的亲身体验,描写了在北京剧场观看京剧表演和在赵庄野外观看社戏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戏场景,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城市和乡村两大看戏群体形象。在鲁迅小说中,最喜欢唱戏的人物当属《阿Q正传》中的阿Q。阿Q总喜欢在不同的场合甚至自己不同的心境中唱戏,他经常唱的戏主要有两出,一出是《小孤孀上坟》,另一出是《龙虎斗》。除了阿Q之外,唱戏者还有《明天》中几乎夜夜在咸亨酒店边喝酒边唱曲至近天亮的老拱们,他们在单四嫂子失去宝儿这一夜终于朦朦胧胧睡去后,踉跄地走出酒店唱起《小孤孀上坟》;《弟兄》中经常夜晚去“看戏”、深更半夜才回来的寓客,在张沛君胡思乱想弟弟的后事时,吟唱的正是京剧《失街亭》。鲁迅在《阿Q正传》中将阿Q因为小D谋了他的饭碗使自己肚子挨饿,而与小D上演的生死决斗称为“龙虎斗”。《伤逝》中的涓生两次在决定子君命运的关键时候,对子君谈论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及其作品。鲁迅在小说中所提及的这些戏剧细节,绝非是内容上的凑巧之事、随意之笔。众所周知,鲁迅的文章向来惜字如金,讲究精粹和浓缩,正像杨义评价的那样:鲁迅小说“所提供的生活细节是经过高度的挑选和洗炼的,笔墨凝练,暗示性很强”[7]6。
这些人物与戏剧的联系方式虽然不同,其角色虽然各异,但鲁迅都别具匠心地通过他们与戏剧的关系灌注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形成了厚重而峭拔的思想与艺术的意义。与人物密切相关的一些戏剧因素,在小说中有时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而已,表面上看似是作者的无意提及,但是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深化主题思想上却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减轻了艺术的负荷。这些戏剧因素不仅紧扣人物的身份、处境,而且还直呈人物的心理、思想与情感倾向,从而使戏剧的原初含义与经过现实语境过滤后的新的含义形成巨大的张力,构筑了小说更为丰厚的艺术意味,生动而深刻地完成了对人物的立体、多面的塑造。
(2)鲁迅小说人物与戏剧的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鲁迅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上。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以其鲜明的个性、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丰富了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鲁迅对戏剧艺术手段的借鉴。鲁迅将矛盾冲突这一戏剧典型手法巧妙地融入人物的塑造中,大大丰富了小说自身的表现力。但是鲁迅更注重人物内在的戏剧性,他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给予了从未有过的、充分的关注。这就摒弃了传统戏剧和传统小说长于利用人物的外部关系制造尖锐紧张的冲突的做法,冲突基本上不从正面展现,常常表现出一种潜在的戏剧性。鲁迅通过借鉴戏剧艺术手段,设置人物之间矛盾对立的关系,凸显人物思想逻辑的非正常性与荒谬性,运用“突转”和“讽刺性对照”揭示人物命运等,充分表现人物的内在矛盾冲突及人物深层的精神世界,并在戏剧性的冲突中自然天成地揭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展示人物普遍处境的戏剧性。戏剧性艺术手段的运用,使鲁迅小说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获得极大的审美愉悦。
鲁迅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这与戏剧在人物关系设置上的原则是一致的。“人物关系”被公认为是戏剧中最有活力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徐闻莺、荣广润在《戏剧情境论》中认为:“剧本所设置的各种人物关系应该含有不平衡、不调合、不相容、不相称的矛盾因素,乃至尖锐对立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一条件,人物关系堆砌得再多,设想得再新鲜,也是无法构成真正的戏剧情境的”[8]186。鲁迅十分注重小说中人物戏剧性关系的设置,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人物的思想性格才能更加鲜明、突出地展现出来。在《呐喊》《彷徨》中,人物矛盾对立的关系具体可以分为:个人与群体的矛盾关系,个体与群体的矛盾关系,这两者均为不对等、不平衡的特殊关系。鲁迅将个人、个体与群体置于矛盾对立的关系中,方显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可怕的毁灭性力量。集体意识容不下个人意识,集体容不下不与之共谋的个人,也容不下脱离整体的个体。在这样的矛盾对立关系中,更可见觉醒知识分子悲愤无奈的复杂内心世界和自身行动意志的局限性,也才更显个体命运的可悲。这种人物矛盾对立关系的设置最能凸显鲁迅小说的悲剧性,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鲁迅小说中人物的思想逻辑常常陷入悖论。除了《故事新编》里像墨子、大禹等正面人物和《呐喊》《彷徨》中极少数觉醒知识分子的思想逻辑正常外,其余大多数人的思想逻辑都非常荒谬可笑,具有矛盾性、冲突性。美国学者道森曾经颇有洞见地指出:“戏剧家的大多数人物的创造在本质上都是反讽的。”[9]76而鲁迅小说中人物思想逻辑的非正常性与荒谬性,同样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反讽效果。人物思想逻辑的戏剧性,关键在于人物思想的偏执:四铭老爷总想引出孝女的故事;爱姑总想从封建统治阶级那里讨个说法;孔乙己总不肯脱下长衫;九斤老太总觉得今不如昔;等等。人物的偏执,从主题思想上来说,实际上是人物心理病态的反映,是社会病态现状的折射,意味着人物思维逻辑必然的非正常;从艺术手法上来讲,是为了使人物的思想与矛盾对立的一方具有不相容、不调和、不平衡的强度。戏剧中关于人物的选择,就像美国戏剧家L·埃格里所说的那样:“软弱无力的人物无法承负长时间的冲突。这种人物撑不起一出戏,因此我们不能让他们充当主角。没有竞争就没有游戏。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没有对位就没有和声。戏剧家不仅需要为信念而奋斗的人物,而且需要既有力量又有耐心把这场斗争推向结局的人物。”[8]376
鲁迅小说充溢着执于人物命运的热情,人物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命运感,仿佛有鬼似的,冥冥之中已有定数,并且人物的命运常常瞬间逆转。可以说,人物的命运几乎是突转式的,短时间内前后形成鲜明的反差,构成强烈的讽刺性对照。鲁迅小说对于人的命运的揭示正是运用了“突转”和“讽刺对照”这两种最富于戏剧性的戏剧技巧,才使人物的命运极具戏剧性,从而产生吃惊的戏剧效果,带给人心灵上极大的震撼,并使人能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深入反思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命运。鲁迅小说中人物生存状态及命运的戏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抗——失败,希望——失望,人性——奴性,救人——治死,梦境——现实。戏剧性的突转和讽刺性对照增强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也更强烈地触动了读者的心灵,引人深思。
鲁迅将戏剧性巧妙地融入小说的叙事艺术当中,大大丰富了小说自身的表现力。鲁迅小说中所包含的更强烈的感情,及其对读者所产生的更快更直接的感染力,是中国传统小说所不能及的。
(二)鲁迅小说的艺术与戏剧艺术的关系
鲁迅小说的艺术与戏剧艺术的关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鲁迅小说的叙事时间与戏剧的叙事时间
鲁迅小说对故事时间的巧妙安排,体现了鲁迅崭新的时间观念和深刻的思想意义,并产生了类似戏剧艺术的魅力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鲁迅小说的叙述时距与戏剧的演述时距。鲁迅小说以场景与省略交替的戏剧化节奏改变了小说的常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追求客观、直观、写实的审美理想。戏剧总是在固定空间与固定时间中表演的,这就要求戏剧的叙事与表演必须时距高度集中,这是戏剧演述的特点,而鲁迅小说的叙事时距正有戏剧的这种特点。那些故事时间很短的小说姑且不谈,即使是故事时间跨度很长的小说,如《故乡》,其叙事的时间也很集中。鲁迅小说能在很短的篇幅中包容丰富的内容,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借鉴戏剧艺术的叙事经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二是鲁迅小说的叙述时态与戏剧的表演时态。鲁迅小说采用现在时的基本时态所表现出来的戏剧艺术特性,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在叙事时态功能上的观念。戏剧作为表演的艺术,其时态一般是现在时。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突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构了与戏剧一样以“现在”为核心的叙事时间体系,其基本的方式就是将过去、未来一起纳入现在中展开叙事,如《祝福》,其价值取向与情感态度也始终具有现在性。三是鲁迅小说的叙述频率与戏剧的叙述频率。从叙述频率来看,重复叙述无疑堪称鲁迅小说叙事上的显著特色。鲁迅小说中的重复现象包括:词汇、句段、道具、人物的重复,场景的重复,情节事件的重复,情节首尾之处的重复(封套)。鲁迅小说对重复叙述的普遍运用使其获得了与戏剧在结构上喜用重复手法所创造的相似的审美效果,不仅使小说的结构更为紧凑整饬,人物形象更为鲜活典型,而且使主题更为集中鲜明,效果也更迅速强烈。但是,鲁迅小说中多次叙述发生一次事件的重复叙述和异质重复则超越了戏剧中重复手法的功能,表现出自身特殊的艺术效果。对鲁迅小说而言,重复叙述不只是形式结构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其思想上的含金量。鲁迅小说的主题意蕴就是在这些重复的痕迹中不断地得到丰富、深化、升华[10]。
2.鲁迅小说的双重情节结构与戏剧的内外结构
鲁迅小说中情节结构的设置十分巧妙,分为外部情节结构和内部情节结构,这与西方戏剧的内外结构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效果是相似的。戏剧内外结构的功能侧重不同,外结构重在组织情节、安排场面;内结构重在创设主题立意。戏剧结构在时空高度集中原则的限制下,要想尽可能地扩大时空与生活的容量并深入开掘主题意义,就要用虚实结合的原则处理时间与空间。戏剧结构的“实”体现的是戏剧的“整一性”,而戏剧结构的“虚”则对主题意蕴的深化起着重大的作用,它能使戏剧突破狭窄的时空和封闭的结构,获得更为广阔的内涵。也就是说,戏剧的外结构和“实”的一面是受到演出时空限制的,而戏剧的内结构和“虚”的一面却与整个生活相沟通。
鲁迅小说外部情节结构具有西方戏剧“三一律”的特征:时间、地点、情节统一,也具有“三一律”结构所形成的审美效果:线索清晰、表达凝练、故事整一。这正是鲁迅小说“短小精悍”的艺术魅力之一。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是直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可感的,根据场景的组构顺序可以明确完整地概括出情节发展的脉络。从形式上来看,它是有始有终、时空狭小、首尾呼应的封闭结构;从内容上看,它是单纯明朗、转换迅速、富于戏剧性的完整故事。就外部情节结构而言,鲁迅小说与戏剧一样都是戴着镣铐舞蹈,而最终使其破茧化蝶的就在于鲁迅别具匠心的内部情节结构的设置,它使小说的主题立意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寄予了作者的热切期望。鲁迅小说的内在结构个性鲜明,内蕴的展开匠心独运,但也与戏剧的内在结构一样,具有主题、情境、意象创设的开放性特征,如《药》《非攻》等。鲁迅小说的内部情节结构是不完整的、缺少变化的,其结果是不明确的,其存在的时空是相当阔大的。这一似乎很难把握的情节结构则承载着鲁迅小说的深层意蕴。在鲁迅小说中,内外情节结构的关系是交叉并存,互为包含的,内部情节结构以外部情节结构为存在的形式,外部情节结构靠内部情节结构彰显内蕴。内部情节结构的阔大时空使小说突破了外部情节线的封闭结构昭示着小说的深层意蕴,外部情节线的封闭结构正是内部情节线的原因。外部情节结构与内部情节结构的有机统一,赋予了鲁迅小说多样的神采与无穷的魅力,这一独具匠心的结构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结构的重大突破。
3.鲁迅小说的表现手法与戏剧的艺术手法
鲁迅小说在表现手法上对戏剧艺术的借鉴,主要体现在鲁迅小说的“无背景”方法与鲁迅小说的“油滑”手法两个方面。一是鲁迅小说背景的简单化与中国戏曲空台艺术的关系。鲁迅自觉地借鉴了戏曲背景的虚拟手法,不仅使小说背景简洁传神,富于写意性,而且充分发挥着表演的效能。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说,他小说的背景设置与中国旧戏的背景设置一样,都崇尚“虚空”。这种追求,使鲁迅小说与中国戏剧一样,常常不去大段地描绘风月,而注重构造象征性的环境,特别是具有精神内容的文化环境,形成意味丰厚的审美效果。在小说背景的展现上,鲁迅积极借鉴了中国戏曲背景的表现方法,均采取了动态的展现。鲁迅的小说有时也会写自然环境,但这些自然环境要么是精神化了的象征环境,如《狂人日记》中的“月夜”;要么是渗透了某种文化内涵的社会化了的环境,如《风波》中的“农家乐”。并且,对于这些精神化与社会化了的环境,鲁迅很少静态描绘,而是像戏剧一样,通过人物的活动等进行动态的展示,并在展示的过程中完成对人物心理、性格的揭示及思想主题的表达,这在其现代小说与历史小说中均是如此。
二是鲁迅小说中的“油滑”手法与戏剧的关系。鲁迅小说的“油滑”手法,固然得益于鲁迅多方面的艺术素养,但从直接的关系来说,则是鲁迅借鉴戏剧特别是民间戏剧审美特征的成功尝试。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1)“油滑”与中国戏剧中丑角的关系。鲁迅在《二丑艺术》《大观园的人才》等文中曾多次谈到戏剧中的“丑角”,丑角的基本特征就是油滑。如果将鲁迅首次使用“油滑”手法塑造的《补天》中的“古衣冠的小丈夫”与戏剧中的丑角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所使用的艺术手法及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十分类似的,都是以滑稽姿态对现实进行揭露和讽刺。(2)“油滑”与戏剧的间离效果。首先,鲁迅小说常常像戏剧一样运用喜剧人物形成间离效果,其基本方式是让古人说今话,在“古”与“今”的跨越中形成间离效果;其次,鲁迅小说也常常通过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戏剧化关系构成间离效果。
4.鲁迅小说的语言与戏剧的关系
鲁迅小说的语言与戏剧关系密切而多元。
(1)人物话语的动作性。从戏剧艺术审美来看,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话语明显地体现出戏剧话语的审美特点——不仅显示人物的性格,而且具有很直观的动作性。具体表现在人物“自然”对话的动作性和个人独白的动作性两个方面。首先,人物“自然”对话的动作性。戏剧,尤其是话剧中人物的对话与小说中人物对话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具有动作性,鲁迅小说人物的对话多具有话剧人物对话的动作性,如《长明灯》《奔月》等,这些具有动作性的对话具有两个作用,一是在动态中揭示人物的性格并进而揭示人物的精神特征;一是展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意志冲突与内心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凸显主题的意义。其次,个人独白的动作性。在鲁迅小说中,人物的独白被发挥到了极致,一篇小说甚至就是由一个人的独白所构成的。鲁迅小说中的个人独白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内心独白,无假设听众,如《狂人日记》《伤逝》等;另一种是戏剧式独白,有假想听众,如《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等。这两种人物内心话语不仅具有戏剧艺术表达的直观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动作性。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动作,成为鲁迅小说中长篇独白的主要原动力,从而使长篇独白能够衍生成小说的整个情节或参与小说情节的重要构成。鲁迅小说长篇独白的动作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与他者的意志冲突和性格冲突;人物内在的情感律动;人物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和内心与外界的互动。除了直接内心独白和戏剧性独白之外,鲁迅小说还有一种戏剧式展现人物内心独白的方式——静止。如果说前两种独白相当于戏剧中的有声独白,那么静止也就相当于戏剧中的无声独白。谭霈生指出:“优秀剧作中的‘停顿’是富有戏剧性的,这正是因为在这个静止不动的瞬间,寄寓着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内容,它甚至比让人物用冗长的台词把内心隐秘和盘托出具有更大的艺术效果。”[11]48
鲁迅小说中这两种富有动作性的人物话语,不仅指向人物的生存状态,而且指向人物的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西方戏剧的现代性。鲁迅小说在塑造人物手段上对戏剧艺术的借鉴、融合和创新,增加了自身的表现力,使其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展示获得了更为直观、客观、生动的戏剧艺术审美效果。
(2)鲁迅小说中的色彩语码与绍兴地方戏。鲁迅小说的语言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色彩感,这主要表现在色彩语码,即颜色词的广泛使用上。经细致统计,鲁迅的33篇小说,如果就颜色的基本层次范畴和低层次范畴而言,共使用76种颜色,使用颜色次数共721次。主要颜色占所用颜色的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白色31.90%、黑色19.56%、红色17.34%、黄色11.65%、青色8.18%、绿色6.2%、蓝色2.50%、紫色1.80%。除了《头发的故事》,鲁迅其他小说均运用了较多的色彩语码。如《补天》一文中就运用了24种具体颜色,有些颜色还使用了很多次,如“白”色使用了12次。鲁迅小说广泛运用色彩语码,不仅与鲁迅个人所具有的很高的美术修养有关,而且与其少儿时期所接触的绍兴地方戏密不可分。绍兴地方戏与其他戏曲一样,都喜用装扮的颜色和脸谱来隐喻角色的身份、性格、品质等,因为鲜明的颜色可以更强烈、更刺激地被室外剧场的观众感官所感知,在短时间内调动和影响观众的情绪,并能够引领着观众更全面地认知角色,从而起到更好的舞台效果。绍兴地方戏在装扮上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专门青睐于白、黑、红三种颜色搭配所造成的强烈的感官刺激和非凡的视觉艺术效果,这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并对鲁迅后来的艺术审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在小说中大规模地借鉴了绍兴地方戏关于颜色的隐喻化认知思维方式,及其艺术审美经验和艺术形式,有意识地运用了众多的色彩语码,着力凸显了白、黑、红这三种色彩语码,并在这些色彩语码中赋予了自己独特的精神观念与文化价值,形成了其极具个性的颜色隐喻化认知形式,更好地发挥了小说语言在表现主题意蕴、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强大功能。如鲁迅在小说中总喜欢将极具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身上涂以“黑色”:《孤独者》中魏连殳黑色的眼睛和脸庞被反复凸现;《理水》中大禹“面貌黑瘦”,黑脸黄须,他的随员也是黑瘦的;《补天》中女娲“头发漆黑的搭在山顶上”;《奔月》中后羿“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铸剑》中眉间尺“漆黑的眼珠显得格外精采”,宴之敖同样是一个黑色人,“黑须黑眼睛”,小说中共12次写到“黑色人”;《非攻》中墨翟的脸是“乌黑的”等。在鲁迅小说中这一醒目而独特的“黑色人”家族中,无论是魏连殳这一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还是女娲、后羿、宴之敖、大禹、墨子等古代英雄或劳动者形象,在他们的灵魂深处都存在着巨大的悲哀与孤独。鲁迅对黑色的隐喻认知独具匠心地从颜色域投射到性格域,用“黑色”这一个性颜色隐喻这些人物坚毅实干与冷峻寡言的冰火性格。他们为天地立“心”,然而又不被世人所理解,因此他们一方面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方面又对那些破坏其劳动成果的人保持冷峻不屈的姿态,并给他们精神上造成严冷的威压。可以说,鲁迅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到了他的小说文本以及这些人物的灵魂之中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物形象就是一个文本化了的鲁迅。这就形成鲁迅小说中具有鲁迅个体精神观念的独特的黑色隐喻意义。鲁迅十分珍视这一类的黑色隐喻意义,它们在鲁迅小说中是黑暗中的亮色和希望。由上述可见,鲁迅小说中的黑色人,如同目连戏中浑身雪白的“活无常”和身着大红衣衫的“女吊”一样引人注目,用富有个性的颜色隐喻人物鲜明的性格,并引领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悲剧性的主题。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小说中色彩语码的隐喻表达更为注重的是负面的意义与价值,而具有正面隐喻内涵的色彩则通常出现在非现实的理想世界或“梦”里。鲁迅善于将色彩语码广博、深沉的隐喻内涵与社会人生密切结合,犀利地折射出现实社会的本质。
小说与戏剧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渗透是艺术发展的历史事实与必然逻辑。整个欧洲小说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戏剧对小说的渗透无处不在;中国小说和戏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一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戏剧和小说之间的互相改编屡见不鲜,而且在艺术手法上的相互借鉴也有案可稽。鲁迅小说作为“海纳百川”般的艺术杰作,其对戏剧艺术的借鉴和汲取正是其“纳新”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构筑其艺术世界的重要一维,而关于鲁迅小说与戏剧关系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还只是刚刚起步。因此,这一论题所包含的内容与问题,随着理论的不断丰富和人们认识的不断发展,必将不断被发现,也将不断地得到研究。
[1] 鲁 迅.鲁迅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 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 迅.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鲁 迅.鲁迅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鲁 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王雨海.从“少不读鲁迅”说开去——论鲁迅与青年及其他[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3(1):111-116.
[7] 杨 义.鲁迅小说会心录[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8] 大连市艺术研究所剧作理论研究组编.剧作艺术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9] [美]S.W.道森.论戏剧与戏剧性[M].艾晓明,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10] 孙淑芳.鲁迅小说的叙事时间与戏剧[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1):13-19.
[11] 谭霈生.论戏剧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韩大强)
2014-12-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51056);2013年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3Y406)
孙淑芳(1976-),女,河南信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I210.6
A
1003-0964(2015)02-00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