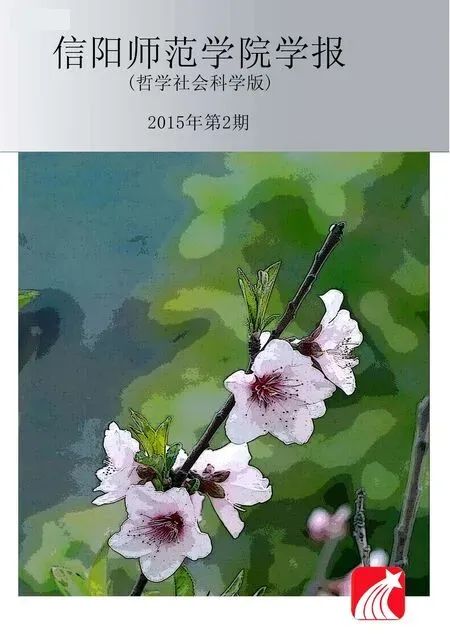鲁迅小说书写风物的传统性与创造性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专题研究:鲁迅小说修辞研究·
鲁迅小说书写风物的传统性与创造性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鲁迅小说书写风物手法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白描手法的精巧使用方面;其修辞的传统性则主要表现在采用“少做作”的自然修辞方面。鲁迅小说书写风物的手法及修辞的创造性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的白描及“少做作”的自然修辞的创造性使用方面。
鲁迅小说;风物;白描;自然修辞
“少做作”是鲁迅所认可的白描的一个方面的特点。白描这个特点落实在修辞上就是根据对象的本真状态遣词造句,最大限度地叙述和描摹出对象的原样,尽可能地摒弃主观性的评判语汇以及“掉书袋”似的叙述与描绘,让呈现于作品中的对象有“自然”之气,形成一种“自然修辞”。
在鲁迅的小说中,采用白描手法所形成的“少做作”的自然修辞事例比比皆是,其中,对风物的白描所形成的“少做作”的自然修辞事例又是鲁迅小说中最集中的事例。它们以最显然的存在及特有的魅力,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鲁迅小说采用白描手法形成的“少做作”的自然修辞的神采,也直接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修辞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造性。
一、书写风物的传统性
“风物”是自然之风景与人为之物景的总称。风物虽有自然与人为之别,但对文学创作者来说,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对象,具有同质性,用什么样的手法及修辞来叙述与描写这些客观对象,对于作者来说是千人有千法,对鲁迅来说也是如此。在鲁迅的小说中不仅叙述与描写风物的手法多样,修辞方式丰富多彩,而且即使采用白描手法及“少做作”的自然修辞书写风物的例证也屡见不鲜,所以,我这里只能列举几个事例。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狂人日记》)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孔乙己》)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药》)
这时候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理水》)
这些例子,并非是我刻意选择的,而仅仅是依据鲁迅小说的排列顺序,将几篇小说开头对风物的叙述与描写罗列出来的。这些例子既有选自现代小说的,也有选自历史小说的,既有选自典范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如《孔乙己》《药》中的例子,也有选自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小说的,如《狂人日记》中的例子,还有选自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的,如《理水》中的例子。但不管是从鲁迅创作的什么类型的小说中选择出来的,也不管这些小说的艺术规范具有怎样泾渭分明的差异与不同,这些书写风物的文字,从手法上都具有鲁迅对白描特征的基本要求——“少做作”。在修辞方面,无论是词语的使用,还是句子的修饰,可以说都有“自然之气”,是自然修辞。这种手法与修辞,与中国传统小说对风物的书写十分一致。由于“风物”意指自然风景与人为景物,因此,我这里分开论述,先论述中国传统小说对自然风景的书写。
提到中国传统小说的自然风景书写,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要数《水浒传》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1]127。鲁迅自己还专门写过一篇杂文,高度地赞赏《水浒传》描写雪景的这句话,“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2]582。《水浒传》这句书写下雪情景的文字的确很有“神韵”,这种神韵,不仅比“大雪纷飞”这句话的神韵“好得远”,具有一种感觉上的“压迫感”,能唤起阅读者的情景想象与多样联想,而且一个“紧”字还直接地写出了雪下得既密又大的景象,进一步地强化了小说前面所写的“那雪早下得密”的情景,将小说前面“密”字所书写出的大雪存在的“静态”状况“动态化”了,写出了大雪“生成”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征,为读者提供了可以想象的引导,并凝聚了可资分析的审美内容。所以,鲁迅才高度赞赏“那雪正下得紧”这句话很有神韵,一般的人们也才更记住了《水浒传》书写自然风景的这句话,并将这段描写自然风景的文字作为中国传统小说采用白描手法书写风景的经典例子来提及,而对《水浒传》前面一段同样是书写自然风景的“那雪早下得密”的文字视而不见了。因为,从修辞效果上讲,虽然两句书写雪景的文字都采用了白描的手法,其修辞也都具有“少做作”的自然修辞的特点,但“紧”字的使用的确比“密”字的使用更有“神韵”,“紧”字的使用不仅将“密”字所要表达的内容表达出来了,而且将“密”字所呈现的空间静止状态进一步地动态化了。
提到中国传统小说对人为物景的描绘,其精彩绝伦当首推《红楼梦》对“大观园”的书写。在书写“大观园”的景象中,小说呈现了诸多精彩的段落,也采用了诸多漂亮的手法及修辞,甚至以诗词的形式,在亦歌亦咏中展示了“大观园”的美景、美态。白描的艺术手法及“少做作”的自然修辞也是小说在书写“大观园”的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手法与修辞,并且也取得了美轮美奂的审美效果。这是《红楼梦》对“大观园”正门景观的书写:
贾政先秉正看门,只见正门五间,上面桶瓦泥鳅脊;那门栏窗槅,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矶,凿成西番草花样。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果然不落俗套,自是欢喜。[3]100
此类对“大观园”物景的书写还有很多。小说不仅采用白描及与景观一致的自然修辞有效地呈现了“大观园”美不胜收的自然美,而且匠心别具地通过观看者的“题对额”展示了“大观园”的人文美。不仅直接书写出了“大观园”的静态美,而且通过人们的边走边看展示了“大观园”的动态美。“大观园是以楼、亭、阁、院、馆、斋等建筑为主景,与山、水、花、石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然景观美;它还通过‘试才题对额’这一情节线索,以匾额、对联的应景点题,融历史文化于自然景物之中,形成人文景观美,使自然景观呈现出文采风流”[4]1。这里所说的“自然景观”的山、水、花、石等,其材质虽然是自然的,但由于是人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安排在“大观园”中的,因此,这里的自然景观,实质上就是人为的景观,“自然景观美”其实质也是人为的景观美。这段评说《红楼梦》对“大观园”景象书写特点的文字,虽然在概念的使用上存在不周密的情况,特别是将“大观园”建筑的景观美划入“自然景观美”之中,混淆了自然景观与人为景观的区别,具有明显的误解性,但这段评说,还是很好地剔析出了《红楼梦》对人为景观书写的特点与神采。对照上述所引鲁迅小说白描风物的文字,其传统性是显而易见的。就书写自然风景的文字来看,鲁迅小说中三段书写自然风景的文字与《水浒传》中书写雪景的文字,不仅手法一致,都采用了白描的手法,而且修辞也一致,都采用了“少做作”的自然修辞。同时,其艺术效果也都具有相似的“神韵”。这种“神韵”如果进行概括就是用最简短的文字写出对象最主要的特征,呈现对象最真实的自然状况,达到“形似”基础上的“神似”,并给读者留下充分想象的引线。《水浒传》中的一个“紧”字的使用就具有这样的艺术功能,而鲁迅小说书写自然景物的文字,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艺术功能,如《药》的开首所书写的自然之景的文字就是如此。陈鸣树先生曾经指出:这段文字“简到无可再简了。因此,‘什么都睡着’也就更得到了强调”[5]234。也就是说,在陈鸣树先生看来,这段文字中最出彩的文句是“什么都睡着”,而这段文句所使用的艺术手法恰恰是最典型的白描,既没有使用任何表达主观评判的文辞,更没有任何“做作”的书写,完全是如实地叙述与自然的修辞。但就是这样的白描及完全自然的修辞却写出了万籁俱寂的情景,构成了与自然之景相一致的“形似”;同时,这种形似中又分明地具有“神似”的内容,也就是陈鸣树先生所说的“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黑夜里,却正在演出夏瑜英勇就义和华老栓去买‘人血馒头’的悲剧”[5]235。陈鸣树先生概括的是这段使用自然修辞白描风景文字的一层“神似”的内容,而且是基于“共时性”的视野概括的,在我看来,这段文字中更为直接的“神似”的内容则是不仅直观地写出了自然之景下正在“演出”的社会悲剧,而且象征地写出了大众的灵魂悲剧,即沉睡在鲁迅所认为的“铁屋子”里的大众不觉悟的精神状况,他们的愚昧、麻木的精神状况也如这自然之景一样地“都睡着”了。
鲁迅小说不仅书写自然风景的文字具有这种形似基础上的“神似”的神韵,而且其书写人为物景的文字更具有这样的神韵。这种神韵与《红楼梦》对“大观园”大门的书写也十分相似:不仅直接地采用白描及“少做作”的自然修辞写出了对象的“美”,而且在这种“美”中灌注了人文的内容。如《孔乙己》中对咸亨酒店柜台的书写,有研究者就认为,这样的书写表面上看似乎很平常,虽然使用的是白描及没有做作的自然修辞,但却不仅书写出来了一种物质文化(酒店文化)在一个特殊地方存在的状况,而且还反映出了一种精神文化的内容,这种精神文化的内容就是一种“格局”似的内容。这种格局似的内容的基本规范,虽然具有地方性,也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所说的“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但是这种规范反映的不仅是鲁镇人的“集体无意识”,而且也直接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在人与人之间的尊卑贵贱的关系中体现出来(如短衣帮与长衫帮),而且在建筑的室内布局中也体现出来,鲁镇酒店“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而不是当街一排屏风或如“衙门”一样的当街几块“回避”“肃静”的牌子的布局,就是这种规范的直接体现。这样的布局在显然的形态上虽然体现的是酒店的特性与功能,在观念上所体现的则是社会建筑“各司其职”的伦理规范。同时,这样的大柜台主要是为“短衣帮”服务的,“穿长衫”的有钱人则是“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所以,鲁迅书写酒店格局的文字虽然很短,所采用的基本手法是白描,也没有任何具有主观评判的修辞,但其中却不仅包含当地风俗及当地民众心理的内容,而且包含了由建筑的室内布局所体现的伦理规范,其书写的意义也就自然非同一般。
二、书写自然风景的创造性
鲁迅小说书写自然风景与人为物景都显示了很强的创新性。人为物景的创造性我们姑且不论,因为鲁迅小说书写的人为物景,其对象本身就与中国传统小说书写的人为物景有很明显的不同,这里我只着重从书写自然风景的角度来论述其创造性。其中,主要以《狂人日记》与《理水》两篇小说中书写的自然风景为例。
《狂人日记》中的自然风景书写虽然是从文内叙事者“狂人”的视角展开的书写,但不仅所采用的白描手法和“少做作”的自然修辞与《药》一样,而且同样在“形似”的基础上显示了深刻的“神似”。从“形似”来看,小说对“今晚月光”的书写只有九个字,也是简短得不能再简短了,但也就是这九个字却准确地白描出了月光出现的时间——今晚,以及月光的状况——“很好”。从“神似”来看,如此简洁的自然风景书写,不仅为后面揭示狂人面对“今晚月光”“精神分外爽快”的欣喜和对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的人生反思以及对今天人生的重新认识等复杂情怀提供了依据,而且其所构造的意境之美,由于与整篇小说的恐怖气氛及书写的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吃人”事件、各种想吃人的心态的不协调。而在鲜明的对比中构成了一种力透纸背的反讽:自然风景的美一方面烘托了吃人事件及想吃人的心态的丑,不仅使吃人事件及想吃人的心态的丑显得“更丑”,而且也直接地否定了吃人事件及想吃人心态丑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直接地解构了“自然风景美”自身的价值。
为什么说《狂人日记》这段书写自然风景美的文字在与吃人事件及想吃人的心态构成的反讽中,不仅具有否定吃人事件及想吃人心态的合理性的功能,而且具有自我解构的功能呢?对吃人事件及想吃人心态合理性否定的功能,由于外在形态美的自然风景与本质上丑的“事件”“心态”的对比十分鲜明,具备了“不言自明”的特性,不需要过多阐释。这里需要重点分析的是这段书写自然风景美的文字的自我解构功能。
这段书写月光之美文字的自我解构,首先就是从很好的月光出现的时间及对月光的“很好”下判断的人物——狂人开始的。月光虽然表面“很好”,其实这种“很好”是缺乏有力依据支撑的,也就是说,支撑“很好的月光”的依据在逻辑上不严密,在事实上不真切。从逻辑上看,这所谓“很好的月光”出现的时间——三十年后经不起推敲和质疑,三十年后才有这“很好的月光”,那么三十年前这“很好的月光”又到哪里去了呢?从事实上看,这所谓“很好的月光”并非客观存在的现象,而是由精神不正常的狂人自己做出的判断。事实上“狂人”本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其思维不仅紊乱,而且常常充满幻觉,“他”认为“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也未必不是“他”自己对“今晚”“月光”的一种幻觉,也未必不是在“胡言乱语”。所以,小说通过这个本来就思维紊乱且充满幻觉的狂人之“眼”来书写月光,其可靠性、真实性本身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次,这段书写月光之美文字的自我解构更因为所书写的“很好的月光”笼罩的是一件件吃人的丑事或一个个“想吃人”的丑恶心态,也就是说,“很好的月光”在小说中的功能不过是丑事、恶事的遮羞布,它越好,能量越大,其负价值则越明显,它自身的正价值也就越被消解。“很好的月光”自身的价值逻辑就是如此。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从开篇‘月光’、‘赵家的狗’所渲染的抑郁、恐怖的氛围,到赵太翁、路人、小孩子等社会成员的接连出场、对狂人的联手排斥,再到大哥、母亲、仆人、医生等家族力量合谋迫害狂人,不仅为狂人铺就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网罗,而且在小说文本世界中弥散着一种无边的压抑感”[6]121-122。而小说开首出现的“很好的月光”也就如泥牛入海一样地消失在了整篇小说恐怖、压抑的气氛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再也没有出现的结局,正是这“很好的月光”自我消解的结果。因此,整段关于月光的书写,虽然没有一个字词直接地表露作者的情感与思想倾向,相反,小说完全采用白描和“少做作”的自然修辞,但很好的月光所呈现的风景之美与吃人事件及想吃人的心态之丑的不协调,以及很好的月光之景自身不可靠、经受不起质疑的存在,却通过反讽使作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及礼教弊害”的思想倾向及激烈的反封建的批判意识,在简短的自然风景的书写中也得到了机智的显现。这正是《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书写自然风景的一种深沉的匠心和杰出的“神似”。
至于《理水》中采用“打引号”的文句对自然风景的书写,也具有同样的神韵。如果进行细读,《理水》中采用“打引号”的文句对自然风景的书写,不仅符合白描的规范,其修辞也是“少做作”的自然修辞,而且其对风景书写形成的形似及神似更有深意,其艺术的匠心更为显著。
之所以说《理水》中书写自然风景的文句是“打引号”的文句,而不说这两句书写自然风景的文句是“引用”的文句,是因为这两段文字既有所本,但又与原文有差异。这两段文字,据《鲁迅全集》中的注释云,是鲁迅根据《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7]401改造而成的。如果按照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对“引用”这种修辞格的界定,小说中这两个使用了引号的句子,从形式上看应该属于“明引法”,因为“明引法”的基本规则就是使用引号将引用的原文“标示”出来。但是,从这两个使用了引号文句的实际情况看,这两段文字又与“原文”有差异,没有完整地实行“明引法”所要求的“语意并取”[8]101的规定;如果说这两个书写自然风景的文句在“略语取意”[8]101方面符合“暗用法”,但这两个句子又使用了“暗用法”不需要使用的引号。因此,从修辞的角度看,《理水》这篇小说书写风景的这两句话,既不符合“明引法”,又不符合“暗用法”,真可以说是“不伦不类”了。不过,尽管这两段使用“引号”书写自然风景的文字在形式上显得不伦不类,其修辞的方式也难以归于一般修辞学的“格”中,但从艺术手法上看,这两句“打引号”的话,其手法也是白描,它们如实地呈现了洪水滔滔的自然景观。从修辞学上看,这两句话所使用的修辞,也是不带任何主观情感的自然修辞。同时,由于这两句书写自然风景的话,并非是真的“引用”,而是被鲁迅改造了的古文,所以,这两句书写自然风景的话,也就因为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引经据典”而消除了“掉书袋”“做作”的嫌疑,呈现的是不做作、自由的书写姿态。
同时,当进一步结合整篇小说展开分析,我们发现,这两句不伦不类的“引用”语,不仅具有如实地书写出客观自然景象的功能,达到了对自然景象书写的形似,而且,其“神似”则更为引人注目。也就是这两句不伦不类的“引用”却为整篇小说定下了艺术书写的基本规范,显示了这种“不伦不类”书写规范的“神采”。这个不伦不类的书写规范可以从两个方面看,首先,如果从艺术原则上看,这种不伦不类的规范就是解构神圣、崇高,回归俗人俗事情怀的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规范。正因为它是“不伦不类”的规范,在中外文学的经验世界和文学理论世界中无法归于任何一种书写类型的规范,所以,它也当然是一个完全反传统、消解传统的规范,也是一个具有“先锋性”而且过于超前的书写历史、神话、传说的新规范。当然也是鲁迅在创作历史小说中首创的规范,它彻底地革新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严肃地书写历史事件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则,解构了采用“宏大叙事”书写重大历史事件,采用类型化的方式塑造著名的历史人物或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基本规范,并由此而创建了一种崭新的“故事新编”体的规范,一种前不见古人,后启来者的书写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新规范。这种“故事新编”体的规范与古今中外一般历史小说规范的最大不同就是:“它可以尊重‘历史真实’,也可以阳奉阴违;可以初步消解,也可以彻底颠覆;可以修正,也可以更大程度上地重构等等”[9]9。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故事新编”体的规范太超前了,没有任何文学作品的经验范式或文学理论的历史资源可以解说它,所以,在后现代主义理论还没产生之前,在我们还没有知晓后现代主义为何物之前,我们面对《理水》这样的历史小说不知道如何言说,即使勉强按照经典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规范,甚至时髦的现代主义理论规范展开言说,也总觉得难以自圆其说,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其次,这一规范如果从艺术手法上讲,那就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7]354,不拘泥于古法,也不拘泥于古人,也就是像《理水》中“打引号”的书写一样,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地书写。这一手法既承续了鲁迅创作第一篇历史小说《补天》时的“油滑”手法,又在新的历史时期,即1935年深化了“油滑”手法的艺术意蕴。如果说,《补天》中的油滑(包括《奔月》中的油滑)很明显的是采用现代话语将现代事件直接写进历史小说中的话,那么,《理水》则已经逐步地抹去了这种过于“现代性油滑”[6]227的痕迹,“而将第一篇实验之作(《补天》——引者注)的包容可能性放大,直到确认它能脱离既有的创作规则、取得自足”[6]227。也就是说,鲁迅所独创的“故事新编”体作为一种“自足”的文体,是到了《理水》才最终完成的。而在这种具有自足性的小说文体的完善过程中,《理水》所采用的引用古文写古事的白描手法,及引用古文但又不全照搬古文,既保留了古文的大致意思,又没有“死”抄古文的“少做作”的自然修辞,也功不可没。这也许就是《理水》书写自然风景时鲁迅将这两句话“打引号”的卓越的艺术意义。
三、书写自然风景的象征性神采
上面这些分析不能说都没有道理,也不能说都没有价值,但是,我们也要正视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风物的书写不管多么详尽、独到、精彩也难以形成“重大”的内容,尤其是对纯粹的自然风景书写来说,更是如此。无论在什么类型的小说中,关于自然风景的叙述与描写虽然也很重要,尤其从构成人物活动的背景及情节展开的角度考虑,自然风景的书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就书写的自然风景本身而言,却难以形成独立的具有“重大”思想价值内容,如我上面已经简要地分析过了的“那雪正下得紧”就是如此,虽然,这句对自然风景书写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但其中却也难以剔析出有什么重要思想内容,包含了什么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硬是要说,“那雪正下得紧”一句是暗指社会形势“紧张”,暗示身处这种雪景中的林冲的处境“紧张”,虽然也能差强人意,但终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或过度阐释之弊。
无法形成重大的思想价值,这是自然风景书写在小说中的局限,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作品中,我们固然可以寻索到大量书写自然风景的杰出事例,固然可以对这些杰出的书写事例展开审美的言说与分析,但我们却实在无法从这些杰出的书写自然风景的文句中剔析其“本身”所包含的重要思想内容。
也许正是因为洞察到了自然风景书写的这种局限,所以鲁迅不仅在小说中大量采用白描与自然修辞的方式书写自然风景,而且在理论上,鲁迅也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0]526这一观点,不仅是鲁迅对自己的小说“描写风月”特点的概括,而且是鲁迅对自己小说采用“力避行文的唠叨”的方式与小说创作思想目的关系的阐述。因为他创作小说的目的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风月的描绘,恰恰与这样的目的离得太远,风月描绘得再杰出,也无法有效而直接地表达小说的创作主旨,所以鲁迅在创作小说的时候,才“力避行文的唠叨”,在描写风月时尽量采用白描及“少做作”的自然修辞。鲁迅小说及鲁迅对自己在创作小说时“不去描写风月”的艺术追求的表述,也正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风月描写”的局限性及风月表达意义的有限性。
那么,陈鸣树先生以及其他人和我对鲁迅小说自然风景书写的分析,难道没有这种过度解读的弊病?当然,这样的解读虽然有点“过度”,虽然也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不可否认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的依据就是修辞。因为,在修辞中本来就有一种使用较为频繁的“格”,即“象征格”,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这种修辞格不仅使用频繁,而且其良好的思想与艺术的效果还十分显著,如在中国传统小说的自然风景书写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篇话本小说,当杜十娘跳江自尽的悲剧发生时,作者的“但见云暗江心,波涛滚滚”的自然风景的书写,就具有这种象征的意味。至于小说对人为物景书写的象征意味就更为明显了,如《红楼梦》中对花园环境的描写,“再迟钝的读者也能感觉到《红楼梦》中每个人物的性格及命运与他的居住环境之间的那种象征性联系”[11]250。其题目“红楼梦”本身就具有象征性。而象征这种修辞格与白描手法及“少做作”的自然修辞又是不矛盾的,也就是说,采用白描及“少做作”的自然修辞同样可以构成“象征”修辞,尤其在风物的书写中更是如此。王富仁先生在论鲁迅小说时曾经指出,《祝福》中鲁四老爷书房的陈设,是鲁四老爷陈腐的旧观念的象征,而这种象征效果的获得,鲁迅小说所采用的正是白描及“少做作”的自然修辞。这是《祝福》对鲁四老爷书房书写的文字: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为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平气和”。[7]6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本来不具有构成重大意义和价值内容的风物能具有象征性?或者说,作者如何书写风物才能构成象征?弄清了这个基本的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解说为什么“那雪正下得紧”的自然风景描写不具有象征性,而鲁迅小说的风物书写具有象征性的问题。
象征具有什么规范呢?黑格尔曾经指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12]10小说中的象征,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象征具有什么特点呢?“具体到小说中的象征这一修辞问题,传统小说的经验就是:只有当象征是形象的、并且作为一个有机的部分依附于以塑造人物为中心的叙事主体的时候,它才有可能与小说内部各种因素建立起和谐而均衡的辩证关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塑造人物、喻示主题等修辞目的,最终有助于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修辞交流目的”[11]261。(这里所说的“传统小说”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古典小说,而是相对于现代主义小说而言的一个概念——引者注)中外人士对象征规范及特点的解说,虽然层次不同(黑格尔更多的是从哲学层次的解说,李建军则是从小说创作实际层面的解说),却从两个主要的方面揭示了“象征”得以形成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无论象征由什么感性事物构成,这些感性事物本身不仅应具有某种特性,如松树的坚挺、柳条的柔韧,而且它们自身的这些特性,还积淀了一定历史的认知内涵,与一定的思想“意义”或价值取向建立了相应的联系,只有与一定的思想意义或价值取向相关联的感性事物,才可能构成象征。在现实生活中,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一样,如狮子、狐狸等这些可见可感的动物,圆形、三角形这些图形,都有一定的象征性,“狮子象征刚强,狐狸象征狡猾,圆形象征永恒,三角形象征神的三神一体”[12]11。这些感性的事物之所以能构成象征,具有象征性,是因为“在这些符号例子里,现成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已具有它们所要表达的那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象征就不只是一种本身无足轻重的符号,而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已可暗示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内容的符号”[12]11。第二个条件是,感性事物的象征性往往与作品,尤其是叙事作品中所要塑造的人物及所要表达的思想有内在的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显在或隐蔽地帮助了作品主旨的表达。
以此来看《水浒传》中著名的自然风景描写,虽然鲁迅高度赞赏了其“神韵”,但很明显的是,鲁迅主要赞赏的是这句书写风物的文句本身的神韵,尤其是赞赏用一个“紧”字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从天空中飘洒下来的状况的“神韵”,鲁迅并没有赞赏,也没有指出这句书写自然风景本身的文句具有什么“微言大义”,其在表达思想或塑造人物方面如何有“神韵”。即使联系小说后面所书写的林冲看管的草料场被人为纵火的内容来看,我们承认,这句关于自然风景的描写似乎具有暗示林冲处境“紧张”的作用,但就这段描写自然风景的文句中的“感性事物”——雪来看,由于雪这一意象,无论从实际的意义上看,还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看,都不具有黑格尔所认可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已具有它们所要表达的那种意义”,即雪这种感性事物本身就不具有表达“紧”或“紧张”的意义。一般来说,雪作为感性事物,由于它自身的颜色是透明的“白色”,因此,在现实生活中雪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纯洁、安宁的意义。在文学作品中,雪也基本上是作为纯洁、白净、美好的意象来使用的,如唐诗中描写雪景的著名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就是最好的例子,与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紧张”等思想意义没有任何关系,也与作品所要表达的对社会、人生批判的价值取向没有任何关联性。即使是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中所书写的“雪景”,也是如此。这部杰出的戏剧所书写的下雪情景的象征性,也不是由“感性事物”雪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决定的,而是由“时间”决定的,戏剧所要表达的“窦娥的冤”和所要控诉专制制度“把人不当人”的思想意义,是通过对“七月飞雪”这一违反自然规律的想象性书写完成,而不是通过雪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完成的。
同时,从“那雪正下得紧”这句关于风景书写的文句存在的具体情况看,这段文字书写的是林冲所面对的自然风景,但林冲所面对的这种风景对塑造林冲这个形象来说,除了具有交代林冲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意义之外,既没有暗示或烘托林冲这个人物性格、思想、情感的作用(如《红楼梦》中对人物生活的大观园等物景的书写一样),也没有象征性地揭示人物悲剧命运的作用(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所书写的风景一样),对作品主旨的表达也不起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所以,如果硬性要将《水浒传》中这句精彩的书写风物的文句进行拓展似地解说,甚至将其引申到社会领域,认为其中所书写的自然风景有暗示社会环境“紧张”的意义,这样的解说我们姑且不说是一种牵强附会,也起码是一种溢出感性事物本身意义及感性事物与小说人物关系意义的过度的解读。
与之相比,鲁迅小说的风物书写的象征性则是十分明显的。这种风物书写的象征性,也正是鲁迅小说在继承传统小说风物书写神韵方面的创造性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姑且不谈鲁迅小说对人为景物书写的象征性,即使是纯粹的自然风景的书写,也是如此。《药》的开头所书写的夜景,是纯粹的自然风景的书写。陈鸣树先生从“夜”这种自然风景中解读出社会性的悲剧,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夜”这种“感性事物”本身就具有“黑暗”“恐怖”的意义,具有象征悲剧的意义,而革命者夏瑜被杀头正是恐怖的事件、黑暗的事件、悲剧的事件;愚昧、麻木的华老栓对这件恐怖、黑暗的悲剧事件不仅没有任何“感觉”,相反,还听信别人的劝告,去购买由夏瑜的血所浸染的馒头为自己的儿子治病,其行为本身也是让人感到恐怖的。更何况,在鲁迅的小说中,黑夜,不仅是鲁迅小说中常常书写的对象,而且与黑夜如影随形的色彩“黑色”,在鲁迅的一系列小说中,如《狂人日记》中的“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明天》中的“黑沉沉的灯光”等,还常常“被鲁迅赋予以强劲的力度”[13]107,而鲁迅本人“是深通艺术的巨匠。他在少年时代便与绘画结下了缘分。在鲁迅的一生中,对于绘画、木刻以及色彩学,有着精辟的见地。在小说创作中,他是重于白描手笔的,他极力用节省的笔墨勾勒自己的人物,因此,在设色润墨上,自然十分考究”[13]107。这使鲁迅在创作小说的时候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色彩一旦形诸文字,便满蕴着情思,并不断地深化着它的意味。”[13]107所以,陈鸣树先生的解读是有依据的。同样,我的解读也是依据“一切都睡着”的白描展开的,因为“睡着”作为一种自然的状态,其本身就有“不清醒”的意思,而人的精神状态的愚昧、麻木,也正有精神不清醒的意思,所以,对感性对象本身就具有的“不清醒”意义进行社会性、人性的解读也是完全符合“象征”修辞的规范的。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发现,在白描风物的时候,鲁迅小说所采用的“少做作”的自然修辞,虽然与中国传统小说,尤其是《水浒传》这部杰出的小说白描风物的修辞“神韵”有很明显的一致性,都用最少的文辞,生动、形象地书写出了风物的本来面貌,具有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但鲁迅小说在白描风物时,由于很好地注意了小说的思想意图的表达及其他意义表达与所白描风物的“象征”性关系,因此,鲁迅小说所采用的“少做作”的自然修辞,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对风物“简略得不能再简略”的书写,而且充分地显示了“少做作”的自然修辞的特有神采,这种特有神采就是“言简意赅”。作为典范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药》的风景书写是如此,作为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狂人日记》的开头的风景书写也是如此,即使是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理水》中采用“引用”的形式对风景的书写也是如此。这正是鲁迅小说采用白描及“少做作”的自然修辞书写风物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也是鲁迅小说在书写风物方面继承传统而又全力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
[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2] 鲁 迅.“大雪纷飞”[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曹雪芹.红楼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4] 黄清泉.红楼梦·前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5] 陈鸣树.鲁迅小说论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6] 刘孟达.经典与现实——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7] 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9] 朱崇科.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M].上海:三联书店,2006.
[10] 鲁 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2] [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 孙中田.色彩的诗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韩大强)
2014-12-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51056)
许祖华(1955-),男,湖北仙桃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I210.6
A
1003-0964(2015)02-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