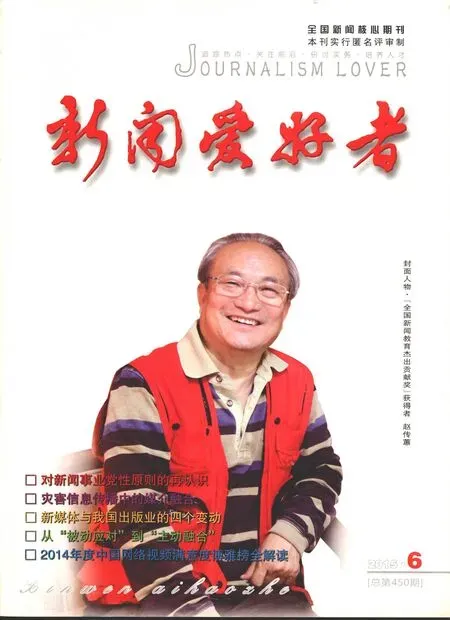杂文的“闲适格调”——兼评林语堂和鲁迅的杂文风格
□刘福智 张继忠
杂文的“闲适格调”——兼评林语堂和鲁迅的杂文风格
□刘福智张继忠
除战斗与批判之外,闲适格调也应容许在杂文写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格调具体表现为杂谈琐议和针砭讽喻。林语堂在鲁迅的匕首、投枪之外,在杂文园地里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丰富了杂文的艺术手法,这正是其闲适格调价值之所在。
杂文;闲适格调;林语堂;鲁迅
一提到杂文,有人立马就会想到匕首、投枪,想到批判战斗,想到严责怒斥,好像杂文与所谓的“闲适”毫无瓜葛。其实,“闲适”作为一种格调,应当为诸多文体所接受,杂文中也应该容许有它的一席之地。为什么一种文体只能有一种格调呢?这大概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思想吧。
现在有些杂文依然是严肃有余而幽默不足,批判有余而美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由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首倡的杂文“闲适格调”就特别值得借鉴。
一、“闲适格调”的手法和技巧
有人把林语堂的“闲适格调”看作内容上表现“闲情逸致”,语言上则一味“自然平和”。这种看法未免失之片面,或者说未能理解和把握这种格调的实质。林语堂在《人世间》发刊词中曾经阐明,他所倡导的“闲适格调”,不是指思想内容和描述对象,而是指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所谓“格调”,就是笔调;所谓“闲适格调”,就是一种带有闲适特点的个人笔调。大量阅读林语堂的杂文之后,他的“闲适格调”可作如下两方面的归结。
(一)平中见奇的杂谈琐议
西方将散文分为小品文和学理文,认为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小品文下笔随意,学理文章法分明;小品文不妨杂谈琐议,学理文则为题材所限而谨言慎行。因此,西方人称小品文为个人笔调(Personal style),也可译为“闲谈体”或“娓语体”。总之,杂文的“闲适格调”,就是一种清闲安逸的行文方式和语言特色。这种格调自然适于叙写山间明月,江上清风,身边琐事,闲情逸致。但是除此之外,也完全可以用于暴露丑态,戳穿伪善,抨击时弊,斥责罪行。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攻击假恶丑必定要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慷慨激昂,骂语连篇。当然,这样做非常痛快、非常解恨,但是如果篇篇如此,那也未免单调。杂文也完全可以采用闲适的格调,表面上是山间明月,安然祥和,实际上却是地火汹涌,义愤填膺;表面上是江上清风,清闲安逸,骨子里却是狂风怒号,慷慨激昂。这样的行文方式比起骂语连篇,自然更有情趣。这种杂谈琐议,之所以被称为“平中见奇”,其“平”,在于表面上的清闲安逸;其“奇”,则在于骨子里的慷慨激昂。
如林语堂《谈言论自由》中的一段文字:
《伊索寓言》一书,专门替鸟兽造谣,谤毁兽类与人类一样的奸诈。假定鸟兽能读这种故事,他们也不会懂得。比方狐狸看见树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开,决不会无聊地骂酸葡萄。惟有人类才有这样的聪明。
文中说人类“聪明”,不过是运用反语,实则是以人类和兽类相比,讽刺人类的虚伪。林语堂此处或有实指,却并不明言,让读者去联想那讽刺的对象;他也不直言在这一点上“人不如兽”,反而刻意夸奖人类。语言是平和的,讽刺却有些辛辣。
(二)绵里藏针的针砭讽喻
所谓“针砭”,原是中医的一种医疗手段,这里是借指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所谓“讽喻”,不是讽刺,这是一种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讲明道理的修辞手法。针砭用的是小小的银针而不是投枪,讽喻相对来说应是温和的,而讽刺却是犀利的。
所谓“闲适格调”,就意味着一种恬静的心态、一种平淡的语气、一种温和的语言;而不是亢奋的心态、冲动的口气、激昂的语言。文章的内容可能并不恬静平和,而作者却完全可以采用这种相对温和的格调对假恶丑进行揭露和批判。作者并不怒骂,怒骂就意味着正颜厉色的抨击;也不嬉笑,嬉笑就意味着笑谈戏言的嘲讽。“闲适格调”则意味着一种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行文手法。如果同味觉相联系,那么,正颜厉色的抨击会使人感到辣,笑谈戏言的嘲讽会使人感到苦,而这种恬静平和的漫谈,则使人初始感到淡,而后却感到余味浓厚。
林语堂在《谈言论自由》一文中举例“猫叫春”,认为猫是“非常自由,很有魄力的”,反衬人类在求偶时就不会有如此的自由了。即便有,也断无如此的魄力。作家笔锋一转,说中国的老百姓“痛时只会回家咒骂,而且怕人家听见”,这分明是批评当时的政治生活不民主,人们没有“喊痛的自由”。但作家并不用诸如“独裁”“专制”“压制民主”等极端的字眼去抨击当局,而是用一种淡泊的态度、幽默的文笔娓娓叙谈,这正是所谓的“娓语体”。读者仿佛可以窥见那“绵里”隐藏的“针”的影子了。这种抨击,并不是握着匕首,猛刺过去,使论敌遍体鳞伤,而是稍稍闪动一下“针”的锋芒,使对方感到隐隐作痛。这些文字,虽然是一种平和的中性的言辞,但是,难道我们不能从这种恬静平和的讽喻中感到一种坚硬、愤懑的指斥吗?
林语堂一篇杂文中还有一段题为《言论系讨厌的东西》的文字:
中国向有名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又谓知人秘事者不祥,又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由此可以推知言论是讨厌的东西,岂容你自由?所以好言人是非者,人家必骂为狗:“狗嘴吐不出象牙。”只有称赞颂扬人的,人人喜欢,奉为象。政府所喜欢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并非好喊痛的百姓。比如此刻有侦探在坐,必认为林某人讨厌,而认守口如瓶之诸位是比我好的国民。……
所谓“言论是讨厌的东西”,这是当局者的看法。作家这段文字,意在抨击当时的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政府所喜欢的”,“只有称赞颂扬人的人”,起码“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而“并非好喊痛的百姓”。对于没有言论自由,甚至不许“喊痛”的社会,作家自然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并不用激烈的言辞予以迎头痛击,却是以清闲安逸的笔调,以说“风凉话”的形式,给以旁敲侧击。这种笔调和形式给予批判对象的虽然不是切肤之痛,以至于使其生出彻骨之恨,但也使其感到小小的不自在,感到自己的世界并不十分美好。
林语堂议论时政而且内容颇为敏感的另一篇杂文是《论政治病》。作家写道:
……在要人下野电文中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指出:脑部软化,血管硬化,胃弱,脾亏,肝胆生石,尿道不通,牙蛀,口臭,眼红,鼻流,耳鸣,心悸,脉跳,背痈,胸痛,盲肠炎,副睾丸炎,糖尿,便闭,痔漏,肺痨,肾亏,喇叭管炎……还有更文雅的,如厌世,信佛,思反初服,增进学问,出洋念书,想妈妈等(毛病就在古文的不是,“养疴”二字若不是那样风雅,就很少人要生病了。)……总之,人世间上可有之病,五官脏腑可反之常,应有尽有了。只有妇科不大有,其理由是中国女子上台下台者尚少,不然一定子宫下坠,卵巢左倾……
政坛上重要人物(即文中所谓“要人”)的凡此种种病症,其实往往是一种托词,是一种勾心斗角的手段,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病”,“是他们政治上斗争的武器及失败后撒娇的仙方”。有趣的是,作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那么多的疾病,而有的病并不见得就有,比如“卵巢左倾”等,这些都是为了说明政坛上的“要人”为了与政敌较量而挖空心思,胡编乱造,扰乱视听。林语堂这一段犹如相声一般的语言,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不是在写文章,却像是好友之间的闲谈、神侃、东拉西扯。原来,杂文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杂文完全无须板起面孔训人,瞪起眼睛骂人,而完全可以用一种轻松活泼、信马由缰般的语言来论事说理。
以上两点,应是林语堂“闲适格调”的具体表现。
二、“闲适格调”的价值和局限
林语堂的杂文,往往牵涉严峻而敏感的话题,大多表现政治内容,而作家却都以清闲安逸的文字来表现,反映了他特有的格调。可以说,林语堂在鲁迅的匕首、投枪之外,在杂文的园地里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丰富了杂文的艺术手法,这应是其“闲适格调”的价值之所在。
但是,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推崇鲁迅及其杂文,于是,林语堂的杂文及其“闲适格调”就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甚至以鲁迅“划线”:赞同与追随鲁迅的作家,便是革命作家;反之,便是反动作家。林语堂便成为批判对象。
鲁迅和林语堂在当时都是著名杂文家,同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职任教,又同时经历了当局枪杀刘和珍等青年学生的“三·一八”惨案。事后,二人为了悼念自己的学生,分别写出《记念刘和珍君》和《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两篇著名杂文。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就可见两位杂文家文章格调的不同。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文字,是愤怒,是控诉,是锋芒逼人,是长歌当哭。现引录两段于后: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的杂文,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面对论敌那丑角般的表演,他会写出嬉笑式的文章;面对论敌残暴的行径,他便失去了嬉笑的情绪,而只能给予严斥和怒骂。面对自己所器重的学生“无端在府门前喋血”,他只有痛惜、震惊、愤懑,面对反动当局的暴行,他毅然痛击、怒斥、冷嘲热讽。这是一篇感情深沉的悼文,也是一篇锋芒犀利的檄文。
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也写得情真意切,认为刘女士“称为中国新女性而无愧”“可称全校革命之领袖”。文中也表达了作家的哀痛之情和对自己学生的怜惜。此文最后一段如下:
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与鲁迅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毕竟缺少深情,缺少锋芒,缺少深刻的思辨。不同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精神境界和理论深度,必然表现为其文章的深浅、优劣以至于成败。这里,倒不是说林语堂文章是浅薄和低劣的,而是说,题材相同的两篇文章,鲁迅写得更为精彩。
面对同一题材,不同的作家固然可以采用不同的思想风格和语言风格,而且有时同样能取得上佳的效果,使得文章显得异彩纷呈。但应当注意的是,内容和形式的搭配应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内容和任何形式都能适当搭配的。作家一旦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很难超越它,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不论面对什么题材都统统采用一种固有的风格,那就未必能写出佳作。一个作家应以不同的风格驾驭不同的题材。风格的多样化才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适格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如果用同样一种风格去应付各种题材的写作,那么写出的文章就有高下之分了。前述他与鲁迅面对同一题材而写的那两篇文章之所以给人留下不同的印象,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若“闲适格调”运用不当,就会影响文章的质量。
当然,林语堂也有自己的苦衷,面对当局的暴行和青年的鲜血,他何尝不想严斥和怒骂,但在那文祸惨烈的岁月里,他起初也有锋芒毕露的激昂,后来因为明哲保身,也只有将锋芒收敛了许多,而终于无奈地选择了“闲适格调”。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其自传中写道:“我初时的文字即如那些学生的示威游行一般,披肝露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这显然是指他20世纪20年代收入《剪拂集》的那些小品文。自传又道:“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的‘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在这个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写作者了。也许如某人所说,人人太悲惨了,因此不能不世故圆滑,否则将要闷死。”“这一路的滑口善辩,其中是含有眼泪兼微笑的。”
这无疑是指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采用“闲适格调”所写的抨击黑暗政治和社会弊端的小品文。他对自己文章格调的转变是深感痛惜和无奈的。其实,这种痛惜和无奈,即便有胆有识的鲁迅也不能免除。林语堂所讲的“如某人所说”的“某人”,极有可能就是指鲁迅。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曾对林语堂在其创办的《论语》《人世间》《宇宙风》中提倡“性灵”“幽默”“闲适格调”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不免有些过火,但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批评还是切合实际的。鲁迅对林语堂杂文的“闲适格调”深表理解,他自己在杂文写作中也往往“先行抽去有些骨头”并为此痛惜而无奈。而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之中,“哈哈地”吐闷气者颇多,而“为笑笑而笑笑的”也不少。其实,鲁迅的杂文也并不都是“匕首”和“投枪”,恐怕此类作品尚未占其半数,此外,也有“哈哈地”吐闷气者,也有“为笑笑而笑笑的”,也往往采用“闲适格调”。此种格调虽为林语堂首创,却为众多杂文家所采用,可见此种格调的生命力之强大。
林语堂的“闲适格调”应当肯定;准确地说,应当有条件地肯定。我们经常赞赏“文学的百花园”,这是指文学文体的多样性。其实,就某一种文体来说,也应是一个百花园。比如杂文的写法,除匕首投枪之外,还可以杂谈琐议,还可以针砭讽喻,还可以闲聊神侃,还可以吐闷气,还可以只是“笑笑”,还可以说俏皮话,还可以……
总之,这才是百花园!
(本文参考书目:《林语堂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鲁迅杂感选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刘福智为商丘学院文学院教授;张继忠为商丘学院文学院教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