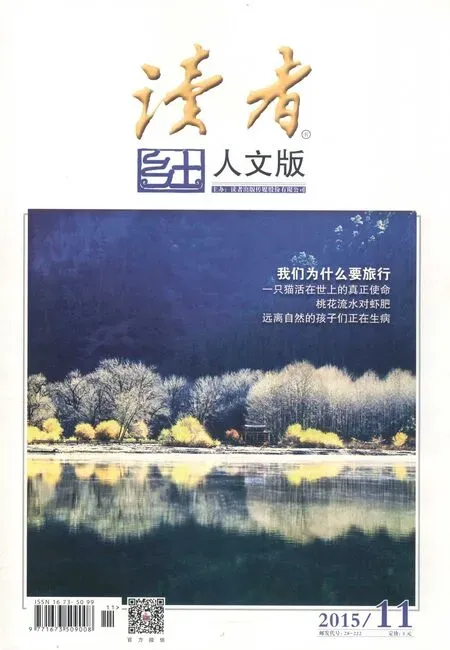韭菜花
文/汪曾褀
韭菜花
文/汪曾褀

五代杨凝式是由唐代的颜、柳、欧、褚到“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我很喜欢他的字,尤其是《韭花帖》,不但字写得好,文章也极有风致。文不长,录如下:
“昼寝乍兴,輖饥正甚,忽蒙简翰,猥赐盘飧。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实谓珍馐。充腹之余,铭肌载切。谨修状陈谢,伏惟鉴察,谨状。”
使我兴奋的是:
一、韭花见于法帖,此为第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此帖即以“韭花”名,且文字完整,全篇可读,读之如今人语,至为亲切。我读书少,觉韭花见之于文学作品,这也是头一回。韭菜花这样的虽说极平常却极有味的东西,是应该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
二、杨凝式是梁、唐、晋、汉、周五朝元老,官至太子太保,是个“高干”,但是收到朋友赠送的一点韭菜花,却是那样的感激,正儿八经地写了一封信(杨凝式多作草书,“韭花帖”却是行楷),这使我们想到这位太保的口味和老百姓的距离不大。彼时亲友之间的馈赠,也不过是韭菜花这样的东西。今天,恐怕是不行的了。
三、这韭菜花不知道是怎样做成的,是清炒的,还是腌制的?但是看起来是配着羊肉一起吃的。“助其肥羜”,“羜”是出生五个月的小羊。杨凝式所吃的未必真是五个月的羊羔子,只是因为《诗·小雅·伐木》有“既有肥羜”的成句,就借用了吧。但是以韭花与羊肉同食,却是可以肯定的。北京现在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或以为这办法来自蒙古或西域回族,原来中国五代时已经有了。杨凝式是陕西人,以羊肉蘸韭菜花吃,盖始于中国西北诸省。
北京的韭菜花是腌了后磨碎了的,带汁。除了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外,就这样单独地当咸菜吃也是可以的。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
从前在科班里学戏,给饭吃,但没有菜。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韭菜花很便宜,拿一只空碗,到油盐店去,给上三分钱、五分钱,售货员就能拿铁勺子舀给你多半勺。现在都改成用玻璃瓶装了,不卖零,一瓶要一块多钱,很贵了。
过去有钱的人家自己腌韭菜花,以韭菜和沙果、京白梨一同治为碎齑,那就很讲究了。
云南的韭菜花和北方的不一样,昆明的韭菜花和曲靖的韭菜花又不同。昆明的韭菜花是用酱腌的,加了很多辣子。曲靖的韭菜花是白色的,乃以韭花和切得极细的、风干了的苤蓝丝同腌成,很香,味道不很咸,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甜味。曲靖的韭菜花装在一个浅白色的茶叶筒似的陶罐里。凡到曲靖的,都要带几罐送人。我常以为曲靖的韭菜花是中国咸菜里的“神品”。
我的家乡是不懂得把韭菜花腌了吃,只是在韭菜花还是骨朵儿尚未开放时,连同掐得动的嫩薹切为寸段,加瘦猪肉炒了吃,这是“时菜”,过了那几天,菜薹老了就没法吃了。做虾饼,以爆炒的韭菜骨朵儿衬底,美不可言。
(吕佳佳摘自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人间滋味》一书)

杨凝式《韭花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