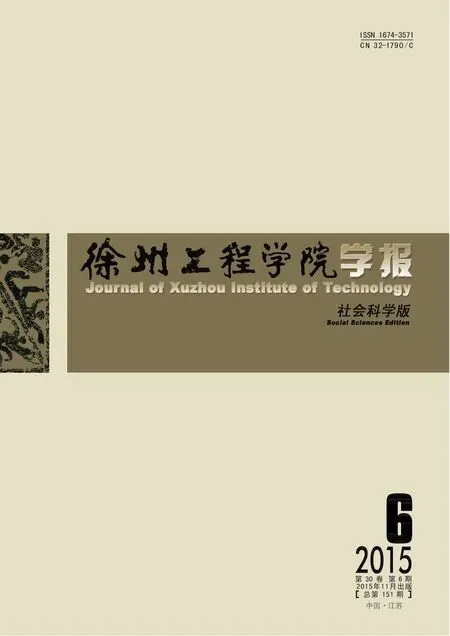困境中的大爱丰碑——评长篇小说《远东来信》
江守义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困境中的大爱丰碑
——评长篇小说《远东来信》
江守义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摘要:《远东来信》借助潘进堂等人二战期间救助犹太孤儿雷奥和谢东泓历经艰难破解信件两个故事的交织发展,通过多种艺术手法对潘进堂、雷奥、谢东泓等人物形象加以塑造,揭示了故事背后的大爱情怀和人性内涵,在当代文学领域树立起一座困境中的大爱丰碑。
关键词:《远东来信》;大爱;困境;人物;人性
长篇小说《远东来信》通过留德学生谢东泓1993年在德国跳蚤市场上淘到的8封远东来信为线索,通过对信件的“文本分析”和“实地认证”[1]60-61,还原了1938年到1945年德国犹太孤儿雷奥在中国上海和河南上蔡历经磨难的故事。但小说的重心不在描写雷奥的磨难,而在展示雷奥磨难过程中所得到的中国人的无私帮助。1938年到1945年,中国正经历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民生艰难,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仍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乃至生命来呵护远道而来的犹太孤儿,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老百姓对犹太人的无私大爱。同时,谢东泓在窘迫的留学生涯中,耗费大量精力,还原雷奥故事的真相,向世人宣告“中国人……不但在乎自己,也在乎别人”[1] 16,展示出另一种大爱。小说通过雷奥磨难故事和谢东泓还原真相故事的平行推进,共同构筑起一座困境中的大爱丰碑。
一
大爱在雷奥磨难的故事中有集中体现。由于纳粹的犹太政策,雷奥一家不得不逃离德国,在前往美国、法国、英国的希望破灭后,中国为他们敞开了大门,大爱由此拉开帷幕。大爱源自无功利的爱心。当何姓签证官“冒着生命危险和撤职风险,私自带出签证章”,在自己家中为素不相识的犹太人秘密签发“生命签证”时,他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他拒绝雷奥母亲表示感激之情的金戒指时所说的话,流露出他的善良品性:“戒指戴在手上是好东西,但压在心上会太沉重”[1]28,和趁火打劫、压低首饰价格的德国店主相比,签证官对犹太人的处境是同情和理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他们提供帮助。这种无功利之爱在小说中比比皆是,王家甫如此,潘进堂如此,潘姨、喜鹊如此,八仙、老纪、桩子也如此,他们不计回报,用智慧、行动和生命让雷奥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大爱有一种责任和担当意识,这在王家甫和潘进堂身上有突出表现。由于买船票的钱不够,雷奥和母亲莎拉来到上海,父亲和姐姐则留在家中,不久被纳粹杀害。王家甫和雷奥一家在德国相识相知,面对颠沛流离的雷奥母子,他认为在上海照顾好他们是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他出谋划策,让雷奥上学,让莎拉开面包店,尽全力照顾他们母子。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秉承德国旨意,准备秘密处理上海的犹太人,王家甫冒险将雷奥送到河南上蔡自己的大舅子潘进堂那里,并机智地让日本人的秘密得以公开。潘进堂对妹夫承诺要照顾好雷奥之后,就有强烈的担当意识。在日本人、土匪、无知村民的眼皮底下,在灾荒、饥饿的包围中,在多次险恶的情境下,他都以保护雷奥为己任,以保证雷奥的身份不暴露为第一要务。大爱是一种无私奉献,这不仅需要无功利的爱心,还需要牺牲的精神。小说中,无私奉献是中国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品质。潘姨为帮助莎拉的面包店,每天起早摸黑,甚至耽误自己的儿子保立上学也在所不惜;喜鹊为了尽可能地让雷奥吃好,宁愿自己吃树叶喝野菜汤,在和雷奥同患疥疮时,宁愿自己不涂膏药而死,也要让雷奥多涂膏药而尽快复原;八仙为保护雷奥,自觉在村头放哨,并让自己的儿子桩子代雷奥而死;老纪也为了雷奥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犹太人莎拉也有自我牺牲精神。在得知上海的犹太人要遭殃的消息,她虽然心理上认同王家甫的逃亡方案,但她“不忍心看到这么多的好人因为这个方案而担当不可预测的风险”[1]147,决定留在上海,只让雷奥一人离开上海,最终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降低了王家甫一家人暴露的风险。
雷奥故事中的大爱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时事艰难,生活窘迫。日本控制下的上海,人们生存不易:孩子游戏的舟山公园,同时也是日本人杀戮中国人的场所;雷奥涂抹日本布告的恶作剧,差一点让他命丧黄浦江;莎拉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也能被杀害。同样是日本控制下的上蔡,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异常艰难:潘进堂等人不仅因为饥荒吃不饱,而且要在高野中尉、伪县长孙宝康、土匪“陈家将”的眼皮底下周旋,冒着杀头的危险来保护雷奥;马兰兰由于貌美,差一点成了高野的女人;老纪呼喊“猴屁股失火了”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私塾先生不给日本人写标语就被活活捅死[1]296……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老百姓之间的相互关爱仍无处不在,这不仅需要善心,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听到县长夫人因为高野而来给马兰兰说媒,孩子们利用恶作剧时所看到的马兰兰的身体,暗示马兰兰不干净,打消了县长夫人说媒的念头;当高野要追查雷奥演戏失败的原因时,老纪以生命为代价的呼喊不着痕迹地救了雷奥;当土匪怀疑潘进堂撒谎要砍他的脚时,喜鹊以和老天爷对话为由让土匪落荒而逃。人们在关键时刻的急中生智,在给读者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读者感到沉重的压抑:环境如此恶劣,人们动不动就有生命危险,虽然用机智躲过一劫,但劫后余生的恐怖仍在。小说虽然通过人们的机智写出了爱的温暖,但充溢其间的,仍是生存的艰难和冷酷的现实。
就谢东泓的故事而言,大爱的表现主要有二:一是人们因信件而感动,二是多方合作,还原真相。就第一点看,随着对信件的翻译和整理,谢东泓转变了淘宝赚钱的动机,一心想弄清信件的内容,想找到雷奥;导师沃尔德教授觉得自己作为德国人,有一种对战争和对犹太人的负罪感,鼓励谢东泓将信件整理出来,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再不要发生这样的战争”[1]217;同学杰瑞让家人在美国帮助查找犹太人的相关资料;汉堡汉学研究所的“狐狸”博士,不仅肯定信件价值和谢东泓工作的意义,还多方提供帮助;汉堡犹太人协会主席霍夫曼女士听了信件的事情便主动提出为谢东泓的“实地认证”提供资助;巴黎的四位犹太老人,尽可能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上海的经历,以帮助谢东泓;上海档案馆的芮玮,更是竭尽全力提供谢东泓所需要的材料。这么多人,为一件已经尘封几十年、与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事情,加以关注,投入热情,施以援手,既是被信件所反映的大爱内容所感动,也是被谢东泓破解信件的大爱行为所感动。就第二点而言,和第一点密切相关,正是由于人们的感动,才使得多方密切合作,最终还原了真相。只不过,第一点是就人而言,第二点是就事而言罢了。这其中,上海档案馆、上蔡外事办和县志办、重庆的民政部门以及汉堡犹太人协会的支持犹为关键:芮玮不仅找到了谢东泓所需要的资料,还在档案馆老馆长的提醒下,找到了王家甫的病历[1]267,为谢东泓的整理工作提供证明;上蔡外事办和县志办查找了一个多月的资料,证实了信件中的地点和人物的确切情况,重庆民政部门提供了保立的消息,汉堡犹太人协会则和雷奥本人取得了联系,这一切,让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和寻找历史真相的人站在一起成为可能,让故事中受助者感受到的无私大爱和现实中故事整理者的爱心交融在一起成为可能。和雷奥的故事相比,谢东泓的故事的困境显然要小得多,但要破解并证实毫无来由的8封信件,对贫穷的留学生谢东泓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困境。困境中的坚持,是良心的坚守,也是爱的展示。
二
一部小说的成功,离不开其中的人物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是小说历久弥新的决定性因素。《远东来信》虽问世不久,但可以预见的是,其中的人物形象如王家甫、潘进堂、八仙、雷奥和谢东泓等将会使小说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果因为题材的原因(第一部写中国人帮助犹太人的小说)而被写进后来的文学史,这些人物也将会在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按照马振方先生的观点,人物可分为扁形人物、尖形人物和圆形人物(其中,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和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一致)。“扁形人物是围绕着单一的观念或素质塑造的”[1]255,其特点在于观念化和特征化,如小说中的高野中尉和伪县长孙宝康,他们从出场到结束都是一副恶人嘴脸,任天放则始终是德才兼备的爱国者形象;圆形人物则不能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他们“宛如真人那般复杂多面”[2]27,其特点在于多面性和复杂性,如小说中的雷奥和谢东泓,他们的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发展;尖形人物其实是最常见的,他们既有性格的多面性,又有一两个特征很突出,“就像几何图形中的各种锥体”[2]35,如小说中的王家甫、潘进堂、八仙,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担当意识,但同时王家甫的机智、潘进堂的坚韧、八仙的风趣也展现了他们性格的多面性。就人物性格的发展而言,扁形人物的性格是不发展的,从一出场就定型了;圆形人物的性格不仅是发展的,而且是变化的,呈现出性格的复杂性;尖形人物的性格是发展的,但发展只是呈现出性格的多面性,性格本身是不变化的,性格虽然有多面性却并不复杂。
《远东来信》中最能体现困境之爱的人物,包括尖形人物王家甫、潘进堂和八仙,尤其是潘进堂,也包括圆形人物雷奥和谢东泓,尤其是雷奥。在雷奥故事中,尖形人物潘进堂是爱的奉献者,圆形人物雷奥是爱的直接受益者;在谢东泓故事中,圆形人物谢东泓是爱的奉献者,圆形人物雷奥由于最终的“返乡”成为爱的间接受益者。无论是爱的奉献者还是爱的受益者,都有最终的指向:跨国界的人间大爱。
潘进堂一开始收留雷奥,只是为了帮妹夫王家甫的忙而已,只答应雷奥在自己家里呆一个月;但一旦承诺,便竭尽所能,挖地窖以备不时之需,教唱戏以传做人之道。由于变故,一个月变成遥遥无期,他仍然矢志不悔,义无返顾地照顾着雷奥,承诺于是成为责任,他要学一回程婴救孤,宁愿自己千辛万苦,也要保雷奥周全。在与雷奥相处的日子里,虽然备尝艰辛,也毫不厌倦,因为在他心理,已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将雷奥当作自己的孩子,“既然是俺的娃,待一辈子也没问题”[1]285,不仅是表达心意的坚定,也是他的真实意愿。正是由于这种自觉意识,他才有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举动: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毅然破天荒地请任天放当雷奥的家庭教师,这完全将雷奥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加上他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雷奥就是他唯一的孩子,这唯一的孩子既然已经学习过,就不应该中断学习;凭着让土匪砍自己的脚也不让雷奥暴露,因为是和自己的孩子本来就应该是共生死的;为对付饥荒而卖唱讨饭,为治好雷奥的疥疮而变卖戏班子的家当,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妻子喜鹊死后,雷奥就是自己唯一的亲人,此时的潘进堂,照顾雷奥不再是自己的意识,而是一种本能,所以在自己嗓子毁坏后,自然而然地要将自己唱戏的功夫传给雷奥,在他的潜意识中,雷奥就应该是自己的传承人。为了雷奥,潘进堂先后失去了老伙计老纪、机灵的戏班子成员桩子和妻子喜鹊,还搭上了他的戏班子,除了自己的生命,他真是付出了一切,但当抗战胜利雷奥要被接走时,他为了让雷奥有一个好的前程,毅然割舍了历经磨难形成的亲情,让雷奥离开自己贫穷的家,亲情至此升华为超越一切的大爱。由承诺——责任——意识——本能——大爱这一过程来看,作为爱的奉献者,潘进堂最突出的特征是勇于担当的意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也有机智、诙谐、暴躁等多方面的表现。性格的多面性使潘进堂成为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
作为一个8岁逃难到中国的犹太小孩,雷奥一开始展现出来的是孩子气的活泼、调皮、聪明、善良,他和小伙伴们在公园里玩捉迷藏,涂抹日本人的布告,起哄要王家甫讲他的恋爱史,指斥“猴子”爸爸打小孩子就是坏人,和保立争论自己在学校乐队的重要性,展现的都是一个孩子的童心;同时,他也有由顺境转入逆境的痛苦,在得知父亲和姐姐遇害后,闷闷不乐;在啃上海的窝窝头时,难以下咽。总体上看,上海时期的雷奥,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小孩。到上蔡后,雷奥由单纯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刚到上蔡,他只是来学戏,和村里的孩子比起来,显得娇气和不懂事:在上蔡的第一顿饭,他只吃鸡蛋不喝碱水汤,以后吃饭时也心安理得地吃别人吃不到的好东西,在大人很累时,仍吵着要练习“跑龙套”,别人稍微说两句就哭,在戏班子吃饭时专挑自己喜欢的肉,平时起床就喊饿。如果和穷苦出身年纪稍大的桩子相比,此时的雷奥展示出来的是一个不能吃苦的少爷形象。在得知母亲遇害后,雷奥似乎突然开窍了,主动喊师傅和师母“大”和“娘”,在潘姨离开时,主动给她唱一段戏,因为自己的母亲已经听不到了;在喜鹊去世后,他长大了,和“大”潘进堂之间慢慢有了默契、有了依恋,他知道给“大”烧火做饭,给“大”擦脸,和“大”说话时说上蔡土话;在自己的作文中,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大”和“娘”、热爱自己所生活的村庄;在即将离开时,他来到桩子、老纪和“娘”的坟前,磕破了额头,对这些因他而去的人,表达歉疚和怀念。但雷奥毕竟是一个犹太小孩,虽然开窍了,长大了,还是不如以桩子为代表的穷苦人家的孩子懂事:母亲去世后,他几乎没有帮助潘进堂和喜鹊做什么事,潘进堂责怪他粗心而踢他一脚,他就三天不理潘进堂;喜鹊去世后,他和“大”相依为命,但“大”累得睡着了他还叫着“热”让“大”给他扇扇子。正因为雷奥是犹太小孩,才不会和少年老成的桩子一样,处处体贴照顾别人,而是理所当然地接受别人的照顾,即使开窍、长大,也不改孩子本性,以中国农村的标准衡量,他是一会儿懂事,一会儿又不懂事,体现出复杂多样的性格特征。这种由单纯——享受——蜕变——复杂的过程,使雷奥整体上成为一个被动的爱的受益者形象,同时也成为一个心存感激、知恩图报的人。
和潘进堂、雷奥相比,谢东泓展现出来的是精明和执着。小说开头写谢东泓在跳蚤市场上的规划,虽然有些夸张,却将上海人的精明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谢东泓的精明在小说中多有体现:他做拿手菜时的功利考虑,他起初破解信件的赚钱动机,日常生活中的精打细算,买阿尔卑斯山牌巧克力的心机,等等。在信件破解的过程中,他的精明逐渐让位于感动,他的私心逐渐让位于爱心。信件中的王家甫形象使他由敬意上升到敬佩,由敬佩升华到敬仰[1]210,他决定将破解后的信件“捐”出去而不再是当初的“卖”出去。这是正面描写谢东泓的感动和爱心。小说第十一章写谢东泓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王家甫、潘进堂、喜鹊、桩子等人焦虑、受苦的不同情形,让他为自己的精明感到惭愧,梦醒后毅然拒绝汉堡犹太人协会的资助,则从侧面写出谢东泓的感动和爱心。被信件内容感动后,谢东泓将破解信件当作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为此辛苦打工,在上海、汉堡、柏林、波茨坦、吕贝克等地奔波,走访信件中提到的诸多地方,在奔波的过程中,他对二战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对信件有了更深刻的感触,明白了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良心”[1]151的过程,在“良心”的驱动下,他利用“文本分析”确定了雷奥呆在上蔡的村庄名称,最终破解了信件,让老年雷奥回到了年轻时曾生活的上蔡,由此展示出他的坚韧和执着,也进一步彰显出他的爱心。有趣的是,在因感动而执着、因执着而愈发感动的过程中,谢东泓仍然展示出他精明的一面,撇开他生活中的一贯精明不谈,他能利用“实地认证”、搜集资料和写信的机会,用自己的执着精神来打动和感染芮玮,逐步发展出和芮玮的爱情,可谓精明之致。在日常生活中的精明——因感动而不再精明——在感动与执着的交互前行中又伴随着精明这样一个链条中,成就了谢东泓的大爱情怀。
三
小说是艺术地展现生活,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的题材内容,更在于它的艺术成就。《远东来信》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突出的有视角、结构和对照手法三个方面。正是通过这些艺术手法,《远东来信》才形象地再现了困境中的大爱丰碑。
视角是观察事件的角度,同时也暗含了叙述者的立场。《远东来信》的视角是传统的全知视角。全知视角的叙述者高高在上,如上帝般俯瞰整个事件的发展和所有人物的行动及其内心活动,并随时对事件或人物发表评论。对一部小说来说,视角的选择几乎是决定性的,就《远东来信》而言,雷奥故事显然是谢东泓根据雷奥过去的8封信件整理的结果,叙述者又根据自己现在的立场对这些整理结果进行加工。如果单纯复述信件内容,即通过雷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叙述他所经历的故事,也是一种选择,但人物视角必然会存在许多晦暗不明的地方(即谢东泓着力破解的地方),这就使信件展示出来的内容不够完整,同时人物视角还带来理解上的偏差。用全知视角,带来的好处是:其一,全知视角的叙述,是对信件相关内容有充分理解后的叙述,叙述者交代了很多信件没涉及到的内容(即雷奥视角不可能知道的内容),这就还原了事件的真相,为读者的理解打开了方便之门。比如说,王家甫和潘进堂计划如何向雷奥隐瞒他母亲去世的消息,雷奥当时肯定是不知道的,即使后来有所了解,也不可能在信件中写得像小说中那样详细。小说详细描写了莎拉如何被杀,凸显了上海的白色恐怖,也决定了雷奥不能返回上海,这直接影响到情节发展;小说细致地展示了王家甫、潘进堂和八仙对话的场景,这一场景既表现了潘进堂慨然救孤的凛然大义和王家甫让雷奥情愿留下来的机智,也刻画了八仙对待面包的郑重态度和举动,还反映了“人间的温暖和无言的亲情”[1]280,这些对王家甫、潘进堂和八仙三个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有重要作用;同时,这一场景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艰难以及八仙心中对延续“香火”的重视,为后文大家不惜牺牲自己来救雷奥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使情节的发展显得合乎逻辑。其二,全知叙述有一个优点,它让叙述者随时将自己的情感和评论夹杂在叙述语流之中,显得很自然,叙述者由此介入故事,从而表达自己的倾向性。表达倾向性的方式很多:或是抒情,例如,针对王家甫辅导雷奥德语,叙述者感慨:“在一个离德国万里之遥的村庄里,在一个寒冷阴暗的农户茅屋内,一个中国人在教一个德国孩子学德语……琅琅的读书声回荡在茅屋内,回荡在中国男人和德国男孩的心间,温暖着院子里寒风中的中国男人,也温暖着门外的中国女人……”[1]299叙述者的感慨表达出对大爱无疆的赞美。或是说明中夹带评论,例如,叙述者对“龙套”的介绍:“‘龙套’在戏台上,大部分时间是静,静静地站着……‘龙套’要静得庄重,静得威严,静得冤屈者慷慨陈词,静得刁痞者语无伦次,静得万民敬仰,静得乾坤朗朗。”[1]236叙述者的说明虽然针对戏里的故事,但“静得万民敬仰,静得乾坤朗朗”的评论又何尝不是在说戏外的人生。其三,全知叙述中的很多内容是对信件内容的补充和解释,而这些补充和解释又得益于谢东泓的努力。这就方便将雷奥故事和谢东泓故事交替展开(这涉及到下文要说的结构),让困境中的大爱在今昔对比中显得更加鲜明。
和视角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对小说题目的理解。从字面上看,接受“远东来信”的人,是德国的音乐教师,说“远东来信”的人,应该是一个德国人,最好是一个犹太人,换言之,就小说题名看,可以设置一个德国犹太人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但小说显然不是如此。小说将远东来信交到一个中国留德学生谢东泓的手里,在谢东泓看来,来自祖国的信件是不会被理解成“远东来信”的(芮玮写给他的信,他不可能理解为“远东来信”,只能作“祖国来信”或“亲人来信”之类的理解)。但他在解读信件的过程中,觉得这些信件意义重大,为破解这些信件,在德国跑了很多地方,牵涉到不少犹太人,尤其是他在柏林犹太人博物馆里看到了一封逃到美国的犹太小孩写的信,信中词句和雷奥信中的词句相像,这又强化了雷奥信件是“远东来信”的概念,同时,对知道这些信件的德国人来说,称呼它们为“远东来信”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小说虽然采用全知视角来叙述故事,但小说以“远东来信”为题,还是暗含了人物视角,即德国人乃至西方人通过“远东来信”如何看待中国的视角,中国人通过“远东来信”如何展示自己的视角。
小说的结构是双线结构,雷奥故事和谢东泓故事两条线索平行推进。小说的主体共16章,雷奥故事和谢东泓故事各占8章,交错展开,雷奥故事的8章内容是叙述者依次对谢东泓破解的8封信件加以组织的结果,谢东泓故事的每一章则是交代破解信件的原由或展示破解的艰难过程。巧妙的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故事又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不清楚第一章谢东泓的故事,就不明白第二章雷奥的故事,不清楚第二章雷奥的故事,就不理解第三章谢东泓的故事……,依此类推的结果,使两个故事表面上是平行发展,实际上是相互推进,最后在“尾声”中两个故事相交,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雷奥和谢东泓走到了一起,形成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就写信的雷奥和破解信件的谢东泓而言,雷奥故事应该再现当事人的主观感受,谢东泓故事应该显示破解者对信件的认识。但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跳出这一窠臼:雷奥故事再现了雷奥在艰难环境下所得到的帮助,其中很多帮助是雷奥所不知道也无从感受的,这不仅突出了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帮助是无私的,而且是不想人知道、不求回报的,这是真正的大爱情怀。谢东泓故事展示了破解工作的艰难和破解者的感动,破解者的感动自然是由于对信件的认识而感动,破解工作的艰难则暗示出另一种爱的存在,因爱而感动,又因这感动而付出另一种爱,这是谢东泓故事的高明之处。从结构上看,小说在主体的16章之外,还有“引子”和“尾声”,“引子”仅仅摘录三位作家的名言,与故事暗合,无关痛痒。“尾声”则花了一定篇幅让两个故事的主人公见面,让雷奥唱起他心中的歌,写得很感人,让小说爱的主题在此得到升华。但就结构而言,“尾声”中的“大团圆”让人疑惑,因为在谢东泓故事中,老年的雷奥一直置身事外,一个让局外人都感动的故事,故事的当事人几十年来难道都无动于衷?虽然“尾声”说雷奥在50年内写了60封寻亲信,但这仍然是苍白的,既然谢东泓都能最终破解信件,写信的雷奥还能找不到自己当年住的地方?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同时,小说的双线推进结构与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类似,但稍有不同的是,后者的两条线索基本上不是相互依赖、交织发展的,但后者的长处是,两条线索的主人公都是梁君璧(分别是青年和老年),她深入骨髓的“回回”情结在两条线索中是一贯的,且对推动故事发展都起到关键作用,“回回”情结成为《穆斯林的葬礼》情节结构的内在动力。以此衡量,《远东来信》在结构的内在动力上有所欠缺,“犹太人”对故事的发展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雷奥故事中提到的“犹太人特别抱团”[1]139是个例外)。雷奥是犹太人的构思,当然可以展示中国人在二战这一特定背景下的大爱情怀,但即使雷奥不是犹太人,王家甫、潘进堂等人的形象也丝毫不受影响。
就小说的具体手法而言,对照是比较突出的。小说中的对照情形很复杂:或是物件对照,雷奥单方面的信件,反映出潘进堂等人的担当与执着,在中国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中国人和德国犹太人之间的爱的赞歌;谢东泓和芮玮之间的通信,也反映了谢东泓的担当与执着,在中德两个国家的土地上,传递着两个中国人之间的爱情。或是不同场景的对照,何姓签证官无私帮助犹太人的场景,与德国人抢劫犹太人财富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对照。或是相似场景的对照,在上海的大街上,很多上海的街坊邻居帮助落难的哈雷尔;在汉堡的地铁里,不同肤色的人都在买谢东泓卖的报纸。或是现实和内心的对照,如“虽然外面的世界饿殍遍野、寒意逼人,但王家甫要让潘家院子里的三间茅屋风调雨顺,春暖花开”[1] 290。或是同一地点不同事件的对照,1940年的舟山公园,既是雷奥等孩子们的游戏乐园,同时也是日本人杀戮中国人的场所。或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照,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比较含蓄,“悲伤藏着,兴奋也藏着”[2]373,中国人则认为“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1] 298-299。或是同一国家不同时间的对照,40年代的纳粹残酷屠杀犹太人,70年代的勃兰特在波兰对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或是同一事件不同时间的对照,如日军寻找雷奥,50年后的谢东泓也寻找雷奥。或是人物同一举动之间的对照,少年雷奥“泪流满面地”唱着“小苍娃”是由于伤心[1]340,老年雷奥在坟前“含泪高唱”《在东方》是由于感动[1]459……小说中几乎随处可见的对照,是从不同角度来歌颂人类的爱,尤其是中国人对犹太人的爱。
四
从小说的写作看,作者1995—2010年探访相关地方,为写作准备素材,到2013年写成,历时18年,18年写一部小说,在当今文坛可谓罕见。从作者花15年时间搜集资料来看,作者应该是有抱负的。从相关报道看,作者曾留学德国,经常听他国学生说“中国军民只是为自己而战”,“中国不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这让他耿耿于怀。1995年,他偶然从德文报纸的夹缝中看到了二战时期上海曾收留三万名犹太人的消息,他便有了为中国“正名”的想法,开始搜集资料[3]。经过18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远东来信》,填补了文学领域此类题材的空白。对此,作者很自信,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以文学手法来介绍50年前发生的这段真实的历史,对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作用说不定比其他书籍还要大!”[1]381“有中文的,后面就会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希伯来文的、日文的……”[1]452
从小说的内容看,作者的用意在于宣扬中国人曾不计代价地救助过犹太人,有跨国界、跨民族的大爱情怀。小说第四章提到雷奥刚到上海时就已经知道“到目前为止,有接近三万人生活在这里”[1]69,小说第五章又通过芮玮的口说出“三万多犹太难民真真实实地在上海生活了几年”[1]105。王家甫、潘进堂等人救助雷奥的故事只是中国人帮助犹太人的一个缩影。王家甫、潘进堂等人对雷奥的帮助是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谢东泓在巴黎走访4位曾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人,他们的回忆是温馨的,50年后他们仍记得中国人对待犹太人的宽容态度,“没有看到一起中国人对犹太人动手动刀的事”[1] 384。中国人在国难当头时刻的宽容和大爱,让曾经呆在中国的犹太人“刻骨铭心”[1]385。翻看历史,当全球笼罩在纳粹的阴影之下,当犹太人在全球逃难时,中国曾庄严承诺收留犹太人,1939年,时任行政院长兼财长的孔祥熙曾致电国民政府:“无国籍之犹太人之情形特殊,我国素重人道……吾人理应力之所能,予以协助”,中国政府表示:犹太人可以不用签证,直接来中国避难[4]。在这种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的反衬下,那种“中国不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的言论完全是信口雌黄,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小说着力刻画潘进堂等人的无私大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包容和担当,正如作者所言:“创作本部小说的过程,是我对家乡、对民族重新认知的过程。我的家乡虽然世代贫瘠,但她和彼岸的城市一样美丽;我所在的民族虽然历经苦难,但她和彼岸的其他民族一样心胸辽阔,大爱无声。”[5]
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小说被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本文所引徐树铮诗词文章,均见于《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中之《视昔轩文》《兜香阁诗》《碧梦盦词》诸集中,不另一一注明。。但细看小说,小说的用意不在犹太孤儿雷奥的身上,而在王家甫、潘进堂、八仙、喜鹊、任天放等人身上,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人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别人强加的结果,而是源自他们的善良本性。小说在宣扬大爱的同时,也歌颂了人性的纯真和美好。
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并通过社会心理折射出某种人性。20世纪80年代曾就人性问题展开大讨论,讨论达成共识:人性具有动物性、社会性和超越性。所谓动物性,是说人性包括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等动物性生命体征。《远东来信》提到老怂在大饥荒的艰难中,想通过告发雷奥来换“两个窝头”[1]396,毛妮子因为想吃糖豆告发了雷奥,这些都是人性动物性的正常体现。所谓社会性,是说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雷奥对母亲的依恋、雷奥和王家甫、潘进堂、喜鹊等人的精神上的交融,八仙和潘进堂的默契,马兰兰的善良,高野中尉的残忍,孙宝康的为虎作伥,都是人性社会性的表现。但小说最用力的,还是对人性超越性的关注。所谓超越性,是说人性还存在超越动物性和社会性的一面,有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有一种人文理想。王家甫对莎拉和雷奥的帮助,不仅是由于相知相识,更由于一种爱的悲悯情怀;潘进堂倾其所有地抚养雷奥,为的是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喜鹊用生命来呵护雷奥,是由于她和雷奥之间已由非血缘关系发展到本能的亲情关系;八仙为雷奥用心良苦,不惜牺牲桩子来救雷奥,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任天放对雷奥的精神指引,既是中国人的良心在起作用,也是为了塑造雷奥健全的人格。
需要指出的是,雷奥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其人性的展示是单纯的,善良者极其善良,恶劣者极其恶劣,这种善恶明显的人性描写可以使小说在善恶对比中来展示普通中国人的无私大爱,但略有遗憾的是,人性描写的单纯,遮蔽了人性的复杂。不过,雷奥故事中的个别小角色和谢东泓故事中的一些人物,人性的复杂得以呈现。老怂等人因为桩子偷吃庙里的窝窝头,要剁手加以惩罚,按住桩子手的汉子说:“孩,闭上眼,咬紧牙!”[1]372,寥寥数语,将他的关切之情表露无遗。一边要剁一个孩子的手,残忍!一边是提醒孩子如何承受,温情!这种残忍和温情的交织写活了旧中国农民的善良和愚昧。谢东泓精明能干,会打小算盘,但被雷奥故事感动后又“犯傻”,开始不计报酬、不遗余力地投身到真相的寻找之中,既精明又犯傻的人性展示,既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也表达了他对爱的感动;杰瑞既有美国人的优越感和对中国人的偏见,有些高傲,又能尽力帮助中国人谢东泓,显得热情,高傲和热情的交融,再现了美国当代青年的真实状况。《远东来信》对人性描写的简单或复杂,既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也出于作者表达爱的需要。展示中国农村人的人性简单,既是事实,也是为了集中刻画中国人的高贵品质和大爱情怀;展示当代青年的复杂人性,既体现了当代社会和生活实际情况,每个人都为寻找真相贡献力量,又体现出爱的力量和感染。正是由于雷奥故事中的爱的精神,才让不同国别的很多人投入其中,真正表现出大爱无疆!
总之,《远东来信》选取中国人帮助犹太人这样一个填补空白的题材,来刻画人物,通过多种艺术手法,揭示了故事中的大爱精神和人性内涵,在当代文学领域成功地树立起一座困境中的大爱丰碑。
参考文献:
[1]张新科.远东来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马振方.小说艺术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郑晋鸣,陆金玉.张新科:一位大学校长的《远东来信》[N].光明日报,2014-12-11(3).
[4]邓虹.人性价值追忆的涉渡浮木——评张新科长篇小说《远东来信》[N].文艺报,2014-09-17(2).
[5]高秀川.《远东来信》:另一种救赎[N].中华读书报,2015-03-04(11).
(责任编辑蒋成德)
A Monumental Work of Love in Plight:
Comments on the Novel ofLetterfromtheFarEast
JIANG Shou-y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Anhui, China)
Abstract:Letter from the Far East revealed the great love and humanity connotations through the interwoven descriptions with the rescue of Reo,a Jewish orphan,by Pan Jintang in the World War II and Xie Donghong's deciphering of the letter.The creation of the characters of Pan Jintang,Reo and Xie Donghong etc. established a love monument in plight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Letter from the Far East; love; plight; character; human nature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6-0071-07
作者简介:江守义(1972- ),男,安徽庐江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小说叙事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