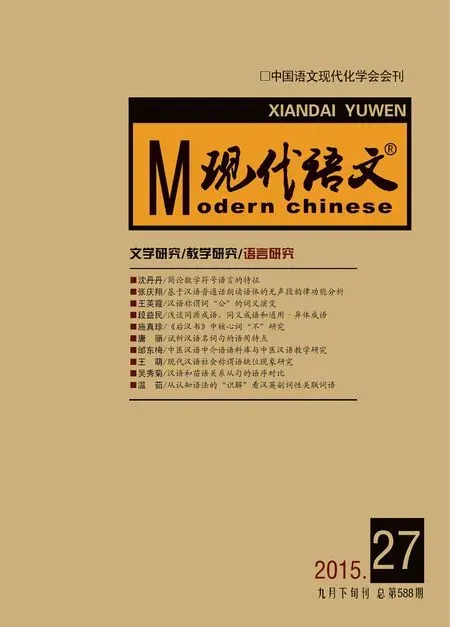对奥古斯丁“符号”思想的解读
□吴晓峰
对奥古斯丁“符号”思想的解读
□吴晓峰
人类思想史上对符号集中深入的思考,往往发生在文化转型期。中世纪伟大思想家奥古斯丁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论基督教教义》和《忏悔录》里对符号的基本概念、符号与事物的关系以及符号的多义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代表了早期基督教时期人们对符号的思考,也是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历史源泉,在符号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奥古斯丁 《论基督教教义》 《忏悔录》 符号 符号学
20世纪初,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提出,得到众多学者的响应,并影响了整个思想界的发展。不过,事实上在此以前,符号学有一个漫长的潜学科阶段:作为符号学核心思想的符号及其意义的思考早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童年——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产生,贯穿了整个中世纪、近代直至现代,并将继续指向未来。这是因为符号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表达单位,代表着人类精神构造和物质构造的基本元素;一旦人类思想出现困扰和怀疑,势必回到这个基本点,重新进行思考。所以在人类思想史上,对符号集中深入的思考往往发生在思想转型期,20世纪符号学的蓬勃兴起就是一个明证。而在1500多年以前,人类也同样经历着一场政治、思想上的大动荡,历史摇摇摆摆地从古代进入中世纪。伟大思想家奥古斯丁(Augustine),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代表了早期基督教思想的最高成就。作为神学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他同样对“符号”(sign)有着强烈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思考,相关论述集中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论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和《忏悔录》(The Confessions)中。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理论论述,后者则更多地结合了生存体悟。本文将对奥古斯丁有关“符号”的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并讨论其与现代符号学思想的关联。
一、符号的基本概念
艾柯指出“符号学应当被看作是对记号概念进行的理论研究”[1](P45),罗兰·巴特也提出“我们可以把符号学正式的定义作记号的科学或有关一切记号的科学”[2](P12);毋庸置疑,“符号”是符号学的核心概念。然而,不同学者对“符号”有不同的界定,此外还有许多词表达着符号的类似意义,如表征(symbol)、征兆(symptom)、表达(expression)和标记(index)等。那么奥古斯丁关于“符号”的定义是怎样的呢?
《论基督教教义》:“……我所谓的符号:它们即用作表示他物的事物。”(…what I call signs:those things,to wit,which are used to indicate something else.)[3](P625)
《论基督教教义》:“符号是这样一种事物,它超越其在感官上造成的印象,并产生另一事物进入内心,作为其自身的一种结果。”(A sign is a thing which,over and above the impression it makes on the senses,causes something else to come into the mind as a consequence of itself.)[3](P636)
从这两个定义来看,奥古斯丁的符号的第一层属性即它的物质性。符号首先是一个事物,作为物质的存在,它必须有一定的外在形式。以奥古斯丁关注的语词符号(signs of word)为例,在口语中它以声音(sound)为形式,但声音一接触空气就随即消失了,因此为了永久的保存下来,于是人们使用字母(letter)作为语词的书面形式。因此语词符号首先是声音或字母。但符号又不同于一般的事物(thing),作为符号的事物必须具有指示的功能,它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反映是另一事物。例如:看到烟,如果人们获得的不是关于烟的知识,而是由此知道了产生烟的火,这时烟就成为火的符号。因此,奥古斯丁的符号的第二层属性是复杂的心理效果,即“超越其在感官上造成的印象,并产生另一事物进入内心”。符号既是一个物质对象,又是一个心理实体。当这种观念在1500多年后被索绪尔明确提出时,被认为是一种深刻的见解,而事实上它在早期基督教时期就已经萌芽。此外,现代符号学关于符号就是“代表另一物的某物”的这一普遍看法也早被奥古斯丁明确化了。
人们为什么要使用符号?符号为什么会充斥人们的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这是由符号的功能决定的。还在吮乳阶段,“逐渐我感觉到我在什么地方,并要向别人表示我的意愿,使人照着做;但是不可能,因为我的意愿在我的身内,别人在我身外,他们的任何官感不可能进入我的心灵。我指手划脚,我叫喊,我尽我所能作出一些模仿我意愿的表示。这些动作并不能达意。别人或不懂我的意思,或者怕有害于我,没有照着做,我恼怒那些行动自由的大人们不顺从我,不服侍我,我便以啼哭作为报复。”[4](P8)当婴孩开始呀呀学语的时候,一方面凭借天赋的理智,“用呻吟、用各种声音、用肢体的种种动作,想表达出我内心的思想”,另一方面“听到别人指称一种东西,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我便记下来,我记住了这东西叫什么,要指那东西时,便发出那种声音”,并通过“一再听到那些语言,按各种语言的先后次序,我逐渐理解它们的意义,便勉强鼓动唇舌,借以表达我的意愿”[4](P11-12)。现代语言学发生学研究会很高兴看到奥古斯丁这段儿童习语的回忆的。一方面对儿童语言的观察研究是语言学家了解早期人类掌握语言工具的重要途径,奥古斯丁的回忆无疑是一个可供分析的个案。虽然这是他成年后的回忆之作,但与后来人们对儿童习语的观察结果是基本吻合的。另一方面奥古斯丁的论述与基督教《圣经》记载的事物命名乃是“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不同,他侧重的是人类后天对于已命名的事物的掌握过程,进而更突出了人类交流意识的主动性。
据奥古斯丁的回忆,在呀呀学语的儿童使用的符号那里已经出现了自然性(natural)符号和惯约性(conventional)符号的区别。诸如凭借天赋理智来表达心愿的呻吟,各种声音和肢体动作是一种自然性的符号,它们更多地与自然的生理反应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暗示。与这种符号相对的惯约性符号是指“生物出于表达的目的尽其所能的相互交换他们的内心感受、他们的知觉或者他们的想法的符号”[3](P637)。这种符号的掌握有赖于后天的学习和模仿。其过程可概括为:记忆出场事物——记忆他人赋予事物的符号——事物、符号的反复对应——记忆符号所指称的事物。如果将《圣经》中亚当任意命名事物的故事和奥古斯丁符号习得过程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符号学某些观念的雏形,即语言符号是先验任意的和后验非任意性的,并且“在人类学的层次上,在类比性与非理据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性:在使非理据性自然化和使理据性合理化(即文化化)时有双重的(互补的)倾向”[2](P144)。
另外,奥古斯丁还根据符号与所指事物的紧密程度做了另一种划分,即专有(proper)符号和譬喻(figurative)符号。当符号被用来指称它们预计所指的对象时,它们是专有的;而当我们用专有的符号表示的事物来表示其他事物时,符号是譬喻的。“譬喻的符号”的观念对现代符号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是符号学的对象由语言学进入其他文化领域的前提,因此现代符号学又被称作“记号譬喻学”(sémiotropie)。专有符号和譬喻符号的划分还表明,在符号和事物之间不仅存在简单的一对一关系,还可能存在更复杂的对应关系。奥古斯丁对这种复杂的对应关系进行了丰富的探讨,并肯定这种复杂性是“有用的”。
二、符号与事物的关系
奥古斯丁明确区分了符号与事物。符号是一种事物,但并非所有事物都是符号,只有当该事物用来指称他物时,它才有可能成为符号。与现代“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观念不同,奥古斯丁的符号更多是一种能指成分的事物。与能指、所指概念相对应,奥古斯丁使用的是“符号”与“事物”。而就符号而言,奥古斯丁虽然也讨论了烟示火、人体肢体动作等符号,但他认为在符号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语词,因此对符号与事物关系的考察又进一步具化为语词及其意义的关系考察。
奥古斯丁经常用器皿和所盛物来比喻语词和意义。他说文辞是“贵重精致的容器”,里面盛的是“迷人的酒”;辞令是“器皿”,而知识是“菜肴”;“总之,智与愚,犹如美与恶的食物,言语的巧拙,不过如杯盘的精粗,不论杯盘精粗,都能盛这两类食物”[4](P72-77)。与索绪尔“一纸两面”的比喻不同,奥古斯丁把语词和意义看作两个相互独立的事物。酒杯不盛酒还是酒杯,并且具有欣赏价值。因此,尽管奥古斯丁不相信福斯图斯的讲演中包含真理,但他仍可以赞赏他出色的辞令。这其中似乎包含着某种类似20世纪形式主义的观点,即对形式独立艺术价值的肯定。
奥古斯丁论符号与事物的可分割关系,真正目的与其说是肯定符号的独立价值,毋宁说是为讨论事物可以不假语言符号或身体动作而由光照传递到人的心灵设定前提。在《论教师》中谈到学习语言意义的过程时,他说:词语的意义在于它们所指示的事物,但在语言交流过程中,“我们应该把握与记住给予词语意义的事物。对事物的把握,依赖的不是词语,而是我的眼睛。”[5](P151)而与眼睛相关的力量是“光照”。因此,语词的作用在于提醒心灵注意它们所指示的事物,但这种提醒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不通过任何符号,以显示自身方式发生于我的心灵的事物何止一两件,而是成千上万件”[5](P151)。这无异于说仅靠光照就可以创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而相对于这种作为本源的光而言,符号只不过是可供取用的工具罢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奥古斯丁主观上否定了符号在人们把握事物中的作用,或者说否定了符号的认知价值。
尽管如此,奥古斯丁理想中的符号仍然是指称事物的理想工具,对于福斯图斯的演讲,“总抱着一种空洞的想望——我所忽视的内容,随着我所钦爱的辞令一起进入我的思想中。我无法把二者分别取舍。因此我心门洞开接纳他的滔滔不绝的辞令时,其中所蕴涵的真理也逐渐灌输进去了。”[4](P89)这再次表明符号在人类认知事物的过程中或许可以缺席,但在人类思想的交流和传承中,信息的发送和接收中,符号是不可或缺的。思想一经产生进入交流的过程,它就不可能天马行空,而必须借助符号作为载体得以保存。
符号的交流功能依赖于它的惯约性,而惯约性的实现依赖于人的记忆。因此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用了整整一章(第十章)对记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首先将事物分作几类——可被感官接受形成影像的事物、抽象的知识和内心的情感——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贮藏在记忆之库中:“我记忆的无数园地洞穴中充塞着各式各类的数不清的事物,有的是事物的影像,如物质的一类;有的是真身,如文学艺术的一类;有的则是不知用什么概念标识着的,如内心的情感……我在其中驰骋飞翔,随你怎么深入,总无止境……”[4](P201)接着,他论述了记忆的过程:“事物先在场,记忆然后撷取它们的影像,使我能想见它们,如在目前,以后事物即使不在,我仍能在心中回想起来。”[4](P200)而他把这一过程形象地比作食物的吸取和反刍。只是这里的食物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精神粮食。然后他进一步肯定了记忆在人的思维活动中的地位:“这是由于人的思想工作有三个阶段,即:期望、注意与记忆。所期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4](P255)通过记忆,符号与各类事物的联系建立起来,并成为人们思想工作的工具。在其他论著中,奥古斯丁还指出阅读书写的知识即语法“对于消除对符号的无知是必要的”[3](P641)。“语法是一门支持并规整言语的学问”[6](P53),它是对语词符号的惯约性理论的系统表述。人们对语法知识的学习同样是通过有意或无意的反复记忆来实现的。因此,记忆对于掌握符号,使用符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神学家的奥古斯丁,他对符号的论述决不仅仅是语文层面的,他最终指向对基督教经典的解释和宣扬。而符号与事物既可分割又相关联的观点,为他主张的《圣经》文字的多义性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三、符号的多义性
在《论基督教教义》中,奥古斯丁开章明义:“所有关于《圣经》的解释都有赖于两件事:探求正确含义的方法和含义探明后使其被知晓的方法。”[3](P624)前者涉及记事的真假,后者涉及作者的本意。《圣经》所载事物的真实性在虔诚的基督徒眼中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对于《圣经》的解释仍有成千上万种,这主要是对作者的本意存在不同的理解。
摩西的本意、处理文字的方式是天赋的,是主的意志的体现,因而是不容质疑的。人类不能通过符号完整地把握《圣经》的意义,而只能做只言片语的发挥,原因之一是人的认知能力存在缺陷,因而可能产生对《圣经》的错误释义。有两种因素妨碍书写文字的理解:不认识的符号(unknown signs)和有歧义的符号(ambiguous signs)。歧义的符号又可能是直接的(direct)和比喻的(figurative)。不过,这些因素不足为惧,人们可以通过学习新的符号,或者留意上下文、比较多个译本和参考原始用语来克服。但即使是认知能力再完备的人也不能说自己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因为作者的原意本来就是多义的。
奥古斯丁是这样解释天主通过摩西表现的意图的:“你的真理既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某人的,而是我们全体的;你公开号召我们来分享你的真理,你还严厉地警告我们不要独占真理,否则便要被剥夺真理。谁把你提供给我们共同享受的东西占为己有,以共同的东西作为私有,势必因私而废公,也就是舍真理而就谎言”[4](P280);因此,《圣经》就选用了一种合适的表达思想和修辞选句的方式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使尚未领会天主如何创造天地的读者也不能说我的文字超过他们的能力,而具有理解能力的读者,能在你仆人的寥寥数语中不放松一字,找到通过深思便能出现的各条真理”[4](P281);“譬如一股泉水,衍为许多支流,灌溉了大片土地,泉水在狭窄的泉源中比散布在各地河流中更加洋溢澎湃,同样传达你言语的人所作的叙述,供后人论辩,从短短几句话中流出真理的清泉,每人尽可能汲取真理的这一点那一滴,然后再加发挥,演出鸿篇几巨著”[4](P282)。简而言之,这是一种“词近旨远”“言简意赅”的表达。在奥古斯丁看来,这种文字是天主的智慧的体现,在现代人看来这正是《圣经》的魅力所在:它省略掉多余的东西,表现出晦暗不明的,甚至是模棱两可的主题,并且它用未说出的东西来引诱我们,使我们很自然地被引导着去发现它们。借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典文化的一个可能的定义是迫使我们为自己而思考,因此,它不再为某一世纪所独占,而是属于一切心灵了”[2](P33)。但“词近旨远”“言简意赅”,具体而言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这有赖于对符号与事物关系的把握。
前面已经论及了符号与事物之间除了简单的一对一关系,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一对多和多对一。就前一种关系,奥古斯丁明确指出“同一个语词并不总是表示同一个事物”[3](P666)。譬如当它是一个比喻的符号时,它借以表达的词语往往是从一个与之相似或关系密切的事物那儿借来的。由于事物可以有多种方式显示出与其他事物的相似,我们就不能假设这样一条规定,即一种事物在此处用比喻表示的意义在其他地方也都适用。因此,一种事物它在这里表示一种事物,在那里表示另一种事物,那么它就能表示意义相反或是有差别的事物。同样的,其他事物的意义也不是单一的,根据其与事物的联系来看,它们中的每一个表示的不只是两个,有时甚至是几个不同的事物。例如,同一个词“影响力”(leaven),天主可以在此处表示好的意义,也可以在彼处表示坏的意义。因此,对于《圣经》的解释,我们不能把符号具有的一个意义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意义用在所有的地方,而必须通过上下文去判定它究竟是直译的符号还是比喻的符号,作为比喻的符号它又是以何种相似方式表示他物的。
对于多个符号与一个事物的对应关系,奥古斯丁没有专门论述。但是在谈《圣经》的翻译时有所涉及。对于相同的意义,不同的民族会选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由于翻译者认识的局限,有时选用的符号并不能表达《圣经》原意的完整性和同一性。因此,对这多个符号的相互比较,以及对原始用词的参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解释《圣经》的片面性。
在奥古斯丁看来,正是借助符号工具的特殊性,“独一无二的天主通过摩西,使《圣经》配合后世许多读者,并使读者看出种种不同的,但都正确的解释”[4](P286)。这种看法,蕴涵着某种现代主义明确倡导的一种多元主义思想。除了天主拥有独一无二的同一的完整的思想外,其他任何人的解释都是片面的,但又同为正确的。因此,每个人都能够在《圣经》中产生各自对事物所具有的正确见解,但决不应以为只有自己才表达了正确意义,而排斥其他与己相异但也同样正确的见解。同样的,现代解释学也主张每个读者都享有对文本解读的平等权力,对一个文本意义的完成依靠不同见解的对话交流。不同的是现代对话主义思想认为这种对话不仅发生在不同读者之间,也发生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即具体到《圣经》文本的阅读,《圣经》意义的完成不是实际作者天主独立完成的,而是天主和他的仆人们共同实现的。但这种看法放到基督教时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把主和他的仆人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讨论,将主不为主,仆不为仆,这无疑是对神圣天主的亵渎。因此,在解释《圣经》这部在西方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文本时,奥古斯丁时期虽然已经有了多元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仍坚持了作者是解释的唯一权威。故而现代主义作为传统思想的反动,由尼采首先提出“上帝已死”,进而“作者之死”才成为可能。
通过梳理奥古斯丁对符号的阐述并对比现代符号学思想,我们看到,发生在1500多年以前早期基督教时期对于符号的理解已经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深刻性。但也要看到,这个时期对符号的认识只是神学思想的附庸。因为符号学首先是语言学的附属物。从整个符号学思想史来看,符号的研究几乎与语言的研究同轨。直到20世纪,符号学才从语言学中独立出来。而在奥古斯丁时期,语言学自身尚不具有独立地位,它和哲学、神学、修辞学结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奥古斯丁的符号学思想的两大倾向:1.神学倾向。对符号进行讨论最终是为了证明天主的神圣和权威,是为了对《圣经》进行解释和宣扬。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神学符号学思想。2.语言学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奥古斯丁对符号的考察还局限在语言符号中的较低层次——语词;而现代符号学的对象不仅已由语词走向了句子、篇章,更由语言符号走向了其他文化符号。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之复杂、研究方法之丰富,已迫切要求符号学从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但饮水思源,我们仍要充分肯定奥古斯丁等早期思想大师关于符号的思考对今天符号学的成熟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1]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上海:三联书店,1988.
[3]Augustine.On Christian Doctrine[A].Encyclopedia Britannica[C].Chicago:Britannica Company,1982.
[4]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奥古斯丁.独语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吴晓峰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