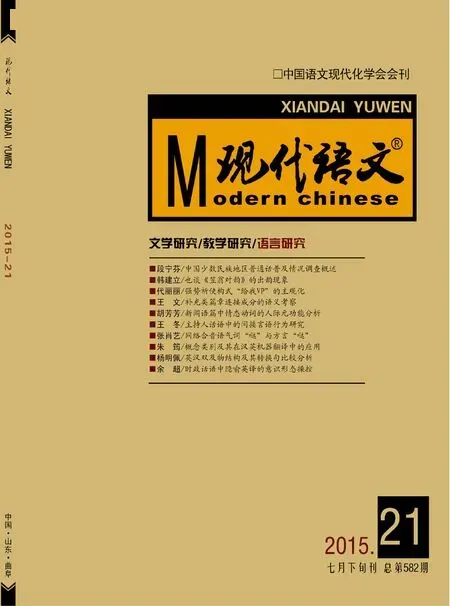新闻叙事隐喻研究
□辛 媛 刘晨红
新闻叙事隐喻研究
□辛媛刘晨红
本文以新闻叙事隐喻为研究对象,从语言结构、新闻叙事语言的生成过程以及新闻叙事隐喻的评价功能三方面,分析了新闻叙事隐喻所表达的主观意义和倾向性。分析发现,新闻叙事隐喻可以填补明显话语的语义空洞,帮助叙事者言说意义,传达深层内涵。
新闻叙事隐喻意义
一、新闻叙事隐喻相关概念简述
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认为,“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没有叙事的民族,从来不曾存在过。”[1]可见叙事广泛存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叙事。根据《叙述学词典》的定义,叙事指“一个、两个或多个叙述者向一个、两个或多个受述者交流的一个、两个或多个或真实或虚构的事件的再现。”[2]由定义可见,叙事的构成要素包括数量不定的叙述者和受述者以及性质不限的事件,叙事的方式是“再现”。其中,事件是叙事的核心,无事件也就无所谓叙事。既然叙事的方式是“再现”而非“还原”,原本客观自示的事件一旦经过叙事者的“再现”,那么“当作者通过选择名词、动词、副词和形容词进行描写时,他实际上是对读者说话,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看待某些人物或事件。”[3]也就是说,叙事语言被叙事者赋予一定的意义。
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虚构的文学作品之中,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研究范围也有所扩展。新闻作品作为一种不同于文学作品的特殊文本,进入叙事学研究的视野。因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新闻就是媒体(叙述者)向受众(受述者)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而叙事是报道新闻的主要方法。因此,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这种活动,就是“新闻叙事”[4]。再现新闻事件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就是“新闻叙事语言”,它是再现新闻事件的工具和场所。
新闻报道讲求客观,但却是一种有倾向、有“意义”的客观。梵迪克认为,“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理性的社会事件的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设定的意识形态。”[5]我国学者李彬也认为,“(新闻)话语没有单独的作者,它只是一套隐匿在人们意识形态之下,暗中支配着人们的言语、思想及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与潜在机制。”[6]事实上,这种“重构”与“支配”所蕴含的意义在新闻叙事语言的词汇、句法、篇章以及修辞等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这是由新闻叙事的特殊性决定的。从新闻叙事文本建构的微观层面来看,新闻叙事隐喻是帮助叙事者进行“重构”与“支配”的手段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思维,隐喻的语言形式产生于隐喻性的思维过程,是隐喻思维的外在表现。因为从本质上讲,隐喻不只是一种表面化的语言现象,而是存在于人脑中的思维和认知现象。束定芳先生认为,“它(隐喻)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从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7]因此新闻叙事隐喻是叙事者为了取得特定的认知效果而运用隐喻思维的外化表现。
二、语言内部结构为新闻叙事隐喻传达意义提供前提条件
从语言的内部结构而言,能指和所指间的语义空间是新闻叙事隐喻生成并传达意义的前提。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概念和音响的结合叫作符号,我们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8]“能指”是由语言声音、形象等物质性体现的客观成分,组成文本的表达方面;“所指”是被表达的主观意义成分,组成文本的内容方面。但是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并非完全一一对应,“所指”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和引申性。当语言符号获得表意性时,就获得了意义的延展性,即“本义与引申义”,或者称为“字面义与隐喻义”。例如“松、竹、梅”的字面义指“一种特定的植物”,而隐喻义则引申为“富有超越性的气质、傲骨和精神”。
新闻叙事语言由一系列符号排列组合而成,即由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构成。所指作为符号的意义,具有无限的延伸性,也正是这种延伸性使得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富有张力的语义空间。当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出现裂隙,即所谓“指称与命名”“意义与指涉”发生了“争吵与分裂”时,就产生了隐喻义。所以说,语言的隐喻义产生并存在于“能指”与“所指”意义的空白、断裂之处[9]。因此,新闻叙事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语义空间是隐喻生成并传达意义的前提,这是由语言的内部结构决定的。
新闻叙事语言中的“风雨”一词,若其能指与所指重合,即无隐喻用法时,它就是指自然界的风雨现象。如“老人在街边摔倒,路人围圈帮挡风雨”(新浪网,2014-11-26);但在“安妮·海瑟薇笑对风雨活出精彩”(凤凰网,2014-11-28)这一新闻标题中,“风雨”一词的能指与所指出现语义的空白与断裂而产生深层的隐喻义,它可以表达人经历的苦难及人内心情感的波动。事实上,这样的隐喻关系反复运用,隐喻义已经固化为词义的一部分,从而凝结为一种预存单位。在新闻叙事语言中,更引人注意的是词的新义是由隐喻方式所赋予的语言现象。如“毛大庆用什么来洗刷商业的‘尘埃’”(新浪网,2015-03-09),作者用引号将“尘埃”标记为隐喻关系——商业的“尘埃”即商业盈利精神,毛大庆用独特的人文情怀和信仰来平衡它。离开了这一特定的新闻叙事语言环境,“尘埃”的隐喻关系和隐喻义也就不复存在。又如“习近平参加广西团审议:扶贫少搞盆景多搞实事”(新浪网,2015-03-09),“盆景”一词本身不存在能指和所指的语义空白,也不具有隐喻义,此处语言环境赋予隐喻关系,喻指“表面华丽但无实际价值的扶贫政策”。
三、新闻叙事语言中叙事者的隐喻“选择”表达倾向
从构成隐喻的新闻叙事语言的生成过程而言,新闻叙事语言是叙述者的主体表达,叙事者有意识地选择隐喻作为表达手段,多数是出于表达主观意义和倾向性的需要。“叙述者的主体表达”指的是叙事中叙述者通过使用话语手段,调整时间元素和结构,将自身视角、情感、认识融入所叙之事,从而在话语中留下个人印记的一种表达方式[10]。新闻叙事语言是叙述者对新闻事件的“再现”,不是完全一致的“还原”,客观事件投射到话语中一定经过了叙事者的意向活动。是否选择隐喻作为一种再现手段,以及选择什么喻体构成隐喻,都体现着倾向性,它取决于叙事者及其代表的媒体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说,“选择”就意味着倾向。新闻学者杨保军认为,“新闻传播者总要在陈述事实信息的过程中表达一定的价值判断,表现出或强或弱的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流露出传播者的情感态度和审美情趣等。”[11]
在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泰晤士报》对两届奥运会的报道就存在着明显的倾向。据统计,《泰晤士报》对两届奥运会的报道,中立态度居多[12],这是作为一家国际性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所在。但对北京奥运会也不乏态度偏激的报道,在负面问题的报道上,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为伦敦奥运会的两倍。如该报对北京的环境污染问题、奥运会期间西藏暴力事件、奥运会安保等问题的过度关注。尤其在开幕式当天,该报头条新闻标题为“BeijingGamestobegininsmogofcontroversy”(北京奥运会在充满争议的烟雾中开幕),报道指出奥运圣火在充满政治性的空气里和充满污染的环境中传递。这里标题中叙事者选择“smogofcontroversy”这一隐喻突出其报道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
又如人民网新闻:“占中”,一场荒诞而疯狂的绑架(2014-10-03)。在新闻标题中,叙事者直接将“占中”行动定性为“绑架”,仅从这一隐喻用法,我们就知道在叙事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看来,“占中”是一场暴力、非法甚至犯罪行动,必须依法处置。在报道正文中,叙事者又分几个方面具体叙述了“占中”行动是对香港法律、经济、市民的正常生活以及学校教育秩序的“绑架”。因此叙事者对隐喻的选择就是其主观意义和倾向性的表达。类似的用例又如大公网的一系列新闻标题,李继亭:“占中”黄粱一梦勿拉港人“陪葬”(2014-09-03),罢课是占中前哨战学生被人当“炮灰”(2014-09-09),“6.22”是彻头彻尾的“老千局”(2014-05-30)。
四、新闻叙事隐喻通过“显隐”和“过滤”实现评价功能
就隐喻实现的功能而言,新闻叙事隐喻具有评价功能,表达叙事者对新闻事件的情感、判断和鉴定等蕴含意义。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发展而来的评价理论,主要研究作者如何在语篇中表达主观态度。一般认为,词汇选项是表达评价意义的主要手段。新闻叙事隐喻多以词汇选项的形式出现,在新闻叙事语言中具有评价功能,常常被叙述者赋予一定的评价意义,具体包括情感意义、判断意义和鉴定意义。束定芳认为,“(通过隐喻)我们可以借用对源域事物评价的方法来评价目的域的事物。”[13]那么,评价功能如何实现?认知隐喻观认为隐喻具有显隐功能,隐喻既可以突出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也可以隐去某一方面,甚至以偏概全,转移视线,扭曲事物原貌,创造“媒介真实”。在语义学研究中,这种现象称为“过滤原则”:我们选择某个词构成隐喻,就是选择将经过过滤的喻体的某些特征投射给本体,从而实现整个隐喻的意义,过滤后保留的特征才是我们要表达和突显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用什么样的隐喻看出他对认知对象的认知角度和态度。”[14]例如:“最年轻院士”倒下用制度堵死“经费黑洞”。(人民网,2014-10-17)
黑洞具有“质量极大”“密度极高”“引力场极强”等特征,但在“经费黑洞”这一隐喻中,叙述者经过过滤和筛选,只保留了“引力场极强”这一特征,也就是只将这一特征投射到本体身上,以此实现对科研项目经费特征的评价。“一些地方科研经费管理的制度黑洞,同样引力超强,不少科学家经不住钱的诱惑,沉沦其中……因此在道德谴责之余,我们更应反思,如何从制度上杜绝经费黑洞。”
又如FT中文网(2014-14-04)的专栏文章“再说《新华字典》对文化传统的阉割”,只从标题中“阉割”这一隐喻的使用,我们便可预见新闻叙事者对《新华字典》的褒贬评价。
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明显话语只能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的逼迫出场,而这个没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内部销蚀所有已说出的东西的空洞。”[15]语言作为表达的工具,不可能以说出的东西传达意义的全部内容。新闻叙事隐喻是已经说出的明显话语,它除了呈现在受众面前的符号形式外,还具有填补明显话语语义空洞的深层内涵,即它所表达的意义,因此它是协调言语的有限性和内涵的无穷性矛盾的有效手段。
注释:
[1]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杰拉德·普林斯著.叙述学词典[M].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5][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6]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束定芳.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6).
[8]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9]付军龙.叙事语言中的隐喻[J].学术交流,2007,(8).
[10]李凌燕,马晓红.叙述者的主体表达与新闻的意义建构[J].江西社会科学,2012,(3).
[11]杨保军.新闻事实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2]刘桦艺.中英主流媒体对北京-伦敦奥运会报道的比较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3]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教学出版社,2000.
[14]谢之君.隐喻认知功能探索[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5][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
(辛媛刘晨红宁夏银川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7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