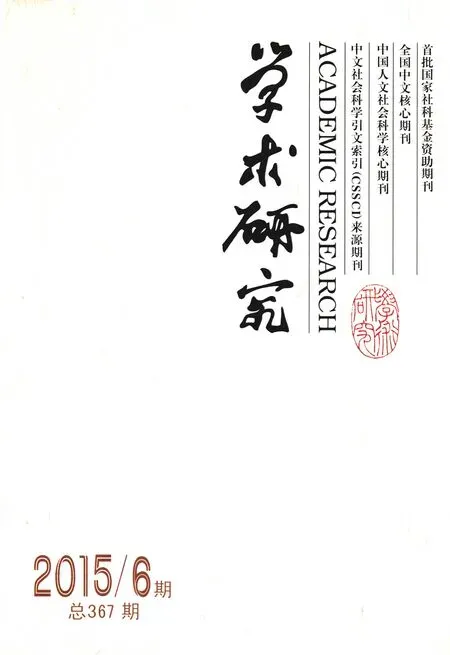散文理论:审美、审丑和审智范畴的有序建构
孙绍振
文学 语言学
散文理论:审美、审丑和审智范畴的有序建构
孙绍振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散文与当代文化·
[编者按]散文历来是 “文体之母”。它不仅历史悠久、积累丰厚,而且是中华民族感情的结晶、精神的载体和智慧的凝聚。但长期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中,散文研究一直处于小说、诗歌研究的阴影之下,成了一种理论资源匮乏、文体边界模糊与缺乏理论建构的 “次要文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当代散文的创作与阅读热度却与日俱增,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文化散文为标志的 “散文热”,更将当代散文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 “散文热”也未见消退。该如何看待散文这种创作与研究背离的现象,以及如何去挖掘发现中国散文的价值,建构中国散文的理论体系,并使散文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这是摆在每一位散文研究者面前的问题。为此,本刊邀请孙绍振、王兆胜、陈剑晖三位学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孙绍振从审美、审丑和审智范畴有序建构的角度,探讨建构散文理论体系的可能性。王兆胜从承载中华民族基因和密码的角度,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语境中挖掘散文的价值。陈剑晖从文化根基性、文化生命理想、审美抒情范式和自我和谐与和谐社会等方面,探讨散文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本刊认为这种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语境的探讨是有价值的,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散文,既推动散文的研究向前发展,又可以促使散文有效地介入到当代文化建设中。
理论范畴的准确性必须建立在确定的外延基础之上,但散文是多种亚文体的综合交错,恰恰缺乏确定的外延,这就造成了现代散文理论十分贫困。建构散文理论的当务之急,一是在错综复杂的外延中确立基本范畴,在矛盾转化中衍生新范畴、亚范畴,构成自洽的、有序的散文范畴系统,二是在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辅之以三分法,三是摒弃以静态的眼光对散文史作孤立直观的表层描述,而以动态的历时视野将逻辑范畴与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就散文发展演变而言,抒情审美的极端造成滥情、矫情,乃有审丑和亚审丑之幽默散文,而亚审丑幽默所遵循的并不是理性逻辑,故其思想深度受到限制,此等矛盾遂导致既非抒情审美亦非亚审丑幽默的审智的产生。因此,将文学性散文归纳为 “审美”、“审丑”、“审智”三大范畴,既是逻辑的有序划分,又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填补世界散文理论空缺的有益尝试。
散文理论 范畴 审美 审丑 审智
一、散文理论的困境
比起小说、诗歌、戏剧花样翻新的理论,现代散文理论显得十分贫困。从 “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
“叙事与抒情”,到上世纪60年代的 “匕首投枪”、“形散而神不散”,再到80年代巴金的 “讲真话”和至今仍然风靡学界的 “真情实感”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散文尚未形成内涵确定、具有内在丰富性、足以衍生发展形成体系的基本范畴,学科理论的草创阶段尚未开始。从世界散文历史观之,散文没有起码的理论范畴,更谈不上系统性。原因在于:理论范畴的定义属于内涵性质,其准确性必须建立在确定的外延基础之上,但是,散文几千年来恰恰缺乏确定的外延。这种现象在中国、在世界均有其历史根源。
我国从先秦到晚清并不存在纯文学性散文文体,只有 “文”的观念。诗言志,文载道,文是与诗相对的。文又可分为古文和骈文。骈文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同时也是官方实用文书的常用形式,而古文则比较复杂。在姚鼐的 《古文辞类纂》中,古文有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等等,可见散文包含了文学性和非文学性,审美情感性质与实用理性两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文是多种亚文体的综合交错。此等情况不但是中国特有的,而且是世界性的。
台湾学者郑明娳认为:“在中国散文虽然不居于文学的地位而生长,但在西方,散文却没有自己的地位。”她援引董崇选 《西洋散文的面貌》说:“在西洋文学里,最初的三大文类是戏剧、史诗与抒情诗。可是后来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渐渐增多,……有些文学成份很高的传记、自传、性格志、回忆录、日记、书信、对话录、格言录与艾写 (essay)等,既不是戏剧,也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而既然这些文类的作品,通常都是用 (最广义或较广义的)散文写成的,所以就有很多人把这些文类的作品合起来,笼统地称为prose(散文)。”[1]这种说法很精辟,但不全面。西方最初的文学并不是只有戏剧、史诗和抒情诗这样的韵文,还有非韵文的对话体散文,如柏拉图的经典之作 《苏格拉底之死》、《理想国》,此外还有重要性不亚于对话的演讲。其时书面的传播以非同一时空的间接性为特点,尚不甚发达,直接的同时空的演讲在公众生活中很重要,产生了大量的演说经典之作,如苏格拉底的 《在雅典五百公民法庭上的演说》。亚里斯多德的 《修辞学》就主要是论述演说术的,在理论上提出了打动听众的三个要素:诉诸人格的说服手段 (ethos),诉诸情感的说服手段 (pathos),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 (logos)。这说明,演说作为一种相对于史诗、戏剧、抒情诗等韵文的独立文体,是以非韵文为特点的。它在当时不但广泛存在,而且产生了 “修辞学”这种与 “诗学”并列的经典理论。演说这种非韵文体裁,还延续到古罗马,产生了西赛罗那样的演说和理论经典。在鲍姆嘉通的 《美学》中还说道:“美学同演说学和诗学是一回事”。[2]演说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强调,是因为它在小说尚未发达的中世纪,是主要的非韵文文体。作为非韵文文体的演说,在西方历史上,其经典比比皆是,差不多每一个时代的大政治家,都有其相当经典的演说。但奇怪的是,文论相当发达的欧美却并没明确地把这种公开场合所普遍使用的文体归纳到散文中去,演说作为文体至今并没有得到西方百科全书的普遍认同。
正是因为散文外延和内涵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在英语国家的大多数百科全书中,没有单独的散文条目,只有和prose有关的文体,例如:alliterative prose(押头韵的散文),prose poem(散文诗),nonfictional prose(非小说类/非虚构写实散文),heroic prose(史诗散文),polyphonic prose(自由韵律散文)。这就造成了散文的尴尬,在西欧北美,散文 (prose)并不是作为一种文体而存在,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既可以是审美抒情的,也可以用之于实用理性的载体。
这种错综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在先秦只有诗和文两体。诸子之文大多是对话体,如 《论语》和 《孟子》,属于传统文论中所谓 “记言”性质,而记言无非就是对话和独白。在间接传播媒介不发达的当时,除了歌谣,不具实用性的言论是不会被文字记载下来的,记载下来的往往是对公众有相当实用意义的。在非韵文中,审美与实用理性的交融在东方和西方可谓息息相通。
被刘勰称为 “诏、策、奏、章”之 “源”的 《尚书》,本最具实用理性,但是恰恰是这些权威公文,具有 “记言”的特点,强烈地表现出起草者、演讲者的情感和个性。 《盘庚》篇记载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为了避免水患,抑制奢侈的恶习,规划从山东曲阜 (奄)迁往河南安阳 (殷),遭到了安土重迁的部属的反对。盘庚告喻臣民说:“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是对部属的拉拢,用
了当时谚语,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东西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接着说自己继承先王的传统,不敢“动用非罚”,这就是威胁。不敢动用,就是随时都可用。至于,你们听话,我也 “不掩尔善”,不会对你们的好处不在意。 “听予一人之作猷……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意思是:听我的决策,我负全部责任,邦国治得好,是你们的,治得不好,我一个人受罚。话说得如此好听,表面上全是软话,但这是硬话软说,让听者尽可能舒服。可到了最后,突然来了一个转折:你们大家听着,从今以后:“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你们要安分守己,把嘴巴管住,否则,受到惩罚,可不要后悔。[3]这样硬话软说,软话硬说,软硬兼施,把拉拢、劝导、利诱和威胁结合得如此水乳交融,其表达之含而不露,其用语之绵里藏针,其神态之活灵活现,都十分出色。这样的文章,虽然在韩愈时代读起来就 “佶屈聱牙”了,但是只要充分还原出当时的语境,不难看出这篇演讲词,用的全是当时的口语。怀柔结合霸道,干净利落,实在是杰出的情理交融的文学性散文。这样的政府公文中透露出来的个性化的情志,用亚里斯多德的演讲动人三要素来衡量,既有诉诸人格的说服手段和诉诸情感的说服手段,也有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也就是说既有实用理性又有审美抒情的性质。
但是,中国古代的散文不论是说理还是抒情,又有中国的特色,那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纯粹“记言”的日益减少,纯粹 “记事”的日益发达。从 《春秋》开始,形成了中国的 “实录”叙事传统,到 《左传》史传散文达到成熟,即把情感和理性隐藏在记事之中。固然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说把神圣化了的经典还原为历史的记事,但袁枚的 “六经皆文”(“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4])似乎更警策。而钱钟书则无异于提出了 “六经皆诗”的命题:“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5]这就是说,古史从文体功能来说是历史的记事,然而从作者情志的表现来说,却无不具有审美价值。钱钟书还以《左传》为例,指出 “史蕴诗心、文心”,特别指出记事性质的历史散文其实隐含着作者的想象和情志:“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6]中国古代史家虽然标榜 “实录”精神,但事实上,记言,并非亲历,且大多并无文献根据,其为 “代言”、“拟言”者比比皆是。就是在这种 “代言”、“拟言”中,情志渗入史笔,历史性与文学性互渗。更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史家以记言记事为务,仅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但是并非绝对没有理性的评论。司马迁发明的附加在列传之后的 “赞”(太史公曰),就完全是理性的评论。如 《项羽本纪》后面这样说:“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 ‘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 ‘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7]这里,就与 《本纪》中对项羽英雄气概的溢于言表的审美表现不同,而是理性的分析批判。这说明,史传散文的记事记言不但是与抒情而且是与实用理性结合在一起的。
叙事、抒情、说理三者在对话、演说和史传中,自然、自发地互渗,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开始有了某种文体的自觉。
二、拘于审美价值的自我遮蔽
大量先秦文章的审美性质还处在胚胎形态,并不纯粹,文学的审美超越理性和实用理性错综交织,有时实用理性还占着优势。早期文史哲不分的特殊性,决定了散文具有 “杂种”性质。审美价值与实用理性是如此错综,连袁枚、钱钟书这样的大家都未能彻底洞察。袁枚所言 “六经皆文”和钱钟书所言“六经皆诗”都有强调审美性质,抹煞实用理性的嫌疑。只有从当代审美情感与实用理性分家的高度,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分析出这种低级形态中的审美基因。也只有充分理解了低级形态的 “杂种”基因,才能洞察中国散文史中情感与智性 (理性)犬牙交错的复杂性,也才能理解在数千年的中国散文史上,纯粹审美抒情散文为什么屈指可数。
中国散文从娘胎里带来的 “文体不纯”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轫期,在西方随笔散文的冲击下,曾经面临着某种历史转机。早期 《新青年》的随感录,与西方的随笔 (essay)有某种接近,但是,西方的随笔以智性思绪为主,其审美价值尚未从文化价值中分化、独立出来。这引起了周作人的犹豫,结果是他在1921的 《美文》(按:这是法语belles letters的译文)中选择了晚明小品的 “性灵”,确立了“叙事与抒情”的纯文学/审美方向。这在当时反桐城派的载封建之道,张扬个性,造成散文大解放、大繁荣,有历史的功绩,但是,也造成了把散文局限于审美抒情的弊端。鲁迅的智性散文,被打入另册,异其名曰 “杂文”这一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体,以致时到今日,连鲁迅的杂文算不算散文,还有争议。更有论者对 “散文同时可能是——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特写、随笔、书评、文论、时事评论、回忆录、演讲辞、日记、游记、随感式文学评论等”感到愤怒,表示要把散文理论 “推倒重来”。[8]有学者甚至天真地提出要 “净化散文”文体。这不但是受了周作人 “叙事与抒情”狭隘散文观念的遮蔽,而且是受了林非 “真情实感”论的误导。以为散文只能审美抒情,实在是画地为牢。
真正科学的态度,不是把主观的狭隘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遵循历史的丰富、复杂、错综的过程,从中找出总体的和个案的深邃奥秘。西方理论对于散文这一可能是最普遍、最广泛,又是最为复杂多样、最为丰富多彩的文体没有作出起码的归纳,他们的理论空白,本该是我们用武的广阔天地,但是,我们因缺乏理论原创的自觉,却以幼稚的直觉对待散文。先是杨朔提出把每一篇散文都当作诗来写,后是林非提出 “真情实感”这样的概括,更有些教科书将散文分为平列的 “叙事”、“抒情”、“议论”、“说明”四体。其实这样的划分十分荒谬,违反了形式逻辑划分不得交叉的规范。从中外文章史观之,审美抒情和理性议论从来都是共处的,哪有一篇文章纯粹叙事而不抒情的,或者纯粹抒情而禁绝叙事、议论或者间或说明的?四者在文章中往往错综交融。然而既不符合逻辑,又与历史相悖的 “真情实感”论,居然被尊为不言而喻的不刊之论,岂不是国人的悲哀。我国的文学理论从小说到诗歌,从戏剧到电影,向来以引进西方文论为务,然而唯独散文,西方却没有理论可引。于是就产生了国人以零碎的感觉和狭隘经验为基础的内涵贫困、毫无历史感的上述 “理论”。这些理论从严格意义上说,几乎不成其为理论。最明显的是,它们缺乏理论所必需的全面涵盖性。
就以流行最广,至今仍然载入百科全书、写入教科书的 “真情实感”论而言,在美学上属于审美价值范畴,从创作实践上来说,乃是对客观对象和主体情感的美化和诗化,但是,就中国散文史而言,这在逻辑上显系以偏概全。在 《史记》中有 《滑稽列传》,其为文并不以美化诗化为务。早在扬雄就有《逐贫赋》这种带有某种自嘲、戏谑性质的文章,显然与诗化抒情背道而驰,但却成为延续千年的母题。到了唐朝,文起八代之衰的正统大师韩愈,以其 《送穷文》拓展了这个母题。其 “穷”不是物质上的贫困,而是称己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恳请 “五穷鬼”离去。穷鬼却称自己与韩愈同命运四十余年,虽主人迁谪南荒,百鬼欺陵,遭人讨厌,而穷鬼始终忠心不改,不离不弃,说得主人垂头丧气,“上手称谢”,“延之上座”。[9]韩愈死后30年,友人段文昌之子成式为 《留穷辞》(按此文已佚),论者以为与韩文比,有 “辞反之胜”。五年后,成式复作 《送穷祝》(一名 《送穷文》)。唐宣宗时,有自称 “紫逻山人”者,有 《送穷辞》。北宋王令亦有 《送穷文》。清戴名世有 《穷鬼传》,也是要遣送穷鬼,穷鬼不肯去,理由是韩愈之所以不朽,都是他的功劳,穷鬼数千年才遇到韩愈,又近千年而得遇先生,先生之道寡,“独余慕而从焉”,“岂不厚哉?”[10]仅从 “送穷”母题千年不断可以看出,审美抒情以美化诗化主体与环境为务,而送穷母题则反之,以自我调侃、自我贬抑为务。这种自我贬抑的文章,绝非审美范畴所能概括。在理论上,理论落后于实践,创作实践的突破和理论的故步自封,是古今中外的规律性现象。
“五四”以降,林语堂自英语引入幽默,他和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的幽默散文到了40年代,蔚为大观,成就空前。反诗化的幽默拓展了审美诗化的美学原则,把自己写得很狼狈,很可笑,很弱智,甚至心术不正,为散文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鲁迅虽曾严词拒斥幽默,激进文士至今奉鲁迅之言为圭臬。认为国难当头之际,倡言幽默,可能使大家将屠夫之凶残化为一笑。然而,同在国难时期鲁迅的
《朝花夕拾》,作为中国现代幽默散文之经典,其幽默丝毫不亚于林语堂。如在 《长妈妈和山海经》中写长妈妈讲述太平军俘虏女人,清军来攻城,令女人立于城墙,脱下裤子,清军大炮立炸。对这样荒谬的迷信,鲁迅并没有据五四 “赛先生”的科学理性加以批驳,而是说她有 “伟大的神力”,对之产生 “空前的敬意”。这样的反讽显然是美化诗化的反面:表面上是对长妈妈和自己的贬抑,但读者并不觉得鲁迅愚昧,相反觉得有趣。读者从显而易见的荒谬中心照不宣:这不是鲁迅的实感,而是虚拟。这种虚拟悖谬,或者用西方人的说法incongruity(不一致,不和谐),构成一种有异于情趣的谐趣。这种谐趣之品味,之所以并不在情趣之下,原因在于:这里表面上表现的是长妈妈的愚昧,实质上透露着她并不虚伪,意不在恐嚇,相反相当真诚,对自己的高见自信、自得,而鲁迅对其荒谬明明洞察,却故作愚言,表现出对小人物宽容。
此等风格在西方属于幽默。西人虽幽默之说多端,迄今未有内涵确定的定义,甚至有 “为幽默下定义本身就幽默”之说。西人视定义为研究之出发点,然无法定义并不影响幽默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之显学。盖定义乃内涵性质,抽象之语言声音符号,很难穷尽对象之全部属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外延之存在。西人之学术定义,往往局限于单独概念之孤立概括,殊不知一切事物、观念均处于关系之网络中。故孤立为幽默散文定义难,而将之与诗性散文联系起来,观其诗与反诗,美与醜之对立,以及醜与丑之转化则易。西人孤立定义之失还表现为未能在逻辑上将幽默与审美作系统之贯通,即未能意识到幽默散文与审美散文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审美、审丑和审智范畴的有序建构
西人不能为,束手无策之时,正是吾人用武之地。
幽默与审美,自我调侃与自我诗化对立,诗化之极致,乃有反诗化、反美化之必然。其极致,如柏杨、李敖等幽默到不怕醜的程度,表面上是醜,但是,从情感上说并不醜,尽显其心地率真、宽宏、坦荡。因而此醜之性质并不在生活之醜,而在艺术之 “丑”。 “丑” (丑角)在中国戏剧中,往往是外形醜陋,而内在机智,富于人情之美。在西方戏剧中小丑往往于荒谬之中说出真理。西方象征派诗歌有“以醜为美”①一般诗论均因汉字简化译为 “以丑为美”,似不当。丑角不醜,其性质乃是以醜化丑。丑中之情感与机智即是美。之原则。在幽默散文中,则是以醜化丑,以醜为丑。无以名之,当名之为 “审丑”。西方之 “美学”(eathictcs),原为相对于理性的感知与感情,日人以汉字译为美学,以中外幽默散文检验之,显系以偏盖全。在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中,情感有独立之价值,有情为美。然情感有渗于华彩之表象者,亦有以醜陋之意象为载体者。就审美价值而言,情感超越科学之真、实用之善为美,无情则为丑。于散文中,此类鲜见,于小说戏剧中则比比皆是,如 《红楼梦》中之贾政,《雷雨》中之周朴园。幽默散文之宽宏心态,并非绝对无情,故径直以 “审丑”名之,亦不尽合,以 “亚审丑”名之当更恰当。[11]
西人近代学术以概念之演绎为长,其缺失乃在脱离文本。吾人效其长,当察其短,宜辅之以从文本归纳,以具体分析补足,以突破其从概念到概念之藩篱,提出从审美走向对立面,产生审丑之范畴乃是必然。幽默与抒情至此遂不各自孤立,其外在对立与内在统一,只有在联系中方能见出。吾人之原创性不能在孤立的定义中产生,而在关系的转化中显现。
然而散文的关系丰富,在审美审丑 (亚审丑)之二元对立和转化之单一层次中并不能穷尽。审美与审丑 (亚审丑)虽显相反相成之联系,仍然不能涵盖散文之丰富外延。最明显莫过于在中外散文史上,存在大量既不抒情亦非幽默之散文,其中绝大多数,乃是纯粹理性之文章,属标准的理性的论文,不属于文学美学范畴,宜于理性范畴另作研究。但是中国传统的议论文,有其特别的话语,那就是论说文,在理性阐释时,论和说联系在一起。 《文心雕龙》提出的 “论”、“说”是不一样的:“‘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必使心
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12]“论”是比较严格的理性文章,所论皆经国之大业,以全面 (如正面、反面)为上,具有 “大品”性质,其经典性的作品如贾谊的 《过秦论》,柳宗元的 《封建论》,欧阳修的 《朋党论》、《纵囚论》,苏洵的 《管仲论》,苏轼的 《留侯论》、《贾谊论》,苏辙的 《六国论》,方孝孺的 《深虑论》等等。这当然不属于文学的审美性质。然而同样为议论文章,刘勰又提出 “说”之体,指出其出于先秦的游说之士,作为文体的根本特点乃是 “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辞”。[13]强调的是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 “说”不像 “论”那样特别强调理性的全面和严密,但以机敏的智慧出奇制胜。 “说”本源于先秦游说之士,日后由于纸的发明,超越了现场的口舌之机敏,而成为一种文体。这种文体虽然智性很强,但是,以巧喻 (类比推理)为基础,严格以理性考究起来,往往是片面的。如晏子使楚所言 “使狗国者从狗门入”的大前提,就是情绪性的,其动人之处恰恰就在智慧机敏性,从文体来说,并非以情感的激发见长。韩愈 《马说》一开头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论断先声夺人,接着说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文气上说,是很充沛的,但逻辑并不严谨,前提是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既然伯乐不常有,则千里马相应地当为不常有,然而韩愈却说千里马常有,这样的结论在逻辑是不能推出的。如果是 “论”,则不能成立,但这是 “说”,其旨皆在以巧驭智,其焦点在一得之机,甚至以一面之词的机敏取胜。与之相近的还有某些 “记”、“序”等,王安石的 《读孟尝君传》可为典型:“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14]一百多字的文章,论国之兴败,仅仅抓住 “得士”一点,对历史共识作翻案文章。说得很机智,很简洁,颇有深邃之处。然而,显然并不全面。秦之胜,齐之败,如果用 “论”的文体,则要求 “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也就是有全方位,至少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系统的分析,岂是 “得士”这样单一的原因就能决定的。但是,“说”并不是严密的理论,只以机敏的智慧,巧妙地、出奇制胜地把 “理”推导出来。柳宗元的 《捕蛇者说》、苏轼的 《石钟山记》、刘基的 《说虎》皆为经典。表面上是在说理,实际上并未达到 “论”那样的严密的理性,充其量只能达到智性的层次。这种智性,其语言又往往带着很强的感性,因而,这样的文体生命不在抒情,亦不在幽默,而在从感知直接导向智慧。这类文章不但在古典散文中源远流长,经典辉煌,而且在现代散文中亦比比皆是,鲁迅、聂绀弩等人的文章,社会文明批评比之古代此类文章更为深邃和犀利。但在理论上,处境却十分尴尬,既不能列入全面说理的论文,又不能列入审美的散文。冠之以 “杂文”之名,实质乃显其于散文体系中无所归属。其源皆在当年周作人将中国散文传统仅仅定位于晚明性灵小品,以 “叙事与抒情”为准则之误导。从理论上说,囿于狭隘之审美,其极端乃是杨朔 “把每一篇散文都当作诗来写”之论风靡30年。
极端拘守于审美之狭隘概念,更增加了在理论上为鲁迅等人的杂文作文学理论阐释之障碍。其实,不从概念出发,而从散文历史和风格各异的文本出发,则不难发现,此类文章,既不抒情,亦不幽默,非审美、审丑二元对立范畴所能概括。其精神全在从感性出发,以智慧之趣取胜,既不同于审美抒情之情趣,又不同于亚审丑之谐趣,而是超越情感元素,从感知直接深入到智慧,当为智趣。
西人之失,第一,于趣味缺乏分析,未能察情趣与谐趣之异,亦未能悉情趣、谐趣与智趣之逻辑联系;第二,于eathetical缺乏分析,未能在概念上从审美、审丑中引伸出 “审智”;第三,于思维方法局限于二元对立,殊不知,散文之外延,非二分法所能穷尽。揭示审美、审丑、审智之内在联系和转化,非突破二分法,代之以三分法不能成井然有序之体系。其实,这样的系统性与亚里斯多德的演讲动人三要素也颇有谋合之处,其诉诸情感的说服手段相当于审美,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相当于审智,至于诉诸人格的说服手段则为二者之综合。亚里斯多德的不足,乃尚未提出审丑范畴。原因盖在于,当时的对话与演讲,诉诸情感与理性者多,罕见有诉诸幽默者。当然,演说作为文体,既有审美抒情,亦有幽默审
丑,更有审智为说者,不过其成败不由作者单方面决定,而由现场听众之互动及互动生成之程度决定。如此说无大误,则不难见西方前卫文论长于概念之演绎,短于直接经验之归纳概括。西方之审智散文,源远流长,不过其名曰 “随笔”,以智性的随想为特点,其杰作从蒙田到梭罗荦荦大端者比比皆是。然西方前卫文论,囿于演绎传统,无前人概念之依傍,乃对之视而不见。
由此观之,与吾人相较,西人之文学理论,于小说、戏剧为长,于诗各有千秋,而于散文则为短,既未形成基本范畴,亦未有范畴贯通为体系之自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吾人得益良多,百年来成就斐然,唯察人之短,展己之长,于西人之空白与之争一日之长短,尚未自觉。一味奉西人之软肋 (如周作人从法语借来的 “美文”)为金科玉律,遂致散文理论百年徘徊颠倒于审美。积百年之教训,国人当自强不息,破除弱势文化自卑的文化奴隶心态,于西人束手无策之处,在建构散文理论中大展宏图。
无可讳言,散文理论建构之使命比之小说诗歌要复杂艰巨得多。中国古代散文,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在没有总体理论的情况下,以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实践着审美、审丑、审智的创造,而散文理论家,要么视众多的历史坐标而不顾,要么以摸着一块石头的狭隘经验而自喜,而忘记了过河的任务。建构散文理论的当务之急,乃是思想突围。第一,须具备比前人更加宏大的气魄和宏观的视野,熔古今中外于一炉,在错综复杂的外延中,以空前的魄力作第一手的、前无古人的、原创性的概括,确立基本范畴,作为逻辑起点,并赋予此逻辑范畴以内在的丰富性,在矛盾转化中衍生新范畴、亚范畴,构成自洽的、有序的范畴系统。第二,在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辅之以三分法。第三,摒弃以静态的眼光对散文史作孤立直观的表层描述,而以动态的历时视野,将逻辑范畴与历史发展结合起来,揭示二者互动的历史流程——前一个流程蕴含着矛盾和不足,导致后一个流程的产生,弥补了前一个流程的缺陷,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不足,从而导致新的流程。如抒情审美的极端造成滥情,走向反面,而成矫情,乃有审丑和亚审丑之幽默散文,而亚审丑的幽默,所遵循的并不是理性逻辑,而是非理性的二重错位逻辑,[15]故其思想深度受到限制,此等矛盾遂导致既非抒情审美,亦非亚审丑幽默的审智的产生。如此三范畴,既是逻辑的有序划分,又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然而,统一并非僵化,统一中又有分化,按否定之否定轨迹,螺旋式上升,以至无穷。
基于此,将文学性散文归纳为 “审美”、“审丑”、“审智”三大范畴之有序过程,不过是填补世界散文理论空缺的一个初步的尝试。
[1]郑明娳:《现代散文类型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第3页。
[2][德]鲍姆嘉通:《美学》,刘小枫选编:《德语美学文选》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3][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3-235页。
[4][清]袁枚:《答惠定宇书》,《小仓山房诗文集》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第1529页。
[5]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8页。
[6]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66页。
[7][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339页。
[8]周伦佑:《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红岩》2008年第3期。
[9][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70-572页。
[10][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9-431页。
[11]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04页。
[12][13][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8、329页。
[14][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95-396页。
[15]孙绍振:《论幽默逻辑》,《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责任编辑:王法敏
I207.6
A
1000-7326(2015)06-0126-07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 (福建 福州,35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