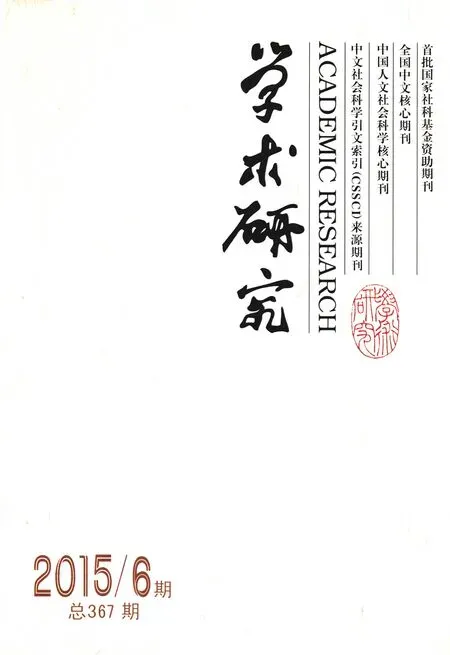李翱与儒家心学
吴杰锋
李翱与儒家心学
吴杰锋
中唐时期,李翱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阐发以心性道统为主线,带有鲜明的心学特征:一是 “以心通”承道统,为儒家道统说引入传统心性思想内涵;二是以心性开经典,推崇和阐发 《礼记》《孟子》等著作中的心性思想资源,明确将 《中庸》定义为心性之书;三是以 “复性”为工夫,强调内在的心性修养,对儒家心学的创建有发端之功。
李翱 道统 经典 复性
儒家心学的思想渊源及发展脉络是当前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周炽成先生认为,“心学”概念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儒家心学通常被认为是源于 《尚书·大禹谟》“十六字心传”。[1]冯国栋先生认为,作为学术名词的儒家 “心学”,最早见于南宋湖湘派胡宏所撰 《知言》中。[2]本文认为,儒家心学思想源于孔子、子思和孟子,历经千年的发展低潮,到中唐由李翱开始进入儒释道融合发展时期,经吸收佛教心学精髓,发展到宋明陆王心学达到了理论高峰。李翱提出从儒家心性之学角度梳理和阐发经典,强调越过汉儒回到孔子、子思和孟子承接儒家心性之源。李翱创造性提出 “以心通”承道统的方法,明确把 《中庸》定义为儒家心性之书,阐发 “复圣人之性”的心性修养工夫,对儒家心学理论的创建和发展有发端之功。
一、“以心通”承道统
唐代是佛学发展的全盛期,道教亦被奉为国教。面对佛、道二教的空前发展,儒学在中唐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在思想学术界兴起一股对当时和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 “明道”思潮。[3]韩愈对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4]深感不安,特阐明正统提振儒学,弘扬儒家之道,提出著名的道统说: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5]韩愈坚持儒家自有传统,并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以来的道统谱系清晰地描绘出来,对后来的儒学尤其是宋明新儒学影响深远。李翱亦深受韩愈道统思想的影响,他说:
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圣人所由之道也。吾之道塞,则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则尧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绝於地矣……吾之道,学孔子者也。[6]
李翱推崇孔子之道,以儒家仁义思想释道。在 《复性书》中,李翱不仅以传道为己任,还认为自己是孔子、孟子之道的传人:
仆之道穷,则乐仁义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则推行之于天下也,何独天下哉?将后世之人,有得于吾之功者尔,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7]
李翱认为重提圣人之道并不止于简单复述古圣贤的话,而应该结合时势赋予新意:“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8]韩愈建立形式上的儒家道统,李翱则在内容上为道统引入心性思想内涵。他在《寄从弟正辞书》中说:
仲尼、孟轲殁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9]
李翱并不满足于按韩愈的说法 “照着讲”,而是以旧瓶装新酒 “接着讲”。在道统思想的框架下,李翱用 “吾心”体贴圣贤之心,以儒家道统承接和重新开启失传已久的儒家性命之源:
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 《中庸》四十七篇,以传於孟轲……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惟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於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10]
在对道统问题的阐释上,李翱和韩愈既有认识上的一致性,亦有思想上的互补。如果说韩愈建立道统是为证明传授之渊源以自重,李翱则可看做是为儒家道统注入心性思想内涵以自强。李翱认为,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古圣先贤之道之所以得不到弘扬,原因在于儒家传承只有 “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却遗漏了最重要的 “性命之源”。阐道统以开性命之源,可谓是李翱作 《复性书》三篇的初衷。李翱在 《复性书》中指出:“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命曰 《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乌戏!夫子复生,不废吾言矣。”[11]李翱强调儒家道统实乃性命之道,将韩愈点了题却又未深化的道统问题引向了深入。韩愈论道统并未提及子思,而李翱在 《复性书》中却特别提到子思得其祖之道,并述 《中庸》以传于孟轲,子思经李翱之手跻身道统之列,与 《中庸》具有丰富的心性思想内涵有密切关系,这是李翱发前儒所未发。
对韩愈和李翱共同阐扬道统的学术意义,冯友兰先生认为 “宋明新儒家之学之基础与轮廓,韩愈、李翱已为之确定。二人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不可谓不重要也”。[12]在冯先生看来:“韩愈和李翱为道学奠定了基础。他们制造了一个 ‘道统’,为道学作历史依据。他们提出了 《大学》、《中庸》,作为道学的基本经典,加上 《论语》(韩愈和李翱曾合注 《论语》)、《孟子》,成为后来的道学的 《四书》。”[13]儒家提出道统说的目的是要与佛学抗衡,但李翱与韩愈在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韩愈所强调的道统,主要是相对于佛、老之道而言。其道统说外衣下面,依旧是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14]为内容的先秦旧说,对佛道缺乏思想理论上的包容。故冯友兰认为韩愈:“企图从理论上 ‘排佛’,可是并没有接触到哲学的根本问题,并没有从哲学根本问题上与佛教作斗争,并不能把佛教驳倒。”[15]而李翱则借鉴佛学的思路,并把 《中庸》 《孟子》定义为心性之书来进行提炼阐发。冯友兰由此对李翱给予很高评价:
李翱的 《复性书》也引 《易传》。 《易传》后来也成为道学的基本典籍。但是也还不够。道学家必需把这些典籍中的思想加以提炼,把其中有一大部分原来只是伦理的思想,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李翱开了这样一个途径,后来的道学家都是照着这个途径进行的……到了南宋时期,道学的体系完全建立起来,韩愈在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地位,就降低了。这是因为韩愈只是为道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而在哲学上,还不能列入道学的创始者的行列。[16]
李翱被视作儒家心性之学的重要思想家,与其解释儒家心性经典的思想方法有重要关系。有人问李
翱与前人注解 《中庸》有何不同,李翱的回答别具心学方法论的意味:“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17]受佛教心传思想方法的启发,李翱提出 “以心通”的方法来体悟道统之内涵,明显有别于汉代经学 “以事解”的解经方法。汉代经学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均围绕 《春秋》纪事做文章,李翱将其方法归纳为 “以事解”,而标榜自己是 “以心通”。心性论是隋唐学术讨论的主要问题,李翱提出以心性为线索贯通道统,从而给儒家道统赋予心性思想属性,走出一条以心性传承道统的经典解释新路。
二、以心性开经典
传统经学大致可以划分为汉学和宋学,其中汉学重视五经,宋学则强调四书。唐代初期儒家奉九经为经典(唐朝太和年间已有“十二经”刻石),《中庸》 《大学》仍只是 《小戴礼记》中的单篇文章,尚不具有经典的地位。中唐以后,《中庸》 《大学》地位提升很快,发展到宋明已跃升四书之列。 《中庸》被儒家重新认识和推崇,缘于被儒家定义为性命之书,必须从李翱注解 《中庸》谈起。
儒家经学历来以解经的方式表达新的学术主张。朱彝尊在 《经义考》中提到,李翱著有 《中庸说》但未流传。[18]考察李翱对 《中庸》的看法,一般把 《复性书》作为李翱阐释 《中庸》思想的主要文本。在 《复性书》中,直接或间接引用 《中庸》的内容就有七处,有四段话被 《复性书》整段进行引用:
子思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诚则明矣……
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大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以上四处引用主要是以 《中庸》“至诚”和 “中和”的思想来说明 “天道性命”问题。另有三处,是李翱对 《中庸》的引用和发挥,其中:“性者,天之命也”源自 《中庸》“天命之谓性”;“颜子得之,拳拳不失”源自 《中庸》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於时”则源自 《中庸》“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最终得出 “诚者圣人之性”的结论:“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则能归其源矣!”
《复性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中庸》注疏,但 《复性书》讨论心性问题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中庸》。 《复性书》以 《中庸》里面的 “诚”、“明”概念来讨论和阐述圣人之性,其思想立场很明确,就是坚持用儒家自有的表达方式来解释心性问题,并建立区别于佛教心学的儒家心性之学。李翱通过以心性阐释道统,将儒家心性论讨论引向深入,引发儒家对 《中庸》等先秦儒学心性论资源的重新认识和关注。李翱并不像韩愈那样局限于道德伦理、社会经济等领域反佛,他要直入佛家胜场的心性之域,与僧侣辩论性与道的问题。傅斯年对李翱推崇 《中庸》给予高度的评价,其 《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一文指出:“儒家书中,谈此虚高者,仅有 《孟子》《易·系》及戴记之 《乐记》、《中庸》、《大学》三篇,于是将此数书提出,合同其说,以与二氏相角,此 《复性书》之所由作也。戴记此三篇,在李氏之前皆不为人注意,自李氏提出,宋儒遂奉之为宝书。”[19]
李翱在 《小戴礼记》中发现 《中庸》具有丰富的心性思想资源,证明儒家心性之学本有渊源,《中庸》被学界重新认识。清儒全祖望提出:“自秦、汉以来,《大学》、《中庸》杂入 《礼记》之中,千有余年,无人得其藩篱,而首见及之者,韩、李也。”[20]六朝时,戴颙、梁武帝等人皆曾注解 《中庸》,可惜这些注释现已散佚。由于唐朝之前的儒家鲜见注解 《中庸》的作品,有学者认为唐代以前的佛子反而比
儒者更容易走进 《中庸》的世界,《中庸》与佛教思想相对比,亦更容易显现它的精神。[21]
韩愈推崇 《大学》,李翱推崇 《中庸》。他们所推崇和阐发的内容并非新说,但他们看待和解释 《中庸》《大学》的立意和方法,确是有别于汉儒。简要言之,这两本典籍在唐宋期间最重要的转折是变成了 “性命之书”。 杨儒宾先生认为:“儒者性命之学的需求与这两本典籍隐藏的心性论资源会合之后,两本典籍的性格脱胎换骨。”[22]李翱的 《复性书》被称为 “《中庸》之义疏”。通过 “以心通”的方法,李翱将 《中庸》纳入儒家道统的重要环节,《中庸》被明确以儒家心性之书的面目被解释和宣传。他还曾与韩愈合著 《论语笔解》,都带有典型的经学思维色彩。 《复性书》后来被认为是理学 (尤其是心学)先声,《中庸》以心性之书的面目走上儒家经典的中心舞台,与李翱将 《中庸》定位为心性之书进行解释和阐发有着重要的关系。以心性思想资源为标准梳理和引用文献这种手段性 (而非目的性)的行为却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效果——为儒学经典从五经系统向四书系统转移准备了条件。
在宋儒眼里,传道的过程就是传心的过程。[23]为继承儒学传统,李翱曾与韩愈合著 《论语笔解》。为了论证儒家自有性命之学,李翱大力挖掘经典,重新梳理儒家传统中具有心性思想的资源。从 《复性书》引用儒家经典的情况来看,《周易》 《论语》 《中庸》 《孟子》 《大学》均被李翱多次引用。暂且不论引用目的是认同抑或是批评,除了 《周易》这本备受儒道两家推崇的经典以外,另外四本书恰好是唐代以后受宋明新儒家极力彰显、为官方首肯的四部经书。以时间计算,从李翱29岁作 《复性书》,到南宋朱熹 《四书集注》在漳州刊出,时间跨度近400年。
儒家心性论的理论建构是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儒家首先面临的是寻找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问题,需要用心性之学的视野和眼光来梳理、圈定可资倚重的经典文本。李翱并没有局限在传统儒家视野范围的 《诗》《书》《春秋》三传等儒家典籍中解经传道,而是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 《中庸》《大学》《孟子》等具有丰富心性思想内涵的文本上来进行梳理和研究。 《复性书》除了推崇 《中庸》之外,还广泛吸收、引用和发挥了 《周易》《论语》《中庸》《孟子》《大学》《史记》《诗经》《尚书》《左传》等儒家著作中的心性思想,为梳理和总结先秦以来的儒家心性理论,开启以心性讨论为主题的宋明新儒学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与 《论语》《孟子》相比,《大学》和 《中庸》在唐代尚不具有与前者并列之地位。 《复性书》不仅引 《中庸》,还引用大量其他文献。李翱作 《复性书》主要是在引用 《中庸》以论证儒家心性之传统,而不只是理解子思著 《中庸》所希望表达的原意——注释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中庸》被李翱塑造成为儒家心学的重要经典。李翱开了一个头,他提出以心性立论来框选儒家经典,这是汉学五经经典系统转向宋学四书经典系统的关键。
三、以 “复性”为工夫
围绕心性问题著说立说在唐代蔚然成风,韩愈、柳宗元、皇甫湜、杜牧等儒家学者纷纷参与其中,但多未跳出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框架:韩愈的 “性三品说”实际上是董仲舒人性论的改良翻版,皇甫湜的《孟荀言性论》、杜牧的 《三子言性辩》则是在对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以及扬雄人性善恶混说基础上对人性观点的对比罗列。而李翱则以孟子的性善论作为心性修养的前提,提出自成一家的 “复性说”: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圣也,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24]
循礼而动,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25]
情者,妄也,邪也。邪与妄则无所因矣。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26]
通过性情关系的角度来解释人性善与不善,李翱从哲学的高度将人性从善与不善的争论中独立出来,主张圣人之性与百姓之性无差,并给出了复性以成圣的方法,不可不谓唐宋儒家心性论中带头推陈出新之举。李翱进一步将儒家圣人之道与心、性关系的处理相结合,把性善论置身现实考量,提出以“复性”为修养工夫。李翱认为:“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
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27]“莫能明”的原因,主要不在性命之书本身,而在于如何体会和把握其中的工夫。工夫是 “为道”或 “见性”的实践、过程和方法,是心对身、心对物的专注和控制。冯友兰认为 “可总代表宋明新儒家讲学之动机。宋明新儒家皆认为当时所认为有兴趣之问题,在儒家典籍中,亦可得相当之解答。宋明新儒家皆在中国典籍中寻求当时所认为有兴趣之问题之解答也。”[28]李翱阐扬四书,探讨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推崇的更是一种 “修己治人”的工夫论。四书学后来被发展成为儒者立志于成就为内圣外王的一整套工夫论是具有充分理由的。[29]
李翱认为圣人制礼作乐以 “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将心性思考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提出“复圣人之性”:第一步为 “正思”。他在 《复性书》中指出:“正思者,无虑、无思也。”为了排除情对性的干扰 (“溺于情”),必须做到 “斋戒其心”,以达到 “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第二步为 “至诚”。 李翱认为,“弗虑弗思,知心无思,情乃不生,虽为正思,离动不离于静,犹未足以复其性”。斋戒其心,心只是静。此静乃与动相对之静,不静时即又动矣。 “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30]此处所指的寂然不动,并非与动相对之静,乃 “动静皆离”,即超乎动静之绝对的静。故圣人虽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其心之本体,仍是 “寂然不动”也。此即所谓 “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 “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第三步为 “循礼”。李翱重视在社会秩序的角度将 “复性”实践与遵循礼乐之道相结合:“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圣也,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安於和乐,乐之本也;动而中礼,礼之本也……视听言行,循礼而动,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31]通过 “循礼”,“复性”乃从个人的道德实践上升为现实社会的群体性意识和行为。
李翱讲究修心养性,其修养方法主要是受子思的影响。同为儒家,孟子和子思的心性修养方法并不相同。孟子主张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重正面直截的易简工夫,其治心只一个 “尽”字,尽心即是诚;子思主张去自欺以存诚,对 “不诚”而 “诚之”,一言致曲有诚,着力点是落实在了反省其心之向于邪妄而去之而成诚。同样是儒学根柢,同样是治心,虽然推崇孟子,但李翱强调 “复圣人之性”,走的是 《中庸》的修养路径。有学者认为,李翱不满意于刘禹锡和柳宗元直接借用佛教的心性论,也不满足于韩愈的心性理论,他要吸收佛教的心性论改造儒学。虽然显得生硬,但却是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一次探索实践,也是儒家在心性论方面的较大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李翱的复性说为后来宋儒的心性论作了铺垫。[32]其实,李翱对复性之方的阐释并不严密,以致成为后儒争议之端,正如冯友兰评价李翱之修养方法时所言:“大学格物致知之说,宋明新儒学对之各有解释。且因其对之解释之不同,宋明新儒家之派别亦因之而分。李翱亦可谓系此后此中争辩之发端者。”[33]李翱的复性论准确地抓住由外在权威向内在权威转化的关键——“人性”问题进行探究。魏晋玄学中也经常讨论性与情的问题,但往往重于 “情”,强调个体的感受,李翱则强调 “性”,强调除去妄情而使人皆有之的圣人之 “性”显现出来,由此建立起内在的权威。
唐代以后,李翱的学术地位日趋提高。北宋欧阳修推崇李翱,认为:“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具论也。”[34]清朝全祖望认为,唐人中 “解 《论语》解 《孟子》,则习之一人而已”。[35]傅斯年认为:“北宋新儒学发轫之前,儒家惟李氏有巍然独立之性论,上承《乐记》、《中庸》,下开北宋诸儒”。[36]心性论成为儒学讨论和关注的重心,是儒学发展史上一次由伦理论向工夫论,由世俗世界向精神世界的重要变化,儒家关注探讨的问题开始逐步从外在的行为规范 (礼)转向内在的道德修养 (理)上来。李翱 《复性书》思想虽然在理论上还不够精致,但其探讨儒家心性论的方向、方式和框架基础上形成的心学理论开创了唐宋时期儒家心学理论建构之先河。
[1][23]周炽成:《“心学”渊源考》,《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
[2]冯国栋:《道统、功夫与学派之间——“心学”义再研》,《哲学研究》2013年第7期。
[3]吴相洲:《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4][5][14][唐]韩愈撰、钱仲联等校:《韩愈全集·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0页。
[6][7][8][9][10][11][17][24][25][26][27][30][31][唐]李翱撰、郝润华校点、胡大浚审定:《李翱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54、55、8、65、7、8、11、6、7、13、8、10、7页。
[12][28][33]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4、253、254页。
[13][15][1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三松堂全集》第9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9-590、587、590页。
[18][清]朱彝尊撰,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冯晓庭主编:《经义考新校》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83页。
[19][36]傅斯年:《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性命古训辨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0-181页。
[20][35][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11页。
[21][22]杨儒宾:《〈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4期。
[29]朱汉民:《朱熹 〈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2]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 (隋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34][北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49页。
责任编辑:罗 苹
B241.6
A
1000-7326(2015)06-0026-05
吴杰锋,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广东 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