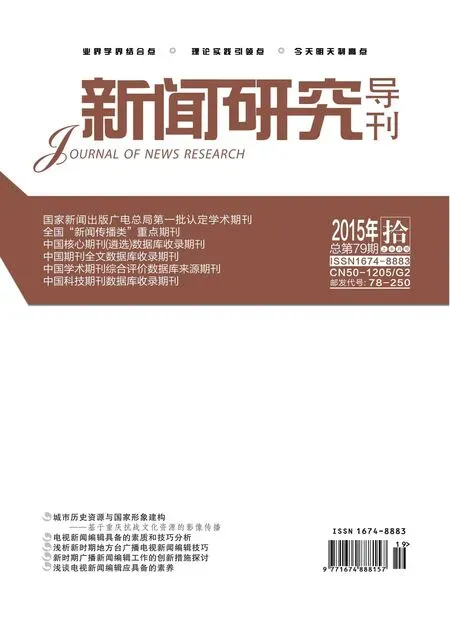浅析重庆《新华日报》是促进新闻界大团结的榜样
唐筱童
(重庆文理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重庆 402160)
浅析重庆《新华日报》是促进新闻界大团结的榜样
唐筱童
(重庆文理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重庆 402160)
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坚强领导下,以抗战大局为重,为了使抗战事业得到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该报率先垂范,广交朋友,普结人缘,打破了国统区中心城市新闻界以往一盘散沙的状态,促成了进步新闻战线的空前大团结。
重庆;新华日报;团结;抗战
按照范长江的说法,抗日战争前,国统区“新闻界过去情形,总是依他的报纸做活动范围,很少有超出一个报纸局面,”基本上处于互不往来的分散状态。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御辱成为时代的潮流。在这一大气候下,为了使抗战事业得到强有力的舆论支持,新闻界的团结问题就显得日益紧迫了。
一、审时度势倡团结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底,武汉沦陷后迁往陪都重庆继续出版,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一再勉励报馆人员,要以抗战大局为重,通过开展统战工作,尤其是新闻界的统战工作,争取友军,来做好报纸工作。1938年9月1日,这天首次被官方定为记者节,《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九一记者节》指出,“从新闻记者本身来讲,第一是新闻记者团结问题”,“希望全国的新闻记者更加团结起来!这种团结的精神,不仅是新闻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同时也是争取民族解放胜利的保证。”文章还批评国民党当局苛刻的新闻、图书检查制度,阻挠了记者们的团结和记者工作地发展。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在国统区中心城市武汉或后来的重庆,不外乎存在三类性质的报刊:一是作为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喉舌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二是与之对立的国民党各派系的报刊。三是民营中间性质的报刊。在民营报刊中,尽管政治背景、立场各有不同,但在宣传抗日救亡这一点上,与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相一致的。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不仅使《新华日报》首当其冲,深受迫害和压制,也使民营报刊苦不堪言,他们也要求摆脱这种羁绊。还在武汉时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16家出版单位就曾联名发表过《武汉出版界请求撤销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呼吁书。而国民党各派系报刊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也非铁板一块。在抗战初期,他们也宣传抗敌御辱,由于中共地下党员几乎渗透到国民党各派系报刊,他们直接或间接和《新华日报》联系、配合,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进步性。据《重庆报史资料》统计,这批中共地下党员达八九十人之多。其中有:中央社的编译人员、记者左恭、刘尊棋等;《扫荡报》记者、编辑谢爽秋、谢挺宇、曹祥华等;《时事新报》总主笔张友渔,国际版主任陈瀚伯;《益世报》经理任廉儒,《西南日报》总编辑张兆麟(刘乐扬)。而在民营报刊中的地下党员就更多了,如《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徐盈、杨刚、彭子冈、高集、高汾、李纯青、季崇威等,《新民报》的记者王素、秦天芬、田君实(田伯萍)等,《国民公报》《商务日报》也有中共地下党员。以上这些因素的存在,为《新华日报》在国统区新闻界开展统战工作,增进团结,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广交朋友促团结
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普结人缘”的教导,《新华日报》在团结报界同仁方面做出了种种表率:1938年5月27日,《新华日报》董事会负责人秦邦宪(博古)、潘梓年、何凯丰等在武汉普海春西菜社设宴款待从徐州会战中突围归来的战地记者,其中除了本报记者外,还有中央社、《扫荡报》、《武汉日报》、《大公报》、新加坡《星中日报》、泰国《华侨日报》等报社记者。此举表明,共产党对在抗战宣传中出过力的各报记者,不以门户之见,是一视同仁的。同时也打破了以往不同党派报刊互相敌视的局面,当时即被新闻界同仁誉为开了报界一个新纪元。
《新华日报》还曾派代表参加“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工作,协助各报在日寇大轰炸后,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办理疏散事宜;恢复出版后,协调分配各报纸张、米、煤等物资,共同商定报纸广告价格等。此外,还参加报界联谊会,各种体育、排字竞赛等活动。在此过程中,《新华日报》与各报有关人员建立了联系,互通有无,互济困难,甚至还曾接济过一时发生纸张短缺的《中央日报》。
《新华日报》的努力初见成效。1939年5月初,重庆连续遭受日军飞机大轰炸,各报损失严重。国民党当局乘机提出由《中央日报》社牵头,组织《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扫荡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等十家报纸共同出一张《联合版》,由国民党中宣部控制,一则统制舆论,二则借此取消《新华日报》和民营报刊。《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当即表示《联合版》是有期限的,到时候即要求复刊。《大公报》等民营报纸也纷纷响应,国民党当局无奈,只得于当年8月13日同意各报复刊。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表新四军为“叛军”,并撤销其番号的“通令”和“谈话”,要求各报刊登,并配发社论。周恩来连夜派人登门造访市内几大报馆,告知事变真相。1月18日,《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刊出周恩来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民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等民营报纸甚至孔祥熙派系的《时事新报》,对于蒋介石的“通令”、“谈话”均采取了沉默、拖延的消极态度,淡化处理,敷衍了事。例如,当时周钦岳主持的《新蜀报》,1月21日在第三版左下角刊出一篇不到200字的短评《肃军与抗战》,对新四军持同情态度,指出,“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希望这种痛心的事件,今后永远绝迹。”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也就是从这时起,大多数民营报刊逐渐倒向以《新华日报》为主体的抗日民主力量一边了。
三、并肩作战大团结
战斗在国民党各派系报刊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为《新华日报》提供了不少重大新闻线索和重要情报。例如,中央社的刘尊棋借1939年9月随前线抗敌将士慰劳团访问延安之际,将毛泽东“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谈话写成文章(即《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提供给《新华日报》和国际新闻社,向国内外广为传播,对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到了积极作用。共产党员徐亦安、杨培新等打入由国民党特务把持的《商务日报》后,逐渐掌握了该报的采编、经营大权,将言论和新闻转到“在商言商”、“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的方向上来。
到旧政协会议前后,绝大部分中间性质报纸和其大部分采编人员被《新华日报》争取过来了,在重庆出现了进步记者群,他们经常在《新华日报》七星岗采访部聚会。每逢集会活动,各报大都推《新华日报》为召集人或召集单位,每逢重大事件、重大报道,总是看《新华日报》抱什么态度,相互策划,达成默契,或采取不同对策,或毅然发表声明、签名书(信)等。在与“谣言制造厂”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新闻专制主义报刊斗争过程中,在舆论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1944年9月16日,毅然全文刊登了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报告,除《新华日报》大登特登外,重庆其他各民营报刊亦相继刊登,这时的《商务日报》甚至全文照登。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一呼百应掀起新闻、图书拒检运动,导致国民党战时新闻、图书原稿送检制度垮台。1946年2月“校场口”事件发生后,中央社、《中央日报》将郭沫若等被特务、暴徒打伤者,诬为打手,将打人的特务刘野樵等说成被害者,即有许多记者签名表示抗议,并揭露亲眼所见事实真相。至此,国民党中央御用报刊人心丧尽,彻底孤立,在抗战初期一度出现的以国民党为主导的中国新闻界大团结局面,逐步变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进步新闻战线大团结局面。
《新华日报》之所以能够促成中国新闻界的大团结,其力量源泉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作指导(如“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有日益强大的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武装力量作后盾,敢于说真话,坚持真理等诸因素使然。另外,由于众多友军的配合,《新华日报》从一开始就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在一个纵深的阵地上作战。《新华日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曾与之共同奋斗的进步新闻战线转入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继续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一分力量。
团结新闻界同仁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共同奋斗,《新华日报》的不懈探索积累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党报、对我国新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里就不赘述了。
[1] 韩辛茹.新华日报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 廖永祥.新华日报史新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3]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G216.2
A
1674-8883(2015)19-0125-01
唐筱童(1967—),男,四川三台人,硕士,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