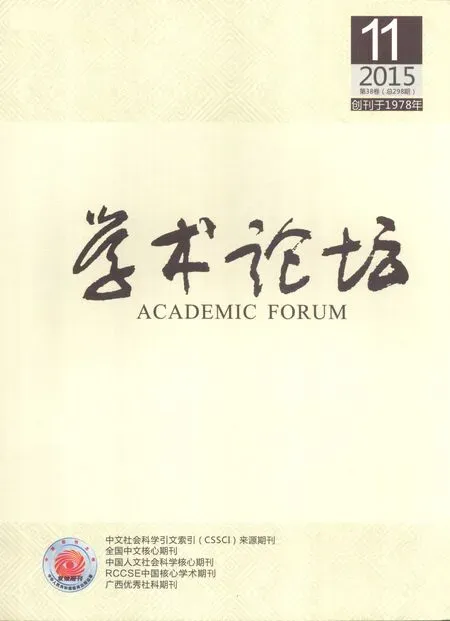论监护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张海龙
一、歧义的“相应的责任”
“相应的责任”在我国法律规范中较为常见,但具体含义往往不同。 有时它是多种法律责任的泛称,如《公务员法》第54 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有时它针对“与有过失”情形,指依法减轻后的责任或由受害人自己负担的部分损失,如《侵权责任法》第35 条第2 句;有时它又指数人侵权中的按份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12 条。
“相应的责任”具有多义性,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责任”的词义较广泛,既可以是因不法行为而生的否定性法律评价,如刑事责任、违约责任,也可以是非因不法行为而由主体所负担的义务,如《侵权责任法》第32 条中的“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 二是没有具体交代“责任”要与什么相适应。 “相应”通常指两类对象的相适应或相符合,而这些对象一般由上下文具体指明,如先交待“问题”、“危机”、“情况”,再提出“相应的措施”或“相应的办法”。 在法律文本省略前提对象时,即需借助语境辨明真意。 如《公务员法》第54 条,因“依法”要件而属引致性规范,其“相应的责任”须由被引用的条文来确定。 由于各类责任的成立要件不一、不同案件事实所能适用的法律不同,该条所针对的案件事实可能只构成民事责任,但也可能构成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等不同类型的责任竞合,因此该条“相应的责任”就只能是一种泛称。
在语言环境较为复杂的时候,辨明“相应的责任”会比较困难,容易发生不一致的理解,进而影响适用法律的准确性。其典型如《侵权责任法》第9 条第2 款:“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学界对此“相应的责任”就形成下述六种主张。
一是“非连带责任说”。 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认为,“在存在教唆人、帮助人的情形下,监护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过于严厉。 本法没有规定监护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1](39)。
二是“类似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责任说”。 全国人大法工委立法规划室吴高盛教授等认为, 该责任并非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而是类似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责任[2](29)。
三是“按份责任说”,即监护人与教唆人、帮助人依各自过错或者原因力的比例向受害人负责[3](P989)。 主张该说的学者相对较多,但因对责任人过错的认识不同,又孳生“次要责任说”、“与过错相适应的责任说”[4](P502)、“减轻说”[5](P51)等几种。
四是“相应的责任说”。 王利明教授等认为,监护人依过错或原因力的比例向受害人负责,而教唆人、帮助人就受害人的全部损失负责,双方在监护人负责的范围内构成共同负责。教唆人和帮助人是终局责任人,监护人承担了相应责任后,有权就其相应的责任向教唆人和帮助人行使求偿权[4](P503)。
五是“单向连带责任说”。 杨立新教授认为,第9 条第2 款规定了一种特殊的连带责任,即只准教唆、帮助人向监护人追偿,但不准监护人向教唆、帮助人追偿[6]。
六是“特殊的补充责任说”[7],又被称为“不真正补充责任”[8]。 薛军教授等认为,仅在教唆、帮助人不能完全弥补损害的前提下, 监护人才承担侵权责任, 并且也只承担相应其过错程度的损害赔偿。 由于补充责任通常以教唆人、帮助人财产不足为前提,而监护人也有一定过错,所以不宜确立监护人对教唆人、帮助人的追偿权。
仅着眼《侵权责任法》第9 条第2 款,难谓上述主张孰为立法真意,因为“相应的责任”在文义范围上得囊括前述诸解释, 而诸解释在利益安排上也都有各自的道理。 由此可知,目前属于歧见相持、尚无通说的学术争鸣阶段。
二、违反解释规则的解释
“相应的责任” 在第9 条第2 款出现歧义解释,即存在“复数解释之可能”,根据法解释学规则,此时无法仅由文义解释辨明法条真意, 须辅之以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其他方法,藉其他要件或其他法条的限制,辨明该用语在具体条文中的准确含义[9](P142)。 然而前述诸解释仅关注第9 条第2 款本身,未考虑该款应与第9 条第1 款、第32 条保持“体系一致”,因此会导致不可调和的法律冲突。
(一)因教唆、帮助人赔偿范围不同造成的法律冲突
排除语焉不详、无法操作的“非连带责任说”之后,前述解释可分成两类:一是教唆、帮助人的赔偿限于过错从而与第9 条第1 款不同(“按份责任说”);二是教唆、帮助人对全部损失负责从而与监护人赔偿范围不同(“按份责任说”之外的几种)。根据法解释学规则,这两类解释将造成下述条文的法效冲突。
其一,将教唆人、帮助人的赔偿限于过错,会造成第9 条前后两款发生冲突。
虽然教唆、帮助的对象不同,但第9 条两款所针对的事实具有类似性与可比性,而教唆未成年人实施不法行为的主观恶性更大,其法律责任显然不应轻于教唆成年人实施不法行为所遭受的制裁。 例如,我国刑法第29 条即规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9 条第1 款令教唆、 帮助人与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其价值取向是 “优先保护受害人”;但“按份责任说”为了避免对监护人“过于严厉”,将第9 条第2 款解释为教唆、 帮助人只须依过错比例负责部分赔偿, 价值取向有所改变。 若该说成立,则意味第9 条前后两款自相矛盾:过错程度相同甚至更重的教唆、帮助行为,侵权责任竟然因对象认知、管控能力较低而减轻!同样的教唆偷窃,教唆成年人的要对全部损失负责,但教唆父母疏于管教的未成年人却只须对部分损失负责,这显然有违“举重明轻”解释规则,会造成“碰撞式价值判断矛盾”[10](P402), 同时也不符合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宗旨。
其二,让教唆人、帮助人对全部损失负责而监护人对部分损失负责,会导致第9 条第2 款前后分句发生冲突。
既然“相应的责任”是监护人对受害人的过错责任,那么监护人与其他责任人一样,都具有未被推定的过错,理当被同等对待。 责任人要么都以过错为限对受害人负责,要么都对受害人全额负责,否则就会导致不平等待遇,同样造成“碰撞式价值判断矛盾”。 监护人还可能兼具教唆人或者帮助人的身份, 因此存在该款前后两分句都规定损害赔偿的竞合。 依该款前一分句,监护人应向受害人全额负责;依该款后一分句,监护人却只须承担相应过错程度的赔偿。 此时,若责任主体仅为监护人(即不存在多数人责任),那么两条文均使监护人负担相同的损害赔偿。 由于法效一致,虽然竞合也无冲突;但如果还有其他的教唆人或帮助人,那就会因为法效不同而形成法律漏洞。 此外,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过错与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过错有所不同,进而导致据以确立的责任份额比例可能不同。司法审判可能综合考虑两种过错之后再重新确定更高的比例,也可能是取两者中的较高比例甚至是较低比例,在法无明文规定的背景下将无法合理约束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二)因监护人赔偿范围不同造成的法律漏洞
除第9 条第1 款外,第9 条第2 款还须与第32 条“体系一致”。 两条文的联系可从非完全行为能力人的赔偿得以求证。 第32 条明文规定受害人可向有财产的非完全行为能力人完全求偿,但第9条第2 款却无此规定,此时若不允许受害人求偿显然不公,因为受人教唆、帮助显然不是非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免责事由,所以在适用第9 条第2 款的同时应适用第32 条,令有财产的非完全行为能力人负赔偿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32 条第1 款第1 句规定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11],如果将第9 条第2 款“相应的责任”理解为监护人承担过错责任,会形成二元归责的监护人责任。 与第32 条第1 款第1 句相比,第9 条第2 款后一分句的构成要件多出了“过错”,因此,当同一法律事实同时符合上述规定的构成要件时,就发生构成要件包含的法条竞合。 由于前述诸解释认为监护人仅负部分给付义务,而第32 条第1 款第1 句却规定监护人的全部给付义务,所以上述竞合条文将产生法效冲突(即“规范矛盾”的法律漏洞)。
“规范矛盾” 能够而且也必须被避免或排除[10](P394)。 要保证第9 条第2 款具有规范意义,必须限制或者排除第32 条第1 款的适用,学界因此提出三种方案:一是主张依法律适用规则限制第32 条。 当监护人有过错时,两条文虽然构成竞合,但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优先适用第9 条第2款后一分句,由监护人承担“相应的责任”;[12]当监护人没有过错时,两条文不存在竞合,只能适用第32 条第1 款[4](P504),由监护人承担适当减轻的无过错责任[13](P267)、有财产的非完全行为能力人承担公平责任[14](P268)。二是主张“尽到监护义务的监护人不承担责任”,从而以此为据排除适用第32 条[15](P80)。三是采用限缩解释,使第32 条仅针对未受教唆、帮助的非完全行为能力人侵权,从而实现两条文调整范围不同以及不发生竞合的目标[7]。 然而上述三种方案都有一些问题。
第一种方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制造了更不合理的新漏洞。 按照这种方案,监护人无论是否有过错都须负责,即有过错的监护人依第9 条承担相应其过错比例的份额责任,而没有过错的监护人依第32 条对全部损失承担适当减轻的责任。 假设“过错比例”为(A),“适当减轻的比例”为(B),全部损失为(M),则“相应的责任”为(M×A),而第32条的赔偿责任是(M﹣M×B)。 如果(M×A)﹤(M﹣M×B), 即没有过错的监护人责任竟然重于有过错的监护人责任,那么显然存在轻重失衡的错误,构成“碰撞式价值判断矛盾”。 即使“相应的责任”高达全部损失的80%,但只要有一起判例确定“适当减轻的比例”为19%以下,比较两案判决都会发现不公。 难道说规定“相应的责任”就是为了让监护人因为“有过错”而减轻赔偿?
第二种方案未论证其论据(即“尽到监护义务的监护人不承担责任”)的真实性,以致“排除适用第32 条”的结论存在逻辑错误。 该论据未被现行法明文规定,也不能由过错责任推出①根据文义解释,不能证明第9 条第2 款表述了“监护人无过错构成免责”的法效。 根据体系解释,也不能认为过错责任本身就包含着“没有过错构成免责事由”,因为这会使无过错责任的存在基础荡然无存。 因此,“没有过错”在侵权法上并非免责事由,而仅仅是不具备“过错要件”的证明,或者公平责任的前提要件。,因此最多算第9 条第2 款后一分句的学理解释。第9 条第2款后一分句是假言判断, 而该论据否定了这一判断的前件与后件, 因此属于对第9 条第2 款后一分句的“反面解释”。 “反面解释”是原命题的否命题[16]。 当原命题是充分条件假言判断且为真命题时,其否命题不一定成立;当原命题是必要条件假言判断或者充分条件假言判断且为真命题时,其否命题成立[17](P119)。 传统民法因此禁止对前一类条件关系的规范进行“反面解释”[9](P116),而不禁止对后两类条件关系的规范采取“反面解释”[18](P375)。 就第9 条第2 款后一分句与第32 条第1 款第1 句的法律效果而言,如果两者不同,那么即使做“反面解释”也只是排除“相应的责任”,而不能排除第32 条的监护人责任;如果两者相同,那么第9 条第2 款后一分句就是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就不能对其进行“反面解释”。
第三种方案限缩解释第32 条的理由并不充足。 虽然有学者认为,“必须对第32 条所调整的范围进行限缩解释,将其限缩解释为只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受到第三人的教唆、帮助的情况下,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监护人承担一种不可推翻的推定过错的责任才是合理的”[7]。 然而从比较法来看却存在推翻这一理由的域外法规定。例如德国民法典在第830 条第2 款规定教唆人与辅助人的共同侵权责任、第832 条第1 款规定推定过错的监护人责任之后[19](P240),由第840 条第2款承认上述两款发生法条竞合——排除第420 条(按份责任)的适用以确保受害人免受个别责任人无支付能力之虞, 从而使监护人与共同侵权人须向受害人承担不真正连带债务, 监护人仅在与共同侵权人的内部关系中不负义务[20](P764)。
令人担忧的是:排除适用第32 条可能造成架空监护人无过错责任的危险。 监护人为了避免第32 条的无过错责任, 或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份额, 在不构成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可能找到无资力的人假充帮助人, 从而实现加重受害人的举证义务、减轻自己实际负担的不法目的。 如果此类经验口口相传,第32 条就难免沦为法律白条的命运。
三、否定连带责任的理由
前述诸解释认为监护人仅负部分赔偿,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由监护人对教唆人或者帮助人的最终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的做法是难以理解的, 这相当于认为监护人的监护对象还包括教唆人和帮助人”[8]。 二是“第9 条第2 款并没有确定教唆人、 帮助人与实施侵权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之间的共同侵权关系, 因此二者之间也不是一种连带责任关系”[7]。三是“在存在教唆人、帮助人的情形下,监护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过于严厉”[1](P39)。
然而这些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将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视为监护范围扩大的说法不知师承何处,逻辑显得较为诡异。 依据我国司法审判经验,数未成年人共同危险行为侵害第三人,或者数未成年人共同加害第三人的,其监护人之间也要承担连带责任,难道这些监护人对彼此的子女都形成了监护关系? 又是哪种法律事实导致了这种溯及既往的变更?
其次,依当前通说监护人责任与教唆、帮助人责任确非共同侵权, 但不构成共同侵权不等于不存在连带责任,因为“债务人不是基于相同的规定或理由而承担责任,不影响其连带性”[21](P207)。 以此由否定连带责任,是无法解释下列现象的:(一)并非共同侵权,但被《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为连带责任的第51 条、第74 条等规定[1](P35)。 (二)并非共同侵权而立法表述也无“连带”字样,但通说认为发生连带的现行法规定, 如《侵权责任法》 第43条、第68 条、第83 条。 (三)规定监护人与教唆、帮助人发生连带责任的域外法,如瑞士、奥地利、荷兰、 台湾就有类似前述德国民法条文的相关规定或者判例[22](P405)。
最后,“连带责任对监护人过于严厉” 的判断有失片面。 在许多人看来,第32 条对监护人规定无过错归责,是为了保护受害人而不得已为之,监护人可责难性往往不重;在出现教唆人、帮助人的时候,鉴于存在可责难性更强的其他责任主体,此时应还个“公道”给监护人,使其免于承担全部责任。 这样的愿景看似很美,却可能遭遇顾此失彼的现实不公, 因为监护人较其他责任人可责难性更重的情况也时常发生,“监护人可责难性较低”可能只是先入为主的错觉。 前不久山西太原某家长向其亲戚借车,明言是供未成年的儿子学车,孩子在学车中发生交通肇事伤害无辜路人,鉴于监护人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综合比较因素远高于提供车辆的帮助人,法院判决家长与车主共同承担连带责任[6]。 此案说明:其他责任人的出现未必是改变受偿不能风险负担的关键。 但按前述诸解释,则有两类结果:一是判监护人承担部分赔偿、帮助人承担全部赔偿,二是判监护人、帮助人均为部分赔偿,其赔偿比例依过错程度或原因力而定。 然而前者会导致过错重的责任人承担部分赔偿、 过错轻的责任人承担全部赔偿,后者会导致因责任人的增多而加大受害人的风险负担,总之都是悖于侵权法常理的不公。
四、基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解释
当前诸说均为学理解释,因此仍可探寻符合法解释学的立法意思。 依我国理论与实务广泛采纳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本文建议从内部效力的角度解释 “相应的责任”(前述诸说则从外部效力,即监护人与受害人之间进行解释)。 也就是说,将“相应的责任”仅理解为监护人依过错负担的内部责任,监护人对受害人的外部责任仍由第32 条确立,第9 条第2 款与第32 条形成法效果内容不同但性质上可以并存的竞合。 受害人对教唆、帮助人依第9 条第2 款前段分句、对监护人依第32 条第1 款第1 句,可提出全额赔偿的侵权请求权。 虽然这两种请求权的发生基础、法律性质、构成要件皆有不同,如教唆人为自己责任而监护人为替代责任,但理论上可解释成因法条竞合导致的不真正连带债务。
就外部关系而言,第9 条第2 款前段分句与第32 条第1 款第1 句均为独立的侵权请求权基础。 监护人责任与教唆人、帮助人责任虽基于不同原因而发生,但目的均为满足受害人利益,也均因向受害人全部清偿而消灭,法效果并无冲突。 虽对同一法益提供重复保护,但不使受害人重复满足即可[10](P213),因此得为并存,使各责任人对受害人独立负担全部给付义务。 这样既反映了第9 条规定监护人责任的内在逻辑,也体现了连带债务的整体性和选择性。
就内部关系而言,第9 条第2 款后一分句与第32 条第1 款第2 句不会出现法效冲突,因为前者针对内部责任(责任人之间)而后者针对外部责任(受害人与责任人之间)。 由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务人之间虽然通常没有追偿关系,但法律可对不真正连带债务中的追偿作出特别规定(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40 条第2 款或者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3 条第2、3 款),所以第9 条第2 款后一分句作为规范内部责任的特别规定是没有问题的——当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时,须按过错比例与教唆、帮助人分担损失,可就超出比例的已赔部分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在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时,可就其承担的赔偿向教唆、帮助人全额追偿。
这种解释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满足体系解释规则,遵循“优先保护受害人”的统一价值取向,避免相关条文形成法律冲突。 二是依托传统民法理论解释现行法规定,既符合司法实践经验,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创新[6]。 三是遵循同样思路可以解决类似竞合问题,如“教唆、帮助人”也是非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情况。
五、结 语
《侵权责任法》第9 条第2 款所引发的争议,折射出域内外立法技术的差异:语义含混的“相应的责任”在我国现行法广泛使用,但在传统民法却极其罕见。 两相比较,“连带债务”、“按份之债”、“损害赔偿义务”等术语更加准确、规范、可操作,而“相应的责任”却像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虽囊括按份责任、连带责任、竞合责任等多种类型,但却使本该责任类型化的条文丧失具体指示作用,无谓的增加司法操作难度,不必要的扩大司法裁量范围。
“相应的责任”作为立法技术由来已久,早在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 条就规定:“教唆或者帮助造成损害的人,应以共同致害人对待,由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部分共同致害人无力赔偿的,由其他共同致害人负连带责任。 ”在草创《民法通则》的时代,立法语言粗糙一些情有可原,但在法学昌明的当下,却必须正视这项从前未曾注意、未能改正的沉疴。 对照传统民法的经典表述可知,至少在侵权法领域,我国能够并且应当使用更规范的术语来替代“相应的责任”。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吴高盛,邢宝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精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3]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4]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 孟勤国,张海龙.质疑“单向连带责任”[ J].社会科学战线,2015,(3).
[7] 薛军.《侵权责任法》对监护人责任制度的发展[ J].苏州大学学报,2011,(6).
[8] 王竹.论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原则[ J].苏州大学学报,2014,(2).
[9]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10]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1] 金可可,胡坚明.不完全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构成之检讨[ J].法学研究,2012,(5).
[12] 杨立新.教唆人、帮助人责任与监护人责任[ J].法学论坛,2012,(5).
[13] 程啸.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4] 周友军.侵权责任认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5] 奚晓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16] 吕曰东.反对解释:规则与适用[ J].山东审判,2006,(2).
[17] 雍琦.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8] 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丁晓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9] 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M].齐晓琨,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0] 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M].杜景林,卢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1] 高圣平.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和示范规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2] 王泽鉴.侵权行为(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