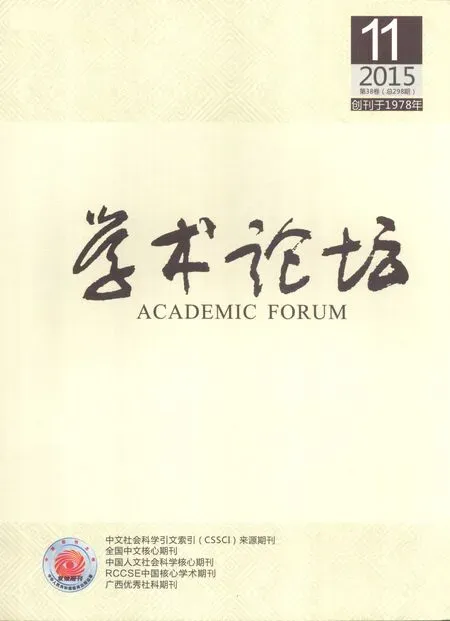儒家人权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
黄 英
一、问题的提出与产生的背景
“儒家”与“人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近代西方人权理论诞生前夕。 “早在17、18 世纪,儒家思想就已经在遥远的欧洲与人权观念发生了联系,促进了欧洲近代人权观念的产生。 ”[1]这就是国人引以为豪的“东学西渐”。 然而,时移势易,鸦片战争以后,西学强势东渐,以“人权”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又反过来成为批判和讨伐中国传统儒学的利器。新文化运动中,“儒家”与“人权”被认为是不共戴天的两极,“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势若水火。 如今,人们又破天荒地发明了“儒家人权思想”这样的新词,并如火如荼地探讨如何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那么,问题来了:“儒家”与“人权”百年来的恩怨究竟因何而起? “儒家人权思想”这一表述是否言之有据? “创造性转化”有何新意和深意? “儒家人权思想”又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而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都与近代中国面临的“大变局”息息相关。
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乃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第二次历史变迁,是数千年一遇的具有整体性、根本性、革命性、长期性的历史巨变[2](P29-30)。“大变局”颠覆并摧毁了传统儒学,且几乎酿成亡国灭种的惨剧, 中国从此进入曲折而艰难的社会转型期,“现代化” 成为救亡图存乃至强国富民的唯一法门,“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 就是中国的现代化”[3](P146)。 为此,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当前的改革开放,无一不是中华民族为了走出大变局、实现现代化而做出的努力。 “儒家人权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便是这种努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是近代中国“大变局”背景下产生的新思路和新课题。
百年来,围绕“儒家人权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论战,争议的焦点有三:第一,传统儒家到底有没有人权思想? 第二,儒家人权思想能否进行创造性转化? 第三,儒家人权思想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二、传统儒家是否具有人权思想
传统儒家到底有没有现代人权思想? 这一问题自“五四”以来就备受关注。 各种说法纷至沓来,聚讼纷纭,先后出现了“古无有也”“古已有之”和“本无后有”三派观点。
早期的思想家,无论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儒家,都毅然决然地坚持“古无有也”的观点, 认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产生 “权利”的意识和观念。 梁启超、嵇文甫和梁漱溟即是该派的主要代表①由于当时“人权”话语尚不流行,相关的论著常以“权利”和“民权”代之。。 梁启超指出:“民权之说,中国古无有也。法家尊权而不尊民,儒家重民而不重权,道墨两家此问题置诸度外,故皆无称焉。 ”[4](P228)嵇文甫认为,民权思想的产生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那就是近代工商业(即资本主义)的发达与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的出现,这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他确信中国古代没有民权思想[5](P446-474)。 梁漱溟也断言:“人权自由之观念,诚非中国所有。 ”他还进一步解释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6](P232,238)这些论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直指中国文化的软肋,因而极具说服力。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坚持这种看法②国内学者如陈弘毅(香港大学)、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和乔清举(南开大学)等始终坚持“古无有也”的观点,国外的比较法学者如德国的K·茨威格特、H·克茨,美国的H·W·埃尔曼,法国的勒内·达维德,以及汉学家李约瑟和史华慈等也都否认中国古代有人权观念。。
然而,传统毕竟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尤其是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已然成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依托。 割裂了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的联系,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此,20世纪末,国学研究持续高热,在传统中发掘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并将它们与现代文明相对接,成为新时代的普遍共识,“传统儒家到底有没有人权思想”的问题再度引发关注和热议,相继产生了“古已有之”和“本无后有”两派观点。
“古已有之”派与“古无有也”派相对立,其主张可大致分为萌芽说、部分说和丰富说三种。 萌芽说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姜广辉为代表, 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权利”观念,儒家所具有的只是一些人权思想的萌芽。 部分说认为传统儒学中含有现代意义上的第二、三代人权,其“民本”、“仁政”、“富民教民”、“制民恒产”等思想就是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 但缺乏现代人权思想中最最核心的部分,即第一代人权所主张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大陆学者陈来、李存山和台湾学者李明辉都曾持此观点③参见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21-34 页; 李存山:《儒家的民本与人权》陈启智、张树骅:《儒家传统与人权·民主思想》,齐鲁书社, 2004 年第83-96 页;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47-65 页。。此外,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传统儒家蕴含着丰富的人权思想,如倡言良心自由和人格尊严、主张法律平等和公正处罚,坚持思想言论自由、反对治心,以及推崇爱国和大同世界等,谷春德、汤恩佳、李世安、陈志尚、林桂榛等为其代表④参见陈启智、张树骅:《儒家传统与人权·民主思想》,齐鲁书社,2004 年第23-28 页;中国人权研究会:《东方文化与人权发展》,东方出版社,2004 年第139-148,164-171,172-180,198-204 页;林桂榛:《话说儒家思想与人权标准》,联合早报,2010 年3 月22 日。。
相形之下,“本无后有”派的观点相对持正公允,因而最终为人们所接受。 他们强调指出:人权思想作为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不仅中国古代没有,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古代社会都没有。 但是,“本无”并不排斥“后有”,因为“对任何一个传统来说,都会有些东西是其本来没有而将来也难以接纳的;同时也都会有些东西是其本来所没有而后来或将来可以接纳的”[7](P29)。陈来、陈弘毅、李明辉、俞吾金、乔清举等都是该派的领军人物⑤参见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21-34;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47-65 页;陈弘毅:《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人权观念》,法学,1999 年第5 期;俞吾金:《西方的人权理论与儒家的人的学说》学术界,2004 年第2期;乔清举:《论儒家思想与人权的关系》,《现代哲学》,2010 年第6 期。。 至此,“传统儒家有没有人权思想”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研究的重点转入下一环节。
三、儒家人权思想能否进行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转化” 由台湾学者林毓生率先提出,意指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加以重组或改造,使之既符合时代精神,又保持民族特色。 “创造性转化”是我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重大课题,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而儒家能否开创出自己的人权学说,首先要看“儒家”与“人权”之间能否进行“创造性转化”。 这一问题经过近20 年的探索, 在西方汉学家、海外新儒家以及国内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达成了如下共识:
(一)传统思想与现代文明的结合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一个传统是可以逐渐演化的,甚至可以更新自己。 ”[8]儒学作为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接受和吸收人权思想并非没有可能:“把人权语言还原后的内容与儒家思想进行交谈,便可发现,已有的人权国际公约的内容, 没有什么是儒家精神立场上所不可接受的。 ”[7](P32)进一步说,儒学要复兴,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必须走与人权等现代文明相结合的道路。
(二)传统儒家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直接与第二、三代人权理论相对接。 人权学说自17、18 世纪由欧洲启蒙思想家创立以来,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至今已形成比较系统的三代人权理论,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以及发展权、环境权与和平权。其中第二、三代人权更多地体现为民生和集体人权的内容,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民本、中庸、协和、立人达人、天人合一等精神完全契合,可以直接转化为与现代人权思想。
(三)传统儒家还有一些思想资源可以促进第四代人权理论的开发。 当今世界价值多元、诉求各异,且国际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以致贫富差距、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滋生蔓延,严重危及人类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应该进一步发展现代人权理论,开出第四代人权,而儒家思想中的某些精髓(如絜矩之道)正好可以作为第四代人权的理论支点①如乔清举认为:“儒家思想不仅可以转化(为人权思想),而且从当今人类的存在状况来看,它还具有‘校正’现代人权观念,形成第四代人权观念的价值”。 参见乔清举:《论儒家思想与人权的关系》,《现代哲学》,2010 年第6 期。。
(四)传统儒家的本质精神与第一代人权理论的要求背道而驰。 传统儒学始终以维护宗法等级和君主专制为终极目标, 极力倡导忠孝节义纲常伦理以压制个人权利和民主自由。 在这样的思想钳制下,根本不可能产生与“权力”抗衡的“权利”意识,也不可能形成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而只能是封建帝王一人之下的“臣民”,这与第一代人权理论中的公民权与政治权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备受推崇的所谓“民本”,其本质也只是为民做主、吊民伐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因此, 传统儒学与第一代人权理论之间存在重大分歧和本质冲突, 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化解二者的矛盾,成为儒家人权思想理论建构的关键。
四、儒家人权思想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诚如论者所言, 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与第一代人权理论是根本对立互不相容的。 首先,儒家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和君主专制制度为最高宗旨,所谓的“民本”仅仅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这与现代人权理论捍卫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主张是本末倒置的。 其次,儒家特别强调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和忠孝节义等纲常伦理, 人权理论则旨在维护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因而极力主张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 再则, 儒家宣扬家国同构,重视群体利益,排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而后者正是现代人权理论的核心和基础。 对比分析后不难看出,传统儒学的立论根基存在重大缺陷,不仅有违人权理论,而且严重背离时代精神,必须做出重大调整和实质改变,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完成与第一代人权理论的对接, 进而开创出自己的人权学说。
(一)援“法”入“儒”,接受现代法治理论,转变德主刑辅观念,将儒家人权思想的理想落到实处。“儒家哲学作为一个精神传统是有活力的,但高远的理想难以落实,于是造成了当前的困境。 ”[9](P3)事实上,这也是儒学的历史困境,中国两千多年的治乱循环不啻为儒家治平理想一再落空的明证。 而“高远的理想”之所以“难以落实”,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程序保障, 在更深层面上则是由于对“法”的认识过于狭隘和偏颇,将“法”等同于“严刑峻法”,忽视了法的行为矫正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治、德治和礼治,进而为君主专制所利用和操纵,导致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人权”本身也不是空洞的口号,它包含着明确而具体的内容,需要通过法律加以规范和保护。 因此,儒家必须重视和充实“法”的观念,跳出德主刑辅的思维窠臼,摒弃传统的人治模式,用现代法治的理念和方式将“儒家人权思想”的愿景加以严格而缜密的贯彻落实,才能避免该理论最终不流于空谈。
(二)弃“君”守“民”,吸收平等自由观念,拓展民本主义内涵,使儒家人权思想的内核饱满完整。传统儒家虽然重民爱民,倡导民贵君轻,但更加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主张“天生民而立之君”,在“民”之上另设一个“君”来主宰其命运,并且要求“民”绝对服从“君”的统治。 这种无条件的顺从和效忠不仅助长了“君”的独断专行和肆意妄为,也从根本上剥夺了“民”的权利和自由。 因此,儒家的“民本”不过是一具抽掉了“民治(by the people)”之实的空壳,徒有“民有(of the people)”和“民享(for the people)”之名。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民有”和“民享”在事实上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能不能“有”和能不能“享”全在“君”的一念之间,是“君”的恩赐和施舍,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甚至可予可夺。 由是观之,果断而彻底地抛弃“君”本位,固守“民”本位,同时摒弃宗法等级观念,引入自由平等思想,让每一个人做自己的主人,才是儒家唯一正确的抉择。 “儒家的民本思想经过批判继承,吐故纳新,扬弃其落后的等级尊卑观念,承认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便可以同‘第一代人权’的观念相契合。 ”[10](P93)惟其如此, 也才能保证儒家人权思想的精神内核饱满而完整,长久而稳定。
(三)重“义”尊“利”,融入当今权利语境,走出重义轻利误区,为儒家人权思想的发展谋求空间。传统儒家勇于担当,“仁以为己任”,义利之说不仅被誉为儒家第一要义,也塑造了中华民族“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传统美德。 然而,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明显有悖于当今的权利本位观,也与儒家人权思想的要求自相抵牾。 更有甚者,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义”与“利”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根本对立而无法并存的。 因此,“舍小利存大义”、“因公义去私利”甚至“存天理去人欲”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更被视为最大的“义”而大肆宣扬。 于今观之,这些观念都因过于偏颇而严重背离了时代精神, 更无法与现代人权理论相接榫。 因此,必须彻底颠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走出重义轻利的误区,在当今流行的权利话语框架下,承认“利”的正当性,把“利”摆在与“义”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视“大利”为“大义”,这才能够为儒家开创出自己的人权思想谋求适当的发展空间。 反之,一味地抬高“义”而贬低“利”,将使儒家人权思想的理论无以立足。
当然,在传统儒家的思想宝库中,还有很多与人权相关的精髓(如仁爱、忠恕、人性、天爵等)值得我们认真检视,在当今的多元文化背景下进一步加以提炼和创造性转化,以丰富和完善儒家人权思想。 此外,近年来,儒家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也得到了某些西方汉学家的青睐,认为由此可以为儒家阐释人权开启新的通道[11](P94-95)。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儒家人权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是儒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局”背景下产生的新思路和新课题。 该命题的提出和论证表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经过百年的沉寂和反省, 已经走出了挫败、迷惘和困惑,走上了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道路, 而这也正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的号角已经吹响, 民族复兴的步伐愈益坚定,但是,中国的发展显然不宜过分依赖经济和军事,而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制度等软实力的建设,以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家形象。 因此,有理由相信,“儒家人权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对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复兴, 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至“中国梦”的实现,都具有至为重大的意义。 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我们没有权利做一个旁观者,我们必须以良心、智能与热忱加以拥抱。 ”[3](P156)
[1] 乔清举.论儒家思想与人权的关系[ J].现代哲学,2010,(6).
[2] 程燎原.中国法治政体问题初探[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3]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4]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 嵇文甫.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民权思想么[A].嵇文甫. 嵇文甫文集(上)[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6]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 陈来. 孔夫子与现代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 陈弘毅.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人权观念[ J].法学,1999,(5).
[9] 刘述先. 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展望[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10] 李存山.儒家的民本与人权[A].陈启智,张树骅. 儒家传统与人权·民主思想[C].济南: 齐鲁书社,2004.
[11] 沈美华.人权的儒学进路[ J].韩锐,刘晓英,译.现代哲学,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