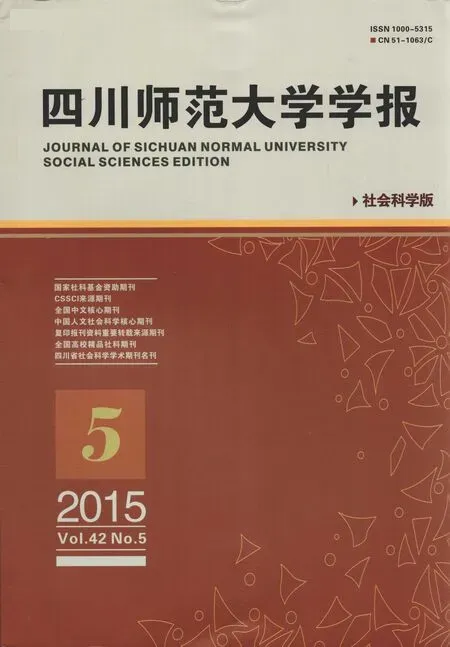古代小说语-图互文现象初探——以插图本《三国演义》为例
王 凌(1.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21;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710062)
古代小说语-图互文现象初探——以插图本《三国演义》为例
王 凌1,2
(1.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21;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710062)
摘要:明清小说插图的绘图者们热衷于通过对最具“孕育性”顷刻的把握、特殊的时空分割方式以及独具意蕴的静态绣像描画以达到最真实、准确再现文字信息的目的;而插图对故事场景进行的带有情感倾向的取舍、图题的褒贬寄寓以及有意无意的图、文不符现象,又表明绘画者试图对小说作出符合自身审美习惯解读的努力。在插图本小说中,文字与图像之间呈现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明清以来各插图本《三国演义》,正是明清插图小说语-图互文规律的代表。
关键词:明清小说;语-图互文;《三国演义》;小说插图
一
在我国传统文化之中,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密切,“图”、“书”二字的正式结合在《史记》中已有表现,“左图右史”、“左图右文”是古代书籍早已采用的表现形式[1]132。有学者曾将我国插图艺术的起源追溯至战国秦汉的帛书插画[2]17;而木刻版画的出现,则一般以晚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扉画为开端①。具体到小说插图,学界普遍认为唐代的佛教活动——“变相”对其产生了直接推动[3]93-105。胡士莹先生认为,“变文中的图画,往往在故事情节关键处加以提示,图,显然是为了加强故事气氛而展开”,表演者“指出某‘处’画面让观众看,同时开始将画上的情景唱给观众听,加深了观众的印象。这对话本中散文叙事之后,插入一些骈语和诗词来描绘景物,是有直接影响的,而后世小说插图的来源和意义,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示”[4]34-35。文与图的关系如此密切,只因在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创造意境等方面各有优势,二者结合方能让读者获得最为丰富的阅读体验。自20世纪鲁迅、郑振铎等学者开始关注文学插图以来,学界对明清小说的插图研究已经积累相当成绩;不过,对传统插图研究多从我国版画发展史或书籍出版印刷史角度展开②,集中从小说文本意义及接受视角切入插图的研究还是相对晚近的事。西方叙事学、图像学理论的引入为传统小说研究带来新的活力,“读图”作为近年流行起来的文化视野也推动了小说插图研究的繁荣景象③。不过,我们对语言与图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命题——互文性仍然所论不多④;有学者甚至认为“中
外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中国古代叙述中这一十分明显而独特的现象”,而这“不仅有违中国古代叙述的原初形式与阅读交流状况,而且也难以全面揭示中国古代叙述独特的叙述原则与叙述风格”[5]。
程锡麟将互文性理论分为以热奈特为代表的狭义互文观和以克里斯蒂娃及罗兰·巴特为代表的广义互文观,他认为,前者将互文性界定为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后者则将互文性内涵扩展至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6]。互文性涵盖文本的意义生成与意义接受两个维度,是文学研究中难以回避的理论话题。互文性理论否认文本边界的存在,认为每个文本都向其它文本开放,作品意义的生成及解读完全依赖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泛文本化的互文视野中,“其它文本”既有可能是完全独立于该作品之外的另一部具体作品,也可能是与作品有着密切联系,甚至本身从属于作品的特殊部分(如插图)。插图是画家在忠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基础上进行的创作,是“用图画来表现文字所已经表白的一部分意思”的艺术[7]3,“是对文字的形象说明,能给读者以清晰的形象概念,加深对文字的深刻理解”[8]234。尽管古代小说的文字文本与图像文本出现各有早晚,但二者作为共时存在呈现给当代读者却是不争的事实,语言叙事与图像叙事之间相互参照、互为背景的特殊关系因此也就成为小说读者了解作品的必然途径。对于文学作品中文字与插图之间的关系,热奈特曾将其归入“跨文本性”中的特殊类型——“副文本性”⑤。事实证明,作为插图的副文本不仅能为阅读“提供一种氛围”,从而引导读者的接受,而它本身也表现出对小说作品的独特理解。文字与图像之间究竟是“因文生图”还是“以图解文”?也许只有“互文”这一“中西结合”的特殊概念才足以囊括这种奇妙关系的全部所指。本文就以明清以来的插图本《三国演义》为具体考察对象(《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有不同名称,在此为方便起见,故统一称号),对古代小说中的语-图互文现象作一尝试性探讨。
作为明清时期最重要的白话长篇之一,《三国演义》拥有该时期小说的典型文本呈现特点。明代出版业的繁荣曾对小说的创作、传播造成巨大影响,二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插图本(绣像本)的出现便是出版商针对读者趣味作出迅速反应的表现之一。万历年间的小说出版已达到“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的程度[9]51。这些以营销为直接目的的插图本小说,不仅以其形象、直观的优势成功吸引了读者眼球,还通过图像的叙事、抒情功能从不同角度引导着后续读者把握文字内容,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向我们传达了以绘图者为代表的读者群对作品的理解,成为我们了解小说接受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三国演义》的故事内容历来深受大众欢迎(从说书活动的繁荣即可见端倪),而出版商更希望迎合读者口味来获得更大利润,因此在插图上颇用心思,也就造成了大量插图本存世的局面。现存插图本《三国演义》中,叶逢春本(《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出现最早,该本采用常见的上图下文版式,每页一图(现存1500余幅),内容详尽;汤学士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插图形式与之类似,也是上图下文;周曰校本(即万卷楼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双面连式对叶大图(每则一图,存160幅),插图标题书于右侧,此外插图左右各有图题一句,根据图中所题刻画者姓名可知插图属金陵版画。此外,李卓吾评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存图200幅;英雄谱本(《二刻英雄谱》)为崇祯年间建阳雄飞馆所刊,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合刻本,插图形式为半叶大图,共100幅,《三国演义》62幅。诸如此类,不可遍举。
文字叙事依赖语言符号,读者通过阅读文字生发联想与想象,在脑海中勾勒出故事情景,由此完成对作品的理解;而图像叙事则具体可感,它通过线条、图形、色彩等直接诉诸视觉,为读者带来感官体验。莱辛在《拉奥孔》中论及诗与画的界限,认为诗叙述的是“时间上先后承续的动作”,而画则描绘“空间中并列的物体”[10]222。有学者因此指出,“图像叙事是叙事媒介由时间艺术向空间艺术的转变”[11]174。在表现故事时间性(或情节性)方面,文字叙事颇占优势;而在表现故事的空间性上,图像叙事亦拥有独特方便。
以万卷楼本《三国演义》图16为例,该图配合连环计王允谋董卓情节,绘图者选取了最精彩的吕布戏貂蝉片段,插图右侧为仙鹤古树掩映之下的董卓双手扶冠,左侧为吕布与貂蝉在亭中缠绵,画戟被置于吕布身后,双页合并,画面场景的空间感极强,两个分镜头并置,呈现突出的戏剧性效果:太师入后园
之前先正衣冠,庶几暗示其对貂蝉的用心;而貂蝉与吕布的私会则对此形成解构(见图一[12]146-147)。

图一
文字叙述遵循线性时序,先述吕布趁董卓与献帝议事而入后堂寻貂蝉,后述貂蝉与吕布在凤仪亭私会,再述董卓因不见吕布在侧而生疑遂入园寻找。带给读者的是清晰的时间—因果线索。而插图的优势不在于交待故事发生的因果逻辑,而是通过对瞬间场景的捕捉为读者呈现一个富于张力的意义世界。如果说直观的自然环境画面营造出的是扑面而来的现场感,那么人物微妙却又复杂的神态表情却传达出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引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
二
小说插图原为配合文字内容而来,表达的是“特定文本中的特定故事”[13],因此天生具有依附性。“因文生图”也就成为古代小说语-图互文关系中最基本的层次。明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曾针对小说插图有云:“此书曲尽情状,已为写生,而复益之以绘事,不几赘乎?虽然,于琴见文,于墙见尧,几人哉?是以云台、凌烟之画,《豳风》、《流民》之图,能使观者感奋悲思,神情如对,则象固不可以已也。”[14]可见,插图的首要功能是配合文字内容,通过图像的直观性感染读者。那么,如何有效地捕捉小说的文字信息,并将之以生动可感的画面呈现,不同的绘图者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一)挑选“孕育性的顷刻”
在将文字叙述的时间艺术转化为图像符号的空间艺术过程中,绘图者必须首先对内容作出选择。莱辛指出,“(绘画)艺术由于材料的限制,只能把它的全部摹仿局限于某一顷刻”,因为“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10]18。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并非故事情节的高潮,而往往是事物到达高潮之前的某一瞬间,这是因为事物“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10]19。而透过最富“孕育性的顷刻”,读者则可以充分发挥想象,推测、认识事物的前后语境。



图二
在众多《三国》版本之中,插图的密集程度各不相同。有每页配图者(称“出相”),如采用上图下文版式的叶逢春本每三百左右文字配合插图一幅,密度极大。在凤仪亭吕布戏貂蝉一段情节之中,单是吕布与貂蝉在太师府中相见情景,叶逢春本就配有三幅插图:一幅绘貂蝉初入府中为吕布所窥(卷一图58左:吕布于帘外偷望,梳妆中的貂蝉似有所觉,遂转身做忧郁状与吕布眼神互动);一幅为吕布与貂蝉在董卓榻前眉目传情(卷一图59右:吕布于董卓榻前张望,貂蝉则掀开帷帐一角与之迎合,娇媚之态尽显);一幅为吕布与貂蝉凤仪亭幽会(卷一图59左:吕布在亭边右手执戟,左手似作推阻之势,而貂蝉于亭内身体左倾,大有追扯吕布之势)。三幅插图皆着意摹仿和再现文字内容,且排列密集,故能相对完整
的表现故事情节,呈现出与连环画类似的连贯动态效果(见图二[15])。按小说所述,吕布担心董卓发觉而急于离开凤仪亭,而貂蝉则欲巩固矛盾,故以柔情激怒吕布。貂蝉为离间董卓父子而表现出的心思细密,吕布惑于女色而应对的愚笨无谋,皆在这段文字中得以发挥。然而,插图仍然无法复制人物之间的对话,它只能选取一个特殊的情景片段表现所有。第三幅插图以吕布将去未去、欲留不得的瞬间为中心描述,人物的动作、神情成为刻画重点。吕布的留恋之态表现了勇夫的好色单纯,而貂蝉的挽留之举却暗示了殚精竭虑的谋略心机。图像与文字在此表现出一种上下呼应、相与阐发的共存互动关系。同一情景在汤学士本中以吕布与貂蝉二人亲热携手瞬间为构图中心,虽可见吕布对貂蝉之迷恋,却难见吕布之无谋与貂蝉之韬略(见图三[16]83),在意蕴的丰富程度上与叶逢春本尚存差距。

图三
万卷楼本240幅双面连式对页大图(称“全图”或“全相”[17]33),平均每图配合万字左右内容,其画面所需承载的信息量更高,也就对绘图者选择和把握“孕育性顷刻”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上图下文版式插图侧重于帮助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理解故事情节,其主要功能尚在叙事,那么整版插图则除了叙事功能之外更具审美意味。以“长坂坡赵云救主”为例,插图以赵云为护阿斗而与敌军奋战为中心:画面一侧赵云怀抱阿斗挺枪于战马之上,枪头所及一人扑倒于战马上奄奄一息,一人已身首异处,另一人则颈部流血不止(见图四[12]784-785)。该本插图表现战场景象多采用交战双方各一战将对峙交手的构图形式。人物周围亦有刀剑林立、军士混战痕迹。该回文字从众人误会赵子龙投奔曹操叙起,至张飞掩护赵云撤离结束,环境涉及正面战场及后方,场景甚广。选择怎样的瞬间既能充分传达战争信息又强调主人公的英勇形象,成为绘图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细部观察,插图中赵云腰间佩剑,时机当在杀夏侯恩夺曹操“青釭”宝剑之后;又阿斗被赵云庇护在怀,当为晏明、张郃追赶赵云之时。其实,在此段混战中,最惊险的瞬间发生在赵云为张郃追赶连人带马颠入土坑之时,红光罩体的宝马发挥神力从土坑中跃起方使赵云摆脱困境。插图选择了高潮发生的前段,使读者既对故事发展有充分认识,又有后续的紧张情节可供联想,颇具意味,而子龙的忠心护主与神勇难挡也在这一简单的画面中得以传神表现。

图四
(二)共时性叙事:时空场景的分割
古代小说在叙事视角选择上习惯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以此可居高临下、事无巨细地讲述情节发展的方方面面,对此前人论述已多。与这一特点颇相契合的是,我国古典绘画艺术在构图中也擅长使用所谓“散点透视”原则,即通过移动视点(或谓多视点)进行观察,将各个不同立足点上观察所得全部组织到画面中来⑥。正因为这种与西方“焦点透视”不同的处理技巧,古人才能绘出如《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之类的宏篇巨制。相对来说,“散点透视”不追求与描述对象的形似,而更求神韵与意境。这种传统绘画技巧自然影响到小说插图的绘制,在时空表现形式上,既有对小说情景“一时一地”的反映,更有利用简单的线条、山石、云团、屋宇等作为分割界线,以表现“同时异地”、“同地异时”以及“异地异时”的场景[18]。运用巧妙的处理技巧,就可轻易完成文字无法实现的共时性叙事,不能不说是图像的神奇之处。当然,明清小说的插图绘制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朴拙到复杂、精致的过程。在早期上图下文版式中,画面空间窄仄,人物与景物多在同一高度,构图效果极为平面化,叙事信息量有限,也难有意境可言⑦。但随着插图制作艺术的改良,尤其是
单页或对页大图的出现,使得画面空间开阔,画工们更有条件合理安排构图,除了通过对象的高低错落营造立体效果之外,还可通过将不同场景进行浓缩和融合以增加叙事信息量,并配合文字内容创造特殊意境。
万历双峰堂刊本《三国志传评林》图“周瑜喝斩曹公来使”将周瑜斩使的场景由“大帐”移至“船上”,目的就是为了将曹操遣使渡江送书与周瑜斩使两个场景同时容纳到画面中来。崇祯雄飞馆《英雄谱》本赤壁之战一节插图则囊括孔明借箭、蒋干中计、曹操赋诗以及阚泽诈降四个经典场景,时间、空间的跨度更大。清两衡堂刊本《李笠翁批阅三国志》八十一回插图中既有范疆、张达蹑手蹑脚进入张飞寝室的情景,亦有二人靠近张飞床前行刺的瞬间;一百五回插图“魏拆长安承露盘”亦将马钧建议曹叡拆取承露盘与马钧带领军士于柏梁台拆取铜人金盘两个场景合二为一,皆是按照时间流动表现情节进程的实践(见图五[19]163,212)。这些插图通过独特技巧尽力体现时间和空间的延展性,其根本的目的仍是更加真实、传神地再现文字信息的内容。

图五
(三)自然环境、绣像的静态表现
除以上所论动态色彩较强的出相、全相插图之外,《三国》小说中还存有少量的静态环境插图,由于不表现具体情节,其主要功能不在叙事。如叶逢春本6卷第63图(左)描绘“曹操御园”景致,画中仅有神鹿、仙鹤及参天古树等自然风物,全无人物,亦无情节信息可言,所配合的文字内容却是许芝向曹操介绍管辂善卜之事(见图六[15])。紧随其后的六十四图(左)亦绘曹操宫室殿宇之貌,文字内容却仍叙管辂神算救人。这可能是因为管辂生平事迹内容繁多,又属情节次叙述层,加之63图(右)已绘许芝推荐管辂情景,画工为避免重复才以自然景物作为描绘对象。当然也不排除绘图者的个人喜好等因素。又“耿纪韦晃讨曹操”一节,文字乃叙耿纪、韦晃二人饮酒密谋讨操之事,插图则配殿宇宫室严整之状。庶几因为单页篇幅有限,文字叙述信息量较少,紧接此页又有表现“耿纪、韦晃、伟德论操”之画面,则此图亦为避免重复所设?类似情形还出现在“曹兵杀主簿杨修”一节,前四图分别对杨修猜中曹操“鸡肋”之意、杨修命军士做撤退准备以及杨修破解曹操“门活而阔”之谜题进行了刻画,第五幅插图(6卷89图左)则仅绘曹操驻兵之地斜谷溪山之自然风貌。不过,将这山峰、松树所构成的清冷之境置于杨修之死的文字之侧,是否也暗示了画工对杨修命运的些许悲伤与惋惜?此外,还有4卷图49(左)、图56(左)等也属类似情形。这类景物插图一般多出现在图像密集的版本之中,从整体上来看也能起到调节和舒缓叙事节奏的作用。

图六
人物绣像插图(主要人物肖像)多在小说正文之前或之后集中出现,此类作品在清代大量涌现,如清光绪年间刊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图画》等,书中皆有近百个人物绣像。与一般情节性插图不同,绣像插图的叙事功能下降,有时甚至连人物所处的环境背景也被省略,仅凸显人物的服饰装扮、样貌体态。有学者认为,绣像插图的大量出现,实际是出版商节省出版成本的结果。因为插图虽能招徕顾客,但毕竟耗费成本,而人物在插图中又无论如何不能省略,于是只好独存人物要素,“谋求最小限度上‘俱全’的插图本”[20]47。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绣像插图的大兴实则是版画发展走向低潮的表现。绣像在表现人物时具有“类型化”特征,人物容貌神态多有雷同,能使形象之间区别开来的重要标示是衣着武器等外在装备,画工一般会依据小说的描述选择最能代表人物特征的装束表情,或者根据经典场景为人物安排动作。如在清贯华堂《四大奇书第一
种》、光绪桐荫馆刊本《三国画像》以及光绪同文书局《增像三国演义全图》中,孙夫人都是一身戎装、手执宝剑造型,以此对应小说对其飒爽英姿的描述。而个性迥异的糜夫人在《三国》画像中则多是怀抱阿斗的慈母之态(如贯华堂本、光绪同文书局本等),显然是针对她舍身护子的牺牲之举。这类插图虽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有限,却能直观地反映小说人物在当时的接受情况,具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
三
小说插图虽力图对文字信息进行全面的模仿再现,但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在转换中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信息的遗漏、溢出或错位等情况,这正是学者所指出的图-文转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意义“缝隙”[21],实则也是语-图互文关系中的另一层面。这种“缝隙”很大程度由绘画者主体意识所致——插图是经过绘图者主观视角过滤的小说信息,是绘图者首先作为普通读者对小说进行个体解读的结果,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插图是对小说文本的二度创作。这种二度创作对后期小说读者能产生直接影响,插图在此就对原始小说文本形成了一种反向互动。
(一)场景选择与审美取向
陈平原先生曾认为,“(小说插图)的功能并非只是便于民众接受;选择什么场面、突出哪些重点、怎样构图、如何刻画等,其实隐含着制作者的道德及审美判断”[22]136。绘图者的主观意识决定了插图的价值取向及审美风格,我们可从不同阶段的《三国》小说插图中得到印证。
以对曹操形象的表现为例,叶逢春本插图总是选择对人物有利的观察视角或场景瞬间进行描绘,即便作品内容对曹操有明显的贬斥之处,绘图者也会避重就轻。比如针对曹操杀吕伯奢情节,绘图者故意将表现时机安排在“曹操陈宫见吕伯奢”瞬间,将曹操行凶的场景轻轻抹去(见图七[15])。又小说曾述曹操征讨袁术过程中下令军士不得践踏麦田,百姓因此感戴之事,虽然在作品中只是一笔带过的简单叙述,但在插图中却得以大力表现:曹操等一众军马行过,百姓虔诚跪拜,感戴之情流露于神色举止之中,插图题曰“百姓感激曹操遮道拜送”,更强化了曹操受百姓爱戴的仁主形象。又陈宫被杀情节之侧小说配图,一为“曹操差使讨陈宫家小”,一为“陈宫父母见曹操”,皆为表现曹操宽仁之心。与叶逢春本情况不同的是,汤学士本插图对曹操的态度就没有如此宽容,杀害吕伯奢的血腥场面就得以强调和特写:曹操拔出的长剑尚未回鞘,吕伯奢已身首异处(见图八[16]40)。这样的描绘虽与文字内容略有出入,但却恰好透露了绘图者有意表现曹操凶残之用心。更有意味的是画面中仅有曹操和吕伯奢而不见陈宫,显然出于对这位不屑与曹操为伍者的维护。此外,周曰校本插图也对曹操许田射鹿、重勘吉平、缢死董妃、杖杀伏后等场面进行了正面特写(尤其是对吉平、董妃、伏后临刑之际血肉模糊惨状的刻画足令观者动容),贬斥之意自不待言。有学者将各本插图对曹操的表现进行对比,指出叶逢春本插图对曹操的态度是维护和美化,而诚德堂本插图对曹操不褒不贬,双峰堂及明后期各刊本插图则极尽指责与批评[23]。这也可见不同时期读者对小说人物的看法和态度。

图七
如果说对曹操形象的不同描画反映的是绘画者们并不一致的价值取向,那么对“庞统理县事”情节的不同表现则告诉我们绘图者们还拥有各自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审美习惯。针对这一内容,叶逢春本、周曰校本、李渔评本(两衡堂刊本)等插图皆以庞统审案现场为表现重点:堂上正中坐庞统,旁坐张飞、孙乾,堂下跪二至三名涉案人员,另有衙役伺候在侧。画面表现出典型的明清公案风格,绘图者将小说对人物才能的笼统描写具体场景化,试图通过一个特定案件的庭审现场再现庞统的过人才智⑧。不过,与其他各本正面表现庞统才能不同的是,在汤学
士本中,此段情节所配合的插图却是“张翼德怒责庞士元”,显然是以先抑后扬的方法从侧面反衬人物的才智。汤学士本的这一处理方式不仅不会让读者感到意犹未尽,相反表现出更多的戏剧意味。因为紧连于此的前两幅插图分别表现的是庞统在孙权处遭冷遇以及在玄德处遭疏远,再加上在张飞处遭责骂,恰好形成一个小小的冲突高潮,为接下来的情节逆转做好了充足的铺垫。除绘图者本身的价值取向、审美习惯之外,时代风尚也对小说插图的绘制产生一定影响。如有学者研究发现,明中期之后的小说插图在构图形象上表现出对园林文化的热衷、对人居环境的关注等特点,而这都与当时社会风尚的浸润不无关系⑨。总之,不同风格的插图代表了不同时代的《三国》解读视角和审美取向,插图不仅是小说文字内容的镜像反映,更是绘图者在解读文本基础上的二次创作。
(二)图题的褒贬寄寓
图像之侧用简短文字对画面内容进行概括介绍或补充说明,是白话小说插图的另一重要特点,如“孔明百箭射张郃”、“孔明出师”、“将星坠孔明营”(见《全相平话三国志》)等。图题虽以文字形式表现,但直接配合画面而来,仍属插图范畴。图题由产生之初的四字短语或五字、七字单句,发展至整齐的双句对偶,经历了一个缓慢过程。相对而言,短语或单句图题的叙事功能较突出,而对偶诗句则更偏重于意境、氛围的渲染。图题的发展促成了章回小说回目的形成,在章回小说文体成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已有学者进行深入讨论[24]。图题之间的关系复杂:一方面,插图的直接目的是为方便读者理解作品,以直观的空间形象诉诸读者视觉,使其通过不同的感观体验在瞬间了解故事信息;但另一方面,插图本身也可能存在“图不达意”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插图在表现时间过程上受到诸多限制所致),事实也证明确有许多小说插图离开图题而令人费解⑩。这也就是说,插图的表意功能并不一定超越文字,它有时仍需文字对其进行直观的意义补充或说明。如此一来,小说语—图之间就绝非简单的谁影响谁,谁解读谁,而更多是彼此依存、相互参照或互为补充的特殊互动。

图九
早期图题比较强调叙事功能,其主要目的仅限于为插图提供信息补充,而字数的限制也妨碍了绘图者主观意识的表达。随着图题的表现趋于自由(比如周曰校本图题内容就发展为两大部分:一是概括小说内容信息的单句,二是表现绘图者针对情节所作褒贬评价或感慨的对偶诗句),绘图者主观意识的传达也就更加灵活方便。如周曰校本“吕子明智取荆州”插图,图题“计出阴谋犬吠鸡鸣非将帅,兵行诡道獐头鼠耳岂男儿”(见图九[12]1414-1415),明白透露着绘图者对东吴白衣渡江军事行动的不满。其实,乱世之中战争的正义与否本来就很难界定,兵不厌诈简直就是各军事集团为求生存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更何况当初刘备夺荆州同样也是诸葛亮的智谋巧取,绘图者在此若不是出于对关羽之死的惋惜而迁怒于东吴骄兵之计的制定者,又何至于厚此薄彼?尽管关公的大意轻敌才是吕蒙与陆逊计划成功的关键,然而关羽形象在民间已成为神化的偶像,绘图者作为一般小说读者只能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于英雄的追念与叹息。又如“董卓议立陈留王”一图,画面仅列举董卓等人席间饮酒交谈的场景,读者本来难以窥见绘图者的主观意图,但加上“轻议立君建极殿前云气惨,妄谋废主温明园内鸟声凄”的图题,读者便能很强烈地感受到绘图者对王室衰微的同情、感慨,以及对董卓悖行逆失的愤怒、谴责[25]。与周曰校本情况不同的是,上图下文版式的汤学士本图题形式古拙、重于叙事,在褒贬寄寓上表现得较为客观和含蓄。同是针对吕蒙、陆逊计取荆州画面,其分别题为“孙权封吕布为都督”、“吕蒙用白衣人摇橹”、“荆州百姓迎接吕蒙”等。这些图题并未表现出对失败英雄的惋惜留恋,从叙述语气来看似乎还流露出对吕蒙妙计的默默赞许。图题经过发展逐渐与小说回目合一,也是白话小说版本发展中的重要现象[24]。清两衡堂刊本《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的图题
除在个别字词上与回目略有出入之外,基本与回目一致;而文英堂刊本图题则完全取回目上半句。以上两个版本皆属毛本系统,毛氏父子极力提倡拥刘反曹的立场,经其修改的回目用于图题,进一步丰富了插图的褒贬寄寓。
(三)图文不符的背后
插图的最初目的既然是“用图画来表现文字所已经表白的一部分的意思”[7]3,那么首先应该忠实地传达作品内容。但两种不同的表意符号各有擅长,在转化过程中无法完全做到一一对应;又或者是绘图者认识、理解能力有限,甚至是绘图者的某种主观愿望,都容易造成局部的图文不符。有学者甚至指出“图像叙述的图形变形程度越大,其表现的叙述主体意图就会越明显”[26]。这些特殊的图文不符现象,反映的也许是绘图者对小说文本的某种“误读”,但也可能对后续读者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影响。小说文本中的图文不符,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人物的更改。如叶逢春本卷四图47(右)“孔明见孙权以问曹操事”,描绘孔明与孙权对坐商议、鲁肃等人侍立在侧场景,但实际该图对应的文字内容却是鲁肃劝说孙权联合刘备以抗曹操,插图将文字内容中的关键人物鲁肃改换为孔明;而紧接于此的“孙权与孔明同行诚问智略”插图,其对应文字内容则为张昭言挑孔明,插图将主要人物张昭改换为孙权,亦与小说内容不符。可能是绘图者意识到孙权与孔明在决定战、和问题上的关键作用,因此将二人之间的互动作为构图中心反复表现。这一更改看似无意,却能对读者造成一种阅读导向,加深其对情节重点的理解。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更改是绘图者的粗率大意所致。如叶逢春本四卷图3(左)题为“玄德问牧童卧龙何往”,画面中却显示中年农夫;又四卷图18(右)“张顾欲杀甘宁,孙权自休”,改凌统为张顾,是很明显的理解错误。若不仔细阅读原文,读者也可能被插图的直观印象所误导。
其二,场所的变换。多属绘图者的有意为之,往往能反映其独特的叙事习惯及审美取向。如周曰校本将关云长刮骨疗毒的场所由帐中改为亭阁间,初看似无意,细较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是周曰校本插图普遍重视环境描绘,并追求室内装饰的审美习惯所致。相比早期上图下文版式中插图的狭窄局促,周曰校本的双面对页大图显然为绘图者提供了更多发挥的空间,而绘图者趋于精细化的创作态度和审美追求也成为该本插图重视场景氛围的直接因素。此外,还有的场景更换是为了整合叙事信息。如双峰堂本《三国志传评林》将“周瑜喝斩曹公来使”的发生地从帐中移于船上,目的是将两个情节片段(曹操遣使渡江与周瑜斩使)同时容纳于画面,也是绘图者为发挥图像的共时叙述功能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对此上文已有分析,此不赘论。
其三,时序的错乱。如叶逢春本卷五图1(左)表现“孔明令鲁肃造七星坛”景象,而实际对应文字内容却是周瑜因顾虑火攻无法实施而吐血犯病,孔明造七星坛祭风情节当在后两页位置,插图将叙述时序进行了调整。而此前的图1(右)“周郎山顶观风”则直接承接上卷“曹兵被风吹折旗帜”而来,是典型的延迟叙述。两幅插图一缓一快拉长了读者对情节的体验过程,同时也强调了东风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实际是为诸葛亮的多智形象进行渲染。又熊佛贵刊本“关羽独行千里”插图绘关羽骑马荷刀造型,实际当为前两页内容,也是典型的插图预叙。
其四,细节的错漏。如叶逢春本五卷图74(左)表现“韩遂与曹操叙旧”场景,画面中二人对面站立交谈甚欢,身后则有贴身侍卫牵马等候。插图看似正常,实则背离了小说原意。按小说所叙,曹操特意邀请韩遂“轻衣匹马”而出、二人“马头相交各按辔对语”,只有在马上的位置、距离,才最适合曹操对韩遂进行各种含糊的问候,而旁无他人的私密性更足以引起马超的疑心。插图将情节原意按个人理解直观化,却在最关键的细节上出现了漏洞。又卷一图75(右)绘“李相求见孔融”,实际文字内容却叙孔融求见李膺,且孔融此时年仅十四,不应是图中所示中年模样。这应当为绘图者大意所致。这些错漏说明绘图者对小说作品的理解是有限的,而插图也确实无法做到与文字叙述完全同步。
“因文生图”反映的是插图对小说文字文本的直观再现,是同一内容在两种符号之间的转换,在这个维度上,插图是文字直接作用的结果,处于被动地位。在形形色色的《三国演义》插图中,绘图者们通过挑选“孕育性顷刻”、特殊的时空分割方式以及颇具意蕴的静态绣像描画,试图达到最真实、准确再现文字内容的目的。“以图解文”则指向插图对文字文本的主观解读,插图既反映小说在画工群体中的接受情况,同时也对后续读者产生引导,进而影响小说在更大范围内的接受和传播,因此,它又具有某种主
体性。从插图表现出的对故事场景的挑选取舍、插图图题的褒贬寄寓以及有意无意中流露的图文不符等现象中,我们也感受到小说插图绘制者试图对文字文本作出自身解读的努力。本文虽仅以明清以来插图本《三国演义》为重点关注对象,但根本的目的却是以此切入明清插图小说的整体规律。
注释:
①但郑振铎先生则认为该画“是相当成熟时期的作品,决不是第一幅的作品”,版画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对此学界尚无确论。参见: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2010年版,第12页。
②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阿英《中国连环图画史话》(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线装书局《古本小说版画图录》(1996年版)等皆属此类。
③新世纪以来涉及古代小说图像主题的专业论文不下百篇,宋莉华《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与传播》(《文学遗产》2000年第4 期)、汪燕岗《古代小说插图方式之演变及意义》(《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程国赋《论明代通俗小说插图的功用》(《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陆涛《图像与叙事——关于古代小说插图的叙事学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刘文玉等《图像时代下的中国古代插图研究》(《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可为代表,其中又以颜彦《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及金秀玹《明清小说插图研究》(北京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论述最为系统。
④直接以语-图互文现象切入明清小说研究的论文不足十篇,代表作有张玉勤《论明清小说插图中的语-图互文现象》(《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1期)、陆涛等《明清小说插图的现代阐释——基于语图互文的视角》(《集美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明清小说出版中的语-图互文现象》(《鲁东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等。除陈平原《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对古代小说语-图关系有所论述之外,目前尚无此方面专著。
⑤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性是指“一部文学作品所构成的整体中正文与只能称作它的‘副文本’部分所维持的关系组成,这种关系一般来说不很清晰,距离更远一些,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性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或是他人留下的标志,他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选·隐迹稿本》,史忠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⑥“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是两种绘画结构方式,前者是指“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视点状态下,人们对景物的综合透视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也称多点透视。它是相对于一个视点的焦点透视而言的”。参见:李峰《中国画构图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⑦但也有例外情况,如《三分事略》图24表现督邮问责刘备太守被杀之事,尽管画面狭长逼仄,但仍用线条分隔出两个空间,同时表现室内和室外情景。《三国志平话》沿袭《三分事略》,插图亦与此同。
⑧在1994年拍摄的《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庞统理县事也通过一个具体的审案过程加以表现(借用民间流传的包公审案故事),可见将文字概述转化为具体情节,是插图和影视改编艺术中比较通用的处理技巧。对此笔者已另撰《<三国志演义>影视改编的互文性策略》(《西安工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一文进行说明,此不赘述。
⑨颜彦认为,《三国演义》早期上图下文式插图,“往往以微观写实的手法再现战争中身首异处的暴戾场面,体现战争的血腥性与残忍性,而对战争以外的生活常态的描绘则大而化之。发展到单页大图,图像在描绘战争场面的同时,亦对人居环境的刻画给予了极大关注”。参见:颜彦《明清小说中的社会风尚影响——小说文本中插图形象的演变解读》,《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⑩比如叶逢春本卷四图63(右)表现周瑜与刘备对坐、云长侍立在侧的场景,配合的是周瑜设鸿门宴欲杀刘备,但因顾虑云长而最终取消暗杀计划的情节。插图虽对三个重要人物皆有描绘,但本应特加强调的人物表情却表现平平,三人神情淡定且非常雷同,根本谈不上反映各人暗自盘算的复杂心理。这种插图的表现效果显然不够精彩,但加上“周郎欲害玄德,云长辅佐莫能”的图题,就相当于将读者无法从画面中一眼获知的情节信息以另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补充传达出来,及时弥补了插图的不足。
参考文献:
[1]程国赋.论明代通俗小说插图的作用[J].文学评论,2009,(3).
[2]祝重寿.中国插图艺术史话[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美〕梅维桓.唐代变文[M].杨继东,陈引驰译.北京: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4]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于德山.中国图像叙述学:逻辑起点及其意义方法[J].社会科学战线,2004,(1).
[6]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1).
[7]郑尔康.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插图之话[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8]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M].上海:上海书店,2010.
[10]〔德〕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1]陆涛.图像与叙事——关于古代小说插图的叙事学考察[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6).
[12]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G]//古本小说集成.影万卷楼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3]王逊.论明清小说插图的“从属性”与“独立性”[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14]《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全书》[G]//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袁无涯刻本.台北:天一出版社,1974.
[15]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M].影西班牙皇家修道院本(叶逢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6]罗贯中.《三国志传》[G]//古本小说集成.影汤学士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7]鲁迅.连环图画琐谈[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8]颜彦.明清小说插图叙事的时空表现图式[J].中国文化研究,2011,(春之卷).
[19]李笠翁批阅三国志[M]//李渔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20]金秀玹.明清小说插图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3.
[21]张玉勤.“语—图”互仿中的图文缝隙[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22]陈平原.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3]张玉梅,张祝平.明代《三国》版画对曹操的褒与贬[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6).
[24]李小龙.试论中国古典小说回目与图题之关系[J].文学遗产,2010,(6).
[25]胡小梅.论周曰校本《三国志演义》插图的情感倾向[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责任编辑:唐 普]
[26]于德山.“语—图”互文之中叙述主体的生成及其特征[J].求是学刊,2004,(1).
Preliminary Study on Text-Image Intertextuality of Ancient Novels:Taking the Illustrated Edi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s an Example
WANG Ling1,2
(1.School of Humanities,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21;
2.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2,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illustrations in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drawers are found to re-appear text information through holding a moment,special spatio—temporal segmentation, and painting static tapestry portrait.Their choice of story scenes for illustrations,judgments on images and titles,and 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 discrepancies between illustrations and texts all demonstrate drawers’efforts to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ovel with their own aesthetic habits.Novels’illustrated editions present a special kind of interaction between words and pictures.Illustrated edition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 gdom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perfect examples of text-image intertextuality of illustrated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ext-image intertextuality;Romance of the Three Kin gdoms;Illustrations
作者简介:王凌(1980—),女,湖南常德人,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明清小说互文性研究的专题分析与体系构建研究”(15XZW013);2015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专项基金项目“互文性视阈下明清奇书小说文本与接受研究”(15JK1359)。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5-0153-10
收稿日期:2014-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