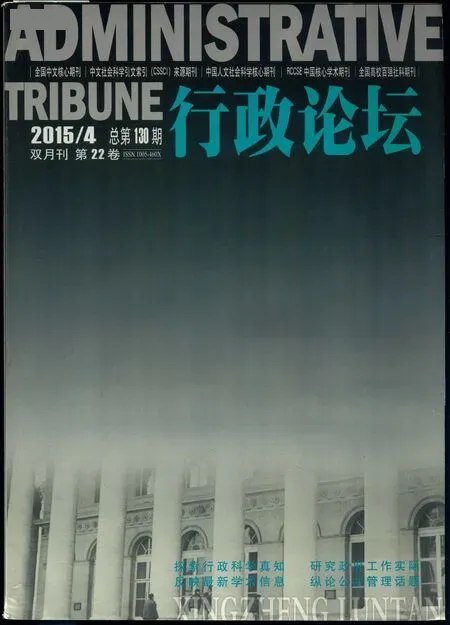亨廷顿和维巴的政治参与观比较
罗爱武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政治参与是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术语,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政治参与就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就是其中的代表,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研究政治参与,必须回答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何为政治参与、哪些现象属于政治参与,也就是首先要界定政治参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虽然政治参与已成为政治学界极为流行的术语,但对这一概念的具体界定,学者们还没有定论。亨廷顿和维巴的观点之间,以及两者和其他学者的观点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了解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理解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对于我们进行相关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将在描述亨廷顿和维巴的政治参与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比较二者政治参与观的异同之处,并从理论基础、问题域和方法论等三个方面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最后总结出政治参与概念的基本共识。
一、政治参与的含义与类型
(一)亨廷顿的政治参与观:含义与类型
亨廷顿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1]5。这一定义所界定的政治参与的具体特征有:第一,政治参与只包括活动而不包括态度。第二,政治参与是指平民的政治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充当平民角色的那些人的活动。第三,政治参与行为的对象指向政府。第四,政治参与活动包括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所有活动,而不考虑这些活动根据政治系统的既定准则是否合法,只要是试图影响政府的行为,都是政治参与行为。但职业革命者的行为不包括在内,因为其行为已具有职业性,不满足亨廷顿政治参与定义的第二个特点。第五,政治参与包括试图影响政府的所有活动,而不管这些活动是否产生了实际效果。第六,政治参与不仅包括本人自发参与的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还包括行动者受到他人动员而参与的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亨廷顿将前者称为自动参与,后者称为动员参与[1]5-7。
亨廷顿根据他对政治参与的定义,将政治参与分为以下五种模式:第一,选举活动,它除了包括公民的投票行为,还包括他们为竞选捐款、为选举组织工作、为候选人游说或者其他影响选举过程和结果的活动。第二,院外活动,指个人或者团体通过与政府官员和政治领导人的私下接触,在涉及个人或公共利益的问题上试图影响政府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决定的活动。第三,组织活动,它是指某一组织中的骨干或者成员的参与活动,这种组织的基本目标是影响政府决策。第四,接触,它是指为谋求个人或者小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指向政府官员的个人活动。第五,暴力,即以伤害人身或者毁坏财产的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如军事政变、暗杀、骚乱、叛乱等[1]13-15。
(二)维巴的政治参与观:含义与类型
维巴在《美国的参与:政治民主与社会平等》一书中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以及(或者)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活动”[2]2。这一定义中政治参与的特征主要有:第一,政治参与是试图影响政府行为的活动,这种影响有两种方式,或者是通过影响政府工作人员所做的选择而直接影响政府行为,或者是通过影响对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而间接影响政府行为。不管公民的活动是否成功,只要这种活动发生了就表示公民参与政治了。但是这一定义中不包括“礼仪性”或者“支持性”参与。第二,政治参与是指政治活动,不包括对参与的态度。第三,政治参与的对象指向政府部门,即政治参与的目标是政府,目的在于影响政府。第四,政治参与是限定在“系统内部”的活动,只包括以合法手段影响政治的活动,即只包括“普通的”(ordinary)政治行为,而不包括各种非制度性甚至非法的政治行为。第五,政治参与并不局限于投票和竞选这类选举性政治参与活动,在两次选举间隔期间,公民也可以参与政治活动。只是那时公民参与的目的不是试图影响对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而是试图影响政府工作人员所作的选择[2]2-3。
维巴对政治参与模式的研究建立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他首先提出了划分政治参与类型的四个标准:政治参与行为施加影响的类型、政治活动结果影响的范围、政治参与所造成的冲突面、政治参与所需要的主动性[2]47-51。然后,维巴根据这四个标准,利用调查所得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这种统计分析技术,将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归纳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及其包括的参与活动为:第一,竞选活动,包括劝说其他人去投票、积极为政党或者候选人服务、参加政党会议或者集会、为政党候选人捐钱、加入政党俱乐部等。第二,投票,包括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投票、在美国地方选举中投票等。第三,社区活动,包括和其他人合作解决地方性的问题、建立一个组织来解决地方性问题、成为社区活动积极分子、为解决社会问题接触地方官员、为解决社会问题接触州及联邦政府官员等。第四,特殊接触,包括为解决个人问题接触地方官员、为解决个人问题接触州及联邦政府官员等[2]72。后来,维巴将这一分类方式运用于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荷兰、印度、尼日利亚和前南斯拉夫等七国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这七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模式也与这四种类型基本吻合[3]。罗森斯托恩在维巴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公民政治参与行为概括为选举性政治参与和非选举性政治参与两大类,前者对应于维巴政治参与分类中的投票与竞选等影响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的行为,后者对应于维巴的特别接触与社区活动等影响政府工作人员所做的选择的行为[4]。
二、亨廷顿和维巴政治参与观比较
比较需要一定的标准。孔奇的研究为我们将亨廷顿和维巴的政治参与观进行比较,提供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标准。对于学者们围绕政治参与概念的争论,孔奇将主要分歧归纳为六个方面的问题[5]。第一,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形式:政治参与应该只包括积极的行动,还是应该包括消极的情感和意识。第二,攻击性的还是非攻击性的行为:政治参与应该包括公民反抗和政治暴力,还是应该限定在传统的行为上。第三,结构性的还是非结构性的目标:政治参与应该包括改变或维护政府形式的努力,还是应该限定在改变或维护政府权威以及(或者)他们决策的范围内。第四,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目标:政治参与应该被限定在直接指向政府权威、政策以及(或者)制度的行为,还是应该包括政府范围之外的现象。第五,动员的还是志愿的行为:政治参与应该指由政府发动并指导以提高自身福利的行为,还是应该限定在公民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发动的行为。第六,预料到的还是未预料的结果:政府没有预料到结果的行为是否应该被定义为政治参与。根据孔奇提出的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亨廷顿和维巴之间,以及两者和其他学者之间政治参与观的区别。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亨廷顿和维巴的政治参与观在孔奇所提出的第一个和第四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一方面,在政治参与是仅指积极的行动还是应该包括消极形式这一问题上,与马什将公民对温和抵抗和政治暴力的态度归属于政治参与行为不同[6]59,也与毕福勒将公民观看电视新闻、收听广播新闻、阅读报纸或杂志、与他人就政治问题进行交谈或辩论等获取政治信息、表达观点的行为看成政治参与行为不同[7],亨廷顿和维巴都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客观的行动而不包括主观的心理和认知,都将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意识作为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外在因素之一,而不把它看成是政治参与行为,因为态度、意识和行为之间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不是一回事。政治态度和情感属于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范畴,而不属于政治参与范畴。对政治行为的态度和意识并不必定意味着实际参与政治活动,而只是参与政治的前提条件,它们可以用来解释人们为什么参与或者为什么不参与,但是不能说明政治参与术语本身的含义。另一方面,在政治参与的目标指向是应该局限于政府部门还是应该扩展到非政府组织这一问题上,与布斯将政治参与范围扩展到指向非政府目标的社会参与行为不同[8],亨廷顿和维巴都认为政治参与行为指向的对象是政府部门,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目的在于影响政府,要么促进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和政府行为,要么阻止对他们不利的政策或政府行为。那些指向非政府部门的行为因为不是试图影响政府,所以只是政治参与的外在影响因素之一,而不是政治参与行为本身;二者都强调政治参与行为的主体是平民,而不包括政府工作人员,也就是说,二者都认为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性活动不同于普通公民志愿性的政治参与活动。
另外,亨廷顿和维巴还在孔奇没有提到的政治参与的方式这一问题上,与某些学者也是不同的,就是二者都认为政治参与方式不应局限于公民的投票和竞选等选举性行为,还应该包括个人接触和社区活动等非选举性行为。虽然自行为主义革命以后,政治参与就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但早期的政治参与研究往往局限在投票或竞选等选举性参与活动上,如坎贝尔的《美国选民》一书就仅研究公民投票这一种参与行为[9]。按照维巴的定义,选举性政治参与实质上是公民影响政府工作人员选择的行为,即通过直接影响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而维巴和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不仅包括公民在选举期间通过投票、竞选等选举性活动,来影响政府工作人员选择的行为,还应该包括公民在非选举期间,通过个别接触、社区活动等非选举性参与活动,以影响政府政策选择的行为。
在孔奇提出的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六个问题上,亨廷顿和维巴的观点是不同的:首先,关于政治参与是应该包括攻击性的暴力行为还是应该仅限与非攻击性的普通参与行为,维巴的政治参与概念不包括骚乱、暗杀和所有其他类型的非制度性、非法的参与行为,而亨廷顿的定义则包含游行、示威、抗议、暴乱、叛乱、军事政变、暗杀等非制度性、非法的暴力行为。在这一问题上,巴恩斯和亨廷顿的观点是一致的[6]59。其次,关于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应该包括改变或维护政府形式的结构性目标,还是应该限定在改变或维护政府权威或者他们决策的非结构性目标范围内,维巴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可以试图改变政府决策或者做决策的人,但不包括试图改变现存政治系统和政治游戏规则的行为;而在亨廷顿的政治参与定义中,除了包括试图改变现存当局的决策和更换现存当局的行为,还包括试图改变现存政治系统和政治游戏规则的行为。对于这一点,巴恩斯和亨廷顿的观点同样是一致的[6]59。再次,对于政治参与行为是应该仅限于公民的志愿参与,还是应该包括由政府发动的动员参与这一问题,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包括动员参与,而维巴则排除了“礼仪性”或“支持性”的参与。在这一问题上,布斯和亨廷顿的观点是一致的[7]。最后,对于政治参与是局限于预料到的结果还是应该包括未预料的结果这一问题,亨廷顿认为应该包括未预期到的结果,而维巴排除了这一点。
三、政治参与观差异的缘由
通过对亨廷顿和维巴政治参与观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学者们围绕政治参与概念所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概念范围的大小,即对哪些现象属于政治参与、哪些现象不属于政治参与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在给概念下定义时,如何在概念的概括性和概念的精确性这两种竞争性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概念的概括性要求,定义范围必须足够宽,以包括不同背景中的一系列现象;概念的精确性要求,为了提高概念的解释力,定义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过度追求概括性,就会导致概念的范围过于宽泛而失去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一味追求精确性,又将导致概念的范围过于狭窄而无法包含丰富的现象[5]。从概括性和精确性相平衡的要求看,亨廷顿和维巴通过将政治参与概念的范围从投票、竞选等选举性参与扩大到个别接触、社区活动等非选举性参与,而增加了它的概括性;又通过将政治态度、政治意识、社会参与活动和政府管理活动等排除在其范畴之外,而提高了它的精确性。在此基础上,维巴又通过排除非制度性参与活动和结构性目标的参与活动,进一步缩小了政治参与的范围。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可以从各自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域和方法论等三个方面来探析。
第一,与早期的政治参与研究将参与类型局限于投票、竞选等选举性参与行为不同,亨廷顿和维巴都将政治参与的种类从选举性参与扩展到非选举性参与,这是由于他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早期研究的理论基础不同而形成的。
一个概念的理论基础影响其含义的界定,政治参与概念的含义必须通过它所嵌入的民主理论背景来理解。“参与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民主概念”[10],政治参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受民主理论影响,每种政治参与定义背后都有民主理论基础,不同的民主理论有不同的政治参与观。
早期的政治参与研究受精英民主理论影响。精英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11]415,是精英竞争政治职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是从作为候选人的精英人物中选举出政治领导人。“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者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11]415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是产生政府,或者说是产生一个中间体,再由中间体产生全国行政部门或者政府。以精英民主理论为基础的政治参与观认为,公民只能通过选举决定政府的产生,至于政府产生以后,人民能否决定和影响公共决策,决策的结果是否有利于公意,都是无关紧要和意义不大的问题,只要存在每隔一段时期公民可以选择或罢免统治者的选举程序,民主就是充分和完善的[12]。早期的政治参与研究由于受精英民主理论影响,研究对象大多仅限于公民的选举性参与,如米尔布雷斯的《政治参与》一书,书名虽然叫“政治参与”,但其研究的范围却仅限于投票和竞选等选举性政治参与活动[13]2。
亨廷顿和维巴的政治参与研究受多元民主理论影响。和精英民主理论一样,多元民主理论也认为,政治事务最好是交给那些积极参政、有能力管理国家的少数人。但与精英民主理论不同的是,多元民主理论认为,为了制衡少数人的统治,统治者必须从社会各个部分选取,他们必须为得到某一职位而公开地相互竞争,向选民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民主”是一种权力为众多团体所分享的“多头政制”,是“多重对立的少数人”的统治[14]。多元民主理论的政治参与观认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不像精英民主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仅仅局限于选举性参与,公民还可以通过个别接触、社区活动等其他非选举性方式参与政治过程,表达政策偏好,影响政府决策。这样,随着民主理论从精英主义发展到多元主义,政治参与的含义也相应地由单维度的参与选举扩大到多维度的影响决策。同时,这一研究范围的演变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民主制度下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发展历程。
第二,在界定政治参与的含义和划分政治参与类型时,亨廷顿将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都归属于政治参与之内,而维巴则将“礼仪性”或“支持性”动员参与排除在政治参与范畴之外;亨廷顿将军事政变、暗杀、骚乱、叛乱等试图改变现存政治系统和政治游戏规则的非制度性参与包含在政治参与行为之内,而维巴则将政治参与限定在制度性参与行为之内,将骚乱、暗杀和所有其他类型的公民暴力等,试图改变现存政治系统和政治游戏规则的非制度性参与,排除在政治参与行为之外,这主要是由于二者所关注的问题域不同而造成的。
亨廷顿研究的问题域是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扩大和政治民主化的影响,研究的对象是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1]前言1。他将政治参与的扩大看成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和基本要素之一,关注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15]。
从其研究的问题域出发,亨廷顿把动员参与包含在政治参与之内,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内,(1)动员参与和自动参与之间的界限在现实中不像理论上那么容易分辨,与其在界限不甚分明的二者之间人为地划出一条线,不如把这两种参与行为都纳入研究范围。(2)政治参与实际上是动员参与和自动参与的混合,如果把注意力局限于自动参与,就容易错误地认为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社会中特有的现象。(3)从动态关系上来看,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都有可能相互转化。(4)动员参与和自动参与都能为领导人提供机会或构成约束,都对政治系统产生重大影响[1]8-10。
亨廷顿之所以把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包含在政治参与之内,是因为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有限,制度化参与本身效率也比较低,所以非制度性参与也就成了发展中国家公众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果将这类非制度性参与形式排除在政治参与范畴之外,研究人员可能会发现某些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至少很少存在政治参与这类现象了。另一方面,合法和非法政治参与之间的界限,在不同国家之间是不同的,同样一种行为,比如和平示威,在有的国家可能是合法的,在其他国家就可能是非法的。即使同一个国家内,合法和非法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界限有时是模糊和变化的,很难划分一条清晰的界限来。所以亨廷顿将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重要类型之一来进行研究,探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就会不愿采取更和平的参与形式,而趋向于采取暴力;当和平参与的机会丧失时,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人们才会倾向于选择暴力作为最后的手段;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某些社会力量会比其他社会力量更加可能使用暴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暴力将会与其他参与类型发生紧密联系[1]15。
维巴研究的问题域是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参与。与亨廷顿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维巴的研究对象是已牢固确立了公民合法参与权的现代民主国家。维巴将政治参与看成是这些国家中民主制度的核心,认为政府过程中没有公民自由参与的民主是不可想象的[16]。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分析政治参与对于民主国家实现社会平等的影响。
从这一问题域出发,维巴认为将“礼仪性”或“支持性”参与排除在政治参与范畴之外很重要[2]2。因为维巴认为政治参与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影响政府工作人员所作的选择或对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而影响政府的过程,而不是公民受政府影响的过程。“这种参与应该称为民主参与,它强调影响政府政策的过程,而不是执行政策;它强调群众源源不断地自下而上影响政府。”[2]3而公民“参加”“礼仪性”或“支持性”这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对政府的支持,而不是传递对政府的要求。
维巴将非制度性参与排除在政治参与行为之外,是因为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政治制度化程度较高,公民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较多,制度性参与行为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的参与效果,再加上受社会结构和民主制度的限制,非制度性参与也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维巴重点研究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制度性的、“普通的”(ordinary)政治参与,但他并不认为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不重要或者不合适。维巴之所以排除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还因为他认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这两类政治参与活动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无法用同一个理论模型来描述和解释,需要分别研究。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学者对现代民主国家中表现为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所提出的解释模型的理论视角大致可以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两类。从社会心理视角解释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理论主要有群体心智统一理论(the law of mental unity)[17]、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18]、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19]等,从社会结构视角解释公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理论主要有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20]、政治过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21]、政治机会结构理论(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eory)[22]等。 这些解释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理论模型与维巴解释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模型有很大不同。正因为如此,所以维巴才说,“我们关注‘普通的’(ordinary)政治行为,并不意味着这些(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不重要,只是研究这些行为是另外一本书的内容了”[2]3。
第三,与一些学者将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认知等政治心理因素和指向非政府部门的社会参与行为也看成是政治参与现象不同,亨廷顿和维巴都将这两类现象排除在政治参与范畴之外,这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论不同而造成的。
关于政治参与是否应该包括公民的政治心理和社会参与活动这一问题,仅从概念本身出发,很难作出判断,因为概念是用来描述现象的,概念本身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解释,它只是标出了学者所关注的研究对象的界限,这个界限的范围可以随着学者关注点的不同而不同。对于政治参与概念的界定,同样因为学者的关注点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有的学者将公民的政治心理和社会参与行为也归属于政治参与行为[7]。
虽然一个概念只是标出了学者所关注现象的界限,概念本身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但是,由于学者做研究不是为了孤立地界定某一概念而已,还要分析这一概念和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一个合适的概念有助于分析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概念有“ 有用”和“ 无用”的区别[23]7。 由于亨廷顿和维巴的政治参与研究都属于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包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一个是理论模型的设置,第二个是理论模型的经验检验。因此,采用实证方法研究政治参与现象,除了要界定政治参与的含义、划分政治参与的类型,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构建并检验解释政治参与的理论模型。界定一个合适的概念对于构建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并顺利获取经验数据来检验该理论模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亨廷顿和维巴的政治参与定义都将公民的政治心理和加入社会组织状况排除在政治参与范畴之外,就是他们构建政治参与解释模型的需要。
从理论模型的设置方面来看,选择哪些因素作为解释政治参与模型的自变量,如何界定这些自变量和政治参与这一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关模型本身的解释力。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亨廷顿和维巴都认为,虽然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政治认知等政治心理和加入学校、教会、工作场所、志愿组织等社会组织状况与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关系密切,但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行动并不是同一类现象,参加社会组织的行为与参加投票、竞选、个别接触等政治参与行为也是有区别的。因此,在他们构建的解释政治参与的理论框架中,都将政治态度、加入社会组织状况作为政治参与的解释变量,而不是政治参与行为本身。通过将政治态度和社会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亨廷顿和维巴从公民个体视角构建了有较强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政治参与解释模型,即在其他条件相同或不变的情况下,公民的政治知识越丰富、政治兴趣越高、政治效能感越强、加入的社会组织越多,在社会组织中越活跃,则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越大。如果将政治态度和加入社会组织包括在政治参与行为之内,则无法利用他们构建的理论框架,通过公民政治心理和社会参与行为来解释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而需要寻找其他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从模型的经验检验方面看,一个因变量定义独立于自变量定义的模型才在逻辑上具有可证伪性,一个变量清晰、可测的模型才具有可检验性[24]。亨廷顿和维巴将政治态度和社会参与行为从政治参与行为区分出来,将前者作为解释后者的因素,即将公民政治参与行为设置为因变量,将政治心理和社会参与设置为自变量,这种变量分离并独自定义的模型具有可证伪性,能够接受经验数据的检验。如果既将政治心理或社会参与归属于政治参与,又将政治心理或社会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解释因素,那么,这样的模型在逻辑上就无法证伪了。另外,在亨廷顿和维巴的理论模型中,政治心理、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这些概念界定清晰,作为个体层面的心理和行为变量,其测量相对容易,测量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也较高[23]186-192,因而模型检验的难度较低。如果在模型中引入一些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变量的话,则会因为这类变量的测量难度较大,测量结果的信度和效度较低,而增加模型检验的难度。
四、政治参与概念的基本共识
尽管由于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域和方法论不同,目前西方政治学中还没有一个能为所有学者所接受的政治参与概念,但在大多数学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基本共识的。这些基本共识从定义方面看,就是将政治参与看成是“公民试图影响政府的行为”,如米尔布雷斯和格尔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个人试图影响或者支持政府及政治的行为”[13]2,巴里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公民旨在影响公共代表及官员决策的行动”[25]。从政治参与现象的范围看,主要的共识就是认为政治参与只限于实际行动而不包括政治心理;政治参与的目标指向仅限于政府部门,不包括指向非政府部门的社会参与活动;政治参与既包括选举性政治参与,也包括非选举性政治参与;既包括志愿参与,也包括动员参与;既包括制度性参与,也包括非制度性参与;既包括指向非结构性目标的行为,也包括指向结构性目标的行为。政治参与概念的这些基本共识几乎主导了政治参与的经验研究领域,也获得了很多教科书和评论文章的广泛认可[26]。
从这里可以看出,亨廷顿和维巴的政治参与观和西方政治学中政治参与概念的共识性观点基本吻合。而且,与维巴将非制度参与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观点相比,亨廷顿的政治参与观看起来更具有代表性。确实,正如亨廷顿所认为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清晰的界限,有些参与形式实际上是处于这种两分法的过渡地带;两种参与形式也可能相互转化,一次组织良好的和平请愿可能会因某些突发因素而转变成暴力冲突,所以要将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截然分开确实不易。不过,如果考虑到非制度性参与和制度性参与在影响因素、参与主体、表现形式和结果影响等方面确实有较大区别,维巴主张将二者选用不同的解释变量分别进行研究,也不无道理,研究人员试图用一套变量来同时描述、解释非制度性和制度性参与也许并不能得到客观的结论。
就将政治参与限定在制度性的、合法的参与行为这一点来说,维巴的政治参与观也与中国主要政治学教科书中的观点更加吻合。如王浦劬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27],陈振明提出“所谓政治参与,就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政府决策与公共管理的行动”[28]。这些概念都强调政治参与是指行动而不是指态度,参与的目标指向政府,参与的主体是公民,参与的形式除了投票、竞选等选举性参与,还包括信访等非选举性参与,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都强调参与形式的性质必须是合法的。
[1]萨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VERBA S, NIE N H.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M].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2.
[3]VERBA S,NIE N H,JAE-ON KIM.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M].Camb 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53-54.
[4]ROSENSTONE S J, HANSEN J M.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M].New York: Macmillan,1993:42.
[5]CONGE P J.Review Article: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oward a Definition [J].Comparative Politics,1988,20(2) :241-249.
[6]MARSH A,KAASE M.Measuring Political Action [M]//Barnes,Samuel H.,Max Kaase et al.Political Action: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Thousand Oaks,CA.:Sage,1979.
[7]BEEGHLEY L.Social Clas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 Review and an Explanation[J].Sociological Forum,1986,1(3) :496-513.
[8]BOOTH J A,SELIGSON M A.Imag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Latin America[M]//Booth,John A.and Mitchell A.Seligson,eds.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Latin America:Volume 1,Citizen and State.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78:6.
[9]CAMPBELL A,CONVERS P E,STOKES D E,MILLER W E.The American Voter[M].New York:Wiley,1960:2.
[10]SHI,TIANJIA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1.
[11]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2]金贻顺.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J].政治学研究,1999,(2):62-70.
[13]MILBRATH L W,GOEL M L.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M].Skokie,IL:Rand McNally,1977.
[14]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M].周军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0.
[15]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杨玉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5.
[16]VERBA S,SCHLOZMAN K L,BRADY H E.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1.
[1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6.
[18]GURR T.Why Men Rebel[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56.
[19]COHEN J L.Strategy or Identity: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J].Social Research,1985,52(4) :663-716.
[20]MCCARTHY J D,ZALD M N.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A Partial Theor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82(6):1212-1241.
[21]TILLY C.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23.
[22]TARROW S.Power in Movement: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43.
[23]WELSH W A.Studying Politics[M].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3.
[24]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M].郑永年,胡淳,唐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31.
[25]PARRU G,MOYSER G,DAY 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6.
[26]BRADY H.Political Participation[M]//Robinson,J., P.Shaver,P.Wrightsman.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San Diego,CA:Academic Press,1999:737.
[2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6.
[28]陈振明.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