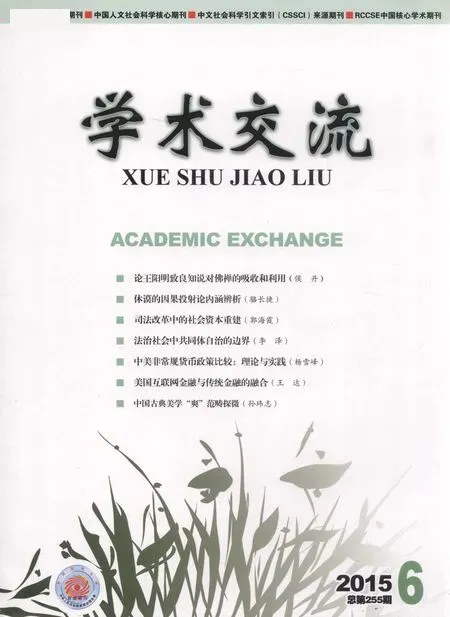重大灾难报道中的仪式传播策略
胡登全,谢流莎
(1.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重庆 400031;2.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0)
新闻传播学研究
重大灾难报道中的仪式传播策略
胡登全1,谢流莎2
(1.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重庆 400031;2.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0)
在重大灾难报道中,应突出仪式传播,化危为机,充分发挥媒介的价值整合作用。结合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和中国文化心理学,仪式传播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实施现场情境中的互动仪式;坚持媒介情境中的互动仪式;突出互动仪式中的集体记忆。
重大灾难;媒体报道;仪式传播
仪式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为意义的象征,它是人类的文化存在。仪式、传播和文化在本质上是共通的。换言之,仪式传播实际上就是文化传播。
人类举行仪式往往与社会生活中的危机和社会冲突相关。人类学和宗教学一致认为,仪式肇始于神话,它创造的社会秩序相较于客观的社会秩序,更符合人类的审美理想和终极价值。在仪式传播中,媒介所构建的稳定有序的景象,能在很大程度上使受众心理得到宣导抚慰,因此,“传播的仪式观着重揭示文化和意义,是对信仰和价值的整合”[1],这在重大灾难报道中的作用尤其明显。
那么该如何实现仪式传播,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的“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理论,提供了较好的参考思路。
一、实施现场情境中的互动仪式
兰德尔·柯林斯认为,仪式互动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是一种相互关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通过仪式的互动能够对共同关注的话题形成一种共同的情感,通过情感能量激发人们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做出他们认为道德上允许的事情。在微观过程中,互动仪式(IR)是人们最基本的活动:在较小空间的、事件现场的、即时发生的面对面的互动,是人类仪式传播的重要情景和所有行动的起点。他进一步认为,人们的一切互动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这种情境是指经由个人所形成的社会关联或网络。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切看法,所积累的一切素材也都来自这种情境。因此,“互动仪式(IR)和互动仪式链理论首先是关于情境的理论”。[2]32
兰德尔·柯林斯指出,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因此,互动仪式与“互动仪式链”理论尤其强调“身体在场”情况下的互动,因为它体现了“面对面的互动”,“在该过程中参与者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并彼此相应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微观节奏与情感。”[2]85也就是说,身体在场的现场情境交流是互动仪式的一个关键。
国外学者在“火星人入侵:广播使美国陷入恐慌”的研究中发现,“个人对广播内容的接受,容易受到特殊的收听情境的影响”[3]。例如,某个听众如果是因为得到一个处于惶恐不安状态中的朋友的通知而收听这个广播,那么在收听情境和对收听内容的反应上,这个听众就必然会与因为其他原因(比如无意识或出于好奇)而收听的听众大为不同。同理,重大风险事件中,事发现场的公众构成了一个身处特殊情境的群体。这个群体对于事件的真相、事件的进展、政府的处理、传媒的报道等都有着不同于外界人群的敏感的解码和编码,他们在现场情境中的言行和情绪对其他公众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因此,对于这部分群体的宣导抚慰、舆论影响更要重视“身体在场”的现场情境和互动仪式的运用。
事件现场既是解决风险的关键场所,又是媒介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事件起因为何?最新进展如何?政府官员的反应及处理情况如何?事件的受害者、参与者、目击者等一系列影响舆论的关键人物也会通过现场的感受形成对事件、对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在此情境中,政府高层领导与公众的“身体在场”——与公众的直接交流,是具有极高沟通价值的互动仪式。正如兰德尔·柯林斯所认为的:在仪式互动中,认同感与亲身在场之间关系紧密,对于政治人物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现场的演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件”——换言之,演讲者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影响能建立起共同的热情[2]101。
事实上,中国几乎所有的风险事件中,公众除了对信息公开的渴望,还有着对政府领导亲临现场的渴望。领导、官员的“身体在场”,更多的是给公众一种心理的抚慰以及信任。这是千百年来“家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沉淀:领导和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担当的是“父亲”的角色,理应在“百姓儿女”遭难的时候在现场体现“父慈子孝”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体系中,家庭、家族和国家的组织结构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都是典型的父亲家长制。从家庭到家族再到国家,社会结构逐层扩大和延伸,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中,父家长是家庭和家族的君王,君王是国家和所有臣民的家长,他们的地位和责任至大。
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和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但“父亲”的文化符号在人们心中依然根深蒂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曾在《我的儿子》中斗志昂扬地对传统的“孝顺儿”进行了颠覆,满怀激情地希望中国人应有“现代父亲”。但他后来又亲力亲为于“整理国故”,引人深思的是,他在死后被广为认可的几个定性评价是:儒士、慈父、孝子。
因此,在国人的文化习性中,“父亲”是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原型。国君、古代地方政权的首脑、现代社会的政府官员都是百姓潜意识中的“父亲”意象,理应体现“仁君意象”。
父亲是慈爱的责任担当者。“父慈子孝”是对父子关系的形象表述。《礼记》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墨子》从另一个角度强调说:“父者之不慈也,天下之害也。”同时,父亲也必须是责任担当者。《庄子》载:“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诗经》曰:“父兮生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源于“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中国人发展出了一种以具体的人格为对象的信任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由亲而信的心理期待:父家长因其血统上的宗主地位,理所当然地统率其族众家人并为他们做出应有的承担。父家长是一家之首领,子女们慈爱的严父,君王是国家的首领、普天下所有百姓的严父。换言之,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在此文化心理影响之下,君王为父,相应的各级官员被看作百姓的“父母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老百姓对良吏“家长”的期待。
事实也证明,较高级别领导和公众形成“身体在场”的互动仪式,往往能满足国民文化习性中的家国同构、青天父母官的心理认知,从而达到较好的沟通效果。鹤岗矿难事件中,各相关领导迅速赶往现场进行救援调查,与公众面对面沟通;瓮安事件中,起初民意沸腾、社会秩序混乱,其后省委书记走进群众家里倾听他们的意见,召开群众座谈会直面民意,三次鞠躬……通过这种“身体在场”的情境与各种仪式的互动,对在短时间里平息事件、引导舆论起到了极好的效果。
二、坚持媒介情境中的互动仪式
“身体在场”的传播,是互动仪式链的重要一环,它主要适用于小范围的、面对面的情境,但由于时间、空间等条件的限制,风险爆发后,媒介、公众与政府或相关人士的交流不可能总是在现场情境进行。对此,兰德尔·柯林斯也认为,互动仪式链包含了多种方式的互动,除了亲身在场,远程的交流同样可以为沟通者提供仪式参与感,进而在对共同话题的关注中共享某种情感,得到心理的慰籍,并且,总体来说,大规模的仪式相比小规模的自然仪式而言,远程交流效果会更好一些:“远距离的交流让人有属于更大群体的感觉。”[2]103-104
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即时的远程(媒介情境)交流提供了条件。下面以网络为例,简要分析媒介情境中的仪式互动。
在博客、论坛,尤其是QQ(群)、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比较强的网络运用中,虽然没有实体的身体在场,但却存在“文字在场”和“心理在场”的特点,互动过程一旦在网络中实现,尤其是即时互动的情况,人们虽然不一定能见到对方的身体,但却能肯定对方一定在“电脑”前,是一个真实的个体,知晓对方真实的身份(在与政府官员和熟人朋友之间)和与对方的关系。这样一来,网络的“文字在场”和“身体在场”构成了交流者身体的“虚拟在场”互动。
网络情境中的“虚拟在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体现:第一,虚拟在场以客观在场为原型。虚拟在场携带了现实原型的某些特征,以数字化的形式在虚拟空间中模拟出来。没有现实的原型(如政府官员和公众),就不会有虚拟在场(网络情境中的政府官员和网民)。第二,虚拟在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就共同情境中的共同问题展开实时与双向的沟通交流,达到对问题和价值的探讨和共享。因此,“虚拟实在能实现远程出场,使主体产生沉浸感。”[4]
这种数字化的虚拟实在,构建了当代社会新的虚拟在场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网络虚拟就媒介技术来说,是一种数字化的构建方式,但其表征的内容却与现场情境的感受性具有相同效果。这种互动方式同样能够产生现场情境互动的“共同关注”和“情感连带”效果,因此互动仪式与互动仪式链理论依然能够产生作用。
兰德尔·柯林斯认为,在互联网这种远程交流的媒介情境中,有着不同于现实身体在场情况下的互动仪式和网络情境,互动仪式发挥效果的前提是“远程传播必须传递观众的参与热情,而不只是领导者和表演者的信息”[2]104。如果缺乏实时的交流互动,媒介情境不能建立起强烈的团结意识,就不能使网络交流具有集体性意义。
网络情境中,“回复”“回帖”是网络实现互动的一个重要仪式。“在线回复”与“延时回复”会产生不同的“团结意识”和“集体性意义”。“在线回复”由于“相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形成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2]3,是一个可以带来更高价值共享的仪式,它能使对话双方对相互关注的话题迅速产生思想碰撞、情绪感染,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双方的交流欲望,在交流中“建立起强烈的团结意识”,“使网络交流具有集体性意义”,从而有利于最快最有效地进行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
传播就是仪式,仪式传播也就是文化传播,因此任何传播都要遵循该传播场域的文化情境。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加快,公众在与政府和官员的交流中,“服从他人的倾向大为减弱,从拘谨变得自主,从柔弱变得富有表现力。”[5]同时,互联网的匿名性、虚拟性、相对宽松自由等特点使网络这种媒介情境具有了自我表露、去个性化、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网络情境下的交流更提倡和坚守平等、自由、民主。
因此,网络舆论引导必须遵循网络情境的规则,与网民展开平等、真诚的互动交流与更加柔性、人性的引导策略。强制关网,封贴删帖,盛气凌人的官语、说教,甚至指责、上纲上线扣帽子等很容易招来广大网民情绪性的“拍砖砸瓦”,引发网络民意的强烈反弹,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
此外,根据互动仪式链理论,微观情境的相互关联形成了宏观结构上的关联,即具体情境中的个体之间通过局部的、反复的、不间断的互动,最终将形成不同情境下的团结性、流通性、成员身份归属性、情感共鸣性等。在这里,互动仪式链理论所强调的并不是一般性的社会规范,而是关注由不同群体在互动中所实际形成的情感团结。因此,其重点是通过情境,而不是认知建构,更不是灌输其意识使共享的情感和主体间的关注洗刷个体的过程。重大风险事件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其进展时时在网络舆论的关注之下,所以风险传播中的网络舆论实际上是两个情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是一个网上网下“仪式互动链”的过程。要达到最佳“互动链”效果,事件现场与网络等媒介情境中的仪式互动必须相互结合,彼此呼应,同时进行,达到宏观结构上的关联和最大限度的社会互动。
三、突出互动仪式中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首次提出的。他在1925年发表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认为,个体的记忆来源于与集体中其他个体的长时间的互动和交往,而集体则通过决定其成员的记忆方式来获得并保有其记忆。如果一种物体/观念要成为集体记忆,就必须有具体的个体或事件作为载体,就必须要使该物体/观念能与集体认同的意义相联系。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核心是“社会群体”,其最终指向是对于国族认同建构的凝聚性。中国台湾学者翁秀琪认为它的凝聚策略表现在三个方面:族群凝聚、族群认同变迁、民族体形成。[6]
受哈布瓦赫的启迪,众多学者投入了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扬·阿斯曼,他在1997年所出版的《文化记忆》一书中将“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进行融合,进一步阐述了文化、集体、记忆之间的同一性。
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该结构蕴含了国民的共同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并不断使过去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这种凝聚性结构的产生和维护,便是“文化记忆”的职责所在。在阿斯曼的理论中,文化记忆的目的就是巩固集体的主体同一性。其次,文化记忆的传承一定是遵循着特定而严格的形式,一定需要相应的符号系统或者呈现方式。[7]
在信息社会,大众媒介必然是集体记忆最为主要的符号系统。一个民族在发展中会遭遇许多风险,尤其是在面对自然灾难、恐怖暴力等社会秩序混乱的时候,更需要媒介传达出“认同、凝聚”的集体记忆,化危为机,快速实现社会动员。
以功能主义观点看,社会管理和机构运行应该满足社会及个体的需求。学者们认为,媒介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机构,其“需求”主要和连续性、秩序、整合等相关。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就提出了媒介“三功能说”: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以及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之后的50年代,赖特在媒介“三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功能,即娱乐功能。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认为媒介具有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一般的社会功能。之后的90年代,麦奎尔则认为,随着大众传播广泛应用于政治和商业宣传,媒介应该加入第五项功能——动员功能:媒介要促进政治、战争、经济发展、工作与宗教领域中的社会目标的活动。[8]迄今为止,麦奎尔的媒介五功能理论,获得了最为广泛的认可,媒介动员功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重大灾难一旦爆发,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文化认同是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抑制心理创伤的必须手段。媒介社会动员的前提是强大的辐射力和号召力。以电视为代表的具有强大社会资本的主流媒体无疑是该项功能的主要实施者和引领者。丹尼尔·戴杨认为媒介事件的生产能够“唤起和重申社会的基本价值并提供共同的关注焦点……事件感,使得某些核心价值感和集体记忆醒目起来”[9]。简言之,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可以通过戴杨所说的“媒介事件”中的“加冕”营造一种全民参与的互动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仪式性+新闻性+参与性”是唤起或构建集体记忆的有效手段。
这种仪式性的媒介事件具有以下8个特点:(1)电视直播。(2)中断了日常生活和日常的电视节目。(3)事件预先策划,按脚本进行。(4)观众规模巨大——整个世界都在观看。(5)具有非看不可的强制性。(6)直播解说中充满着虔诚与敬畏。(7)事件的功能是促进社会整合。(8)典型的功能是提供安慰与调和。戴杨和卡茨认为,这种大型事件的直播,是在唤起传受双方的核心价值与集体记忆。[10]也就是说,无数原本分散的“乌合之众”的受众,通过观看电视屏幕上的媒介事件,意识到自己正作为一个集体的成员参与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仪式,集体感、归属感和使命感由此产生,在此过程中,“社会最高秩序的统一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实现。”[11]
以中国电视报道为例。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5月18日在央视的直播募捐晚会上,千余名明星纵情演唱《爱的奉献》。5月19日,庄严的国旗在万众瞩目中缓缓降落。3分钟的举国默哀后,首都天安门广场和成都天府广场的几十万国人摒弃伤悲,振奋高昂,此起彼伏的“汶川加油!四川加油!中国加油!”通过电视画面的传播,营造了全民参与的仪式,建构了举国上下的情感共鸣场,使所有的受众产生一种“在场”的集体记忆体验。在这种国家叙事框架中,所有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不分阶层、国界、身份,共同的“集体记忆”将他们紧紧地构建成为一个共同体,使他们确认自己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之中,并确信自己是这集体和文化中的一分子,这种寻根式的集体记忆,“把无数早已分枝的枝叶联系到一个共同的根那里,不仅得到了互相认同的基础,而且仿佛找到了力量的来源。”[12]
电视的媒介事件和仪式互动更多属于官方有意而为,而网络媒介则展现了“多难兴邦”的集体记忆对国族凝聚力的无意识唤醒。2013年4月20日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后,腾讯网推出了“直击芦山救援祈祷雅安平安”的专题,在此专题之下分为若干栏目:最新消息、震中日志、腾讯网友慈善平台、网友捐款平台、明星祈福、体坛界祈福、宝贝行动、将爱闪电送达、地震寻人、微信微博寻人等。
此外,当日,百度在地震贴吧中开通了实时新闻发布平台,让网友通过自己的平台为灾区人们祈福,360搜索推出了四川雅安地震寻人平台,搜狐新闻客户端也开通直播服务,全天候24小时连续报道相关新闻,微信推出“雅安地震救助”公众账号,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在当日上线紧急捐赠平台,其他多家公益网络捐赠平台也紧急开通,马云、柳传志、马化腾等企业家和众多明星、公众人物亦通过各自渠道引领民众捐款。凝聚13亿人的中国力量,让无数网民参与其中,网络社区对救灾的建言献策、凝聚士气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见,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仪式性呈现中,既有国家领导人与灾民在现场情景中的“身体在场”的仪式互动,也有媒介情境中的虚拟在场互动,还有媒介与现实的互动,媒介通过这种“仪式互动链”,成功地将分散匿名的大众进行了“有机组合”,集结在“多难兴邦”的神圣庄重的语境中,凝聚成一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现代整体国家,从而完美实现了民族认同和社会动员。
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事关国家形象、人心凝聚和社会价值整合,它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多方面的合力,更需要媒体遵从传播规律、研究受众心理,采取立体多维的报道策略。尽管在近年的此类报道中,中国媒体的社会疏导和社会动员能力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在全球风险社会和新媒体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媒体要充分发挥其宣导抚慰功能,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而融合中国文化心理元素的互动仪式传播无疑是可供参考的一种报道策略。
[1]陈力丹.传播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还是一种仪式?——关于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讨论[J].国际新闻界,2008,(8):44-49.
[2][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刘海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1.
[4]刘大椿,张星昭.网络伦理的若干视点[J].教学与研究,2003,(7):20-26.
[5][英]彼得·史密斯,[加]彭迈克,[土]齐丹·库查巴莎.跨文化社会心理学[M].严文华,权大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309.
[6]翁秀琪.集体记忆与认同构塑——以美丽岛事件为例[J].新闻学研究,2001,(7):117-149.
[7]黄晓晨.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06,(6):61-62.
[8][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社,2006:67.
[9][法]丹尼尔·戴杨,[美]依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3.
[10]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99.
[11]刘燕.媒介认同论:传播科技与社会影响互动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219.
[12]余霞.历史记忆的传媒表达及社会框架[J].武汉大学学报,2007,(2):257.
〔责任编辑:曹金钟 王 巍〕
G212
A
1000-8284(2015)06-0214-05
2014-10-09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风险治理中的舆论引导效果评估及对策研究”(2013YBCB056)
胡登全(1975-),男,四川德阳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与传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