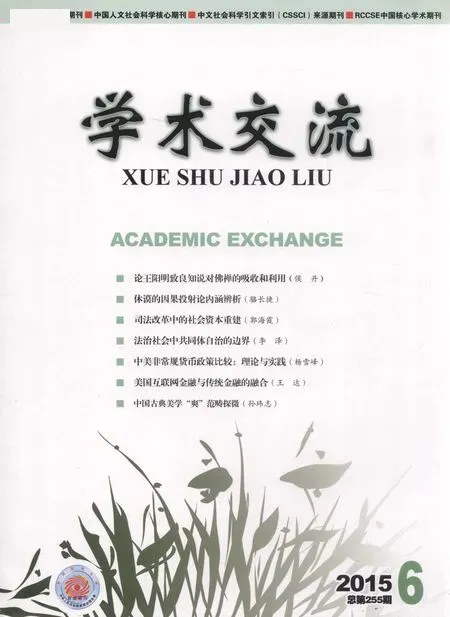鲁迅小说“父亲缺失”现象的精神分析
吴铜虎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浙江 温州 325011)
鲁迅小说“父亲缺失”现象的精神分析
吴铜虎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浙江 温州 325011)
鲁迅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唯独没有清晰的父亲形象。“父亲缺失”既是鲁迅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鲁迅小说的创作现象。如果以精神分析的视角去探究,我们会发现,鲁迅小说中常常以母子关系、兄弟关系、叔侄关系来替代父子关系。因为关系的改变使得鲁迅能更真实、更彻底地表现出对于父亲的爱与恨,尤其是恨。然而对于父亲的恨是不被允许的,这种情感只能伴随着童年的记忆潜沉至意识深处,折磨着鲁迅。而小说创作让鲁迅被压抑的父亲情结能够以另一种改装的形式加以释放,从而修正了对于父亲的恨,化解了自身的精神危机。
鲁迅小说;父亲缺失;精神分析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家喻户晓。当年去仙台学医是为了救治像父亲一样被庸医误治的人们,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是为了救治精神麻木的人们。如果置之于精神分析的语境,那么学医的目的是为了记住父亲,把对父亲的爱转移到他人身上,而弃医的目的是为了忘记父亲,因为鲁迅害怕只要从医就必须时时记起父亲并承受痛苦。父亲的病与死作为鲁迅独特的情绪记忆,对其情感心理的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以父亲的病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意识、文化意识和愤激情绪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创作,成为他创作结构中不少方面的潜在形式和情感原型[1]。而这情绪记忆中必定包括对父亲的恨,这让鲁迅先生痛苦不已。
小说创作已经成了鲁迅缓解内心痛苦、解决精神危机的内在需要与有效手段,这也是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之一。他的墓碑上刻着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理性的声音是微弱的——那么据此推理,感性的声音是强烈的。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能发出“理性的声音”的是超我与自我,能发出“感性的声音”的就是本我。本我被自我、超我压制得越深,爆发出来的声音就越强烈。只是在不被社会与道德允许的情况下,本我以曲折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声音”从而获得平衡,这方式当中包括小说创作。
鲁迅先生早年就介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并有意识地把它融入小说创作之中。在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中,着重表现了“自我母题”,而回避了同样被视为人类最基本母题的“父子母题”。鲁迅对“父子母题”并非无话可说,为何在他的创作中如此费心地躲闪,并形成“父亲缺失”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这其中所蕴含的创作愿望,值得我们深入地分析。
一、存在状态的矛盾:有与无
在鲁迅的小说中,人物的关系结构网中有母子关系、兄弟关系、看与被看的关系,但缺少正常的父子关系。在鲁迅小说中,“缺失”是父亲角色最基本的存在状态,但并不是说鲁迅小说中没有父亲的存在。只是“有”在于扭曲地存在,“无”在于无痕地消失。
(一)让父亲扭曲地存在
在鲁迅的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大致有这么几种:
1.善良无知的麻木者。如《药》中的华老栓,为了治好儿子的病,无意间成了杀害革命者的帮凶。又如《故乡》中的闰土,由机灵的少年变成了麻木、具有浓厚等级观念的中年人。善良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优秀品质,但当这种品质在无形中消逝,甚至在无意间成为恶的源头,这对于麻木的当事人来说是不会痛苦的,但对于清醒的旁观者而言是何等的痛苦。在鲁迅的小说中,这些父亲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被父权社会所抛弃,他们生存于社会主流文化的边缘,存在得毫无价值。
2.道貌岸然的伪善者。如《肥皂》中的四铭,一方面叹息“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仿佛他就是社会道德的模范;另一方面因一块香皂而引发了对于女人的性幻想,整天想着“咯吱咯吱”那样“不要脸”的事情。又如《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标榜学贯中西,自比高尔基,却只想着打牌和看女人的事情,即使去贤良学校应聘也只为看女生而已。这些人自以为是社会道德的象征和社会责任的标杆,其实都是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善者,心里充满着自私、龌龊、邪恶的念头。这种父亲枉为人父,他们只是被奚落的对象,不具有父亲威权的特征。
3.封建守旧的杀人者。封建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父权文化毫不动摇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又维护着封建社会,不容许破坏封建文化、否定父权文化的异类出现。这在无形中谋杀了代表新文化的一类人或一代人。这种父亲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如《风波》中的赵七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阿Q正传》中的赵四爷。他们是潜在的父亲,代表着封建文化的力量,并以这种力量有意或无意地“杀人”。
无论是精神麻木者、道德伪善者,还是封建杀人者,其身份都是“父亲”。这些父亲不知道孩子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扭曲地理解了孩子存在的目的。他们也不知道孩子未来的路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为下一代铺就一条通向黄金世界的道路。他们的存在,是扭曲社会的存在意象,他们的心灵折射出社会扭曲的弧度。在鲁迅看来,除了血缘关系之外,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存在。
(二)让父亲无痕地消失
小说是虚构的,而虚构的内容更能体现一个人潜在的意识。在鲁迅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无论是介绍、合声还是尾声部分,都存在着“父亲缺失”的文学现象:只见儿子,不见父亲。如《药》中的夏瑜、《祝福》中的阿毛、《明天》中的宝儿、《铸剑》中的眉间尺等,他们都失去了父亲。还有《狂人日记》中的“我”只有大哥,《长明灯》中的“疯子”只有伯父,等等。这些还未长大的孩子,不是失去父亲就是父母双亡。这种“父亲缺失”的文学现象,对于鲁迅来说恐怕有着极其深刻的精神意味。由此造成的精神空缺,鲁迅却借着别样的方式来填补。
1.以母亲来填补父亲的空缺,以“母子关系”来替代“父子关系”。鲁迅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的寡母形象,如《祝福》中的祥林嫂、《风波》中的八一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从她们的姓名称呼可知她们的社会地位之低,因为她们的称呼是以丈夫的名字为依托的,却要承担起本该属于孩子父亲的抚养与教育的责任。最典型的是《故乡》与《社戏》,其中的“我”,最具有鲁迅本人的特质。作品中不见父亲的影子,只有母亲的牵挂与教诲。鲁迅引领读者明白父亲缺失的事实,却并未因此感觉到“我”的可怜。这在无形之中,已经由母亲替代了父亲。
2.以长兄来填补父亲的空缺,以“兄弟关系”来替代“父子关系”。鲁迅的小说也塑造了一系列长兄形象,如《狂人日记》中的大哥、《采薇》中的伯夷、《弟兄》中的张沛君等。他们是长兄如父,很大程度上起着父亲的作用,而相对应的狂人、叔齐、弟弟等则幼弟若子,很大程度上成为被照看、被限制的对象。尤其是《狂人日记》中的大哥以家长的名义,以家庭的权威把精神的枷锁牢牢地套在“我”的头上,钳制着“我”的思想,使“我”成了“不正常”的狂人。对于“我”来说,大哥就是父亲,他扮演着父亲的角色,执行着父亲的权力。这种角色错位的方式,虽然不是鲁迅生活的现实(鲁迅没有长兄),但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父母不在,长兄为大”的思维方式,巧妙地消解了由“父亲缺失”而造成的心理紧张。
3.以叔伯来填补父亲的空缺,以“叔侄关系”来替代“父子关系”。鲁迅的小说构造了一些叔侄关系,如《故乡》中“我”与宏儿的关系。整篇文章人物关系的设置很是巧妙,有着明显精心设计的痕迹。“我”与宏儿的父亲都是缺席的,“我”的长辈是母亲,宏儿的长辈是“我”,“我”与宏儿之间形成“叔侄关系”。“我”缺失父亲,却又要扮演父亲的角色;宏儿缺失父亲,却要由一个本就缺失父亲的“我”来扮演其父亲的角色。这种“类父子关系”无法填补“我”的精神需要,也无法填补宏儿的精神需要,而鲁迅还是让真正的父亲缺失。在鲁迅潜意识里面,用“叔侄关系”替代了“父子关系”,是鲁迅对父子关系的另一种替代方式或消解方式。
这三种关系,我们称之为“类父子关系”。其中的“父亲”角色有着父亲的职责,却缺乏父亲威权的明确标志。“没有父亲意味着没有精神的主宰者和现实中的模范者,在儿子的心理上这是一种先天的放逐”[2],而鲁迅让这种“放逐”成了现实,有意无意地让父亲角色在人际网络中无痕地消失。
二、情感表现的矛盾:爱与恨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与恨总是纠缠在一起。丧父之痛因为爱,寻父不得而生恨。鲁迅对于父亲的恨与其爱的毁灭有着必然的联系,“复仇最初源于爱的缺失,也即,最根本的复仇是由爱转化而来的,因为爱的事物的毁坏与伤害,造就肉体或心灵的刺痛”[3],由此产生了恨。鲁迅对于父亲的爱与恨,既是主观感受,也是客观存在。重要的是,鲁迅如何面对。
(一)爱在于对父亲的隐蔽
鲁迅的父亲既是父权文化的维护者,也是父权文化的戕害对象,他仕途坎坷却秉性刚烈,其父入狱而家道中落,孤独抑郁又借酒浇愁,病痛折磨却被庸医误治。父亲命运的悲苦,鲁迅听于耳、见于眼、感于心,他对父亲有着天生的同情,而这种同情源于对父亲的爱。鲁迅对于父亲的“爱”,来自他对父亲悲苦命运的回忆,其爱的情感产生于父亲的病与死亡。
鲁迅在他的《父亲的病》中写道:“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父亲的病痛,鲁迅有着亲身的感受,作为儿子的他希望能够帮助父亲,甚至代替父亲承受病痛的折磨。然而一句“谁也不能帮助”,显示了鲁迅的痛苦与无奈。年少的鲁迅觉得结束父亲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喘完”,这是没有经过任何理性分析的最直接的内心感受。即使年长之后,父亲的痛苦还深深地刻在鲁迅的记忆里,“便是现在”,他也觉得让父亲结束病痛折磨的想法是“正当”的。而且,在父亲临终前的“喊魂”行为,鲁迅觉得这是“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而产生深深的自责,这种深深的自责源自深深的爱。鲁迅的一句“我很爱我的父亲”,不仅是他年少时的直接感受,也是年长时的理性确认。这也是鲁迅在所有作品中对于父亲的爱的唯一表达。
但是,这种爱的表现多出现在他的“散文”之中,而“小说”当中对这类情节或感情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描述。这不是鲁迅没有相关的生活经历,而是他采取了“隐蔽”的方式。
如果说散文具有生活的真实性,那么小说则具有虚构的真实性。生活的真实能直接表达感情,而虚构的真实则更能表达精神深处被遮蔽的感情。父亲的病痛与死亡,能引起鲁迅的同情与爱,这表现在他的散文之中,但父亲的病与死亡给鲁迅带来的精神痛苦以及引发的对于父亲的恨则是无法言说的。鲁迅先生深知自己爱父亲的同时也恨父亲,但在所有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鲁迅直接表达对于父亲的恨,甚至他害怕自己把父亲视为恨与反抗的对象,所以在鲁迅的小说,他把父亲“隐蔽”起来,不让父亲在作品中出现,让父亲处于缺失的状态,这在理性层面上就是一种大爱。
(二)恨在于对父亲的孤立
鲁迅虽然在散文中表达了对于父亲的爱,但在事实上鲁迅并没有接受太多来自父亲的爱,尤其是“五猖会”前背书的无奈、药店柜台前的冷遇、科场案后的重担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助,这一切以及所伴随的痛苦都与父亲有关,而且都历历在目,渗入骨髓,给鲁迅幼小的心灵留下无端的伤害,自然引起他莫名的反抗。所以说,在得不到父爱的前提下却要表明自己对于父亲的爱,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痛苦甚至恨。鲁迅对于父亲的恨表现得相当隐蔽,然而正是这种隐蔽起来的无意识状态,却是最真实的。
1.让母亲痛苦地守寡。从家庭结构而言,男性的缺失对于女性的生存是致命的。在鲁迅小说中,家庭结构网中总是缺失父亲,他让其中的母亲成为寡妇,这些寡妇在无望中痛苦地挣扎。鲁迅的这种感受首先来自自己母亲的真实生活,但更是对父亲的报复:那就是在小说创作中让母亲(父亲的妻子)守寡。如《药》中的夏瑜只有夏四奶奶祭奠,《明天》中的宝儿只有单四嫂子守命,《铸剑》中的眉间尺只由母亲养大,《故乡》中的“我”只有母亲相守,《祝福》中的阿毛只有祥林嫂念着,等等。这些寡妇们因为没有丈夫,有的被迫“守节”,有的被逼“失节”,无论是哪一种“节”,都是他人与自我的双重压抑,都是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父亲原本是家庭的支柱,是孩子赖以生存的根基,失去父亲就等于失去生存的支柱与根基。在日后的生活中,这要由母亲来承担。在鲁迅看来,这些寡母们悲惨的命运,是由作为丈夫与父亲的男人的死亡而造成的。鲁迅在此表达了对于父亲的不满,即父亲对于妻儿的不负责任。如果男人没有生病死亡,那么女子就不用承担那么多、那么重的痛苦。
2.让孩子孤独地死亡。从家庭结构而言,父亲的缺失对于孩子的生存也是致命的。孩子是民族的未来,鲁迅对此也有着美好的期望,那就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鲁迅的本原思想。但其前提是父亲的存在与给予,如果没有父亲“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那也就没有幸福与合理可言。而在鲁迅的生活中,他的父亲没有给他这些,鲁迅也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不是“幸福”“合理”的[4],由此产生了对父亲的恨。
只要把目光投入鲁迅小说之中,我们会发现鲁迅笔下孩子的命运大致有三种:一种是毫无意义地活着,如《风波》中的六斤、《长明灯》中的“赤膊孩子”、《示众》中的“胖孩子”;一种就是毫无价值地死亡,如《药》中的华小栓病死了,《明天》中的宝儿夭折了,《祝福》中的阿毛被狼吃了;还有一种就是希望的破灭,如《故乡》中的闰土,少年时活泼可爱,中年时封建麻木,还有《社戏》中的阿发们,没有知识,不见未来。也有一些失去父亲的人虽然没有过早地夭折,却在孤独中耗尽了生命。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还有《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们都是原有文化的反抗者,却最终走向失败。这是脱离父亲文化环境而成长起来的必然个性,这种个性有着勇敢无畏的一面,但也有着悲剧无用的一面。因为他的觉醒,他的思维,无法正常表达一代人的诉求,无法与其他社会成员形成精神的沟通,最终变得孤独,消解于无用之中,在孤独中耗尽了生命。这是另一种死亡的方式。鲁迅小说中“儿童死亡”的情结相当突出,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父亲的“报复”,让他无子无后,老无所依,备受生活孤独的折磨。
鲁迅对于父亲的恨,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的表述。但他在小说中表现了“母亲的守寡”与“孩子的死亡”,从精神分析的层面上,这是在曲折地表达对父亲的恨。
三、情结交互的统一:父与母
按精神分析学说,恋母情结与由此而引发的弑父情结,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情结。在这种情结之中,母亲与父亲是对立的。在鲁迅的小说中,女娲象征着母亲,而女娲两腿间的那个古衣冠的小丈夫象征着父亲。鲁迅以“自然性”来象征母亲,她创造着人类,是爱的缔造者,而以“文化性”来象征父亲,他道貌岸然,诬蔑爱的缔造。在小说之中,我们可以发现,鲁迅以对母亲的爱来对抗对父亲的恨。
(一)弑父情结
父亲对于儿子,本是一种英雄式的榜样,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柱。但鲁迅的父亲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痛苦的根源,“病”时的买药受尽精神侮辱,“死”时的呼喊遭受精神恐慌。这种童年经历,在鲁迅的精神上烙下深深的印记,最后潜沉于无意识之中。本我的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抗情结被自我、超我深深地压抑着,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来宣泄,其中小说创作就是一种途径。
鲁迅对于父亲有着深层的反抗,这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但如果说鲁迅在潜意识中有“弑父情结”,恐怕会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因为这是对现实生活中鲁迅的一种“污蔑”。但如果从精神分析的层面对鲁迅的小说进行解读,恐怕还是有一些道理。鲁迅小说中的“类父子关系”,其基本存在状态就是压抑与反抗的对立。鲁迅并未直接描述儿子对于父亲反抗,因为这是社会原则与道德原则所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本我的追求是不被自我、超我的追求所允许。
所以,鲁迅在小说创作中有意地回避儿子反抗父亲(包括“审父”与“弑父”)的话题,却以弟弟审判兄长、以自我否定自我、以侄儿反抗叔叔或伯伯等方式来替代。而且鲁迅让反抗的主体变成了“狂人”、“疯子”或“孤独者”,甚至隐藏了性别,以女性的姿态出现(如子君),让他们在非正常的状态下进行反抗,这无形中消解了鲁迅自身作为反抗者的社会审判与道德审判,并在心理上获得了一定的安宁。
1.以“杀他”实现“弑父”的目的。鲁迅从创作小说开始,就设计了“审父”模式,表达孩子对于父亲的精神审判。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狂人的审判对象就从具有父亲威权的“大哥”开始。还有就是《弟兄》中作为兄长的张沛君、《采薇》中作为兄长的“伯夷”,这些“兄”都是被审的对象,而“弟”却不受到任何审判。这里的“兄”实际就是“父”的象征,他们以父亲的准绳来钳住“弟”或“子”的思想。所以说,对于兄长的审判,就是对于父亲的审判,以兄长来替代父亲,其反抗就会更加彻底,不受伦理限制。故以他者为对象进行审判,“审父”的行为变成了“审他”行为。虽然名称改变,但所指不变。
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铸剑》,眉间尺虽因“为父复仇”而存在,最终却表现为“仇父”。在小说中,父亲是爱的对象,国君是恨的对象。但实际上,深入研读小说,我们会发现,父亲与国君是二位一体,是爱与恨交织的完整个体。一个是自然属性的父亲,血缘关系是他们的联结点;一个是社会属性的父亲,文化关系是他们的联结点。因为血缘关系,所以必须爱,但因为文化的压迫,所以产生恨。作为臣民的眉间尺仇杀作为国君的楚王,这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弑父”心理与行为。所以,在复仇的道路上,眉间尺表现得犹豫不决,害怕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来自对于死亡的恐惧,而是对于“弑父”行为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压力的逃避。眉间尺爱他的父亲,也恨他的父亲。爱到极点的时候,也恨到极点;恨到极点的时候,也爱到极点。这恐怕也是鲁迅先生对于父亲的最真实的心理反应,所以他安排眉间尺“自杀”,让复仇的愿望由一个黑衣人来完成。最终的结局是:黑衣人替代眉间尺杀死了楚王。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表面上是他者杀了另一个他者,实质上就是孩子借他者杀死了假想为另一个他者的父亲,将对于父亲的恨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而且“弑父”的人,不是本人,换成了他人。这样把父亲描述为他者,把儿子也描述为他者,这让父亲的存在感以及仇父的真实感大大减低[5]。使父亲未能进入其社会性的反抗视野中,这就完全消解了“弑父”的罪恶。
2.以“自杀”实现“弑父”的目的。鲁迅对于旧式父亲的反抗是非常激烈的,这也是五四时期文人的共同之处。但鲁迅也在努力寻找一种新式的父亲,他们懂得“幼本主义”,懂得为孩子创造未来,让他们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能够获得“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权利。鲁迅希望自己就是这样的父亲,这在他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及《忽然想到》中有所提及,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多有表现,最典型的人物就是魏连殳。
魏连殳虽然没有父亲,却想象着自己做父亲的样子。用自己做父亲的方式,来否定父亲原有的做法。他虽然没有儿子,却把别人的儿子想象成自己的儿子,并给予父亲式的关心,把大良二良他们“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并认为孩子都是“天真”的,表现出新式父亲的样子。同时他也在为自己的父亲尽孝道,把领来的薪水寄给父亲的母亲,即祖母。
魏连殳承担着父亲的双重身份:一个是尽孝道的旧式父亲,一个是爱孩子的新式父亲。最后的结局是:一是他所爱的大良二良都变成“不良”,他也由爱护孩子变成了虐待孩子,这是新式父亲角色的破灭;二是他拒绝结婚,断绝香火,孤独死去,无人尽孝,这是旧式父亲责任的落空。
这里的魏连殳可以视为鲁迅的替代者,鲁迅把自己视为新式父亲,一方面以自己的行为来表达对于父亲的恨,另一方面把这种恨转移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承受。鲁迅在小说中让有可能成为新式父亲的人被动地面对绝望,主动地走向死亡。这是新式父亲的“自杀”式行为,通过把自己杀死,来完成“弑父”的目的。“审父”与“弑父”是孩子对父亲的“惩罚”。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关于惩罚这个潜意识需求的起源,我以为是无可怀疑的。它表现为良心的一部分……我们或者可称它为一种潜意识的罪恶感。”[6]“惩罚父亲”这在意识状态下是大逆不道的,会引发良心的不安,所以只能转入潜意识状态,并以曲折的方式释放出来。
(二)恋母情结
鲁迅在小说中无意识地发生了“弑父”行为,这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亦即“恋母情结”。这是男性在幼年时期天生的一种乱伦欲望,却在父亲的阻止下进入了潜意识。但这种情结并没有就此结束,却以更深刻更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蕾姆特的命运。所以说,弑父情结与恋母情结是一体的。
鲁迅原名周树人,父姓为周,却取笔名为“鲁迅”,因为“鲁”是母亲的姓,可见他对母亲的依恋。即使是母亲包办的婚姻,鲁迅也觉得“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7],虽然无奈,却也理解与遵从,这就是爱。
在鲁迅的小说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妇女形象,唯独对于寡母表现出了同情甚至爱。对于杨二嫂式的势利、柳妈式的恶毒、四婶式的封建、华大妈式的麻木、灰五婶式的守旧……鲁迅都是带着批判的态度来展现她们的丑陋。而对于一些“寡母”,鲁迅始终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她们充满同情,甚至肯定与赞颂。他的笔下,寡母在失去丈夫后并没有对孩子表现出抛弃的姿态,而依然爱着自己的孩子,如单四嫂子对于宝儿的爱,祥林嫂对于阿毛的念,夏四奶奶对于夏瑜的祭。她们都要承受生活的困苦、抚孤的艰难和节烈的辛酸,却依然爱着自己的孩子。这也是鲁迅母亲所要承受的辛酸命运以及她对于鲁迅的爱。对于母亲的命运,鲁迅以自己的方式去述说,在述说中表现了一种爱,即一个孤子对于寡母的爱。关于鲁迅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恋母情结”,本人在其他拙文中已有论述,此不赘述[8]。
总之,“父亲缺失”是鲁迅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包含着鲁迅对于父亲情感的矛盾。他没有父亲又需要父亲,他需要父亲最终又抛弃父亲;他爱父亲是因为自然的血缘关系,他恨父亲却是深沉的文化因素。然而,作为儿子的鲁迅,对于父亲的恨与反抗是不被社会原则与道德原则允许的,于是这种情感或愿望就被压抑至潜意识。然而鲁迅找到了小说创作的方式,让被压抑的愿望通过改装以另一种方式释放出来[9]。这就是精神释放。
精神释放不仅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精品,同时也拯救了鲁迅自己。正如精神分析学家阿恩海姆所说:“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入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10]而陷入情感矛盾的困境之中的鲁迅,他需要通过小说创作来修正对于父亲的“恨”,从而治好自己的“病”。
[1]张建生.鲁迅情感心理中的父亲情结[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94.
[2]林华瑜.放逐之子的复仇之剑[J].鲁迅研究月刊,2002,(8):51.
[3]赵蓉.一个人的复仇[G]//高校学术研究(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20.
[4]张梦阳.“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8):82.
[5]张重岗.中国新文学中的父子母题(上)——以鲁迅、曹禺等人作品为中心的分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87.
[6][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9.
[7]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60.
[8]吴铜虎.从“寡母形象”的塑造看鲁迅的创作心理[J].作家,2009,(3):4-6.
[9][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杨绍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86.
[10][美]阿恩海姆.艺术心理学新论[M].郭小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45.
〔责任编辑:曹金钟 孙 琦〕
I210.97
A
1000-8284(2015)06-0203-06
2015-02-04
浙江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鲁迅小说创作的精神分析解读”(FX2014180)
吴铜虎(1975-),男,浙江温州人,副教授,硕士,从事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