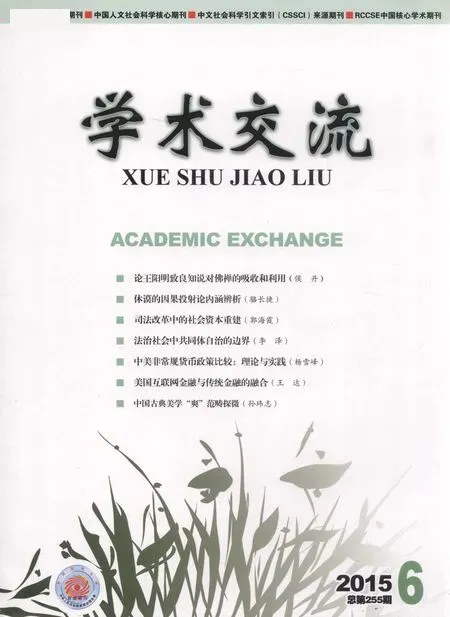美国社会自治传统探源
张 骏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社会学研究
美国社会自治传统探源
张 骏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治理经验,首先需要对其政治和文化传统有一个客观了解。作为美国自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自治是贯穿美国社会成长历程的基本特质和社会治理方式,也是所谓“美国式民主”的根本标志。探寻美国社会自治传统形成之源,可以为认识美国政治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一面镜子。美国的自治传统始于殖民时期的社会自治实践,而追根溯源,这一传统的源头在于早期殖民地开拓者从英国继承的文化基因与新大陆殖民地社会发展现实的碰撞和结合。它并非以英国文化传统为模板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不断壮大和扩张其实力的进程中,殖民地社会立足自治、发现和发展的一种创新和收获。正是坚持兼容并蓄、进取和创造丰富发展了自治传统,并促进了美利坚社会从英属殖民地到现代社会的快速跨越。
美国自治传统;英国传统;殖民时期
自治是美国社会发展的起点,对其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的生活方式。而殖民时期的自治直接源于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尤其是英格兰地方自治的传统习俗。在殖民时期的自治经验基础上,美利坚人将欧洲政治传统和美利坚社会相调适,创制了美国的自治制度。这一制度连同美国社会自我管理发展的实践经验以及制度背后的舆情、文化,共同构成了美国的自治传统。它集中反映了西方政治传统中的自治精神以及美国社会历史变迁赋予它的特质。从克服邦联时期的体制危机、制定联邦宪法到奠定美国未来发展的西进扩张,从早期农耕理想的追求到工业化时代的改革,美国社会的现代化始终立足于社会成员的自治。美国自治传统的源头在于殖民时期对英国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改造。本文从殖民地社会民情、政治、宗教三个方面来追溯美国自治传统的殖民地背景、英国基因及其社会影响。
一、自治:美国文化的标志
自治历来是人们考察美国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切入点。1966年,罗伊·尼科尔斯将自治定义为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与标志。他指出,美国社会的特征就在于:“它是致力于自治的民主文化,从法律上说,一切都同这种自治有关,而且,对于自治的兴趣显然是人民自我认同的关键。自治可以用作我国文化的标志。”[1]托马斯·帕特森则把美国政治精神概括为“自由、平等和自治的核心政治价值观”[2]。从林德夫妇到罗伯特·达尔,许多学者通过对城市治理的个案研究,探究美国式民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从精英、大众到多元主义民主的诸多解释[3]。1984年,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和罗伯特·L·比什从治理和公共服务视角,提出地方政府不但服务于地方公共经济和政治秩序,同时也是公民和自治社团参与地方乃至国家治理的工具。在联邦—州—地方政府间时时存在着谋求支配权和争取自治权的冲突。自治和支配之间既维持紧张关系,又谋求有序平衡的基础在于联邦主义和宪政原则。这种系统化的地方治理结构就是美国社会自治的具体特征[4]。1992年,罗伯特·威布考察了18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200年间美国民主演变的过程和动因,他提出,影响美国民主进程的是个体自决(individual determ ination)与集体自治(collective self-government)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自治的两层主要含义。19世纪的美国是体现社会自治精神的“黄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两个方面的分离则造成了美国民主的衰落,而激发美国民主活力的途径在于恢复个体自决与集体自治之间的平衡[5]。
20世纪末,中国学者开始以译介和评述的方式关注美国的地方治理和公共管理。进入21世纪,中国研究者开始从美国地方自治的源头、城市自治体制个案分析、公民权的构建和作用等问题着手,探究美国社会治理的逻辑,反思美国工业化变革中的经验教训。其中,多数聚焦外部研究,止于功能性或工具性探讨,少有把外部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探索,深入美国式道路的核心及其发展源泉[6]。盲目推崇、机械复制或满足于学理的评述既不利于美国研究学科的发展,也无助于客观认识和理解美国崛起中的经验教训,实现“洋为中用”。从农业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美国的经济、政治危机不断挑战传统,但立足传统而不迷信传统,强调务实、调适和创造是其得以摆脱困境实现自我治理的关键。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原则早在殖民时期就已奠定成型。正是在融合文化传统与现实要求、推进制度创新、克服体制弊端的意义上,自治可以成为美国文化的标志。
二、殖民地自治的英国基因
从欧洲文明的演进来看,争取自治、追求自由的历史就是国王和君主的权力不断被削弱、限制乃至剥夺,而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或大多数人的权力不断增长、发展并逐步推动社会治理和进步的历史。这种自治力量的成长在英国首先从限制王权开始。从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到四个多世纪后的英国革命,再到19世纪的议会改革和20世纪初的《国民参政法》,制衡国王的力量从贵族延伸到工商资产阶级,再到民选议会这个唯一立法机关。1688年之后,英国官方发布了《权利法案》《兵变法》《宗教宽容法》《三年法》《叛国法》《王位继承法》等法律,进一步以法治的形式限制王权的无限性,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英国被恩格斯誉为“地球上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而“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天生的独立自主的权利”[7]678-679。北美殖民地和后来美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正是得益于英国的民情、政治和宗教的文化基因。
(一)民情基因
17世纪到达北美的移民几乎完全来自英格兰,非英格兰移民不到人口总数的1/10,而18世纪到达这里的移民则大部分并非是英国人。正是英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自治奠定了基础。早期殖民地开拓者的“思想、信仰与社会习惯都是英国化的”[8]551。他们不仅把英国传统发扬光大,而且最终促使北美殖民地走上不同于南美、新西兰和澳洲的自治之路。回顾美国自治历程的开端,追求自由是殖民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殖民地社会自治发展的基础。
1729年,造访英格兰的孟德斯鸠指出,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地方相异之处在于英格兰是一国“自由的人民”,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格外有利于个人的自由[9]307-314。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位法国人托克维尔指出:这种差异是由于“这个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没有屏障,惟有自由的流动性”[10]217。相对于旧世界的种种阻碍,自由精神在北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励,并成为反对权威和专制,争取自治和创造的基础。
自由和平等是北美新生活的起点。但自由与秩序常常发生冲突,而保障自由有赖于法治。在新英格兰总督任上几起几落、仕途跌宕的温思罗普就曾被指控犯有专横罪。但是,在为自己辩护的公开演讲中,从殖民地的现实出发,他为自由作了明确的定义:“堕落的自由,……本质就是为所欲为”。它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而公民或道德的自由是神圣的。它支持一切善良和公正,它的力量在于联合。“政权本身的使命就在于保护这种自由”[11]47。珍视自由的初衷引导人们热爱秩序和法律。英国长期的司法实践发展了“普通法”和法治观念,这不仅被各个殖民地吸收借鉴用于殖民地自治,也成为他们对抗英国专制争取和扩大自身自由权的武器。
个人主义无疑是英格兰社会结构的基本表征,因为在英格兰,“与团体和国家相比较,个人享有更大的权利和特权”。而“当英格兰人走下跳板,踏上(这片)福地之时,他们并没有抛弃故国的传统社会结构”。《独立宣言》中所表述的关于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共识正是“发祥于13世纪、甚至更早期英格兰的个人观与社会观”[10]263。而英国的殖民地“一向比其它国家的殖民地享有更多的内政自由和政治独立”,且“这项自由的原则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新英格兰各州得到更为完整的实施”[11]40。新世界的自由精神首先体现在身份的平等,其次是打破身份、等级观念后新世界社会生活的流动性。自由精神不仅拓展了殖民地社会生活的空间,而且为完善自治能力、促进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因
首先,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北美迅速立足并发展的思想基础在于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事实上,英国自治的习惯在中古时代就已形成。早在诺曼征服之后,英国国王便通过颁发特许状的形式赋予城市以自治权。12世纪早期,伦敦市的市民便根据特许状获得了选举村镇长官、行政司法长官的权利。郡、市镇和教区都享有一定的自我管理本地公共事务,不受外部干预的权力。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后形成了新的地方行政司法系统。从郡督、郡长、治安法官到教区职员,既无薪金,亦非专职官僚,绝大多数为本地乡绅。一没有中央政权提供系统的行政法规以供遵循,二没有经济供给和行政司法训练的情况,给与他们履行行政司法职责时相当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自由性,使自给和自治的传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12]85-86。17世纪,移居北美的英国移民则将这一传统带到了新大陆。乡镇是殖民地生活的基础和开端,乡镇精神和统治殖民地社会的政治原则都源自英国乡村的地方自治传统。这是因为在陌生、荒蛮的北美大陆,移民们首先能够依靠的是来自母国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习惯。
虽然各殖民地的组织结构存有一定差异,但殖民地地方自治政府的共同特征是:当地居民享有选举本地官员的权利;许多居民经公开推举,担任没有薪俸的地方公职;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较为公开;相比殖民地整体的政治问题,居民更为关注地方事务[13]306,311。基层的村镇、县级机构成为实施“地方自治,自我管理的实践基地”[14]81,在立法和行政等方面,为殖民地的普通人和地方官员提供了训练和实践的机会。北美新大陆的生活无疑是一种更为丰富、并被赋予新世界特质的自治生活。
其次,殖民地从自治走向独立的组织基础在于英国的议会制度。如果说英格兰村镇地方自治的习惯为北美移民立足新大陆奠定了基础,议会制度则进一步赋予了殖民地维护政治权利的主体意识和制度保障。
13世纪下半叶,英国有了“议会”这个名称,初步建立议会制度。到17世纪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英国的议会制度经历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英国议会的理论和实践无疑首先成为殖民地人模仿和改造的对象。1619年,弗吉尼亚公司选派新总督,在殖民地召集了弗吉尼亚第一次居民代表大会。尽管对这次会议召开缘由存有争议,但殖民地居民代表权的行使无疑标志着代议制原则首次应用到殖民地政府组织。这次会议也成为殖民地议会的始祖。随后,代议制度被北美其他殖民地纷纷效仿,并在日后与母国的关系中发展成为“殖民地利益的主要代言人”[15]27。1620年,以一批清教徒为主的移民,在北美靠港抵达前,共同签字约定“自愿结为公民自治团体”[16]13。作为北美英裔移民中首个自愿达成的社区自治协议,“五月花号公约”与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并列,被称为“美国制度的两大奠基石”[17]52。
事实上,英属北美各殖民地虽然在政治上彼此独立,结构上都以母国为样板。例如,总督和国王对应,参事会和议会上院以及枢密院对应,民选议会和议会下院对应。但北美殖民地议会制度并非英国议会制度的简单拷贝,而是经历了发展和演变,成为独具北美特色的议会制度。如殖民地议会下院的权力从18世纪上半叶起不断扩张,包括对本地财政事务控制权、议会选举的选民资格确认权、税收官员提名任命权,等等。同时,议会下院机制也日益完善,形成委员会制度,在行政和管理上趋向专业化、职业化,从而为造就本地政治精英、强化自治能力和自信提供了舞台[13]312-313,318-319。
(三)宗教基因
殖民地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清教徒的宗教理想——共建人世间的“上帝之城”,按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他们求助圣约思想,取消主教制,重新确立上帝与人、人与人、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强调教众在上帝面前彼此平等、实行教会自治的同时,他们将这一原则运用于殖民地政治关系中,在新英格兰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权力实体——清教神权。作为清教徒政治和道德原则的核心,圣约思想是教会自治和殖民地自治的思想基础,贯穿了殖民地社会自治的实践,并对美国宪政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清教神权建立在“恩典之约”(The Covenant of Grace)、“教会之约”(The Church Covenant)和“公民之约”(The Civil Covenant)三约之上[18]10-11。作为加尔文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清教徒圣约思想中的“约”是确定上帝与人、人与人关系的根本,其中教会之约和公民之约都服务于恩典之约这一根本目的。教会提供了圣徒聚集、牧师宣讲上帝意旨和信仰上帝的场所,负责教众的内在思想;世俗政府则执行教会宣讲的上帝意旨,负责教众的外在行为,为配合教会共同侍奉上帝提供组织保障。在新英格兰,圣约观念对于教会和政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在思想和形式上都起着支配作用。团结教众的并非统一的管理机构或高高在上的主教,而是共同的目标和生活方式。教会自治主义的核心是:适应北美的环境,并由基督徒们不断保持一致意见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真正的基督教会。人与人的现实关系高于神赐或世袭的地位。行动纲领和行为方式高于各种教条和形式[19]18-20。而这一思想给予美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新英格兰范围和殖民时期[17]54-55。
其次,圣约思想贯穿在殖民时期的政治关系中。形式上,教会和政府各自为政,牧师不得直接参与政治,教会无权干预或剥夺居民权利,政府也无权干涉教会事务。但“世俗政府同样是以上帝的律法为律法,以上帝的名义治理人”[18]34。只有教会成员才享有投票权,才能担任政府职务。地方行政官员和牧师都服务于上帝,相互支持,彼此约束。
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组建自治教会的同时,一个个世俗圣约的签署则确立了新英格兰世俗社会的政治关系,缔造了新英格兰自治村镇和殖民地自治政府。以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为开端,这一“圣约模式”扩展到新英格兰每个乡镇和北美其他殖民地,如1638年朴次茅斯的“神圣协约”、1639年的康涅狄格基本法、1647年普罗维登斯宪章以及1707年宾夕法尼亚基本权利宪章。此后,一个接一个的拓荒地上立下的几十个“约”都成为一个又一个自治乡镇和殖民地自治政府的开端[20]。立约和守约既是每个信徒的信仰方式,也成为全体民众组建世俗政府并维护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政治传统。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梅里亚姆所说,“这种圣约理论必须强调个人作为单位在教会和殖民地政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因为教会和国家的基础是自愿的同意而并非神权或习俗。”[21]15作为清教徒政治道德思想的核心,圣约思想中包含的独立自主、个人主义和限权要求,通过乡镇自治和殖民地自治将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结合起来,将个人与共同体紧密联系起来。殖民地的自由精神得到激发,个人权利和殖民地权利得到鼓励[21]18。在殖民地脱离宗教实验和商业投机阶段,走向繁荣自治的全部过程中,乃至独立建国后美国社会成长的各个阶段,“约”的传统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和思想动力。
三、殖民时期的自治
英属北美殖民地是以英王的授权为前提而存在,但到1776年殖民地宣告独立之前,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各自发展了适应其各自环境的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殖民地最终摆脱了从属性走向独立建国的关键,在于它借鉴了英国文化传统但又进行超越教条的自治和创新。
(一)殖民地独立的经济、文化
独立自由的经济文化生活是殖民地社会有别于旧世界的一大特点。首先,土地是殖民时期北美的最大资源,大约90%的人口主要依靠农业生产为生,但主要集中在南部。自然环境的差异没有阻碍经济的自主发展,反而促成了新英格兰、中部殖民地和南部殖民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次,殖民地人拥有以英国文化为主的欧洲文化习俗,但相似的梦想和殖民地艰苦环境让他们在相互影响和融合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倡导自立、兼容、平等的文化教育和思想启蒙伴随着殖民地建设的每个阶段,如各殖民地从很早就确立了实际上的出版自由权。18世纪末,美国人口仅占英国的一半,但每年发行的报纸大约比英国要多出2/3。报纸成为美国“打破一切界限的象征”[19]375。独立革命之前,殖民地社会的等级概念来自旧世界,但新世界的开放和变动性不断腐蚀并解构贵族特权和等级意识。在一视同仁的荒蛮与艰辛面前,旧世界文化中的偏见、狭隘和尊卑观必须让位于自由与平等、“异想天开”的创造和“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们坚信差别只是暂时的,只待自己抓住机会努力改变。因为在北美的广阔天地,地位、家庭出身和经济起始状况不可能永远固定或界定一个人的价值。约翰·亚当斯来自自耕农家庭,本杰明·富兰克林由印刷作坊的学徒步入社会。但是在独立革命时期,他们已然凭借自身努力不仅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而且成为贵族出身的乔治·华盛顿的战友。总体而言,旧世界产生的地位等级、行业界限在这里最终是模糊不清、不确定的,开放无羁的空间成为殖民地的象征。只要愿意响应现实需要,人人都可以进入原来视为专门的行业成为专家。无论贫富之别、职业之别,殖民地社会变动不居的环境和要求都可能使之改头换面。最后,宗教生活的多样性和自由化尤其代表了殖民地的文化特性。所谓异端总能够在荒野中开辟一片自己的家园。人们相信:“一切谬误,只要人人可以自由反驳,就不再是危险。”[16]126对殖民时期的移民来说,北美提供了实现宗教理想或“按设想创建社会”[19]37的机会。直到17世纪中叶,英国历来给予殖民地在经济、宗教等方面相当大的自由。
(二)殖民地独立的政治生活
从英王授权下的自我治理开始,到摆脱英国控制和干预的决裂,在150年的变迁中,殖民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超越政治自治的独立性和扩张性。殖民地自治实践中的一切借鉴、创新或背叛只有一个目的:维护殖民地自身的权利和发展。
首先,对比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发展,北美殖民地的成功归功于它的自主地位。在美洲大陆的殖民竞争中,英国是个迟到者,但后来居上,成为最终在北美土地上的开拓立国者。在自然条件和母国后援条件等方面,英属北美殖民地较之西属南美殖民地并无优势,但“殖民的方式对北美和南美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2]13。
从政治体制看,西班牙在南美建立了与本国相同的政府机构,直接管理殖民地,而英国则实行不同类型的自治政府。这样,南美殖民地实际成为西班牙帝国统治的延伸。特定的政治体制必然塑造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权利观念。西属南美殖民地照搬欧洲本土的社会体制,白人与印地安人、黑人通婚形成一种混杂的文化,殖民者和本地人界限严格,等级观念突出。从法律地位看,北美殖民地居民和英国本土居民法律上权利平等,享有英国国民的所有特权及豁免权,并可自由返回本土。而且在殖民地居民中,不但英国移民及其后裔、非英国移民及其后裔经过相关入籍程序,同样无差别地享有英国人的自由和特权。这与西属美洲殖民地划分来自西班牙的“半岛人”、“土生白人”和本地人的社会等级制形成鲜明对照。相对于北美殖民地特许状保障下的自治社会,南美殖民地则属于被西班牙人征服和奴役的社会。因此,南美殖民地社会权利和管理结构上是自上而下的统治或专制,要求的是顺民而绝非公民。北美殖民地自治则培养了人民普遍的乡镇精神以及对权利、义务和秩序的明确认识。它要求人们成为公民,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与自己参与其中的乡镇社区息息相关。
其次,殖民地地方行政管理的实际权力日趋独立。就权力结构看,尽管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各殖民地通过代议制议会,普遍享有相当的自治权。殖民地政府组织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总督和议会。如果说领主或总督代表王室,议会则代表殖民地人民,双方“权力平分秋色”[21]16。议会由于把握财权,不仅成为具有制约力的一方,甚至常常主导殖民地与英国的对抗。就法治建设看,殖民地人既是欧洲尤其是英国法治观念和制度的继承者,也是改革者、创造者。殖民地“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普通法,并加以改造来适应本地情况”[22]251,即“创造性地运用英国的法制传统和法律资源”[13]267。尽管理论上从属于英国,殖民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始终是殖民地自治实践的出发点。包括约翰·温斯罗普、约翰·科顿在内,殖民地人坚称:“英格兰的法律不适用殖民地”。“根据特许状,只有总督、副总督、助理和殖民地选出的代表或代理人,拥有立法和行政的所有权力和权威,来管理这里的全体人民”[16]34。独立自主、抗拒母国权威的做法甚至成为1684年马萨诸塞被撤销特许状的主要原因。
就个人权利看,根据皇家特许状,殖民地居民不仅享有英国人的权利,而且始终享有殖民地人专有的自治权。“普通民众拥有比英国人更广泛的参政机会和权利”[13]293。虽然沿袭了17和18世纪财产与政治资格相联系的惯例,各地享有选举权资格的财产要求不一,约50%—75%的殖民地白人男性拥有表决权。相对于当时英国90%的国民没有选举权而言,殖民地的政治权力已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此外,殖民地居民可以通过请愿表达民意并影响政府决策[23]74。不可否认,由于财产资格的要求,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只有经济成功的社会精英。但在处理殖民地与英国关系上,维护和扩张殖民地权益始终是殖民地自治的第一要务。
四、结语
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呈现的文明形态是英吉利文明的延续”或“变种”,“美利坚文明的根基不在美国,而在英国”[24]275。的确,美国社会的自治始于殖民时期英王的授权。但正是英王批准的殖民地宪章先后演变为殖民地自治宪章,并成为殖民地人谋求更大范围自治,乃至摆脱从属地位,维护自身权利的起点和最佳理由。尊重法律与秩序,思想独立,热衷公共事务,富于自治精神的社会舆情,加之在北美移植并实行的英国式自治政府共同构成了早期殖民地的社会现实。在殖民时期的总体思想和情感中已经包含了影响并决定美国社会独立自治的萌芽。它固然源于英国的政治文化基因,如对自由和自立的信仰、法治精神、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精神。但与其说美利坚文明只是英吉利文明的“延续”,“无本质变异”[24]275,不如说,英国基因在殖民地开拓者的创造性实践中经过改造调适,最终孕育了美利坚的果实。美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就源于殖民时期开始的多样化的自治实践和根据自身发展对旧世界传统的改造。就殖民时期来看,领先英国近一个世纪的西属美洲殖民地,笼罩在中世纪的色彩和欧洲的典章制度中。而英属北美殖民地不但保存了“历史赋予的遗产”[17]35,而且将英国传统与美洲殖民地社会现实相结合,开辟了一条“美式道路”。面对时代变革的要求,离开传统和借鉴的发展无疑是无源之水,而脱离现实缺乏批判、鉴别地继承和“拿来”必然只是盲目教条。诚然,美国自治传统是殖民地特定历史、社会和自然条件的产物,在信奉新教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拓殖扩张中得以形成。但它不是对英国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批判性地借鉴,是立足殖民地社会现实的一种创新和收获。正是这种兼容并蓄、进取创造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自治传统,并提升了美国社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型中的自我治理能力。
[1]Roy FNichols.History in a Self-Governing Culture[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7,72(2).
[2][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M].顾肃,吕建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3]Robert S Lynd,Helen M Lynd.Middletown:A Stud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M].New York:Harcourt,Brace,and Com pany,1929;Middletown in Transition: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M].New York:Harcourt,Brace,and Company,1937;Floyd Hunter,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M].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3;Top Leadership[M].U.S.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9;Robert Dahl.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1961.
[4][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罗伯特·L·比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美国地方政府[M].井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Robert H.W iebe.Self-rule,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6]苏鹏飞.从伯克利市宪章看美国地方自治制度[J].美国研究,1999,(3);苑治国.美国地方自治形成溯源[J].文教资料,2006,(28);孙英翔.论美国的地方自治[D].济南:山东大学,2008;鲁彬.美国地方政府与地方自治问题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1;赵梅.美国公民社会的构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8][英]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M].张慰慈,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卷)[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0][英]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M].管可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2]郭方.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3]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Charles A Beard,Mary Beard.A Bas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Doubleday,Doran&Company,1944.
[15]满运龙.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探微[M]//齐文颖.美国史探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6]Henry Steel Commager,etal.Documents of American H istory[M].New York:Meredith Corporation,1973.
[17]Samuel Eliot Morison,Henry Steele Commager,W 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Vol.One[M].Sixth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18]钱满素.钱满素文化选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9][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20]Daniel J Elazar.The Covenant Tradition in Politics[EB/OL].(2011-05-12).http://www.jcpa.org/dje/books/ct-vol3-ch1.htm.
[21][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2]钱满素.美国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3]Michael G Kammen.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America:Democracy or Deference[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 inston,1967.
[24]蔡永良,何绍斌.美利坚文明[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责任编辑:常延廷 黄 琦〕
C712.93
A
1000-8284(2015)06-0180-06
2015-01-23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外语教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研究”(15ZS047)
张骏(1965-),男,江苏苏州人,讲师,博士,从事美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