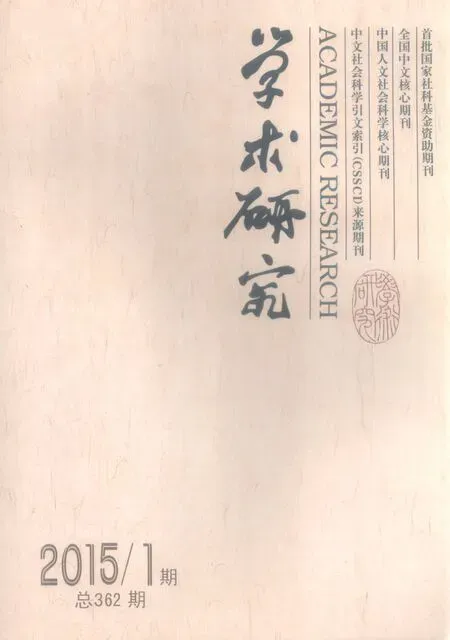严粲《诗缉》“兴之不兼比者”辨*
孙立
严粲《诗缉》“兴之不兼比者”辨*
孙立
在 《诗经》学史上,南宋严粲对 “兴”与 “比”的关系持折衷态度,既不固守毛诗一派 “兴皆兼比”的意见,也不完全接受朱熹 “兴”与 “比”没有关联的论断,他认为毛诗所标识的 “兴”诗大多与“比”有关,但也有7首没有关系。笔者经过逐首辨析后认为,严粲所认定的 “兴之不兼比者”7个案例仅有3例合乎实际,4例有误。这从侧面印证了毛诗学者所论述116首 “兴诗”含有 “比”义的结论基本准确。
严粲 诗缉 兴之不兼比
过往人们对比兴的研究,多集中在毛传、孔疏、朱注上面,对宋代严粲的 《诗缉》多未注意;今人对 “兴”与 “比”的认识,基本上采纳了朱熹的意见,否定毛诗,认为 “兴”与 “比”没有关系。
然则,赋比兴之说起自 《周礼》,成于毛诗。研究比兴,不能完全抛开毛诗一派意见。事实上,战国以迄唐代,兴之兼比是 《诗经》学者的共论。拆分兴、比,虽不始于朱熹,但成于朱熹。对这一做法,《诗经》学者并非没有异议,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南宋末的严粲。其所著 《诗缉》,在入宋以来废《序》的思潮中,体现了折衷的倾向,既坚持兴多兼比,又提出兴也有不兼比,于今仍不无参考意义。
一、严粲 《诗缉》及其论 “兴”
《诗缉》是宋代为数不多的 《诗经》较好注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与吕祖谦的 《吕氏家塾读诗记》在宋代说 《诗》之家 “并称善本。”吕著有集注性质,所集材料远远超过朱熹 《诗集传》,但缺点是较为碎乱,有兼综而少己断。严著 《诗缉》也缉前人 《诗》说,但大多附在己说之后做参证,不象吕著仅排列诸家之说。严著还长于释义,与前此 《诗经》注本较多注意字词训释不同,《诗缉》在疏通诗义方面着力较多,这不仅在宋代 《诗》说中独树一帜,在历代 《诗》注中也不多见。严著的这一特点大约与此书缉成的目的在于教授家中童蒙有关。严氏原序云:“二儿初为 《周南》、《召南》,受东莱义,诵之,不能习。余为缉诸家说,句析其训,章括其旨,使之了然易见。既而友朋训其子若弟者,竞传写之,困于笔札,胥命锓之木,此书便童习耳。”虽说此书,非高头讲章,但作者遵循孟子 “以意逆志”说,由字及词,由词及句,由句及章,由章及篇,串解 《诗》义,殊觉浑融。
严粲论 《诗》的倾向,上接吕著,以存 《序》为主要特征。但在欧阳修以来疑古风气影响下,他对毛、郑并未全盘接受,甚至持怀疑及改造态度。在 “兴”问题上表现出折中倾向。 《诗缉条例》云:
凡言兴也者皆兼比,兴之不兼比者特表之。 《诗纪》曰:风之义易见,惟兴与比相近而难辨。兴多兼比,比不兼兴。意有余者兴也,直比之者比也。兴之兼比者徒以为比则失其意味矣,兴之不兼比者误以为比则失之穿凿矣。毛氏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①《诗缉》卷1,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所引用 《诗缉》,均出自此本,不另注。
他认为 “兴也者皆兼比”、“兴多兼比”,而且同南朝钟嵘论 “兴”曰 “文已尽而意有余”一样,认为 “意有余者兴也”;另一方面也受了朱熹一些影响,指出 《诗经》有 “兴之不兼比者”。他认为毛诗特别标识 “兴”,是因为 “兴”虽 “皆兼比”,但 “比”的意思隐晦些,所以要特别标识。严粲这段话坚守了汉唐以来有关 “兴皆兼比”的主张。 《樛木》小序说:“《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笺云:“兴者喻后妃能以下意逮妾”,将小序与诗的兴义相联,指出 “兴”所隐含的比义。虽说笺义不一定合乎原诗之意,但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兴”所写物象并非孤立的单句,它与下文内容多有意义比拟关系。刘勰 《文心雕龙·比兴》云:“毛公独标兴体,岂不以比显而兴隐哉?”刘氏为何说 “兴隐”呢?是因为兴的手法不易觉察,还是 “兴”含有秘而不宣的意义呢? “兴者,起也。”读者对兴句引领下文的程序并不难发现,所难发现者在于兴句与下文意义上的比拟关系。故揭示兴体,意在提醒读者,此体既为兴,引领下文以起,也含有隐秘的比义。故 《诗》所谓 “兴”者均含比义。
这一说法,除郑玄、刘勰外,唐孔颖达于 《毛诗正义》也披露之,他说:“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1]并在多处强调 “兴必以类”、“兴必取象”、“兴必以喻”诸义例,说明兴多兼比的特征。此外,陆氏 《经典释文》说:“兴是譬喻之名,意有不尽故题曰兴。”[2]即便到了宋代,认为兴与比有关联的仍不乏其人。吕氏 《家塾读诗记》引王安石语曰:“王氏 (临川王氏)曰:以其所感发而况之之谓兴,兴兼比与赋者也。”[3]均将兴和比联系在一起。
《诗缉》在处理 “兴”诗时也基本承续了汉唐以来的主流意见,凡标 “兴”处,均指 “兴而比者”。而且有些毛传未标 “兴”的地方严氏也标为 “兴也”,所以 《诗缉》在 “兴”诗的总数上超过了毛传。严粲 “兴多兼比”的意见是符合 《诗经》兴诗基本情况的,毛传所标116首兴诗,只有极少数是兴不兼比的,大多为兴中有比的兴诗。 《诗缉》中特意标出 “兴而不兼比者”的诗仅 《葛覃》、《卷耳》、《殷其靁》、《旄丘》、《东门之杨》、《杕杜》、《大东》、《鸳鸯》等8首而已,恰可印证他前面所说的“兴多兼比”一语。那么,严粲为何又特别指出 “兴之不兼比者”呢?这8首被严粲视为 “兴不兼比”的诗有无可商榷处?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由于 《殷其靁》一诗毛传不以其为 “兴”诗,暂不予讨论。
二、 “兴之不兼比者”的正确判例
在 《诗经》学史上,唐以前毛诗一派往往既依托文本,又脱离文本,意在寻绎文本之外的微言大义,其渊源来自于春秋断章赋诗的传统及孔门诗教。宋以来非议毛诗的朱熹一派,则力图恢复 《诗经》文本原义,他们从文本出发,意在阐释诗句的本义。前者基本上是经学立场,后者是文学立场,观点自然不同,这是唐前与宋后对 “比兴”有不同认识的原因。今天的 《诗经》研究者应该如宋人那样立足于文本,但在解释 “兴”义时,也应该参酌汉人说法。因为提出 “兴诗”的概念,并认为 “兴”与 “比”有关系的是毛诗,其目的是发掘诗句文字以外的意义,起到某种教育功用。这是经学的做法,也是《诗》能成为经的基础。我们研究 “兴诗”不能离开这一基础,因为所谓 “兴”,是汉人在继承孔门诗教基础上总结的阅读 《诗经》的方法,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作诗方法。但如果离开经学范围,客观地就诗论诗,仅从文学创作角度去研究 《诗经》,那么,毛诗所揭櫫的116首 “兴诗”中,确实有少数 “兴诗”与 “比”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研究 “兴诗”,是彻底抛开提出者进行新阐释呢?还是应该坚守其基本理论内涵,再略加修订呢?我的答案是后者。严粲 《诗缉》所持的也基本上是这样的立场。不过,严
粲虽不像朱熹那样非毛,但多少受了时风影响。他在 《诗缉》中列出 “兴而不兼比者”7例,说明他在研判 “兴”与 “比”的关系上也吸收了朱熹的部分意见。那么,这7例 “兴而不兼比者”的认定是否合理呢?
先看 《陈风·东门之杨》。首章:“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序》云:“刺时也。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 《序》标 “兴也”,认为由树叶之盛 (春夏之日)而兴婚姻失时 (秋冬为婚嫁之日);由亲迎不至兴男女多违。依毛序之义,显然兴而兼比。朱氏 《集传》云此诗 “兴也”,“男女期会而有负约不至者,故因其所见以起兴也。”但并未附会毛序 “昏姻失时”、“男女相违”等 “刺时”之说。严氏 《诗缉》云:“兴之不兼比者也。秋冬为昏姻之时,今东门之杨,其叶牂牂然盛,则春莫而昏姻失时矣。亲迎以昏为期,而至明星煌煌然大明,夜已深而竟不至,淫风行而女有他志也。”严氏此解与毛序并无明显区别,但严氏却说是 “兴之不兼比者也”,令人费解。
按,此诗确难看出 “刺时”意味,首章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及末章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与下句也无直接比拟作用,首句之兴只起以景起情的作用。故就诗论诗,此诗诚如严氏所说,属 “兴而不兼比者也”, 与 《秦风·蒹葭》、《郑风·野有蔓草》的兴例相仿,系以景托兴,引领下句。严氏之失,在于一方面说 “兴而不兼比者”,一方面又将 “昏姻失时”,“男女多违”扯进诗意,造成前后矛盾。
相较于 《东门之杨》的以景托兴,《周南·卷耳》则是以事托兴。诗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严氏注云:“兴之不兼比者也。此言使臣在途,归必劳之。后妃主酒浆之事,豫采卷耳以为曲蘖,故因见采卷耳者而念使臣之劳。谓卷耳易得之草,顷筐易盈之器,今采卷耳者非难且劳之事也,采之又采尚不盈顷筐,嗟乎我矜念使臣,今在道路,其跋涉之劳当如何耶?”朱熹 《诗集传》更云:“赋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耳。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4]以为后妃托言采卷耳,故为赋不为兴。但朱注自相矛盾,所谓托言者,乃借采摘以兴发下文,故标为赋并不合理。所以此诗严氏以为属 “兴”是对的。说后妃采摘,甚或如朱熹所言系文王太姒采摘更属无稽。采摘卷耳也非实采于 “周行”官道之旁,卷耳生于荒野,所谓“采采”云尔,实乃假想之事,作者是以事托兴,这是合理的解释。分歧的关键在于这首诗的 “兴”是否兼比。毛序郑笺孔疏均以为兴而兼比,认为作者是借采卷耳不盈顷筐,比喻心事很重 (忧在进贤),以兴后妃志在辅佐君子、忧劳进贤之义。其中采卷耳,思故人,忧心不已是篇中本义,而所谓后妃之志在辅佐君子云云则由此及彼,这种解释有无问题呢?观毛诗一派解诗,所谓 “兴”者,有作者 “赋诗之兴”,也有释诗者 “用诗之兴”。就此诗而言,毛派所说,实为 “用诗之兴”,即无论毛序,还是郑孔的笺疏,引出的所谓 “兴义”均非文本所有,而是他们从诗中联想生发出来的。
再看 《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毛传标“兴也”,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瀚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观毛传,诗的主人公亦为后妃,诗中所述为后妃在娘家之事。首章兴也,但兴义为何则没有明言。笺云:“此因葛之性以兴焉。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又云:“葛延蔓之时则抟黍 (按指黄鸟,一名抟黍)飞鸣,亦因以兴焉。飞集丛木,兴女有嫁于君之道。和声之远闻,兴女有才美之称,达于远方。”郑氏笺补足毛传,略有修正,一则指出诗中主人公仅为妇人,未如毛传所说为后妃。二则将首章分为两解,首两句喻妇人在母家长成;后四句喻妇人有嫁于君之道,才美达于远方。清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也主张此诗兴而兼比,“诗以葛之生此而延彼,兴女之自母家而适夫家”。约而言之,毛诗一派对所兴内容解释虽有不同,但均认为是兴而有比的。而朱熹 《诗集传》注云:赋也,“盖后妃既成絺绤而赋其事,追叙初夏之时,葛叶方盛,而有黄鸟鸣于其上也。”故为叙实的赋法。严粲 《诗缉》虽认为此诗为 “兴”,但其于首章下云:“兴而不兼比者也。述后妃之意,若曰:葛生覃延而施移于谷中,其叶萋萋然茂盛,当是之时,有黄鸟飞集于丛生之木,闻其鸣声之和喈喈然,我女工之事将兴矣。黄鸟飞鸣乃春葛初生之
时,未可刈也,而已动女工之思,见念念不忘也。先时感事乃豳民艰难之俗,今以后妃之贵而志念如此,岂复有一毫贵骄之习邪?味诗人言外之意,可以见文王齐家之道矣”。观严氏所述,其一,将诗的主人公定为文王后妃太姒;其二,认为诗中所述乃后妃出嫁后之事;其三,言后妃见黄鸟飞鸣而动女工之思。而 “先时感事”,乃豳民艰难之俗,以贵妃之尊犹志念如此,可味文王齐家之道。
上述诸家之说可概括为三派,一为毛诗派,主兴而有比。二为朱熹,判以为赋。三为严粲,主兴而不兼比。今人多以为此诗与后妃没有关系,信然。值得研判的其实只有两点,其一,此诗是否为兴,其二,如果是兴,是否兼比。首章写景,意象有二,一为葛覃绵延生长,二为黄鸟鸣于灌木。单就此章而言,难以判断其是否为兴,也难断其是否兴而有比。为便于考察,迻录其后两章: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 是刈是劐,为絺为绤,服之无斁。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 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第二章开篇仍以葛覃为对象,与首章不同的是,顺而叙写收割、织布之事。至于由葛之延蔓,到刈劐,再到 “为絺为绤”,是实写。全诗应该是女工将要归宁父母,由洗衣想到织布,由织布想到织布材料葛藤,由葛藤想到其生长形态,想到葛藤中翻飞鸣叫的黄鸟,又因黄鸟鸣叫引起归思。诗章顺序写来,诗思却逆向索得,顺逆相绾,浑然一体。诗之首章当为后世诗家所言 “索物以起兴”之例。毛郑严诸家均以此诗为兴,当无疑义。毛诗一派主张兴而有比,是因为他们攀附于后妃,无论阐释的细节有何不同,均以为此诗中的后妃刈劐絺绤,表现出 “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的美好本性。故葛覃之兴,由此及彼,寓含比义。而严粲以为 “兴不兼比”,认为此诗文本并无这样的比喻,当然他也同意诗中写了后妃见黄鸟飞鸣而动女工之思,所以断以为兴,但后文所谓 “先时感事”,以贵妃之尊犹志念如此,可味文王齐家之道诸语,是读诗人 “味诗人言外之意”。由 《葛覃》之诗核之,严粲所说,洵为有理。
综上三例,我们发现,这些兴例,兴句与下句都是讲同一件事情或与事情有关联的场景,兴句只起到引起或衬托的作用,前后句没有意义上的比喻关系。
三、 “兴之不兼比者”的错误判例
观严氏所列 “兴之不兼比者”7例,除上述三例较合诗义外,余者4例尚有可辨析者。
先看 《邶风·旄丘》:“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严氏注云 “兴之不兼比者也”。按此诗毛传以为黎人责卫伯,以卫伯不能救黎侯也。 《诗缉》亦采此说,并谓:“黎臣子初至卫见旄丘之上有初生葛,其节甚密,及其后也,葛长而节阔,故叹云:何其节之阔也?感寄寓之久也。尊称卫臣而问之曰: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见救也。君臣一体,不斥其君而责其臣,婉辞也。”鲁诗及齐诗则以为是妇不见答于夫之词。[5]两者所指人物不一,然而所怨者虽不同,但均抱怨时日之久。所以,无论黎人还是妇人,均假写其登于旄丘之上,因见葛叶蔓延节阔,而悟时移日易,遂生怨义。故前句之葛叶蔓生 “何诞之节”与后句之 “何多日也”既有前后相启之关系,又有比附生义之关系,朱氏集传同《诗缉》,采毛传之说,以为此诗是 “黎之臣子自言久寓于卫,时物变矣,故登旄丘之上,见其葛长大而节疏阔,因托以起兴曰:旄丘之葛,何其节之阔也;卫之诸臣,何其多日而不见救也。”由朱氏集传所言,亦可见葛长大与时日久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能说是兴之不兼比者,因前后二者实有一层比喻关系。
再看 《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此诗毛诗标为 “兴也”。小序以为:“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焉。”据郑笺孔疏,意谓古代明王能善待万物,顺其性而取之于时,故鸳鸯待其能飞始捕之。严氏 《诗缉》采毛诗之说,以为 “兴之不兼比者也。先王之时,入泽设罻皆有时,杀胎覆巢皆有禁,合围掩群皆所不为,故其民渐被仁政,皆有仁心,鸳鸯之鸟,待其长大能飞乃执毕以掩之,有得有不得正,又张罗以网之,待其自入,皆不尽物之意也。德及禽兽如此,宜其寿考而受福禄也。毛氏谓之兴,孔氏谓举一物以兴其余。兴之不兼比者也。”此诗究竟于兴中是否有比,有两个考察途径。一是依毛诗及严氏之说来解析,首章两句的关系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是君子 “福禄宜之”之根据,先有“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后有 “君子万年,福禄宜之”,前者既兴起后者,也可喻示后者,所以如依严氏遵从毛序之说,首章应该是兴而兼比者。二是此诗的诗义并不一定如毛序所说是 “刺幽王”,也没有表达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的意思。毛氏此说曾受到马瑞辰、黄山等人批评,以为非诗之义。[6]今按,此诗实则赞扬君子,并祝君子永享福禄,全诗共分四章,前两章均由鸳鸯起兴,后两章由乘马起兴。而各章取兴所采用的角度各有不同,首章取 “毕之罗之”意,喻示君子如被 “毕之罗之”的鸳鸯一样,福禄集于一身;二章取 “戢其左翼”意,戢,敛也,与首章同以鸳鸯收敛其翅膀为喻,比拟君子福禄聚于一身;三章四章分别以乘马为喻,取 “摧之秣之”意。摧,即莝之古字,莝,委也,餧之省借,餧,饲也,与下文之 “秣”同意,指饲养乘马。作者以饲养乘马起兴,喻示以福禄赡养君子,即下文所谓 “福禄艾 (养也)之”、“福禄绥 (安也)之”。由此可见,四章的开头分别以鸳鸯和乘马起兴,与下文的君子有起兴兼比喻关系,是典型的兴而有比之例。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毛传所标为 “兴也”的诗,基本上都是兴而兼比的,被严粲 《诗缉》断为 “兴之不兼比者”的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妥当的。其实,还有 《邶风·北门》也是值得推敲的。[7]
[1]孔颖达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2]陆德明:《毛诗音义》上,《经典释文》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宋版。[3]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6]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排印本。
[7]孙立:《诗经 “东门”臆说》,《文献》1998年第3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I207.22
A
1000-7326(2015)01-0150-04
*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日本中国文章学研究”(13YJA701541)、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资金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日本中国文章学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3wyxm0180)的阶段性成果。
孙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教授、主任 (广东 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