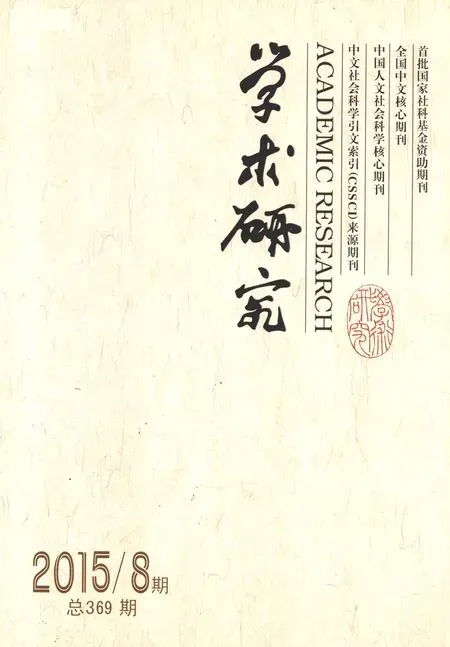论《史记》文章学经典地位在明代的形成*
杨昊鸥
论《史记》文章学经典地位在明代的形成*
杨昊鸥
《史记》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中长期受到重视的文本。在明代以前,《史记》在文学接受方面大致被认为是重要的先秦两汉文章范本之一,但地位低于先秦经部文献,同时在思想倾向和体例设置等方面时常受到批评者的指摘。这种情况在明代发生了转变。明代 《史记》文章学地位不断被经典化,引发了明人研究、评点 《史记》的热潮。 《史记》在明代受到普遍推重的根本原因,是明人试图树立新的文章学典范以对抗宋人,这客观上造成了 《史记》最终被树立为中国文章学的最高典范,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 文章学 明代 评点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经典和文章学经典。 《史记》的史学经典地位在唐代已基本形成,然而文章学经典地位确立则相对较迟。鲁迅在 《汉文学史纲要》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史记》)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矣。”[1]意谓 《史记》是中国古代散文中地位最高的作品。 《史记》这一文章学经典地位的形成始于明代,这和中国文章学理论的发展及明代学术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一、明前文章学对 《史记》的定位
唐代古文运动以前的 《史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评论和思想评论方面。扬雄在 《法言》中以“实录”概括 《史记》的史笔,对 《史记》的思想倾向则提出了 “爱奇”的批评。班固首次对 《史记》做了综合性评论,《汉书·司马迁传》论赞云:“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认为 《史记》的史笔总体详赡而细节不乏疏略与抵牾,思想倾向有悖儒家正统之处,但其行文具有叙事清晰、语言质朴、评论客观的特点。班固的评论得到了后世裴松之、范晔、裴骃、刘勰等文史学家的一致认同。
刘勰在 《文心雕龙·史传》中除了继承班固的看法之外,还有两点创造性意见。首先,刘勰开始对司马迁的文学成就进行定位:“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3]《文心雕龙》的文学
观念是建立在 “原道”、“征圣”、“宗经”立场之上的,所以司马迁的文学地位虽然降格于尧帝和孔子,《史记》的文学价值降格于经部文献,但作者和作品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文心雕龙·史传》特别肯定了 《史记》在文体创造方面的成就:“取式 《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 《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4]
《史记》正式进入文章家的评论视野始于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家开始以 《榖粱传》、《左传》、《国语》、《离骚》、《史记》、《汉书》等先秦及秦汉典籍并举,目的是建立可堪效法的古文传统。如:“参之 《榖粱传》以厉其气,参之 《国语》以博其趣,参之 《离骚》以致其幽,参之 《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柳宗元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5]“旁通百家,爱 《榖粱子》清而婉,左丘明 《国语》辨而工,司马迁 《史记》文而不华。” (刘禹锡 《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6]唐代古文家对 《史记》缺少专门研究,评论也比较笼统,但在理论定位上将 《史记》视为值得学习的文章学范本,这样的观念在 《史记》接受史上具有突破意义。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深入发展的时代,《史记》的文章学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关于 《史记》修辞学和风格学的评论开始兴起,并带动了 《史记》叙事学的研究,评论的形式也日渐多样化。宋人对 《史记》文章学的定位比唐人具体。陈师道云:“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壮伟,其失骋;汉之文华赡,其失缓,东汉而下无取焉。” (陈师道 《后山诗话》)[7]《史记》作为秦汉古文系统中的西汉典籍,其文章学地位大致可以描述为可堪师法,但地位低于先秦经部文献、高于汉代之后的作品。在这个定位中,西汉文虽然在地位上降格于先秦文,但从文章学习的角度却是最利于师法的对象,而 《史记》则是西汉文中最堪师法者。如吕本中云:“文章大要须以西汉为宗,此人所可及也。至于上面一等,则须审己才分,不可勉强也。” (王正德 《余师录》)[8]但由于宋代文章学具有中正典雅、含蓄内敛的美学倾向,宋人同时对 《史记》的行文风格和修辞手法提出过很多批评,总体评价是得之雄健,失之麄率。[9]加之宋人的文章学理论虽然在观念上推崇秦汉古文,在实际的写作、选编活动中真正推崇的却是时文,[10]所以 《史记》对于宋代文章家的实际写作指导关系并不密切。对 《史记》的文章学价值有所重视而不乏批评的观念,在元金之际基本得到了延续。如元刘因云:“司马迁大集群书为 《史记》,上下数千载,亦云备矣。然而议论或驳而不纯,取其纯而舍其驳可也。”[11]金王若虚 《文辨》云:“迁文虽奇,疏拙亦多,不必皆可取也。”[12]
综上所述,明前 《史记》在中国文章学的定位仅是作为先秦两汉文章学资源的重要典籍之一,同时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与缺陷。这样的定位,尚未达到 “无韵之离骚”的经典地位。
二、明代 《史记》文章学地位的崛起
明人的 《史记》文章学研究表现出许多与宋以前不同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史记》的文章学地位逐渐被经典化。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突破了尊经观念的苑囿,使得 《史记》文章学地位超过了像 《左传》这样的经部文献;二、否定前代批评中关于 《史记》思想倾向上不合于儒家正统的指摘,并将这种指摘转意为褒义性的评价;三、打破了文体观念的限制,将 《史记》视为同时影响叙事、议论两大文体类别的文章学经典。
在宋人的文章学观念中,《史记》的突出成就主要源于对经部叙事成分较重的典籍 《春秋》及 《左传》的继承,而在文章学地位上,《史记》是明显低于 《左传》的。而到了明代,这种观念已经开始改变,明正统至成化间的著名学者叶盛对 《史记》的评论十分值得注意:“六经而下,左丘明传 《春秋》,而千万世文章实祖于此。继丘明者,司马子长。子长为 《史记》而力量过之,在汉为文中之雄。”[13]叶盛不仅承认 《史记》对 《左传》的继承关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 《史记》与 《左传》相比 “力量过之”,将 《史记》的文章学价值 (至少在行文雄健方面)置诸经部典籍 《左传》之上。这标志着明代对 《史记》文章学价值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尊经观念的苑囿。
而至明末,甚至出现了 《史记》文章完全胜过 《左传》及其他经部典籍的看法。如单思恭 《甜雪斋
文·读史记》云:“盖 《左氏》即有变化百折,然其琢字琢句必欲求工。吾不病其浮夸,而转病其严谨尔。 《史记》则不然,无之而不疎放也,无之而不挥洒也,酒帐肉簿皆成大书。令后之字摹句袭者于《左》则肖,于 《史》则废然返焉。呜呼,此其所以为子长也。”[14]又如方以智云:“《左传》巧炼,未免隽伤……子长以郁折而成 《史记》,收合百家,洽古宜时。散近乎朴,变藏于平,善序事理,真不虚也。”[15]客观地说,单思恭和方以智的看法都不无言过其实之嫌,其贬低先秦文献如 《左传》“琢字琢句必欲求工”、“巧炼隽伤”,纯粹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是不能成立的,但值得重视的是在明末文学观念中,《史记》的地位已经可以被堂而皇之地置诸经部典籍之上,这是前代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在 《史记》早期接受史中,“爱奇”是对 《史记》的主要负面批评之一。前代 《史记》批评所谓“奇”,主要是指思想倾向不合于儒家传统。而在明代,人们在评论 《史记》时所谈到的 “奇”则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弘治、正德年间的著名文人王鏊 《震泽长语·文章》25则,虽称 “六经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矣”,但详考其文,其中所论最多的文章范本则是 《史记》,25则中有7则提到 《史记》,其中5则专论,1则与韩愈合论,1则与 《汉书》合论,重视程度胜过韩、柳诸家。除此之外,王鏊还特别重视《史记》的 “奇”气,7则论述之中有4则论及 《史记》之奇,如:“《史记》不必人人立传,《孟子传》及三鄒子,《荀卿传》间及公孙龙、剧子、尸子、吁子之属,卫青、霍去病同传,窦婴、田蚡、灌夫三人为一传,其间叙事合而离,离而复合,文最奇,而始末备。”[16]“《史记·张苍传》叙至迁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后又入赵尧,赵尧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后仍入张苍,事核而文奇。”[17]王鏊所谓 “奇”,意指 《史记》叙事手段变化丰富,行文气质雄健奔放。在明代 《史记》批评中,以 “奇”、“奇事”、“奇绝”、“雄奇”、“奇致”、“好奇”这样的词汇来褒扬 《史记》的评论非常普遍。同时,即便是倍受前代评论者指摘的思想倾向问题,到明代也常常出现针锋相对的看法,如康海 《史记序》云:“若夫孟坚所论,龙驹所称,则俟有博雅君子折衷于圣人之道,而是非得失,固难以一人之言尽万世之议者也。至于黄老之谈,盖当时所尚,非先之也……盖既称一家之言,又安能悉合于众人之意?”[18]
早在宋初,宋祁便提出 “屈宋 《离骚》为辞赋之祖,司马迁 《史记》为纪传之祖”[19]的看法。宋祁认为 《史记》的影响主要在纪传文体方面,而并没有完全涵盖到除纪传之外的其他文体。到了明代中期,认为 《史记》的影响不限于叙事型文体的观点也开始出现,如王维桢云:“又曰文章之体有二,序事、议论各不相淆,盖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创为之。真德秀读古人之文,自列所见,岐为二途。夫文体区别,古诚有之。然有不可岐而别者,如 (《史记》)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孙弘、郑庄等传及 《儒林传》等序,此皆述其事又发其义。观辞之辨者,以为议论可也,观实之具者以为叙事者可也,变化离合不可名物。”[20]可见至明中期,《史记》兼含叙事、议论二体的理论准备已有所积累。至明中后期,《史记》的文章成就突破叙事文体局限的观念终于成形。茅坤 《史记钞·读史记法》云:“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且太史公所擅,秦汉以来文章之宗者何,唯以独得其解云耳。……风调之遒逸,摹写之玲珑,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愤,则又千年以来,所绝无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堑矣。魏晋唐宋以下,独欧阳永叔得其十之一二。虽韩昌黎之雄,亦由自开门户,到叙事变化处,不能入其堂奥,唯 《毛颖传》则几几耳。”[21]事实上,尽管 《史记》的部分篇章采取了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段,但其对后世非叙事性文体的影响毕竟有限。茅坤故作惊人之语的目的实质是将前人对 《史记》各个方面的批评一笔否定,进而将 《史记》的文章学地位推向顶峰。
弘治、正德到嘉靖、万历年间是文学复古思潮高涨的时期,也是 《史记》文章学地位全面建立的时期。 “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与李攀龙盛赞 《史记》:“余二人相得甚欢,间来约曰:‘……七言畅于燕歌乎,而法极于杜、李矣…… 《书》变而 《左氏》、《战国》乎,而法极于司马迁矣。’”[22]此处所谓“法”,正是指文法。王世贞又在 《史记评林叙》中谈道:“自今而后,有能绍明司马氏之统而称良史、至文者,舍以栋 (凌稚隆)奚择哉?”[23]王世贞对于 《史记》,盛赞其文法至极,推为 “至文”,这是在前代文学批
评中只能用于评论经部文献的词汇。可见 《史记》在此时的文章学地位已经被经典化至与前代完全不同的高度。晚明诗文家陈继儒对 《史记》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余尝论 《史记》之文,类大禹治水,山海志鬼怪毕出,黄帝张乐,洞庭之鱼龙怒飞,此当值以文章论,而儒家以理学裙束之,史家以体裁义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24]陈继儒提出 《史记》的文章学价值不仅是杰出的,而且是独立的、不依附于经史价值而存在的。这就将 《史记》的文章学价值单独抽离了出来,使前人对 《史记》在思想倾向和史实记录方面的批评不再与其文章学价值纠结在一起。这是在晚明 《史记》文章学地位已经完全被经典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观点。
三、明代 《史记》文章学研究的盛况
明代 《史记》文章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实际写作的师法和 《史记》评点两个方面。
在实际的写作方面,被誉为明代 “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对 《史记》的评价就已经到达了相当高的程度:“迁之文如神龙行天,电雷惚恍而风雨骤至,万物承其秽泽,各致余妍……濂见其劲硬如屈铁,奇峭如削悬崖,泽媚山晖,如蕴珠涵璧,始而大惊,中而释所疑,终则益畏之而发不可企及之叹。”[25]宋濂不仅对 《史记》的文章学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写作上也对 《史记》有意识地学习。宋濂对纪传文体非常重视,早年专门编写过 《浦阳人物记》两卷,载录浦阳地区行宜高尚者29人,另有传记体散文67篇收录入别集 《文宪集》。他传记的人物始终贯穿着发强刚毅、慷慨落拓之志,不难看出作品中寓怀抱于传主行事的 《史记》遗韵,其行文风格更是深得 《史记》雄强奇崛之风。正是因为宋濂在理论和写作上与 《史记》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继承关系,当时已经有人将其尊称为 “太史公”(《明史·宋濂传》)[26]
在宋代,专门以 《史记》为文章范本进行学习的比较少见。而至明代中后期,以 《史记》为文章范本和宗法对象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了。万历五年 (1577)徐中行 《史记评林》序云:“历代之宗 《汉书》,至宋尤盛。其宗 《史记》者,乃盛于今日。”[27]归有光是明代后期另一位对 《史记》接受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作家。他对 《史记》高度重视,《明史》本传载:“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 《太史公书》,得其神理。”[28]他对 《史记》进行评点著成 《归评史记》,开创以五色圈点对 《史记》进行文章评点的模式,是明代重要的 《史记》评点本之一。归有光的散文写作深得晚明及清代文章家的赞赏,认为他深得 《史记》之神髓,对清代桐城派古文影响极大。如钱谦益云:“(归文)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学者举不能知,而先生独深知而自得之。”[29]戴名世云:“震川独得其 (《史记》)神于百世之下,以自奋于江海之滨。”[30]他对 《史记》文章专精研究,对 《史记》写作手法潜心学习,最终扩大了 《史记》在文章学领域的影响范围,拓宽了 《史记》接受的思路。归有光也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理论先导。清代桐城派古文在理论上远祖 《史记》,近绍归有光,可以说归有光正是接通桐城古文理论与 《史记》文章技法的桥梁。
在评点方面,明代的 《史记》评点蔚为大观。笔者根据明代凌稚隆 《史记评林》、贺次君 《史记书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载录,以及通过对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和哈佛大学善本特藏资源库的检索,统计出明代单行的评点本、评抄本共29种 (不计改刻、重刊和同书异名的情况),分别如下:1.杨慎、李元阳 《史记题评》;2.沈科编选、黄养吾校 《史记抄》;3.唐顺之 《史记选要》;4.王鏊《王守溪史记评抄》;5.何孟春 《何燕泉史记评抄》;6.茅瓉 《茅见沧史记评抄》;7.凌约言 《凌藻泉史记评抄》;8.王慎中 《王遵岩史记评抄》;9.王维桢 《王槐野史记评抄》;10.陈沂 《陈石亭史记评抄》;11.王韦 《王钦佩史记评抄》;12.董份 《董浔阳史记评抄》;13.张之象 《太史史例》;14.柯维骐 《史记考要》;15.茅坤 《茅鹿门史记评抄》;16.凌稚隆 《史记评林》;17.凌稚隆 《史记纂》;18.钟惺 《史记辑评》;19.陈仁锡 《史记评林》;20.陈子龙、徐孚远 《史记测议》;21.葛鼎、金蟠 《史记汇评》;22.朱东观 《史记集评》;23.归有光 《归震川评点史记》;24.孙鑛 《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25.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26.邓以讃 《史记辑评》;27.陈继儒评、黄嘉惠辑 《陈太史评阅史记》;28.焦竑、李廷机注释、李光缙汇评 《史记综芬评林》;29.郑维岳 《新锲郑孩如先生精选史记旁训句解》。其中第4至第12计9种评抄本今不可见,只能通过凌稚隆 《史记评林》的辑录来了解,此外20种至今可见。
如将改刻、重刊和同书异名的情况一起考虑进来,数量将增加数倍之多。
对比今天可见的其他一些明代先秦两汉典籍单行评本 (不计改刻、重刊和同书异名的情况),如《诗经》11种,《楚辞》8种,《左传》13种,《战国策》10种,《汉书》6种,①所述几种先秦两汉典籍明代评点本的情况分别参考张洪海博士论文 《〈诗经〉评点研究》(复旦大学图书馆藏,2008年),罗剑波博士论文 《明代 〈楚辞〉评点研究》(复旦大学图书馆藏,2008年),李卫军博士论文 《〈左传〉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2008年),曹晔硕士论文 《明代的 〈战国策〉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图书馆藏,2009年),朱志先 《明人汉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明代 《史记》评点本的数量特别多,可见明人在 《史记》评点上投入的热情较其他先秦两汉典籍更大。不过,明代 《史记》评点本虽然数量众多,却存在着跟风趋时的问题,特别是明末的部分评点本对 《史记》的文辞一味溢美抬高。如贺次君就严厉地指出钟惺的 《史记》评本 “乃拾杨慎、李元阳、茅坤、凌稚隆所为论说,稍加编裁,或间出己意,亦不过如评诗文,争论文句之长短,堆陈浮辞而已。……明自杨慎、凌稚隆而后,评论之风日烈,钟敬伯辈其实无学,但好高论,所以不惜重资以刻 《史记》者,乃投合时尚,愿求名之一闻耳。”[31]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中看到当时的文化风气是以评点、刻印 《史记》为时尚的。
四、《史记》文章学地位崛起的原因
《史记》文章学地位在明代迅速崛起并不是偶然现象,它与明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背景密切相关。在已有的 《史记》接受史研究之中,《史记》在明代受到推重这一文学史现象往往被笼统地归因于明代文学的复古主义思潮。但 《史记》在先秦两汉文章学资源中并不是最久远的著作,相反年代还相对比较近今,何以能够在文学复古主义思潮之中脱颖而出,在明人文章学理论中成为超越其他先秦两汉典籍的最高文章学典范?
首先应该看到,明人的文学复古思潮本质上是企望借助复古理论来实现对宋代学术强大影响的对抗,进而树立富于时代气息和自我意识的文学品格。明代文章学受宋人影响之大,时常令明人自身感到不满,如杨慎就对当时的文化风气做过这样的描述:“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32]他还矫枉过正地批评过宋文,实则是为了挽回明人在宋代强大文章学传统压抑下的自信心,他说:“吾观在昔,文弊于宋……予语古今文章,宋之欧、苏、曾、王,皆有此病 (冗繁),视韩柳远不及矣。”[33]明代文章学受宋人的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宋代文章大家如欧、曾、苏、王等人极其推崇,二是明人在观念上完整地接受了宋人对文章学史脉络的梳理,包括宋人对自身在文章学史上的定位。宋人的文章学脉络观念比较集中体现在“秦汉文——唐宋文”(唐宋文中又偏重于宋文)这个谱系之中, 这样的文章学史基本框架被明人完整接受,并加以深入发挥,如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叙》云:“西京之文号为尔雅……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宋兴百年,文运天启,于是欧阳公修从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韩书,手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而起。”[34]另一方面,明人为了树立文化上的自我品格,有时刻意在表面上回避对其影响最深的宋人,逆溯汉、唐,以期在文化资源上取法高古,自成一家。明代形形色色的诗文复古运动,名为复古,实为去近,所谓近,就是宋。明人对宋代文化在心理上之 “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明初曾鼎撰《文式》示人以作文 (及诗)之法,其第17条 “字法”云:“摘用 《史记》、《文选》、东西 《汉书》、《尔雅》、《广雅》、《晋书》、新旧 《唐书》、《六书考》。 《事文类聚》字不可用多,宋事也。”[35]此处称“《事文类聚》字不可用多,宋事也”,即是因宋事去今尚近,引以用字则嫌缺乏古意,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明人反抗宋人影响的努力。
《史记》的文章学地位在明代不断被经典化,与明人在观念中对抗宋代学术的自觉意识密切相关。《史记》在宋代文章学观念中仅是 “秦汉文”资源之一,并且是不太突出的一种,在地位上不仅降格于先秦经部文献,即便在史部文献中,也低于 《汉书》。明人在接受了宋人建构的整体文章学史脉络观念
的同时,希望树立在文学旨趣上有别于宋人的新型文学典范,进而实现自我品格的树立。于是,宋人对《史记》赞扬的意见,基本被明人所继承,而宋人对 《史记》的批评,到了明代则往往可见针锋相对的意见。如宋人嫌 《史记》文风失于中正典雅,明人则赞赏其奇绝奔放。宋人对于 《史》、《汉》总体上比较推尊后者,明人则推尊前者。宋人常常对 《史记》具体的写法提出质疑和批评,明人则往往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归结为是司马迁富有深意的写作手段。后一种情况比较普遍,试举两例说明。宋人叶适论《史记·管晏列传》,批评司马迁所载录的管仲事迹颇为鄙陋,又其为人曾遭孔子严厉批评,不堪传训后世,所以此传的立意在于:“迁载管仲称鲍叔牙事甚鄙,不可以示后世,子思所谓信乎友、获乎上者,岂若是哉?……且管仲不能尽由礼,故孔子以三归、具官,反坫,树塞门明之,遂谓其 ‘富拟公室’,亦非也。”[36]而明人柯维骐则认为:“古之贤人君子众矣,太史公列传独首伯夷,春秋列国大夫如展季、蘧瑗、铜鞮伯华、叔向、季札诸贤皆不得录,乃次及管晏,且愿为执鞭,何哉?迁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谓 ‘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非与洁行饿死同乎哉?管仲仇也,鲍叔荐之;越石父囚也,晏子赎之,迁盖自伤其弗遇也。”[37]柯维骐结合司马迁本人的身世遭遇来阐释 《管晏列传》的主旨,比叶适单纯从儒学立场出发做出的批评要中肯得多,也较切合 《史记》写作的原意。总体而言,明人的 《史记》批评较为活泼,能够打破正统儒学思想的限制,对 《史记》写作手段的认识比较灵活,研究的细致程度也达到了前人所未及的地步。
但在某些时候,明人又存在着对 《史记》过度阐释的倾向。例如关于 《孟子荀卿列传》的讨论,宋代陈仁子较有代表性地提出由于孟子在汉初学术背景下地位不如后世那么高,所以 《孟子荀卿列传》存在着体例上的瑕疵:“愚曰:汉初不知尊孟子。夫孟子接孔氏之正传,仁义七篇,杲杲行世,岂可与诸子同科?迁也以孟、荀同传已不伦矣,而更以驺子、淳于髠等出处实之,何卑孟邪?”[38]而明代焦竑则语带讥讽地反驳陈仁子的意见,认为他不了解 《史记》文章写作的深意:“陈仁子曰:‘汉初不知尊孟子……何卑孟邪?’按史法,有牵连得书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叹孟子所如不合,而驺子、淳于髡之流,棼棼焉尊礼于世,正以见珷玞轻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驽马竞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见谓为卑孟,是不知文章宾主也。”[39]以 “主客”或 “宾主”来讨论 《史记》的文章技法是明代 《史记》评论中常见的概念。明人普遍认为司马迁在写作 《史记》每一个具体篇章时都具有较强的布置意识,对篇章及其所记述的人物与事件都做出了主次、详略、虚实上的自觉安排。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并不适用于解决 《史记》中所有的写作问题,如上述例子中,焦竑的意见就很难有效解释为何 “客”的篇幅较长,而 “主”的篇幅较短,以及 “主客”之间相互反衬的具体特征体现在哪里,只能说是一种较为主观的说法。
当然,《史记》之所以能够被明人有意识地树立为新的文章学经典,也与其自身文本形态的独特性紧密相关。 《史记》虽被后世定义为正史之首,但考察其实际写作的原始状态却是藏之名山的私家史,带有强烈的子书性质,这和先秦两汉其他经史典籍有所不同。 《史记》在文本气质上既有学究天人、通变古今的恢弘气魄,同时具备独抒怀抱、成一家之言的个性意识。 《史记》这样的文本气质,与企望树立自我品格的明代文化心态非常契合,受到明人的推重也正是情理之中的事。
《史记》文章学经典地位在明代的形成,是中国文章学史上重要的现象,对后世乃至今天的文学观念仍有着巨大影响。在清代,将 《史记》视为最高文章学典范的观念已成为共识,评论者往往以 “古今第一”(唐彪 《读书作文谱》),[40]“冠古今”(张谦宜 《絸斋论文》),[41]“文章不祧之祖”(梁章钜 《退庵论文》),[42]“集文字之大成”(顾云 《盋山谈艺录》)[43]来盛赞 《史记》的文章学成就。这种声口近似、陈陈相因的观念在清代及民国以来,几乎很少得到学理上的讨论。今天,《史记》文学研究仍然是古代文学学科的显学之一。推尊 《史记》固然有助于我们深入、多角度地去审视这部伟大的文史名著,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这样的观念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演进逐渐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今人的 《史记》文章学研究应客观审慎地对待这样的观念,从而将研究推向更加客观实际的方向。
[1]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5页。
[2][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3][4][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73、576页。
[5][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3页。
[6][唐]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112页。
[7][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5页。
[8][12][15][16][17][33][34][35][40][41][42][43]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7、1137、3218-3210、1646、1646、1670、1783、1557、3541、3873、5156、5852页。
[9]杨昊鸥:《宋代文章学视野下的 〈史记〉》,《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0]吴承学:《宋代文集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1][20][21][23][27][明]凌稚隆辑校,[明]李光缙增补,于亦时整理:《史记评林》第1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0、171-172、173-178、13、30页。
[13][明]叶盛:《水东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0页。
[14][明]单思恭:《甜雪斋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9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38-339页。
[18][明]康海:《对山文集》,明代论著丛书,台北:伟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第218-219页。
[19][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22][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明代论著丛书,台北:伟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第3416页。
[24][明]陈继儒著,王凯符选注:《白石樵真稿》,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
[25][明]宋濂:《文宪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7页。
[26][28][清]张廷玉等编:《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87-3788、7383页。
[29][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29页。
[30][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19页。
[31]贺次君:《史记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79页。
[32][明]杨慎:《升庵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7页。
[36][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2页。
[37][明]柯维骐:《史记考要》,明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38][宋]陈仁子:《文选补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
[39][明]焦竑:《焦氏笔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
I206.2
A
1000-7326(2015)08-0152-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的阶段性成果。
杨昊鸥,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广东 广州,510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