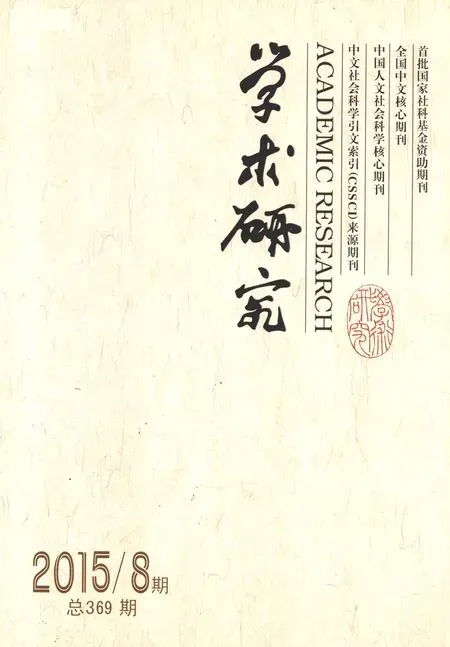释风格*
栾栋
文学 语言学
释风格*
栾栋
从个性观瞻,“风格就是人”(布封)。从文体切入,风格乃 “体性”(刘勰)。前者抓住了个性,但是推到极端,难免堕入 “唯我”或 “独一”。后者兼顾文体,然而文体之内,尚未剖析 “他者”与 “多元”。本文主张 “风格非一”,在肯定上述成果的同时,解开了个性与文体的封闭性束缚,凸显了风格作为“自由花”、“体裁树”和 “文化节”的多重品行,把差异性、多样性和节点性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是风格,展示风格如是。
风格 非一 自由花 体裁树 文化节
琴师忌讳胶柱鼓瑟。作文忧虑墨守成规。这里说的忌讳和忧虑,在风格学上看,就已经涉及到了逃避俗熟的呼吁和启发创新的意识。呼吁脱俗是风教的本义,启示创新是格调的真容。风格的真精神就在其中。无声无字的呼吁和启示,是无限多样的风之精神和格之思想,教给人们的是丰富多彩之文教和谐与不胜枚举之艺术差异。换言之,防套路,避程式,畏定格,辟蹊径,这就是风体的不言之教。
一、风格是自由花
风格何风?自然而然之风。风格哪格?苟新日新之格。从青蘋之末到茫茫世界,风起于自然,格显于人文,在天为大气,在物为造化,在人为性命,所谓风格,乃自由之花。自由之花非一,她是风格的真谛。风格非一,首先在于自然非一。风格作为自由之花,根本上是自然之花。自然是风格的调色板。人的风格,文的风格,说到底,其质地便是自然风格。风云变幻的宇宙,尽显瞬息万变的气象。数不胜数的星丛,各携电光火石迸涌,突作无形烟尘隐遁。宇林宙丛,时空混成,漫天星体,各不相同。大气氤氲的地球,潜移默化,物种沙数,类类成因独特,品品质地迥异。数以亿计的人类,族族文化奇特,人人面目有别。十里不同风,百里各有俗。秉性,举止,语言,文字,情采,作品,无不以特殊而有别,因特点而名世,并且以特色而著称。倘若求取对风格原道性的解析,刘勰关于 “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文心雕龙·原道》)不失为有见地的概括。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 《春夜宴桃李园序》),自然之于风格的关系,原本是造化给于命运的意义。
风格非一,也在于人们的品性各各不同。血性造人,脾气各异。禀赋众多,应物如风。就文心而论,所谓风格,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借法国人布封的说法,风格 “其实就是人”。老子法天法地,孔子乐山乐水,庄子梦蝶而知鱼,孟子养气且乐群,屈原起骚问天,韩非说难孤愤,司马迁洞悉史蕴诗神,刘彦和擅长文心雕龙……从古到今,俊才云蒸,风格千姿百态,思想异彩纷呈,“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性情”(刘勰 《文心雕龙·体性》)。究其要点,可以抓住品性这个关键,气质是充斥其中的主色调,秉性是贯穿始终的大脉搏。古今众多的诗学论述,对风格做过锲而不舍的解析,从内在的意蕴上讲,抓住品性者,也就抓住了风格的核心。真正的风格学,应该是完整的品性论。品性的独特性,诠释着风格的无限多样性。
风格非一,还在于人生逆旅所逆各异。存在限定意识,意识酵化着存在。在风格独立特行的意义上,存在只能限定庸人和常人的意识,却不能决定阻抗暴虐的非凡精神。古来能成就某种非常风格者,无不是匡正存在或博弈命运之人。正因为如此,才有各民族迥然有别的原始神话,能够在异常严酷的条件下产生,才有伏生等人的藏书活动,在秦始皇帝残暴的统治下进行,才有司马迁的学术建树,在汉武帝超常的专制下完成,才有鼓动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塞万提斯,才有杜撰庞大固埃的拉伯雷,才有前苏联时期的巴赫金。社会存在决定论之所以偏颇,偏就偏在过分看重统治机器的强大和历史条件的严重,过分高估一刀切文化政治的厉害,而没有看到任何风格的成功,原本都有逆水行舟者的个性化胆色,都有经磨历劫者超拔俗常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风格是个体与其生存环境相磨相荡的产物,是自由种芽与生长条件相生相克的缘分。
风格非一,非一孕生于反窠臼思想的过程。人文创造本应比自然更加异彩纷呈。然而常见的状态更多的是一体化的辖制。一体化的裹胁不仅来自专制制度,还有学界 “泰斗”的窠臼化版型。前者造成的一体化不难分辨,后者潜制的一体化则常常被学界忽略。 《圣经》的唯一性窒息风格,逻各斯的统一性吞并风格,柏拉图的理念观框定风格,巴门尼德的 “一是”说扼杀风格,老子的 “得一”论误导风格,韩非的拥帝术奴化风格,既成的文体束缚风格,大腕的狙击枪毙风格……就风格而论,一化是死穴,然而造成死穴的罪孽并非只是使动者一端,被动者心底也潜藏着自我无风的空洞。就文思而言,如果说执一性的窠臼是风格的癌病灶,那么跟风追风随大流的惰怠则是毁坏风格的气质性病变。马牛风,不相及,人文格,也有别。风异于一体便是自由,格别出他者就有风骨。随大流必然会堕入窠臼,风息,格灭,精神萎顿,思想泯灭,遑论风格。
风格是多面神,有多面神则逸出 “整体即谬”(阿多诺)。风格是自由花,有自由花就不致 “满室皆假”(李贽)。自由花是人文世界的瑶草奇葩,越非一越显得生机勃发。自由花是精神园地的万紫千红,越非一越能让景色如画。自由花是思想王国的续根作物,越非一越分蘖异种新芽。只要思想的王国里有风格,由来已久的执一论就难以称孤道寡。在精神的场域中,最多姿多彩的就是风格,在文化的大地上,最可贵的体性依然是风格。风格非一,因为风格本身就是非一性的体现。风格非一,显示的是风格契合的诸子百家。能容得下非一,就不会有家天下。呵护无限的非一,就可成就差异的融洽。虽然说有风格的非一让习惯于划一者难堪,然而去除真善美伪同一的状态,终究可以消减世人的尴尬。因为非一本身就是严格的自律,风格的非一性意味着对他者的尊重。非一,是风格的变体性基因,是它让风格成为生生不已的千变万化。
从国内到国外,常见的风格论无不强调个性化的小一,于是风格到头来成了唯我者的托词。从文史到哲学,所有的风格说无不潜藏一个思辨性的大一,从而风格最终变作排他者的借口。本文关于风格非一的解说,跳脱了从小一到大一的思想陷阱,在自我非我和自由非一的学理深层,揭示了风格之为风格的根本特征。非一当然非唯我,非一自然敬重他者,非一没有真善美统一的高调,非一给一切有志于风格的人投出了改造俗熟乃至创造新我的支持票。
二、风格是体裁树
风格如树,篇篇成体裁,犹如树树有风姿。在人文林苑,风格以风采出,也以风度胜。风情、风范、风骨、风节,均属风格树的奇珍异果。文学史出落的体裁好似枝叶繁茂的小树丛,郁郁葱葱,摇曳多姿。思想史蕴涵的风格有如巨木参天的大森林,莽莽苍苍,波澜壮阔。不论是体裁抑或风节,都是风格多样性的表现。文化是其水土,人物是其枝干,作品是其花果。此处我们仅从以下几个瞭望点,领略风格在文化学方面玉树临风的资质。
第一个看点,风俗之风情是风格树的肺腑。文化树是社会的体裁,风情是风俗之肺叶。风俗的体裁是风情,风俗经过风情而变为风格。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这是一种风俗,披露的是从远古到高古众多华夏部族血浓于水的融合。龙,亦虚亦实,且俗且雅,当祂作为民族的信念与族徽的标志而传承之时,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体裁,也就是说,龙文化既是中国心的内容,也是中国人的象征。中国的山海各有传说,中国的家族各有谱系,中国的民歌地殊而调异,中国的戏剧种繁且曲盛……不难看出,风俗是风情的历史深呼吸,风情是风俗的文化精气神。风情依风俗而厚重,风俗因风情而清俊。风情是风俗得以升华的格调,风俗是风情源源不绝的底蕴。从低处观瞻,风俗一如江河出青海而气贯长虹,在高处眺望,风情好似日月照昆仑而气象万千。风情作为结构,如树如林,浓缩天地厚爱于根须,激扬历史精华于枝叶,花美,果丰,尽显其人文体裁的多姿多彩。在一切可称为风格的风情中,那些个富于韵致的变化,或以隐喻,或以象征,都让人深刻地感觉到其格调的与众不同。
第二个看点,风化之风教是风格的脉络。风化的体裁是风教,风化经由风教而成为礼仪。风教既是体式,也是过程。公元前2100年至前800年的夏商周三代文化,分别以 《连山》、《归藏》和 《周易》而闻名,世称 “三易”,其实就是兼包内容与形式的风教。商周古歌 “风雅颂”也有此类特点,既是教化体裁,又是教化活动。儒道佛的教场经变,虽然所涉神格深浅有别,但在风教礼仪方面,都有各自的体系制式,都对各自的行为有体用求合的规范。风教根于善缘,越是通和致化,越可和光同尘。风教最怕封闭,越加壁垒森严,越是陷于困顿。风教难脱权轴,越是政教合一,越会沦为权柄。在文化史上常常有这样的现象,风教之大宗,其开山鼻祖还算有容乃大,而后来的信徒却画地为牢,逐代蜕化,终至僵局且积重难返。谈风化,论风教,体式之化裁非常重要。只知其成体裁,守成规,不懂化裁,所陷处无不是迷途危境。
第三个看点,风度之风致是风格的年轮。风度是量度风格的风采气度,风致是检点风格的风雅情致。风致的体裁是品题。风致者,风度情致之总称。品字三口,已是缘合,题入释教,意为经师正果。缘起义,品修义,教化义,三义在此融会。我们把风致与品题并论,是要揭示体裁方面的一个化境。文章学论体裁,往往忽略风致,风格论讲风致,却又淡化文体。在先秦大儒的眼中,风有致,品有格,题有序。三才合于道,四始总于诗,六艺归于教,有大端而无隔阂。中古虽分文体,仍不失融通大旨。《昭明文选》列文体为39类,同时代的理论家刘勰则述文体而重通变 (《文心雕龙》涉及文体林林总总70多种),体性的阐发说明他很在意风格与体裁的关联。文体是社会分工在文章学方面的表现,风格则是沟通文体与体性的津渡。而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我们只提取了风格的三个看点,解析的也只是风格的三个节目,即肺腑、脉络和年轮。这些节点都是通过历史体裁现身说法。风俗格于风情。风化格于变奏。风致格于品题。在风格学的琼林玉宇,其美好的情致不是以繁茂取胜,而是以通变见长。在文学发展到文体如此细腻的今天,提倡化感通变是其时也。文体小体裁,风教大文体。风可以俗显,世人谓之风情。风可以礼节,国族泛称教化。风可以格致,本文赞为风骚。风情格于韵律。教化格于礼仪。风骚格于品题。此三者名异实通,均属人文之大体裁。此处讲大体裁,是在宽泛的意义上梳理风格的体式。
风格风出了自由,风格格出了节律。风格有自由,斯世才值得生活。风格有节律,人生便知耻且格。风格可风,风让文化绚丽多彩。风格可格,格使世界错落有致。
三、风格是文化节
风格的奥妙在于风而有格。风格的执着在于格而成节。风格的文化在于节而可化。节是风格的时空节奏、品性节点和审美节庆,因而,我们也将风格称作人类为差异性而默契的文化节。容忍和默许风格之为风格,意味着包容以至欣赏各种差异性。
风格是文化节,是说任何风格都体现为一定的节点。节点是事物的关键所在。称得上风格的人、文、事、情,无不是由其自性凝聚着的多种元素之集成,或者说无不是由内化了的互文性凸显出其与众不同的那样一种差异性品节。风格之节点有其结,是缘分之结,品格之结,力量之结,但也可能出现僵化之结。成风格者,可结缘、结义、结体,但是不可结帮、结仇、结怨。风格要有格,结缘、结义、结体就是格。格是风骨,有格不意味僵化。孔子讲 “君子不器”,“君子不党”,“君子和而不流”,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器,党,流,风格之三忌。为器结壳,执一守固,虽也有风,然而僵在其中。风格要有节,节是亮点,也是品节,但不是结节,尤其不要结帮组派。世上许多领域有派别,而且都有各自成派别的理由,唯独文学艺术和学术事业不可帮派化,因为文艺是无为有为的超越性活动,学术是化感通变的本真性事业。无为有为和化感通变,恰恰是风格之风格,或曰风格之母题。每一种风格都是母题中的一个节点,是通和致化的节点。而母题则是非一性的唯道集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所有推崇流派的文艺理论持不同看法的原因,直白了讲,宗派不好,流派也不值得赞赏。
风格是文化节,意味着风格有其是介非界的差异品格。此节是介,此节非界。界者,限也。界限是隔阂,是壁垒。界限体现的是疆域、对立甚至仇恨,而非差异。此节是介,介是差异,展示的是差别、异样及其关联,蕴含的是和合、和睦还有和平。有风格就有包容,没有包容处就没有风格。没有风格等于霸权裸露,张扬的是权力话语的霸道。作为文化节的风格是介非界,传达出风格的品介特点。介是导入,介通间,是对界的化解。介中包含着此差异性与不同存在的互相让渡,显示出互为主体性的主体间性。介属于包容性的共和,界则是排他性的对立。个体性与其差异性与群体性通和致化,作为文化节的化境凭借化感通变而成化。
风格是文化节,折射出风格有其花海人潮的节日气象。风格的万花筒节点要有特殊的机遇。古希腊古典时代出现过文化风格的井喷。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过百家争鸣的气象。文艺复兴时代出现过百花齐放格局。 “五四”时代出现过姹紫嫣红的态势。这种风格的狂欢节得益于王纲解纽,英才积聚,幸逢专制的闸门崩溃,文化的自由发展成为可能。风格的万花冢披露的是文化节的反面,我们称之为文化劫。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文字冤狱”、“文化革命”,都属于这一类。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很难躬逢风格的狂欢节,但是却非常容易遭遇风格的万花冢。在历史长河与当下现实中,人们都在期盼风格和创造风格,但是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履行着扼杀风格的使命。让文艺做机器,让学术当工具,让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当风格……这就是 “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可悲。
一个没有宽容的民族或国家,是很难出思想家的,也很难出万紫千红的差异性创新。扼杀风格的事情不仅会以 “革命”或 “道义”的名义进行,也会以讨伐别人的 “风格晦涩”、“看不懂”等口实运作。扼杀风格的高手有时甚至不是 “政治家”,而是所谓学术权威、评论家、刊物老总、学界名人。一个庸俗的时代,要比一个专制的时代更可怕,缺少自由的状态下尚可出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或巴赫金,但是平庸的时代只能眼看着产生如山如海的文化垃圾。在人类思想文化的广阔天地,每个人可以喜欢任何一种风格,或愿意成为任何一种风格,这都无可非议,但是万勿自觉不自觉地充当风格杀手。
不论作为文化节的风格何时出现高潮,每一种花卉始终在积聚自己的颜色。不论作为体裁树的风格怎样脱俗变雅,每一个创造者总会找到自己的体式。不论作为自由花的风格遭逢的是哪个季节,每一位花神都会恪尽职守。我们既庆幸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机缘,也赞美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光霜里斗婵娟”的顽强。风格如是,是如风格。
责任编辑:王法敏
I01
A
1000-7326(2015)08-0129-04
*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标志性成果培植课题 “中西方风体学大端问题趋通研究”(14BZCG01)的阶段性成果。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 广州,51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