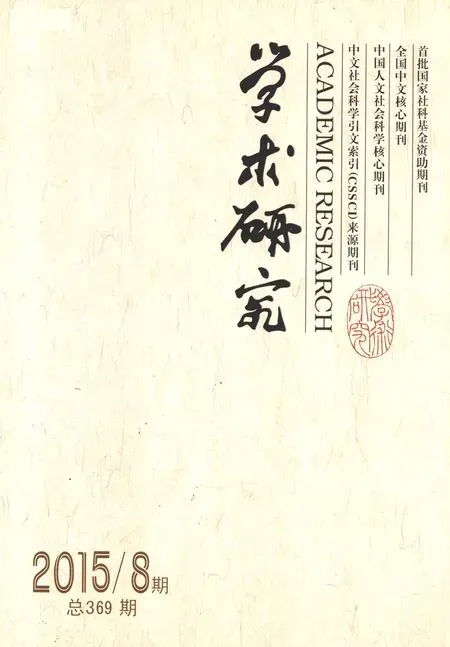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
邢科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
邢科
直到近代,中国才出现 “世界史”一词,但中国对世界历史的书写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 《史记》。在 “华夷观”的影响下,以 《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史书都采用了 “中国中心”的书写视角。这一视角延续到了晚清时期。鸦片战争后,中国学者继续从 “华夷观”的角度书写 “世界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 《四裔编年表》虽仍在彰显中国的尊贵,但其中已经蕴含了西方的史学因素。 “中国中心”视角逐渐衰落后,“欧洲中心”视角成为民国 “世界史”的主流。但从20世纪20年代,以陈衡哲、何炳松、杨贤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分别从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 “欧洲中心论”提出挑战。周谷城《世界通史》的问世,则表明反 “欧洲中心”的书写视角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 “世界史”的书写视角经历了一个从 “中国中心”到 “欧洲中心”,再到反 “欧洲中心”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出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世界史 晚清 民国 中国中心 欧洲中心论 文化自觉
近20年来,世界历史在中国的发展逐渐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历史的传入,二是世界历史在20世纪,尤其是建国之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①关于世界历史的传入,主要研究成果包括邹振环的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李孝迁的 《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关于世界历史在20世纪的发展,学界亦有研究,代表作有齐世荣的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历史回顾与前途展望》(《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于沛的 《世界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何芳川的 《世界史体系刍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等。关于晚清至民国时期世界历史的书写问题,尚无专门的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的书写视角及其变化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世界史”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直到近代,中国才出现 “世界史”一词,且晚清至民国时期的 “世界史”与今天所说的世界历史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晚清时期,介绍世界历史的书籍多以 “外国史”、“万国史”、“泰西史”、“西洋史”等名字出现。民国时期才有越来越多的著作使用“世界史”这一名称。但无论标题是什么,这些史著都是以讲述欧洲历史为主,涉及范围主要包括亚欧大陆、非洲北部和北美,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鲜有涉及。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的
“世界史”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①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种不完整的世界史,所以给世界史一词上打引号,以区别今天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尽管 “世界史”的概念出现得较晚,但中国很早就已经开始书写世界历史了。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认为,“历史编写者想方设法去记载重大的和可知的所有过往历史,因而他们据其所知而撰写的那部分地球的历史可以归之为世界历史。所以,照此标准,希罗多德和司马迁不仅是各自史学编纂传统的奠基者,而且可称为世界历史学家。”[1]的确,以 《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官修史书记载了当时所有“重大的和可知的”历史,都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从总体上看,在书写世界历史的时候,中国传统史书都采用了 “中国中心”的书写视角,美国学者柯文称之为 “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2]“中国中心”的基础是先秦时期的 “夷夏之辨”。最初,“华”、“夷”的概念是以地域而言的。[3]但后来,“华夷之辨”成为了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之争。[4]再后来,以地理和文化为基础的 “华夷观”演变成了 “华夷秩序”。传统史书中的 “中国中心”就是这种 “华夷秩序”的反映。作为第一部正史,《史记》中已经包含了 “中国中心”的书写视角。[5]而且,这种书写视角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盛行到晚清时期,并影响到了当时 “世界史”的书写。
一、晚清时期:“中国中心”视角的衰落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中国学者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知识梳理成系统,编成 《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等外国史地介绍。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动摇 “华夷观”的主导地位。因此,在梳理世界历史时,中国学者都在著作中强调了中国的 “中心地位”。例如,《瀛寰志略》在 《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开篇写到,“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6]清代历史更是表明,“我朝威德覃敷,远无弗届……西海穷陬,从古未通之国,靡不向化输诚,梯赆航琛,来庭恐后。”[7]在这种视角中,中国是中心,其他国家则是 “叠受天朝怀柔”。[8]魏源在 《海国图志》中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那么 “制夷”之后呢?魏源表达得比较隐晦,他在叙言中引用了 《越裳操》中诗句:“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9]《越裳操》相传为周公所做。根据东汉学者蔡邕的解释,“周公辅成王,成文王之王道,天下太平,万国和会。江黄纳贡,越裳重九译而来,献白雉。”[10]也就是说,“制夷”之后,中国仍旧是世界的中心,恢复到天下太平,万邦来朝的历史常态。刘鸿翱在 《瀛寰志略》的序中写道:“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天君泰而百体从令,圣人出而万国咸宁。”[11]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格局的基本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刘鸿翱担任福建巡抚,曾组织军民抗英,对西方国家的 “坚船利炮”有一定的了解,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闭目塞听之人。他在晚年写出这样的序,足见这种世界历史观念对中国影响之深。
第二次鸦片战争削弱了 “华夷观”,但 “中国中心”的书写视角仍然存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四裔编年表》。 《四裔编年表》出版于1874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和中国学者严良勋同译,中国学者李凤苞汇编。虽为译著,但该书由江南制造局组织翻译、汇编、出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 “世界史”的书写视角。 《四裔编年表》的 “中国中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书名中使用了“四裔”一词。 《尚书·尧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东汉学者马融在注中解释,幽州为北裔,崇山为南裔,三危为西裔,羽山为东裔。[12]“四裔”是一个与 “华夏”相对应的概念,是传统 “夷夏观”的反映。因此,这本书的书名中就包括了 “中国中心”的含义。其二,在行文中使用抬格。 《四裔编年表》中的抬格有这样几种情况:单抬,也就是高出一格。在叙述前朝时,该书使用 “唐”、“宋”、“元”,但从顺治元年起,改用 “大清”,且 “大清”抬一格。[13]挪抬,也就是在称谓前面空一格。提到中国时,“中国”两字前通常会空一格,如1613年的英吉利一栏中,载“始与 中国通商。”[14]平抬,也就是将称谓换行顶头。这种情况在书中也较为常见,但由于表格中每列只有四个字左右,所以平抬并不是很明显。抬格是对表述对象表示尊敬的一种格式。值得注意的是,在
《四裔编年表》中,除中国外,其他国家的国名并没有抬格,这就暗示中国高别国一等;而 “大清”一词,一方面显示本朝比前朝尊贵,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中心地位。正如学者所言,在朝代前面冠以 “大”字,是自我中心观念的产物。[15]
虽然体现出了 “中国中心”的书写视角,但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 “世界史”著作相比,《四裔编年表》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其一,由于传教士参与了该书的翻译,所以其中融入了一些圣经历史。例如,开篇提到了圣经中的创世记和大洪水,“西历前四千四年间,开辟天地,肇生人物,有亚当子孙相传千有余年。该隐嗣立无道,天降洪水”。[16]其二,将中国传统的帝王纪年、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同西方的公历纪年结合在了一起。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人为的时间观念是文化的产物,接受一种异域的时间观念,也是在接受一种异域的文化观念……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带来了一种时间心态的重要转变,从而形成历史叙事上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17]从总体上看,《四裔编年表》体现出了“中国中心”的书写视角。但与鸦片战争后的 “世界史”著作相比,该书的中国视角更多表现在形式上,就内涵而言,其中已经蕴含了西方的史学因素,以及更宏大的历史视野。
甲午战争的失败颠覆了传统的 “华夷观”,但以此为基础的 “中国中心”视角并没有消失。王先谦创作的 《日本源流考》和 《外国通鉴》稿本仍在沿用这种视角,这两部书是清末重要的 “世界史”著作。 《日本源流考》刊行于1902年。从1905年开始,王先谦在 《日本源流考》的基础上进行删增,形成了22卷的 《外国通鉴》稿本,其中增加朝鲜、琉球、土耳其、印度、暹罗、真腊、骠国、越南、马来亚、吕宋、爪哇等国家或地区。[18]之后,他又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形成了33卷的 《外国通鉴》稿本。但到王先谦去世时,该书尚未完成,最后仍停留在 “稿本”阶段,因而并没有正式刊行。 《日本源流考》和 《外国通鉴》也是从 “中国中心”视角书写出来的,这仍然可以从称谓中窥见端倪。 “《日本源流考》引用 《日本史》、《日本维新史》两书,原书是日本人所撰 《大日本史》、《大日本维新史》,王先谦引用时用成 《日本史》和 《日本维新史》,略去 ‘大’,不能简单理解为使用简称,《日本源流考》基本不用简称。”[19]王先谦的另一本著作 “《五洲地理志略》,把中国排在第一,称 ‘大清国’,其他国家之前一律不加 ‘大’。王先谦承认外国为 ‘国’,但在内心深处,仍觉得中国还是 ‘天朝大国’,含有一定的情感因素在内,他是一个 ‘中国中心主义者’”。[20]总之,王先谦 “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其史学思想中也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夷夏之辨观念。”[21]
对于 “中国中心”的书写视角,晚清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在重刻 《四裔编年表》时,皇甫锡璋对“四裔”的用法提出了质疑:“自我而外为四裔,中国史家通例也。阅至今日,会全球五大洲之人相与联盟,均为列国。由是而再执旧例以为之书,其不至于迷瞀者几何?若李君凤苞之编 《四裔年表》固旧例也,苟弗为之剖著明显,于今何裨焉?”[22]可见,作者并不赞同从 “夷夏观”的角度书写历史。宋恕也对 “中国中心”提出了批评:“近人攥外史,如 《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是反辱国矣。”[23]对于书写 “世界史”的视角,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盖学者习史,外国不能不略,本国不可不详……或问:‘子攥外史,体例、题名若何?’曰:‘体例仍魏、徐氏,而题曰 “外国史略”,则名正言顺。’”[24]如果撰写 《外国史略》,宋恕的基本思路是“详本国”而不 “尊内”。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中详细介绍中国历史,但并不以中国历史为中心,这就颠覆了 “中国中心”的书写视角。
遗憾的是,宋恕并没有撰写这部 《外国史略》,所以他的治史思想只是停留在观念阶段。真正试图打破 “中国中心”的是黄遵宪。在 《日本国志》的 “邻交志”中,黄遵宪讨论了中国称谓的问题,“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故今以华夏名篇。”[25]虽然 “华夏”与 “中华”只有一字之别,但其中就包含了淡化 “自尊卑人之意”,说明作者试图摆脱 “中国中心”的书写视
角。在黄遵宪笔下,日本已是一个与 “华夏”和 “泰西”诸国并列的国家。但这种突破也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并未在 “世界史”的编纂中成为主流。
纵观晚清时期,随着传统 “华夷观”的瓦解,“世界史”里的 “中国中心”也呈现逐渐衰落的趋势。19世纪40年代的史地著作仍然延续着 “夷夏观”,夸耀中国的 “无远弗届”,将西方国家称为 “夷”,在 “英吉利”前面加上反犬旁或口字旁。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 “世界史”著作仍将其他国家称为“四裔”,仍然在行文中凸显中国的地位,但在文字上已经没有了带贬低色彩的偏旁部首,而且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某些文化观念。到20世纪初,《外国通鉴》稿本也只能在文字上做文章了。尽管 “中国中心”的书写视角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但晚清的学者并未完全摆脱这个框架。
二、民国时期:“欧洲中心”与反 “欧洲中心”
正当王先谦把 《日本源流考》改编成 《外国通鉴》的时候,中国的 “世界史”书写视角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癸卯学制”的颁布为世界历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直接结果就是大量汉译世界史教科书的问世,迈尔的 《迈尔通史》、本多浅治郎的 《西洋历史教科书》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这批汉译教科书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书写历史的时候,采用了 “欧洲中心”的视角,这种视角对民国时期的“世界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吴于廑将世界历史中的 “欧洲中心论”归纳为两点,一是将欧洲历史分期视为世界历史分期,二是以欧洲作为历史主体,尤其是突出欧洲在近代史上的作用,主题是宣扬近代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欧洲人所创造的近代文明,以及这个文明向整个世界的普及。[26]“欧洲中心论”也得到了部分中国学者的认可。例如,杨人楩在 《高中外国史》中认为,“在外国史中,当然要以欧洲为中心,本书也就是如此;因为欧洲不特占的地位多,而且它的变化也较重要。”[27]在民国时期,这一观点具有较大的影响。
然而,尽管 “欧洲中心论”成为民国 “世界史”的主流,但这种视角也受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1924年9月24日,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张闻天译毕了美国作家房龙的 《人类的故事》,并将其更名为 《西洋史大纲》。[28]他在译序中解释了更名的原因:作者 “所说的人类,差不多完全以白种人为中心,对于有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与印度,只在原书第四十二章内略略说了一点,敷衍了事。不幸就是这一点也已经犯了许多错误!我觉得删去这一章对于读者既没有损失,而且他所说的既以欧美人为中心,倒不如把原书的书名改为 《西洋史大纲》较为近于实际。”[29]更名表示译者认为不应将 “欧美人”作为“人类的故事”的中心。张闻天的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带有反 “欧洲中心论”的书写视角,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马克思主义与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属于同一层面,本文仅是从世界史书写的角度将三者并列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破坏了西方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而且动摇了西方的价值观。一些学者相信,西方文明的根源导致了这次战争。战后,欧洲作为世界中心和世界发展排头兵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认为,应该在思想交流、相互支持和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全球共同体,形成 “文化世界主义”。[30]陈衡哲的 《西洋史》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想。 《西洋史》的撰写视角与上述观点有两点联系:其一是重视文化。在该书的导言中,陈衡哲明确提出,“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31]在叙述历史时,她使用了 “文化的欧洲”,以区别于 “地理的欧洲”。[32]其二是用建立世界文化的方式来抑制战争。在书中,陈衡哲将其表述为 “国际主义”:“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在求人类的彼此了解,及各国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他的重要工具,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帝国主义的目的,则适与国际主义的相反,他是以增加人类的误解及怨仇为任务的;他的重要工具,是战争。所以这两个现代文化势力的竞争,即不啻是战争与和平的竞争。使国际主义而能战胜帝国主义,那么,和平的梦想,即可实现。”[33]“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就是对世界文化的初步构想。在建立世界文化的过程中,陈衡哲非常看重中
国文化的作用,“以己国对于文化的贡献,视为国家荣誉的标准者,于是他们便能以藏兵毁甲为发达国家个性的第一个步骤了。这犹之高尚孤洁之士的不以富贵利禄而以一己的人格来作为生命成败的标准一样。”[34]不慕 “以富贵利禄”的 “高尚孤洁之士”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标准。这既表现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又表现出她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成为世界文化的基石和标杆。总之,传统的 “欧洲中心论”将欧洲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典范,而在陈衡哲设想的世界文化中,欧洲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中国为代表的非欧洲文明不但是世界文化的重要基础,而且能够引领世界的发展,纠正西方文明的偏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 “欧洲中心论”。
如果说 “国际主义”是站在全球的角度反对 “欧洲中心论”,那么 “民族主义”就是站在国家的角度反对 “欧洲中心论”。安东尼·史密斯指出,“民族主义”原本是个神学用语,后来逐渐倾向等同于民族自大和自我中心。[35]具体到民国时期的 “世界史”,民族主义的表现就是强调中国的重要性。以何炳松的 《外国史》系列教科书为例。一方面,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中国的强大。虽然中国也曾受到过入侵,但 “中国人抵抗他们的方法,或用刚,或用柔……再加以外交手段的高明……结果总是中国人得到最后的胜利。”[36]被中原王朝击败后,匈奴的 “一支则于公元后四世纪末叶侵入东欧,把白种的日耳曼民族赶得四面奔逃,引起罗马帝国的大乱和衰亡。就这点来看,古代中国人抵抗外族的力量和持久,实在远比同时的罗马帝国为强。”[37]这暗示了中国的汉帝国比欧洲的罗马帝国更强大。另一方面,作者从现实的角度,突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中国既担负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重任,又要实现自身的民族解放。而且,“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关系世界前途确是非常重大。”[38]此外,何炳松还直接阐述了民族主义的现实意义:“自从一九一一年后,中国本身乃得到一种民族主义的新武器。”[39]在书中,这种 “新武器”被作者视为可以拯救中国的 “民族精神”。
不仅如此,何炳松还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升华,探讨了一种有别于 “欧洲中心论”的 “世界重心论”。 “旧式外国史总以欧洲一洲为中心;东洋史则以中国一国为中心。欧洲和中国固然为东西两洋文化的重心,不可忽视;但亦不宜偏重。”[40]这样,世界历史就从 “一个中心”变成了 “两个重心”。 “世界重心论”与 “欧洲中心论”有两点区别。首先,“欧洲中心论”以文化不平等为基础,而何炳松更强调文化的平等性。在他看来,虽然各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有大小之分,但文化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别,世界文化是所有文化共同积淀的产物。其次,“欧洲中心论”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单向性,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因此在文化交流上片面突出西方文化的输出,而世界其他地区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何炳松的 “世界重心论”则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多向性,任何一种文化既是文化的输出者,也是文化的接收者,世界重心本身就是文化多向交流的产物。总之,在何炳松创作的 “世界史”中,无论是在叙述中突出中国的重要性,还是将中国视为 “世界重心”,都使中国获得了与欧洲相对平等的地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 “欧洲中心论”。
总的来说,“国际主义”和 “民族主义”都是从资产阶级史学内部,对既有视角的调整,而马克思主义则为世界历史书写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周谷城早就指出,“欧洲中心论”是为资产阶级扩张服务的:“只注意扩张和侵略,自然会以欧洲为中心。”[41]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它将被压迫阶级视为世界历史的主人翁。20世纪20年代末,化名为 “柳岛生”的共产党人杨贤江将日本革命家上田茂树的 《无产阶级世界史》译介到中国,取名为 《世界史纲》。之后,他又续写了该书,取名 《今日之世界》,该书记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约十年的历史。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世界划分为三个阵营,一个是苏维埃阵营,即无产阶级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阵营,即资产阶级阵营,具体地说就是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个则是被帝国主义盘剥的广大殖民地。作者认为,时代主题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一新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又普罗列搭利亚特获得政权时代”。①普罗列搭利亚特,即英文 “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音译。
[42]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控制的欧洲非但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反而成了历史发展的绊脚石。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 “欧洲中心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世界历史才刚刚起步,相关研究尚不成熟。以陈衡哲、何炳松、杨贤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只是初步具有了反 “欧洲中心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零散的,既缺乏理论高度,又缺乏社会深度,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扭转 “欧洲中心论”的书写视角。但他们的探索还是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49年,周谷城出版了 《世界通史》。正如学者所说,这部著作 “突破了 ‘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强调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对中国的世界史建设有开拓性的作用。”[43]“自周谷城《世界通史》开始的反对欧洲中心论,不仅在世界史研究中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在今天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现实意义。”[44]这表明,反 “欧洲中心”的书写视角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结语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45]晚清至民国时期世界历史书写视角的转变正折射出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费孝通通俗地解释了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 ‘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 ‘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 ‘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 ‘全面他化’……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46]也就是说,文化自觉是要客观地理解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然后对其进行去粗取精。
“中国中心”的基础是 “夷夏观”,“夷夏观”的问题在于,在强调自身文化优越性的同时,忽视或贬低了其他文化,这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晚清的学者基本都受过传统教育,对中国文化有着高度认同。因此,在书写 “世界史”的时候,他们的落脚点仍然是中国文化。例如,王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认为 “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47]他积极主张变法,但 “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48]王韬在 《重订法国志略》的序言中提出 “以法为鉴”的主张,认为基督教势力过大是 “法削弱之所由来也”。[49]可见,他并不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富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相反,他在思考问题时经常强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 “道”。总之,王韬是 “最具有世界主义观念的人,但仍坚持认为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具有普遍的意义,适用于分析世界历史的趋势。”[50]黄遵宪也是如此,尽管为突破 “中国中心”做出了努力,但他希望以 《周礼》为理论基础,重新建构新的世界秩序。[51]甲午战争后,有人续写了 《四裔编年表》。作者在叙例中说:“书缅、越、朝鲜灭,而知手足之剪也;书俄、法、英之界约,而知衣裳之裂也。”[52]作者最后写到,“绝笔于德取胶州何也?著瓜分之祸之首也。”[53]面对 “瓜分豆剖”之势,作者的悲愤已经溢于言表,但他试图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推陈出新,却是续写带有 “夷夏”色彩的 《四裔编年表》。重视本国文化本无可厚非,但晚清学者在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并没有深入挖掘其中存在的问题,继续从 “中国中心”的视角书写 “世界史”。因此,他们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很难书写出具有突破性的世界历史。
民国时期的 “世界史”则倒向了另一个极端。 “欧洲中心”视角下的 “世界史”过分地强调西方,忽视东方。这当然也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但与晚清不同的是,许多民国时期的 “世界史”学者既受到过传统教育,又受到过西式教育。陈衡哲出身官宦世家,母亲是画家,大伯陈鼎曾任翰林院编修,另一个伯父陈范在清末执掌过闻名全国的 《苏报》,舅父庄蕴宽亦为清末民初的风雨人物。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陈衡哲从小就学习 《尔雅》、《诗经》等传统典籍。[54]1914年赴美留学,主攻西洋历史。后从芝加哥大学读取硕士学位。与陈衡哲相比,何炳松的家学更为深厚,他的先祖何基是南宋理学家,曾师从朱熹的高足黄榦,开创了北山学派,世称北山先生。[55]童年时期,何炳松也受到过传统教育,14岁中秀才。后留学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但何炳松并没有忘记中国的传统学问。1932年,他
出版了代表作 《浙东学派溯源》。这样的教育背景可以使他们将东西方进行对比。在对比中,他们对东西方文化有了相对客观的认识,并尝试将其去粗取精。陈衡哲意识到了西方的弊端,并试图用 “国际主义”加以纠正;何炳松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并从 “民族主义”的角度加以强调。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创作的 “世界史”已经初步体现出了文化自觉。
综上所述,晚清至民国时期世界史书写的视角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强调中国,到片面强调西方,再到较为客观思考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借用费孝通的话,“中国中心”视角反映的是 “复旧”,而 “欧洲中心”视角反映的是 “西化”,这都是缺乏文化自觉的表现。反 “欧洲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化自觉,但自觉的程度还不够深入。
建国之后,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放眼世界,仍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回顾晚清到民国时期 “世界史”书写视角的变化,可以为今天书写世界历史带来几点启示: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全面而准确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无论是破除 “欧洲中心论”还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都不能脱离唯物辩证主义。总之,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和书写世界历史的立足之本。第二,世界历史中不能没有中国,在将中国融入世界史的过程中,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包括本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化,自信而不自大,虚心而不盲从,这样才能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56]第三,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陈衡哲与何炳松的撰写视角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但也都有缺陷。陈衡哲的视角,优点在于高屋建瓴,能够站在全球的高度思考问题,但缺点在于,世界文化太过宽泛,不好把握。何炳松的视角,优点在于重视中国,但如果发生偏差,“民族主义”可能会倒退为 “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狭小,观点片面。因此,如果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宏观视野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那么中国的世界历史书写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1][美]威廉·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夏继果、[美]杰里·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2][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1页。
[3]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200-201页。
[4]李龙海:《汉民族形成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5]王永平:《从 “天下”到 “世界”:汉代中国对世界的探索与认知》,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175页。
[6][11]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6页、序第3页。
[7][8]梁廷枏:《海国四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64、103页。
[9]魏源:《海国图志·原叙》,清光绪二年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
[10]蔡邕:《琴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12]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57页。
[13][14][16]林乐知、严良勋译,李凤苞汇编:《四裔编年表》,表四第26、22页、表一第1页。
[15]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17]邹振环:《〈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8]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外国通鉴稿·王先谦外国通鉴稿影印前言》,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第4页。
[19][20]程天芹:《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述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43页。
[21]王青芝:《王先谦的史学成就及思想与观念》,《船山学刊》2008年第2期。
[22]皇甫锡璋:《重刻四裔编年表序》,《四裔编年表》,光绪丁酉印本。
[23][24]宋恕:《六字课斋津谈·史家类第六》,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3、63-64页。
[25]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26]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5期。
[27]杨人楩:《高中外国史·叙》,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第4页。
[28]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29][美]房龙:《西洋史大纲:张闻天手稿》(影印本),张闻天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30][德]夏德明:《寻求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刘新城主编:《文明研究》第1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53页。
[31][32]陈衡哲:《西洋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导言第4页、第27页。
[33][34]陈衡哲:《西洋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324、324页。
[35][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页。
[36][37][40]何炳松:《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68-169、83页,编辑大意第1页。
[38][39]何炳松:《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下册,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02、900页。
[41]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
[42]柳岛生:《今日之世界》,《杨贤江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77页。
[43]于沛:《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成就》,《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44]张志哲:《周谷城及其 〈世界通史〉》,《世界历史》1985年第10期。
[45]《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第1版。
[46][56]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47][48]王韬:《答 〈强弱论〉》,《弢园文录外编》卷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66、167页。
[49]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原序》,光绪庚寅年淞隐庐印本,第2页。
[50][美]伊格尔斯、王晴佳: 《全球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5页。
[51]刘涛:《黄遵宪 〈日本国志〉与晚清国家、天下格局之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52][53]《续 〈四裔年表〉叙例》,江标等编:《湘学报》第1册,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8、700页。
[54]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33页。
[55]房鑫亮:《忠信笃敬——何炳松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K092
A
1000-7326(2015)08-0113-08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民国时期 ‘世界历史’的输入和兴起”(2014M561174)的阶段性成果。
邢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天津,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