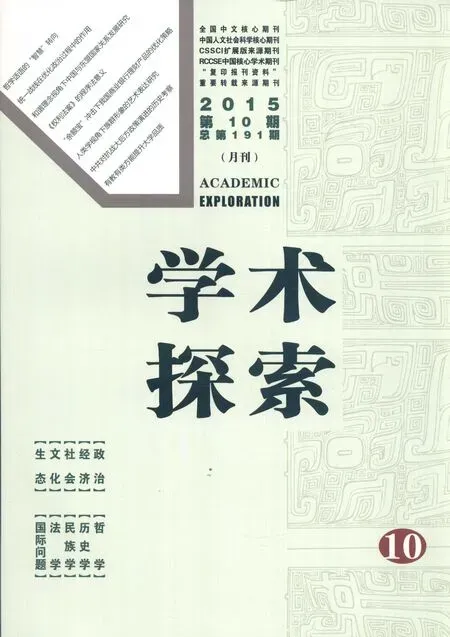《权利法案》的程序法意义
汪 栋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权利法案》的程序法意义
汪 栋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权利法案》的程序法条款是将公民权利写进宪法的一种独特立宪方式,表明将公民权利宣言载入宪法具有道德必要性与技术可行性。权利价值是宪法的正当性泉源,是现代政治的道德基础与根本出发点,作为立国之基的宪法首先是一个道德宣言。宪法程序是道德权利明确化、实在化的基本形式。运用程序技术的术语书写与阐释抽象权利,注重对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司法程序保障,是英国普通法的传统。《权利法案》的意义,不仅在于继承了普通法人权司法程序保障的传统,还在于将这种司法程序保障提升到宪法的高度,使得以陪审制为代表的普通法程序跻身成为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宪法程序。
权利法案;道德权利;普通法;陪审制;程序法
一、权利入宪的考量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弗吉尼亚州的代表乔治·梅森的一项提议必定会在宪法史上留给后人很多思考,这个提议就是将公民权利宣言列入宪法。尽管四年之后,公民权利宣言以《权利法案》的形式成为联邦宪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制宪会议在当年审议时却是以十比零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梅森的建议。[1](P34)概括而言,制宪会议对梅森提议的否决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宪法规定难以穷尽所有的公民权利。就立法技术而言,制宪者不可能将所有的公民权利逐一写进宪法。这是因为,权利先于宪法,宪法是权利保障的结果,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逻辑上,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转化而来,而公民权利则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公民权利的种类与数量之多不是一部成文宪法能够用文字表述无遗的,这是成文宪法固有的局限性;相反,成文宪法对于国家权力的规定则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文字的有限性恰好符合有限政府的原则,符合制约权力的旨趣。
其次,公民权利入宪难以避免人们的认识与理解偏差。成文宪法在表述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实体权利上的困难与欠缺,会对宪法正当性产生不利影响。更有甚者,宪法文本是神圣的,成文宪法将公民权利固定化,同时也就限制了人们对待公民权利的态度与视野,人们将会囿于文本的表面规定去考量权利,从而认为公民权利的享有只限于宪法的明文规定。这种理解很容易颠倒宪法与权利的先后关系,将先有权利而后有宪法的逻辑关系变成了先有宪法然后才有权利,似乎宪法是权利的渊源,而实际上,宪法是对权利的最高法律表述,表述有限而权利无限。无论如何,权利入宪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对权利的认识必然受限于宪法的文本规定:公民有无权利只以宪法文本为判断依据。然而,这是对宪法的误识,实际上,宪法只是表述、规范权利事实,它甚至不能限制公民权利,就更不必说对公民权利进行斟酌损益了,“就严格意义而论,人民不交出任何权利;既然人民保留全部权利,自然无需再宣布保留任何个别权利”。[2](P429)一方面,成文宪法不可能总括所有的公民实体权利,另一方面,宪法只能有限列举权利的后果堪虞,人们会对宪法未列举或难以列举的那些权利产生疑虑,甚至会误以为宪法的权利性条款不是保障权利而是限制权利。[1](P406)①为打消这种疑虑,权利法案第九条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只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所保留的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轻忽”。
再次,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在反对者眼中还是多余之举。宣示权利的目的无非是保障权利,如果这个目的能够通过宪法对国家权力的严格限制而得到实现,那么,是否在宪法中列入公民权利宣言,对于立宪目的而言似乎无关紧要。“宪法本身在一切合理的意义上以及一切实际的目的上,即为一种人权法案……在建立政体的大法的任何部分中既可发现人权法案的内容,则公民权利的次序如何列举自然无关宏旨。”[2](P430~431)人民主权是宪法基本原则,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者行使统治权,宪法对国家权力逐一列举,于是宪法实质是一份人民授予政府权力的清单。这份权力清单意味着,政府只能行使宪法明确列举的权力,而不在列举之内的权力是剩余权力(权利),它们归公民所保留。人民将权利“转让”给政府,只是指政府代表人民行使这些权利,而不是指人民转让了这些权利以后,就丧失了这些权利,因而,所谓“转让权利”“剩余的权利”“保留的权利”只是一些政治学修辞,人民的权利实际上完整无缺。
最后,制宪者们最大的担心是宪法关于权利的措辞易为人寻隙滥用。对此,汉密尔顿有详尽的分析,他认为限制政府权力与保障人权是一体两面的问题,从限制权力的角度侧面体现尊重人权的方式更为可取,更为审慎。而如果正面阐述公民权利,则由于语言所固有的局限性,反而可能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本为强调权利保障,效果则适得其反。假若通过权利条款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此种权力又没有经宪法授予政府,这不仅非常荒谬,而且事实上形成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方式扩大政府权力的结果。举例言之,宪法所列举的政府权力没有包括政府对出版自由的干涉,倘若人权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出版自由,此条款就不仅多余,而且显然暗示政府可制定相关法规,这就实际上突破了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列举限制,使得政府权力清单变成一纸空文。因此,“将人权法案列入拟议中的宪法,不仅无此必要,甚至可以造成危害……由于鼓吹人权法案者的盲目热情必将使持建设性权力论者得到许多把柄”。[2](P429~430)
总体而言,反对权利入宪者认为联邦宪法的简短序言已经对公民权利做了概括性宣示,②美国联邦宪法的序言是:“我们美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树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宁,筹备公共防务,增进全民福利,并谋求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福起见,特为美利坚合众国规定和制定这部宪法。”[1](P394)因而既没有立法技术上详尽列举的可能,更没有再做规定的必要,“此语(即宪法序言)乃对民众权利更好的承认。各州人权宣言中此类文字作为一篇伦理学论文的内容较之列入一部政府宪法更为合宜”。[2](P429)
反对将公民权利宣言列入宪法的上述理由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占了上风,联邦宪法草案对公民权利几乎未置一词,这表明反对者提出的理由是很有说服力的。虽然事实上后来梅森的提议得到了《权利法案》的肯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对权利入宪者的理由不成立。《权利法案》是正反两方面意见的折中案,是兼顾两个方面考虑的结果。
二、宪法的道德性
将公民权利宣言载入宪法具有道德与技术两个方面的意义。自然权利是宪法的正当性泉源,是现代政治的道德基础与根本出发点,作为立国之基的宪法首先是一个道德宣言。作为道德宣言书,宪法又是将自然权利加以明确化、实在化的最权威形式。③“实在化”一词的确切说法是“实在法(positive law)化”。英语positive的词根posit-源于拉丁词pōnō,是“安置(put)”的意思,其衍生的pose(把……摆正位置,提出)和expose(揭露、陈列),均具有“揭示”和“阐明”的含义,因此,positive law即是明确表述的法,也就是成文法、制定法、实在法,与此对应,自然法其实就是尚未经过主权权威认可并公示的不成文法。[3](P185~186)公民权利宣言具有巨大的价值内涵,将其写入宪法具有深远的道德意义。现代国家立足于深刻的人性价值,它实际上比传统伦理宗教社会更加注重政治的道德基础。无论是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还是东方的儒教帝国,作为传统政治形态,它们都将统治的正当性、道德性作为政治的首要问题,现代政治同样如此,区别只在于道德正当性的基础或来源不同。古代政治将统治的正当性归之于自然法或“天命”,而现代政治正当性则诉诸人的权利本身。诚然,时至今日,人权或自然权利取代了自然法或“天命”的地位,但是,自然权利从未取得像自然法或“天命”那样不言而喻的神圣地位,这就有必要用宪法去高扬权利的价值。进而言之,自然法与“天命”式微之后,它们留下的价值空白必须有什么事物填补进去,任何政治共同体都不可能没有情感、信念与道德的凝聚核心,就现代社会而言,权利或人格尊严是人们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最终价值基础。根据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人性假定,人首先是激情的生物,而不是理性的生物,在此意义上,倘若宪法欲图激发人们由衷而热烈的情感认同,欲图真正取得共同体成员持久稳固的信仰,那么,宪法就必须成为人格与权利崇拜的政治图腾。就此而论,我们才能理解梅森对于美国费城宪法草案缺乏权利条款的批评意见,确实,一部没有公民权利宣言的宪法,是不值得人们去眷恋,更不用说去信仰了。
虽然宪法通过对国家权力体制进行设计与规范能够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但是,将公民权利宣言写入宪法仍然有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而绝非简单的重复规定。我们必须注意将权力性宪法规范与权利性宪法规范进行区分,认识到两者各自的存在价值。首先,从目的上看,权力性条款旨在防范权力之恶,而权利性条款则意在彰显权利之善。其次,从性质上说,权力性条款是授权性条款、禁止性条款、防范性条款,对国家权力持不信任与严格控制的态度。权利性条款则是确认性条款、宣言性条款,是对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正当要求的宣告与肯认。[4]再次,权力性条款与权利性条款的功能不同。前者的功能是人民通过宪法逐项授予政府权力,经由权力性条款而组织、实现与规范国家权力,从而确立政体的基本架构,厘清、协调基本的权力关系。而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则不仅能够提示权力不得为恶,而且能够弘扬公民进取之心,成其公民之志,基本权利条款最重要的功能是为政治制度提供道德基础与正当性泉源。最后,权力性条款与权利性条款的立法方式也有区别。这个区别是两种宪法规范的性质与功能不同的逻辑延伸。权力性条款的性质多为授权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强制性规范,有限政府原则要求此类规范必须以明确具体的文字逐一列举各项国家权力,只有在非常必要时,并且在严格的程序约束之下,才能概括式授予政府权力,简言之,权力性规定以列举式为原则,以概括式为例外。权利性条款因为多是确认性规范、宣言性规范、任意性规范,所以与权力性规范相反,以概括式宣告为主,而以列举式强调为辅。[4]即使同样是列举式规定,对国家权力而言,旨在列出权力的清单,禁止国家机关行使权力清单没有列举的权力;而对公民权利而言,列举式规定意在清晰阐释概括式规范的内涵,强调公民权利的道德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比较主要是权力性条款与公民实体权利条款之间的对比。公民的程序权利条款则是概括与列举并重,就列举的立法方式而言,它既不像权力列举那样起限制作用,也不像公民实体权利列举那样仅为宣告、强调、阐释之用,而是具有更多的指示操作的意义。
清单列举式的立法对于国家权力而言具有深刻的法治内涵。有限政府是宪法基本原则,政府权力的有限性表现在目的、范围、方式等等方面,列举式规定的限制作用主要表现为清晰界定政府权力的范围,禁止政府行使宪法未列举的权力。正因为列举具有限制与禁止作用,因此,宪法原则上不能对政府做出概括式授权,权力性条款必须是列举式规范。“宪法草案规定国会权力,即国家立法机关权力,应及于若干列举事项。此处个别事项的列举自系对国家立法机关拥有普及各个领域的立法权的排除。因为宪法意欲授予普遍性的立法权,则逐项授予其个别权力即为荒唐无用之举。联邦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同样亦经宪法明文列举。所列各项即为联邦司法的确切范围,此外则非联邦法院权力之所及,因其受理的各类案件业已逐项列举,如不排除此外的任何权力,则所列举的各项权力即失去其意义。”[2](P417)
总括而言,列举式立法的技术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意义。针对国家权力,必须以列举式立法限制其范围;然而,针对公民的实体权利,列举式立法难免捉襟见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使得制宪者于进退两难之间一度放弃了将公民权利写进宪法的尝试。然而,列举式立法技术面对公民权利的局限性,换一个角度,则不妨看成是它的开放性,也就是说,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列举式规定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权利结构,而是一个能够不断接纳新的权利种类的开放性体系。
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的实在化、宪法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什么样的权利需要以根本法的形式加以确认与强调,视具体的社会与历史情境而定,自然权利与宪法权利之间的转换是一个动态、开放、持续的过程。如果坚持以自然权利原则作为宪法的道德基础与源头活水,那么,作为自然权利宪法表现形式的列举式规范体系就不会陷入僵化的困境。而且,公民的实体权利诚然根本无法列举穷尽,幸运的是,公民的程序权利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列举完备。只要妥善运用列举式立法技术,选择程序保障的角度,辅以概括式的规定,将公民权利写进宪法是可行的。
三、设置权利的技术
美国宪法是一个完整的权力体制设计,纵观历史,没有先例可作援引,然而,将公民权利写入宪法却有现成的立法技术范例可循。作为古老的“英国人权利”的继承者,美国制宪者的法律文化基因是普通法传统,而普通法具有悠久的运用法律程序术语阐释抽象权利的历史。美国1791年《权利法案》的意义,不仅在于继承了普通法人权司法程序保障的传统,还在于将这种司法程序保障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使得以陪审制为代表的英国普通法程序蝶变成为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宪法程序。
(一)实体权利的表述方式
1791年《权利法案》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大都以程序的术语进行书写。因此,不奇怪的是,《权利法案》所载明的公民权利不像《独立宣言》那样呈现为抽象的道德权利,而是表述为法律权利或宪法程序权利,它们都是直接引自普通法上的司法程序权利,或古老的“英国人权利”,当然,这些传统“英国人权利”的实质是《独立宣言》所宣示的新时代的自然权利理念,是“旧瓶装新酒”。作为宪法性文本,《权利法案》不像《独立宣言》那样直接宣示实体性的权利,而是以间接的、程序性的方式做出表述。
首先,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性规定宣示公民权利。《权利法案》第一条是对国会立法权的禁止性条款,它是对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请愿权利等公民实体权利的保障;第八条则是以禁止酷刑、过重罚金的方式,间接地确认公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第九、第十条是以概括的方式宣示公民的未列举权利或保留权利,强调它们不得为联邦与州政府所妨碍。这些实在法规定简明、确切,既强调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又表明了对基本权利的尊重。
其次,通过程序规则的术语表达对公民实体权利的关怀。“程序先于权利”是英国普通法的悠久传统,“英国人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程序权利,这些程序权利也即司法程序权利如果得到实现,那么,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和财产等实体权利也就能够确保无虞。美国人将此英国普通法经验与传统重申于其宪法文件。如第四条宪法修正案规定:“人民有保障其人身、住所、文件和财物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不可侵犯的权利。除有以宣誓或正式证词为依据的可能的理由,其中特别说明应予搜索的地点,拘捕的人等或查封的物件外,不得颁发搜查证、拘捕证或扣押证。”[1](P405)《权利法案》所列举的大部分公民实体权利,均述之以程序的语言,运用的是美国人熟悉的普通法术语。《权利法案》对公民实体权利不做直接、具体的规定,其复杂的考量一如前述,而不仅是立法语言难以尽之。诚然,公民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相比,前者抽象而且难计其数,尽管如此,实体权利即自然权利却具有不可估量的道德价值,而这是程序权利难以比拟的。不过,普通法程序权利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英国人法治智慧的结晶,它能够以自身形式主义的确定性克服实体权利的不确定性。因此,同样是对公民权利的宣告,《权利法案》作为一种法律书写,截然不同于《独立宣言》的政治修辞,前者是对后者的实在化、形式化、技术化重述。一言以蔽之,如果说《独立宣言》是自然权利的价值结晶,那么《权利法案》则是实在法的技术杰作。
(二)实体条款与程序条款的比较
从宪法修正案条款的数量上说,《权利法案》共10条修正案,直接确认公民实体权利的只有一条,即第二条修正案关于公民持枪权利的规定,间接规定的有第一、第八、第九、第十修正案,其余五条修正案都是程序性条款。[4]虽然实体权利条款与程序权利条款各占一半,但是,程序权利条款的文字篇幅则占《权利法案》全文八成以上。另外,第八条实体性条款隐含程序的意味,即是说,程序权利条款其实有六条之多。因而,无论是从文字篇幅看,还是以条款数量论,“权利法案的大多数条款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
从立法技术上比较,总体而言,无论是实体权利抑或程序权利,都是将概括式规定与列举式规定相结合。具体而言,则又各有侧重。实体权利以概括为主,列举为辅;程序权利则相反,是以列举为主,概括为辅。这种将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融于一体的书写或表述方式,既可克服实体权利列举式规范的不周延性,又可避免实体权利概括式规范过于抽象。
对实体权利采用概括式规定是由于实体权利无法逐条予以列举详述,只能在第九条和第十条以概括的语言,宣布《权利法案》未列入的公民权利,国家不得加以妨害。程序权利的概括式规定即“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贯穿《权利法案》全篇内容,是所有程序权利的灵魂。同样是概括式规定,对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意义不一样,实体权利的概括式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实体权利的确难以逐一列举,而且也不可能列举穷尽;程序权利的概括式规定即第五条“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不像实体性权利概括式规定那样出于列举不周延的无奈,而是对所列举的所有程序权利精神的归纳与提炼,能够被用以统率、协调所列举的全部程序权利。当然,实体权利概括与程序权利概括的功能相似,不同的是两者的立法缘由,前者是出于弥补实体权利列举式缺陷考虑,后者则更多是出于协调程序权利列举式冲突的需要。
同样是列举式规定,实体权利列举旨在道德宣示与强调,程序权利列举则意在法律实施与适用。实体权利难以列举穷尽,而程序权利则基本能够做到比较完备地逐一列举。诚然,从理论上讲,程序权利也不可能列举完全。但是,毕竟程序权利旨在实际应用,其操作性、可行性更强,相比而言,程序权利的列举的完备程度更高,这是没有大的疑义的。《权利法案》只确认六种实体权利,即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人身自由、生命权、财产权及反抗压迫权。与公民实体权利规定相比,《权利法案》关于公民程序权利的规定,则形成了一个以“正当法律程序”为核心,以一系列司法程序为具体内容的完备的程序保障制度。[4]
(三)《权利法案》与普通法程序
普通法程序传统与自然权利理论的融合造就了经典文献《权利法案》。该宪法文献所列举的公民程序性权利,迄今仍然构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法治所必备的基本内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说:“权利法案的大多数条款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5](P858)[6](P3)这句话是对《权利法案》制度与价值渊源的精辟概括,法治必然以自然权利为价值归依,对权利的司法程序保障则是普通法的传统,换言之,宪法程序权利的价值基础是近代新兴的自然权利学说,制度渊源则是历史悠久的普通法规则。
就精神实质而言,《权利法案》与《独立宣言》同样是自然权利的宣言书。因此,与其将《权利法案》规定的公民实体权利看作是实在权利或法律权利,毋宁将这些规定理解为自然权利宣言。“权利法案由宽泛而抽象的关于政治道德的一些原则组成,这些原则以一种极其抽象的形式囊括了政治道德的所有层面,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这种政治道德能够给个人的宪法权利提供牢固的基础。”[7](P109)不唯实体权利实质上是道德权利,程序权利也同样具有道德性。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实在权利与自然权利,正是如此浑然融为一体。
自然权利先于宪法且是宪法的道德基础。因此,宪法唯有确认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权利和自由,才能成宪法之所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通过对公民实体权利的规定,自然权利经由宪法确认而明确化、规范化,从抽象的自然权利变成实在的宪法权利。当然,自然权利以实体权利的方式进入宪法,也就为宪法提供了道德与价值基础。现代国家是一个以宪法信仰为价值核心而凝聚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宪法信仰的实质是人格崇拜,而人格崇拜即是权利崇拜。宪法确认公民实体权利,是自然权利实在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宪法为自身奠定道德基础的必然要求。
因此,自然权利经宪法确认且由法律程序保障即构成其实在化的完整过程。以正当法律程序为主轴,辅之以切实细致的司法程序权利,建造公民宪法权利体系,是自然权利实在化的关键环节。如前所述,宪法以直接规定程序权利的方式,间接地确认实体权利,这样才能以程序权利的确定性、可操作性,弥补实体权利的模糊性、抽象性,从而完成自然权利的实在化。自然权利的实在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程序性保障固然不是自然权利实在化的唯一途径,但是,程序性保障毕竟是自然权利实在化的普遍方式。在所有的程序保障机制中,司法程序是最基本的方式,而且,司法程序作为保障与实现人权的基本方式,其来有自,是历史上英国普通法传统的结晶。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权利法案》规定的公民程序性权利几乎都是司法程序权利。
如前所述,《权利法案》的十条宪法修正案中有六条是程序性条款,其中第三条是较为宽泛意义上的法律程序权利,是对居民住房军事征用权力的程序限制。从第四条直到第八条共五条是司法程序权利,第四条修正案主要是对人身,住所的司法程序保障。第八条修正案禁止国家滥用刑罚权对公民施以酷刑。这两条修正案虽然规定了司法程序权利,并且突出了对公民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保护,但是,比较而言,其完整程度不如第五、第六、第七这三条修改案。
第五条修正案规定的三项司法程序权利是,公民若涉嫌犯罪则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公民享有一事不再罚或免于双重危险的权利;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①此处未逐一注明出处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权利法案》诸条款内容均参考相应中文译本,对照英文原文略修改,力求更为准确、忠实地转达英文原文的旨趣。后文援引的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的条款,如未特别注明,均依此例。赵宝云的《西方五国宪法通论》一书附有《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相关宪法修正案的中文译本,该译本对美国宪法内容的排序是按“条”下设“项”,而不是按照国内通常的法律文本体例,即“条”下设“款”,“款”下再设“项”,我们在引用时遵循国内通行的体例,因此,这里所说的“款”即是赵宝云书后所附译本的“项”。
第六条修正案确认五项司法程序权利:刑事诉讼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刑事案件告知权与知情权;刑事诉讼对质权与辩论权;刑事案件控辩双方同等的调查取证权利;刑事诉讼律师协助与辩护权。
第七条修正案规定两项司法程序权利:民事案件陪审权;民事陪审裁决一审终审权。
在我们看来,第五、第六、第七条这三条修正案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条款表明宪法程序与英国普通法传统一脉相承,宪法程序之中很多内容,尤其是那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程序,是直接受之于普通法。这三个条款对司法程序权利的描述几乎完全采用了普通法的措辞。例如,第七条指明民事案件的性质必须是“普通法(the common law)”上的纠纷,而且,民事案件的事实裁决,须依照“普通法”的特殊规定方可上诉。又如,陪审制是英国对抗式诉讼制度的核心,也是英国普通法程序的核心,“陪审”或“陪审团”(Jury)在这三条修正案中均有规定,反复出现过四次。当然,“普通法”“衡平法”“陪审”等概念在宪法的正文中也有表述,它们出现在宪法第三条关于联邦司法权的规定中,如该条第二款规定:所有刑事案件均由陪审团裁决,弹劾案除外。费城制宪会议设立此程序时,有代表提议民事案件也应当一概实行陪审制,因为各州早已经将民事陪审作为常规审判方式。但是,另有代表反对说,各州的民事陪审团组成方式不同,适用范围不一,因而不宜在联邦宪法中做统一要求。②关于陪审制在美国各州的适用范围的差异,汉密尔顿在为联邦宪法草案未统一规定民事陪审制辩解时有过详尽的说明。[8](P765)[2](P420~421)民事陪审程序最终未被写进宪法草案,这曾经引起人们对整个宪法草案的极大的质疑,“对制宪会议的宪法草案最大的意见是指责宪法缺少民事案件由陪审团审判的规定。……宪法中未提到民事诉讼被解释为废除陪审制度”。[2](P415)人们对陪审制命运的广泛担忧,迫使汉密尔顿不得不为宪法草案的这一疏漏专门撰文辩解:“凡拥有设立法庭之权者,自当拥有规定审判方式之权;因此,如宪法中无陪审问题的明文规定,则立法机关自然拥有采用或不采用陪审制的自由。在刑事诉讼方面,由于宪法有明文规定,一切刑事案件由陪审团审判,立法机关自无选择的自由余地;但在民事诉讼方面,宪法既未作明文规定,立法机关自可权宜行事。”[2](P416)这段辩解表面上很有说服力,但是,立法权的“权宜行事”是有限度的,必须尊重民事陪审制的普通法传统,一定意义上,对以传统、民情、信念等方式间接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立法机关只有将其提升为法律之责,而没有罔顾违逆之权。因此,笔锋一转,汉密尔顿又写道:“宪法特为一切刑事诉讼规定特定的审判方式确系对民事诉讼必须采用同样方式的排除,但并未剥夺立法机关视情况需要采取同一方式的权力。因此,所谓国会将无权将联邦司法的一切民事案件交由陪审团审判之说,实为毫无根据的妄言。”[2](P416)这一段向民众妥协的政治修辞,为稍后的宪法修正案补充规定民事陪审制留下了转圜的余地,而《权利法案》第七条也果然对民事陪审制度的基本原则做出前文所述的明确规定。自此,陪审制度成为宪法规定的适用于所有刑事、民事司法的基本程序,普通法的这一核心程序终于被确立为宪法程序,而且还是宪法程序的主要组成部分。
(四)宪法程序的创新
宪法程序是制宪者以自然权利原则对普通法程序进行创新的结果。美国宪法之接续普通法传统突出地表现在《权利法案》关于司法程序的第五至第七条修正案中。陪审制是普通法程序的精髓,第五、第六条修正案不仅是对宪法正文第三条第二款的具体阐释,也是对刑事陪审原则的重申。如前所述,第七条修正案关于民事陪审制的规定是对宪法正文缺憾的弥补。刑、民陪审制进入联邦宪法的不同历史,特别能够体现美国人对普通法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宪法程序对普通法传统的继承已经在前文详述,创新普通法传统则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首先是以成文宪法赋予陪审程序以最权威的法律地位,使之由普通的法律程序上升为宪法程序;其次是因陪审规则成为宪法的普遍性规定,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了陪审制的适用范围,统一了陪审制的适用规则;最后但最为重要的创新则是陪审制度的价值转换。因此,宪法程序对普通法程序的继承更多是制度与技术意义上的,而宪法程序对普通法传统的创新则不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根本的价值层面,即将陪审制这一发源于英国中世纪的古老司法程序视为“自由政体的守护神”,以自然权利原则彻底更新了传统陪审制的价值基础。在汉密尔顿看来,宪法草案取刑事陪审原则,而弃民事陪审原则,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刑事陪审直接关乎自由的存亡,非列入宪法不可。民事陪审组成方式、适用范围等各州参差不同,因而不宜列入宪法做统一规定。然而,这些都不是民事陪审入宪之路坎坷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在刑事陪审中也存在。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未发现自由的存亡与在民事诉讼中维持陪审制有何不可分割的联系……民事案设陪审制的优点似与维护自由并无关系”。[2](P418~419)姑且不论汉密尔顿关于民事陪审与自由之间关系的观点能否成立,毫无疑问的是,宪法对普通法程序取舍的根本标准是自由或自然权利原则,利于自由者存之,无关或看似无关自由者舍之。
值得注意的是,宪法程序对普通法传统的创新还表现在其本身将程序与实体融为一体。《权利法案》中列举的六条宪法程序,都不是纯粹的程序性规定,而是兼具实体内容,即以程序规则表现或暗示实体权利价值。第五条修正案集中体现了这种立法技术的特点,它在确立刑事陪审与正当法律程序这两个程序原则的同时,还同时确立了两条实体原则,即禁止双重危险与不得强迫被告自证其罪。这两条实体原则都源于自然权利哲学,是自然权利价值在刑事领域的具体表现。因而,第五条修正案规定的陪审制与正当法律程序这两个宪法程序,可看作是自然权利价值与普通法传统水乳交融的典范。第八条修正案规定刑事司法禁止酷刑与过重罚金,也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自然权利思想对传统司法程序的深刻影响。另外四条关于宪法程序的修正案也是如此。在我们看来,将自然权利价值与普通法传统融会贯通的第五条修正案,最能代表宪法程序对普通法的继承与创新,尤其是价值创新,因为该条款不仅重申、完善了宪法正文中的刑事陪审原则,赋予陪审制“自由政体守护神”的新使命,而且,为整个宪法程序规则体系确立了一个核心原则,即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将正当法律程序载入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不是对这一普通法古老术语的简单重复,而是制宪者运用自然权利哲学改造普通法传统的巨大创新。正当法律程序概念是人们对第五条宪法修正案,以及后世颁行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概括,是《权利法案》的精髓,也是所有公民权利的守护神。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要义有二: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受不利处分者享有申辩权;第五条修正案将其简练地表述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P405~406)正当法律程序概念的外延几乎囊括美国联邦宪法所规定的全部程序权利,因而,不仅其内涵已经不限于上述两点,而且,其外延也扩大到包括陪审制在内的其他程序规则。
就正当法律程序的历史发展而言,可从内涵和适用范围两方面简要言之。内涵上,正当法律程序最初仅指纯粹的程序性规则,后来演变为对权力提出公平、正义等实体性约束。适用范围上,第五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起初仅约束联邦政府,1866年第十四条修正案明确规定正当法律程序同样约束联邦的所有州政府。
正当法律程序是自然权利原则与普通法程序历史融合的结晶。源于英国普通法的代表性程序如陪审制、人身保护令、任何人不得为自己的法官等,经过自然权利革命性的价值改造而成为正当法律程序,并最终在美国联邦宪法中找到其归宿,成为根本法所规定的宪法程序。
四、余论
宪法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相互紧密交织,两者的区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尽管如此,实体与程序仍然有明显的不同,实体规则是对法律主体地位、资格、能力、利益等等方面的规定。例如,宪法对公民的生命、自由和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的确认,对国家机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授予,都属于宪法的实体规范。对《权利法案》的上述分析表明,与程序规则相比,宪法实体性条款固然不可或缺,但是也不应该规定过多,这是因为下面几个理由。
首先,将所有的公民实体权利都载入成文宪法不具有立法技术上的可行性。
其次,宪法实体性内容需要确定的形式加以表述,需要成文规则将其实在化、形式化,过多的实体性规则会造成宪法文本形式上的冗长繁复。
再次,人们所追求的实体权利与价值虽然数不胜数,但是,它们都需要程序规则加以实现,如果对实体利益与价值做出具体设定,实际上反而构成了对实体权利的不必要、不正当的限制。因此,与其一一规定或列举实体权利,毋宁以具体的程序规则对抽象的实体利益加以保障。
最后,在宪法作为国家道德宣言书的意义上,宪法固然应当载入公民的实体权利,也应当对国家的任务与目标等实体内容进行最低限度的规定,但是,如果宪法为民众设定过多的实体目标,就将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很大的限制。“人类智慧之光不是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向四外散射,而是在各地交互映辉,美国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9](P208)确定无疑的是,一旦设定过多的公共目标,国家会变成奥克肖特所说的“事业联合”型国家或行政技术型国家。[10](P158~159)在这样的国度里,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个体的所有力量都将可能被强制征用于国家的目标。在此意义上,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有限政府原则要求避免或减少将实质性特定目标纳入政府决策范围。以美国联邦宪法及其修正案《权利法案》为例,其基本构成要素是个体价值(也即自然权利)、有限政府、权利竞争、宪法程序。[11](P16)这四个要素是彼此具有内在关联的逻辑整体,共同构成现代政治的有限政府原则。根据自然权利原则,主权的职能只限于维持权利交易或竞争的秩序与安全。与此相适应,宪法主要规定的是权利交易关系和权利冲突的协调程序。就此而论,《权利法案》的程序法条款虽然在形式上可溯源于英国古老的普通法传统,但是,在根本价值上却是以近代政治哲学的有限政府原则或自然权利原则为基础的。
[1]赵宝云.西方五国宪法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2]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汪栋.霍布斯公民科学的宪法原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4]汪栋,董和平.论公民权利的宪法设置——以《权利法案》为例[J].河北法学,2004,(12).
[5]Justice William O.Douglas's Comment in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v.Mcgrath,se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Reports(95 Law.Ed.Oct.1950 Term),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1951.
[6]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M].刘丽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下)[M].尹宣,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9]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1]Frank M.Coleman.Hobbesand America:Exploring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7.
The Significance of Bill of Rights in Procedural Law
WANG D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Law,Shand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Taian,271018,Shandong,China)
The enactment of provisions of procedural law in Billof Rights is a uniqueway of constitution-making,for its inclusion of civil rights in the constitution.It ismorally necessary and technically feasible to enshrine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citizens in the constitution,as human rights are the source of the legitimacy of constitution and themoral foundation ofmodern politics,and the constitution,as the foundation of state,is firstly amoral declaration.Therefore,the constitutional procedure is the basic form in which themoral rights could get explication and actualization.Besides,it is the tradition of British common law to articulate abstract rights in procedural terminology,and to pay attention to protecting personal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judicial procedures.In conclusion,themeaning of Bill of Rights is not only to inherit the tradition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judicial procedures,butalso to raise such procedures protection to constitutional height,whichmakes the common law procedures,represented by jury system,elevate to supreme constitutional procedures.
Bill of Rights;moral rights;common law;jury system;procedural law
D911.04
:A
:1006-723X(2015)10-0052-08
〔责任编辑:黎 玫〕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FX054)
汪 栋,男,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宪法思想史、中国宪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