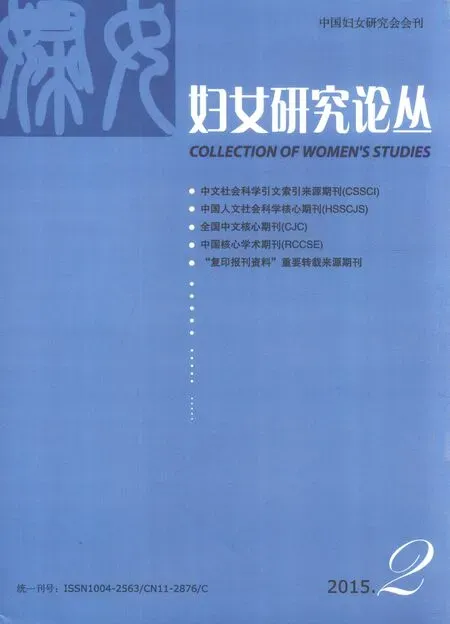被动的主动:清末广州高第街妇女权利与地位研究
——以契约文书为例
张启龙徐哲
(1.2.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被动的主动:清末广州高第街妇女权利与地位研究
——以契约文书为例
张启龙1徐哲2
(1.2.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清代;广州高第街;契约文书;妇女
清中后期,高第街作为广州城的商业老街聚集了众多盐商。在一批反映清末广州南城高第街房地产交易的契约文书中,出现了一些女性参与买卖过程的案例。通过对相关契约内容的分析发现,以寡母(寡妻)为主的一些高第街妇女能够以“买方”“卖方”和“中人”等多元的身份在家庭大宗交易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是在特定情况下的被动行为,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社会男性家长制度下女性的经济能动性。

契约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物权、债权关系的一类体现,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其能够体现经济交易中关系双方或多方的权利与义务,并以法律效应和道德约束的作用对经济活动给予保证和规范,故契约也具有一定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可以说,契约文书是民间社会经济活动的证明,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普遍的一致性,立契流程、格式和规范都有着约定俗成的固定套路,如关系双方均需要在契约文书中体现,并以签字画押为证,同时需要明晰交易内容,并对“中介”“中证”等参与交易的第三方进行交代。可见,契约文书以其直观的特性和比较正规的佐证方式,具有极高的社会承认度,在民间生活中被广泛接受和采纳。更重要的是,契约记载的是民间经济活动,尤其多是土地、房屋等大宗交易,与买卖双方的实际利益密切相关,多能真实地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还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在古代传统社会,契约文书所体现的是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人们普遍认为,丈夫在
世时,妻子是无权处置家庭财产的,一般只有在丈夫常年在外不归或丈夫离世等几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妇女以“守志寡居”的身份才可以获得一定处置财产的权力并在家庭活动中担任主要角色,《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一书中指出:“土地买卖文书中的女性立契人基本上都是已婚女性,其中的大多数是寡妻(寡母)身份。”[1](P89)本文所指的妇女多是此类情况。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妇女实际参与到土地、房产等大宗买卖中的案例越来越多,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仍有许多值得拓展的空间。例如,妇女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程度如何?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作用有何特点?一份契约文书涉及多个关系人,既有交易双方的主体“卖方”和“买方”,也包括交易过程中的第三方,如“中人”等。那么,契约文书如何体现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彰显其在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地位?直观的考察方式便是女性角色能否担当一份契约中所涉及的各个关系人,尤其是主要的交易关系人。
清朝末年,广州是清政府面向世界的重要门户,也是西方资本国家来华的首要之地,商品经济发展极为迅速,是较早开始近代转型的地区之一。有许氏等盐商大户和盐务公所落户的高第街①高第街是广州著名的古老商业街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经历过数次繁华、萧条的转型。今天的高第街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接北京路,西连起义路,成为一条以内衣为主的服饰批发街道。高第街临街建筑保持骑楼风格,许氏家族的旧宅“许地”仍可以找到,现在整条街道内巷房屋全部被“改房成仓”并面临拆迁,各方多有呼吁保护这条著名老街的声音。作为当时广州南城的著名商业街区,有着联系主城区与珠江商贸区的地理优势。本文选取一批反映1794年至1849年高第街房地产交易情况的契约文书②本文所用契约为广州高第街许地许氏后人、现居香港的许子皓先生所藏,共计29份,始于乾隆五十九年,止于道光二十九年,均为高第街房地产契约文书。这批契约分为定帖2份,正式房产交易27份。本文所引契约尽量呈现文本的本来面目,契约中数字书写大小写并存、缺字现象皆系原文如此。,对其中涉及女性参与的七份案例进行分析,以期窥见清末时期广州城以寡母(寡妻)为主的一些妇女如何能动地参与男性主导的房地产交易,并在其中增强自身的经济权利。
一、女性担当卖房者身份
在分析寡居妇女社会地位时,我们既要看到她们所遵循的“夫死从子”的纲常,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社会“以长为尊”的“孝”文化。所谓“从子”更应从清律中“丧服制度”理解,而非理解成“绝对服从”。传统社会并非受到单一思想的影响,众多思想自有其先后逻辑,其中“长幼有序”的尊卑观优先于“夫死从子”的伦理观,这使得寡居妇女作为家庭的长辈,始终有着一定的地位。高第街这七份契约中,担当直接卖房者身份的妇女多是以寡居身份来处置家庭财产的。虽然身份为寡居女性,但是具体到每宗交易的实际情况,妇女主持处置家庭财产的方式又各有不同。根据掌握材料来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寡母携子同商”;二是“夫族长辈见证下寡妻主持”;三是“寡妻独自操办”。无论哪种情况,契约中的寡身妇女都承担着顶门立户的家庭责任,并且此类家庭结构在清末广州高第街区具有较高的认同程度。首先,“寡母携子同商”类的契约有一例:
(1)立明永远断卖房屋契人杨允中,系番禺县人氏,缘允中有自置房屋壹间,坐落大南门外高第街居仁坊,坐东向西,上盖连地壹间过,深一进半,活十七桁,前至街,后至旧临全馆,左至倪宅,右至张宅,墙心为界。兹因急用,母子商议情愿将此屋转卖与人,取要时价银四百两正,先召亲房人等,各不愿买,次凭中人何三引至许宜和堂,依口还足屋价银四百两正净元司码平兑。连签书洗业俱在其内。三面言明,两二家允肯,经于本年七月初二日书立定贴,杨允中亲手收到许宜和堂定银壹百两,标贴明白,订至七月初四日交易,兹届交易之期,允中又亲手收到许宜和堂屋价银三百两,连定银壹百两,共成四百两之数,即日书立永远断卖屋契一纸交与许宜和堂收执。此屋委系允中自置之业,与各房伯叔兄弟侄毫无干涉,亦非留尝业,又无重复典当债折加写等情,即日交与许宜和堂永远管业,任凭其拆卸起造,如有来历不明及别人争论,系卖主同中人理明,不干买主之事,其屋价银两委系允中亲手如数收足,并无低伪少欠,此
是明买明卖,两相情愿,今欲有凭,立明永远断卖契壹纸,并付上手红白契四纸,一并交执为照。
一实卖出高第街居仁坊,坐东向西屋一间,深一进半,活十七桁,前至街,后至旧临全馆,左至倪宅,右至张宅,墙心为界。
一实收到屋价银四百两正净元员司码平兑。
一实交出上手红白契四纸,付与许宜和堂收执,如有日后检出远年老契,作为废纸,合并批明。
中人何三
道光廿八年七月初四日
立明永远断卖房屋契人杨允中的笔
允中之母杨马氏指模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番禺县人杨允中与其母杨马氏在中人何三的牵线下,将一间“坐东向西,位于高第街居仁坊内,深一进半,活十七桁”的自置房屋卖于许宜和堂,卖价银四百两。此屋立帖交定金,再立帖结全款,流程较为正规。由契约可知,此间房屋是杨允中之父离世后,“兹因急用”,“母子商议”之下,将此房屋出售。寡居母亲在这宗买卖交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儿子允中与母亲意见一致后才将此屋出售,落款也是由杨允中亲笔并同附母亲指模。
“无子寡母”或者“子幼寡母”在处置家庭财产时的情况又略有不同。“有子寡母”处置承夫之产时可与其子商议,无须夫族长辈或族人见证,而“无子寡母”或者“子幼寡母”虽也有权处置夫产,但是在处理过程中需要顾及夫家族人的意见和颜面,情况更为复杂和微妙,例如下则契约:
(2)立断卖铺屋契人倪袁氏,今因急用,有自名下受分铺屋壹所,坐落新城高第街居仁坊口,坐北朝南,深壹进,正铺屋阔七桁,楼上阔十五桁,前至官街,后至章宅,左至远芳鞋店,右至高元登笔店,神楼、户扇,瓦面俱全,问明亲族,均不愿承买,今凭中出卖于王姓,议定价银足重番面银捌拾两,即日当中,番银铺屋两相交清,并无短少,亦无债折抵偿。此系自相情愿,明买明卖,亲族人等,日后不得另有别议。此铺屋系袁氏家公于嘉庆四年十二月买沈同人大屋,于十年三月拆大屋改造小屋二十四间,铺屋一间,袁氏于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经亲族长分受养口,并无来历不明,所有上手原契现存长房收执,作为废纸,恐后无凭,立此为据。一批实收到铺屋价银捌拾两正。一批此铺屋并无另有税契,即后有税契亦作废纸论。
见中伯公倪珏,亲伯倪廷纶,沈何氏
嘉庆拾贰年陆月初五日
倪袁氏的笔
这份契约文书签于嘉庆十二年,是倪袁氏经家中伯公以及沈何氏为中人介绍,将自名下受分铺屋一所卖与王姓人家。此房坐北朝南,深壹进,正铺屋阔七桁,楼上阔十五桁,坐落新城高第街中心地段居仁坊口。倪袁氏这间房屋是袁氏家公于嘉庆四年十二月从沈同人之处购得的一间大屋,又于嘉庆十年将大屋拆改成二十四间小屋和一间铺室,后倪袁氏于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经亲族长分得部分屋产以养家糊口,来历清晰可查。此处倪袁氏所承房屋是娘家袁氏配分的产业,即使如此,倪袁氏在处置这批房地产时,也需要在夫家亲伯等人的见证下完成交易,以避人口舌。故而契约中强调“亲族人等,日后不得另有别议”。
妇女独立主持家庭大宗财产交易的例子不多,尤其是以寡妇身份处置遗夫财产,一般需要先征求夫家长辈的意见,并要在其见证下完成交易。而高第街倪陶氏在其主持的两宗出售故夫遗屋的契约中,展现了少有的妇女独立处置家族大宗交易的一面:
(3)立明永远断卖房屋契文人倪陶氏,系绍兴府上虞县人氏,缘氏故夫倪衡斋遗有经分名下房屋一所,坐落高第街中约居仁坊内,西向,上盖连地,平排两间过,共阔叁拾贰桁,深叁进,前至自开之街,后至旧临全省馆,右至濠,左至许府,墙心为界,另屋前食井壹口,均在契内,氏于上年因楷弟三婿同往饶平县游幕,今年春间,氏在饶平寄信回省,嘱胞侄倪国安、婿胡椿龄将此屋出帐,召人承买,信内写明取实价银壹仟零伍拾两,另胞侄国安签书银壹佰两,如即时有人买受,即先行代立定贴,接收定银,倪氏于秋间返省交易,如买主急于改造,则于立定之后,先行出屋,任其拆卸等语。倪国安、胡椿龄于接信后,先召房亲人等,各不愿买,次凭中人赵昌、全石泉引至许宜和堂依口还足屋价银壹仟零伍拾两。另胞侄倪国安签书银壹佰两番面成元司码平兑,即于五月廿四日倪
国安、胡椿龄亲手代收定价银壹佰伍拾两,由胞侄亲笔代立定帖,其余屋价银壹仟零伍拾两,签书银壹佰两由许府立交银单交国安收,俟倪陶氏回省立契交清。因许府正须兴工建造,即于二月初六日出屋,任从许府拆卸,兹氏于九月十九日回省,择吉于九月廿日立契交易,由许府将应我屋价银壹仟零伍拾两,签书银壹佰两,凭单兑交,氏手收用,由氏面嘱胞侄国安代写断卖文契,交许府收执,即日银契两相交易清楚,惟此屋上手红契前于道光十三年月间因氏夫倪衡斋与王三槐堂争讼将契呈堂,尚存番禺县署,并无领回,是以不能交付。今经转卖。另立此契赴县报换投税为据,其缴存县署之上手红契,将来毋论何人领出,均作为废纸。倘有人执持上手红契藉端向许府索诈者,由氏与国安自行理明,与许府无涉。至此屋委系氏故夫经分名下之业,与别房叔侄兄弟无干,亦非留祭尝产,并无重复典买等弊情,现系明买明卖,亦无债折等情,其屋前食井亦归许府之业,自立定之后,业经许府将此屋拆清改造,如有来历不明及别人争论,均系卖主同中人理明,不干买主之事,三面言明,两家允肯。今欲有凭,特立永远断卖契一纸交付许府收执为据。
一倪陶氏亲手收足应我屋价银壹仟零伍拾两,先日国安代收定银壹佰伍拾两,亦经交回氏手收讫。
一实卖居仁坊房屋壹间,平排两间过,深叁进。
一胞侄国安签书银壹佰两,亦经国安手收讫,验价银壹仟壹佰伍拾两正。
在场见议人王行庄
中人赵昌、全石泉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廿日立
永远断卖屋契人倪陶氏代笔胞侄倪国安的笔
(4)立明永远断卖房屋连街文契人倪陶氏,系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缘氏故夫倪衡斋有经分名下房屋四间,坐落高第街中,约居仁坊,西向,平排三间,内二间深一进半,共阔廿八桁,又一间深五尺五寸,阔廿一桁,前至本坊街,后至许宅,左至和生藤席店,右至许宅,其东向一间,深一进,阔九桁,前至本坊街,右至永生鞋店,左至隔壁,另有屋上楼一座,楼阁下另有小地一叚。因氏夫在日,借与别人,今自卖之后,任从买主取回改造,统计四间,上盖连地,并本坊街道由本屋地叚起至本坊街尾止,查本坊之街系氏故翁从前将大屋改造小屋,自行开造之街,其初原无别家房屋在本坊之内,嗣氏翁将各屋分与各房伯叔子侄,其后由各房伯叔子侄陆续分卖与人,始有别姓居住,惟现在别姓分卖本坊各屋,先经卖与许府承买,而倪陶氏名下之屋,现因急用出账,凭中人王竹庄说合亦卖与许府,依口还足屋价连街道共银捌佰两正成元司平。所有签书洗业酒席,一应在内,至居仁坊内之屋,既尽归许府承买清楚,则居仁坊之街亦应听从许府任意相造,契内合并声明,三面言明,二家允肯,当即写立定帖标贴明白,兹于本月十九日立契交易,由倪陶氏亲女王倪氏代笔写契,即日银契两交清讫,此屋委系倪陶氏故夫经分名下之业,与伯叔兄弟侄无涉,亦非烝尝祭产,并无重典重卖及债折等情,如有来历不明或别人争认,系卖主同中理明,不干受主之事,至氏尚有各房夫侄及侄孙数人皆系无赖之徒,向来各管各业,毫无干涉,无庸预名签书。倘有争执,由倪陶氏自行理论明白。自卖之后任从许府拆卸平地,任意起造,特立永远断卖文契一纸交许府收执为据。再此屋本由大屋改造,仅有大屋红契一纸,因经分以后,本坊房屋陆续卖与别人,且年代已久,其红契早已遗失,合并声明,将来如有人拾得,作为废纸,特此批明。
一实收到许府屋价银捌佰两正成元司平,由倪陶氏亲收。
一实卖出高第街中约居仁坊内房屋四间,另有地一小叚,连本坊街道在内。
一批明倪陶氏未择继立嗣,故以长女王倪氏代笔书契。
此系倪陶氏之女王倪氏照此底稿摹写卖契,原稿底存倪陶氏,所写大吉昌三字,另行摹写,不是原稿,特此注明,以备日后稽查。
中人王竹庄
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十九日立
断卖文契人倪陶氏立大吉昌
代笔女王倪氏
契约(3)、(4)均是由倪陶氏主张房屋出售所留下的记录。倪陶氏,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她的丈夫
倪衡斋已经离世,她所出售的房屋均是故夫留给她的遗产,但其所出售房屋的情况比较特殊,产权关系较为复杂。
首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所立的契约,是在倪陶氏不在场的情况下委托他人所立。这年所交易的房屋在高第街中约居仁坊内,西向,共阔三十二桁,深三进,另屋前食井一口,均在契内。倪陶氏在道光二十七年离乡出游,而在道光二十八年的春季时节,写信给家乡的侄子倪国安及女婿胡椿龄,委托他们将故夫倪衡斋的房子出售,写明卖价一千零五十两,交代其侄可以先收定银一百两,并立定银契约,待她秋季回乡再继续交易,还细致到如果买家着急,可以交了定金后便拆屋改造。倪国安和胡椿龄于接信后便立即着手此事,在中人赵昌、全石泉的牵引下,以银一千零五十两卖于许宜和堂,并于五月二十四日代收定价银一百五十两,由胞侄亲笔代立定帖,其余房款候倪陶氏回省立契交清。倪陶氏于九月十九日回省,并在九月廿一日完成交易。但是此屋上一手红契因为道光十三年与王三槐堂有所争议而存放在番禺县署,故在契约中有所说明。
在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十九日的这纸契约中,倪陶氏又将其故夫倪衡斋名下的四间房屋售出。这四间房屋坐落高第街居仁坊内,西向,平排三间,其东向一间,另有屋上楼一座,楼阁下另有小地一段。居仁坊自所售屋起到本坊街尾都是倪氏先翁由大间房屋所改,分于各房居住,后又各自买卖。这四间房屋于倪衡斋在世时借与他人居住,倪陶氏因急用出账,在中人王竹庄说合下,将房屋收回出售,再次卖给许府,以银八百两正成元司平成交。但是这份契约并非是原稿,而是倪陶氏的长女王倪氏代笔的摹写稿,写有大吉昌以便区分。
可以看出,此两份契约中所涉及的五间屋子,都是倪衡斋的妻子倪陶氏全权做主出售的,即使倪陶氏远在外地,也可以书信指挥乡中亲友帮其完成买卖事宜的前期工作,而重要的立契和结款事宜还是由其亲自接手处理。从倪氏占据居仁坊不少房屋的情况来看,倪氏也是规模不小的家族。倪陶氏在夫亡后,以寡居身份出游,并在她“未择继立嗣”的情况下,主持家中大事。倪陶氏的行为完全出于一家之主的身份,其故夫家族于她而言,是“各房夫侄及侄孙数人……向来各管各业,毫无干涉,无庸预名签书。倘有争执,由倪陶氏自行理论明白”。可见高第街区对于寡居妇女在经济活动中地位的接受程度。
综合以上契约来看,直接在经济交易中担当卖房者身份的女性有“杨允中其母”“倪袁氏”和“倪陶氏”。“杨允中其母马氏”虽非以独立身份处置家庭资产,但在交易过程中她的意见对杨允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契文中有其指模说明了寡母在处置家庭大宗交易时的参与程度。“倪袁氏”基本上能够主张自家房屋的出售,但是鉴于男权家庭寡母身份的尴尬,倪袁氏出售房屋需要有倪氏伯公的见证。倪陶氏是这批契约中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得以充分展现的代表。倪陶氏故夫倪衡斋留给她不少房产,她在没有他人干预的情况下,主张将这些房产依次出售。第一次是在她于外省出游时,一封家书便可委派胞侄、女婿按照其预想的价格和步骤将房屋出售,要求先收定金,待她半年后回乡再亲自收齐尾款,可见她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威望。倪国安等人也是完全按照她的要求去完成这次房屋的出卖事宜。第二次,她亲自操持将倪衡斋生前暂借于他人使用的四间房屋出售,在没有倪氏家族人员参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这次大宗交易,其长女代笔立契,原契亲自保留,细致到临摹契约一份并做好标注,处事比较周全独到。
可见,高第街妇女的确能够较大程度地参与家庭财产交易的经济活动。但“杨氏之母”要与儿子同商共议,“倪袁氏”交易需要在倪氏族人的参与和见证下完成等情况也说明,一方面“男尊女卑”、“男主女次”的传统思想依旧对当时社会有着深刻影响,使得妇女在孤寡的情况下才有支撑门户的可能;另一方面,社会舆论也使得妇女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夫家其他男性进行自家的财产处置。不过这种情况并非绝对,以高第街倪陶氏两次极为独立的出售案例来看,高第街对寡居妇女在家庭中担任主要角色并执行“家长”权力处置家庭财产的现象给予了一定的认可,这应与高第街特殊的商业环境不无关联。
二、女性担当买房者身份
阿风在统计契约文书中的女性参与者时强调:“相对于如此多的女性卖主而言,女性买主却十分少
见。”[1](P97)道光十八年十月初八日的一份契约则反映了这类少有的情况:
(5)立断卖屋契人番禺豹蔚堂赵,今因急用拮据,愿将承父自置遗下房屋壹间,坐落大南门外高第街居仁坊内,向西入巷第四间,深两进两间过,共计阔瓦面三拾贰桁,此屋上盖连地,瓦面、地基、神楼、板帐、门窗、户扇、井灶、门口、街石、砖瓦,木石,一并俱全。至因拮据急用,先召房亲人等,各不愿买,是凭中人出账,召人承买,要到时价银伍佰两正,凭中人王氏执帐引至秀杰堂盛府甘氏,三面言明,二家允肯,依口还足屋价银伍佰两正成元司码平兑,交收其屋价银伍佰两正,系豹蔚堂赵生桥亲手收迄,其屋就即十月初八日立契卖与秀杰堂盛府甘氏买受永远业,银屋交易,两相交讫,无得异言。此系明买明卖,并无债折等情,亦无重典重当,亦无兄弟分产等情,所有屋四至丈尺分明,自墙为界,南至左邻张宅,北至右邻陈宅,前通看墙为界,屋后宅四至自墙为界,亦无官租地税之纳。如有来历不明,不关买主之事,系赵生桥理明,同中人追究,不能多生事端,亦无异言,一卖永断。恐后无凭,立明契交执存据,并红契一纸,上手契一纸,如有契纸冒留,是为故纸。
一实收到卖屋价银伍佰两正。
中人王氏
道光十捌年十月初八日立
断卖契赵星桥的笔立
契约买卖双方为豹蔚堂赵星桥与秀杰堂盛府甘氏,中人为王氏。《广东碑刻集》光孝寺重修碑记中有载:“盛秀杰堂捐银一十二两一钱。”[2](P20)可见,秀杰堂是盛氏家族的产业,那么盛府甘氏则应是名为盛甘氏的寡居妇女。契约中的房屋是赵星桥继承于父亲,坐落在大南门外高第街居仁坊内,向西入巷第四间,大小为两间深两间过,共三十二桁,屋内所有设置一切均归买方盛府甘氏,盛府出价五百两。
为何多有妇女参与、出售家庭大宗财产的案例,而鲜有寡居妇女购置大宗资产的现象呢?从现实环境来看,“明清中国妇女寡妻者多而且时间长是不争的事实”[3](P56)。“受夫权、父权、皇权控制的汉族妇女,……她们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4](P266)可见,大部分妇女在古代传统社会基本很难从社会生产中获取财产收入,一旦失去家庭男性这个主要劳动力,无子或者子幼的“守志寡妻”生活便很容易出现问题。在非固定资产不足以保证基本生存的情况下,出售故夫遗产成为换取生活所需的唯一办法。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夫为妻纲”的男权社会十分强调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权和对财产的支配权、继承权,一般只在男性离世或者长期外出不归的情况下,妇女才有机会以夫姓顶门立户。即便如此,其在处置家产时还需要顾及夫家长辈、兄弟甚至子侄的意见。寡居妇女生活存在巨大的压力和负担,夫族在人情道义上为了解决寡居妇女及其子女的生计问题,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认可寡居妇女处置故夫遗产的行为,但往往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并在其见证和监督下完成。
由此可见,古代传统社会中,妇女只有在失去家庭男性家长且“无子”或“子幼”的契机下,才能靠“以长为尊”孝文化的支撑担当起家长的角色并行使权力。即便如此,寡妻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还是受到了夫族和社会舆论的制约和束缚。出于生存的需要,寡妻出售故夫遗屋的现象比较普遍,也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寡妻主张购置房产的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基本生存考虑,一方面寡居妇女本身生存能力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寡居妇女如果出现此类行径,在没有特殊原因说明的情况下,会被夫家当作是她擅作主张侵犯了亡夫财产甚至是夫家尊严。但就此类行为本身而言,寡居妇女能够克服较大的生存压力,突破夫权、父权等男性主宰社会意识的束缚,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支配经济的行为折射出女性在经济领域和独立人格上愈发提升的能动性空间,其实质是对伦理教条下男权社会生活体制的挑战。
以契约中的房产交易来看,“杨氏其母”“倪袁氏”二人是将自家的房产折换成现银而并非挥霍自家的财产,卖因皆为急用,因此更易为家族和社会的接受。以寡母或者寡妻身份主持资本消费,以钱财去购买地产或房产的大宗交易所体现的则是妇女在家庭活动中具有的决定地位和支配权力。契约(5)中,“秀杰堂盛府甘氏”用五百两银购入赵宅房屋的记载则证明高第街妇女已具有决定大宗交易的权力。
三、女性担当第三方身份
妇女在经济活动中除了担当交易中“买方”与
“卖方”的直接关系人外,还有第三方身份,具体有“买卖参与者”“中人”以及“代笔人”等。立于乾隆六十年五月十六日的这份契约,即是妇女以参与者的第三方身份出现在家庭经济活动中:
(6)立明断卖屋契人谭门麦氏,自置房屋一间,坐落高第街中约广司厅左便巷内,西向,深一大进半,阔十五桁,四围墙壁、板樟、砖石、木料、瓦,门扇上盖连地,一应俱全,四至分明,左至郑宅,右至杨宅,前至巷通街,后至朱。今因急用,夫妻姐弟商议,愿将自置业屋一间出卖与人,先召亲房人等,各不愿买,次凭中人问至周宅,取要价银番面银肆拾伍大员,当中收足重,签书洗业,一应在价内,三面言明,二家允肯,就日当中写立契约,交清银两,系麦氏夫妻亲手接回应用,并无少欠分厘,亦不是债折等情,亦无重叠典按,如有来历不明,系卖主同中理明,与买主无涉。自交银契之后,毋得异言,今欲有凭,立此断卖屋契一纸,并上手契一张,交与周永成收执为照。一实收到屋价银肆拾伍大元,夫妻亲接回应用,重叁拾贰两肆钱正。一实退出高第街一间,深一大进半,西向,门至通街见交银。
中人麦卿口伍祥
代笔中人麦瑞英
乾隆六十年五月十六日立
卖断屋契人谭门麦氏指模
契约所载是由谭门麦氏经中人麦卿口和伍祥搭线,以银番面银四十五大元卖与周宅的一宗交易。此房是麦氏自置房屋,但因急用,由麦氏夫妻姐弟共同商议之后决定卖出,可见夫妻之间有着较为平等的地位,妻子有一定参与、处理家庭大事的权力。同时,麦氏与兄弟姐妹之间也比较团结,家庭成员共同参与讨论,其姐作为一名家庭成员,也以文字形式将其意见呈现在契约之上,能够看出麦氏之妻以及其姐在其家庭生活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家务参与权。最后交易所得钱银也是由夫妻二人共同亲手接收,说明麦氏之妻有权处理家庭的经济财产。
一份交易之所以能够立契成交,是因为交易双方或多方能够对交易本身达成意向。交易之初,买方或卖方的意向是不关联的,这就需要第三方“中介人”牵线搭桥以促使彼此意向的契合。同时,交易意向促成后,还需要在“中保人”的见证下完成交易,以避免纠纷。《二刻拍案惊奇》载有宋绍兴年间的一则熟人间的交易故事:“你我虽是相好,产业交关,少不得立个文书,也要用着个中人才使得。”[5](P209)即便是彼此熟识的亲友,立契交易也要有所谓的第三方“中人”参与,可见“中人”已经成为立契的一项重要因素。嘉庆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许拜庭③许拜庭(1772-1846),名赓飏,字美瑞,号拜庭,广州著名盐商,高第街许地许氏家族的创始人。和倪双玉伯侄所立的三份契约便是妇女担任“中人”的例子,因三份契约除了在房屋格局以及交易价格的表述上略有不同,其余格式和内容均一致,故将三份契约整合如下:
(7)立明断卖屋契人倪双玉仝侄廷纶、廷森、廷栋、廷经,今有先年兄弟同置房屋壹所。坐在新城高第街中,约南向,平排五间,各深五进,每阔十七桁,后地一叚,前至街,后至濠,左至 宅,右至 宅,四至明白,上盖连地,门窗、户扇、砖瓦、木石俱全/坐在新城内高第街中约,南向,平排二间,每深五进,各阔十七桁,前至街,后至濠,左至 宅,右至 宅,四至明白/坐在新城内高第街新胜里内,东向平排八间,内三间,各深二进半,阔各十五桁。前至街,后至宅,左至濠,右至宅,四至明白。上盖连地,门窗、户扇、神楼、板帐、砖瓦、木石俱全。
今因凑用,伯侄商议愿将此屋出帐,召人承买。先召房亲人等,各不愿买。次凭中人引至许拜廷兄承买。
一实还到屋价银九百两番面成元司码/一实还到屋价银六百二十两番面成元司码/一实还到屋价银九百两番面成元司码。
签书酒席在内,三面言定,二家允肯,先经下定标贴明白,今卜吉日立写卖屋契,银屋两相交易,其银系双玉与姪亲手照数兑收,并无短少。其屋听从许宅改造,永远管业。此屋实系双玉兄弟同置之屋,并非尝产,与房族兄弟无涉,亦无重典按。倘有来历不明,别人争论,均系双玉伯姪同中理明,不干许宅之事。今欲有凭,立明断卖屋契一纸,并付上手红契一纸,一并交执为照。
一实卖出高第街屋壹所,深阔列前/一实卖出
高第街屋二间,深阔列前/一实卖出新胜里巷内屋捌间,深阔列前。
一实双玉、廷纶等亲手接到卖屋价银九百两番面成元司码/一实双玉、廷纶亲手接到卖屋价银六百二十两番面成元司码/一实双玉、廷纶亲手接到屋价银九百两成元司码。
中保人倪卢氏
中保人代笔凌自培
仝卖屋男松龄
仝卖屋孙积福
嘉庆拾叁年四月二十八日
立明断卖屋契人倪双玉、廷栋、廷纶、廷森、廷经
此契约的落款处写有“中保人倪卢氏”,可知作为妇女的倪卢氏是见证这场交易的保证人之一,以便日后产生不必要纠纷时可以出来佐证。而契约(2)记有:“见中伯公倪珏,亲伯倪廷纶,沈何氏。”倪珏、倪廷纶是倪袁氏的夫家长辈,作为这宗交易的中人自不必说,沈何氏以外姓担当这份契约的中人,既起着牵线搭桥的介绍作用,又有见证担保之职,可见其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
除了“中人”外,还有一类第三方身份。契约(4)记有:“一批明倪陶氏未择继立嗣,故嗣改以长女王倪氏代笔书契。此系倪陶氏之女倪王氏照此底稿摹写卖契,原稿底存倪陶氏,所写大吉昌三字,另行摹写,不是原稿,特此注明,以备日后稽查。……代笔女王倪氏。”可知,倪陶氏未立子继嗣,选长女王倪氏代笔书契约。其女王倪氏虽非这份契约的主立人,但是作为家中长女,她以已嫁女的身份代母书契,用当今的观点看,女儿王倪氏是其母的法定代笔人,有权参与到家庭的大宗交易活动中。
四、妇女参与高地街区经济活动的特点
“妇女出卖土地等财产在明清时代已经是一种被认可(包括国家与宗族)的行为……不仅仅在徽州……其他地区……在明清时代地权变动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妇女也已经参与到土地买卖中来。”[6](P81)通过对这批契约中妇女参与经济活动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清末广州南城高第街区妇女的确可以参与土地、房屋类的家庭大宗交易。妇女能够独立担当买、卖主体的角色或者以其他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彰显了她们的家庭权利以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默许和承认。
(一)妇女以主体地位处置家庭财产的权利被承认
以契约(3)、(4)中的倪陶氏为例,她首次交易故夫遗产是在游历他乡之时,只凭一纸信函便可委命其侄、婿按照她的计划去执行交易步骤,且关键的立契环节和结款环节皆在她回乡之后完成,比起对夫家男性的请求,其性质更似对夫家男性的远程指挥。第二次交易则是倪陶氏完全独立地处置故夫遗产,没有任何夫族男性参与到这次交易中来。从倪陶氏的两则例子中能够发现,高第街区的妇女在丈夫去世后不仅可以有着非常自由的生存环境,对于故夫遗产的处置也不必太过顾虑所谓夫族的意见。《大清律例》明文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7](P199)倪陶氏“饶平县游幕”是否符合“守志贞妇”的情况已经很难说清,又“未择继立嗣”,且认为“各房夫侄及侄孙数人皆系无赖之徒,向来各管各业,毫无干涉,无庸预名签书。倘有争执,由倪陶氏自行理论明白”。可见贞洁守志、立子继嗣、夫家为主这三个妇女继承亡夫遗产的要素倪陶氏都不甚符合,但她却能够在夫家认同或忽视夫家意见的情况下完成处置故夫遗产的一系列行为,倪陶氏可谓实现妇女执掌家庭财产的一则典型案例。同时,结合盛甘氏掷五百两购置一处房产,以独立的寡妻身份主持家庭大宗交易等案例,说明高第街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承认。
(二)妇女参与土地买卖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特点
广州高第街妇女参与家庭财产交易的程度不仅较高,其在经济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也非常多元。七份契约提及并参与的女性共有“谭门麦氏夫妻及其姐弟”“倪袁氏及中人沈何氏”“中保人沈何氏”“杨允中其母”“倪陶氏与其代笔亲女王倪氏”几位。虽然只有七则案例可供分析,但一份正规房产交易契中所应涉及的关系个体基本齐全,即卖方(含参与者)、买方、中人(介绍人和证明人)以及起草人等。以中人为例,作为促成交易完成的载体,首先要求“中人”有一定的经济意识和广泛的信息渠道,这是作为经济中
介的基本要求。同时能够作为土地房产等大宗交易的见证人,其本身亦需要一定的资信地位。“中人在契约中最明显的作用是缔约双方之间的中介、见证……同时起到调解人的作用和一种平衡作用……中人的参与实际上已成为缔约时的一种必要程序。”[8](P139,141)可以说,中人是传统社会契约成立的一个必要成分,能够让妇女担任“中人”一职,执行中介和中保的功能,本身便说明清朝末期在广州高第街等商业活动区域,妇女已经具有了些许经济活动意识,能够走出家庭,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而其他第三方角色,如“杨氏母子同商”的例子证明“长幼有序”的尊卑观在传统社会的确是先于“夫死从子”的礼教观,即妇女作为尊长时所具有的家庭地位是不可忽视和回避的事实;“谭门麦氏之妻姐”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共同参与到处置财产的商讨中,这是妇女家庭地位提升的表现;“王倪氏”以家中已出嫁长女的身份为母亲倪陶氏的代笔立契,体现了非长辈的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参与到家庭经济活动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事实证明,妇女已经不单纯以“生存需要”为目的,通过买、卖这样直接的形式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而是开始以不同的身份和方式广泛地参与到家庭生活和经济活动当中,并且所担当的责任和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多元。
(三)妇女处置财产权利的不充分性
虽然高第街的妇女能够参与到经济活动的多个方面,并且参与的程度比较高,但我们还是不能过分强调或夸大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她们能够发挥的主动性。从七份契约中的案例来看,除了谭门麦氏之妻与其丈夫一起参与房产的出售外,其他担当立契人的妇女始终未能跳出以寡居身份对家庭财产进行处置的前提。“纵观服制诸图,可以发现五服制度所确定的亲属等级关系……都是以男性血缘关系为枢纽兼及姻亲而建立。”[9](P88)自明律伊始,五服制度所建立的伦理教义正式入律,几千年来的伦理观念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礼’已作为‘法’”[6](P88),深深植根于社会大众的心中。以财产的来源来看,寡妻所置财产多是家族、故夫遗留下来或是夫妻共同奋斗攒下的家业。“如果丈夫去世,无子寡妻“合承夫分”,这是基于“夫妇共财制”,寡妻行使“存命者权”(right of survivorship),……而有子寡妻则形成“母子共财关系。”[1](P12)契约中多见“承夫”“遗有”等字样,可以说妇女所能主动处置的资产多是被动继承的,几乎看不到此时期未婚妇女或者已婚人妻的独立经济权。可见妇女在处置这些被动拥有的资产时,其主动性是有条件的。“妻为夫族服图”所展示的是男性为尊的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所掌控的大部分主动权利都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因此,考察妇女在传统社会的地位以及权力,不可跳出妇女主动性并不充分的背景,即过分强调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只有通过考察妇女参与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动性的方式和程度,才能较为真实和客观地分析妇女在一个被动和从属社会环境下,提升自身地位和发挥自身能力的过程,从而窥见传统社会妇女地位的全貌。
五、结论
岭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边陲之地,自古受中央王朝的控制较松,在意识形态上受到的教化也不如北方中原地区和帝都周边严格。伴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成为经济发达且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此过程中,北方移民不断流入,同时海上航路的兴盛加强了与南洋诸国的交流,奠定了其比较自由和包容的文化。
清朝中后期,广州曾一度成为清王朝唯一对外通商的口岸,加之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渗透,广州④“广州”有交广分治之意,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治所番禺是广州城的前称。文中所指广州在当时谓之“省城”。作为一个兼容南北又融汇东西的商业城市,本身有其特殊性。而南城高第街所处的地理位置同样有其特殊之处。广州城的城市形态因明嘉靖四十二年增筑南城而大体确定下来,后又于清朝“加筑南城并于顺治四年由总督佟养甲将南城东西两翼加筑延伸到海边。即今外城东西临海二城也”[10](P148)。当时广州城主要分内城和南城,内城为城市行政中心,多为行政衙署和军营,南城为商业区。随着清代珠江沿岸的不断发展,南城作为连接内城和沿江商业区的枢纽之地,城门数量极多,共有12道作为连接内城与江边商业区的通
道,依靠发达的城市水系成为广州城商业发达的区域。高第街便位于在南城的中央地带,毗临重要水道玉带濠。清中后期,盐务公所坐落于高第街区,使得这片区域成为广州盐业贸易的中心,许拜庭、李念德以及潘仕成等著名的盐商都与这里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高第街是一条非常商业化的街区。高第街只是清中后期广州众多商业街道中的一条,这批存于许氏后人之手的29份契约,其中虽然只有9份涉及到了妇女参与房地产买卖的案例,已经较为丰富和全面的展现了妇女在大宗交易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可以想见广州城乃至珠三角地区对于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认同程度。已有学者指出:“寡居长辈女性主持买卖土地在清代珠三角已是一种被国家和地方社会认可的行为。”[11](P58)
总之,清朝中后期,进步的社会经济、地权的频繁变更和广州地区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赋予妇女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夫权至上的束缚,使其在家庭经济活动中拥有了更积极的能动性。一些生活在高第街的妇女以实际参与行动证明了她们在家庭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能担任更多元的角色,在处置家庭财产时也拥有一定的主动权,但社会大秩序还是以男性为尊,妇女的主动权是有条件限制的。然而,妇女参与到家庭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以契约文书为载体,用一种比较规范和具有普遍社会认同的书面材料保留下来,意味着妇女已参与到土地等大宗不动产的交易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1]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谭棣华.广东碑刻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
[4]沈海梅.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5]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6]阿风.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土地买卖中的权力与地位[J].历史研究,2000,(1).
[7]沈之奇.大清律辑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8]李祝环.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中人现象[J].法学研究,1997,(6).
[9]郑秦.十八世纪中国亲属法的基本概念[J].比较法研究,2000,(1).
[10]史澄等.番禺县志(全)[M].台北:成文出版社,1956.
[11]刘正刚,杜云南.清代珠三角契约文书反映的妇女地位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4).
责任编辑:绘山
ZHANG Qi-long1XU Zhe2
(1.2.School of Literatur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Guangdong Province,China)
Qing dynasty;Gaodijie in Guangzhou;contracts;women
As an old commercial street in Guangzhou,the Gaodijie gathered a large number of salt merchants in the mid-late Qing Dynasty.In a batch of contracts sign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flected buying and selling situation of the estate,there are some records about women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By analysis on the contents of the contract,the wom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amily transaction as"the buyer","the seller"and"the intermediary",and had very high status in society,which reflected that,in a certain extent,the initiative of women's economic consciousnes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ystem male dominated.
D442.9
:A
:1004-2563(2015)02-0096-10
1.张启龙(1987-),男,暨南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史、文化史。2.徐哲(1989-),女,暨南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