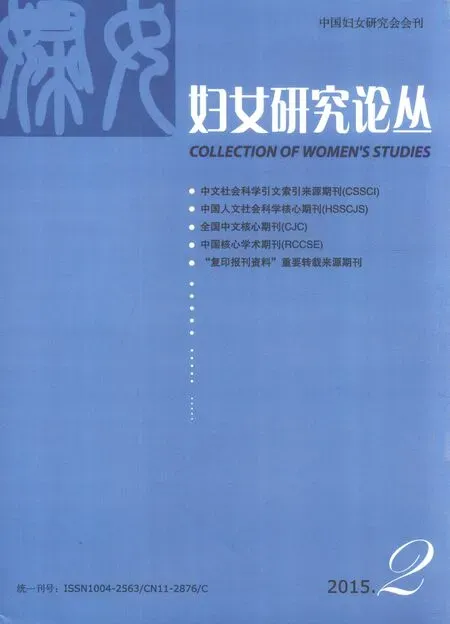《反家庭暴力法》亟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对《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分析
周安平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反家庭暴力法》亟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对《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分析
周安平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家庭暴力;反家暴法;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家庭暴力的界定,不在于是否共同生活,也不在于是否近亲属,而在于是否存在亲密关系,以及这种亲密关系是否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家庭暴力由于具有持续性和控制性的特点,因而对于伤害后果的法律要求,不能同于一般暴力对于伤害后果的要求。家庭暴力案件中的不告不理原则、调解原则未考虑到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制约了反家庭暴力的有效性,同理,其举证责任的分配也应该有别于一般暴力。关于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法律应当规定可以单独申请、其执行措施应当具有现实性,应当禁止双向保护裁定,对当事人应当称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应当赋予被申请人的救济权利。此外,《反家暴法(草案)》还存在立法的矛盾、重复和非规范性的问题,需进一步完善。
最近,中国首个《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已制定完成,并进入公开征集意见的阶段。《反家庭暴力法(草案)》虽然有所创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倘若得不到及时补正,一旦正式出台,则不免陷于被动。本
文就相关议题进行探讨。
一、家庭暴力的界定及范围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家庭暴力从成员关系来看可以析解为两类:一类是配偶、父母、子女之间,一类是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之间。前一类似无争议,但后一类则存在很大问题。根据条款,后一类可归为家庭暴力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共同生活,一是近亲属,且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换言之,如果是近亲属,但不共同生活,或者虽然共同生活,但不是近亲属,即排除在家庭暴力的范围之外。据此,是近亲属,但不共同生活的祖孙、兄弟姐妹等,如果发生暴力均以一般暴力对待。而如果不是近亲属,但有共同生活的,如同居关系,具体而言如婚前同居关系、婚外同居关系、同性恋同居关系以及雇主与保姆等诸如此类的亲密关系,如果他们之间发生暴力,均不被视为家庭暴力,而作为一般暴力对待。此外,恋爱关系,则既不属于亲属关系,也没有共同生活,更是排除在家庭暴力之外。笔者以为,《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失误在于受传统家庭认识的束缚,而没有从性质上将家庭暴力与一般暴力区别开来。
家庭暴力与一般暴力的不同,关键不在于是否共同生活,也不在于是不是近亲属,而在于是否存在亲密关系。何为“亲密关系”?“亲密”一词在英文中为“intimacy”,解释为:亲密、亲昵、关系密切或者性行为,词源来自拉丁文“intimates”(与……熟悉)和“intimus”(最深处)。其词源表达了亲密关系既是一种熟悉的关系,又是人类最深处的情感,具有隐私性和情感性。情感构成了亲密关系核心内容,只要情感的交融能达到亲密的程度就可以称作亲密关系,并不要求利益上的“亲密”。亲密关系具有情感性、私密性和自治性的特点,从而决定了亲密关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1]。
家庭成员就是一种典型的亲密关系,以家庭关系为例可以很好地说明亲密关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多的是借助于彼此的生物性情感而得以维系,亲属间的利他性伦理原则是亲情的一种自然流露,私人化、情感化是家庭的主要特征。在家庭中不需要程序的技术设计,也不需要实体的正义规则,家庭成员当中的权利与义务并不像(甚至有时不需要)法律规定的那样泾渭分明。亲族之间的纠纷及其他有关家庭的事件,从自古以来的淳风美俗和特有的家庭制度上看,以道义为本用温情来解决是最理想的[2](PP63-64)。因此,“法在亲友之间是不活跃的”,亲属之间的“爱”可以包容一切,在家庭领域中谈论平等与正义似乎是多余。但在一般社会关系中,特别是在陌生人社会中,则是一个工具性联合体。在陌生人之间,对法的要求也最多①此为美国行为主义法学家唐纳德·布莱克的观点,参见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下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848页。。这种动辄诉诸法律和外力的援助,在一般社会关系中常见的做法,却在亲密关系中并不常见,究其原因,一是情感性降低了对于正义的需求,二是将亲密关系诉诸法律或外力的举动容易招致负面的道德指责。正因此,发生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与发生在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暴力具有实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导致了法律态度的不同,即不能将发生于亲密关系的暴力与一般社会成员的暴力作同等对待,否则,发生于亲密关系之间的暴力很难获得法律救济。因此,对家庭暴力的界定不在于其成员是不是近亲属,是不是共同生活,关键在于成员与成员之间是不是存在亲密关系。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扩大家庭形式的外延,将各种亲密关系的伴侣纳入家庭的范畴之中,就成为各国学者之共识,并为各国法律所实践。威斯就认为,“家庭”与其他社会组织在形式上的区别并不明显,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性质可能才是区分家庭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暴力的关键[4]。这种关系可以是夫妻,也可以是其他有同居生活的亲密关系。英国皇家警察督察提供的定义为“曾经或现在有亲密关系的伴侣之间发生的身体、性、情感或经济方面的伤害行为”[4]。美国律师协会全国家庭暴力委员会就认为“当一方亲密伴侣使用暴力、胁迫、威胁、恐吓、隔绝孤立
以及情感、性和经济暴力谋求保持对另一个亲密伴侣的权力控制时,即发生家庭暴力”[4]。印度尼西亚《关于消除家庭暴力的法律》(2004年第23号法律)则将家庭暴力扩展到了家庭雇工[5]。巴西Maria da Penha《女权保护法》(2006)第5条包括了在“家庭单位”中实施的暴力,即在共享的永久性空间中犯下的暴力,无论是否有家庭纽带[5]。澳大利亚联邦法律改革委员会则认为“家庭暴力系指一成年人对另一人(两人为已婚配偶或有事实上的恋爱关系)犯下的实际的或威胁的暴力行为”[4]。显然,这种“家庭”概念的外延也就延伸到了“非法定家庭的形式”但有亲密关系的共同生活的伴侣之间。
如果借鉴这些国家的立法例,那么,非家庭成员关系,如婚前同居关系、婚外同居关系、同性恋同居关系以及雇主与保姆等诸如此类的亲密关系,均可纳入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的保护。不过,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婚前同居关系、婚外同居关系、同性恋同居关系均系非法关系,理不应受法律保护。笔者以为,这种理解有失偏颇的。非法的同居关系,法律不保护的只是其婚姻关系,或者说法律不以婚姻关系来看待和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法律也置若罔闻。只要他们之间形成了亲密关系,而以一般暴力当不足以提供法律保护,自然可以视为家庭暴力。正如劳动法不保护妓女的工作,但并不表明法律不保护妓女的人身安全。同样,对于雇主与保姆之间发生的暴力,也可能会有人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工作关系,当可以按一般暴力对待。笔者以为,是按一般暴力对待,还是按家庭暴力对待,标准仍然是看他们之间是否形成了亲密关系。
问题是,亲密关系又该如何认定?这个问题其实关涉认定家庭暴力的另一个参照标准,即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亲密关系之所以难以获得一般法律之保护,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亲密关系容易导致成员之间形成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种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极大地增加了被控制人诉诸法律的困难,因而削弱了被控制人诉诸法律的信心。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与暴力的发生往往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这种“控制”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暴力类型。因此,在认定家庭暴力时,既必须注意到成员之间是否具有亲密关系,还必须注意到,这种亲密关系是否形成了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经济上、精神上以及情感上去判断,如果一方在经济上、精神或情感上依赖于另一方,或者不能摆脱另一方,就表明他们存在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只要他们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并且这种亲密关系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发生的暴力就可视为家庭暴力,而不必要求他们必须是共同生活,也不要求他们必须是近亲属。
二、家庭暴力的法律后果
将家庭暴力与一般暴力区别开来,其目的就在于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相对于一般暴力受害者更有效的法律保护。如果法律对于家庭暴力受害者与一般暴力受害者提供同等的保护,即从实体上与程序上并无不同,那么,将家庭暴力单独予以立法,除了有政治宣传的意义外,并没有多少法律规范的意义。
法律对于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与对施害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第三十七条规定加害者的法律责任有:(1)行政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2)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显然,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表明,家庭暴力的施害者与一般暴力的施害者的法律责任是一样的,除了重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的有关内容外,并没有实际内容。
以刑事责任为例,根据刑法规定,可以对应家庭暴力的犯罪行为除了虐待罪外,其他行为均作一般暴力犯罪处理。而根据刑法规定,一般犯罪对于危害后果特别重视,它往往是量刑的重要指标。将犯罪后果作为一般暴力犯罪的量刑指标,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作为家庭暴力犯罪的量刑指标,则忽视了家庭暴力犯罪的特点。家庭暴力的发生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暴力,从时间上看就在于家庭暴力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加拿大学者安拉利丝·艾科恩(Annalise Acorn)针对家庭暴力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提出了“虐待行为累积效应”的概念。她说:“一个行为,在一个平等、互相尊重的非暴力关系中,妻子可能会将其视为完全无害的,而在一个虐待关系中,就会成为一种极富威胁和伤害性的举动。在一个平等和相
互尊重的夫妻关系中,用拳头重击桌子可能只被视为失望感的暂时发泄,而在经常存在虐待关系的家庭中,它会被看作严重的暴力威胁和丈夫恐吓对方加强自己暴君式的一家之主地位的企图。”[6](PP160-161)关于家庭暴力,笔者在拙著《性别与法律》一书中指出,孤立来看,其中某一特定行为一般都未达到犯罪的程度,隔离、恐吓、威胁、指责等一系列行为在一般暴力的概念中均无立身之处,即使是人身伤害,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伤害后果,法律也不要求行为者承担责任。这是因为法律假设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自主能力以抵制他人的此种侵犯。然而,家庭暴力则不然,在家庭中,存在大量的不同种类的行为,虽然单个看,均无多大影响,但这些行为彼此间可以相互增强影响的效果,而使受害人产生持久性的精神恐惧,并且由于家庭领域的相对封闭和经济生活上的从属而使得这一恐惧得以放大性的增强[7](P156)。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律师似乎只是关注构成人身侵害指控的一记耳光或某个重拳。他们根本不考虑一次拳打脚踢或推搡前前后后的那些侮辱、恐吓、性侵犯、隔离行为。如果把这些都考虑进去,就会发现,它比一次孤立的拳打脚踢恶劣得多”[6](PP160-161)。正是基于对“虐待行为累积效应”的认识,加拿大安大略省1999年度联合委员会关于家庭暴力的定义就规定:“家庭暴力可能仅包括单一的一种虐待。它也可能包括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孤立地看很细小或很琐碎,但是整体来看,他们构成了一种虐待。”[8]可能正是“虐待行为累积效应”的理论支持,加拿大的法律并不区分最轻微的接触和更严重的侵害,任何程度的违背相互信任意愿的接触都可以定罪[8]。非常遗憾的是,加拿大这样的规定在中国刑法中和目前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并未有所体现。而如果法律对家庭暴力构成要件与一般暴力的要件的规定相同,那么,家庭暴力单独立法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当然,《反家庭暴力法》不是刑法,也不是诉讼法,它无权改变刑法的规定。问题是,家庭暴力与一般暴力的法律责任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不同,那么,《反家庭暴力法》的法律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三、家庭暴力的司法程序
当然,如果家庭暴力与一般暴力只是法律要件相同,但在司法程序上有所不同,那么,家庭暴力与一般暴力在法律上仍然能有所区别。不过,这一点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也没有多少新的体现,只是重复立法,再次宣示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及“可以进行调解”的规定。
1.关于“不告不理”的问题
“不告不理”原则将起诉的权利交给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表面上看起来,受害人具有主动权,但考虑到受害人与加害人可能存在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受害人可能出于非真实意愿的原因而放弃起诉,从而变相地鼓励了暴力关系的延续。基于此考虑,《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第二十条规定:“受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与情感性,或许起诉人还应该拓宽范围才是。对此,有学者提出,反家庭暴力法作为对弱者利益的保护,也应当属于公共利益。因此,“在反家暴立法中,中国应当明确规定反家暴公益诉讼机制,扩大家暴案件的原告范围,赋予妇联、公益法律组织、检察机关以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提起反家暴公益诉讼”[9]。但遗憾的是,《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只是规定:“受害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未代为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告诉。”这极大地缩减了家庭暴力获得公益诉讼救济的可能。
2.关于“可以进行调解”的问题
“可以进行调解”的原则与“不告不理”的原则一样,也忽视了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能起到有效救济的作用。由于受害人长期的受虐经历,已经对施暴人产生了持久性的恐惧心理,调解双方并不具有平等的商谈能力,特别是由于家庭与社会的伦理规则不同,前者在很大程度可以宽容暴力,因而调解者的努力方向主要是“调和”。而在“调和”目的的支配下,调解人与施暴人容易自觉与不自觉地结成同盟,其最终结果往往以受害人的退让和妥协而结束,妥协的结果是进一步维持和延续了暴力的关系。调解只是应用于私人领域的规则,并不能作为解决人权侵害的手段[7](P173)。正如长期从事司法实践的一位检察官所指出的,家庭暴力案件可能因为双方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而不适用调解,调解可能是某些人威胁受暴人妥协的结果[10]。有学
者更是直接明确地提出,调解不能作为解决家庭暴力的规则[11](PP84-86)。
3.关于举证责任的问题
无论是刑事自诉,还是民事诉讼,都涉及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按规定刑事自诉与民诉都得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由于家庭暴力的私密性和控制性,使得家庭暴力的举证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我们知道,“谁主张,谁举证”是建立在举证能力大致相当的基础上,当两者举证能力不对等时,法律得做出举证责任倒置的安排以平衡双方举证能力不对等的关系。由于家庭暴力延续的往往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受害者的举证能力在被控制中被减弱或丧失,因此,在处理家庭暴力的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有学者认为,只要受害者能提供一些“家庭暴力”的基础性证据,能够证明当事人之间很可能存在家庭暴力行为,而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否认或无证据推翻受害者的主张,即可推定家庭暴力事实存在。基础性证据类型比较广泛,包括伤情照片、身体伤痕、证人证言、被告书写的不再施暴的保证书、报警记录、社会团体的相关记录纪录或证明、病历、录音录像、短消息、网络聊天记录,等等。此外,家属提供的证据也是重点考察的范围。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部分程度上有利于解决一些家庭暴力受害者举证难的问题[12]。也有人认为,原告就其与被告发生纠纷的事实及损害结果负举证责任,被告否认的,应就原告系第三人伤害或自伤的负举证责任,被告举证不能的,由其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10]。
学者的上述合理意见,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第二十三条得到了部分体现,“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不过,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如何谓之“合理”,这并不明确;二是法官是否有权不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三是《反家庭暴力法》是否可以制定有关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定。这种直接修改民诉法关于举证责任的举动,与前面提到的顺从刑法关于家庭暴力后果的法律要求做法相反,即《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在家庭暴力后果上保持了立法的谦抑,却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扩张,这在逻辑上很难解释得通。
四、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说到《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亮点,当首推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规定。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在草案中,相比于其他许多仅具有宣示意义的条款而言,最具有实际意义和规范意义。但是,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仍然存在以下不可小视的问题:
1.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依附性问题
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只是依附于离婚、赡养、抚养、收养、继承等民事诉讼,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是因为上述诉讼,便不可以单独提起人身安全保护的司法请求,因此,受害人所抱有的不想离婚,而只是想约束加害者暴力行为的愿望就不可以实现,尽管这样的愿望是非常合理且有广泛代表性的。正如李明舜教授指出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最不合理的一条是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一定要依附于其他诉讼,“应该让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作为一个独立的解决家暴的方法,而不是必须依附诉讼才能执行”[13]。
2.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执行问题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中的部分内容因客观条件所限并不具实际操作性。如“责令加害人迁出受害人住所”,如果被申请者与申请人仅有一个共同住处,要执行就不太可能[12]。并且,“禁止加害人接近受害人”必须由公安机关来执行才有效,而警务工作并无这项内容,凭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无法保障工作的常态化。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发出之后,如果被申请人未履行或未能履行,申请人是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如何强制执行?这些都是《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未能明确的。“适用法律最为急迫的目的还在于维持该系统的可信度”[14](P108)。法律失信远比法无规定所带来的后果更令人不安。
3.双向人身保护裁定的问题
在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申请上存在这样一种情形,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申请,另一方当事人以同样遭受了对方的暴力为由,也要求法院做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对于这种情形,是分别做出裁定,还是一并做出裁定?分别做出的裁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裁定,即给原告和被告各发一个裁定令。一并做出的裁定,是在一个裁定中同时针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做出的裁
定。这两种情形都可以称之为双向保护裁定。双向保护裁定是否可以,这在理论上存有争议。一般认为,原则上法院应避免做出双向保护裁定,因为,双向保护裁定对真正的受害人有着不良影响,加剧受害人孤独无助的受害心理。双向保护裁定之禁止,要求法院在裁定时必须判断清楚谁是真正的加害人,谁是真正的受害人。但是遗憾的是,《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并未明确禁止双向保护裁定。
4.当事人的称谓问题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申请人往往是受害人,但从诉讼的角度来看,他只是声称受害的人,并非一定就是实际上的受害人。同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被申请人往往是加害人,但从诉讼的角度来看,他/她也只是申请人声称为加害的人,并非一定就是实际上的加害人,至多是加害嫌疑人而已,正如,在刑事审判前,没有罪犯之称谓,只有犯罪嫌疑人之说是一样的道理。因此,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诉讼中,不可以有受害人与加害人之称谓,而只能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称谓。但是,《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直接以加害人和受害人的称谓来指称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显然有失公平和严谨,不利于保护真正的受害人。
5.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问题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既然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加害人,那么,人身安全保护令也就存在滥用的可能。由于《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是将人身安全保护令依附于其他诉讼上,申请人就有可能为达到离婚、侵占财产等目的而滥用申请,通过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给被申请人制造阻力,从而在诉讼中占据主动,置被申请人于不利地位。促成此种可能的原因还法院必须在48小时之内做出裁定,无法保证查清事实,并且基于保护弱者利益的立场表达,法官往往会倾向于支持声称受害的申请人。因此,为避免申请人滥用而致被申请人于不利地位,法律在规定申请人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权利的同时,还应当规定,如果因申请人的滥用,导致被申请人损失的,应当赔偿被申请人的损失,同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对滥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予以民事制裁。对此,《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有所遗漏,缺乏对被申请人权利的司法救济。
五、立法技术问题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矛盾、重复和非规范性的问题。
1.关于立法的矛盾问题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与《婚姻法》密切相关,许多内容都是两部法规调整的对象。但是,仔细分析两部法规,发现一些相关内容,或存在矛盾,或表述不一致(见表1)。

表1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与《婚姻法》不一致处对比
法规之间不一致甚至矛盾,是立法之硬伤,其危害在于导致当事人无所适从,同时也为责任人逃避责任提供了规范理由。
2.关于立法的重复问题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有许多内容与其他法规的内容存在重复(见表2)。

表2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与其他法规重复内容对比
第1、第2项是重复表述其他法规的内容,第3、第4、第5项则是重申其他法规的内容。无论是重复还是重申,其弊端是浪费立法资源,还可能导致公众误解。当然,“重申”的问题不只是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有,许多法规都存在这种现象,在最后的“法律责任”一章中,大都会重申一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尾巴式”的重复立法,有三个可以质疑的问题:(1)倘若无此“重申”,是不是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2)从法规关系来讲,是不是刑法得听令其他法规的调遣?(3)法规中最后的“法律责任”对应的法条只是部分法条,是否可以推论,其他没有被对应的法条就不存在法律责任之说?笔者以为,这也是《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许多法条具有非规范性问题的一个原因。
3.关于立法的非规范性问题
除了重复立法外,《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许多条款只具有宣示意义,并不具有操作性,规范性程度较低。除了关于原则规定的条款外,还明显具有非规范性,或规范性弱的条文(见表3)。

表3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非规范性条款

第八条 中小学校应当开展反家庭暴力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第九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应当将反家庭暴力工作纳入本系统的业务培训和统计。医疗机构应当对工作人员进行家庭暴力受害者诊疗、处置要求及常见心理行为问题的识别与转介等方面的培训和指导。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反家庭暴力预防工作,组织和支持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组织开展心理健康、家庭关系指导等服务。第十一条 各类调解组织应当及时调解家庭纠纷,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第十二条 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等场所应当对被判处刑罚或者被依法拘留、逮捕的家庭暴力加害人依法进行法制教育、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治。第十三条 有关单位、组织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和求助后,应当及时劝阻、调解,对加害人进行批评教育。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办理家庭暴力案件工作进行法律监督。
上述条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操作性低,缺乏评价性,并且也无相应责任。规范性低的条款降低了法律规范属性,削弱了法律的规范效力。如果一定要从积极方面去肯定的话,其意义也仅限于表明法律的态度,具有宣教的作用,但不具有规范的功能,这是《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一个突出的缺点。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从法条的内容来看,或可归属于婚姻家庭法,或可归属于刑法,或可归属于诉讼法,或可归属于律师法,或可归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或可归于行政法,给人以杂陈拼盘之感。这种拼盘式的立法模式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上述问题。我们期待《反家庭暴力法》正式通过时,上述问题能够得以解决。
[1]韩长安.亲密关系对国家法消解的原因、机理和结果分析[J].比较法研究,2008,(4).
[2][日]川岛武宜著,申政武等译.现代化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张学军.试论家庭暴力的概念、原因及救助[J].金陵法律评论(秋季卷),2001.
[4]黄列.家庭暴力: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上)[J].环球法律评论(春季号),2002.
[5]夏吟兰.家庭暴力概念中的主体范围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14,(5).
[6][加拿大]安拉利丝·艾科恩.家庭暴力与法律改革[A].刘伯红主编.女性权利——聚焦《婚姻法》[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7]周安平.性别与法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8][加拿大]李恩·汉森.加拿大家庭暴力的对策及其在中国的潜在适用性[A].刘伯红主编.女性权利——聚焦《婚姻法》[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9]徐卉.反家暴立法中的证据规则与公益诉讼机制[J].妇女研究论丛,2014,(5).
[10]陈本建.反家暴,我们走了有多远———“推动中国反家暴立法与实施研讨会暨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第三届年会”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2006,(1).
[11]陈敏.解决家庭暴力纠纷不适应调解[A].荣维毅,黄列主编.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国际视角与实证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陈苇,段伟伟.法院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情况为对象[J].河北法学,2012,(8).
[13]专家律师建议性暴力、同性恋间暴力纳入立法[E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Lawyer/content/2014-12/15/content_5886536.htm,访问日期:2014-12-22.
[14][美]迈克尔·瑞斯曼,高忠义、杨婉苓译.看不见的法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绘山
ZHOU An-ping
(Law School,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93 Jiangsu Province,China)
domestic violence;Law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protection order of one's safety
The defini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is not tied to whether people involved live together or they are related,but if they have intimate relationships,especially in which one is controlled by another.As domestic violence persists and involves controlling behaviour, the legal rulings in relation to the outcome of injuries from domestic violence cannot be the same as those in other types of violence.The existing approaches to domestic violence including non-interference,no reporting,and mediation hav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us,constr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ight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Likewise,the dis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present evidence should also be different from other types of violence.On the application of protection orders for one's safety,the law should decide that it can be applied individually,and enforced as the conditions require and to avoid two way protection orders.It is important to separate those to whom the protection order is applied from those who are protected,and providing those who are protected with rights to relief assistance.In addition,the draft of theLaw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still contains legal irregularities and repetition.
D923.9
:A
:1004-2563(2015)02-0049-08

周安平(1965-),男,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理学、法社会学以及性别与法律。
本文系本人主持的司法课题“网络舆论视野下司法公信力建设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SFB2004)之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