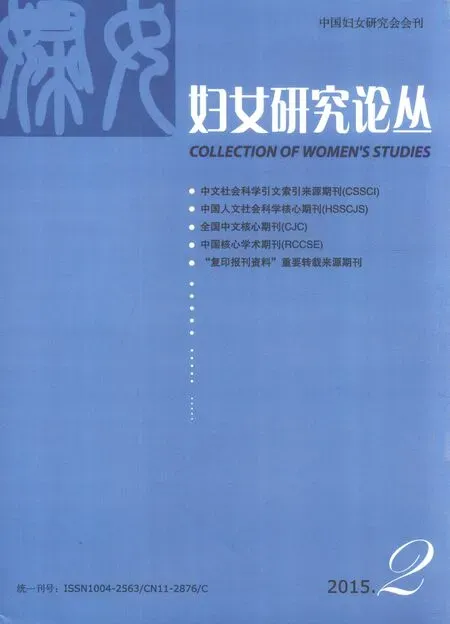“性别”抑或“性别体制”?:女性涉腐理论解释框架探析
宋少鹏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系,北京 100872)
“性别”抑或“性别体制”?:女性涉腐理论解释框架探析
宋少鹏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系,北京 100872)
性别体制;性别—腐败关系;女性清廉争论;性资本;性别化社会转型
文章基于中西方“性别与腐败”关系的研究,聚焦各项研究的解释性框架进行探究性分析,提出应该超越对“女性是不是更清廉”的判断,把问题意识转向探究“性别体制与腐败之关系”,询问在具体的政经制度、社会文化语境中,性别体制/性别秩序是如何影响两性对待腐败的态度和行动的。对于中国语境下女性参与腐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性资本”理论进行对话,提出“性别化的社会转型/性别化的市场社会+性别体制/性别秩序”的分析视角,作为探究女性/性别与腐败之关系的一个可能的路径和切入点。
腐败,国际上广为使用的定义是滥用公职谋取私利。中国《刑法》第八章定义了各类入罪的腐败行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1]。以“权”谋“私”是腐败的行为特征,所以,经典的腐败研究关注“权力”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而对“谋私者”的性别并不在意,从驱利的人性假定出发,假设“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面对腐败时的环境激励、行为动机是相同的。2000年,两份研究报告宣称女性是比男性更清
廉公正的性别[2][3]。2001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政策报告《赋予发展以社会性别: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发展》[4],采纳前述两份研究报告,并以此为据,把促进妇女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参与作为反腐的工具性策略,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从而引发了西方学界特别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历经十余年的争论,性别与腐败也成为一个学术议题。
性别与腐败关系的研究刚刚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笔者查阅中国知网,共发现两篇学术文章。其中一篇还是对西文文献的综述[5],真正基于中国语境的研究只有一篇,是汪琦、闵冬潮、陈密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4期的《性别与腐败——以中国为例》[6]。该文指出了“以性别—妇女为焦点的对腐败的媒体报导与对中国腐败的学术研究中性别忽视二者之间的空缺”[6](P6)。笔者深为认同这个批评。同时,笔者认为除了汪琦等指出的“媒体频频曝光并着意突出腐败中的女性”[6](P6),可能还要加上执政当局的关注。多年前,执政当局就已注意到腐败案中家属助贪的问题,除了告诫党员干部要管好“身边人”,一些地方纪委和妇联也开始大张旗鼓地推“廉内助”的活动。中共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铁腕治党、整顿吏治,腐败案曝光率剧增。2014年6月以来,中纪委对于违纪官员的通报中频现“与他人通奸”的字样。只因中纪委没有把权—色交易与一般性的情欲自由剥离开来,惹来僭越公私界限的质疑。为此,执政党用“党纪高于国法”为自己正名。但不管如何,政治公文中出现“通奸”字样,说明执政当局已意识到“性”“情人”与贪腐之间的纠结关系和直面它的决心。对于内嵌在腐败中的性与女性的角色和作用,相较于媒体报导民众关注的聚焦及执政当局的严阵以待,腐败研究和性别研究已显得严重滞后于现实了。所以,笔者希望追随汪琦和闵冬潮等前辈学者的呼吁,首先对已有的研究进行综述和分析,探讨相关的理论,为将来的实证研究做一些铺垫性的基础工作。
一、女性比男性更清廉?:西方关于“性别与腐败”关系的研究述评
1.性别特质视角:女性是更公平清廉的性别
千禧年前后,两个具有政策倾向的研究机构同时发布了两份研究报告,宣布同一个发现:在腐败问题上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相对男性表现出更不能容忍腐败的态度。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减少腐败,应更积极地促进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包括参与政府和参与经济活动[2][3]。安纳德·斯瓦米(Anand Swamy)研究小组1999年在马里兰大学的“体制改革和非正式部门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Informal Sector,IRIS)①由著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1990年在马里兰大学成立,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向公众报告了自己的研究发现,2001年正式发表论文。隶属于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The World Bank)的戴维·多拉尔(David Dollar)研究团队几乎同节奏公布了自己的研究发现。1999年报告面世,2001年正式发表论文。不清楚这两项研究是不是有意安排的互证式研究,但从研究成员的署名机构来看,都与世界银行有密切关系。事后,世界银行引用了这两份报告。
这两项研究的预设受西方行为主义研究的启发和影响。行为主义研究基于对个体行为的观察,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具利他主义和公德心。他们根据这些微观层面的研究发现形构了宏观层面上的假设:若一国政府中妇女参与率高,该国的腐败度就低。多拉尔小组利用跨国数据库进行国家层面的宏观比较,衡量各国腐败状况的数据来自于“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的腐败指数;另一个衡量指标“议会中妇女”,数据来自于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他们根据已有的腐败研究提炼出认为会影响腐败的因素,例如人口、公民自由、平均受教育程度、贸易开放度、族裔分裂度、殖民历史、宗教、法律渊源,作为需要控制的变量。利用统计学的多元回归分析,多拉尔小组发现:妇女在政府中的高参与与低腐败之间存在着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尽管作者为自己的乐观结论留了一个谨慎的口子:对两者关系的考察可能还有一些“未被观察到的变量”起着作用[2](P427)。
斯瓦米小组的研究更复杂一些,不仅使用微观层面的数据,也利用宏观层面的跨国数据;不仅考察妇女的政治参与率,也考察妇女的经济参与率与一国腐败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分。
第一部分,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包括1981年对18个国家的调查和1990-1991年对43个国家的调查。“价值观调查”有几百个子类,用于调查被访人对于各类不诚实和违法行为的接受度。该项研究选取各国男女在受贿方面的主观态度进行考察,即,对“执行职务时接受贿赂”的认同度。控制年龄、婚否、宗教这些被认为会影响个人行为的变量之后发现,77.3%的妇女、72.4%的男性同意这种行为“绝不认可”[3](P33)。这项数据隐含着另一个事实:1/5多的男性,认同腐败是正当的。数据显示,在对待腐败的态度方面,在绝大多数国家中都发现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在1991年的43个国家中,36个国家的女性比男性更不能接受腐败,其中24个国家的性别差异超过5%,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7个国家②这7个国家是意大利、尼日利亚、印度、韩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后两个国家的性别差异超过5%。的男性比女性更不能容忍腐败,其中只有2个国家的性别差异超过5%,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1981年的18个国家中,都显示出女性比男性更不容忍腐败,其中9个国家的性别差异具有5%以上的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据此,作者得出结论,对待腐败态度方面的性别差异看起来或多或少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3](P33)。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可能有人会认为女性更少支持腐败只是因为女性更少被雇佣、更少从腐败中受益,所以对待腐败的不同态度有可能只是反映了雇佣状态的性别差异。为了回应这种解释,斯瓦米小组控制“雇佣状态”这一变量后,发现性别差异更大了,男性更负面了。由此得出结论:对待腐败态度方面的性别差异与就业率中的男女差异之间的关联并非虚构,此结论也是呼应了该文对于妇女高经济参与与低腐败之间关系的结论。第二部分,斯瓦米小组利用1995年世界银行对于格鲁吉亚350个公司、2219名企业主和资深管理人员(男性1717名、女性502名)行贿情况的调查数据。在控制所有权性质、规模、业务范围、运营区域等企业因素以及被访者受教育程度这些被认为可能影响行动者行贿意愿的因素之后发现,男性业主和管理者比女性业主和管理者更愿意行贿,行贿概率在两倍以上(女4.6%vs.男12.5%)。作者认为,这说明在行贿方面也存在着性别差异。第三部分是宏观层面的跨国比较。与多拉尔小组的研究相比,斯瓦米小组的研究除了继续验证妇女参政与一国腐败的关系,还考察了妇女就业与一国腐败的关系。其腐败指数综合运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又称腐败感知指数)、世界银行考夫曼等(Kaufmann et al.,1999)设计的的渎职指数(Graft Index)、“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的腐败指数。控制被认为会影响个人行为的变量,如人均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宗教性质(天主教、穆斯林等)、前英国殖民地、殖民地历史、主流族裔占人口份额、政治自由等,妇女影响力变量析分为“议会中妇女”“政府中妇女”“妇女就业”。数据显示,妇女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率与一国腐败的水平成负相关。斯瓦米研究小组声称认同性别差异来自社会化,而非生物决定论,这就意味着妇女更不能容忍腐败的行为和道德倾向是由后天建构的,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种逻辑推演:越是性别平等的社会里,两性在对待腐败的态度与行为方面差异越小。事实上,斯瓦米小组在文中也引用犯罪学的研究发现来佐证这一逻辑推演:越是趋于性别平等,男女犯罪也会趋同。因此,斯瓦米小组没有把对待腐败方面的性别差异看作永恒现象,而是视为历史现象。但是他们认为,在中期来看,对待腐败的性别差异仍是存在的。因为即便在经合组织这些妇女高就业率的国家,对待腐败态度的性别差异现在也仍存在。为此,他们得出结论:推动妇女在政治和经济中的参与,在中短期方面仍可以用作反腐败的有效手段[3]。
2001年,世界银行发表的《赋予发展以社会性别》[4]吸收了多拉尔小组和斯瓦米小组的研究发现,并以此为据,认为促进性别平等,推动妇女更多地参与政治和经济领域③世界银行虽是以工具性的理由推动赋权妇女,但客观上是对妇女权利的背书和支持。那么,一个信奉新自由主义、致力于在全球推动经济自由主义的国际机构,为什么致力于推动女性权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与妇女到底是什么关系,给妇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有助于改善治理结构、减少腐
败,从而间接促进经济发展。世界银行把提高女性权利当作反腐利器,推销给发展中国家,是延续其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推行全球治理的手法。用妇女去稀释和清洁腐败政府,可以减少以监督和诉讼的方式惩治腐败带来的“痛苦、昂贵和有政治困难的过程”[7](P364)。更重要的是,按世界银行的逻辑,较低的腐败可以吸引较多的海外投资,带来经济增长,若性别平等可以降低腐败,各国政府就有动力去推动性别平等。世界银行这份报告的中文版④中文版译名是《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似乎没有译出Engendering Development——赋予发展以社会性别——的涵义,却道出了世界银行工具化性别平等以促进发展的真实意图。2002年就在中国出版了,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4]。
2.制度视角:否认妇女是更清廉的性别,自由民主体制抑制腐败
把女性参与作为反腐手段,经过媒体和NGO组织的广泛传播,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甚至被女政治家用来作为推动妇女参政的理由,以及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发展援助的附带要求[8]。与此同时,工具化地定位赋权妇女的功用也激起学界的广泛争议,激发学者运用各种数据库、各种研究方法不断地来验证这一结论。
哥伦比亚大学的宋洪恩(Hung-En Sung)是根本上否定这一研究设问的代表。他指出多拉尔小组和斯瓦米小组的研究存在方法论的问题:从微观层面的个人行为推断集合层面的结果,是跨层次进行因果推论;而且统计学上的相关性未必就是因果关系。宋洪恩提出以“更公平体系”(fairer system)替代多拉尔的“更公平性别”(fairer sex),来解释一国妇女的高参与与低腐败之间的相关性。宋洪恩认为,这两者之间夹着一个转换性的“未被观察到的变量”(多拉尔小组的隐忧)起着中介作用,这个中介变量即自由民主体制。自由民主体制既鼓励妇女的参与、提升妇女的参与率,同时也抑制权力的滥用、降低政府腐败,从而使妇女的高参与与低腐败之间建立了表象上的相关性。宋洪恩使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的妇女参政数据,与自由民主体制的三个变量(法治、出版自由、选举民主)之间进行统计学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当制度变量被控制时,妇女参与与低腐败之间的联系失去了显著性。所以,宋洪恩认为两者之间的联系“至少部分是假象”[9]。而在制度因素中,司法和出版自由(即,自由制度)对反腐的作用更明显,选举民主的作用最弱[9]。
2006年,伴随女性登上某些国家与政府首脑的位置,有媒体乐观地宣扬女性清洁政府的功能性作用,宋洪恩再次质疑“女性是更公平性别”的假设,重申制度视角,认为抑制腐败只能通过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来管住权力。若不改变制度结构,只是推进妇女参政,参政妇女也仍是部分精英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表,这种妇女解放既不会增进民主也不会改善治理。从理论上说,只要腐败的动机和机会在总体层面上不变,妇女参政引发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并不会改变腐败总体上盛行的现象。他甚至预测,若其他环境不变,只提性别平等,伴随参政妇女的增加,女性官员的腐败数量会增加,同时男性官员的腐败数量会减少[8](P140、143)。
当然,也有与宋洪恩的观点相左、支持多拉尔和斯瓦米结论的研究。丹尼尔·特瑞斯曼(Daniel Treisman)认为,虽然多拉尔和斯瓦米的推论逻辑尚有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根据他的研究,在控制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变量之后,妇女参政与低腐败之间的联系仍不能轻易消除。他使用的是2000年议会中妇女数、2001年妇女参与政府的人数与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发现两者存在着显著的统计学上的联系[10](P238)。
3.文化特性视角:具有性别平等文化的西方国家中的女性更清廉
同样来自世界银行的维维·阿拉塔丝(Vivi Alatas)研究小组选择使用实验研究方法来验证多拉尔小组和斯瓦米小组提出的“女性更清廉”的假设。实验研究可以观察个体的实际行为。多拉尔小组和斯瓦米小组的研究所利用的大数据,采集的是被访者的回答,判断的是被访者的主观态度。澳大利亚墨尔本、印度德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新加坡四地的四所大学的1326名(其中男性596名,占45%)三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了实验。根据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长期被认为是全球最
清廉的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被标识为最腐败的国家。阿拉塔丝小组选择样本时还有一个考量,他们认为,以前研究的样本大多来自于西方国家,所以研究结论可能只适用西方社会,他们特意选择澳大利亚之外的三个亚洲国家作为实验地,以此来验证自己的推测。实验设计成三方序贯博弈游戏(a three-person,sequential-move game),每次实验至少30名参与者,随机分配“公司”、“官员”、“公民”三个角色。第一步,扮演“公司”的参与者花费一定的交易成本找到正确的“官员”行贿。第二步,“官员”决定接不接受贿赂,并记录面对多少数额时愿意受贿。第三步,“公民”决定是否对贿赂双方实施惩罚,以及多少数额的代价愿意去惩罚贿赂行为,惩罚会减少被惩罚者的收入,但对于惩罚者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是一次有效博弈(one-shot game),惩罚贿赂双方的收益并不会回馈“公民”。由此,选择惩罚的行为动机不是经济刺激,而是道德激励。实验显示,只有澳大利亚妇女在三个方面都显示出比男性更不能容忍腐败的态度,而其他三个亚洲国家在三个方面都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只是在决定惩罚腐败时的金钱数额方面稍显性别差异。因此,阿拉塔丝小组认为对待腐败的性别差异可能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可能更多的是文化特性,即,西方国家的文化特性。为什么三个亚洲国家⑤阿拉塔丝在文章的第28和第31注释中提到了中国,认为在容忍腐败方面,中国不存在性别差异。对待腐败方面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该研究的解释是:相比于妇女更能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社会(当然是指西方国家),在更父权的社会里,妇女在公共领域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妇女对于社会议题的看法可能受男性影响的程度更高。该研究进行跨国比较发现,女性的跨国差异远远大于男性。对待腐败的三个方面,各国男性的态度和行为更趋同,只在惩罚腐败方面稍有不同,印度尼西亚男子选择惩罚的更多。四国的女性在三个方面的差异都很大。阿拉塔丝小组对此现象的解释是,相比于男性,不同社会女性社会角色的差异更大。对于把推动女性的公共参与作为反腐利器的政策建议,阿拉塔丝小组尽管没有直接反对,但认为应谨慎断言,特别是在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因为按阿拉塔丝的研究推论,该项政策只能运用于西方国家[11](PP663-680)。
4.性别体制视角:面对腐败机会和腐败网络没有性别差异,行为动机有差异
阿尔哈桑-阿罗(Namawu Alhassan-Alolo)选择使用问卷与访谈的调查研究方法,到该政策的实施地去验证增进女性参政、减少腐败的观点。阿尔哈桑-阿罗研究的背景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发布之后,增加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的参与作为反腐工具,成为发达国家向受资助的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一剂特效药。依据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被标识为高腐败国家。在发展项目的推动下,受资助国(包括乌干达,20世纪90年代以来乌干达在妇女参政方面的进步举世瞩目)采取了一系列增进妇女参政的积极政策。加纳也制定了促进妇女参政的配额制。阿尔哈桑-阿罗选择对加纳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研究。阿尔哈桑-阿罗根据犯罪学上的差别联结/机会区隔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and Opportunity theory,DAO)和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⑥差别联结/机会区隔理论假定,个人的行为和态度与所处的环境与接触的人和机会有关。所以,差别联结/机会区隔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在腐败网络里个人的腐败动机。社会角色理论认为社会期待影响着个人对于自己行为、他人行为的认知,个人的行为和态度受到社会期待的压力。,提出了三个假设:(1)面对腐败机会时,对待腐败的态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2)身陷腐败网络时,对待腐败的态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3)当社会期待把某些腐败行为视为道德义务时,对待腐败的态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阿尔哈桑-阿罗在加纳的警务和教育两个政府部门中抽取了135名公职人员(78名男性和57名女性),调查他们对虚拟情境里的贪污行为所持的态度。配合三个假设,设计了三个虚拟情境。第一个虚拟情境,办理护照部门的官员在极小风险下收受客户的礼物(腐败机会)。第二个情境,某政府机构的一群官员为弥补收入不足组成一个小团体,从客户处收取额外收益(腐败网络)。第三个情境,假定外交部主管被亲属要求利用她的影响为亲朋获得西方国家的旅行签证(社会义务)。研究显示,女性官员与男性官员在三个虚拟情
境下的态度,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阿尔哈桑-阿罗得出结论:若不限制腐败的机会和网络,妇女更多地加入公共领域并不会显示出更少腐败的行为倾向。同时,阿尔哈桑-阿罗的研究发现,两性在腐败的行为动机上有差异。针对第三个情境的访谈显示出,两性为自己行为的辩护理由是不一样的。男性官员把为亲朋徇私的理由归结为西方国家制造的不合理的签证困难。女性官员对自己行为动机的解释是其所面临的社会期待。女性更被期望照料家人和亲属,若违背了这一性别规范,会被视为“邪恶”和“铁石心肠”,恶名会被传播。据此,阿尔哈桑-阿罗得出结论:女性比男性更受性别规范压力的影响。阿尔哈桑-阿罗的研究强调性别体制对于女性个人行为动机的影响。对于把促进女性参政作为清洁政府之手段的政策建议,阿尔哈桑-阿罗提出了严肃的警告:以女性的道德优越作为前提假设、以反腐的工具性价值作为激励当局促进妇女参政的理由,隐含着潜在的政治风险。因为如果这项政策失败的话(阿尔哈桑-阿罗的经验研究并不支持这项政策),对于推动性别平等和性别主流化是不利的[12](PP227-237)。推动妇女参政应从权利出发,本身就应是值得追求的目的,而不应沦为手段[8][9][12](PP227-237)。
5.避险视角:性别不平等让女性比男性更遵从规则
埃萨雷和切里罗(Justin Esarey&Gina Chirillo)在以往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构设了自己的研究假设。阿拉塔丝及类似的研究基本上把妇女高参与与低腐败共存的现象限定在西方民主国家,而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显示出性别差异。宋洪恩提出了制度中介的解释,阿拉塔丝和阿尔哈桑-阿罗宽泛地讲都是在文化路径上解释此现象的区域差异。埃萨雷和切里罗试图把这些发现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整合性的验证,并提出一个统合性的解释框架。为此,他们的研究仍是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宏观比较。首先验证“腐败容忍度”与“政体”之间的关系。把“容忍腐败的性别差距”(gender gap in tolerance of bribes)作为因变量,把“制度化的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institutionalized democracy and autocracy)作为自变量。前者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2002);后者的政体分数(polity score)来自2010年的“政体特征与转型数据库”(Polity IV Project),并与“民主化指数”(Democratization Index of Vanhanen,2005)进行替换检验。控制性别歧视、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的变量后发现:在政体得分低的国家中,对待腐败方面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相反,在更民主的国家中男性显得比女性更能容忍腐败。第二部分考察妇女参政、制度化民主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共验证157个国家,10年的时间跨度(1998-2007年)。因变量是腐败。腐败指数选择世界银行治理数据库的控制腐败指数(World Bank Control of Corruption Index from the World Bank's Governance Indicators Dataset),利用透明国际、国家风险指南的腐败指数进行交叉验证。自变量是“妇女参政与体制化民主”。妇女参政数据来自各国议会联盟(2012),“制度化民主”根据政体分数衡量。作者根据政体分数把国家分成两个子类:零分以下的威权国家和零分以上的民主国家。发现,在威权国家中妇女参政与腐败没有相关性,但在民主国家中存在负相关性。埃萨雷和切时罗从外部刺激——两性对风险的不同反应——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女性对于外部环境的激励反应不同于男性,女性比男性更不愿担风险,有更强的激励去遵从既存规则。女性不愿担风险不是来自于天性,而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系统性歧视使女性处境相比于男子更脆弱,女性跻身政界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反之,违背规则更容易招致惩罚(例如更容易被指责、被排挤)。民主政体提供的是抑制腐败的激励,所以,在民主政体下女性相比男性对腐败更不能容忍,只是女性更遵守规则,而与女性的道德无关。威权体制下,更强调个人的忠诚、裙带关系,甚至腐败被视为治理的一部分,在这种政治文化下,女性卷入腐败同样只是因为遵从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女性贪污还是不贪污的行动激励,都只是为了巩固她在体制中的位置。由此出发来推断促进妇女参政作为反腐策略的有效性,埃萨雷和切时罗认为不同政治社会情境下的妇女参政对于反腐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录用方式会影响妇女在体制内的行为。在民主政体国家中,妇女整体上仍比男性拥有更少的机会和网络,女性进入政府可能在短期内会增进政府廉洁。但官员录用和晋升主要依据自上而下任命方式的威权政体,录用和晋升首先意味着新来者必须
首先被纳入既存的腐败体系,女性参政并不能带来清洁政府的作用。当然,埃萨雷和切里罗已注意到他们的结论不适用印度,印度是高民主得分的高腐败国家。在阿拉塔丝的实验研究中,印度在对待腐败方面也不存在性别差异。埃萨雷和切里罗对此的解释是“其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7]压过了民主体制提供的激励。
6.对各家解释框架之评析
综观以上各家研究,不管是借助大数据的跨国统计分析,还是微观层面的调查研究和实验方法,首先都是试图揭示性别与腐败是否存在联系,以及何种情境下存在联系,并提出自己的合理解释。假如认同这些研究的有效性,那么,组合这些互相对话的各家研究,大致可以拼合出关于性别与腐败关系的粗略图景:在对待腐败的态度和行为方面,西方民主国家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威权国家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相比于质性研究,量化的统计数据更需要研究者对数据注入解释,因为数据本身不会讲话。从某种程度上说,解释往往是外在于数据本身,相关性永远期待着因果关系的证成。先撇开对方法论的探讨,这些研究确实提供了多种视角和多样的解释框架,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剖析这些解释以及解释尚未明示的隐藏之义,为研究中国语境下的性别与腐败关系提供可供借鉴的合理视角和思考路径。
当多拉尔和斯瓦米提出性别与腐败关系的设问时,是试图从女性化的伦理道德中来解释女性更清廉的原因。宋洪恩拒绝性别与腐败关系的设问,认为是伪问题。对这两项研究最主要的批评和挑战都是指向女性具有“内在”的道德优势的研究假设。多拉尔和斯瓦米的研究确实对于生物决定论的立场很暧昧。多拉尔的研究只是引用了以往的行为主义研究结论,没有讨论女性的性别特质的来源。斯瓦米小组的研究尽管申明并不是从生物性来讨论女性的性别特质,而是从女性的社会角色出发,但结论部分还是暧昧地称女性化的道德特质到底来源于生物性还是社会性,“几十年的争论,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3](P52)。不管如何,就算多拉尔和斯瓦米的两项研究是从“文化”路径出发的,这种“文化”也是从“母亲”和“照料者”的社会角色推导出女性更具利他和公德心的道德倾向。母职路径就使女性的性别特质有了普适性,于是研究结论就有了普适应用的前景。
阿拉塔丝用“文化特性”来修正多拉尔和斯瓦米研究的“普适性”,把后者隐藏的性别本质主义特性反而彰显出来了。阿拉塔丝的“文化特性”是指西方的性别平等文化,性别越平等的(西方)社会,对待腐败的态度和行为的性别差异越大。按其逻辑,在更平等的性别文化中,女性能更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所以两性行为的差异显现出来,在压抑女性的父权制国家中女性追随男性,所以对待腐败问题表现不出性别差异。无疑此推论隐藏着性别本质主义。若按文化建构论推演,性别越平等,两性行为将更趋同,事实上,斯瓦米的研究也承认这一点。阿拉塔丝的比较视野恰恰把从女性内在性别特质出发的解释路径的逻辑困境彰显出来了。
阿尔哈桑-阿罗的文化路径的解释,不同于阿拉塔丝的“文化特性”解释。前者从外部社会规范的角度来解释行为动机的性别差异,极富有启发性的视角是从性别体制和性别规范的角度来解释女性官员从事腐败的行为动机。阿尔哈桑-阿罗拒绝普适性的内生的性别特质,而从地方性的性别规范出发来理解女性的行为。但是,“性别特质”与“性别规范”两种视角在女性参政能否促进政府清廉的问题上意见相反,事实上共享着一个基本假设:性别会影响腐败。只是多拉尔和斯瓦米小组寻找女性不贪污的内在道德动力,而阿尔哈桑-阿罗在寻找女性贪污的外部社会压力。或者说,前者关注性别特质(心理/道德特质),后者关注性别体制(社会制度)。另外,阿尔哈桑-阿罗的性别体制/性别规范的解释框架虽然来自于地方性研究,但也隐含着一种普适性解释:“恰是性别体制,曾经被用来证明女性倾向于更少腐败和更贴近公共,本身可能也是女性腐败的根源,因为女性努力要去履行她们的性别角色”[12](P227)。这句出现在文章摘要中的总结性解释,已包含了对西方国家女性更少腐败原因的解释。
埃萨雷和切里罗的“两性对于风险刺激的不同反应”是一种普适性解释框架,可以同时用来解释西方民主国家和非西方的威权国家的两种现象。隐藏在这一解释框架背后的一个假设是:不同政治性质的社会,实质共享着一个相似的社会性质,即,都是
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只是,埃萨雷和切里罗强调公共领域中的性别歧视,尽管他们也承认缺少对于不同社会中公共领域中性别歧视的程度、范围的了解。阿尔哈桑-阿罗展示的是私领域中的性别规范如何影响到了公领域中女性官员的行为选择。两者的解释框架都指向既存的性别体制/性别秩序与腐败的关系,而超越了“性别”——男性和女性——的比较视野。这是笔者在梳理和分析这些研究中逐渐意识到的,并深受启发。
综观这些研究,宋洪恩从制度视角出发,否认性别与腐败之间存在关联。除此之外,其他的研究不同程度地承认性别/性别体制会影响两性对待腐败的态度和行为。通过分析这些研究的解释框架,笔者认为应该超越对“女性是不是更清廉”的判断,而是把问题意识转向探究“性别体制与腐败之关系”,询问在具体的制度、社会文化语境中,性别体制/性别秩序是如何影响两性对待腐败的态度和行动。
二、对国内研究的述评及商榷
1.对“女性更清廉”的两派意见
国内的研究虽不多见,但都注意到了多拉尔和斯瓦米这两项研究及其经典假设。围绕“女性是否更清廉”国内学术上存在两种相左的意见。相比于大众舆论更愿意以“女祸论”推想女性参与腐败,学者似乎更愿意接受“女性更清廉”的预设。2013年,时春荣、程小佩发表综述性文,介绍多拉尔和斯瓦米的两项研究及宋洪恩的批评,作者明确表示斯瓦米和多拉尔的结论“不但成立,而且对各国的反腐败斗争和妇女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价值”[5]。就此逻辑,文章后半部的介绍就转向了妇女参政。2014年7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聂辉华、仝志辉撰写的反腐败研究报告分析了涉腐官员的性别分布。该报告收集整理了2000-2014年3月底所有公布的367个厅局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女性占全部厅级贪官的3%,其中,担任“一把手”职务的有219名(占大约60%),女性有3名,约占1%。对比2009年全国地厅级干部中女性比例为13.7%,报告认为相比于女性干部占全部干部的比例,女性干部腐败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13]。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因为女性相对谨慎保守,更害怕贪污受贿的风险,另外由于家庭分工的原因,女性腐败的机会相对较少”[13]。作者没有说明女性的“保守”是来自于“天性”还是“社会”;“家庭分工”与“女性腐败机会相对较少”实质也指向性别体制和性别秩序,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展开更细致的分析,这些极富洞见却又蜻蜓点水式的解释,可能是缘于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对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察,而非作者自觉的性别意识。有意思的是,该报告援引了斯瓦米“严谨的理论研究”[13](P15)以佐证自己的研究发现,看来作者是把“女性更清廉”作为女性干部贪污少的原因了。性别敏感的《中国妇女报》记者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亲女权主义的结论,尽管这份研究报告的主旨是讨论“一把手”腐败的问题——权力缺少监督的问题,性别与腐败关系的探讨只是报告中微不足道的副产品,内容不足一页纸。《中国妇女报》以《反腐败研究报告称:女性干部比男性更清廉》为题摘编了这部分内容。这篇文章也出现在中国推动性别平等的最高国家机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14]。
汪琦、闵冬潮、陈密对女性更清廉的观点持反对立场。她们收集2000-2013年以来媒体报导过的17个女性官员腐败的案例,发现这些女贪官同样集中在财政金融、国有企业高管、党政正副领导,政府土地基建项目负责人等腐败高发部门,认为“女性官员腐败案与男性官员腐败案的特征是一致的”[6]。“腐败的官员是男是女并无区别。在一个权力监督制衡至今仍然薄弱的制度环境下,握有实权的女人一样会滥用权力、堕落腐化。女性腐败案相对较少未必说明女人比男人廉洁,而毋宁说明了女人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6]这些女性贪腐的案例证明女性更公正清廉只是一种“神话”[6]。腐败容易发生在“一把手”,换言之,权力缺乏监督时容易产生腐败,这一点聂辉华、仝志辉与汪琦、闵冬潮、陈密两个研究在核心观点上并无差异。有意思的是,前者从参与腐败官员的性别数量差异得出女性更清廉的结论;后者根据腐败案的特征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客观地说,从方法论上这两项开拓性研究所提供的经验证据都不足于得出总括性结论,因为个案研究(特别是只根据已暴露的腐败案)根本无法推断出一个性别整体是否清廉的论断,就像宋洪恩所指出的微观层面的结论不能理所当然地推演到宏观层面。但正如笔者在分析西文文献中逐渐认识到的,我们无需纠结于“女
性是否更清廉”这个问题,而应把问题意识转移到性别体制对于两性腐败行为之影响的研究。
2.女性参与腐败的原因:性别体制
在性别与腐败之关系问题上,中国媒体和官方舆论透露出,中西方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焦点事实上是有所不同的。相比于西方学术首先预设女性比男性更有道德感,中国的主流舆论和文化氛围似乎更愿意把女性及女性贪婪默认为男性贪腐的推手。或许是受“女祸论”预设的引导,相比于西方关注“性别”之差异,中国似乎更关注“女性”参与腐败的问题,特别是家属助贪和情人参腐,嵌入在贪腐中的权—色交易更是吸引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汪琦、闵冬潮、陈密对中国语境下女性参与腐败问题进行学术回应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她们把参与腐败的女性分为三类:作为官员参与腐败、作为情妇参与腐败、作为家庭成员参与腐败。提出“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经济转型国家中女性参与腐败的原因。“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是指“因经济转型造成的资源向富人、男人、有权人流动的准无政府状态以及资源分配中有效控制的缺失”[6]。实质是指行动主体做出行动决策的外部制度环境。她们推论在“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环境中,“对女性政府官员来说,这意味着,她们惟一的机会可能在于,抓住一切违法机会,无论是什么,到流向男性贪官口袋里的经济资本和各种资源里分一杯羹。对大多数女人来说,性别歧视和女性就业市场的性化特征阻碍了她们拥有与男人一样的平等的职业发展和大致平等的致富机会。这使她们转移焦点,利用个人性的策略和女性魅力换取她们本该在就业市场获取而未能的经济收益。对她们来说,与男性贪官结盟是拥有舒适体面生活的捷径”[6]。对于后者,她们又提出“性资本”理论来解释女性在“权—性—钱交易”中的主体性。作者对“性资本”的界定是“个人在一个领域内以性为中介用来获取地位的资源、能力及禀赋”[6]。“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性资本”理论框架的优点是,联接起“被动接受腐败环境的影响与主动选择参与腐败行为二者之间的关联”[6],赋予女性以主体性,避免把女性视为被动牺牲者。同时,又把女性这种看似不正确的主体性归因于对女性不利的宏观环境——经济转型期中国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状况,从而避免了对参与腐败的女性的道德指责。尽管,笔者非常认同把个体行动者放入宏观制度环境中——考察个体与制度互动——的整合性研究视野,但是,“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性资本”的解释框架仍值得推敲,并有继续修正完善的空间。因为如果不引入讨论“性”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的社会环境,“性资本”这一看似中性的学术概念,仍有可能沦为学术版的“女祸论”。另外,“混乱”无法解释“转型”时资源为什么会向男性的富人、有权人集中?因为“混乱”也有可能使权力和财富向女性集中,而且“转型”的起点是一个号称相对均等和信仰男女平等的集体主义时期。所以“转型”过程发生的故事无法以“混乱”一词盖之。笔者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转型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性别化的社会结构。性别化的经济转型过程最典型的证据是,农村改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彰显男系家户的重要性、城市改革始于女工下岗。性别化的转型结果是,公私分离社会结构+再生产职能的私人化。“私人化”不是“个人化”,“私人化”是与家庭的私化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被推入家庭的再生产职能很大程度上由女性承担起来,父权文化下的性别分工服务于资本积累的欲望,造成绝大多数女性的结构性不利。如果说,性别化的经济转型可以部分解释女性经济上的不利地位,那么,还需要解释为什么在公开声称支持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暂时搁置消费主义文化下的性/性别观念的影响)的社会主义政权下,女性在政治领域也会处于边缘地位?性别化的转型是全方位的,而不仅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也包括权力结构的性别化转型,尽管在转型前中国,妇女参政的数量和权位都没有真正实现“半边天”,但是,“妇女”是一支国家承认的可见的政治力量,因为在集体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生产是最大的政治。作为集体的“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力量”和“伟大的人力资源”,被国家所承认,并体现在各级生产机构和国家政权中。她们中的优秀分子——劳模——成长为干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集体主义生产方式解体,逐步转向以“个人”为单位的市场经济。解除了“妇女”的经济基础,作为政治力量的“妇女”也无法存在了。在新的社会结构里,个体的“女性”将以何种方式重新集结成一种政治力量,那已是90年
代甚至21世纪的议题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遭遇到的“差额选举冲击波”——各个层级的女性领导数量的急剧下滑[15],实质上就是上层建筑的权力结构对经济基础变迁的反应。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妇女”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历史性的集体失落。当我们用“素质”——归责妇女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现象时,实质是用转型后的意识形态来合理化转型,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转型前社会。“去集体化”的过程中,集体主义时期——当“妇女”作为集体的力量存在体制内时——被抑制的个体的父权/男权因素很大程度上被释放出来。在权力重构的过程中,以个体身份进入政治领域的精英女性已然无法挽回“妇女”作为集体力量的失落,也无力对抗权力结构内集体性的男权力量。所以,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知识分子干部替代工农干部的阶级重构的过程中,已隐藏着性别权力的重构。现在,精英女性即便由配额制⑦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政治资源加上体制内国家女权主义力量的不懈推动,20世纪90年开始,妇女配额制(领导班子中至少一名女性)逐渐成为中组部、国家政策和法律中的刚性安排。若任由政治市场的自由竞争逻辑支配,估计女性在政治权力上的失势很难在短期内止住。助力,仍无法进入权力核心。女性干部不仅整体上数量少,在权力结构中也是正职少、副职多,多负责教科文卫等非重权性部门。所以,笔者提出,用“性别化的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替代“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能更清楚地展示权力和财富向男性集中、女性被排挤到社会/政治边缘、男性性别优势再造的历史过程。
汪琦、闵冬潮、陈密推论在混乱的转型过程中,财富和权力向男性集中,迫使失去了平等机会的女性“不择手段”地去瓜分本应属她们的财富和资源。这一推论似乎缺少了一个逻辑环节,自利的理性人假定也有以偏概全的嫌疑。环境再恶劣,绝大多数女性并不必然选择贪腐或使用性资本。即使对于参与腐败的女性来说,要突破既存旧规范——包括性贞操的女性性别规范和守法的政治规范也不容易,可能存在另一种激励机制支持此类行动。性交易古已有之,但“性”成为“资本”是转型后市场社会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历史产物。市场社会把交易原则渗透进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原本不属于市场的私人的性和公共的权力。当“交易”正当化、道德化,色—权交易和权—钱交易的道德压力就减弱了。这是部分女性使用“性资本”的外部社会环境,也是以权谋私盛行的社会环境。在反腐对策上,“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建设绝不可少,极为重要。但是,认识到正是市场社会激励了贪腐的欲望,而不仅仅是贪腐的机会,同样重要。认识这一点才能对新自由主义的反腐方案——进一步市场化,全面解除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权力——抱一种谨慎怀疑的态度。从性别与腐败的研究角度来看,分析“性资本”存在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性别化社会转型的结果是“性别化的市场社会”。女性的贪欲与男性的贪欲本质上是同一种社会环境制造出来的,在性别化的社会里,男性和女性只是在自己的社会位置和制度结构里,在各种甚至相互冲突的激励(比如使用性资本或遵守传统性道德)中,选择自己认可的合适的行为方式和路径追求自己的利益。
另外,“性资本”理论也存在解释效力的局限。性资本理论无法解释家人(特别是儿女)参与贪腐的原因,因为妻/女不需要用性资本与官员交换。就算夫妻关系中存在性资本的交换,如恩格斯早已批评过的资产阶级婚姻的财婚性质。但是,婚姻中的性契约订立于婚姻缔结之时。婚姻契约成立之后,家庭变成了一个受法律和伦理保护的利益共同体。家庭中的女性不再需要利用性资本去参与腐败。促使家人参与腐败的,是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家庭制度,妻子参与腐败恰是传统性别规范的作用。根深蒂固的家庭/家族传承的传统观念,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重新催生的私有观念相结合,才能解释为什么贪腐案往往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贪腐。只要家庭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就会有忠心耿耿的父母,为家庭努力累积财富,并确保私有财产世代传续。在环境纵容下,甚至不惜采取贪腐的方式快速敛财。从女性的角度看,当下的婚姻家庭制度和社会伦理基本上仍是鼓励和支持女性把自己的利益和命运维系在男性/家庭身上。参与贪腐的妻子/母亲往往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原谅,因为她只是爱家护
犊过了头的妻子或母亲,某种意义上是对女性必须要为子女谋利和为家庭牺牲的性别规范的背书。中纪委寄希望于贤内助反贪,估计是靠不住的。贤内助和贪内助本质上是同一的。顺从丈夫、奉献于家庭的传统性别观念加上市场私有观念,可能会加剧女性在贪腐中的作用。若只是把家人参与腐败的原因归于妻/母的贪婪——个人德性的缺失,很大程度上会遮蔽结构性的制度原因——性别体制与私有制度结合下产生的激励机制。
情人参腐与家人参腐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从所依附的男性官员的腐败行为中分享利益。区别只在于情人与家庭成员的制度性身份不同。前者只是基于性契约的利益共同体,不受法律保护和道德认可;后者是基于婚姻契约和儿女的血缘亲情建筑起来的利益共同体,受法律和道德的保护。腐败搭档配上情人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希望私人性的亲密关系为纯粹的脆弱的利益共同体增加一份情感联结和安全保障,如同家庭的利益共同体的牢固很大程度上依靠血缘。情人反目和家人反腐的动因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无非是曾经的利益共同体破裂了,记恨报复,一损俱损。家人参与腐败时,家庭是一个显在的制度背景,而人们聚焦情人参与腐败时往往只看到“个体”的情人,事实上很多贪官情人的背后同样存在着一个家庭。严格地讲,贪官的“通奸”甚至可能都没有挑战社会基本制度——婚姻契约和家庭制度。当由情人参与的腐败共同体产生的利益,源源不断向贪官家庭和情人家庭输送时,家庭作为利益共同体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贪官的通奸行为没有破坏婚姻家庭制度,而是在服务于这一制度。另外,男性贪官多情人和女性用“性资本”换取利益,性别等级和性别秩序更是一目了然。所以,笔者提出用“性别体制/性别秩序”来取代“性资本”理论,这样可以同时解释妻子和情人参与腐败的现象。
“性别体制”同样可以部分解释女性官员贪腐的原因。2015年3月12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首次发布了深圳市女性职务犯罪的基本情况,称近三年来(2012-2014年)女性职务犯罪呈上升态势(2012年9人、2013年18人、2014年27人),涉及贪污、受贿或挪用公款罪的比例较高。关于犯罪原因,报告总结了四个主要原因:从众心理、默认潜规则(“收人钱财为人帮忙、为人帮忙不能白帮忙”的社会规则)、“黑中介”利诱(被外界拉拢利诱)、攀比心理(消费欲望)[16]。前三个原因主要指腐败机会和腐败网络,与阿尔哈桑-阿罗对加纳公职人员贪污原因的分析很类似;第四个原因涉及消费主义文化对于女性气质的规训。按阿尔哈桑-阿罗的研究,并非女性所独有,而后者涉及贪腐的社会环境——性别化的市场社会,“性别体制”的分析框架能发挥作用。特别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报导称“不少涉案女公务员,其赃款多用于家庭、孝顺父母等支出”[16]。报导列举的典型事例中,有用赃款孝顺父母,有希望用受贿的钱财来维系与丈夫的脆弱情感,也有因情感困境(丈夫出轨)敛财百万却没花一分钱,等等。事实上,深圳市检察院的报告已意识到女性公职人员贪腐动因与“家庭”的关系,只是未摆脱女性是情感动物的性别刻板观念的束缚,把女性公职人员贪腐原因归结到“缺爱”“家庭都不幸福”,于是救济之道就落到“家庭的温暖”,呼唤“她们内心对于廉洁的坚守”[16]。这一救赎之道自然立即遭到批评,“女性涉贪,缺的不是爱是监督”[17]。但是,这一批评方向却也拒绝探究女性涉腐与性别体制的关系,而深圳市检察院报告呈现的经验事实,提示我们不应再盲视深嵌在女性贪腐中的性别体制/性别规范的作用。
另外,关于一些女性官员参与腐败案中揭露出来的以权易色的事情,作为对传统性别秩序的反转,能否用“性别体制”来解释?本文作一个大胆的假设,有可能是“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的”的性别观念起了部分作用。女性官员贪腐案,包括其他女性的参与腐败案,除了要检测传统性别体制可能起的作用,现代性别规范也可能在发挥作用。一个社会中的性别体制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一元体制,几种不同甚至对抗性的观念可能同时存在。中国是一个拥有“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的历史记忆的社会。在一个男性化的权力环境中,握有重权的女性官员模拟男性行为(像男性一样行使权力,甚至以权谋私、以权易色)⑧媒体曾报导落马的深圳罗湖公安分局原局长安惠君的贪财、好色,并凸显其经常调模样周正的男干警一起出差这件事。,不只是向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男性气质的致
意和靠扰,更可能是一种宣示自己权力的方式。琼·斯科特(Joan Scott)早已指出,社会性别是表达权力关系的一个主要场域,也是维护权力的方式[18](P19)。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需要实证经验的验证。
综上,笔者提出“性别化的社会转型/性别化的市场社会+性别体制/性别秩序”的分析视角,来修正汪琦、闵冬潮、陈密提出的“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性资本”的分析框架,作为中国语境下探究女性/性别与腐败之关系的一个可能的路径和切入点。当然,本文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对已有研究分析的逻辑推演,期待着进一步更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并提出更符合中国现实的理论解释框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EB/OL].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官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17/content_4680.htm.
[2]Dollar David,Raymond Fisman and Roberta Gatti.Are Women Really the“Fairer Sex”?:Corruption and Women in Govern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01,46(4).
[3]Swamy Anand,Steve Knack,Young Lee and Omar Azfar.Gender and Corrup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1,(64).
[4]世界银行.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5]时春荣,程小佩.“性别与腐败”关系之理论的发现及其意义[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3).
[6]汪琦,闵冬潮,陈密.性别与腐败——以中国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4,124(4).
[7]Justin Esarey,and Gina Chirillo."Fairer Sex"or Purity Myth?,Corruption,Gender,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J].Politics&Gender,2013, (9).
[8]Hung-En Sung.Fairer Sex or Fairer System?:Gender and Corruption Revisited[J].Social Forces,2003,82(2).
[9]Hung-En Sung.From Victims to Saviors?Women,Power,and Corruption[J].Current History,March,2006.
[10]Daniel Treisman.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form Ten Years of Cross-N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7,(10).
[11]Vivi Alatas,Lisa Cameron,Ananish Chaudhuri,Nisvan Erkal and Lata Gangadharan.Gender,Culture,and Corruption:Insights from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2009,75(3).
[12]Namawu Alhassan-Alolo.Gender and Corruption:Testing the New Consensus[J].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7, (27).
[13]聂辉华,仝志辉.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2014年年度报告)[EB/OL].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http://nads.ruc.edu.cn/displaynews.php?id=2029.
[14]反腐败研究报告称:女性干部比男性更清廉[EB/OL].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官网,http://www.nwccw.gov.cn/html/67/n-171167.html.
[15]李慧英.试论改革对女性领导发展的推进[J].妇女研究论丛,1994,(1).
[16]李亚坤.贪腐女官员家庭都不幸福[EB/OL].南方都市报,2015-03-12,南都网,http://epaper.nandu.com/epaper/H/html/2015-03/12/content_3394750.htm.
[17]果冻.女性涉贪,缺的不是爱是监督[EB/OL].南方都市报,2015-03-13,南都网,http://epaper.nandu.com/epaper/A/html/2015-03/13/content_3395648.htm?div=-1.
[18][美]琼·斯科特.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A].王政,张颖等主编.男性研究[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责任编辑:含章
SONG Shao-p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CCP,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gendered system;gender-corruption nexus;debates on incorruptible females;sex capital;gendere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Western and Chinese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gender and corruption"by focusing on the theoretical and interpretive frameworks.It proposes to stud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dered system and corruption"rather than that of"whether women are less corruptible".It asks how the gendered system or hierarchy in a particular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may influence how different a woman or a man reacts to corruption.It discusses why women participate in the corruption process in China in contrast to the current theories on"chaotic capital/resource acquisition+sex capital".In the end,the paper proposes a new way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that gender plays in co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gendered social transformation/gendered market society+gendered system/gender hierarchy".
C913.68
:A
:1004-2563(2015)02-0005-12

宋少鹏(1971-),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女权主义思想史、妇女运动史、妇女与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