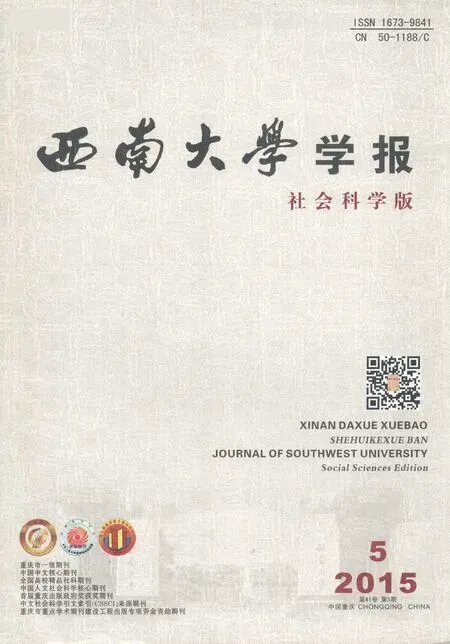抗战时期中美之间陆空战略之争再探析
付辛酉
(大连大学历史学院,辽宁大连116622)
抗战时期中美之间陆空战略之争再探析
付辛酉
(大连大学历史学院,辽宁大连116622)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之间存在的“陆空战略”之争,实质上是中美间关于对华军事援助重心的争论.由于后勤条件的限制,如何使用有限的军事援助,成为中国战区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这场争论的主要内容是优先改善中国战区的后勤,还是尽快以中国为基地发动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受到这一争论的影响,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发生了多次转移.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中美军事同盟关系,开罗会议后中美关系一度极为紧张,美国的空中战略是极为重要的原因.1945年中美军事合作进入最佳时期,美国放弃空中战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抗战时期;中美军事同盟;陆空战略;史迪威;正面战场
中美在战时关于陆空战略的争论,学界一般指发生在1943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史迪威与陈纳德关于驼峰空运物资分配方案的辩论.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次争吵影响了美国的对华军事援助,也有学者强调争端的起因在于史迪威个人品质的恶劣[1][2][3][4][5][6][7].最近有研究指出美国并未满足蒋介石提出的增强中国战区空军实力的要求,对中美关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8],有学者则提出当时并不存在陆空战略之争.[9]中美间的这次争论严重影响了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因此有研究认为开罗会议是战时中美关系的转折点[10][11][12][13]49,部分学者将会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归因于马歇尔破坏了罗斯福的对华友好政策[7]204.也有学者指责马歇尔为避免影响欧洲战场,在对华军事援助问题上,采取了“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政策[14]26.
然而上述研究并未重视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在陆空战略上的分歧,也忽视了罗斯福对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具体内容的干涉.“陆空战略之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未得到重视.开罗会议后,罗斯福逐渐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提出军事观察组进入延安和史迪威指挥权等问题,内在的原因是出于其空中战略的需要.仅胡越英在其研究中提出马特洪恩计划对史迪威指挥权等问题有影响[15],但并未进一步阐释其关系.本文将通过梳理中美两国档案文献,力图以此争论为切入点,剖析中美两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战略分歧,解释两国同盟关系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
一、中美间陆空战略之争的双重含义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两国不仅在先欧后亚,还是先日后德的大战略层面存在分歧,在中国战区的具体战略上也存在激烈的争论.学界以往重视蒋介石与美国在华军事代表史迪威之间的冲突,而忽视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矛盾.而且从实际情况上看,前者是双方存在误解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中美间的真实矛盾.
学界将陈纳德在接待美国特使威尔基时,托其转交给罗斯福的信件视作陆空战略之争的起点[16]212-216,并认为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两人关于驼峰物资分配方案的辩论是争论的主要内容.[17]224蒋介石在1943年初否决了史迪威提出的局部反攻计划,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提高陈纳德的地位,以及有利于陈纳德航空队的驼峰物资分配方案[17]214.在华盛顿会议期间,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全力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攻势计划”[17]223,使得这次争论从史迪威与陈纳德争夺后勤资源的辩论,变成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直接冲突,并上升到影响中国战区战略走向的层面.
蒋介石与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规划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史迪威认为当时的中国陆军无力承担保卫机场的任务,因此他主张将有限的军事援助优先用于军队改革和反攻缅甸,以便能进一步改善中国战区的后勤状况.而蒋介石面临国内正面战场更为直接和实际的压力,同时他认为中国军队无力承担反攻的主力任务,因此积极争取英美在反攻上扮演主要角色,并且决定在英美做出明确承诺前,拒绝参与反攻战役.因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导致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战略意图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史迪威在华盛顿会议上指责蒋介石唯一的战略错误就是“储存大量物资和装备,以及一支空中力量来结束战争”[18]383.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指责并非毫无根据.他认为蒋介石对反攻缅甸态度消极,“不愿作战”[19]183,而他的判断不仅来源于在缅甸保卫战期间合作的经验,也依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对1942年浙赣战役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中,即便一向与中国政府关系良好的美国海军观察人员经过实地调查后,也表示:“在丽水的中国指挥官有着装备良好的部队,并且急切的希望战斗,但重庆下达命令,表示出于政治原因,要求他们避免与日军作战,并从丽水撤退.”[20]118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怀疑还有美国陆军内部指挥权争议的因素.由于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而且陈纳德也对美国陆军在亚洲的指挥机构表达过强烈的不满,使得美国陆军认为陈纳德有成为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的野心[21]481-482.蒋介石为陈纳德争取独立指挥权的措施,本意上为了提高中国空军战斗力和奖励陈纳德,但却意外地加剧了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加深了史迪威对他的误解.
史迪威指责蒋介石试图以“空中战略”取代对地面部队的改革和对缅甸的反攻是一种误解.在军事上,中国正面战场需要增强中美空军的实力,以便能更有效地支援地面作战.1943年4月19日,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向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转达中国目前形势严重的情报,指出日军打通由武汉至宜昌的长江航线之后,如果在夏季沿长江发动攻势,中国恐怕难以支持[17]220-221.之后在鄂西战役期间,蒋介石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是长江三峡后,曾多次指示宋子文,要求其向美国政府请求陆军航空队的援助.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认为“如美空军能协助我陆军作战,则我陆军集中后,当可向宜昌取攻势也”[23]476.
而在外交方面,因为中国军队实力有限,蒋介石拒绝采纳史迪威提出的北缅局部反攻作战方案,坚持英美方面出动优势海空力量的全面反攻方案,在外交方面大力开展对美国政府的游说,提出“非先以英、美海空军遮断敌军接济路线,与确实占领仰光,打通滇缅路至仰光全路交通线不可”[17]227,并且极力争取美国陆军参战[17]245.在协商过程中,中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英国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愿对缅甸南部进行两栖登陆作战[17]257.因此在1943年8月份,蒋介石再次致电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的罗斯福与丘吉尔,要求“现在雨季将过,敌情与事实上不能再事迁移,务请阁下等在此次会议中对远东战略及反攻缅甸、打通仰光至昆明之交通路线具体决定实施计划与整个步骤”[17]259.
从宋美龄劝说蒋介石收回召回史迪威的理由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并未有以“空中战略”取代反攻缅甸的想法.蒋介石要求宋美龄结束访美向罗斯福辞行时,提出与史迪威合作困难,希望由罗斯福主动召回史迪威.但宋美龄认为召回史迪威会影响对缅甸的反攻时[23]854,蒋介石表示“对史迪威事并非正式要求其撤换,不过使之察知实情而已.待有便乘机以闲谈出之,否则不谈亦可”[23]854.
中国方面的真实态度是积极推动盟国实施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并争取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参战,同时要求美国加强中国空军以及在华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实力,以此支援中国正面战场.在宋美龄即将离美前,蒋介石嘱咐其游说罗斯福:“惟望其能加派陆军若干师,如不能派三师,则二师亦可.请再相机恳谈,或能收效”[23]853.但由于中美两国首脑在具体战略上存在极大的分歧,蒋介石的外交和游说活动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陆空战略之争中,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学界重视.这一分歧体现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热情地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空袭计划,但并不支持蒋介石最为企盼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参加缅甸反攻计划.罗斯福本人对空袭日本的想法极为热情.在美国的既定战略中,中国的重要性在于为美国陆军航空队提供袭击日本的基地.在1942年底迎接以治病名义访美的宋美龄时,霍普金斯曾针对宋美龄提出美国集中全力对付日本的要求,婉转透露出罗斯福对于中国战区的战略设计:“此建议切不可在罗总统面前提起,因为其绝不可能接受这一观点.如果提起(此点),则(总统)将继续表现出最友好态度但不再认真对待(夫人)此次访问.(夫人)若能取得(保证)使以前确定的大政方针,即将中国战区在空军力量方面视作第三重要战区之定论得以付诸实施,则访问定能获得成功.如此,蒋夫人当前所持观点必须摒弃”[24]228.罗斯福之所以积极支持陈纳德,并采纳蒋介石的建议,促使美国政府在1943年将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转向尽快在中国发动“空中攻势计划”,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以中国为对日空袭基地已经是美国的既定战略.
另一方面,从1943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当时唯一能够实质性支援中国正面战场和打击日本的力量,是陈纳德指挥的陆军航空队.因此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后,罗斯福不顾马歇尔的反对,接受了蒋介石的物资分配方案,并且将陈纳德指挥的陆军航空队改组为第14陆军航空队[17]216.在华盛顿会议时,罗斯福也在“空中攻势计划”问题上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方案[17]232,并且对宋子文表示“陈纳德需要战斗机及运输机,都不成问题,余当力为设法”[17]236.
然而在蒋介石更为关心的反攻缅甸和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参加反攻问题上,罗斯福最初态度游移,并不明确,甚至在英国官员的游说下,曾一度试图劝说中国政府取消宣布反攻.1943年3月2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致信罗斯福,提出由于会影响对欧洲大陆的入侵计划,英国总参谋部并不看重全面反攻缅甸的安纳吉姆计划.在29日白宫会议中,英国负责战时船运的大臣刘易斯·W.道格拉斯进一步说服了罗斯福,为尽快完成入侵欧陆的准备应该放弃安纳吉姆计划.因此,罗斯福在次日向马歇尔透露了可能为了满足入侵欧陆的需要而放弃反攻缅甸的想法[21]620-621.
二、美国政府内部关于陆空战略的分歧
与中美之间的分歧相比较,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更不受关注.首先这一分歧体现在罗斯福与马歇尔之间.为避免反攻计划被彻底取消,马歇尔在4月3日制定了有限的安纳吉姆作战计划,计划占领缅甸北部以及阿恰布地区,以开通穿过缅甸北部的陆上援华交通线.马歇尔的计划也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李海和金的支持.[21]627-629在马歇尔和宋美龄的反对下,罗斯福最终撤回了取消反攻的要求,而接受了局部反攻的计划.宋美龄并没有意识到,马歇尔在促使罗斯福接受局部反攻计划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在向蒋介石汇报谈判结果时,表示“此次谈判之一大收获,即英、美本拟将反攻缅甸计划完全放弃,经妹交涉,现美已允助我维持新路线”[23]835.
马歇尔与罗斯福的分歧还体现在对于“空中攻势计划”的态度上,马歇尔在3月16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后勤问题是制约美国在华军事行动的主要因素,而且保卫美国陆军所需要的机场以及驼峰航线终端的任务必须由中国军队承担,但根据中国军队在浙赣战役中的表现,过早展开空中攻势会造成恶劣的后果.[21]587以往研究都强调史迪威与马歇尔在华盛顿会议时对陈纳德的反对,事实上马歇尔本人并不反对美国在华的空中战略,只是认为当时的条件不适宜执行这种战略.他曾在1943年初的一份备忘录中赞赏陈纳德在航空领域的战术天才,但同时指出陈纳德忽视了后勤方面的困难,而这一点是限制美国在华空中力量规模的关键因素.马歇尔强调,在目前手段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补充陈纳德的空中力量会削弱对日本进行真正的打击.开放顺畅的地面运输线是史迪威在努力试图通过春季在缅甸北部发动的攻势解决的问题.一旦后勤问题得到解决,美国有可能将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航空力量集中在中国的基地[21]502-503.
马歇尔在反对立即执行空中攻势计划的同时,积极推动盟国对缅甸发动反攻.由于史迪威的请求,他曾计划将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派往印度,交给史迪威指挥参与反攻.耐人寻味的是,他在电报中嘱咐史迪威对这一计划严格保密,尤其强调罗斯福对此尚不知情[21]578.但最终这一计划成为具文,并未得到执行.
马歇尔在推动盟国对缅甸的反攻以及美国地面部队参加反攻等问题上,显然比罗斯福更接近蒋介石的主张.然而马歇尔的计划最终没有被采纳,不仅是由于罗斯福的消极,更主要是美国陆军内部的反对意见.史迪威在华盛顿会议时提出派出两个师的作战部队到印度参战,对于这一要求,考虑到会因此带来指挥权、后勤、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可能影响到欧洲战场,美国陆军最终决定避免向印缅战场派出地面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陆军做出不向印缅战场派出地面部队这一决定过程中,后来接替史迪威出任美国陆军中国战区司令兼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发挥了重要作用[25]142-143.
美国陆军内部也存在陆空战略的争论.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之所以支持罗斯福的决定,原因是美国陆军航空队计划在中国布置还处于试验状态的B-29“超远程轰炸机”[18]299.美国陆军航空部门研制“超远程轰炸机”和“超重型轰炸机”(超远程轰炸机项目代号Very Long Range,简称VLR;超重型轰炸机项目代号Very Heavy Bomber,简称VHB)的计划启动于1939年11月10日.[26]6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预计在1944年将有10个B-29轰炸机组完成部署,但适合作为B-29基地的太平岛屿,预计只有到1945年才能被美国海陆军占领,也就是说在1944年只有中国能提供合适的基地.因此也需要中国为超远程轰炸机项目做准备.[26]17
史迪威在华盛顿会议中不仅反对陈纳德的计划,也对陆军航空队在中国部署B29轰炸机的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陆军航空队过于乐观地看待了后勤困难.但作为战区指挥官,史迪威不得不提出代号“暮光”的作战方案[26]18.在魁北克会议期间,由于美国海军采用了新的战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将夺取马里亚纳群岛的时间预计为1946年,同时陆军航空队对“暮光”计划作了一定的修改.虽然预计在晚些时候马里亚纳群岛将作为主要基地,但近一年的时间内,陆军航空队只能使用中国的基地.因此发动B-29空中攻势必须克服中缅印战区的后勤困难,而且从政治角度看,为了提高中国战区的士气也要求发动这个攻势[26]19-20.在华盛顿的压力下,史迪威接受了名为“马特洪恩计划”的作战计划[26]21-22.
由于执行“马特洪恩”计划需要中国的协助,因此在开罗会议前,罗斯福请求蒋介石完成建造“马特洪恩”所需要的机场[26]23,去电指出“对于日本本土重要之目标,吾人现将发动猛烈轰炸之攻势,此举似较预定为早.为完成此项目的,须在成都区域,有5个长型之轰炸机机场,以供新式强力飞机之用,并需少许房屋之设备”.并提出“对于专门技术之指导,吾人当能予以供应,但其必需之工人及物资而在空运补给线之外者,则惟阁下是赖.余将利用租借法案之经费以拨发其必需之款项,倘如是而得依限加速完成其工作”[17]285.
三、陆空战略之争被低估的影响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在中国战区的军事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和改革训练中国陆军.在美国“欧洲第一”的大战略主导下,限制美国对华援助规模的主要因素是日军对中国的封锁,以及地理条件造成的后勤障碍.而缅甸战役失利后的形势,不仅使美国以中国为空袭日本本土基地的战略无法进行,也不能满足中国陆军进行改革的需要.因此,缅甸保卫战和浙赣战役之后,马歇尔和史迪威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从最初的以中国为对日空袭的基地转向争取打破封锁,优先改善中国战区的后勤状况.
但在陈纳德提出其战略计划后,由于罗斯福的推动,并借助蒋介石的支持,美国的战略逐渐转向空中战略.然而这一时期美国空中战略的主要内容并不是陈纳德提出、蒋介石支持的“空中攻势计划”,而是美国陆军的“马特洪恩计划”.在第二次开罗会议期间,英美联合参谋会议的决议要“采取必要和实际措施,将中国作为一个有效的盟国和对日作战的基地,增强中国从事战争的实力”,[27]811但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的阻力在于后勤交通方面无法满足增强中国陆军实力、扩大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规模以及支持超远程轰炸机的要求.因此无论从积极的角度,即将中国作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基地,开展对日本本土以及海上运输线的袭击,还是从消极的角度,即维持中国战区的稳定,盟军都必须尽快开始对缅甸北部的攻势,以打开中国陆地运输线,并改善驼峰航线的运输条件.
但反攻战役开始后,中国政府与盟国间的关系一度恶化.第二次开罗会议中,由于罗斯福收回了对蒋介石的承诺,导致蒋介石拒不出动驻扎在云南的远征军配合盟国的缅甸反攻战役.在战役开始后不久,日军发动对盟军后勤基地英帕尔的攻击,曾一度迫使史迪威提出中止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而南下支援英军的建议[28]271-273.与此同时云南远征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援缅北战役和英帕尔战役,自然引起了英美的不满.因此,马歇尔在4月7日建议史迪威,如果蒋介石仍拒绝出动云南部队,他可以将用于装备远征军的驼峰租借物资转拨给第14航空队以及B-29重轰炸机部队使用.史迪威在11日回电称他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并且取消了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合同,接管其租借的飞机.马歇尔的命令在4月14日得到了罗斯福的批准.[29]408
与军事冲突同时进行的还有中美之间的财政谈判,因为汇率等问题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协议,谈判期间,蒋介石甚至以拖延“马特洪恩计划”所需的机场建设对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让步[26]69[30].这无疑也降低了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好感.然而这时罗斯福仍避免为实现美国的目标,而对蒋介石采用强制手段.罗斯福的这一态度也体现在军事观察组问题上.美军观察组担负有多重使命,其主要任务是为“马特洪恩计划”服务,搜集华北地区的气象资料和日军情报.1944年2月9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派遣美军观察组的要求.[31]329但中美双方都清楚美军观察组势必进入中共控制区域活动,因此这一请求被蒋介石否决.最终因为美国陆军积极回应蒋介石提出的增加援助以应对正面战场的危局,所以在访问中国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重庆前,蒋介石决定在观察组问题上对美国妥协:“正午主持军事会报,决定准美国派员驻延安,专为办理美国空军人员被迫降落共匪区域内时救济事宜,而非为军事代表团也.”[32]285
同时,由于中国国内正面战场的局势逐渐严峻,陈纳德和史迪威都提出推迟执行“马特洪恩计划”,但他们的建议都未被采纳[26]80.阿诺德反而要求更快地执行“马特洪恩计划”,以此来支援中国的正面战场.在6月6日,阿诺德指示第20轰炸机指挥部,因为日军对长沙的进攻威胁到了陈纳德前进基地,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对日本进行一次袭击,以此减轻中国战场的压力,同时援助太平洋战场上的“重要战役”.然而乌尔夫调查第20轰炸机指挥部的物资储备后,表示无力按照阿诺德所期望的规模执行任务.而且在6月4日,史迪威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授予的权力,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将驼峰空运每月1 500吨的份额转交给陈纳德,但未批准蒋介石提出的将第20轰炸机指挥部在成都的所有储备移交给陈纳德的要求[26]98-99.由此可见,通过驼峰运入中国的物资不足以支持B-29发动大规模对日空袭,也无法满足中国战区自身的需要,因此阿诺德曾在7月20日考虑将B-29撤往其他战区[26]126.
华莱士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在6月28日的报告中指出:事实表明,华东地区包括美国在此地的前进机场将全部落入日军之手,然而如果美国采取正确措施,中国的局势并非毫无希望.他也指出在合适的人选下,蒋介石会采取适当的政治军事改革措施.但华莱士强调史迪威已经丧失蒋介石的信任,并不适合继续在中国为美国服务[31]235-237.然而罗斯福并未完全采纳华莱士的建议,而是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向蒋介石提出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
长沙失陷后的7月4日,马歇尔对罗斯福指出中国局势异常严峻,如果日军继续西进,将有可能造成美国陆军航空基地被摧毁、中国崩溃的结果.因此他建议罗斯福采取激烈的措施,以挽救美国在这一地区所做出的努力[29]503-504.虽然在备忘录中马歇尔也将拖延改革和反攻,以及坚持依靠空中力量的责任归结于蒋介石,但他仍将推动改革以便更有效地保护航空基地作为劝说罗斯福的主要理由.
从史迪威事件之前的中美历次冲突中可以看出,美国这一时期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仍然是以中国作为基地发动对日空袭,即使是反攻缅甸战役中强迫蒋介石出动远征军,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改善后勤运输能力状况,以便更好地发挥B-29轰炸机威力.在中美双方交涉史迪威地位和指挥权问题时,由于蒋介石的不断呼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25日同意增加空运指挥部中印运输部门的运输能力,但仍然将空运物资分配的优先权列为:(1)维持对华空运线,保证作战的顺利进行和保护第14航空队和B-29轰炸机作战所需要的基地;(2)执行马特洪恩计划,每月225架次;(3)满足中国陆军和空军的要求[26]128-129.而之所以提出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也是因为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失败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空袭战略.所以罗斯福采纳了马歇尔的建议,电告蒋介石“自日军进攻华中以来,形成极严重之局势,不仅使贵政府感受威胁,且使美国在华基础同受影响.倘欲挽救危局,余认为须迅采紧急之措置,鉴于现状之危急,余意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并向蒋介石保证“余绝无向阁下干预中国政事之意念”[17]634-635.
由于史迪威在9月19日当面递交的罗斯福电报措辞过于强硬,导致蒋介石下决心驱逐史迪威.罗斯福不得不于10月19日同意蒋介石的要求,任命当时担任东南亚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的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同时将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划分为中国战区和印缅战区,由魏德迈担任美国陆军中国战区司令官[17]688-689.史迪威事件后,蒋介石曾担心会因此影响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援助政策.然而,美国政府被迫召回史迪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政策在“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只是对人事和机构进行了调整.
魏德迈接替史迪威之后,美国陆军并未放弃在华的空中战略.他在10月28日接到美国陆军的命令,其主要任务包括:协助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进行对日作战;指挥美国战斗部队进行以中国为基地的对日空战,以及协助中国陆空部队的作战、训练和后勤补给;除非为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得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介入中国内部冲突;接受蒋介石参谋长的职务[33]271.
经过史迪威的不懈努力,缅甸战役进展顺利,这一局面极大地改善了中国战区的后勤状况.然而在魏德迈抵达中国的时候,盟军的后勤状况仍极不乐观,无法承担空中战略和改革中国军队的双重任务.盟军夺取密支那后,驼峰空运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虽然陆上运输线实际上在1945年2月才开通[34]48,但美国陆军航空队所属的空运指挥部能以更快的速度运入中国陆军所需要的物资和器材.1944年12月的实际空运吨位31 935吨[35]138,而到1945年8月份日本投降前,空运吨位达到53 315吨[35]143.
最初魏德迈并不反对在中国继续执行美军的空中战略,但后勤方面的问题促使他要求将B-29撤出中国[36]161,以便将更多物资用于援助中国政府和军队.在1945年1月份,维持B-29轰炸机所需要的物资就占去了驼峰12%的空运[35]146.B-29轰炸机撤离中国不仅意味着中国不再是美国陆军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而且也意味着更多的空运物资能用于魏德迈主持的军事改革.美国政府内部的陆空战略之争最后转向了执行地面战略.由此可见,魏德迈接替史迪威之后,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不再是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本展开空中袭击,而是转回对中国军队进行改革,支援中国军队并提高其作战效能的战略.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战时中美之间存在的陆空战略之争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以往学界强调的陆空战略之争,将陈纳德、蒋介石、罗斯福作为空中战略的支持者,而将史迪威、马歇尔作为地面战略的支持者,然而未被学界重视的是,影响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争论实际上发生在美国政府内部,而且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也存在严重的陆空战略之争.实际上战时中美之间的陆空战略冲突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容,蒋介石与史迪威、蒋介石与罗斯福以及罗斯福与马歇尔之间都存在类似的意见分歧.而且这一争论也严重影响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成军事同盟,但两者并不是平等的同盟伙伴.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中国,而带有更强烈的满足自身战略需要的色彩.这是1945年之前中美军事同盟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这种紧张状态并不是由于史迪威或者马歇尔破坏了罗斯福的对华友好政策,而恰恰是执行罗斯福坚持的空中战略的结果.开罗会议前后,罗斯福从积极支持蒋介石的“空中攻势计划”,到提出军事观察组和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其对蒋介石态度转变的内在的原因是出于其空中战略的需要.
由于后勤条件的限制,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数量极其有限.如何使用有限的军事援助成为中国战区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美国陆军选择了执行空中战略,同时避免向亚洲投入地面部队.这就造成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是为了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而不是帮助中国的局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局面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蒋介石不懈争取的结果.
纵观战时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决策过程,罗斯福是最终的决定者,而美国陆军参谋长仅是其主要助手之一,通过备忘录等形式修正罗斯福的战略.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则从战地通过各种报告、备忘录为决策者提供情报和其自己的意见.在这一决策过程中,马歇尔并不是决策者,不仅如此,马歇尔提出的建议还经常遭到陆军和海军其他人员的反对,并最终被取消.其中,史迪威多次要求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参加反攻的否决意见来自于美国陆军内部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同样,在修正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方向上,中国政府并非毫无作为,蒋介石不仅能通过正规的外交渠道向罗斯福提出要求,他还充分发挥院外游说的作用,从而影响美国的对华援助.然而,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支持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选择性.蒋介石期盼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投入到缅甸反攻并未得到罗斯福的明确支持.
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后,中美军事合作进入最佳状态,不仅是后勤状况得到改善的结果,也是由于美国将对华军事援助的重心重新转向解决中国的危局的结果.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获得了更好的基地,促使美国陆军停止在中国执行其空中战略.B-29轰炸机撤出中国,意味着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能用于中国陆军的改革,并解决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局.
[1]罗志田.从史迪威事件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矛盾[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99-109.
[2]严四光.史迪威陈纳德龃龉与美国对华政策(1942-1944)[G]//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376-397.
[3]金光耀.试论陈纳德的空中战略[J].近代史研究.1988(5):202-219.
[4]李亚平.史迪威、陈纳德之争与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4(4):24-30.
[5]王真.史、陈矛盾及其对战时中美关系的影响[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78-83.
[6]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13册[M].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84.
[7]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订版)[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5.
[8]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J].近代史研究,2009(3):45-62.
[9]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2-194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68.
[10]梁敬錞.开罗会议[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220.
[11]福田茂夫.从开罗会议到波茨坦会议[C]//夏景才.日本学论坛,1983(4):37.
[12]Ronald Lan Heiferman.The Cairo Conference:a turning poin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M].Ann Arbor.Mich.:UMI,1991.
[13]Charles F.Romanus&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M].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Washington.D.C.,1956.
[14]Hans J.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M].New York.Routlege Curzon.2003.
[15]胡越英.二战后期美国马特洪恩计划与核战略[J].抗日战争研究,2008(3):52-69.
[16]Claire Lee Chenault.Way of a fighter,The Memorie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M].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9.
[17]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18]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The Way Against Japan[M].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1982.
[19]Joseph W.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M].arr.and ed.by Theodore H.White.New York:Walliam Sloane Associates.Inc.1948.
[2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M].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56.
[21]Larry I.Bland.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ume 3[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
[22]高素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3册[M].台北:国史馆,2011.
[23]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24]吴景平,林孝庭,主编.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5]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M].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Washington,D.C.,1956.
[26]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V,The Pacific:Matterhorn To Nagasaki, June 1944 To August 1945[M].University of Chicago.Chicago.1948.
[2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3.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M].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
[28]Sir William Slim.Defeat into Victory[M].London.Cassell.1956.
[29]Larry I.Bland.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volume 4[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30]任东来.被遗忘的危机: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的争吵[J].抗日战争研究,1995(1):112-137.
[3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4.China[M].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7.
[32]叶惠芬.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7册[M].台北:国史馆,2011.
[33]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M].New York.Henry Holt&Company.1958.
[34]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5.China[M].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9.
[35]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The Army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I,Plans and Early Operations.January 1939 to August 1942[M].University of Chicago.Chicago.1948.
[36]Charles F.Romanus&Riley Sunderland.Time Runs Out in CBI[M].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Washington.D.C.1959.
责任编辑 张颖超
[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本期收两篇论文。王日根所撰之文,以晋江安海新县设置失败为例,对明代东南沿海海疆经济分量加重与设县中的官、私较量过程,作了全新的考辨及其论析;田茂旺所撰之文,则对曾任川滇边务大臣与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在川边的茶务整顿与边疆建设作了颇为翔实的研究。两文所涉时段,跨越了明清两代,且空间区域包括东南海疆与西南边疆,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无不涉及到明清两代的边疆经济及与此相关的边疆行政,且与史学界从中原到边疆的研究取向若合符契。
毫无疑问,在明清两代,无论是东南海疆经济,还是西南边疆经济,在当时的国家经济运行中越发凸显分量加重的趋势。在此经济发展过程中,以走私贸易为主体的“私”的经济行为的兴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官、私较量,显然是当时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诸如此类的问题,若是将其置诸海上丝绸、茶叶、瓷器贸易与陆上茶马贸易的大背景下加以系统的考察,必将使明清边疆经济史乃至政治史的研究引向深入,且为目下“一带一路”宏伟战略的实施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
K264
A
1673-9841(2015)05-0162-08
10.13718/j.cnki.xdsk.2015.05.022
2014-05-10
付辛酉,历史学博士,大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