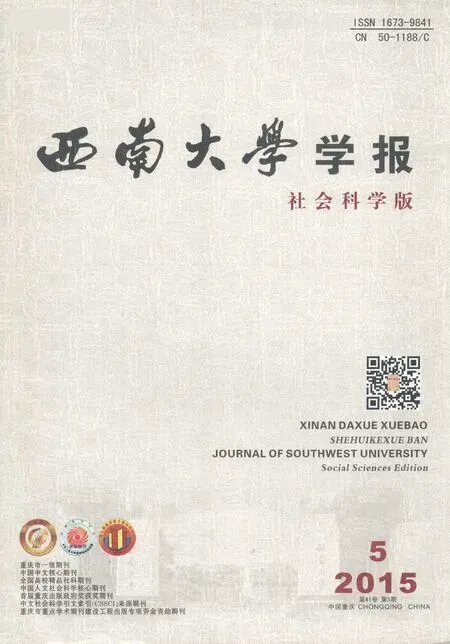王明清笔记著作中的文学思想研究
张瑞君,韩 凯
(1.太原学院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32;2.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王明清笔记著作中的文学思想研究
张瑞君1,韩 凯2
(1.太原学院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32;2.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王明清笔记著作中的文学思想,学界目前对之关注尚显不够充分.王明清笔记著作中的文学思想极为丰富,不仅可以使研究者站在以文学论文学的维度上对宋代文学予以观照,而且可以使研究者以文学生态视野对宋代文学诸多重要现象予以考论,对深入了解宋代文学发展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文学;王明清;笔记;文学思想
王明清的笔记著作,《全宋笔记》收录6种:《挥麈前录》《挥麈后录》《挥麈第三录》《挥麈录余话》《投辖录》《玉照新志》(笔者按:《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二册尚收录有旧题王明清所著《摭青杂说》,但《全宋笔记》收录时题著者为佚名,今从之).究其总体而言,其笔记著作对宋代文学研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四库馆臣评《挥麈录》“援据赅洽”[1]卷一百四十一子部五十一小说家类二,p3604,评《玉照新志》“盖明清博物洽闻,兼娴掌故,故随笔记录,皆有裨见闻也”[1].目前对王明清笔记著作的研究尚乏深入,以文学思想为专论之研究更是少见.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从以文学论文学维度考察王明清笔记中的文学思想
王明清笔记中的文学思想,在文学创作论方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昔人不以蹈袭为非”.《挥麈录余话》卷之一明确提出: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阴铿诗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诗》云:“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后人以谓以此讥之。然子美诗有“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一联,已见《晋书》载记矣。如“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孟蜀王诗,东坡先生度以为词。昔人不以蹈袭为非。《南部烟花录》:“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唐人方域诗。《新唐书·艺文志》有方域诗一卷。《烟花录》一名《大业拾遗记》,文词极恶,可疑。而《大业幸江都记》自有十二卷,唐著作郎杜宝所纂,明清家有之,永平时扬州印本也。[2]35-36
类似于此,《挥麈后录》卷之八亦提到古人文学创作的这一规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画堂一枕春酲.’又皆柳词中语.”[3]193
“昔人不以蹈袭为非”之说,实质上是对文学创作发展规律的揭示,除了便于对作家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有所了解及认识之外,还在于通过化用前人语句而对作家人格思想的形成有所认识.如苏轼“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4]卷一《沁园春》(孤馆灯青),p70,明显化自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苏轼人格受到杜甫非常大的影响,《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八)称“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在其宦途生涯中践行杜甫“一饮一食,未尝忘君”的高尚政治人格,“所以他在朝便敢于并乐于言政,不顾念个人的得失荣辱.当地方官便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出卓著的政绩,赢得人民的厚爱.直到晚年他还说‘许国心犹在’”[5].
王明清在文学创作及批评论方面,推尊文学的政教功用,注重文学的实用性,认为文学应该有裨于后世.这在《挥麈后录》卷之十一有所印证:
绍兴丁卯岁,明清从朱三十五丈希真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维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读至此,启云:“窃有疑焉。”朱丈云:“敦儒与先丈皆秦会之所不喜,此文传播,达其闻听,无此等语,至掇祸。”明清云:“欧阳文忠《与王深父书》云:‘吾徒作事,岂为一时?当要之后世为如何也。’”朱丈叹伏,除去之。[3]223
按:维垣益公,即秦桧.《宋史》秦桧本传有云:“十七年,改封桧益国公.”据朱希真所云“敦儒与先丈皆秦会之所不喜”,可断定“维垣益公”即秦桧.王明清借用欧阳修《与王深父书》中的一句话说明:“吾徒作事,岂为一时?当要之后世为如何也.”由此不难看出他主张文学创作应立足于诗文的政教功用,注重文学讽喻后世的教化功能.
重视诗文的政教功用,是中国文论的一个悠远而重要的传统.当此种思想发展至极端,会带来文学自身艺术美感的缺失.宋初柳开即鲜明的例子:“他反对‘辞之华于理’,却不反对‘理之华于辞’,贬抑艺术形式美的倾向是很明显的.”[6]王明清文学思想的可贵之处就是虽推崇诗文的政教功能,但同时强调诗文艺术上的美感,如《挥麈第三录》卷之三评时人曹筠致秦桧诗语:“筠因便介,姑作诗以致祈恳,末句云:‘浩浩秦淮千万顷,好将余浪到滩头.’其浅陋不工如此.”[3]273-274
在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方面,相比于古代诗话诗评类著作多以抽象的思理表述,王明清以鲜活生动的例子使文学研究者有直观而信实的了解.如《挥麈后录》卷之十一载:
舅氏曾宏父生长绮纨,而风流酝藉,闻于荐绅。长于歌诗,脍炙人口。绍兴中,守黄州,有双鬟小颦者,颇慧黠,宏父令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二赋,客至代讴,人多称之,见于谢景思所叙刊行词策。后归上饶,时郑顾道、吕居仁、晁恭道俱为寓客,日夕往来,杯酒流行。顾道教其小获亦为此技,宏父顾郑笑曰:“此真所谓效颦也。”后来士大夫家与夫尊俎之间,悉转而为郑、卫之音,不独二赋而已。明清兄弟儿时,先妣制道服,先人云:“须异于俗人者乃佳,旧见黄太史鲁直所服绝胜。”时在临安,呼匠者教令染之,久之始就,名之曰“山谷褐”。数十年来,则人人效之,几遍国中矣。[3]225
这里提到苏轼及黄庭坚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以生活中的例子加以说明:曾宏父于宋高宗绍兴年间守黄州期间,令双鬟小颦诵苏轼前后《赤壁》二赋,后与郑望之、吕本中等人往来交游,郑望之复“教其小获亦为此技”.由之可见苏轼作品不仅在后世士大夫中有深远影响,即当时普通伶人小妾亦熟谙之.而黄庭坚对后世之影响,则可由“山谷褐”“数十年来,则人人效之,几遍国中矣”窥其端倪.
在文学创作的意象论方面,王明清着重对一些时人罕知的文学意象进行说明,从而可使后世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意.如《玉照新志》卷第四中解释“高桥客死”意象:“欧阳文忠公诗云苏子美挽词‘奏邸狱冤谁与辩,高桥客死世通悲’,以为用事亲切,而世不知‘高桥客死’之义.后来绍兴中,秦熺势方鼎盛,尝托其客陆升之仲高下问于明清.偶省记得见《吴地记》,后汉梁鸿客食吴门,死于高桥,而子美亦然.因以告知,熺甚以赏激.未几,会之殂,熺亦逐矣.”[2]192
在文学创作的背景论方面,王明清侧重对作家某一作品创作的背景进行细致描述,可使后人更好地对作品抒发的情志以及创作心理有较好的认识.《挥麈录余话》卷之一记蔡挺创作《喜迁莺》的背景:
熙宁中,蔡敏肃挺以枢密直学士帅平凉,初冬置酒郡斋,偶成《喜迁莺》一阕:“霜天清晓,望紫塞古垒,寒云衰草。汗马嘶风,边鸿翻月,垄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难报。塞垣乐,尽双鞬锦带,山西年少。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圣主忧边,威灵遐布,骄虏且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尊频倒。”词成,闲步后园,以示其子朦。朦置之袖中,偶遗坠,为应门老卒得之。老卒不识字,持令笔吏辨之。适郡之娼魁素与笔吏洽,因授之。会赐衣袄中使至,敏肃开燕,娼尊前执板歌此,敏肃怒,送狱根治。娼之侪类祈哀于中使,为援于敏肃。敏肃舍之,复令讴焉。中使得其本以归,达于禁中,宫女辈但见“太平也”三字,争相传授,歌声遍掖庭,遂彻于宸听。诘其从来,乃知敏肃所制,裕陵即索纸批出云:“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筦有阙,留以待汝。”以赐敏肃。未几,遂拜枢密副使。御笔见藏其孙稹家。史言“献肃交结内侍,进词柄用”,又不同也。[2]27-28
此则材料详细记述了蔡挺名作《喜迁莺》创作前后的背景,既谈到了创作兴起之由,“以枢密直学士帅平凉,初冬置酒郡斋”,又谈到了创作之后的影响.后世研究者据此及《宋史》蔡挺本传“在渭久,郁郁不自聊,寓意词曲,有‘玉关人老’之叹.中使至,则使优伶歌之,以达于禁掖”推定,蔡挺《喜迁莺》抒发的乃是嗟叹不得进用意欲报效朝廷之志.
二、以文学生态视野考察王明清笔记中的文学思想
王明清笔记著作中的文学思想最具价值之处,是在于使文学研究者跳出以文学论文学的限制,从“生态环境”视野对宋代文学面貌进行整体研究.
“文学生态”重在全方位探讨文学发展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其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挥麈录余话》卷之一载:
沈睿达辽,文通之同胞,长于歌诗,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肃学其笔法,荆公得其清劲,而文肃传其真楷。登科后,游京师,偶为人书裙带,词颇不典。流转鬻于相蓝。内侍买得之,达于九禁,近幸嫔御服之,遂尘乙览。时裕陵初嗣位,励精求治,一见不悦。会遣监察御史王子韶察访两浙,临遣之际,上喻之曰:“近日士大夫全无顾藉,有沈辽者,为倡优书淫冶之辞于裙带,遂达朕听。如此等人,岂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适睿达为吴县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时荆公当国,为申解之,上复伸前说,竟不能释疑,遂坐深文,削籍为民。其后卜居池阳之齐山,有集号《云巢编》行于世。[2]36
此处提到士人沈辽由“登科”为“吴县令”而后被“削籍为民”的原因,是由于登科后游览京师时所写之文“词颇不典”,以致引起神宗不满.神宗所言“淫冶之辞”,即同于齐梁宫体绮艳秾丽空洞乏物的诗风.神宗之所以因一个士人的文风即欲惩治,是他看到文学对政治的巨大作用及影响,即文学影响着承担国家基石重要角色的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文学对政治有巨大影响,政治对文学也有非常大的作用.其中尤以统治者对待文学的态度及思想文化政策对文学发展影响巨大.《挥麈后录》卷之一提到:
徽宗居藩邸,已潜心词艺。即位之初,知南京曾肇上所奉敕撰《东岳碑》,得旨送京东立石。上称其文,且云:“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韩师朴云:“巩也。”子宣云:“臣兄遭遇神宗,擢中书舍人,修《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与欧阳修、王安石皆名重一时。”上颔之。由是而知上之好学问,非一日也。[3]81
王明清在《挥麈后录》卷之七再次提及:“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3]184徽宗“在潜邸日,已自好文”,对文学艺术颇为痴迷.检阅《宋诗纪事》发现,爱好文艺是宋代统治者的普遍情况,“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7]卷一,p2,“真宗皇帝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可谓好文之主也”[7]卷一,p4.
宋代统治者热心文艺,还特别重视文化典籍整理.《挥麈前录》卷之一提到了这个对宋代文学面貌影响甚巨之现象:“国朝承五代抢攘之后,三馆有书仅万二千卷.乾德以后,平诸国,所得浸广.太宗乡儒学,下诏搜访民间,以开元四部为目,馆中所阙及三百已上卷者,与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馆之书别为书库,目曰秘阁.真宗咸平三年,诏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一卷,给千钱.送判馆看详,委是所少书数及卷秩别无差误,方许收纳.其所进书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试问与出身.又令三馆写四部书二本.”[3]17-18这一做法极大促进了士大夫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热情,据《挥麈前录》卷之一所记,“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3]18,推动了宋代文学向学问化、典实化方向发展,表现出不同于前代文学的显著特点.杨亿《西昆酬唱集序》指出其创作乃“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亦言明“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就促进了宋代文学“以才学为诗”的特征.
宋代政治对文学的推动促进作用,除上述两点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相对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与舆论氛围.陈寅恪《寒柳堂集·论再生缘》指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这也在《玉照新志》卷第五中得到印证:
《诗话》云:昭陵时,近臣赋诗,一联云:“秦帝宫成陈胜起,明皇殿就禄山来。”或有谮于九重者,上览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台”,即不复视。天语以为器量如此,何足观耶?谤焰遂熄。呜呼!昭陵岂不见全篇?倘尽以过目,则不可回互矣。此尧、舜之用心,宜乎享国长久。[2]209-210
宋仁宗面对罗织谮语选择了“即不复视”的态度,由之可以看出宋代相对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与之相应,宋代舆论氛围也相对宽松,仁宗曾“诏群臣实封言时政阙失”[8]卷五十六宋纪五十六宋仁宗嘉祐元年纪事,p1363.宽松的环境及氛围促成了士大夫慷慨任气及喜辩论的性格特征,“感激论天下事、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遂成为当日士人的普遍风尚”[9]导言,p2-3.
宋代文学的自由气氛是相对的,提及宋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北宋后期的党争及文字狱对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挥麈录余话》卷之二载:
绍圣初,治元祐党人。秦少游出为杭州通判,坐以修史诋诬,道贬监处州酒税。在任,两浙运使胡宗哲观望罗织,劾其败坏场务,始送郴州编管。黄鲁直罢守当涂,寓居荆南,作《承天院塔记》,湖北转运判官陈举迎合中司赵正夫,发其中含谤讪,遂编管宜州。陈举者,乃宗哲之婿,可谓“冰清玉润”也。[2]44
此处提到秦观与黄庭坚的贬谪均因时人“罗织”,而当时士人还极有可能只因诗文里的一句话致罪于身.《挥麈后录》卷之六记汪辅之贬官,即因简单的一句话获罪:“汪辅之登第,熙宁中,为职方郎中、广南转运使.蔡持正为御史知杂,摭其谢上表有‘清时有味,白首无能’,以谓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以卒.”[3]160
文字狱及党争使北宋后期士人或多或少在潜意识中形成了噤颤畏祸的性格.往日唐人身上那种俊朗自信的精神气质、昂扬阔大的生命胸怀已不多见.王明清敏锐地把握到了党争政治环境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挥麈后录》卷之六载:
范景仁尝为司马文正作墓志,其中有曰:“在昔熙宁,阳九数终。谓天不足畏,谓民不足从,谓祖宗不可法,乃裒顽鞠凶。”托东坡先生书之,公曰:“二丈之文,轼不当辞。但恐一写之后,三家俱受祸耳。”卒不为之书。东坡可谓先见明矣。当时刊之,绍圣之间治党求疵,其罪可胜道哉!陆务观云。[3]165
这里苏轼拒绝书写范镇为司马光所作墓志的原因,“但恐一写之后,三家俱受祸耳”,并非出于元祐年间二人的矛盾.“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赐银绯.二月,迁中书舍人.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10]附录一铭传,p2807苏轼于熙宁二年二月还朝后,初次体味到党争之烈,即有了全身避害的想法,于熙宁三年所作《送刘攽倅海陵》“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11]卷六,p243即可一窥端倪.遭遇“乌台诗案”沉重打击后的苏轼居黄州期间,“轼素喜作诗,自是平居不敢为一字”[12]卷十,p114,此语虽稍涉夸张,苏轼居黄期间创作了不少文章,只是直击时弊之语少了许多而已,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党争及文字狱对苏轼心理的影响.
这样的政治环境对宋代士人之影响非仅限于苏轼一人,而是在当时士人身上普遍存在.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即是此意.从众多记述中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人相比于唐人而言,生活重心由外在功名追求转向内在生命意义探寻,因而宋人相对趋于内敛温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同宋代党争、文字狱的政治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王明清的笔记著作可为文学研究者提供的宋代文学宏观“生态环境”维度,并不仅限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环节,还包括其他方面.从思想史角度看宋代文学,《投辖录》“蓬莱三山”载:
祥符中,封禅事竣,宰执对于后殿。真宗曰:“治平无事,久欲与卿等至一二处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内侍数人入一小殿。殿后有假山甚高,而山面有洞。上既先入,复招群公从行。初觉暗甚,行数十步则天宇豁然,千峰百嶂,杂花流水,尽天下之伟观。少焉,至一所,重楼复阁,金碧照辉。有二道士,貌亦奇古,来揖上,执礼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逊让,然后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论皆玄妙之旨,而肴醴之属又非人间所见也。鸾鹄舞于堂,笙箫振林木,至夕而罢。道士送上出门而别,曰:“万机之暇,毋惜与诸公频见过也。”复由旧路以归。臣下因以请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谓蓬莱三山者。”群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后亦不复再往。不知何术以致之。祖父闻于欧阳文忠公。[2]79
真宗与宰执重臣前往“蓬莱三山”,与二道士相得甚欢.这对考察宋代“三教浑融”思想史状况有所裨益,从中可看出宋代统治者与道士之间良好的关系.统治者的接受许可,对道学在宋代的发展以及推动儒、释、道三教浑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群臣位列道士之次,更是可以看出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士大夫对道学的接受认可.《挥麈录余话》卷之二记载士人同道士的交游称:“宣仲昔在京师为学官日,与侍晨道士时若愚游.”[2]53亦不难看出道学在宋代具有较高地位.
宋代各派思想文化已趋融合,形成三教融合之势,文化精神渐趋收敛.受此影响,宋代士人创作了一定数量的道趣诗,如苏轼《楼观》“闻道神仙亦相过,只疑田叟是庚桑”,刘攽《拟古六首》其五“嵯峨三神山,浩荡仙圣游”,陈抟《赠金励睡诗》其二“至人本无梦,其梦本游仙”等,亦可见道教对宋代文学之影响.
文学的微观生态在于文艺发展同创作主体情性之间的关系,文士间的交游唱和是考察文学家主体情性不可忽视的维度.王明清笔记著作中的文士交游,如《挥麈后录》卷之七:
崇宁三年,黄太史鲁直窜宜州,携家南行,泊于零陵,独赴贬所。是时外祖曾空青坐钩党,先徙是郡。太史留连逾月,极其欢洽,相予酬唱,如《江樾书事》之类是也。帅游浯溪,观《中兴碑》。太史赋诗,书姓名于诗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诗文一出,即日传播。某方为流人,岂可出郊?公又远徙,蔡元长当轴,岂可不过为之防邪?”太史从之,但诗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随”,盖为外祖而设。[3]178
王明清的外祖父曾纡同黄庭坚在宜州交游唱和,并将作品结集.宋代不仅文士之间交游唱和,有时酬唱活动会由最高统治者组织,如《挥麈录余话》卷之一载:“明清顷于蔡微处得观祐陵与蔡元长赓歌一轴,皆真迹也.今录于后:‘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斋宫即事,赐太师:报本精禋自国南,先期清庙宿斋严……太师臣京恭和.’”[2]11
宋代士人乐于交游的情性爱好对当时文学之影响,既表现于宋代文学中出现了较多的赓和唱酬之作,还表现在促进了宋代诗社的形成与发展.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13]收录现存宋人唱酬应和及诗社总集6种:李昉编《二李唱和集》、杨亿编《西昆酬唱集》、佚名编《同文馆唱和诗》、朱熹编《南岳唱酬集》、邵浩编《坡门酬唱集》、吴渭编《月泉吟社》.该书“附录散佚宋人总集考”收录散佚宋人唱和及诗社总集36种,如王溥编《翰林酬唱集》、丁谓编《西湖莲社集》、欧阳修编《礼部唱和诗集》、廖伯宪编《岳阳唱和》、熊克编《馆阁喜雪唱和诗》等.宋代士人数量如此丰富的唱和及诗社酬和之作,足以证明交游唱和在当时士大夫中受欢迎的程度.
交游成为一种时尚,必然会对士人主体性格产生影响,进而对文学面貌产生直接作用,这正是宋代士人乐于交游的主体情性对宋代文学的深层影响所在.因宋代士人交游多围绕自然环境展开,形成了热爱自然、萧散洒脱之主体性格,进而使宋代文学于“筋骨思理见胜”之外呈现一种平淡自然的文学面貌.如范仲淹《秋香亭赋并序》:“一朝赏心,千里在目.时也,秋风起兮寥寥,寒林脱兮萧萧.有翠皆歇,无红可凋.独有佳菊,弗冶弗夭.采采亭际,可以卒岁.”[14]平淡之辞中尽显喜爱自然之情.
宋代士人除热衷交游外,还善于戏谑.《挥麈录余话》卷之二载:
东坡先生出帅定武,黄门以书荐士往谒之。东坡一见云:“某记得一小话子,昔有人发冢,极费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语盗曰:‘公岂不闻此山号首阳,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盗慊然而去。又往它山,治方半,忽见前日裸衣男子从后拊其背曰:‘勿开,勿开,此乃舍弟墓也。’”[2]40-41
苏轼以伯夷、叔齐为戏谑主人公,以其劝阻盗墓人而展开,构思巧妙生动,足见苏轼善于戏谑之性格.善谑是宋代士人的普遍风尚,有时亦会因之致祸上身,《挥麈后录》卷之六载:“一日聚饭行令,鲁直云:‘欲五字从首至尾各一字,复合成一字.’正夫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鲁直应声曰:‘来力敕正整.’叶正夫之音,阖坐大笑.正夫又尝曰:‘乡中最重润笔,每一志文成,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鲁直曰:‘想俱是萝卜与瓜□尔.’正夫衔之切骨.其后排挤不遗余力,卒致宜州之贬.一时戏剧,贻祸如此,可不戒哉!”[3]165
宋代士人善戏谑之性格对文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较多地“以文为戏”“以诗为戏”,于思理之外有了活泼灵动之色彩.《宋人总集叙录》著录了两部宋人“以文为戏”的著作:林希逸、胡谦厚编《文房四友除授集》,郑持正编《文章善戏》.《文房四友除授集》叙录称:“唐韩愈《毛颖传》,宋张耒《竹夫人传》等皆嗣其响,然作者甚少,到南宋末造,此种文体方再兴并转盛,所谓‘以文为戏’是也.”[13]373足见宋人在喜于戏谑的心灵中对“以文为戏”创作之偏爱.
宋代文学在“以文为戏”之外,尚有一不可忽视之现象,即“以诗为戏”.宋代文学中不仅出现了较多的“戏答”“戏赠”“戏和”诗作,如杨亿《戏赠颍州万寿尉吴待问》、欧阳修《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苏轼《戏赠》等;还多以日常习见之物为其戏谑诗作之对象,绝妙灵动,如范仲淹《咏蚊》诗:“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蚊子可作戏谑对象,反映出对日常生活的细致灵动、物我同一的独特审美灵感.
经由唐代韩愈对儒学“经世致用”的重振,到宋代经世之学成为宋学主脑.经世之学对宋代士人主体情性之影响,形成了刚毅不屈、达观乐道之“君子人格”.《挥麈后录》卷之七载:
东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史君还。”太守刘士彦本出法家,山东木强人也,闻之,亟谒东坡云:“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徙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东坡笑曰:“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徙二年以下。”[3]176-177
苏轼面对泗州守对其所作辞章恐致祸之语而答以“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徙二年以下”,可见出苏轼面对仕宦浮沉的从容达观态度与刚毅不屈性格.
宋代士人“士志于道”情性对文学的影响,还在于宋代文学普遍呈现出对君子人格“士气”的鼓励赞育.范仲淹《上都行送张伯玉》:“南山张公子,气象清且淳.怀有绮绣文,朝无瓜瓞亲.寸心如铁石,不羞贱与贫.”对奸邪之人,宋代士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呈现出了慷慨昂扬、骨貌凛然的气势.
三、结 语
综上所述,王明清笔记著作对深入探讨宋代文学基本面貌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为古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笔记观照维度.
首先,王明清的笔记著作是其抒发思想见解、记录文学典实的重要载体.“昔人不以蹈袭为非”概念的提出,反映出宋代文学于宋祁倡言“夫文章必自名一家”与苏轼主张“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的自我树立外,注重师法前代、重视典实的学问化倾向,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江西诗派何以会在宗杜的同时又提出“点铁成金”及“活法”之说.从他的文学政教论观点,可以看出儒学于宋代复兴的重要现象,从而解释宋代文学何以出现较多如田锡《上太宗答诏论边事》、苏洵《审势》这类慷慨言事、直击时弊、献言陈策的作品,对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文学影响至深.这也是欧阳修、范仲淹等人所倡导的以“士气”“君子人格”为内核的“庆历风神”形成的内在思想动因.王明清笔记著作中的这些主张无疑对研究者探视宋代文学特征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王明清笔记著作中对一些作家作品的介绍评价,构成了这些作家接受史研究上不容忽视的一环.如对苏轼作品“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的评语,可看出苏轼在生前即有巨大影响,可为探究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提供佐证.
最后,王明清笔记著作提供的宋代文学生态考察的视野,使研究者得以对宋代文学一些特征的形成之因有所把握.就文学的宏观生态而论,记述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宋代统治者对文章教化作用的重视,即可解释宋代统治者何以力矫五代文风之弊及宋代末期诗风何以未如晚唐复归于绮艳.统治者爱好文艺、注重典籍的整理工作,以及相对宽松的文学创作氛围,构成了宋代文学全面繁荣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讨论北宋中后期士人普遍的噤颤畏祸心态以及文学中较多出现如苏轼《王莽》这样的微言政治抒情诗的成因,王明清笔记著作中记载的党争及文字狱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记述宋代文学的“三教浑融”背景,记述文士同道士交游,可使研究者在思想史的高度上深入把握宋代文学于思理之外,对平淡自然文风的追求及士人呈现出追求养生、注重内在生命意义探寻的普遍趋势.就文学的微观生态而论,记述文士间的交游雅会,热衷戏谑及以道自任的主体情性,对深入把握宋代文学所呈现出的自然灵动、气韵浩然、丰神骨直的风貌,有很大的裨益作用.突破以文学论文学的限制,以文学生态的视野全面深入考察文学思想,正是王明清笔记著作的文学思想在宋代文学观照意义上的最具价值之处.
[1]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6编第2册[G].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6编第1册[G].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4]苏轼.东坡乐府笺[M].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张海鸥.两宋雅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8.
[6]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7.
[7]厉鹗,辑撰.宋诗纪事补订[G].手稿影印本.钱钟书,补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M].标点续资治通鉴小组,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
[9]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0]苏辙.栾城集墓志铭[M]//苏轼.苏轼诗集: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魏泰.东轩笔录[M].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范仲淹.范文正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56.
责任编辑 韩云波
I207.41
A
1673-9841(2015)05-0121-07
10.13718/j.cnki.xdsk.2015.05.017
2014-10-14
张瑞君,文学博士,太原学院文学院,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笔记中的文学思想研究”(10BZW046),项目负责人:张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