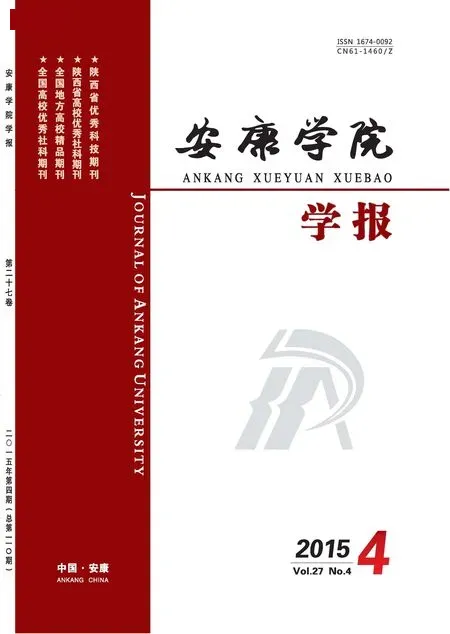论柳永对敦煌词的受容
王 娟
(河南科技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在两宋词史中,柳永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对于他的贡献,众所周知的是他对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然而,柳永对词体的发展,敦煌词已启其端。如慢词,敦煌《云谣集杂曲子》中的《内家娇》即为104字的长调;《倾杯乐》109字,“上片六韵,下片五韵,是更为典型的慢曲长调”[1]。再就词调而言,“敦煌曲子词调名见于《乐章集》者共十六阙,其中《倾杯乐》全同,《凤归云》、《内家娇》部分相同,此外如《斗百花》、《玉女摇仙佩》、《凤衔杯》、《慢卷轴》、《征部乐》和《洞仙歌》等调也有直接和间接的继承关系。”[2]柳词对敦煌词的受容还表现在意象、题材及表现手法等方面,这都说明柳词和敦煌词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的表象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以及柳词对敦煌词的接受在词史上意义,都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
一、从意象分析看柳永对敦煌词创作传统的继承
在两宋词史中,柳永一直被认为是最著名的通俗词人,这和其词语言风格有着莫大的关系。如胡仔引《艺苑雌黄》曰:“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3]“柳永在北宋,犹如乐天之在中唐。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不仅看出柳词的走红,还似乎与敦煌词句有某种嫡传关系。‘明白而家常’的风格……都是从好用俚语俗词着眼。”[4]这实际上指出了敦煌词与柳词的传承关系。我们试从意象的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
从《尊前集》到《花间集》,再到欧阳修、二晏等宋初词家,词作中的意象逐渐趋于富丽堂皇,充斥着一种极致的富贵气。试看以下作品:
和凝《临江仙》:“披袍窣地红宫锦,莺语时转轻音。碧罗冠子稳犀簪,凤凰双飐步摇金。肌骨细匀红玉软,脸波微送春心。娇羞不肯如鸳衾,兰膏光里两情深。”
欧阳修《越溪春》:“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阆苑繁华地,傍禁垣、珠翠烟霞。红粉墙头,秋千影里,临水人家。归来晚驻香车。银箭透窗纱。有时三点两点雨霁,朱门柳细风斜。沈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
金步摇、金鸭、金杯、玉壶、玉炉、红宫锦、珠翠以及诸如此类的玉墀、银簟、银带、银屏、玉鞭、金舆,碧流、玉笼、玉钗、红罗、绿鬓、红额等意象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奢华、艳丽而眩目的图景。这股浓重的富贵气与五代至宋初词的功能以及词的创作环境、作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表明,“花间派”词人乃至欧阳修等人的作品,受齐梁宫体诗和晚唐五代宫词的影响更深。他们的创作虽然表现出文人化、典雅化的努力,但词的意象空间却由此变得狭窄。于是,与敦煌曲子词一脉相承的柳永开始改变这种状况,使词向着它诞生时的状态转变。我们从意象使用的频率上可以观察到这种变化。

表1 五代宋初词色彩意象统计表
如表1所示,敦煌词和柳永词并不倾向于大量使用具有奢华色彩的意象。如果这组数字的对比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么从色彩意象的组合中还可以看出差别。敦煌词与柳永词中尽管也有玉箫、银烛一类的意象,但大部分色彩用于描述景物而非奢华的器物。比如:在《花间集》中,“碧”多见于“碧瓦”“碧玉”;“翠”多见于“翡翠”“珠翠”等。而在敦煌词和柳永词中,则多见于“烟翠”“碧霄”“碧波”“翠柳”等。同是咏妓词,试看以下两首词:
毛熙震《后庭花》:“轻盈舞妓含芳艳。竞妆新脸。步摇珠翠修额敛,腻鬟云染。歌声慢发开檀点,绣衫斜掩。时时纤手匀红脸,笑拈金靥。”
柳永《木兰花》:“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妒。玲珑绣扇花藏语。宛转香裀云衬步。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花楼东畔住。”
比起花间词人,柳永不再追求用语言色彩的繁华侬丽去冲击读者,而是向敦煌曲子那种初生的民间词一样,用一种清新流利的笔触刻画描写对象及以直白的叙述来表达心情,这就打破了长久以来垄断词坛的那种表面奢靡华艳而内容空洞贫乏的词风。这其实表现出了柳永要摆脱唐、五代文人词的局限的努力。为此,他需要重新回归民间词传统。也正是这种回归,对他的创作乃至宋词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从创作题材看柳永对敦煌词的接受
词产生于民间,在文人接手以前,它的题材丰富多样,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二北先生在其《敦煌曲初探》中,更将敦煌曲分为二十类,即:疾苦、怨思、别离、旅客、感慨、隐逸、爱情、伎情、闲情、志愿、豪侠、勇武、颂扬、医、道、佛、人生、劝学、劝孝以及杂俎等。而“唐末温庭筠登上词坛,标志着曲子词的自发无序的原始状态的结束,而走向定型化、规范化的成熟阶段,同时也走入了单一化、统一化的狭窄蹊径。”[5]词走上狭境,和词人的题材取向有关。《花间集》500首曲子中,仅仅有43首与描写女性无关;到了宋初,欧阳修的写景词和范仲淹的边塞词在众多作家作品中亦是凤毛麟角,最多的还是以二晏作品为代表的咏妓词或者“托女子之口言己情”的闺怨词。
柳词和敦煌词一样,都表现出了题材多样性的特点。《乐章集》涉及敦煌曲子词中的大部分题材。有咏妓、闺怨宫怨、羁旅行役及相思、景物节令、咏史怀古、祝寿和投献、游仙、送别以及咏物词等等。历来论者对柳永这些词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如陈廷焯曰:“耆卿词,善于铺叙,羁旅行役,尤属擅长。”[6]王灼引宋人言:“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7]李调元称:“诗有游仙,词亦有游仙,人皆谓柳三变《乐章集》工于帏帐淫媟之语,羁旅悲怨之辞。然集中《巫山一段云》词,工于游仙,又漂漂有凌云之意,人所未知。”[8]题材的多样性,体现出柳永扩大词境的努力,也反映了他的词作和敦煌词的亲缘关系。
女性题材更能说明这种关系。《花间集》以来的文人词,多从赏玩的角度描写艳情。再联系上文对文人词意象的分析,不难得出他们的创作其实与宫体诗及宫词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柳词的女性题材,有论者认为柳永“以长调慢曲铺叙展衍,极尽‘尊前’、‘花间’纤艳之情。……柳词既由‘尊前’、‘花间’浸润而来。”[9]应该说,柳永的一些词作,的确表现出了花间词的创作特征。但这种表面的相似,并不能说明柳词是由“‘尊前’、‘花间’浸润而来”。相反,柳词和敦煌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对爱情生活的珍视,对下层女性甚至对妓女的极大同情;细腻的心理刻画,平实而真挚的语言等等。
然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它们直露无隐的抒情方式。敦煌女性题材词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抒情明白直接。如《菩萨蛮》(发愿),以超乎常态的夸张表现永恒不变的情感。这类词往往一开头就会表露心态,情感抒发不可遏抑。如《望江南》(莫攀我),开头即以“莫攀我,攀我太心偏”表露对强迫的不满与愤恨;《南歌子》(悔嫁风流婿),一个“悔”字直接把读者引向情境。这种一开头就表露心态的表现手法,在当时的一般文人词中却是十分罕见的。而柳词处理“爱情”的方式则表现出了敦煌词的接受。如他的《菊花新》:
欲掩香帏论缱绻。先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
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
在这首词中,一个“欲”字就把情感抒发引入主题,直露而热烈,我们看不到传统文人笔下女性的矜持。“他的风格近于通俗。同样可以由此看出,他问情道情几乎直言无隐,几乎濒临‘滥情’的地步。传统文人词客笔下的个人与情爱总是保有某种美感的距离,欲语还休。但在柳永笔下,这种传统价值观念荡然无存。”[10]如写与妓女的合欢:“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墙头马上初相见,不准拟、恁多情。昨夜杯阑,洞房深处,特地快逢迎。”(《少年游》(层波潋滟远山横))这种写实的风格,没有了其他文人词的含蓄蕴藉。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文人词客之中,深受《云谣集》与其他敦煌曲词影响者,柳永是第一人。”[10]
就女性题材词作的思想意义而言,柳词和敦煌词表现出的反抗意识是最需我们注意的。敦煌词写普通女性的悲恨,如《捣练子》六首写孟姜女故事,完整地表现离别、送衣、骂秦、哭城、收骨等情节,控诉繁重的徭役给百姓造成的痛苦。甚至写到妓女的反抗:“严格的讲,敦煌词没有狎妓词,只有弱女子的反抗词。”[11]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望江南》(莫攀我)。柳词中的女性,大多是青楼歌女。当柳永描写这些女性的时候,他的笔触是饱含深情的。在《少年游》十首这组词中,他写与妓女的合欢,倾诉对她们的仰慕,赞美“丰肌清骨”的舞女,带着深情抒写她们的离恨。其《少年游》(其八)写道:“一生赢得是凄凉……王孙动是经年去,贪迷恋、有何长。”她们是多情的女子,想不迷恋,却又思念,她们的付出,得到的只是王孙们的忍心“相忘”,最终“一生赢得是凄凉”。这是她们的群体性命运。这种控诉,和敦煌词《望江南》(莫攀我)是一样的。
另外,如果我们再加以分析,便会发现,柳永对女性的同情,是建立在对她们热情歌颂基础之上的。这些女子,无不才貌超凡。她们柔媚多情,对男子有刻骨铭心的爱恋,而由此又容易感伤。对于这种创作模式的心理成因,是他“以幻觉的已身在众多女性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来反证自己的才学与地位,从而获得心灵上的自我慰藉。”[12]当这种创作心理和反抗意识及自己的身世之感直接联系起来时,柳永在词中所抒发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享乐和淫乐之情了,更重要的是对个体价值的体认和个性自由的追求。如在《黄钟宫·鹤冲天》(黄金榜上)这首词中,柳永写自己狎妓,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不得志(“明代暂遗贤”)后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一腔激愤。“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言,柳词有失忠厚。以今观之,柳词中表现的反抗意识,却有着较大的社会意义。”[13]这正昭示了柳永的女性和艳情题材词作对敦煌词的接受与开拓。
三、从叙事看柳永对敦煌词的继承
敦煌词的一大特点,是它的叙事性。“单纯描绘自己的感情的敦煌曲子词是极少的,而大都是那些缘事而发的词。”[11]甚至一些浓郁的抒情性的词作也包含着叙事性,如《菩萨蛮》(发愿)。敦煌词的叙事性使一些词作具有了戏剧色彩,如《南歌子》(相思问答):
斜影朱帘立,情事共谁亲?分明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谁绾?甚人踏破裙?蝉鬓因何乱?金钗为甚分?红妆泣泪忆何君?分明殿前直说,莫沉吟。
自从君去后,无心恋别人。梦中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自绾,被狲儿踏破裙。蝉鬓朱帘乱,金钗旧股分。红妆垂泪哭郎君。妾似南山松柏,无心恋别人。
该词上片叙写男子回家,看到妻子的变化,心生疑窦,一气连提五个问题。“莫沉吟”一句可想其急迫心情,下片则为女子陈述自己独居时的种种情态。这首词中的情节冲突极富戏剧性,夫妻二人之间的问答别出心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体现了民间词人的卓越艺术才能。
当词从民间转到文人手中时,词的叙事性逐渐让位于抒情性,以秾丽细密的笔触,抒写侧艳哀婉之情。柳永却继承了敦煌词的叙事传统,刘熙载云:“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14]如《婆罗门令》(昨宵里):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中夜后、何事还惊起。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
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攲枕难继。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此词叙述自己睡前、梦中、惊梦、醒后的情景,或插叙、或补叙,结构上却不显散乱,表现出很高的叙事技巧。“长于叙事,写得比较详尽直率,几乎是所有民间文学以及受民间文学影响较深的文人作品的特色。……柳词被不少人评为卑俗,不得为词坛正宗,这就规定了这种特色不能在后来的词作中得到发展。”[15]也正如此,柳词的存在才弥足珍贵。
文人词以抒情为主,而以小令最具代表性。而柳词为了突出叙事的艺术性,就不能不用铺叙敷衍的手法。对柳词的铺叙,论者多认为是受赋的影响。如日本学者宇野直人认为,“柳永对适合慢词的各种手法都进行了摸索,连同‘赋’的手法一并吸取之。”[16]但如果联系柳词对叙事的重视,便不难得出,他受敦煌词的启示更多。而且词的铺叙手法本也始于敦煌词,上文所引《南歌子》(相思问答)便是一例。这足以反映出柳词和敦煌词之间的亲缘关系。柳词对铺叙手法的运用,使叙事不仅不影响抒情,反而有利于表现复杂、深切的情感。如《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锦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问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此词“惨绿愁红”的刺激性环境描写,“暖酥消,腻云亸”浓艳笔触下的人物形态,“终日厌厌”所渲染的寂寞心境,以及下片的串串相思痴语,层层铺陈,畅快淋漓地把歌妓的一腔闺怨抒发出来。完全没有其他文人小令的含蓄蕴藉。所以李端叔评柳词云:“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17]而所谓“韵终不胜”却也可从反面论证柳永对敦煌词的借鉴。
对叙事的重视,使柳永在创作中继承了敦煌词的铺叙手法。而他较高的文学修养,又使他把这从民间文学中习得的创作方法,从对人物情事的素描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如羁旅行役、都邑题材等等。如他的《破阵乐》(露花倒影),这首词描述了北宋仁宗时君臣士庶游赏汴京金明池的一次盛况。从晨景写起,至暮景结束,铺写一天的情景,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充分体现了柳词“层层铺叙”的特点。又其将叙事、抒情、布景巧妙安排,而创造出独特的时空结构方式。如《浪淘沙》(梦觉),第一片写现在的痛苦,第二片追忆过去的欢愉,第三片设想从将来回忆现在。又如《八声甘州》(对潇潇),在此词中作者设想情人思念自己。这种多重时空结构方式,是柳永对词体发展的一大贡献。而这些特点,正是柳永在民间词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变化的结果。
四、柳永接受敦煌词的意义
敦煌曲子词是民间词的典型代表,正如前面所论,它的题材,是丰富多彩、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它的形式,是灵活多变,无所拘泥的样式;它的风格也是多变的。詹安泰先生曾指出,从《敦煌曲》来看初期出现的词篇,就具有多种多样的艺术风貌,如雄壮、爽快、激切、泼辣、婉曲、真率、悲痛、隽永、清新、质朴、精绝、明丽等等。这些艺术风格的表现,在宋词中都可以看到。以上足以说明,民间词不仅是词的最初样态。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局限,词转到文人手中时,文人词渐渐走入狭径。“他们运用的形式,绝大部分是小令;他们作品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因而他们的艺术风格也不能不局限于‘婉约’、‘柔厚’这些方面。”[18]扭转这种情况的是柳永。对民间词传统的继承使柳永能够摆脱晚唐、五代文人词的局限而自成一家,并在宋词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他对慢词的发展巧妙地使用铺叙手法等诸多方面。
柳永接受敦煌词的意义还在于对民间词生活属性的回归。“民间文学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与其说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不如说它是生活的。”[19]我们说的这种生活,不是士大夫贫乏空虚的日常生活,而是广阔的民间生活。柳永作为落魄文人,他所接触的,是完整的社会生活。他了解士大夫阶层的笙歌艳舞,也品味过贫民百姓的喜怒哀乐。他的词,是敦煌曲子词的继续。除了上文所论的意象和题材方面的继承,在柳词中,还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我们在五代和宋初词人笔下,看到的不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的奢华享乐,就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无尽愁绪。然而,正如生活五味杂陈,柳词写尽了人生中的喜怒哀乐。《望海潮》(东南形胜),表现出柳永面对繁华都市的欣喜与自豪;《凤归云》(向深秋),透出柳永对流年的感叹和出世之想;《西江月》(腹内胎生异锦)尽显才子的风流自赏;《雨霖铃》(寒蝉凄切)则是人间离别的满腔深情与留恋。这些无疑对柳永以后诸多词人开拓词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胡适先生认为,文学样式生于民间而死于文人之手。词被文人采用之后,就渐渐远离民间,从而逐渐僵化乃至死亡。柳永借鉴敦煌词的意义,正在于使词重新从民间汲取营养,从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柳永的词是“平民的文学”[20],他作为一个沟通民间词和文人词的词人,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木斋.论柳永体对民间词的回归[J].东方论坛,2005(4):47-52.
[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23.
[3]胡仔.苕溪渔隐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19.
[4]魏耕原.唐宋诗词语词考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19.
[5]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7.
[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2.
[7]王灼.王灼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5:232.
[8]李调元.雨村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1391.
[9]邓乔彬,周韬.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J].东南大学学报,2007(4):78-85.
[10]孙康宜.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11]吴国瑞,王文宝,段宝林.中国俗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261.
[13]房日晰.欧阳修柳永之艳词比较[J].南昌大学学报,2003(2):86-90.
[14]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8.
[15]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7.
[16]宇野直人.柳永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3-74.
[17]张宗橚.词林纪事[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2:104.
[18]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M].汤擎民,整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427.
[19]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1.
[20]胡适.白话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