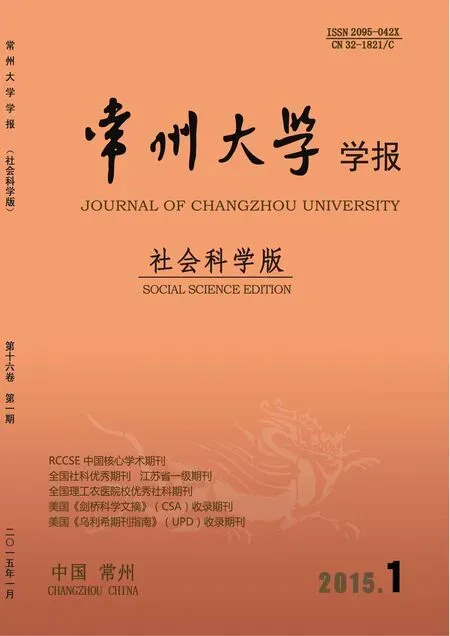沃尔夫林风格学理论的特点及问题研究——以《哀悼基督》主题为例
张一弛,樊 波
(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210000)
一、沃尔夫林与风格学理论
艺术风格学的方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美术史学界从形式风格角度研究美术史的一种新的方法。目前,风格学研究的初步确立可以追溯到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在他的理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艺术意志”这一概念,即艺术作品是人类根据特定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同世界抗衡的根本态度——艺术意志——而创造出来的。这个概念在19世纪末形成,明显受到了当时德国古典哲学中唯意志论、历史决定论的影响,是20世纪初德语国家流行的艺术学术语。“李格尔正是运用这个概念,排除艺术外在的东西,着重分析艺术风格自身内在发展的历史,他的理论改变了19世纪的艺术史写作方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艺术史界与美术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32
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hrich Wolfflin,1864—1945),是瑞士艺术史家和美学家。他先后任教于瑞士、德国等地的多所名校,如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苏黎世大学等。沃尔夫林对于风格学理论的研究较之李格尔则更为系统和完整。他在其代表作《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提供了一种陈述性的研究模式,其基础建立于严格的视觉分析,即通过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和形式比较来探索它们的一般特征。经过长期的研究,这一方法先后归纳出了五对具有辩证关系的基本概念:线描和涂绘、平面和纵深、封闭的形式和开放的形式、多样性的统一和统一性的统一、清晰性和模糊性。沃尔夫林以这五对基本概念作为准则,对文艺复兴艺术与巴洛克艺术进行了比较,认为艺术不是人类模仿出来的历史,而是视觉经验的历史。因为人们是以特殊的方式来观察自然的,既有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也有表达这些需求的特殊手段,沃尔夫林由此得出了“一部美术史就是一部风格的演变史”的观点。
英国的艺术史界认为沃尔夫林是“那个时代以德语写作的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各种版本的当代艺术史学思想史论著都不约而同地将他称为最重要的现代艺术史家。国内外美学、艺术批评方面的著作,如文杜里所编的《艺术批评史》、阿诺德·豪塞尔所著的《艺术史哲学》、克莱因鲍尔的《艺术史研究导论》、蒋孔阳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等都普遍认为沃尔夫林是现代艺术史学思想史中的关键人物,并对他推崇备至,甚至于直接以沃尔夫林的理论来代表艺术科学或现代艺术史研究的成果。而德国人自己撰写的《德意志文化史》中,也将沃尔夫林于1915年发表《艺术史的基本概念》作为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事件[2]3-4。
二、风格学理论在美术史中的应用——以《哀悼基督》为例
沃尔夫林的风格学研究对于文艺复兴、巴洛克以及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进行断代和深入剖析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哀悼基督》这一题材,是自中世纪开始的艺术家在绘画、雕塑中经常描绘和塑造的主题。由于这一主题的艺术作品为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艺术家们所表现,因此选用沃尔夫林风格学分析中的几对范畴,对于《哀悼基督》这一主题的探究是十分适用的。同时,通过对这一主题的分析,我们也会产生一些疑问,如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风格转化的原因是否在于画面形式的变化上?五对范畴是否能够真正概括风格变化的本质?
(一)“线描与涂绘”的区分
虽然沃尔夫林的《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认为,15世纪之前的艺术家中没有能够代表线描风格的典型作品。然而14世纪绘画中还是有存在着具有线描特征的作品。这里值得猜想的是,沃尔夫林指出,文艺复兴初期甚至更早的艺术作品中体现线描风格而不具说服力,这可能是出于对当时画家绘画技巧的怀疑。如今来看,13至14世纪的绘画作品中,写实技巧虽然显得比较幼稚和生硬,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乔托为代表的绘画作品中已经明显有了线描风格的端倪。以其作品《哀悼基督》为例,作品中每个人物的线条非常清晰,甚至可以看见衣纹边缘清楚的轮廓线。在这里,乔托将线条作为明确的边界,把形体与形体之间区别开来;每一个实体都是平等着力的。因此,虽然画面内容弥漫着无限的痛楚和哀伤,而作品整体却一致微露着一种古典的高贵和平静。
波提切利是晚于乔托的另一位文艺复兴早期画家,他在约1490年同样创作了《哀悼基督》为主题的作品。在波提切利的这幅画中,线描特征就显得更为明显了:所有人物及人物形象范围外的一切重要物体,都用了线条清楚画出。无论是对基督、圣母或是圣徒的描绘,如果脱离整体,则都可以单独形成个体,就如同雕塑一般分明和醒目。
而到了15、16世纪时,提香所作的《哀悼基督》则呈现出了另外一种面貌:画面中的四个人物,已经不再那么清晰和突出,而是将重点集中于耶稣和圣母。画家大刀阔斧的笔法,使画中实体的线条渐渐融于光线的明暗之中。快捷的笔触似乎有意识地把单个成分连接在了一起,“明暗成了独立的成分,它们在不同的高度和不同的深度上相映成趣。”[3]130提香晚年的绘画作品,已经基本脱离了文艺复兴早期及盛期为代表的线描风格,从而逐渐过渡到涂绘的特征。提香对笔触的运用为造型的表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17世纪的巴洛克画家鲁本斯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
鲁本斯在1602年对《哀悼基督》进行了再次创作,风格非常接近提香:画中实体的轮廓线变得柔软,在细节上的处理甚至能够感受到微微的颤动。这里清晰的线条已经走向瓦解。画面里的线条、光线、色彩已经产生了交流,因此作品会有一种温和的动感和闪烁。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从线描和涂绘的角度分析《哀悼基督》的主题是基本符合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风格的变化。但是,沃尔夫林在对文艺复兴初期关于线描风格的判断仍然是有待商考的。他认为:
“线描风格是按线条观察的,而图绘风格是按块面观察的。因此,线描的视觉意味着首先在轮廓上寻找事物的感觉和事物的美——内部的各种形体也有其轮廓——意味着眼睛沿着边界流转并且沿边缘摸索;而在按块面观察时则注意力撤离了边缘,轮廓作为眼睛的视觉途径来说多少有点受到忽视,而且视觉印象的基本成分是被看成小块面的东西”。[4]22
(二)“平面和纵深”的构成
沃尔夫林指出平面构图在16世纪将图画中的实物结合,并逐个层次都平行于图画的平面,而这种构图,到了17世纪便被纵深构图的形式所代替。同时,他认为与15世纪之前的作品相比,16世纪显得更为平面几何化。事实确实如此,将波提切利的《哀悼基督》与梅西斯的同名作品进行比较。波提切利的画面左侧的人物形象,虽然呈一字排开,但耶稣的身体并没有以横侧面的形态平行于底部,而是呈现了一定的弧度。而前景中,怀抱耶稣头部的圣徒与后景右侧的人物,有了明显的空隙,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空间感。如果波提切利的作品纵深风格仍不明显的话,那么15世纪的艺术家戈斯的杰作《哀悼基督》中体现的纵深感,已经十分清楚了:耶稣的尸体是斜向置于画面中的。后期画家梅西斯作于1511年的《哀悼基督》,画中主要形象都非常清楚地坐落于平面上。前景中基督的尸体几乎平行于底线,后景的人物和风景没有拉开画面距离,空间感不明显。
《哀悼基督》题材由平面向纵深的形式转变是从鲁本斯的作品中体现的。他所创作的两幅同一主题的绘画中,都将耶稣的尸体按透视缩短了。同时这两幅画纵深要素的比例也大大增加了,“透视短缩的尸体完全是自然而然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贯穿空间。”[3]131
(三)“清晰性和模糊性”的表现
从清晰性和模糊性的角度来分析《哀悼基督》,可以说这对范畴是与线描和涂绘的风格相辅相成的。这里就以丁托列托的《哀悼基督》为例来解释模糊性的概念。丁托列托之前的艺术家,如乔托、波提切利等人的画面中都呈现了清晰的人物形象(在上述线描和涂绘中都有阐释),而丁托列托的这幅作品轮廓已经模糊了,人物面部的阴影不再理会塑形基础。圣母的五官也没有清晰的描绘,而是重点表现了深深的眼窝。这样的人物造型,已经基本脱离了文艺复兴盛期的清晰轮廓,但是却让画面更具戏剧张力。而后,卡拉瓦乔的《哀悼基督》表现的模糊性风格更为突出,画面的角度只集中于主角耶稣的尸体,而周围的人物几乎都湮没在了阴影之中。
(四)“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呈现
以“封闭性和开放性”来探讨《哀悼基督》这一主题,可以说是与前文中“平面和纵深”是相对应的,原因在于这两对范畴从不同的角度都涉及了绘画作品构图的问题。我们仍以1511年梅西斯的《哀悼基督》为例。这一作品是祭坛三联画中的一幅,因此采用了传统祭坛画的构图样式。画面中的人物基本处于横向排开的状态,但是有了前后层次的表现。所有的表现对象聚集于画面,人物呈现基本平行于水平线,产生了一种平衡感,由此整幅作品使主题的氛围显得更为庄重。所谓平衡感,是指取得画面两半面的比例基本相同,由此作品形成了“封闭性”的构图。这一构图模式在文艺复兴时期盛为流行,以《雅典学院》、《西斯廷圣母》为典型。到了梅西斯的时代,“封闭式”已经有所变化,构图不再如之前那般严谨,但基本保持平衡。但进入以鲁本斯为代表的巴洛克时期,则打破了这种平衡。在他的《哀悼基督》中,人物以侧面、正面形象相互穿插,耶稣在画中的表现不但有了纵深感,而且使整幅构图不再呈现完整的框架,对角线构图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于此画面趋向于一种自由开放的形式,从而更具动感。
(五)“多样性和同一性”的探讨
这一对范畴与“线描和涂绘”的呈现有着很大关联,但“多样性和同一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16至17世纪艺术风格的转变上。17世纪的《哀悼基督》系列作品中,艺术家们创作的一切都服从于此母题。以鲁本斯、卡拉瓦乔的同名作品为例,他们作品中的表现对象紧紧围绕着主体基督这一形象,单个的形体是无法脱离画面而独立存在的,从而形成一种同一性,由此主题被突显出来。但是16世纪之前的作品,由于线描风格的明显,画面中的人物形象则可以完全独立,每个部分都可以作为作品局部细致的描绘,从而有了“多样性”的特征。但是,沃尔夫林又认为“封闭形式的原则自然意味着图画是一个统一体”[3]101。因此我们若从“封闭性和开放性”构图的角度来分析“多样性和同一性”则会发现,16世纪之前的风格是为“同一性”,而17世纪巴洛克为代表的则为“多样性”,由此与前文的论述产生了矛盾。因此,“多样性和同一性”用于概括风格转变的合理性也是形式分析中需要商榷的问题。
三、风格学研究中的影响及问题
通过上述《哀悼基督》主题的分析,可以看出风格学能够较为系统地诠释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艺术形式特征的转变。他的方法不仅在艺术研究领域,而且在其它人文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随之问题也出现了,沃尔夫林将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艺术的风格变化推广到了艺术发展的每个时期,认为这一发展模式可以阐释为任何时期的风格发展,它们在西方艺术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演,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首先,在对《哀悼基督》主题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纵深感和平面性,或是清晰性与模糊性,都是以“线描和涂绘”这对范畴作为基础而衍生的。其次,笔者认为由“线描和涂绘”来决定风格变化的根源在于:艺术家贯穿和描绘事物的位置和角度不同。具体来说,则是对于光的表现而导致的风格上的分歧。文艺复兴盛期的绘画之所以呈现线描、平面、清晰的风格,原因在于艺术家将光线几乎均匀地分布在了实体中。而文艺复兴后期到巴洛克时期,光线开始从画面的某个角落射出,而聚焦于画面的主体,那么画中的实体则不再呈现均匀的明暗了。但是,风格学的运用在这里似乎没有涉及到关于光源问题的讨论,这应该说是形式分析中需要探究的本质问题。最后,在西方艺术史发展到后期,特别是进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古典主义绘画中那些关于“线描”或是“涂绘”的具象绘画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形式分析法已经显然不适用于画面风格的总结了。另外,我们假设以伦勃朗为个案,运用沃尔夫林风格分析法的五对范畴对其作品进行讨论,发现很难解释一个艺术家在创作生命的不同阶段风格转化的原因:伦勃朗是处于巴洛克时期的代表艺术家,但是其绘画作品,在其初期仍然显现了线描风格的特征,中期直到晚年的风格则转变为典型的涂绘风格。这类风格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处于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家倘若出现了线描的风格,我们就很难总结这类风格转变的原因了。由此可见,沃尔夫林的方法是不适用于以所有艺术家个体为研究对像来进行分析的。
四、结语
总的来说,沃尔夫林的风格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改变了艺术史家或作者存疑的作品的目录,而缺少一个时代、民族、区域的艺术作品内在演变逻辑和发展的规律的局面”[5]78-82。因此在美术史研究中,风格学的运用已经非常普遍,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早期留学德国的美术史论家滕固先生将西方的“艺术风格学”概念介绍到中国美术史学界。他吸收和运用了沃尔夫林的风格分析法,主张根据风格来划分历史时期,改变了绘画史陈旧的体例结构,使枯燥乏味的美术史焕发出新的光彩,这在其著作《唐宋绘画史》中是明显能够体现的。
虽然从沃尔夫林提出的五对范畴来看,其风格分析法似乎只关注于艺术品外部形式的剖析,从而来说明风格转变的原因。这也正是他基于“观看方式”的改变而阐述艺术史演变的方式。但是通过前文中以同一主题的形式分析来看,艺术风格正是以形式分析为基础“遵循着它自身法则”而改变的。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沃尔夫林这种“观看”的历史是有着来源于艺术品内部逻辑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沃尔夫林的风格分析理论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正如上文所述其方法的适用性、覆盖面是无法真正概括艺术史每个时期的风格变化,这正是因为艺术形式的历史是无法与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相割裂的。但也许正如沃尔夫林自己所说:“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权讨论这两种类型。一切都是过渡,要对把历史看成是一面永无止境的潮流的人提出反驳是很困难的。对我们来说,理智的自卫本能要求我们应当根据若干结果对大量的事件加以分类。”[3]283
[1]程沁.艺术风格学与美术史研究[J].新视觉艺术,2009(3):32-34.
[2]周保彬.海因西里·沃尔夫林艺术风格理论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3-4.
[3][瑞士]沃尔夫林.美术史的基本概念——后期艺术中的风格发展问题[M].潘耀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瑞士]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M].潘耀昌,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2.
[5]徐习文.论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学”[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8(6):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