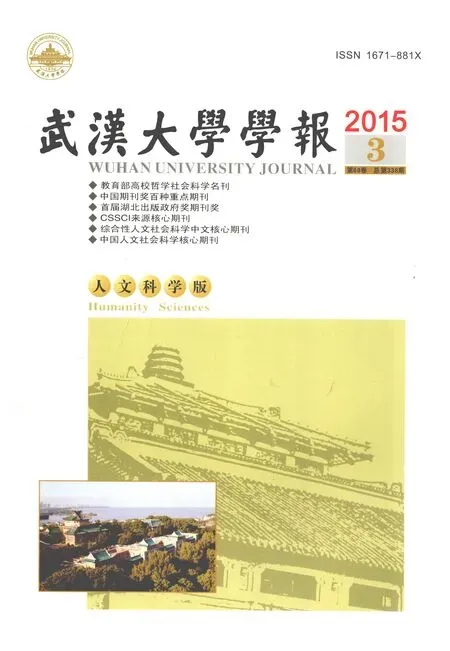钱穆“莎评”论
魏策策
钱穆“莎评”论
魏策策
摘要:钱穆的“抑莎”论无疑是带有偏见的,原因在于他以反驳莎士比亚来反对西方文明,他的“莎评”既有对莎士比亚的溢美之辞,也有对莎士比亚的贬低之语,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钱穆以中国文学的衡量标准质疑莎士比亚文学作为一流文学的合理性,同时他又承认莎士比亚是西方先进文明的典范,以莎士比亚为例指出了国人“慕西”的无知与危险,又对国人的“趋新”心态进行了匡正,钱穆以极强的民族主体意识抵抗西学东渐的潮流,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他的复古言论成为独语。从他的“莎评”个案中可以看出,作为尊古的代表,钱穆的困境在于无法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新的方向和意义。
关键词:钱穆; 莎士比亚; 尊古慕西
莎士比亚文学(下文简称“莎作”)在问世不到五百年的时间里,被不断阐释,高踞经典之巅,莎学研究已成为一门浩瀚的交叉性学科。人们对莎士比亚的赞赏与贬抑也使莎评者分成两个阵营:褒莎派和抑莎派(倒莎派)。海涅、歌德、屠格涅夫、黑格尔、梁实秋等人对莎士比亚赞佩有加,伏尔泰、托尔斯泰和钱穆等对莎士比亚的不屑与嘲讽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心理渊源。在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史中,评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写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经常被当作例证来支持论者的观点或充当论者反驳他人的工具,这使得莎士比亚的符号意义和社会意义被放大,已经超出了戏剧和诗文的文学界限。当莎士比亚被评说的时候,说者总有自己的用意,借莎士比亚来说事也并不鲜见。“莱辛用他来打击伏尔泰,赫德尔用他来召唤‘狂飙’,雨果用他来与古典主义决斗,柯尔律治用他来为浪漫主义张目,普希金用他来清算前任导师拜伦,而别林斯基用他来为现实主义提供范例”*赵毅衡:《“荒谬”的莎士比亚》,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5期,第125页。。毫无疑问,莎士比亚更像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符号,莎作自身意义的丰富性和阐释的开放性为后世种种合理的、荒谬的、矛盾的阐释提供了可能性。归根结底,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的伟大代表,莎作的精华就在于对人的书写,如杨慧林所言,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始终在书写一部“人”的历史,历史的底本正是文艺复兴的代表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以“性格为中心的创作,实质上反映着一种发现人类自身价值的新的社会意识”*杨慧林:《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莎士比亚》,载《文艺研究》1988第6期,第158~163页。。中国的莎学史,尤其在早期的莎士比亚接受和研究中,莎士比亚的“人”学思想往往不被其评论者重视,相反,因为莎士比亚的指涉性和涵盖性,在脱离具体的文本谈论莎士比亚其人其作时,“莎士比亚”往往被当作一个文化符号,呈现出某种有趣的变异,成为抽象的西方文化的代表;而近代中国受西方压迫,不得不学习西方,对西方文化既欢迎又惧怕的矛盾也困扰着一些研究者,
所以,他们对待莎士比亚的态度也往往不能用简单的赞成或反对一语定论*胡适、鲁迅等学人对莎士比亚的态度都比较矛盾。参见孟宪强:《胡适与莎士比亚——〈中国莎学简史〉自补遗》,载《四川戏剧》2000年第1期;顾钧:《胡适与莎士比亚戏剧》,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8日;魏策策:《被悬置的经典——鲁迅和莎学的独特交集》,载《戏剧艺术》2012年第3期。。钱穆的莎士比亚观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个案。钱穆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在中国传统史学和文化研究方面影响很大,由于钱穆坚守民族立场,被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一道成为文化复古的代表。
认为“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的学衡派以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眼光来“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乐黛云:《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汤一介编:《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页。,其所强调的“中正”之眼光,针对国人媚西而提,学衡派倡导保存、发扬中国文化,但因其主将梅光迪、吴宓等都是留洋过的新派文人,他们对西方文化并不陌生,对莎士比亚也有所涉猎。吴宓在1922年的《诗学总论》一文中,谈到诗人的想象力时就以《仲夏夜之梦》为例,写道:“昔柏拉图谓狂有四种,而诗人居其一。而莎士比亚亦谓疯人、情人、诗人,皆为想象力所充塞。实乃一而三,三而一者。诗人凝目呆视、忽天忽地,无中生有,造名赋形云云,皆可互证也”*吴安:《诗学总论》,载《学衡》1922年第9期。。吴宓强调莎士比亚的高超艺术,莎士比亚在文学中对理论形象的诠释在吴宓看来可谓至言,在文学艺术层面上,即使处于新文化对立方的保守派也对西方文化持肯定态度,但如果要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上升为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儒者多半反应激烈,拒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全盘替代。学衡派就是以复古来对抗“全盘西化”。钱穆出于对中国传统的维护,对西学也充满了敌意,他说,“民国二十年,余亦得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但余大体意见,则与学衡派较近。”*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载《中外杂志》1985年第6期,第16页。钱穆所言的接近,主要指他们在反对白话文运动上的立场一致,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和努力上的一致。有趣的是,钱穆在批判西学时,总是以莎士比亚作为西方的例证来说明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在大家都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历史时代,他成了一个抱残守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以莎翁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文明采取民族抵抗主义,成为“抑莎”的典型代表。关于钱穆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学界鲜有论及*可见的一篇论文为翁旻玥:《即彼显我——从钱穆对西方文学的解读看其文学观》,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一、 钱穆对中西文化的想象
钱穆曾回忆1937年游历西部时,和一位在慈恩寺种夹竹桃的老僧的对话,他诘问老僧为什么不种松柏,老僧回答:“夹竹桃,今年种,明年即有花可观”*钱穆:《中华民族历史精神》,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钱穆听后感慨万千:在新旧中西转折之时,世人短视,追逐桃李,厌弃苍松,怎么不令人心痛?或许这是钱穆的一个隐喻来源,他用“苍松老柏与娇桃艳李”*钱穆:《中国文化精神》,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8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0页。指涉中西文化的差别,中国文化温和仁厚,绵延悠久,仿佛厚重庄严的松柏,西方文化短暂肤浅,犹如热烈无常的桃李。钱穆也很重视中西文化的地理背景,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其地缘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根本无法相融,“我的生命是我的,你的生命是你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的,西洋文化是西洋的”*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第18页。,在他眼里,中西文化甚至处于对立地位,西方文化是游牧型商业文化,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和扩张性,有深刻的“工具感”,偏于天人对立,讲求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其文化特性表现为“征伐”和“侵略”,文化精神着重“富强动进”,是一种外倾型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农业型文化,主天人合一,自给自足的生态模式养成了中国文化“安分守己”、“和平为重”、“温良恭俭让”的文化特性*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牟言》中反复申明中西文化类型的差别,中国属农耕文化,安、足、静、定;西方属游牧商业文化,富、强、动、进。参见《中国文化史导论牟言》,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3~9页。。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是一种西方的“文化病”*钱穆:《文化学大义》,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70页。。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期,中国面对西方的帝国主义侵略,一没有抵抗力,二无法接纳融化,导致中国文化内部来不及调整,才造成了混乱局面*钱穆:《文化学大义》,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72~73页。。那么,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中国是否应该俯首称臣,积极学习?钱穆认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在钱穆看来,西方文化的入侵,是对中国文化的吞噬,是一场生死较量的悲喜剧,而中国文化超稳定结构的破坏也正是由于西力东渐的刺激,使国人盲目倒向西化,以为借西化就能崛起,他对此极其反对,认为跟着西方走根本不能渡过自身的文化危机,因为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自由主义的希腊精神、国家主义的罗马精神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141页。的冲突致使西方自身也岌岌可危。正因为钱穆在中国传统中浸润至深,愈加怜爱传统文化,他更主张文化自身的内部调适,他认为要阻止中国文化衰落,必须守住传统,抛弃传统则文化灭,历史绝,民族亡。他甚至假设中国若没有外力干预,等待中国内部生长出变革变化的因子,也能慢慢走上富强之路。
相对于钱穆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想象,对中西文化冲击的柔化处理不在少数,是历史的主流。梁启超曾预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乙丑本《饮冰室文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中西方文化融会在一起,创造出混血型的新文化,梁启超一切以“新”为宗,倡导中西交融,产生新文化,化育新国民,他的“迎娶”姿态展示了一种高昂、热烈、健康积极的文化自信。
胡适在《睡美人歌》中延续了梁启超以中西联姻喻中西融合的类比*《睡美人歌》(民国三年十二月即1914年12月作,民国四年三月十五日追记)中写道: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一朝西风起,穿帷侵玉臂。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昔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戾。画眉异深浅,出门受讪刺。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东市易宫衣,西市问新制。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对中西文化联姻的类比论述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下: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第五章《惊羡体验与西方形象——王韬眼中的西方论述中西联姻与现代性文化想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王桂妹:《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中国这“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吾故曰睡狮之喻不如睡美人之切也”*胡适:《藏晖室札记》第九卷,亚东图书馆1939年,第587~589页。,胡适将中国比作绝代美女,这招致了很多人的心理抵触,学者们从性别意识角度驳斥胡适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放弃与其全盘西化思想的致命之处,认为胡适将中国比作女性,委身于西方是对中国文化主体的自卑想象与放弃,从胡适设想的“遣群侍”和“问新制”看来,东方睡美人并非被动地被西方凌辱,而是知耻后勇,殷勤地向西方学习,作为喻体的中国与西方的联姻依赖于大批中国学人向西方文明取经的努力,这个学习必须付诸行动,取到“起死之神丹”*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4页。,才能度过生死危机,为“主君寿百岁”的中国梦就会实现。胡适这首诗,突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集体“借火”行动,从开始的“睡美人”到“主君”的用词,无意识中也发生了性别的隐匿,中国学习西方才能新生和强大的意味十分明显。
很显然,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夹缝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外乎欢迎、抵抗、不趋附不否定等,梁启超和胡适虽然都对中西融合持乐观态度,但他们都站在以西方文化回报中国文化的角度,试图挽救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以调和中西为目标,期望中国文化后来居上。梁启超称西方的民族主义为“民族帝国主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4~5页。,所以,对近代中国来说,最紧要的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步入现代民族国家序列,赶超西方民族国家。而钱穆时时不忘指出西方国家的帝国本性,他说,“最近一百年内,中国表现得处处不如人。在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狂潮正值高涨时代,几乎无以自存。”*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212页。可以看出,西方庞大“帝国”在与中国“国将不国”的对峙中,以极大的优势战胜了中国,国人西化,失去理性,势难阻挡。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本性,尤其是莎士比亚所属国的侵略性,钱穆进行了痛心疾首的呼告。钱穆认为西方暴力地入侵了中国“安足”的陶醉,而其本身是以“富强”、“侵略”为目的的,所以,中西文化根本不可相融。英国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对资本主义的武力征伐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钱穆对西方文明和英国文化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认清其侵略的野心和面目,不可动摇。接纳西方文化,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除此之外,钱穆还分析了英国文化的弊端。他认为,英国的现代文化可以从其历史演变而看出,如西敏寺代表曾经的“神权”,白金汉王宫代表近代专制的“王权”,国会代表现代“民权”,这就是西方文化“外倾性”的表征,是西方文化物质形象化的例证。在钱穆看来,西方的“外倾”劣于中国的“内倾”,西方文化“外倾”的表现是突进、扩张,倾向于求外在表现,即“文化精神之物质形象化”,这种定型的外化如建筑等,会使人感到压迫、被征服、灵性窒息、生机停滞*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182~185页。。这些感性的表述,正是钱穆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抵抗。钱穆对西方文化的器物、制度等反驳是为了剖析西方文化的侵略本质,担心中国文化在的西方政治殖民和经济欺压裹挟下沦陷。
二、 钱穆对莎士比亚的想象
由于中西文化观的不同,莎士比亚被中国知识分子赋予了不同的内涵,附加了不同的符号意义。钱穆虽然不熟悉西方文学和莎士比亚原作,但只要例举西方文学,就经常引莎士比亚为例指出西方文学的不足,反对西方文明取代中国传统的钱穆自然成了少有的“倒莎派”,相较于托尔斯泰、伏尔泰等人激愤的贬抑,钱穆的点评温和之极,总体来说,他对莎士比亚的态度有以下几个面相。
首先,否定莎士比亚。抓住莎士比亚身世不详的争议点,钱穆提出“欲求在中国文学史中找一莎士比亚,其作品绝出等类,而作者渺不可得,其事固不可能”*钱穆:《中国文学论丛》之《中国文学史概观》,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5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73页。。钱穆从根源上否定莎士比亚,既然莎士比亚的身世存疑,国人仰慕子虚乌有的莎士比亚就显得有点盲目。退一步说,“只因有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才成为莎士比亚。也是说,他乃以他的文学作品而成为一个文学家。因此说,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之意义价值都即表现在其文学里,亦可以说是表现在外。这犹如有了金字塔,才表现出埃及的古文化来。”*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164~165页。西方文学是人生和文学分离的典型,其不足就是单论作品,不管作者,与立德、立功、立言无关,钱穆认为这也是“文化精神之物质形象化”,是一种“外倾性”文学,失去了文学的纯粹性,不足取。中国学习西方文学,背离中国传统,就会有学术和人生分离的危险。钱穆认为作者是作品的灵魂,只有人文合一的艺术,能从作品中推寻作者的艺术才是不朽的。“凡中国文学最高作品,即是作者的一部生活史,也可以说是作者的一部心灵史”,“言与辞,皆以达此心”*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之《略论中国文学》,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259页。。中国文学历来讲究“知人论世”、“文心”、“载道”、“言志”,作者的意义和价值甚至高过作品。在钱穆看来,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文学与人生合一的文学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不朽的文学,“即作品与作家融凝为一”,“文与人一,其人亦在文中”*钱穆:《略论中国文学》,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267页。。因为,“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最高理想、最高艺术”*钱穆:《略论中国文学》,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260页。。显然,钱穆用中国文学观念衡量西方文学有一定偏颇,但他不顾自己言论的失衡,执拗地将对莎士比亚的批判导向对西方文学的批评,否定莎士比亚,是为了否定西方文学,这也是他的旨归所在。因为西方治学,可以不问其人,所以“西方人为学,非学为人,仅重知识信仰,而可离于人生。”“学术愈进步,而人生则益争益乱,永不能达于大同太平之一境”*钱穆:《晚学盲言》(上)之十二《人生之阴阳面》,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8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71页。。钱穆展示了以莎士比亚否定西学的用意,他的否定中潜藏着一个诘问:相比中国传统文学等而下之的西学,对人的内在生命没有提升作用,让文人沦为职业文人的工具化西学难道值得国人追捧吗?
其次,贬低莎士比亚。钱穆评论莎士比亚有破有立,莎士比亚并非国人应该学习的典范,那么国人应该师法什么?钱穆在树立文学样板的同时,极力贬低莎士比亚。他首先将莎士比亚和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归有光比较,“英国莎士比亚与我明代归有光同时代而略晚。归氏善写家庭生活,琐情细节,栩栩如生。至今读之,犹如活跃纸上,尚能深入人心。莎氏则身世不详,至今在英国人无定论。”*钱穆:《晚学盲言》(上)之三十五《操作与休闲》,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8册,第682页。在民国49年的一次演讲中,钱穆曾激赏归有光懂得文学真趣,获得古人真传*钱穆:《中国文学论丛》,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5册,第105页。,提出归有光的小品文,主要是为了反对五四时期文学的讨伐之气和大口号、大理论。他多次肯定归有光的为文、为学,号召今人要先学习古人的为人。拈出归有光,或许仅仅因为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近,至于莎剧和归有光的文字细部的比较,钱穆并没有深入,只是以归氏文字打动人心贬抑莎剧没有灵魂。钱穆贬低莎剧的第二步是指出莎剧缺乏教化功能,他举《秦香莲》和《西厢记》为正面例子,反衬莎剧不足,他说“中国戏剧仍富诗情,寓教育感化之意多。而西洋恋爱小说与戏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惟富刺激性,无教育感化之意义可言。”*钱穆:《中国文学论丛》,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5册,第161页。钱穆列出中国传统经典剧目与莎剧抗衡,对莎剧用离奇的故事吸引观众很不屑,认为这都是技巧层面的心机,应该否定。那么中国有没有比莎剧高明的戏剧?钱穆自然要给国人开出剧目,中国不必慕西,因为中国也有可与莎士比亚媲美的艺术,比如“昆曲仍尚流传,较之歌德与莎翁,影响深远,当犹过之。今日国人则唯歌德、莎翁是崇是慕”*钱穆:《晚学盲言》(上)之三十五《操作与休闲》,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8册,第682页。。至于昆曲比莎剧高明之处,钱穆没有详述,只是泛泛论及其剧情表演曲折,剧辞组织典雅等优点。在对莎士比亚的贬低中,钱穆不断流露出对国人崇洋媚外、自我菲薄的不满,指责民国以来中国学人一味慕西的浅薄。
第三,褒扬莎士比亚。钱穆对莎士比亚少有的赞美集中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一文中,文中他承认莎剧是经典,认为莎剧具有永恒性。“如英美诸邦,入其乡僻,亦复拼音不准确、吐语不规律者比比皆是。彼中亦自有高文典册,虽近在三四百年间,即如莎翁戏剧,英伦伧粗,岂尽能晓?”*钱穆:《中国文学论丛》,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5册,第10页。“故西方文学之取材虽具体就实,如读莎士比亚、易卜生之剧本,刻画人情,针砭时弊,何尝滞于偏隅,限于时地?反观中土,虽同尊传统,同尚雅正,取材力戒土俗,描写力求空灵,然人事之纤屑,心境之幽微,大至国家兴衰,小而日常悲欢,固无不纳于文字。则乌见中土文学之不见个性,不接人生乎?今使读者就莎士比亚、易卜生之戏剧而考其作者之身世,求见其生平,则卷帙虽繁,茫无痕迹。”*钱穆:《中国文学论丛》,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5册,第20页。这两段话,具有明显的所指性。第一段话反对“兴白话”,一方面是因为对古文的依恋,一方面有其士大夫的精英心理基础,举莎剧作为经典,把莎剧当作雅文学的典范,是为了反对废除汉字的思潮,激励当局普及教育,提高民众阅读能力,增强对中国文字的信心。第二段话先扬后抑,举莎剧的超时空与创新性,反衬中国文学的处处着实、亲附人生又超时空的无可比拟优势。
可以说,钱穆对莎士比亚的态度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他对莎士比亚、西方文化的否定、贬低都不够严谨。比如,为什么西方的建筑是其“文化精神之物质形象化”,而中国的不是呢?莎翁的身世的确存疑,但是关于莎氏的传记和年谱数不胜数,而他只抓住身世不详的说法不放,为什么昆曲比莎翁影响深远?这些观点,都需要有力的资料佐证,钱穆基本上只陈列观点,不深入论证。虽然屡屡言及莎士比亚,但浮光掠影,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莎士比亚成了一个工具和符号,成为他论述的由头。钱穆对莎士比亚否定和贬低的观点发表于《中国文学史概观》与《晚学盲言》中,对莎士比亚的正面褒扬集中在民国31年发表的《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中,时间相距30多年,那么,他早期对莎士比亚的褒扬又是出于什么原因?经历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后,钱穆认识到,中西文化交融的美景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文化侵略的现实,根子在于防止国人将“趋新之论转为扫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界就有以钱玄同、鲁迅等为代表的废除汉字呼声,表达接受世界文明的愿望。在钱穆看来,中国在经济政治上受到异族压迫,如果文字也被西方同化,等于成全了西方的文化侵略阴谋,无异于是中国传统的毁灭,将连绵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斩断。钱穆认为文字是中国文化的根,文字若消亡了,中国也就陷入危机,他将莎剧作为雅言的代表,雅言是保存传统的载体,而用雅言写作的作品是应该被珍视的。只要提高教育水平就可以让人人都能读懂雅文学,传统就会继续传续,所以他反对废除汉字,褒扬莎士比亚,并非出于真正心仪莎剧,而是借莎士比亚言中国之事。
20世纪80年代,钱穆到了晚年,台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政治上开始向西方靠拢、过渡,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又一次受到冲击,钱穆忧愤有加,他认为,失去本民族的传统,就失去了民族尊严,因为“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钱穆:《中国文学论丛》,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5册,第146页。,文学是文化的排头兵,所以,钱穆又开始攻击西学,否定莎士比亚,把中西文化和文学作比,目的是要宣扬中国文化的博雅精深,曝光西方文化虚构俗陋,以期警醒国人切勿媚外蔑己。
三、 作为符号的莎士比亚
钱穆对西方文化和莎士比亚的评论大多是断语式的粗泛而谈,只揭示本质区别,不做分析,缺乏基本的逻辑性。他将莎士比亚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进行中西比较,把中西文化作为完全不可调和的对立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和谐、内倾、厚重、不朽、灵性等优越性,恐惧中国文化的断裂,他守护传统文化的情感也让人动容,但他对西方文化弊端的言辞也显得有些随意和情绪化。钱穆用莎士比亚做例子,其实是用莎士比亚做工具反驳西方文学,他不断用西方文学概念偷换莎士比亚,于是,莎作与其人分离就是西方文学作者与作品分离,凡他论及莎士比亚的不足,那就是整个西方文学的不足。可以说,莎士比亚在钱穆的话语中就是西方文学的代名词,而钱穆批判西方文学是借批判莎士比亚来完成的。钱穆主观地设定了文学的高下之分:中国文学优于西方文学,归有光作品超过莎作的价值。为什么钱穆对莎士比亚有如此评价?为什么钱穆会武断地下结论?钱穆对莎士比亚到底是什么态度?
钱穆不通西文,傅斯年曾说钱穆有关西方欧美的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印永清:《百年家族——钱穆》,台北:立绪文化2002年,第137页。。《东方杂志》是东西文化大论战的重要阵地,也是以中国文化的守卫者著称的,钱穆的阅读选择具有心理认同基础。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抽象的名词在钱穆言论中出现不下十次,除偶尔提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之外,其他莎剧几乎没有被提及,可见,钱穆对莎翁的了解出于其名气,对莎剧故事有所耳闻,但深入的阅读不够,莎士比亚在他看来成了西方文明的化身,就算把莎士比亚置换成歌德、雨果等,也不影响他的基本论断,他的褒莎、贬莎、抑莎都指向西方文化,目的是要国人敝帚自珍、返本开新、创新国家民族文化。
钱穆一生与白话文运动有歧异,作为边缘学者的钱穆曾专赴小学任教*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页。1919年秋,钱穆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26岁。,在这之前白话文其实已经势不可挡,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共出了111种白话报*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载周策纵、唐德刚、李孝悌等:《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1年。。前期的铺垫使白话文很快占据主导地位,其普及速度也大大超过了胡适的预期,“说到中国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们在1917年开始(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预计需要10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20年。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这要感谢过去一千年来无数无名的白话作家!我们在一年稍多一点儿的时间里,激起了一些反对的意见,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打胜了这场仗……在我推行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从小所受古典的教育”*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1923年3月12日,载《致克利福德·韦莲司》,台北:联经出版社1999年,第142~143页。。虽然胡适肯定传统的力量,但新文化运动是在“进化论”的背景下进行的,文言文自然成了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而在保守派看来,复兴应该从旧传统中寻找资源,新文化运动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钱穆认为“民初以来,争务以白话诗,然多乏诗味。又其白话必慕效西化,亦非真白话”*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7页。。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他却未如林纾一样挺身攻击白话文运动,而选择了沉默,此后一生他孜孜在念对白话文的不满,在《晚学盲言》中多有感慨。钱穆一直主张返本开新,从传统中求变,为此,钱穆提倡开展一个“旧文学运动”。“中国要变,第一步该先变文学。文学变,人生亦就变。人生变,文化亦就变。我们想要来一个中国旧文化运动,莫如先来一个中国旧文学运动。不是要一一模仿旧文学,我们该多读旧文学,来放进我们的新文学里去。尽可写白话文,但切莫要先打倒文言文。今天我们不读古书、不信古文,专一要来创造新文学、创造新人生,这篇文章似乎不易作”*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钱穆认为,不能将西学与新学划等号,“新旧只是一名词分别,就时间言,今日之新明日己成旧。就空间言,彼此两地亦必互见为新”*《周濂溪通书随劄》,载《宋代理学三书随劄》第10册,第211页。。这个具有哲学意味的辨析固然有几分道理,却忽视了西学带来的冲击。钱穆潜意识里将莎士比亚看作西方先进文明的符号,他也附和主流声音对莎士比亚的推崇,所以,即使贬莎,也是在承认莎翁盛名的前提下进行的,在谈论新文化运动时,他对莎士比亚的态度以褒扬为主,对莎士比亚的肯定,暗藏着一个质问,那就是,既然国人都倾慕莎作,一心向西,那么西方人尊古、尊崇莎作,难道我们不应该学习吗?为什么对西方人珍视传统视而不见呢?“又如莎翁乐府,乃西方四百年前事,国人亦研赏不辍。何以在西方尽古尽旧都足珍,在中国求变求新始可贵。此恐特勇时风气,非有甚深妙理之根据”*钱穆:《中国文学论丛》之《漫谈新旧文学》,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5册,第238页。。这个观点和林纾如出一辙,对莎士比亚的矛盾态度,能看出钱穆因西方文化压迫的自卑而生出的自尊意识,借批判莎士比亚批判西方文学文化,借褒扬莎作批评中国人妄自菲薄、惟西方马首是瞻,告诫国人应该学习西方尊古的传统,学到西方文化带来的富强力量,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遗憾的是,钱穆的莎评尚未深入到莎作肌理,莎士比亚只是他言说自己思想的外衣,莎翁对“人”的书写未能为他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钱穆以为“今日我中国人之自救之道,实应新、旧知识兼采并用,相辅相成,始得有济。一面应在顺应世界新潮流,广受新世界知识以资对付;一面亦当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之成其为中国之根本基础,以其特有个性,反身求之,有一番自我之认识”*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序二》,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第7页。。钱穆也没有拒斥西方文化,或许文化融合必须经过“全盘外国化”的阶段*谭宇权:《胡适思想评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65页。。可以看出,无论支持或反对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时的知识分子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救民族,救文化,都是探寻现代中国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路径。鲁迅、胡适、钱穆都是思想界的旗帜性人物,他们在性格、文化选择和政治立场等都有差别,但都“放眼世界,关怀人类”*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面对中西文化的交汇,不管是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还是鲁迅的“拿来主义”这种以开放心态接纳西方的“向外吸收型知识分子”*陈漱渝:《同途殊归两巨人——胡适与鲁迅》,载周策纵、唐德刚、李孝悌等:《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1年,第44页。,或是钱穆这种文化守成者的反应,都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体意识,他们共同建构着超越时代的中国文化,探索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方向。
在这种探索中,“立人”、“立国”是绕不开的话题,莎士比亚作为西方的经典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莎士比亚的不同态度,源自其对西方文化取舍与精神取向的差异。“立人”是“立国”的根基,梁启超对“少年”的重视,鲁迅呼告“救救孩子”,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等都是“立人”呐喊,也是对寻找中国未来的努力。钱穆对传统文化塑造人的“立人”功能十分看重,他认为理想的国民必须对本国的历史文化有充分的了解,不能忘本。因为历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表现*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第12页。。国家民族的独立有待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个体只有对传统有了深厚的依恋,才不会盲目迷信西学。对理想国民的描绘,钱穆还是以传统儒家的“人人皆可为尧舜”勉励国人要“日新其德”,完成“立人”。
总体看来,钱穆逃避西学入侵的现实,他对西方文化的拒斥,没有跳脱士大夫阶层的局限,他对中国文化的拳拳之心,对西学的极力反抗,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生命体验的儒者对“他者”的防御机制,钱穆的复古和反西化言论变成独语,甚至成为西化派的讥讽对象,他的保守被视作感情用事的“我族中心观”*殷海光:《殷海光全集》第16卷,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494页。。因为,无论“立国”还是“立人”,作为尊古的代表,钱穆的困境在于无法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新的方向和意义。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3.012
基金项目:●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2013-IB-032)
●作者地址:孙霞,武汉理工大学汉语言学系;湖北 武汉 430063。Email:xmswhu@163.com。
陈国恩,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chenguoen503@126.com。
●责任编辑:何坤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