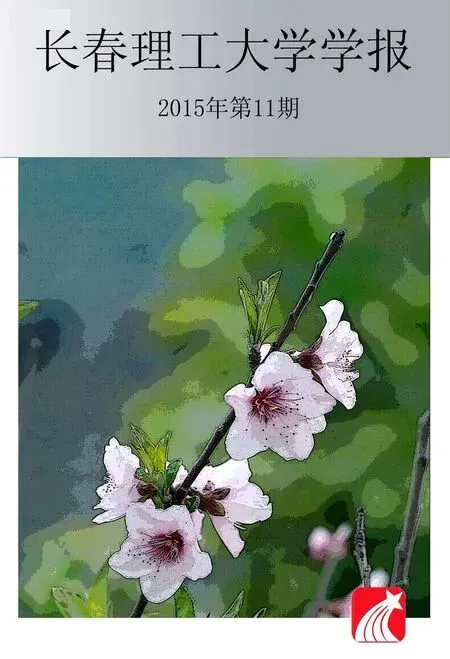性别身份的颠覆——论麦卡勒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代博君
(河南城建学院外语系,河南平顶山,467044)
一、引言
卡森·麦卡勒斯是美国20世纪杰出的女作家。她的作品给她带来了巨大荣誉,她被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美国小说家”[1],但同时,关于她离奇的生平和怪诞的创作风格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002年,一部根据麦卡勒斯人生故事改编的戏剧《卡森·麦卡勒斯:不确切的史实》在纽约百老汇首次上演,在剧中,麦卡勒斯被描绘成一个生理残疾、心理抑郁、酒精依赖、性别倒错的“恶梦般的人物形象”[2]。虽然该剧对麦卡勒斯形象的刻意扭曲和“不确切的史实”引起了评论界的抨击,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几乎在麦卡勒斯的每部作品中,都有双性同体的性别颠覆者,而这些畸形的人物形象既是麦卡勒斯真实的人生镜像,又承载着她对“孤独与精神隔绝”这一主题的传递和对二元制性别秩序的思考。
“双性同体(androgyny)”亦译为“雌雄同体”,是由希腊词语andro(男性)和gyn(女性)组成的。它有着深厚的神话意识和思维。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认为,人类最初是男女两性的合体,后来宙斯因为担心人类造反,便将原本圆满和谐的双性合体分成了男性和女性,从此被切割开后的单性人在情欲的驱使下,踏上了不停地寻找和追求各自的异性伴侣的道路,无法将旺盛的精力和热情对抗众神了。双性同体代表着人们对于两性平等和和谐理想的向往。后来“双性同体”一词被女性主义先锋、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引入到文学创作领域,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到,每个人内心都被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主宰,而作家创作最佳的状态则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融洽之时。”[3]随着女权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双性同体”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承认性别差异和性别意识的前提下,个体中两性特质和谐统一、完美互补,是解决性别二元对立和异化疏离的理想境界。
麦卡勒斯曾经说过,她作品中的每个故事都是她经历过或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她笔下的双性同体形象也恰恰是她自身的现实写照。和她笔下的青春期女孩米克和弗兰奇一样,麦卡勒斯在少女时代就比同龄的女孩高得多,13岁时就长到了5英尺8英寸,当其他女孩穿着漂亮的高跟鞋和长筒袜时,她却经常“穿着脏兮兮的网球鞋或女童子军的牛津布鞋”[4],犹如作品中的女主角们一样,她经常因为男孩子的装扮被周围的人取笑和排斥,米克和弗兰奇所处的尴尬处境正是她年少时的真实映射。成人后,麦卡勒斯就像艾米利亚一样喜欢男人装扮,“总穿着粗棉布裤子或男式长裤”[4],顶着一头短发,经常手着香烟余烬袅袅。而对于她的男性特质,麦卡勒斯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她甚至宣称,“我生来就是个男人”[4]。麦卡勒斯的双性特质使她成为了双性恋者,这使她陷入到无尽的精神崩溃和疾病折磨之中,麦卡勒斯塑造了很多和她一样徘徊在性别边缘的角色,这其中有男性,也有女性,有青少年,亦有成年人。而在每部她的主要作品中,她都塑造颠覆性别的女性形象。
二、妥协与回归的女性身份颠覆者
在麦卡勒斯笔下塑造了很多与典型的南方淑女形象相悖的女性角色,在她的主要作品中,无论是《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艾米利亚,《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奇,还是《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她们有着共同的特点:无论在性格和着装方面都留有男性特质的烙印。艾米利亚又黑又壮,“骨骼和肌肉长得都像个男人”[5]1,短头发,经常穿着长筒雨靴和工裤,性格粗暴古怪;弗兰奇身材高大,像男孩一样赤着腿,留着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头发,幻想和男孩一样投身战争,最喜欢的游戏是飞刀;米克身材瘦长,着装“第一眼看着像个小男孩”[6]31,有着男孩般沙哑的声音。这三个颠覆性别身份的女性在性别秩序的压力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划出了迥异的人生轨迹。
在这三个具有男性特质的女性中,米克和弗兰奇都属于处在性别意识和性别身份正在形成的青春期少女,处在孩童到成年人的过渡期,徘徊于个人评价与社会认同感之间。她们曾经坚定地拒绝社会规定的女性角色,米克目睹了周围的女性所要承担的既定的性别职责:母亲整日为家庭忙碌,家务缠身,而姐姐们则把精力都放在衣着打扮和八卦新闻上,这样庸俗的生活是米克非常排斥和鄙视的,她有伟大的梦想,她渴望成为一位发明家或音乐家。但是,她发现,由于贫困,她甚至连台收音机都无法拥有,而同时,她的哥哥却能接受教育,得到想要的东西,仅仅是因为性别的差异。米克愈发地厌恶自己的性别身份,正是自己的女性身份,使她的梦想连绽放的机会都没有,她竭力地掩盖自己的女性气质,像个男孩子一样穿着短裤,吸烟,说脏话,米克想从服饰和举止上使别人认为自己是“最男孩”[6]33的,从而逃避传统女性在南方社会中的命运,得到男性可以得到的所有东西。弗兰奇和米克有很多相同点,弗兰奇的身高也非常高,“身高五英尺五又四分之三英寸”[7]2,比同龄男孩还要高半头,穿着“蓝色运动短裤,一件汗衫,赤着脚。”[7]2
同米克一样,弗拉奇关心时政,渴望走出小镇,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女兵,但相对于米克来说,弗兰奇不像米克那样抗拒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想通过女性身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且她幻想“人们可以随时来来回回地从男孩变换为女孩,随他们怎么变,只要他们愿意。”[7]42虽然从表面上看,弗兰奇还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对她来说,性别选择就像选择着装一样,女孩子有着男孩的装扮和性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弗兰奇的男孩妆扮恰恰说明她在潜意识中想得到男性的权利。后来,弗兰奇发现自己的梦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甚至,她的假小子形象给她带来了接二连三的挫折,受到了周围的人的不解和排斥,这使她陷入到无比的孤单和惶恐之中。毫无疑问,米克和弗兰奇身上的男性特质挑战了传统文化中坚不可摧的性别观,她们的双性特质背离了父权制社会所规定的女性性别身份。米克和弗兰奇都陷入了一个尴尬和孤立的境地:她们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女性身份对她们梦想的限制,都想竭力地打破性别身份的枷锁,想借助男性特质到达理想自我的彼岸,但结果却给她们带来更多的挫败,她们受到了来自性别规范的斥责和惩罚,被排除在所有的性别群体之外,对于极其渴望认同感的青春期孩子来说,这种愈来愈强烈的孤独感和被社会团体抛弃的感觉是难以承受的,即使是斗争性更坚决的米克也无法无视他者的注视,完全躲避在“里屋”内。这两个曾经离经叛道的女孩最终在传统性别规范面前妥协了,她们不得不重新构建性别身份,回归到“正常的”社会性别角色的轨道中去,米克和弗兰奇都丢掉了男装,也丢掉了坚持,经过彻底的沐浴,和过去的自我道别,换上了裙装,并开始慢慢适应,成为社会所期望的女性形象。对于米克和弗兰奇来说,她们曾经极力地排斥社会强加给她们的性别角色,并进行了长时间艰苦的抗争,但最终在压力之下不得不选择妥协,回归到正常的女性形象,接受传统文化安排给她们的性别角色。
三、抗争与隔绝的女性身份颠覆者
对于女性的双性特质,弗洛伊德认为会有“三条可能的发展路线:一条引向性的禁欲或精神官能症;另一条指向性格的改变,形成男性情结;最后一条指向正常的女性气质。”[8]如果说米克和弗兰奇最终选择了第三条道路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艾米利亚属于第二种。艾米利亚是成年版的米克和弗兰奇,也是麦卡勒斯笔下男性特质最浓厚、与社会性别规范斗争最彻底的女性形象,经历了成长蜕变后的艾米利亚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性别观,尽管小镇上的人“对她产生一种复杂的感情,这里面混杂着恼怒、可笑的痒痒的感觉以及深深的无名的悲哀”[5]68,但靠父亲的遗产和自己的努力,艾米利亚不仅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在男权社会中生存了下来,还成了方圆几英里最富有的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相对成熟的性别观使艾米利亚比米克和弗兰奇在自我性别构建的过程中赢得更多的主动权,更能抵御传统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制度内人们的注视。
艾米利亚的男性气质的形成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她由她性格孤僻的父亲一手带大,这就使艾米利亚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法从其他女性身上获得“正常的”女性特质,她的父亲是她习得性别气质唯一的参照物和榜样。而另一方面艾米利亚父亲的孤僻性格无形中也为她的男性气质的增长提供了一个不受外界规范影响、相对封闭的环境,艾米利亚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可以安心地退回到“里屋”,完成男性特质的建构。此外,她父亲的遗产也为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济保障,使她不用为了生存问题来迎合社会的规范,撕裂自己的双性特质。而她从父亲那里承袭过来的男性特质进一步为她在男权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无疑又反过来促进了她的男性特质,使艾米利亚一度在潜意识里将自己等同于男性。艾米利亚会医术,没有什么病可以难得了她,但除了一种病——妇女病,每当面对这种病时,艾米利亚会表现得像男性一样窘迫和手足无措。事实上,尽管艾米利亚在竭力压制和隐藏自己的女性气质,但她骨子里温柔细腻的一面还是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来,她的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连最小的物件也有其固定的位置”[5]26,在给患儿治疗时,为了不让他们受罪害怕,她会让孩子吃饱喝足,给孩子喂自制的甜酒。镇上的人希望通过婚姻来洗去艾米利亚的男性气质,但是艾米利亚拒绝接受社会规范中的妻子角色,即生育繁衍的角色,最终,马文也“无法把自己心爱的新娘带上床”[5]25,马文的离开代表了艾米利亚男性气质的暂时胜利。而在和李蒙的关系中,艾米利亚和李蒙的关系恰好是传统婚姻关系的倒置:艾米利亚高大强壮,有经济能力,而李蒙恰恰相反,爱哭、软弱、没有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李蒙残疾的身体符合艾米利亚无性生育的理想。艾米利亚对李蒙宠到无可附加的地步,此外,艾米利亚收起了经常穿的工裤,换上了“以前逢到星期天、参加葬礼、出庭诉讼才穿的红裙子”[5]39,试图借助一直藏匿起来的女性气质来吸引李蒙,但讽刺的是,李蒙竟然被前来复仇、充满男性特质的马文所吸引,并在关键时刻帮助马文击败了艾米利亚。艾米利亚的失败宣告了男权体制的胜利。受到惩罚的艾米利亚并没有选择回归到正常的性别角色,她迅速地衰竭下来,头发花白,“身上发达的肌肉也萎缩下去”[5]47,并将自己封闭在门窗都钉上板子的屋子里,残喘着用最后一丝力气进行抗争。
四、结语
麦卡勒斯是一个具有双性特质的女作家,她既具有女性的智慧细腻,又具有男性的独立果敢,但双性特质使她陷入到无尽的困顿和绝望,她将自己的孤独和困惑都融入到作品中,在她的小说中,她刻画了很多和她一样的性别颠覆者,而几乎每部作品的女主角都是具有双性特质的“异类”,处于青春期的米克和弗兰奇渴望通过男性特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被朋友和家人斥责和孤立,同时,她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离开那个封闭的小镇,梦想破灭,在经历了多次的挣扎和挫折之后,她们最终选择了妥协,无奈地接受了曾经坚决抗拒的性别规范。不同于处于性别动摇阶段的米克和弗兰奇,成年的艾米利亚是青春期之后颠覆性别身份的“幸存者”,依靠男性特质,艾米利亚赢得了财富、力量和权威,在婚姻上,艾米利亚用“无性生育”的方式对抗传统的性别角色,但为了挽回李蒙的感情,她又不得不借助于之前一直努力隐匿的女性气质,但最终在男性权威的声讨下,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以一种接近死亡的隔绝状态延续着残生。在父权统治下的社会中,企图颠覆性别身份的女性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要么像米克和弗兰奇一样放弃梦想,放弃对性别传统的对抗,撕裂双性特质,顺从既
定的性别规范;要么像艾米利亚一样遭受更严厉的惩罚,被社会边缘化,逃脱不了衰竭和孤独的悲剧命运。在男权社会中,女权主义者所设想的两性角色相互认同、和谐统一的双性同体的终极理想不可能实现,双性同体的完整性注定要陷入到被割裂的极度痛楚之中。
[1]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M].青岛出版社,1999:58.
[2]林斌.卡森·麦卡勒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小说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06).
[3]弗吉尼亚·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论小说与小说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56.
[4]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卡森·麦卡勒斯传[M].冯晓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5]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M].李文俊,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6]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M].陈笑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7]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M].周玉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8]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M].长春出版社,2004:75.